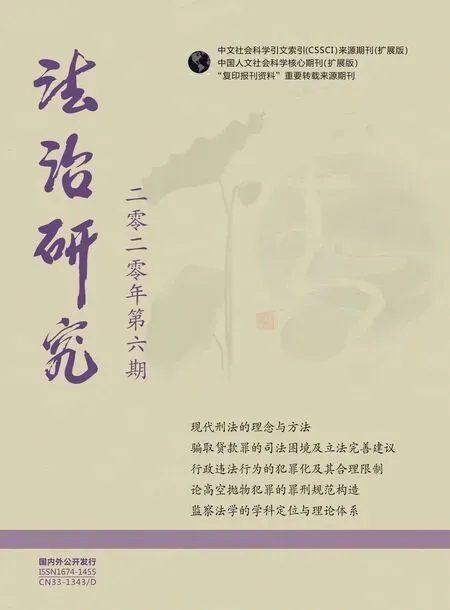高空抛物犯罪案件司法证明之难题
韩 旭
日前,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该修正案第1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我国《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触犯该条可能构成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毒罪,虽然手段各不相同,但都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因此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兜底,此次刑法修正增加的高空抛物行为即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畴,第2款属于危险犯,第3款属于结果犯,通过增列“高空抛物”罪状,使“高空抛物”行为“入刑”。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前,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为已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先例,这为未来司法操作提供了经验。虽然笔者不能给“高空”下一个准确定义,但是依据经验常识,高空主要是指高层楼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城市天桥上、公园和其他公共旅游区域内的摩天轮、索道、树上和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内和风景名胜区的山顶、崖顶等。与“高空抛物”相对的是“低空抛物”,即在地面上或者一层建筑内进行抛物。由于潜在的被害人具有可预防性和不典型性特征,社会危害不大,刑法并未将其犯罪化。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6至2018年3年,全国法院审结的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案件有1200多件,这1200多件中有近三成导致了人身损害;受理的刑事案件31件,这31件里有五成多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①参见《高空坠物何时休?案件多发危害安全,法律制度须加强》,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9/10-21/8984664.shtml。被抛下来的物品更是花样百出,从灭火器、酒瓶到菜刀。比起高空坠物,显然,高空抛物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危险性更高。从近年来高空抛物行为发生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分别是“施工型”②例如,2014年7月4日14时许,被告人夏某某、杨某某在阜新市北方花园小区(老区)41号楼楼顶做防水施工,夏某某将一个装有垃圾的编制丝袋让杨某某从41号楼楼顶东侧扔到地面上,夏某某负责瞭望楼下是否有人,经过瞭望确认没人后,杨某某将装有垃圾的编制袋从41号楼东侧楼顶扔下,将路过的贾某某砸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阜新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尸体检验鉴定,贾某某的死亡原因是生前被钝性外力作用于头部,造成颅骨骨折,蛛网膜下腔大面积出血,小脑、脑干出血死亡。“酗酒型”③例如,2020年1月17日20时许,被告人酒后从永胜县永北镇梨园小区5栋9楼904室自家阳台往楼下有大量人员聚集的广场抛掷一个不锈钢盆,随后又从阳台往楼下抛掷一个铸铁火炉,该火炉砸中在广场上开会的受害人熊某,致使熊某受伤。经永胜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熊某本次损伤程度评定为轻伤二级。“泄愤型”④例如,2018年12月22日下午6时许,杨某兴因退还租房押金问题,与其租住的中山市民众镇六百六路149号“天添住宿”房东王某秋产生纠纷。随后,杨某兴为泄私愤,站在上述出租屋四楼阳台处,不顾他人安危,将啤酒瓶、床板、菜刀等物品扔至楼下道路,导致群众围观以及交通阻断。民警到场劝解后,杨某兴继续往楼下扔床垫、餐具等物品,并以自杀、扔煤气罐等方式与民警对峙。直至当晚11时许,民警破门而入将杨某兴抓获。“报复型”⑤例如,2011年9月21日零时许,被告人李某喝酒后回到其住处深圳市罗湖区金湖路长龙花园1栋并去到楼顶天台。被告人因心情不佳和对小区管理处工作方式不满,便多次将天台上摆放的装有泥土的花盆等物品砸向楼下供行人和车辆出入的公共通道,导致停放在通道上的被害人孙某的粤B×××××汽车、被害人王某的粤B×××××汽车以及被害人刘某的1栋601D外墙热水器排烟管、抽烟机排气管被损坏。。尽管类型各不相同,但都给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此次刑法修正将其“入刑”,加大了对该类行为的惩治力度,有利于保障公众“头顶上的安全”。但立法上的善良美意需要通过司法实践来实现。其中,司法证明上的困难是惩治该类犯罪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对司法证明困难的缘起、高空抛物犯罪案件的司法证明的特点和证明困难的纾解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修正后刑法的顺利实施提供参考。
一、高空抛物犯罪案件司法证明难之缘起
对于高空抛物行为,此前虽有刑事追究的案例,但大多以民事责任进行追究,责任方式主要是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通过后,其实是将民事侵权行为“犯罪化”。此类行为原则上由刑法进行规制,但是如果没有损害结果发生或者穷尽调查手段无法查找到具体的行为人,可能仍会依据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近日,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法院判决一起高空抛物案,判决整栋楼的所有住户每户补偿被害人3000元人民币。4年前,一个不满1岁的婴儿被一个从天而降的健身铁球砸中,不幸身亡。后经警方调查和多方寻找行为人未果,受害人家人便将整栋楼的住户起诉至法院,要求承担民事补偿责任。⑥参见《天降铁球,女婴被砸身亡,凶手4年未找到,法院这样判》,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16742530_115362,2020年9月8日访问。由于民事证明规则与刑事证明规则存在较大差别,决定了刑事责任证明上的困难。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同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民法典》第1254条第1款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无论是《侵权责任法》还是即将实施的《民法典》均规定“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其实是一种行为推定,是在侵权人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不得已的制度安排,主要在于平衡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利益,是价值判断的结果。在民事案件中允许进行过错推定和行为推定,但是在刑事案件中不允许进行推定,只有在极少数案件中且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推定。民事案件可以实行“责任共担”,但是刑事案件必须查明并确定到具体的责任人,“罪责刑”统一乃刑法基本原则,无责即无罪和无刑。两者比较,可以发现,刑事责任的追究尽管有公安机关立案查明,但由于不能进行推定,证明的难度明显大于民事责任。这是刑法修正后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证明标准不同
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中的证明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或者“优势证明”即可,而刑事案件定罪的证明标准应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程度。例如,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6条第2款规定:“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认为有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移送起诉和定罪亦需达到相同的标准。较高的证明标准无疑增加了证明的难度,要求公安机关在立案后侦查中应收集足够数量和较高质量的证据,以满足“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正是证明标准的差异,决定了著名的“辛普森案”审理中,辛普森刑事上被裁决无罪,民事上却被判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
由于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的不同,决定了高空抛物犯罪案件证明上的困难。从近年来高空抛物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看,“侦查难”是一个突出问题。⑦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权衡与博弈: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路径抉择——兼评〈侵权责任法〉第87条》,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12期。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难即包含证明难问题,刑法修正后,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对公安机关确实是一个巨大挑战。“在刑法理论上,对于故意抛物致人损害的行为可以认定为间接故意犯罪,而对于过失抛物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也可以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因此,公安机关应负有进行侦查以确定加害人的义务。而且在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情形下,受害人在遭受损害后(尤其是遭受严重的人身损害后)往往难以查明具体的行为人,完全由受害人负担查明具体行为人的义务,可能导致多数案件中都无法查明具体的行为人。”⑧王利明:《论高楼抛物致人损害责任的完善》,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1期。
二、高空抛物犯罪案件司法证明的特点
高空抛物犯罪隐蔽性强、危害严重,给司法证明带来难题。此类犯罪案件在司法证明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直接证据较少,高度依赖被追诉人口供
该类犯罪案件证明危害结果的间接证据较多,例如现场勘验笔录、伤情鉴定报告、财产损失价格评估报告、物证等,但是锁定行为人的直接证据较少。除非行为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或者有监控录像、目击证人、指纹证据等证据。即使被害人未死亡,其陈述未必能够指向“飞来横祸”的制造者。仅仅根据抛掷物品种类也难以判断直接责任人,毕竟“物证”属于“哑巴证据”,不会开口说话,在证据分类中属于间接证据。从既往成功定罪的高空抛物案例看,几乎都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可以说,此类犯罪案件高度依赖被追诉人口供。尤其在缺乏监控设备和目击证人的场合,没有被追诉人口供,几乎无法定案。“高空抛物侵权行为最大的特点在于无法查清真正的行为人,而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致人损害侵权行为中,作为责任主体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一般是清楚的。”⑨王成、鲁智勇:《高空抛物侵权行为探究》,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2期。在高楼抛物致人损害的情形下,通常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行为人,只能确定可能的侵权行为人的范围。高楼抛物致人损害侵权的最大特点并不在于抛掷物本身,而在于难以发现真正的侵权行为人。⑩同注⑧。
对该类案件,特别要加强证据的审查判断。不排除责任人将抛物责任推给未成年人,以此逃避刑事责任的承担。此时需要审查该未成年人是否在场和抛掷该物的可能性,判断二者陈述是否一致?是否有串供可能?如果具备鉴定条件,可对抛掷物上的指纹进行鉴定,以缩小排查范围,锁定责任人。
(二)非接触型犯罪,可资利用的证据有限
高空抛物犯罪案件属于非接触型案件,通过被害人辨认或者DNA鉴定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传统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案件中证明手段将难以利用。“从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看,高空抛物侵权行为的难题在于信息问题,即该行为的可观测性不足。”[11]同注⑨。除非是“施工型”高空抛物行为,否则难有目击证人。即便是发生在居家中的抛物行为有目击证人,因与抛物人系亲属关系,难以客观真实作证。这就决定了该类案件可资利用的证据有限。证据是证明的手段,在证据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司法证明的难题将无法解决。
但是,本条款至少对从事服务或贸易类的企业具有一定指导意义。这些企业可以在过渡期截止前,通过不可抗力条款或其他合同终止条款,终止合同,然后继续催收相关款项。对于以货币进行的收款行为,如果符合上述“继续收款例外”3个要件,则不会存在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但目前伊朗外汇储备十分紧缺,能源领域付款很可能通过实物(石油)进行,这就有必要向美国政府进行澄清和通报,获得美国政府认可。这样做既可避免“以原油方式收款的行为”被误认为“从伊朗获取石油的行为”而受到美国制裁,也方便其他公司为这些原油的获取提供正常的销售、运输、银行、保险等流转渠道。
虽然可资利用的证据有限,但是仍可通过证据信息挖掘和司法推理实现证明目标。高空抛物案件通常都有“物”这一证据,可以通过“物”是特定物还是种类物的辨析来判断其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如果能够认定“物”系特定物,便可按图索骥找到抛物的地点乃至抛物人。同时,可以通过抛掷物的线路、角度和撞击力度等进行推理,判断其来自何处。在此类案件中,依据经验、常识进行的推理不可缺少,与其他案件相比,推理在司法证明中应得到充分运用。
(三)调查取证量大,需要可能加害人的积极配合
与故意杀人、抢劫等重大案件相比,高空抛物犯罪案件隐匿性强、调查取证工作更艰巨繁重。在城市高楼林立、动辄几百上千人口的楼宇中,仅排查、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工作量就非常巨大。据媒体披露,在有些地方高空抛物事件发生后,为了查找到行为人,公安机关甚至对有可能实施抛物行为的业主进行DNA检测,人数动辄几十人、上百人。[12]参见《物业敦促高空抛物者投案自首,否则对全楼住户进行DNA检测》,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10191651_124689,2020年8月25日访问;《高空抛物,DNA比对18户26人,查出18楼扔酒瓶肇事者!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监护人咋赔偿?》,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13431815_658588,2020年8月25日访问。虽然刑事案件不能实行行为推定规则,但是可能的加害人具有配合调查的义务,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供其在案发时不在现场、不具备作案机会的证据。对可能的加害人提供的证据,公安机关需要进行逐一核实,以确定真假。对抛掷物的来源及其所有者、使用者也要认真核查,查明其出自何处。同时,对人身伤害情况和财物损失价值还需要进行鉴定和估价。如果有目击证人和监控录像,需要进行询问和调取视听资料。这一切决定了该类案件仅靠人力取证比较困难,需要引入高清摄像装置、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支持。
虽然不敢说家庭和谐稳定、品行一贯良好的人不会发生抛物行为,但是品行恶劣、酗酒或者家庭关系不和的人更容易发生抛物行为。为此,公安机关还需要对可能加害人的品行、家庭状况和是否有酗酒习惯进行调查,在施工型抛物行为中,公安机关还需要了解可能加害人家是否正在进行装修、加固等施工。这些工作加大了调查取证量,侦办此类案件的效率必然降低。
上述活动,需要耗费公安机关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只有全面取证才可能使案件的证明达到较高的标准,撤案或者不起诉、宣告无罪的几率才会降低。由于高空抛物犯罪案件多发生在人员密集的区域,一旦发生人员伤亡的事件,必然引起周边群众的关注,该类案件社会影响巨大。如果公安机关不能及时破案,将行为人绳之以法,自然会引发公众的质疑,降低执法公信力,也达不到一般预防的目的。因此,尽管该类案件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工作较为艰巨、繁琐,仍不能掉以轻心或者予以放弃,仍应“有案必立”“有案必查”。对此,《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规定:“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该款规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主要解决被害人举证能力不足、公安等机关怠于调查的问题。
(四)如果被追诉人辩称非本人所为必然加大证明的难度
即便公安机关可以确定抛掷物来自何处,很多时候被追诉人会辩称系家中未成年子女所为或者因大风吹落,例如花盆掉落砸伤他人。当被追诉人提出此类辩称时,公安机关证明的难度更大。除了需要询问未成年子女外,还需要查询气象记录和固定当天的风力情况。必要时,还需进行侦查实验,以验证同等级别的风力是否可以吹落相同重量、摆放位置一样的花盆。
三、高空抛物犯罪案件证明困难的纾解
刑法修正的良法美意若要得以实现,需要司法实务上证明难题的缓解。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缓解司法证明上的困难。
(一)高空抛物犯罪案件尽可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基于高空抛物犯罪案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高度依赖性,获取自愿、真实的口供无疑是化解证明难题的首要选择。如果加害人拒绝承认抛物事实,必将加大证明的难度。为此,可考虑扩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该类案件中的适用范围,鼓励更多的加害人自愿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考虑到高空抛物案件长期以来是作为民事侵权处理,立法上作为刑事案件予以追究时间不长,公众有一个心理接受和逐渐适应的过程,因此在修正后刑法适用伊始,从宽幅度可适当大一些,通过刑罚上的优惠,鼓励更多的人予以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条规定:“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认定其悔罪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为了缓解证明上的困难和被害人一方得到及时赔偿,检察机关可通过相对不起诉,法院可通过判处缓刑、免刑促使加害人认罪认罚并积极主动赔偿,以获得较大的量刑折扣。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适用范围的扩大,尤要警惕该类案件中“顶包”行为的发生。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所做的抛物行为的陈述,应仔细审查,慎重对待。防止成年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相互串通,未成年子女“代人受过”现象的发生。对于家庭成员之间作证的证词,应认真审查,其证明力有限,不能给予过高评价。
即便是可能的加害人认罪认罚的案件,法官如果内心存疑,对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仍可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刑诉法规定的“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只是确立了审理的一般原则,在法官对证据存疑的例外情况下,仍可进行举证、质证等实质化审理,以提升法院对此类案件发现和纠正错误的能力。
对于被追诉人不认罪认罚的,仍要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审理,相关人证应当出庭作证,抛掷物等证据应当出示并经辩护方质证,尤其要重视视听资料、侦查实验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在指控犯罪中的运用,证据之间应能够相互印证,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二)对居民小区和城市马路实行监控录像全覆盖
由于能够证明行为主体实施犯罪的直接证据较少,这是司法证明的难题所在。可考虑通过强化公安等机关、物业管理服务企业进行监控的责任来缓解证明上的困难。考虑到人力监控的局限性,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公安等机关应当在城市主要道路安装监控设备,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应在所服务的区域加装监控设备。这不仅是其职责所在,而且是预防和减少包括高空抛物犯罪在内的犯罪案件发生的重要举措。一旦发生高空抛物行为,即可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发现抛掷物来自何处,甚至可以直接锁定抛掷人,以此纾解证明上的难题。高空抛物行为“入刑”后,增设监控录像,扩大监控范围,势在必行。虽然城市治理的成本会提高,但是有利于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短期内也许会加大社会治理的投入,但从长远看当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由于监控录像的全覆盖,对潜在的加害人具有威慑效应,由此可能会减少高空抛物犯罪案件的发案数量,这意味着侦查破案司法投入的降低。因此,从长远看,遏制高空抛物犯罪的社会治理成本未必更高。
(三)强调可能加害人的配合义务,注重“不在犯罪现场”事项的证明
虽然刑事案件不能实行行为推定,但是其性质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决定了刑事案件比民事案件更加注重可能加害人的配合义务,这是司法证明所必需。加害人在现场,有条件和机会实施抛物行为,这是首先需要证明的事项。为了洗脱嫌疑,由可能的加害人证明自己不在现场确有必要。同时,为防止无辜的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发挥邻里之间相互守望的优势,积极检举揭发加害人,以避免因证明不能而导致的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这一不得已的选择出现。《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可见,“不在犯罪现场”证据属于辩方应当开示的内容,也构成高空抛物犯罪案件中需要证明的事项。这就要求可能的加害人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在案发时正在单位上班、在超市购物、休假、在外地等证据,以排除其作案的可能性。民事证据规则刑事化也是缓解证明难题的主要举措,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1款和《侵权责任法》第87条都强调可能加害人的配合义务。高空抛物“入刑”后,民事证据规则应当成为刑事证明的基本遵循。规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补偿责任,既可以对受害者进行救济和补助,也可让业主通过相互监督、积极举证查找出真正的侵权人,并使其承担法律责任。[13]参见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解读——人格权编·侵权责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33页。我国正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诚信社会,因此可能加害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对于不如实提供证据,甚至制造伪证的人,应当列入失信“黑名单”进行惩戒,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人力资源进行分析证明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高空抛物犯罪案件的证明也越来越重视该技术在司法证明中作用的发挥。通过大数据排查和寻找行为人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早起晨练的人员、送子女上学的成年人和上下班人员的轨迹,进而分析排除可能的作案人。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工智能被广泛用来预测犯罪、侦查犯罪和预防犯罪,所使用的技术包括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枪支检测、DNA和数字化的法医分析等。围绕刑事案件的“七何”要素(何人、何种动机和目的、何时、何地、何种手段、何种犯罪行为、何种危害后果),构建由“案件线索来源、锁定犯罪嫌疑人及到案经过、查证犯罪事实、证据充实性及排他性说明、罪前罪后表现及其他量刑情节、涉嫌罪名”等六个环节组成的证据链体系(又称证据模型)。[14]参见熊秋红:《人工智能在刑事证明中的应用》,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3期。“新加坡环境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通过人员蹲守获取高空抛物的证据,效率低下。从2011年起,环境局用高清摄像机和动态数据处理软件监控高楼抛物者,由于掌握了确凿证据,处罚了一大批肇事者,高空抛物现象明显减少。”[15]李贤华、喻伦泰:《域外关于高空抛物、坠物的法律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19年11月22日。
同时,也可通过物业服务公司的保洁人员和网格员获得相关信息,发现和掌握每户人家的构成、家庭成员间的和谐程度、家庭成员的品行和生活习惯等,这些人员的证言对于查明案情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及时予以收集。“在刑法适用层面,高空抛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行为人主观方面通常系故意。”[16]《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99521.html,2020年8月19日访问。
(五)主观故意的证明可运用间接证据进行
高空抛物犯罪多由间接故意构成,对抛物人主观过错的证明可运用间接证据进行,除非其主动承认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例如,可根据抛物地点、时间、抛掷物的种类、楼层的高度等进行综合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第5条规定:“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准确判断行为性质,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运用间接证据进行证明可以缓解证明上的困难,可以正确认定行为人主观罪过的性质。运用间接证据进行证明时,除了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证明方向一致,各证据之间没有矛盾或者矛盾得到合理解释或排除外,还应注意运用经验法则进行推论,以保证心证的合理性。[17]参见龙宗智:《刑事印证证明新探》,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尤其是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主观上通常以故意构成,这就需要证明行为方式要与放火、决水、爆炸等方法具有相当性,即结合行为地点、被抛物属性、抛物高度等因素判断行为是否具有高度危险;其次,必须要足以危害到公共安全,通常要具备抛物较多和楼下人员密集两个条件。[18]参见李斌:《高空抛物定性不能一概而论》,载《检察日报》2020年8月25日。2019年1月江苏昆山赵某将家中一串玻璃珠饰品扔出窗外,致楼下两辆轿车的挡风玻璃和天窗受损。检察官根据案发时间系凌晨,小区居民多已休息,极少有居民在楼下活动;案发地点系固定车位而非道路、人行道等居民密集活动场所;行为人抛物时具有较大随意性,非针对具体的人或财物等诸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认定行为人并非具有针对不特定人和物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主观故意,而是以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19]《江苏昆山:这起“抛物”构成寻衅滋事罪》,云南网,http://fazhi.yunnan.cn/system/2020/08/25/030911698.shtml,2020年8月25日访问。判断是否能够“危害公共安全”需要办案人员亲临现场,仅靠查阅现场勘验笔录无法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心证”也不准确。首先,需要判断并确定抛物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的区域位置和面积。要根据抛物高度、抛物距离、物品特征、地面硬度、天气情况和是否有遮挡物等因素综合评判。评判危险时可采用案卷审查、现场感受和周围走访三种方法。案卷审查是核查行为人抛物时周围是否有行人驻足围观,行人驻足围观的区域一般可认定为安全区域;现场感受是指司法官站在抛物现场,基于一般人的感觉去评判,如果站在某处想象物品落下而不感到危险,一般也可以认定该处是安全区域;周围走访是指通过对物业人员、小区居民的询问来帮助司法官进行判断。其次,判断抛物行为在上述区域内是否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秉持客观的、一般人的立场,根据区域位置、封闭程度、功能特征、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来综合判定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假如某区域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地,根本不可能有人来到该区域,那么就不可能造成任何人身和财物损害,但如果该区域于一周前被改建成篮球场,随时会有人来打篮球,那抛物行为就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了。[20]参见吴春妹、程涛、蒋希茜:《亲临现场亲眼看,个案还需个案评》,载《检察日报》2020年8月25日。
四、民事赔偿事项何以证明
高空抛物行为“入刑”后,并不意味着行为人无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此,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既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也可以在刑事案件证据不足,公安机关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情况下,由受害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无论是附带民事诉讼还是纯粹的民事诉讼,理应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处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6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第2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据此规定,被害人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可以将该物业服务企业列为共同被告人。物业服务企业承担适当的安全保障责任具有正当性基础:一是物业服务企业收取了业主的物业费;二是物业服务企业熟悉小区情况,在管理和安全保障方面具有优势;三是可以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履行服务职责,保障出入小区人员的安全,同时配合公安等部门的调查和检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1条之规定,应当由被害人一方对物业服务企业“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承担举证责任,物业服务企业可以举反正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来请求免责。在一些情况下,物业服务企业即便已经采取了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高空抛物事件仍有可能发生。就如同物业服务企业已经采取了安全保护措施,盗窃、抢劫事件仍不可避免一样,不能因为发生了高空抛物事件就一概由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赔偿责任。例如,在“施工型”高空抛物事件中,尽管物业服务企业已经告知施工人“禁止高空抛物”,但施工人为了省力方便,将垃圾袋抛下地面。此时,可以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免责。这里需要对《民法典》中的“必要的”程度进行界定,何谓“必要的”,语焉不详。无论如何,“必要的”不等于“完全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之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被害人一方需要对上述损失予以证明,但是考虑到其举证能力的有限性,尤其是被害人可能受伤甚至残疾正在医院治疗,要求被害人举证证明且需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无疑是“雪上加霜”。《民法典》起草者正是考虑到此问题,才规定公安等机关应当及时调查,查明责任人。为了帮助被害人解决民事赔偿司法证明的难题,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履行诉讼关照义务,对于侦查期间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应当允许被害人复印,并作为提起民事诉讼的证据。毕竟,公安机关取证手段、资源丰富,非被害人所能比拟。由于刑事追诉的严肃性以及证据调查的国家职权特性,人证笔录较之普通民事诉讼中获取的当事人陈述或证言,往往较少受到当事人及证人诉讼立场的影响,更为客观真实。因此,在证据资源有限的民事诉讼中,舍弃这类证据材料,不利于发现客观真实。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刑事诉讼笔录证据,这是民事诉讼实务,甚至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所认可的主导性实践。[21]参见龙宗智:《刑民交叉案件中的事实认定与证据使用》,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如前所述,确定具体的责任人是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难点,由于有关机关在查找具体行为人等方面具有各种优势(如技术优势),强化有关机关在查询具体行为人方面的职责,有利于及时发现真正行为人,从而有效解决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归责难题。[22]参见王利明:《论高楼抛物致人损害责任的完善》,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1期。如果能够确定具体的行为人,则适用一般的民事侵权规则,特殊侵权规则自无适用的余地。这也是高空抛物行为“入刑”后需要注意的问题。在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场合,相对于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安全保障责任系次要责任。以笔者之见,70%与30%比例分担较为合理。
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公安司法人员应当转变观念,注重证据规则的运用。在刑事案件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允许被害人一方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救济。由于民事侵权证明标准低于有罪标准,被害人一方可能获得赔偿或者补偿。不能将加害人或者可能加害人赔偿、补偿被害人损失作为有罪的证据,无论是判决还是调解。对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9条规定:“有关支付、提出或承诺支付因伤害而引起的医药、住院或类似费用的证据,不得采纳来证明对该伤害负有责任。”[23][美]罗纳德·J·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页。相对于刑事追责,被害人更关注民事赔偿问题。为了督促加害人或者可能的加害人履行赔偿责任,公安司法人员不应将民事赔偿作为刑事追责的定案证据。但若刑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可将赔偿和谅解情况作为从宽幅度的裁量依据。
关于物业服务企业的赔偿责任,《民法典》1254条第2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标准不明确,决定了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从上述规定看,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证明责任,以证明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如每天由保安进行巡逻、在广告宣传橱窗发布“严禁高空抛物告示”、在小区安装监控设备等是否属于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还是要求每家每户在窗户外都安装编制密集的铁丝栅栏,防止高空抛物行为发生才属于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无疑,今后只要发生了高空抛物行为,物业服务企业都要承担证明责任,对“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进行证明。
需要注意的是,被害人一方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只能是赔偿之诉,而非补偿之诉,其只能要求加害人和未尽到必要安全保障义务的物业服务企业赔偿,而不能要求可能的加害人补偿。如果公安机关将高空抛物案件立案,被害人不得另行提起补偿之诉。可能加害人基于免责考量可以举证证明真正加害人。但是,如果因证据不足或取证不能刑事案件未被立案或者已经立案后撤销案件、作不起诉处理,被害人一方可以提起补偿之诉。补偿之诉中,可能的加害人承担谁是真正加害人的证明责任。“基于相邻关系的熟悉程度、建筑位置高度的相近性等原因,在补偿之诉进行中对真正加害人的确定的证明责任理应分配给已被起诉的可能加害人。”[24]吴岳翔:《建筑物高空抛物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诉讼证明问题研究 ——从程序法角度审视〈侵权责任法〉第87 条的有关规定》,载《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4期。
五、“危及公共安全”的证明
既然刑法将“高空抛物”行为类型化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类手段,那么构成本罪的前提是足以或者已经“危及公共安全”。是否“危及公共安全”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判断活动,需要根据地面是否为公共区域、路面过往行人的疏密、财物的分布及其价值、物品的质量、抛掷的高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此犯罪构成要件,作为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检察机关应当予以证明,公安机关也应收集这方面的证据材料。其实,早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10月21日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该“意见”指出高空抛物行为“损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极易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引发社会矛盾纠纷”,并对高空抛物行为的定罪量刑做出了相应规定:“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准确判断行为性质,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在尚未造成实害的场合,以危险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须对“足以危及公共安全”要件进行证明和说明。通常侦查机关应当收集抛物场所为公共场所、过往人员密集或者系上下班高峰期、往来人员较多以及抛掷物具有致人伤亡危险、多次抛物、一次抛物数量较多等证据。对抛掷物能否足以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无须进行专门的证明,但应符合经验法则。一片树叶、一件衣服和一只空塑料瓶就不能产生危害后果,但是一个啤酒瓶、一块石头或者一把刀具就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甚至死亡。这是基本的生活常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具有显著性。所以,抛掷物作为该类犯罪重要的物证提取后对其能否危及公共安全可以运用司法认知予以确定,无须进行司法证明。应当肯定的是,《刑法》第114条中的危害公共安全,并不是指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实害,如果案发当时高层建筑或者城市过街天桥下没有行人,就没有足以“侵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只是足以“威胁”人的生命、身体,即仅存在抽象的危险,而不能评价为刑法第114条的“危害公共安全”。[25]参见张明楷:《高空抛物案的刑法学分析》,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3期。只要能够证明抛掷物足以对不特定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侵害即可。在证明手段上,除了证人证言外,还可运用监控录像、卫星遥感图像进行证明。例如,2019年11月27日20时许,被告人徐起为发泄情绪,从其居住的重庆市渝北区X幢X层出发,到该幢X层取走灭火箱中的一支灭火器,后从该幢顶楼天台处将灭火器抛掷楼下,致使小区道路旁的绿化带内树枝被砸断。12月2日20时许,被告人徐起为发泄情绪,再次从其居住的X幢X层灭火箱中取走2支灭火器,到该幢顶楼天台处先后将灭火器抛掷楼下,又将顶楼放置的陶土花盆投掷楼下。其抛掷的一支灭火器砸到小区道路后喷洒出灭火粉末,另一只灭火器坠入小区道路旁绿化草丛,花盆坠入小区休闲区域。12月3日,被告人徐起被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事实。重庆市渝北区公安机关以徐起涉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又如,泉州市洛江区万安某小区19号楼一19岁女子林某,从15楼向地下抛掷生活垃圾,里面既有快递包装纸、外卖盒,还有吃剩的厨余垃圾,如钉螺壳等等。该女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上述两个案例中,虽然抛物行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因抛物地点是居民区,过往行人较多,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系“危险犯”,公安机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符合基本的法理。
采用高空抛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人在主观心态上大多是一种放任,例如不管路面是否有行人,随意抛掷足以致人伤亡的物品。但在结果犯中也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对于主观罪过的证明,除非加害人如实供述,否则只能运用推定规则,通过对基础事实的证明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推定事实的存在与否,以此缓解主观罪过证明的困难。
是否会“危及公共安全”将是被追诉人及其律师辩护的一个重点,辩方可能会举证证明不至于“危及公共安全”,比如深夜抛物、行人稀少、非公共场所乃至所抛物品不会损及他人的生命、健康等。由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权能受限,对其证明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只要能够制造一个“合理怀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