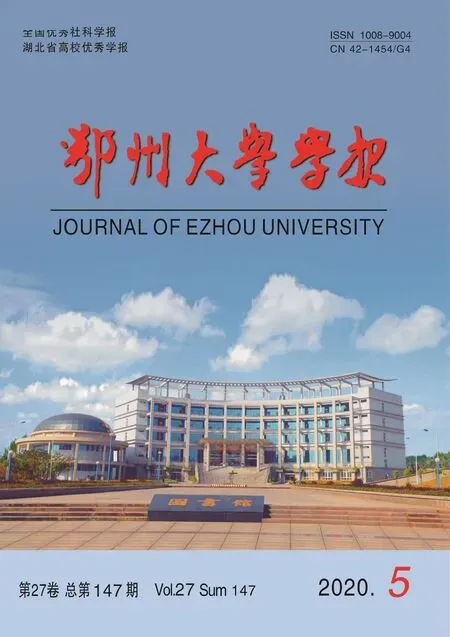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王 颖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925)
莫言出生于1955年的山东,家庭贫困,小学五年级便辍学在家,随后参加了农业劳动,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文学有较为广泛的涉猎。1976年初莫言正式加入了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战士,并在训练期间,勤奋学习,多次尝试文学创作活动,先后发表了具有乡土特色的《透明萝卜》《白棉花》等作品。80年代后期,莫言的农村小说陆续出版,《食草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等文学作品得到了我国文学创作领域的广泛关注,《红高粱》甚至成为我国农村文学的不朽之作。该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远销海内外,并为莫言成为我国首位获得国际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奠定了基础。莫言的小说塑造了诸多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充满了人性的光芒,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理想与愿望,对黑暗阶级的厌恶与讽刺。其中的女性角色是很难用我国传统的道德规范来衡量的,但人物身上的丑与美、恶与善、喜与悲却给读者以诸多的思量与考究。莫言小说中的女性角色用她们独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寻找着她们所希冀的快乐,用坚韧与聪慧锻造着人性的光芒。《檀香刑》中孙媚娘、《白棉花》中方碧玉、《丰乳肥臀》中上官春等人物,都是莫言精神思想的代表,都有超越时代的人性光辉。诵读莫言的小说,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莫言对中国女性的颂扬与关怀。
一、历史文化中的女性形象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女性的地位始终低于男性,始终要遭受封建文化及思想的迫害,进而沦为被奴役、被支配的境地。她们也想追求自由,也想掌握命运,然而她们别无选择,只能任封建礼教、封建思想摆布着自己的生活,统治自己的思想,甚至甘愿沦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以此换得世俗的认可与理解。在以往的社会生态中,中国女性受男人的制约,顺从父亲的旨意,即便丈夫去世后,她们也难以得到真正的自由,家庭的权力与义务将由儿子来掌管和继承,因此在夫权与父权所主宰的社会体系下,女人的生活除了顺从,便是接受,难以看到任何的精神希望。女性是社会的牺牲品,是阶级的附属品,同时也是时代的受害者。虽然我国历史中曾出现过很多女权运动,她们在牺牲自我、完成大我的过程中,寻得自由、寻得救赎,却不断以失败而告终。莫言用文学创作的手段及方法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鲜活灵动且充满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体现女性的自主与坚毅,使其冲破束缚中国女性几千年的封建枷锁得到解放,使其拥有真正的人权意识、自由意识及思想精神。莫言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温顺、聪慧,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所具备的美德,但在新思想的熏陶下,女性角色不断挣脱男人的压迫与束缚,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独立见解与看法。《红高粱》中的戴凤莲形象便颇具争议,她拥有自己的性格特点、价值观念、理想诉求及对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执着,她不甘心将青春与年华交付给自己所不爱的人,不愿将自己的肉体作为筹码,换取“还算可以”的彩礼。她用绝食的方式,反抗着这段婚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他要打破封建思想对自己的控制,要从囚禁女性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中逃离出来,她要觉醒,要让别人知道,她是自己的,不是父亲的,更不是男人的。她想要的,终究会实现,不想有的,也万不能强加给他,她不顾封建思想与世俗观念,毅然决然地选择与余占鳌在一起,并生下了两人的爱情果实——豆官。虽然戴凤莲遭受了封建礼俗的折磨与压迫,然而她的行为却成为反抗阶级、反抗封建的象征,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是她不愿低头,不愿受压迫的完美体现。莫言在小说结尾部分,通过戴凤莲的口吻说出了所有女性共有的心声:“妇道、贞操是什么,我一个女人家是不会明白的,也不愿明白,我只知道这些不会给我带来什么,不会让我幸福。哈哈,作为一个女人,喜欢男人怎么了,追求美好又怎么了,毕竟身体是我的,我有权力做我想做的事。”虽然戴凤莲的价值观念具有明显的偏激性、开放性,然而却是对我国封建社会、封建礼教的有力反击,是对几千年的道德枷锁的全面质疑。在《白棉花》中,方碧玉是智勇双全、有才有德的女性角色,她能够在苦难中寻得快乐,能在权力与欲望中寻得解脱,能够放下女人的矜持,参与男人的事务,追求自己的理想。她像戴凤莲一样,不愿受封建包办婚姻的迫害,敢于与心爱的男人幽会,将自己的所有、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李志高。虽然在反抗封建礼教的方式上,莫言都选择“贞操题材”,给人以循环往复之感。然而在文学创作上,贞操是封建礼教给女性带来最大痛苦的压迫,是制约并压迫女性几千年的枷锁,唯有从“贞操”的层面入手,才能更全面,更有效地体现出女性追求自主、追求人性以及追求自由的意识。鲁迅曾在《狂人日记》自序中指出,人是能战胜所有坏东西的生物,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坚毅,然而社会礼教是难以打破的,因为社会礼教代表的不是一个个体,不是一个阶层,而是整个群体,整个社会,要想彻底地打破,需要有莫大的勇气与毅力。因此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打破封建礼教、封建思想的过程中,也体现出女性角色不畏世俗的精神特点及人格魅力。
二、女性角色的复杂性
莫言笔下的女性角色大多都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普通女子,他们思想开放、有不屈的抗争精神,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性格特征、思想特征及人性特征。巴尔扎特曾指出,小说的灵魂是角色,而角色的灵魂则是“难以捉摸”。这种复杂性体现在角色塑造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角色的行为方式、说话方式及思维方式中,凸显在角色应对困难、面对挑战、迎击敌人的抉择中。他们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有人说,在莫言的小说中的女性身上看到了中国男人的影子,看到了诸多不屈的精神、敢于拼搏的理想以及不畏强权、敢于追求自我的理念,这与我国传统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艺术史上,都很少看到。[1]诚然文学创作是艺术加工的过程,是创作者从生活经验、人生体验中获得思想升华的过程。然而在角色塑造上,作者拥有极大的灵活性与创作性,能够将不同角色的性格特征、身份特征及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创作出外表与性格、本性与思想完全相反的人物形象。莫言便是如此,他的角色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拥有特定的现实基础,并在后续的创作与探索中,不断充实角色、完善角色,使其成为一个全新的角色,以此使角色在构造的过程中,拥有新的特征及特点。在丁玲的回忆录中,也曾有过这样的阐述:“我的人物有时很复杂,因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个集合,是所有人物特征及特质相互融合的结果”。莫言的小说也不例外,在《红高粱》中,戴凤莲超越历史文化的思想理念、个性解放思想,是她所在的时代所不具有的,是很少出现的女性角色。更像是我国古代先贤在阶级反抗中所呈现的精神品质,譬如荆轲等。因此某些人说在莫言的女性角色中看到男人的痕迹,便不足为怪。然而在角色塑造的过程中,莫言根据封建时代,我国女性角色所共有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及家庭背景,使这些女性角色的价值观、思想底蕴更加可信,更加真实。譬如戴凤莲以反抗的阶级斗争方式,便是以追求爱情的过程为载体的,她没有伟大的阶级抱负,也没有争夺财富权利的野心,她要的只是幸福,一个女人应有的幸福。因此,她的反抗精神、抗争意识都集中在她为美满爱情的追求上。而其所不具备的思想观念与精神理念则通过角色的家庭背景、人生历程来实现的,以此使角色更加令人信服、更加真实。因此,莫言小说中的女性角色的复杂性具体体现在人物塑造与价值观确立上。然而在表达方式与性格塑造上,女性角色的复杂性又表现在人物的动作与行为、心理与细节的矛盾上。莫言笔下的戴凤莲虽然拥有普通女性所不具备的抗争意识与反抗精神,能够为爱情奋不顾身,然而在具体的行动中,却表现出显著的顺从与隐忍。尤其在传统封建家庭的影响下,她要做的就是三从四德,不能因为自己的欲望而败坏门风,影响家族声誉。因此,在是否决定与余占鳌幽会时,她是那样的犹犹豫豫。而在被家族长老发现后,被世俗耻笑后,她不仅表现出无畏与坚韧,更表现出女人应有的柔弱与迷惘。而在真正与家族长老对峙时,戴凤莲脸上虽然呈现出果断、勇敢的神情,但在细节描写以及动作描写上,能够发现她的内心依旧是脆弱的、怯弱的以及慌乱的。因此可以说性格矛盾是莫言女性角色复杂性的另一表征。
三、女性角色中的精神意蕴
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倾注了对中华传统女性的赞美与尊重,虽然先生塑造了诸多的男性英雄角色,迫使女性角色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在小说主题意蕴的营造上,依旧拥有着难以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些女性角色不仅丰富了小说社会的多样性,更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使小说的主题更加深刻、更加鲜明,更符合作者的文学创作理念。因此,为凸显女性角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莫言通过塑造软弱无能的角色来衬托他们、烘托他们高贵的品格及坚毅的精神。譬如在《丰乳肥臀》中,最富盛名的铁匠世家是在女人的炭炉上、掌钳中不断走向兴盛的。而在小说《白棉花》中,作者借马成功的口吻说出了这样的话:“很多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往往都在说明一件事,女人心中只要燃烧起爱情之火,她就永远都不会消亡,而男人到时只会像皮球一般瘫软下来,毫无用处。”[2]李志高和方碧玉在棉花垛中被抓住后,李志高唯唯诺诺,缺少了男人本应具有的刚强与坚毅,而方碧玉却只能为了维护爱情,忍受来自世俗的羞辱与谩骂。从精神意蕴的角度出发,莫言的小说并不是在单纯地歌颂女人、赞扬女人,而是以男女平等、女性解放、歌颂自由为主题的,他是在借助女性角色的口吻,宣扬一种正确的、和谐的价值理念。然而在凸显并深化这种精神底蕴时,莫言并没有将视角局限在弱化男权的层面上,而是从女性角色的命运发展、社会道德的体系,呈现出女性角色在摆脱封建束缚后的社会价值、时代价值及精神价值。纵观莫言所有的文学小说,能够发现女性角色往往被放在次要层面,然而这些女性角色所洋溢的精神气息、文化品质及价值理念却牵动着所有读者的心,成为中华民族人性的亮点。
四、女性角色的情感之美
女性魅力是莫言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莫言展现女性角色特质、实现与读者情感共鸣的主要渠道。莫言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拥有较为鲜明的特征与魅力,《红高粱》中戴凤莲与《白棉花》中方碧玉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我国的传统道德,是为世人所不耻的行为,是难以得到广泛认同的道德错误。因此,要使读者真正认同角色的行为,并尊重角色的选择,则需要塑造出具有人格魅力与思想魅力的女性形象,使角色与读者构建情感共鸣的基础上,提升读者的代入感与移情感。[3]莫言在文学小说创作中,主要采用两种策略,即移情与共鸣,通过描写女性角色悲惨的遭遇、凄凉的身世,激发读者的同情感,随后以“难以实现的理想愿望”“不公正的指责”“遭受暴力恐吓”等情节,深化读者对女性角色的同情感。然而构筑同情感并非代表读者会支持角色并喜欢上这个人物,此时,莫言先生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人物情感的表达上,通过情感表达,加固角色与读者间的情感纽带。譬如《白棉花》中方碧玉遭受毒打时,内心的痛苦,《狗道》中主人公被街坊嘲笑时的窘迫感等。但与当代文学创作不同,莫言将人物正经历的情感,通过细节描写完美地呈现出来,使细节成为作者表达情感的媒介与平台,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能用自身经历与人生经验来感受这种情感,深化读者对角色的认同感。
莫言还利用感官描写、主客观描写,将女性角色的感受全部展现出来,即在客观叙述的基础上,增添角色的心理描写,如方碧玉被毒打时,感觉“身上仿佛裂开了几道沟壑,使得冰冷的空气在身体里不断地穿梭,游弋。而直到那家伙停下来,方碧玉才感觉舒服很多。”在原型理论与符号学研究中,情感展现与细节描写,能够激发读者的生活经验,使读者眼前呈现出特定的画面,进而深化对场景及角色的理解,使读者更加认同角色的价值观念及理想信念。而这也有助于读者接受作者的创作理念及小说主题,不至于产生任何的抵触心理。此外,为更全面地构筑女性角色的人格魅力,提升小说作品的吸引力,作者将女性角色的形体美、感官美、性格美刻画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在阅读小说作品时,能够深深地被女性角色的外在特征及内在品质所吸引,进而真正地喜欢上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更理解角色的价值观念及命运抉择。
五、女性角色的文化载体
莫言的文学作品主要以封建社会为背景,将封建社会所独有的道德观念、思想理念及行为规范,描写得淋漓尽致,使其成为阻碍女性角色实现人生目标、价值追求的重要阻碍,从而在丰富小说思想性的同时,提升了角色的思想内涵及人文理念。在小说《生死疲劳》中,二姨太虽然属于权贵阶级,然而却依旧受封建礼教的束缚,难以从根本上实现自己对爱情的追求,无法摆脱封建社会的枷锁,达到个性解放的目的。然而在情节架构及场景描写中,二姨太却表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独有的品德与魅力,她优雅而大方,对长辈孝顺,对晚辈慈爱,对生活任劳任怨,进而帮助作者将我国传统女性所有的美德与品质都展现出来。因此,莫言的文化理念是现实主义而非浪漫主义的,他忠实地还原了传统文化的美好及封建社会的残酷,并使其成为角色塑造与主题构建的依据,提升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与文化性。然而在文化表现与意蕴展示上,作者并非通过特定的事件或礼俗将其叙述给读者,而是将其融入到女性角色的命运发展中,跟随女性角色的行为印迹,渗透出大量的文化元素,使其服务于角色,服务于故事,进而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特定年代、特定地区的风土人情、文化礼教亦或者封建思想。因此在莫言先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是文化表达与展示的载体,是读者感知文化、了解文化的主要媒介。同时也是作者展示封建主义局限性、落后性的关键媒介。唯有如此,莫言小说的层次才更加清晰、逻辑更加鲜明。但从整体角度来分析,小说中的时代背景、文化气息,又不仅仅局限于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描写,有时是以场景渲染、环境铺垫的形式出现,其目的也是服务剧情和主题,丰富小说的文化内涵,使其更加自然生动。譬如在《白狗秋千架》中,主角在返乡后再次看到了传统的酒神祭,心中难免感慨万千,进而有了青梅竹马式的叹息与回忆。在这里,文化描写深深地融入到小说场景之中,并作为故事推进的“激励事件”,帮助作者引出女主角,推动情节发展。
莫言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既表现出传统女性所独有的贤惠、善良,更表现出对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及包办婚姻的反抗精神,表现出女性独立自主、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思想理念与价值观念,体现出莫言对女性的关怀与歌颂,同时也体现出作者深邃的思想哲理与人文关怀。通过对《丰乳肥臀》《红高粱》《白棉花》等女性形象的赏析与探究,能够发现莫言对女性角色的尊重,对女性追求幸福生活的支持与关怀,感受到作者独有的人文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