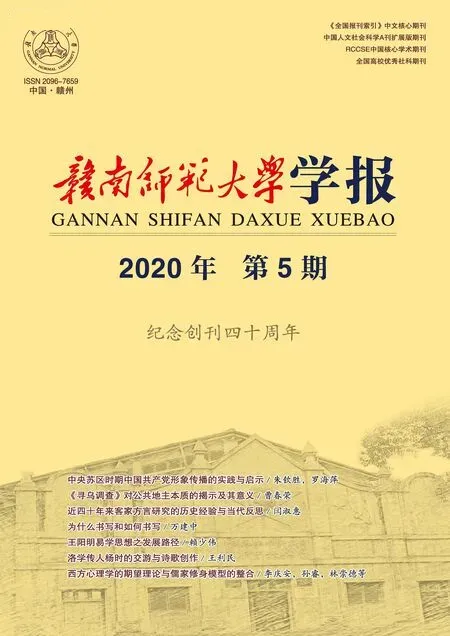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反思*
闫淑惠
(赣南师范大学 客家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客家方言的记述可以追溯到清代黄钊的《石窟一征》,该书采用训诂学方法对辑录的400个客家方言词语进行考证。现代学术意义上客家研究肇始之作《客家研究导论》,用国际音标记录客家方音,并与《广韵》系统作比较;20世纪50年代,董同龢先生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因调查详细、记录准确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客家方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后,随着方言学学科理论的发展、调查手段与方法的改进,客家方言研究方兴未艾。詹伯慧、崔荣昌、刘纶鑫、兰玉英、温昌衍等对广东、四川、江西等客家方言地域研究状况作过系统论述(1)这方面的研究见:詹伯慧.广东客家方言研究之我见[J].学术研究,1997(7):75-77;刘纶鑫,田志军.客赣方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115-120;温昌衍.梅州客家方言调查研究概况[J].嘉应学院学报,2010,28(7):88-93;崔荣昌,李锡梅.四川境内的“老湖广话”[J].方言,1986(3):188-197;兰玉英,闵卫东.四川客家方言研究综述[J].龙岩学院学报,2012,30(6):20-25等。。这些对于客家方言研究的再研究,展现了客家方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丰富了客家方言研究的成果。近年来,随着国家方言调查工作的深入,出版行业的蓬勃发展,学术期刊客家方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基本数据来源。在“期刊”检索项下,以“客家方言”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1978-2019年,共检索到文献894篇。研究过程中,通过人工核查,删除与研究主题弱的相关文献及重复文献,整理包括作者、篇名、发表年度、作者单位、主要内容等信息建立近年来学术期刊客家方言研究基本数据库。通过对客家方言研究的再研究,展示我国近年来客家方言研究的研究成果,为当代客家方言、客家文化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的主要成果
以中国知网 (CNKI) 论文数据库作为检索库,采用论文高级搜索,选取“期刊”,以“客家方言”为检索项“主题”的检索词,匹配:模糊,时间为“1978-2019”,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894篇,其中1980-1989年28篇,1990-1999年146篇,2000-2009年261篇,2010-2019年459篇。需要说明的是,采用同样的检索方式1978-1979年未检索到相关文献。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客家方言语音研究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也是语言变异当中最稳定的因素。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呈现出以语音研究为主,兼向其他领域拓展的发展态势。客家方言语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单点语音描写。研究者深入客家地区,对客家方言进行田野调查与记录,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1980年代,蔡筝、谭厚福、饶长溶、李玉、黄雪贞等分别对江西营前、江西寻乌、福建长汀、广西大鹏、成都龙潭寺等客家方言点进行语音调查。1990年代,客家方言语音调查扩大到广东饶平、新丰、电白、中山翠亨,广西贺县、沙田、陆川、容县,福建武平、四川西昌黄联乡等地。2000年代,广西石门、四保、博白、宾阳,广东英德、湖南资兴、四川西昌黄联关等地客家方言调查相继展开;潘家懿、马重奇、陈晓锦等还对台湾、泰国曼谷等地的客家方言语音进行了调查。2010年代林伦伦、陈晓锦、万波、庄初升等重点对丰顺、广州、大埔、兴宁、五华广东客家方言语音进行调查与整理。二是多点语音对比研究。梁猷刚比较了客家方言梅县话与广东话,论述梅县话语音特点。[1]李如龙比较了长汀县内5个点客家方言语音的异同。[2]邓晓华调查了11个方言点,收集词条三千条以上,各个点都做了同音字表,注重方言内部异质的共时描写和横向比较,从空间的差异比较看闽西客家话历时的连贯变化。[3]詹伯慧记录了饶平上饶客家方言的声韵调和常用方言词,并与梅县话进行比较。[4]潘家懿比较了海陆丰客家话与台湾“海陆客”的共性特点和内部差异。[5]严修鸿等运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论证了粤东北三县见组字在细音条件下软腭音龈腭化不平衡的现象及原因。[6]兰玉英等认为四川客家方言与闽粤赣客家方言在古全浊声母字逢今塞音、塞擦音读为送气清音,古次浊上声与古全浊上声字部分读阴平上类似。[7]三是客家方言语音规律研究。林宝卿、李谱英、邓玉荣、谢留文等论述闽西、广西、江西等地区客家方言声母、连读变调等语音规律。黄雪贞验证了客家方言古入声字逢清声母今读阴入,逢全浊声母今读阳入的特有规律。同时指出,没有入声的客家方言,如长汀,古入声字逢清声母今归阳平,逢全浊声母今归阳去。[8]项梦冰、严修鸿、谢留文等从具体韵部古今比较入手,探讨客家方言语音演变的总体规律。刘纶鑫对客赣方言的声调系统进行综述,认为古声母的清浊、声母的送气与否、古韵类属性影响客赣方言声调分化,客赣方言均存在浊上部分归阴平,次浊随清流现象。[9]万波等通过讨论客、赣方言中全浊声母今读不送气塞音塞擦音的性质,再次验证中古全浊声母今读清塞音、塞擦音时送气,才是客、赣方言的本质特征。[10]汪高文对客赣交界地带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平、入声调值的匹配格局进行分析,发现客家方言“阴平-阳平:阴入-阳入”的调值高低呈现“高-低:低-高”型的反向匹配,例外很少,认为这是客家方言内部一致性很强的一项音节语调特征。[11]温昌衍描写江西石城客家话的小称变调和强化变调,认为后者来自前者,其成因是小称变调功能的提取及凸显对象的转移,同时指出台湾东势客家话的35变调,既有小称变调的性质,又有强化变调的性质。[12]
(二)客家方言词汇研究
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词汇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客家方言词汇调查。饶长溶、熊金丰、林立芳、周日建、陈亦良等分别对长汀、永定、马坝、惠东、贺县、瑞金、梅县的客家方言词汇进行收录、整理与研究。李作南、李惠昌对客家方言词汇、客家方言口语古词语进行整体考察。谢留文通过亲自和他人20处调查,认为“嘴”来源是中古蟹摄合口三等知母或章母去声,与客家方言关系密切的赣语却没有这种现象,并指出,也许这可以作为客家方言区别于赣语乃至其他南方方言的一个重要的词汇特征。[13]温昌衍、魏宇文、张秀珍、黄革对龙川、五华、贺州、平果等地的客家方言词汇进行调查对比,认为它们既具有客家方言词汇的共性,也有其特色。这些研究再次印证客家方言次方言间系统细致的比较能够丰富客家方言词汇系统、体现客家方言的整体语言面貌。[14]二是客家方言词汇系统差异研究。谢留文、林清书较早注意到客家方言与其他方言相比特殊的词汇。邓晓华认为客方言词汇与中原汉祖语文化具有同质性,也有异质性,客方言存在地域差异。[15]张振兴认为西部闽语与客家方言有不少一致之处;南部闽语跟粤语、客家方言都有明显的关系。[16]练春招对客家方言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共同词语考证,认为二者有接触极深的联盟关系。[17]温美姬考察古代文献发现客家方言与西南官话有较密切的历史关系。[18]练春招指出,广东客家方言有一些词语富有南粤特色,省内各地词汇大同小异。[19]温昌衍通过考察古代文献、客家方言与周边方言农业类词语等词汇比较,发现客家方言的地方特色更强,客粤方言关系最为密切。[20-21]三是客家方言词汇研究的理论突破。温昌衍提出客家方言特征词是“一定批量的区内方言多见、区外方言少见的客家方言词”,[21-22]并对客家方言特征词中的近代汉语;客家方言“山话”特性;客家方言词来源等进行了系列研究。(2)这些研究见:温昌衍,温美姬.客家方言特征词中的近代汉语词[J].嘉应大学学报,2001(2):101-106;温昌衍,从外区罕见词看客家方言的“山话”特性[J].嘉应大学学报,2002(1):114-117;温昌衍.客赣方言关系词与客赣方言的关系[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121-125;温昌衍.从词汇看大本营地区客家方言的分片[J].学术研究,2008(4):141-146+160等。兰玉英等运用方言特征词理论发现成都客家方言词汇传承了丰富的客家方言特征词,又吸收了一定量的西南官话词语。[23]王箕裘通过方言特征词的比较等角度论证耒阳方言属于客家方言。兰玉英等根据特色、近亲缘、近地缘原则确定成都客家方言词汇中基本词的身份,发现成都客家方言基本词汇通过交混、迭置、替代和创新等演变方式重建了一个基本词汇系统。[24]
(三)客家方言语法研究
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语法研究成果体现在:一是客家方言语法特色的研究。熊金丰、饶长溶通过客家方言与普通话的对比,分析了永定、长汀客家方言语法特色。严修鸿通过对人称代词单数“领格”的考察发现:客家方言中的人称代词单数的“领格”,实际是实词语素的词汇合音形式,而非“词形变化”和“内部曲折”。[25]曾毅平探讨了石城“龙岗”方言的起始、接续、经历、已然体。林立芳对客家方言中的几个常用结构助词在各种语言结构中的分布情况作尽可能详尽的描写,通过与普通话的比较展现梅县方言的语法特色。[26]温美姬认为,赣语的“刮”与客家方言的“撇”是对应的两个虚词,都表“完成”义,两词在分布上互不交叉,在层次上与各自方言的形成时间大致吻合,它们极其相似的用法是同义同步引申的结果。[27]石佩璇结合文献考察和田野调查,发现“VP-neg”型反复问句是《客家读本》中的主要类型,也是当代粤中、粤东客家方言的主流。“VP-neg-VP”是后起形式。在反复问类型演变过程中,非动作动词先于动作动词,未然形式先于已然形式进入新格式“VP-neg-VP”。[28]二是客家方言语法功能的研究。谢留文认为客家方言通过动词、形容词重叠形式表示反复问句。[29]饶长溶发现,客家方言体貌助词“啊”可以表示多种状态。[30]练春招分析了福建武平岩前客家方言“牯”的泛化、虚化过程。[31]黄小平认为,江西宁都客家方言有体标记“呃”有可能来源于“在”义介词“喺”的语法化。[32]付新军认为,陕西商洛“公”“嫲”“牯”3个典型的客家方言词缀使用场合的缩减以及“子尾词”的产生和增加都反映了客家方言向普通话靠近的具体过程。[33]温昌衍认为,石城客家方言中做补语的“倒”的语法化过程具有一定的语义理据性。[34]温昌衍等研究客家方言中体标记“啊”,表示动作的完成、反复进行或持续,在功能上与普通话动态助词“了”“着”有相似的地方。[35]三是客家方言类型学研究。李小华对客家方言的“得”等进行语言类型学研究,讨论其语法功能、语法特点、语源。[36]黄小平认为,赣南客家方言的“全”表深程度具有类型学意义。[37]
(四)客家方言历史文化研究
方言是考察客家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依据。[38]近四十年来,研究者将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客家族群的迁移、客家民系的形成结合起来,探讨客家方言历史文化。一是客家方言的来源与形成。崔荣昌引用族谱资料阐述,论述四川客家人的来源、四川客家方言岛的形成。[39]周振鹤、游汝杰论述客家人口的迁徙对客家语言传播的影响。[40]曾维才认为,北方话是客家话的远源,中古赣语才是直接源头。[41]周振鹤、黄笑山、吴金夫从移民史、语音史等角度推断客家方言的来源与形成时间。邓晓华指出客家方言极接近唐五代至宋初时的中原地区语言,客家方言的形成是北方移民语言与华南土著居民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42]庄初升认为,客家方言与古代汉语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43]二是客家方言与客家文化的关系。1990年代钟俊昆、严修鸿、崔荣昌、练春招等从客家方言的谚语、禁忌语、特殊称谓等角度讨论客家文化,认为客家方言保存和体现了客家文化。严奇岩认为,客家方言具有情感、文化传递、族群认同等功能;体现了客家人对自己语言的文化自觉和祖先崇拜观念;客家语言态度体现了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的矛盾。[44]兰玉英梳理客家方言词汇,认为成都客家方言词汇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反映了成都客家文化的形态和特征,沉淀了诸如鸟崇拜、生殖崇拜、自然崇拜等原始信仰及其他历史文化和思想观念。[45]温美姬认为,客家方言词汇凸现了客家民系历史上的山地文化特质。[46]练春招通过对客家方言语音、地名“屋”、谚语的分析,认为客家方言反映了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47]刘立恒、甘于恩等阐述客家方言动物类熟语的语言学价值和文化内涵。[48]三是客家方言的保护与传承。崔荣昌发现,客家方言在语音、词汇等方面受到了四川话的影响,客家方言岛逐步萎缩。[39]张一兵指出,客家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首当其冲的便是客家方言,客家方言、客家方言岛快速萎缩。[49]林伦伦等对广东丰顺汤南半山客居民使用语言的现状的调查则显示:村民掌握语言种类的增加,没有影响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方言的高度认同。[50]但是,更多研究者则表现出担忧。兰玉英发现,双方言交际是四川客家人比较普遍的语言生活方式,四川客家双言发生转用四川官话的趋势。[51]王春玲通过对四川仪陇客家青少年的实地调查和分析,认为客家移民方言与文化正面临着传承危机,亟需转变青少年及家长的语言观念,采取多种措施,建立良好的客家话使用环境,扩大客家话的生存空间。[52]吴晓芳认为,台湾客语流失严重。[53]
(五)客家方言其他研究
一是客家方言分区研究。研究者依据客家方言语音、词汇特点对客家方言进行分区,分区问题的探讨反映了研究者对客家方言面貌认识的深入。鲍厚星、颜森分析客家方言在语音、词汇上的主要特点,论述客家方言在湖南、江西的分布。[54]谢留文、黄雪贞对初版《中国语言地图集》客家方言进行了调整和修改。[55]兰玉英等将四川客家方言整体分为四川粤东片、四川粤北片。[7]二是客家方言与其他汉语方言的对比研究。詹伯慧从三大方言比较的视野观察方言间的影响与接触,分析粤方言对客家方言在语音、词汇方面的影响。[56]庄初升、潘家懿、刘纶鑫、林立芳、刘镇发等探讨了客家方言与闽语、赣语、粤语的相互接触。三是域外客家方言文献研究。庄初升、刘镇发、张双庆、田志军等以域外客家方言文献为蓝本,并与今天的客家方言作比较,探讨客家方言的历史演变。四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深入。詹伯慧、陈立中、林伦伦等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对客家研究客家方言语言使用、语言变异、语言发展等问题。此外,近四十年来在客家方言与外语学习关系研究、客家方言与心理学相关问题研究等方面也有新的研究发现。
二、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的特点与研究趋势
(一)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的特点
1.研究方法上重视调查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
方言调查是开展方言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没有方言调查提供的大量素材,就谈不上对方言进行分析整理、深入探讨。[57]7近四十年来我国客家方言研究始终重视客家方言调查工作。主要体现在:一是调查范围广泛。客家方言的调查不仅在赣闽粤客家族群聚居中心区域,也涉及四川、广西、陕西等客家方言零散分布区域,还调查了台湾、泰国、新加坡等境外区域。二是调查内容丰富。既有单点客家语言面貌的全面调查,也有词汇、语法等专项调查,还有针对某点方言的历时对比调查和同一时期不同区域客家方言的横向对比考察。客家方言调查素材为后续的研究创造了条件,铺设了获取科学成果的道路。[57]7
研究方言,归根结底,一要研究方言差异,二要研究方言特征。研究方言差异也好,方言特征也好,都必须从比较入手。[57]7比较是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通过比较才能揭示语言间的共性和差异。语言研究中的比较涉及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近四十年来研究者对我国客家方言进行了广泛的比较:既有同一时期不同地域客家方言的共时比较,也有同一地域不同时期历时客家方言考察;既有客家方言内部方言点的比较,也有同外部语言的比较,如有与赣、闽、粤、湘等相关方言的比较,有与普通话、民族语言的对比,甚至还有同英语、日语、汉语等外语的比较;既有从文献出发,静态视角的比较;也有从调查出发,动态的比较;既有语音语法等某一方面语言要素的微观比较,也有整体语言面貌的宏观比较。通过这些比较,研究者更为清晰地勾勒了客家方言的历史演变、提炼了客家方言语言特质。
方言的形成是由于社会分化、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等原因促成的,研究方言势必紧密联系社会的历史、考察方言形成和变化的原因和过程。[58]近四十年来研究者注重结合客家文化、客家源流、客家与畲、瑶等民族的语言接触、不同地域、不同年龄客家人的语言态度、语言使用、语言认同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综合考察客家方言的流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结合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开展客家地区语言生活综合调查,联系语言规划、语言环境等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综合分析客家方言发展态势,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开阔了客家方言研究的新视野。
2.研究内容上重视语音研究、词汇研究和文化研究
语音是语言中最为稳定的因素,也是方言区分的重要指标。近四十年来,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客家方言语音调查,调查范围广泛,海内外客家地域均有涉及;归纳了诸多客家方言点的声母、韵母、声调系统与规律,形成了同音字汇等方言语音材料;通过客家方言与上古语音、中古语音,与赣、闽、粤等方言语音的对比,研究者追溯了客家方言语音演变的历程,探讨了客家方言与其他方言的接触与融合;研究者还从韵部、连读变调等微观角度深入分析客家方言语音,进一步明晰了客家方言的语音特征,为客家方言的分区和划界提供依据。
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词汇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一是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对各类客家方言词汇进行了汇总和梳理;二是研究者提出客家方言特征词理论,并不断完善,突破了单纯以语音特征来界定客家方言的局限,为判定和区分客家方言特征词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三是研究者对客家方言词汇进行了大量的考释;四是研究者从客家方言词汇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对比,与其他方言、语言词汇的对比,进一步阐明了客家方言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关系、客家方言形成的时间、客家方言与其他方言之间的关系、客家方言词汇变异机制等问题。
作为语言地域变体的方言与当地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关注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客家文化之间的关系。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一是研究者从族谱等谱牒资料出发,结合客家族群的形成和播迁,论证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分布;二是结合客家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分析客家方言独有的文化品格;三是从与潮、客、闽等方言文化的对比中,突出客家方言地域和族群特色;四是关注客家方言发展态势,调研客家方言语言使用、语言接触、语言情感、语言认同等情况,探讨客家方言的文化传承。
(二)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趋势
1.客家方言研究内容系统化
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的水平不断提升。首先,从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田野调查以广东梅州为主,其他地区呈零星分布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调查点有所扩大,但集中在客家方言连片区域;2000年以后,田野调查范围广泛覆盖全部客家地区,辐射客家边缘区域(如赣东北等以往未关注地区),同时延展到台湾及海外地区。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调查点不断增多,呈现散点分布到带状分布再到区域覆盖的趋势。客家方言调查范围的逐步拓展为全面了解客家方言的分布、区分各地客家方言的特点提供了依据,同时为更深层次客家方言问题探讨奠定了基础。其次,从客家方言研究的内容来看。客家语音研究经历了早期单点语音记录到多点语音对比,再到语音演变规律探讨的过程;客家方言词汇研究经历了从整理记录到对比分析再到词汇演变机制探讨,从语音辨识、来源辨别为主到综合训释,特别是方言特征词理论的提出更是丰富了客家方言词汇研究的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客家方言词汇研究的科学化;客家方言语法研究相比前两者关注度略低,但与前两者类似的是客家方言语法研究也经历了从早期记录到后期比较再到近期语法演变过程、语言类型学研究的历程。总之,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调查区域不断扩大、新的理论不断创生、研究内容不断深入、总体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呈现出由表层记录向深层规律探索延伸的演进逻辑。
2.客家方言研究视角多维化
近四十年来的客家方言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于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20世纪50、60年代的客家方言研究即引入了科学计算方法,同时译介国际语言学界客家方言研究成果,这也使得客家方言研究一开始就拥有宏达的视野和开放的气度。20世纪80年代客家方言研究,不仅关注典型客家方言研究问题,还注意到“畲族人说的客话”,重视客家历史文化与客家方言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为当时尚处于争论阶段的“客家的界定”“客家民系的源流与形成”等问题的澄清提供了语言学的佐证。20世纪90年代的客家方言历史文化研究更直接证明客家方言演变与客家族群形成在时间上的一致性。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百年间,西方传教士热衷于方言翻译《圣经》,直接用方言布道传教,他们的相关著作客观上记录了近代客家社会背景与客家方言语料,具有史料和语料价值。[59]21世纪以来,客家方言研究者对西方传教士所著客家方言文献所进行的整理、挖掘与再利用,提供了客家方言“跳出客家,反观客家”的研究维度,进一步充实了客家方言研究的历史文献资源,再次扩大了客家方言研究视野。
3.客家方言研究理论多学科化
方言研究从属于我国传统“小学”中的训诂学,直接源头是西方方言学。正如客家族群客家文化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多元的社会原因,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发展也如此。近四十年来的客家方言研究呈现出跨越学科壁垒、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计算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渗透在客家方言形成年代推算、客家方言与其他方言关联度分析、客家方言分布、客家方言源流、客家方言文化等研究中。特别是21世纪以来,社会学、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变异、语言规划、语言保护等理论更是为客家方言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促进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的产生。
三、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的反思与建议
(一)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的反思
1.客家方言研究手段依然以口耳听辨为主
除了文献材料外,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调查主要是研究者本人的口耳听辨与记录,在研究数据中使用实验语音学或其他技术手段进行调查的寥寥无几。与此同时,客家方言研究对于语言现象的解释与描写,也主要是依据口耳听辨得来的材料。不可否认,听辨是方言研究重要基础。但是,应该看到仅以研究者个体的听辨作为唯一资料依据一定是有弊端的,因为每个人的听辨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客家方言现有研究中出现的同一语言现象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质疑,甚至出现了同一研究者前后研究结果不尽一致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研究手段的单一性问题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2.客家方言研究理论瓶颈有待突破
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从内容和成果来看,较多徘徊在语言现象的记录与描写层面,现有的语言本体研究更多是对以往研究的材料补充,研究新意仍需突破,代表性理论成果较少。21世纪初期,方言特征词理论的提出在客家方言词汇研究领域掀起一股热潮,研究者依据客家方言特征词理论,围绕客家方言特征词的来源、特性、演变机制、客家方言的界定等问题展开一系列研究。此后的客家方言词汇研究主要围绕这一理论展开。可以说,这一理论打开了客家方言词汇研究的新窗口。研究者在大量词汇之中,通过寻求特征词这条路子,打通了进入客家方言研究的一个通道。但在客家方言其他研究领域,类似的具有影响力的理论还比较少。
3.客家方言研究条件相对欠缺
运用与本文同样的检索方法,共检索到粤方言研究文章990篇,数量上远远超越客家方言研究成果。从研究者所属单位和研究人员分布来看,广东高校是客家研究的重要阵地,詹伯慧、林立芳、庄初升、温昌衍、严修鸿等学者是主要的研究力量。福建、四川、特别是江西等地的客家方言研究队伍和研究力量较为薄弱。客家方言研究专业性学术会议唯有客家方言学术研讨会,每隔两年才举行一次,会议规模较小,参会人数较少。因此,从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和研究平台的情况来看,客家方言研究的内外部条件都还比较欠缺,急需大力发展和完善。
(二)客家方言研究建议
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相对以往客家方言研究而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闽、粤、吴等其他方言研究相比,客家方言研究还存在研究手段不够丰富、研究成果影响力不够大、研究队伍力量较为薄弱等不足。今后的客家方言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以求客家方言研究新的突破:
1.加强新技术、新手段的引入和使用
近四十年来客家方言研究调查主要是以口耳听辨为主。这种调查手段,有其优越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当代实验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学研究领域已开发出“斐风”、praat等调查工具。这些工具最大的优点是便捷和准确。但是在现有客家方言研究中,使用现代语言调查工具进行调查的研究和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在传统调查手段的基础上,更多引入和使用新的调查工具、录音手段、统计处理软件等,以提高客家方言研究的效率和水平。
2.客家方言研究有待深入开展
近四十年来,研究者运用语言学、方言学相关理论开展客家方言研究,但研究有待深入。例如,客家方言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引入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研究客家方言,但是对于客家地域语言态度、语言观念、语言使用等问题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研究规模还比较小,研究成果有限;客家方言中社会语言学定量统计方法运用还比较少;缺乏对客家地区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等问题的探讨;对于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之间的研究还处于比较模糊的阶段等。
3.大力培养客家方言研究人员
近四十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客家方言研究者数量不是很多,现有的高质量客家方言研究成果集中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者身上,凸显了客家方言研究力量的不足。因此,急需大力培养更多的人才,壮大客家方言研究队伍。
——以韶关市仁化县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