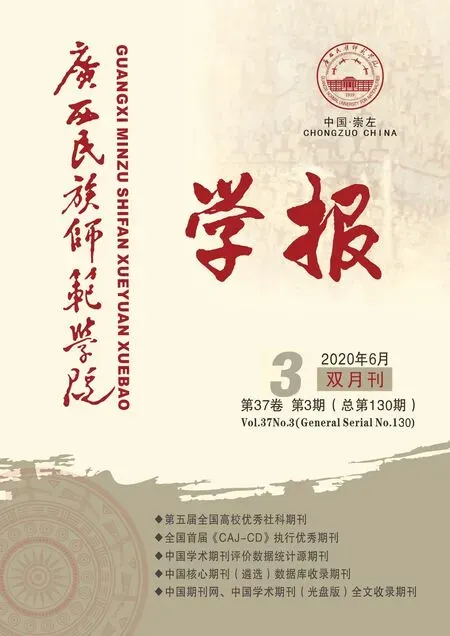徽州民间故事中女子孝行实践类型研究
刘成明
(黄山广播电视大学,安徽 黄山 245000)
在尊奉程朱理学的古徽州地区,孝作为血缘关系而建构起来的道德范式成为宗族社会的中枢神经。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规定,“凡派下子孙,有不孝于其父母、祖父母者革出,毋许入祠”。[1]徽州彭城钱氏宗谱强调:“为子孙者常念罔极之恩,须知孝养之义。族中如有不孝者,族众惩治,再犯不悛者,公逐出祠”[2]这是对不孝者的最大惩罚,使其无法立足于世。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一般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孝道文化之所以在徽州地区受到如此重视,一方面固然与徽州人情有独钟的新安理学有着莫大的关联,另一方面也与徽州特有的经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商的大量涌现,亟须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力量来适应宗族的稳定并维护家庭的和谐,所以“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和支持,促成了徽州孝道观念的风靡”“地方官绅和宗族的践行,促进了徽州孝文化的普及和兴隆”。这一点,张安东教授在《徽州孝文化及其成因之考察》一文中已有明确论述。[3]35-36由此,较之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留守家中的徽州女子则更多地承担起尊祖敬宗、善事父母、慎终追远的孝道责任。
一般而言,民间故事作为大众文化的“传声筒”,具有典型的口头文艺的自在特征,集中体现了一般民众的孝道观念。它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俗知识,而且还渗透着普通民众的审美和伦理诉求,易于让民众所接受。从现有的徽州民间故事文本来看,主要有黄山市文化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制的《徽州记忆》(共五卷)和黄山书社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黄山市分卷》。这两个文本在内容编排上差异很大、少有重复,尤其是它们都大量记载了关于徽州女子孝行实践的生动事象,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学界目前对于徽州民间故事中女子孝行实践的研究,特别是类型研究显得有些薄弱。为此,立足两个文本本身和地方史、志的记载,按照儒家“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等关于“孝”的言说,本文将从能养父母型、敬重父母型、善养父母型、立身行事型四个方面对故事文本进行分类,以期通过阐释每种类型的伦理期待和伦理规范,来发掘徽州孝文化的深层内涵及其价值意义。
一、能养父母型
《论语·为政第二》记录了子游问孝事件。孔子回答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意即孝顺父母,首要的是能够供养父母,这是从物质层面提出了子女赡养父母的底线要求。对女子而言,未出嫁前要在家里好好供养自己的父母;适人从夫后,要与丈夫一同承担起赡养公婆的义务。但由于徽州男子大多外出经商,因此在徽州民间孝行故事里,更多地呈现出女性代替男性扮演家庭管理者的角色。比如流传于黄山区永丰乡岭上村的民间故事《苦娃鸟》,讲述的是一位长相标致、贤惠能干的好媳妇苦娃。在其丈夫外出经商后,她辞去了家中的短工,把家里三亩地的活都揽了下来,一个人插秧、锄草、收割,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每逢过年的时候,苦娃还不远千里将自家腌制的猪蹄送到浙江给自己的丈夫。在丈夫外出经商无辜遭到劫匪杀害后,她与年迈的婆婆更是相依为命,并在婆婆生病之时,将家中为数不多的一点米熬粥给婆婆喝,而自己却靠野菜度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传统的“孝亲”观念与极度贫穷的生活状态相遇时,苦娃没有一点犹豫,她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婆婆。这一理念,也应该可以看作是徽州普通民众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由之引发的舍我求孝使得徽州女子侍奉父母的行为变得更加纯洁高尚,继而在一系列 “苦娃”形象的孝行实践中代代传承、代代发扬。又如流传于休宁县齐云山附近的神话故事《贤媳妇除垢雪冤》,女主人公余蓉花在自己的丈夫和婆婆相继离世后,便暗自叮咛自己,“奴家要加倍孝敬老人,让老公爹愉悦地度过晚年才是”。[4]199后来,她的行为表现是,一日三餐首先考虑的是老公爹的饥饱,春夏秋冬首先忧虑的是老公爹的冷暖。
徽州民间中关于能养父母的孝行故事文本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在能养父母型故事中,主要还是从最低端的物质层面来说的。这些女子的行孝事件,与其笃信的尽孝于父母的伦理观念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也与徽州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主要在于明清之际徽商的大量盛行,使得留守家中的徽州女子很自然地成为继承和发扬孝文化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特别是对于夫君已逝的妇女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外出经商风险很大,一旦遭遇不测,男子的父母便成了孤寡老人,转嫁于女子身上的那种孝敬双亲的责任理念便在徽州大地悄无声息地蔓延。据《徽州府志》记载,婺源县石世珅的妻子汪氏,在其丈夫死后,本想以死殉节,后因父母年老,孩子尚在襁褓之中,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转而承担起照顾家庭、赡养父母、抚育孤儿的重任。[5]363所以,我们不难理解的是,余蓉花的公爹不忍自己的儿媳孤独终老,劝说其改嫁或招赘一个女婿上门后,被余蓉花果断拒绝。可以看出,这样的故事类型,其意义实际已经远远超越了能养的范畴。之所以将其归类于此范畴,最大原因就在于这类故事的孝行文本叙述侧重于此而已。从古至今,孝从来都不只是下对上的物质层面的满足,更多的是要有符合道德上的种种标准。
二、敬重父母型
《论语·为政第二》就提出了孝要有突破物质层面要求的观点,认为“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即如果只是从解决吃饭的角度来定义孝行问题,那么狗和马也能做出孝的举动。所以说,孝不仅仅是一般物质层面的满足,孝还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敬重父母,也就是下对上提供那种源于本心的精神性的满足,这才是人与动物在孝行上的根本区别。就“敬重”来说,它是怎么从晚辈对待长辈的行为表现中体现或者表达出来的呢?《论语·为政第二》就记载了孔子的回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的“礼”就是孔子所说的“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很显然,“敬重”就是要求女性在其父母的日常起居、饮食生活和生老病死中达到“礼”的标准,这在徽州民间故事中有大量的叙事。比如流传于阳湖镇衮溪村的民间故事《端午节的传说》,叙述的事件较为极端,其情节基本是民间故事母题“孝女曹娥”的徽州演绎。文本主要讲述了曹父在一次祭祀仪式上不幸被卷入深不见底的江河中后,其女曹娥悲痛之极,遂跳至江中寻找父尸。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曹娥背着父亲的尸身浮出水面。此等孝行,可以看作是对死者最大的敬重(不惜牺牲自我),对父亲的身体不容毁伤。再比如流传于休宁海阳的歌谣《哭嫁歌谣》,徽州地区历来就有哭嫁风俗,就是在新娘出嫁时履行的哭唱仪式活动。哭唱的内容大多是对新娘未来生活的期望,其中就有“服侍婆家三重大呀”[4]336之类的唱词。这里的服侍,就可以理解为是对婆家长辈的敬重,要在公婆面前做个好媳妇。所谓好媳妇,就是儒家所说的“敬顺之道”,这是女性最为重要的道德品质。
我们都很清楚,在传统宗法社会里,父权文化对女性生理和心理的迫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这是二元对立思维必然演绎的结果。可是,儒家所强调的“亲亲、尊尊、长长”“长幼有序”的礼制规范又对女性寄托着过多的伦理期待,这无形中给女性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虽然孝女、孝妇也在她们的孝行中获得了社会的尊重以及统治者的褒奖,可是在父权文化为中心的儒家典籍中对女子孝行的记载是微乎其微的,即便在一般的民间故事中也是如此。然而,徽州民间故事文本叙事并非这样,它更多地把中华传统美德——孝的践行者和传播者的角色赋予在较为卑弱柔顺的女性身上。比如,14 岁的曹娥,以羸弱之躯果断跳江寻找父尸,这丝毫不逊于《吴孝子传》中刮骨救母的故事。再比如《丢儿崖》,情节设置就更为极端了——在老的和小的难以两全时,为全心全力照顾婆婆,媳妇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解决方案,就是弃儿子于野兽常出没的石崖之下,成全了“孝”的同时,似乎又是对人性的违背。在此种左右为难的境况中,媳妇的果断、决绝也恰恰说明了,在古徽州地区,“敬顺之道”是为妇女之大礼也。所以,“弃子保母”或许在徽州普通民众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孝行实践,这里面包含的心理、生理、社会教化以及地方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极为复杂的。由此可以看出,原本的两难抉择很本能、很自然地在“孝亲”与宠爱孩子的故事架构里被打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孝”已成为植根于徽州女子内心深处的习惯性传承。
三、善养父母型
前文讲述的两种类型,即能养父母型和敬重父母型,或许通过表象行为的实施,是比较容易达到的。我们姑且将这种表象行为称之为“伪善”“伪孝”或者是“愚孝”,这种行为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博取美名或者其他因缘,我们暂且搁置不讨论。《礼记·内则》记载了曾子对“孝”的进一步解释:“父母所爱亦爱之,父母所敬亦敬之”,意即真正的孝就是要顺从父母公婆的意愿,要善于从他们的视角想其所想,善待他们。即便你认为自己的配偶不适合自己,倘若父母却说“是善事我”,那么做子女的也必须要以夫妻之礼对待对方,这便是“善养”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善养”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要和颜悦色地对待自己的父母公婆。《礼记·祭义》指出,“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一般而言,孝子对待父母的时候,面容上要有和悦之色,要温婉真切,而这种情感只有从内心深处生出一种真挚的孝心方可自然流露。古徽州地区就通过民间故事的手段去传播和继承了这种行为规范和思想。比如歙县郑村镇棠樾村的吴氏节孝坊就诉说着这样的故事,虽然该故事没有设置扣人心弦的情节,但对吴氏牌坊树立的因缘作了一番交代,共讲了吴氏的五点功绩,其中涉及孝的占了三点,分别是:服侍生病的婆婆十分尽力周到;培育前妻所生的孤子长大成人,并使其成为清朝有名的书法家;修九世以下祖墓。当时的皇帝表彰吴氏,最大的意图还是在于肯定了吴氏尽心培育了丈夫前妻所生孤子,为鲍家“脉存一线”。[6]177当然,这类故事主要还是对女性扶孤行孝做法的肯定和提倡,因为它有利于维护家族的稳定,这一点对明清时期的古徽州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同类型的故事还有很多。譬如,据《徽州府志》记载,黟县舒尚旰的妻子许氏不仅照顾孀姑,而且还“劝夫娶妾,以慰母心”[5]361。由于许氏不能生育,所以力劝丈夫纳妾,从而了却婆婆延续家族香火的心愿。《孟子·离娄上》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徽州,节烈牌坊处处可见,但对女性来说,尤其是对已婚女性而言,比节烈更重要的是就是延续家庭后嗣,并将其抚养成人,这才能算是尽了孝道。此外,徽州民间故事中也有对不善养父母的惩罚,比如流传于歙东的一则传说《猪肠当麻纱》,讲述了已婚女性冷落了前来投靠于她的亲生父亲——“女儿对他神情十分冷淡”,家里厨房飘着肉香,女儿给父亲端来的却是“一碗冷粥”,最终惹得父亲拂袖而去,不久即被气恼伤肝死去。[6]125此事后为丈夫所知,竟然摔子以绝后患,因为在丈夫看来,有母如此,其子日后也必然不孝,与其如此,不如早早结束其性命。从普通民众心理来说,“孝”与“非孝”向来都是很自然地存在于个体内心深处的悖论。当正统的伦理观念遭遇有违伦理的基本规范时,民众可能就会“不择手段”地找到其他方式规劝他人孝亲报恩。所以,且不论此则故事中对于不孝者惩罚的措施是否正确,单从故事叙述不孝行为的角度来看,“善养父母”的孝行既要有要有面容上的和颜悦色,也要尽自身最大努力满足父母的合理需求。这方面对现代社会来说,也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四、立身行道型
上述三种类型的孝女基本是将女子放置在家庭中进行关照的,只要女子符合一般家庭的伦理期待和道德规范便可称之为孝女。然而,《孝经》提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传统文化观里,孝作为立身之本,扬名以显父母,这是对孝的最高级追求。古徽州地区深受以“孝”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影响,这一点自不必多言,对徽学研究颇有见地的当代学者唐力行、卞利等早已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揭示了徽州孝文化的这一特征。正因如此,徽州女性孝行实践格局特别大,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大孝”,因为徽州女人也将“显”父母作为自身的道德标尺,其落脚点就是建设家乡、造福乡邻。在徽州民间故事里,就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比如《八仙桌嫁妆》一则中,起初赵家庄的村民对赵老四家娶回媳妇桃花得来的嫁妆不是很满意,这个嫁妆只是一张半旧的八仙桌,而赵老四为了让儿子的婚礼特别风光,备置的聘礼可是很丰厚的。但当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冲走村民的一切,使得村民一筹莫展之时,桃花叫丈夫在村民面前用斧子劈开桌面,村民们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因为八仙桌的夹层中居然有一沓厚厚的银票,足足两千两。桃花当场将银票交给自己的公爹,让他带领大家重建家园,过上了美好生活。村民们为了感恩桃花女,遂将赵家庄改名“桃花村”。很显然,这则故事在赞美桃花女义举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徽州女人在稳定家庭、维护宗族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都知道,家庭只是社会的细胞,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当古徽州地区男子外出经商远走他乡之时,家庭中女子的孝行实践便能很好地发挥出推动整个社会建设的巨大作用。孝行实践及其衍生出的道德范式,大多受制于外,也会朝着偏重于普通大众期望角色的方向进行扮演。因此,这样的孝行是“机械性的,而不是理解性的; 是动作性的,而不是认识性的;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自我性的”。[7]356事实上,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推导和鼎力支持。
又如《望娘桥》一则,主人公吴氏在自己的丈夫和公婆相继离世后,本想一死了之,但念及丈夫尚有一幼女需要照顾,便强忍痛苦活了下来,与女儿相依为命。后来,等到女儿长大成人后,吴氏托媒为女儿寻得了一户好人家。由于自家在歙县篁墩村,女儿家在休宁上山村,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吴氏就拿出祖辈和丈夫外出经商时的积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从娘家修了一条青石板路直通上山村。这则故事看似吴氏是为了自己的女儿,然而却在无形中成就了吴氏的“大我”,为当地的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事实上,这则民间故事也能反映徽民的集体无意识,映射出徽州女性在家乡建设上贡献很大。同类型的故事很多,比如《小孤渡》、《死尸讲话》等等都叙述了女性的种种义举。而这些义举,都是以孝为基点,纵向延伸后就成为利国利民的“忠”。所以说,传统男权社会所建构起来的“亲亲”“尊尊”这一道德范式,在使得男子在家事父以孝,在外事君以忠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为女性“扬名于后世”指明了行孝的终极方向。
综上所述,徽州民间故事里记载了大量的女子孝行实践,并在极大程度上对女子的这一行为给予了几乎同男子对等的看待。纵然徽州民间故事里也有几篇“不孝女”的文本,但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搁置在“恶媳”身上,如《黑心大嫂》《女婿和丈人》《姊妹尖的传说》《啼鸟之声》《害人害自己》等等,或许这与当时徽州地区注重宗族讲究血脉亲缘的文化有关,而“媳妇”只是基于婚姻并非血缘建构起来的家庭伦理关系,这一点也恰恰凸显了徽州宗族观念的狭隘与排外。当然,文中所阐述的徽州女子孝行实践的四种类型在民间故事里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与发扬,孝文化的丰富内涵也在徽州大地上织成了一张伦理大网。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达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格局的人伦而存在。”[8]72因此,这张大网主要还是基于体现和维护宗族社会的统治秩序和伦理秩序,女子的孝行大多是出于对封建教化的被动服从。
然而,自20 世纪新文化运动兴起与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渗透使得女性从依附男子的角色逐渐转变成为“人格独立”的形象。女子的孝行也不再囿于被动的服从,而是基于情感与伦理的自主选择,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孝行的内容与形式,比如工作繁忙的女性通过雇佣全职保姆的理性选择来照顾父母和公婆等等。2014 年9 月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含义。”[9]所以,从故事文本入手,全面评价徽州女子孝行实践的传统价值与丰富内涵,找准孝文化的现代转向,探索一条本土孝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对此,笔者将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