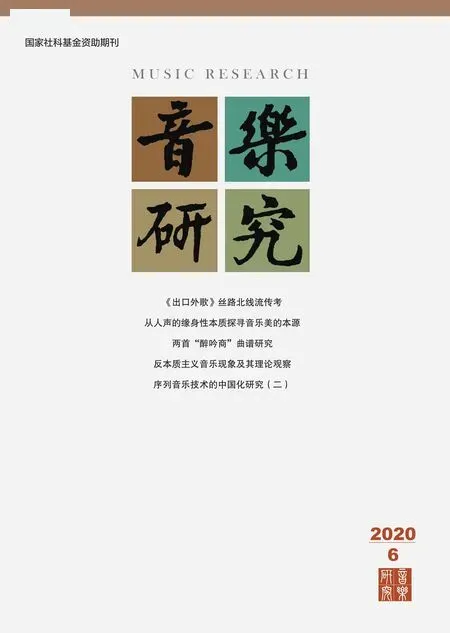论姑娘腔、柳子腔名实及声腔归属
文◎马 莉
清代小说《林兰香》第二十七回的批语中写道:“昆山、弋腔之外,有所谓梆子腔、柳子腔、罗罗腔等派别。”①转引自廖奔《中国戏曲声腔源流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01 页。柳子腔,即清代戏曲四大声腔“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中之“东柳”,是清代戏曲史上影响很大的声腔。今山东柳子戏声腔也因包含齐言柳子腔(简称“柳子”)而得名。然而,柳子戏唱腔的主体并非柳子腔,而是以【黄莺儿】、【山坡羊】、【锁南枝】、【娃娃】(又称 【耍孩儿】)、【驻云飞】等“五大套曲”为常用曲牌,因此,柳子戏又归属于弦索腔系声腔,河南的大弦戏与其同源。与“东柳”一样驰名清代剧坛的还有姑娘腔,又名山东姑娘腔、唱姑娘等。清代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有载:“齐剧也,亦名姑娘腔。以唢呐节之,曲终必绕场宛转,以足其致。”②参见杨米人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158 页。可见,清时的“齐剧”,即是“山东姑娘腔”,当时应该已经传播至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许多地区。
关于“柳子腔”和“姑娘腔”的名称来源,学界存在多种说法。因这两种名称由来,对认识清代以山东、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剧坛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学界对“柳子腔”和“姑娘腔”的名实辨析一直没有停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爬梳文献,以及跨区域、跨剧种的比较,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和声腔辨识,发现二者在名称上有着清晰的历时性关联;并且,在进一步厘清相关声腔剧种关系的基础上,对相关声腔的归属问题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
一、姑娘腔与巫娘腔
一些学者认为,“姑娘腔”一名最早出现在明万历年间抄本《钵中莲》传奇中,但另一些学者将《钵中莲》与清初传奇《长生殿》《长生缘》及清代演出剧本选集《缀白裘》比较后认为,《钵中莲》是清初甚至是清代中期的梨园整理本。③参见胡忌《从“钵中莲”看“花雅同本”的演出》,《戏剧艺术》2004 年第1 期;黄振林《论“花雅同本”现象的复杂形态》,《戏剧》2012 年第1 期;陈志勇《〈钵中莲〉写作时间考辨》,《戏剧艺术》2012 年第12 期。在清代剧坛或戏曲作品中,【姑娘腔】作为曲牌出现于昆曲《麒麟阁》“反牢”一出和《虹霓关》等剧目中。此外,乾隆年间剧本《梁上眼》中亦有“你儿子在山东每日听得都是些‘姑娘戏’”这样的道白,这里的“姑娘戏”,显然指唱“姑娘腔”的戏。可见,“姑娘腔”一名最早可能出现于清代。
清初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讨论当时的戏曲声腔时提道:“近今且变弋阳腔为四平腔、京腔、卫腔,甚且等而下之,为梆子腔、乱弹腔、巫娘腔、琐那腔、罗罗腔矣。”周贻白在其《中国戏剧小史》中认为:“姑娘腔当即巫娘之音讹”④周贻白《中国戏剧小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 页。,“姑”是“巫”的音变。之后,周氏在所著《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进一步指出:“巫娘腔似即姑娘腔……或谓今之柳琴戏,亦名周姑子,即为此一唱调之遗音。”⑤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377 页。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在讨论河南调“女儿腔”时指出:“女儿腔,群众也把它叫作姑娘腔、巫娘腔,因为它的唱腔是从姑娘(妓女)们所唱的弦索调演变来的。所谓女儿是姑娘的同义语,‘巫娘’即是‘姑娘’的音转。”⑥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年版,第31 页。可见,《中国戏曲通史》是将河南调“女儿腔”与山东“姑娘腔”当作同类来看待的,并将“巫”看作“姑”的音变。较为奇怪的是,1992 年修订版《中国戏曲通史》则删除了这段论述。徐扶明对于将巫娘腔、姑娘腔与女儿腔三者视作一个东西,且都归属为“弦索调”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认为“只靠‘同义语’‘音转’之类的方法”来认知声腔是不可靠的。⑦参见徐扶明《元明清戏曲探索》,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359 页。
徐氏所言不无道理,声腔史研究也确实存在因名称相近,误将两个甚至几个不相干的剧种,视为相同剧种或者相关联剧种的情况,如清代文人笔记中就已出现将明代弦索调与清代《太古传宗》中“弦索调时剧”及清代乱弹之弦索腔简单视作一物的现象。笔者以为,不妨把这些由民间得来的称谓当作口述史材料,并将相关声腔放入其历时的生存语境中,结合其他活态材料,来综合分析音义转换背后的声腔演变轨迹。
关于姑娘腔与巫娘腔的联系,纪根垠用文献与大量民俗学资料互证的方法,在《谈【山东姑娘腔】》一文中指出姑娘腔与民间“还愿驱邪的巫觋”有一定的关系。⑧纪氏认为,“民间带宗教色彩、为村民还愿驱邪的巫觋,也唱【姑娘腔】,敲狗皮鼓,演《魏九郎过关》故事,也演《休丁香》《长生乐》等节目。”参见纪根垠《谈【山东姑娘腔】》,《戏曲研究》(第42 辑)1992 年9 月。该文首先讨论了清代传奇《钵中莲》中【山东姑娘腔】,与《缀白裘》第七集《忘记阁》中“反牢”一出【姑娘腔】,昆曲《虹霓关》第九出“骂城”中程咬金所唱【姑娘腔】⑨分别见苏州仁堂刊印版和《国剧画报》第一卷第6 期。,以及山东民歌词义的关联;其次揭示了【姑娘腔】与山东民间歌曲的联系;⑩据孔培培的研究,乾隆年间问世的《梁上眼》剧本第八出“义圆”中【姑娘腔】的结构也是七字上下句。参见孔培培《“姑娘腔”考辨》,《戏曲研究》(第72 辑) 2007 年1 月。再次通过比较山东柳琴戏老艺人赵崇喜、莒南县老艺人张从龙、临沂地区柳琴戏老艺人冯士选的口述资料,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第六卷对“济俗”(即山东民俗)、“跳神”、海州童子戏、安徽端公戏、洪山戏及萨满神歌等仪式环节的记载,再结合对【姑娘腔·迎神调】上下句词格、“似歌又似祝”唱法等类同性和相通性的分析,支持了《中国戏曲通史》所持“‘巫娘’即是‘姑娘’的音转”一说。
从种种迹象来看,笔者以为,“姑娘腔”是因为这些仪式中需要扮演神婆或称女神而得名,山东称“巫娘”“装姑娘”“姑娘戏”,辽宁民香称“唱姑娘”,河南称“女儿腔”。所谓“巫娘”,是指扮演者的神职身份,而“姑娘”,则是附体于“巫娘”的“仙姑”[11]据调查,肘鼓子老艺人称表演时在主人家所悬挂的“轴子”所绘为“北山二仙姑,或南山三仙姑”。,因此,“姑娘”和“巫娘”是一种事物的两种叫法,二者并不存在音转或音讹的问题,如此,所谓巫娘腔、姑娘腔实际上也是一回事。
总之,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清代以来,以山东为中心的戏曲声腔“姑娘腔”的民间宗教起源,学界已形成基本共识。
二、肘鼓子与柳枝(柳子)
与姑娘腔相关的是民间宗教仪式“周姑子”,也称“肘鼓子”。纪根垠根据已故柳琴戏表演艺术家相瑞先的回忆,认为从早期演出“焚香摆供”“奏乐请神”“敲狗皮鼓伴唱”等环节看,“早年不少柳琴戏的男演员也兼演肘鼓子、兼唱【姑娘腔】 。”[12]纪根垠《谈【山东姑娘腔】》,《戏曲研究》(第42 辑)1992 年9 月,第37 页。这说明,民间肘鼓子与姑娘腔甚至成熟的戏曲形式拉魂腔有伴生关系。周贻白认为,“肘鼓子”系“肘悬小鼓按节奏而得名,或叫秧歌腔,则明示其来源”。又谓“周姑子流派颇多,如山东的柳腔、茂腔、五音戏、灯腔,在昔名周姑子,亦作肘鼓子。”[13]同注⑤,第509、377 页。
肘鼓子在山东又称单鼓,类似的鼓,在河北和山西称“扇鼓”。20 世纪末以来,学界逐渐认识到,肘鼓子作为民间宗教仪式,与同源的东北单鼓、太平鼓、兖州砰砰鼓、陕西羊皮鼓、甘肃槟鼓甩辫子、安徽端鼓或喜鼓子、海州童子戏、洪山戏中单面鼓一样,多用于跳神、祭祀。[14]曲六乙发现,“这种扇鼓曾流行于东北、中原地区,为满族、汉族通用的打击乐器。”参见曲六乙《傩戏·少数民族戏剧及其他》,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年版,第71 页。
有学者调查发现,辽宁地区的民间“烧香师傅”,将民香中与肘子鼓有密切联系的唱腔,称作“唱姑娘”或“唱单姑”。笔者认为,“唱单姑”实际上是指“唱单鼓”,即肘鼓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山东肘鼓子对辽宁民香的影响。
有史料表明,清代山东地区巫风盛行,为肘鼓子的盛行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据《聊斋志异》第六卷“跳神”载:
济俗:民间有病者,闺中以神卜。倩老巫击铁环单面鼓,婆娑作态,名日“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妇女,时自为之。堂中肉于案,酒于盆,设几上。烧巨烛,明于昼。妇束短幅裙,屈一足,作“商羊舞”。两人捉臂,左右扶掖之。妇刺刺琐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参差,无律带腔。室数鼓乱挝如雷。蓬蓬聒人耳。
如前文已述,除山东之外,江苏、安徽、辽宁等地乃至北方蒙古族、满族的宗教仪式中,也有与肘鼓子相似的文化表征,它们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鼓的形制与“九”相关的符号学联系。前述《聊斋志异》所记的“老巫击铁环单面鼓”,据柳琴戏老艺人赵崇喜介绍,这种单面鼓“把柄末端弯或圆圈,套缀九个铁环”[15]同注[12],第33 页。。这种形制不禁令人联想到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中称作塔拉哼格日各(汉译作“单面鼓”,俗称“神鼓”)的铁柄单面鼓。如图1 所示,三个大环每环各套三个小环,共有九个小环。与之相应的是,科尔沁蒙古博“过关”仪式常常选在农历九月初九,使用的腰镜是九块,其过“九道关”所需的器具、祭品中,“凡器必九:铡刀九、犁铧九、烙铁九、羊九、牛九……并要有九个以上博师傅参加。”[16]刘桂腾《搭巴达雅拉——科尔沁蒙古族萨满“过关”仪式音乐考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 年第1 期,第54 页。可以说,整个仪式都贯穿着对圣数“九”的崇拜。

图1 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使用的塔拉哼格日各[17]图片摘自刘桂腾《科尔沁蒙古族萨满祭祀仪式音乐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 年第1 期,第53 页。
其二,魏九郎传说及其同主题戏曲剧目(又是一个以“九”为圣数的意象)。据纪根垠的研究,肘鼓子仪式,要在供桌后面悬挂包括“三代宗亲、城隍出巡及魏九郎过关图像”。演戏表现的多是《魏九郎过关》等神话题材的剧目。对于魏九郎的来历,纪氏认为,或传九郎系魏征之第九子,死后封为“请客神”。兖卅砰砰鼓有《九郎上马》,海州童子戏有《九郎借马》,安徽端公戏有《魏九郎背表》,洪山戏有《魏九郎救父》,东北太平鼓也有九郎神故事。[18]参见注[12],第34 页。这些戏曲表现的都是在唐太宗游冥府背景下,魏征第九子魏九郎打表请神系列神话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圣数九的崇拜,应当是借鉴中原道教文化的结果。
其三,仪式中有共同的“请神、安神、送神”环节。肘鼓子演《魏九郎过关》时要唱【点神调】【迎神调】【安神调】【送神调】,说明仪式要经历请神、安神、送神环节。无独有偶,海州童子戏诸环节中,必有请王、安坐、送圣等仪式。兖州砰砰鼓中铺坛和取水之后的演出,其内容也包括请神、安神和送神。同样,科尔沁蒙古族萨满搭巴达雅拉(“过关”)仪式也包括献牲、请神、送神等环节。这些在“请神、安神、送神”环节中所唱的【点神调】【迎神调】【安神调】【送神调】,形成了【姑娘腔】的曲调库,这使肘鼓子与【姑娘腔】表现出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当然,各种仪式都会按各地实际情况有所损益,如海州童子戏,除请王、安坐和送圣之外,还有开坛、献猪、踩门、吹刀、出关、升文和发表等其他环节;科尔沁蒙古族萨满“过关”仪式在请神与送神之间,穿插有“扎都(走钢刀)与霍书(踩犁铧)”“点书嘎(咬烙铁)”“嘎拉都日玛(拢火)”等环节,这些带有深厚早期原始萨满意味的环节,体现了各个仪式在同质基础上的丰富多样性。
其四,共同的功能诉求。这要从中国传统的巫文化功能来解释。《汉语大词典》将“巫”解释为:“古代从事祈祷、卜筮、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祛灾、治病。”在具体仪式中,肘鼓子的功能与“巫”的功能是相同的,如柳琴戏老艺人便常从事这种“开锁子、念神歌、驱魔镇邪”的活动。海州香火会同样有基于“逐疫疠,御旱潦”的功能。[19]宣鼎《夜雨秋灯录》卷6“巫仙”条。肘鼓子正是因为依附于“巫”的祛灾、治病功能,才得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传续。
进一步探究,“祛灾、治病”最首要者是保护子孙繁衍(由孕育到成长),这应该是中国传统社会历久未变的、有终极意义的诉求。如苏北香火执事者“香火童子”“香童”“童子”的称谓,以及海州香火会、南通香火戏等称谓,均暗示了仪式最初或者核心功能的护生保童性质。从这一视角切入,可以揭示“柳子”一名的来历,或者说获得对“柳子”一名功能意义的解释。
对于柳子一名的来历,学界目前也没有统一的认识。周贻白比照湖南北部一带对花鼓戏的称谓后提出:“山东的柳子戏把一种近似梆子的声调叫作柳子调而来代替一般民歌小调。”[20]同注⑤,第504 页。湖南北部石门、慈利一带,将该地流行的花鼓戏称为柳子戏(又名杨花柳、大筒戏),该地所谓“柳子”,就是指在当地流行的(诸如《四季》《五更》《十二月》之类的)民歌小调。湖南与本文涉及的以山东为中心的内蒙古、辽宁、河北、河南、安徽和江苏等地的文化不接近,人文地理相距更远,将湖南柳子戏与本文柳子戏类比,从形态上看难以令人信服。但如果从护生保童的角度来看,二者似乎有联系,因为全国各地花鼓戏的生存环境,都与生殖崇拜有一定的关联。
山东柳琴戏(目前归属于肘鼓子腔系)与山东花鼓戏音乐,在拉腔、衬词和音调上有密切联系,二者表现出共同文化内圈的关系。关于柳子(柳枝)与肘鼓子的联系,可以借助跨民族文化比较的方法,从仪式功能角度获得一些认知。满族萨满文化的“佛多”信仰值得关注。在满语中,“佛立”意为神龛,“佛多”乃柳枝(柳子)。清代满族皇室在坤宁宫所祭祀的是佛立佛多鄂漠锡妈妈(Fere fodo omosi mama),其中omosi 是满语,为“众孙”之义,“鄂漠锡妈妈”则是指子孙奶奶,“佛立佛多鄂漠锡妈妈”就是满族共同信仰的生育神和儿童保护神,民间习惯称这位女神为“佛多妈妈”(fodo mama)或“佛他妈妈”(fuda mama)。fodo 意为柳枝,fuda 意为绳子,鄂漠锡妈妈就是满族民间为保婴、育婴而祭祀的女神。[21]参见孟慧英《佛立佛多鄂漠锡妈妈探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2 期。这就找到了肘鼓子与柳子(柳枝)的文化联系:一个作为仪式的法器,一个为祭祀的对象代码,二者同样承担着保佑子孙繁衍的功能和目的。可见,柳子被赋予了“神”的意义,所以山东柳子腔艺人将《马二头送崇》中的柳子腔称为【神柳】。
至于柳子到底是源于汉族文化还是源于满族文化,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柳子、柳子腔与肘鼓子的联系,是在清朝统治下,汉族文化与满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同时,这也解释了蒙古族萨满与肘鼓子等在仪式功能上的联系,其内在原因是满族萨满与蒙古族萨满有太多的文化关联。
三、【姑娘腔】【柳子腔】的调与“腔”
由上文论述可知,清代【姑娘腔】的音调,就是乱弹诸腔中普遍存在的【柳子】(或称【柳子腔】【柳枝腔】)的源头。从清代传奇《钵中莲》、场上演出底本《缀白裘》、昆曲《虹霓关》,到乾隆年间问世的《梁上眼》可以看出,【姑娘腔】的词格多表现为齐言上下句结构,由此可以想见,其唱腔音调同样应该为上下句结构。这一曲体结构特征,正是今山东柳子戏、河南大弦戏、山东聊城八角鼓、胶州八角鼓、济宁八角鼓、莱阳弹词、京剧(杂腔小调)、北京曲剧、北京八角鼓、辽宁海城喇叭戏、二人转、黑龙江拉场戏、江苏扬州清曲、上海京剧(杂腔小调)、浙江杭州滩簧、福建闽剧罗罗腔、北路戏杂调、河南罗戏等剧种、曲种中,被分别称为【柳子】【柳子腔】【柳枝腔】【赞子】【序子】【罗罗调】【小上坟】【小上坟调】【莺歌柳】【小柳子调】【武赞子】等曲牌音调的共同特点。据相关研究,以上30 多个【柳子】类腔调,都是在两个基础音调上发展起来的:一是上句do 结尾,下句re 结尾,如山东柳子戏《打登州·黄桑店》中的【柳 子】[22]谱例详见《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东卷》,中国ISBN 中心1996 年版,第1125 页。等;另一个是上句mi 结尾,下句sol结尾,如山东柳子戏《火焰山》中的【莺歌 柳】[23]谱例详见注[22],第1123—1124 页。。这与【姑娘腔】的词格是吻合的。
清代【姑娘腔】的另一个特点是“浪腔”。如昆曲《麒麟阁》“反牢”一出中所用的四次【姑娘腔】,在唱词的下句或整个唱词的最后多次出现“浪腔介”或“浪调介”字样;又如,《缀白裘》第六集《乱弹腔·阴送》中出现“急板浪”“急板浪,地方鬼浑介”字样,同集《搬场拐妻》出现“贴唱场上先浪调”字样。对于这些不同名称,但指义较明确的表演形式,徐扶明认为:“大概是耍腔或者过门,再配合一些表演动作。”[24]同注⑦。徐氏所言极具启发意义。笔者以为,所谓“浪腔介”,应该是为了渲染戏曲表演气氛,由演员个人拉腔,或由唢呐类乐器代替人声拉腔,或为众人合腔。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记载和与肘鼓子腔相关的剧种中寻找踪迹。
周贻白认为“拉魂腔”的本源出自肘鼓 子,[25]同注⑤,第510 页。“拉魂腔”系早期对今天山东柳琴戏、安徽泗州戏、江苏淮海戏的称谓。据口传资料,有人因唱腔中常使用尾音高八度的拉腔,将周姑子(即肘鼓子)称为“拉呼腔”“拉后腔”;后雅称为“拉魂腔”,以赞美其腔有动人心魄之意。被山东戏曲界归属为“肘鼓子腔系”的茂腔,是由当地人称唱腔中有“打冒”“打鸣”的谐音演化而来,因它源于肘鼓子腔,又被称为“茂肘鼓”。另有研究表明,“浪腔”或由尾句拖音,由唢呐或人声帮腔而来。张善堂、王晓家提道:“‘本肘鼓’之所以又称‘老拐调’或‘哦嗬唵,是因为当时其基本唱腔,由一人唱众人和,每句在开头和结尾时,往往由全体演员齐声帮腔,尾句拖音下降,或吹唢呐帮腔所致。”[26]张善堂、王晓家《五音戏源流考略》,《齐鲁艺苑》1989 年第4 期。孔培培也关注到剧白中“你唱我帮腔,我唱你帮腔”为【姑娘腔】的表演形式。[27]孔培培《“姑娘腔”考辨》,《戏曲研究》(第72 辑)2007 年1 月。清代旅居北京的吴长元,曾留下了“吴下传来补破缸,低低打打柳枝腔”的诗句,其中的“低低打打”,正是唱【柳子腔】时唢呐作为每句句尾接音帮腔的拟声词,至今民间流行的《钉缸调》仍保留了这种唱奏结合的形式。
余 论
行文此至,另一个延申出的问题,仍需要做一些讨论,那就是—东柳是属于拉魂腔系、肘鼓子腔系,还是属于弦索腔系?
在清代四大声腔“南昆、北弋、东柳、本梆”中,南昆、北弋、西梆各自具有独特的区别性特征,它们的声腔构成各自已经自成体系,并且对其他众多剧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对三者的“腔系”也没有分歧,但是,对“东柳”作为“腔系”地位的认识,无论从它的体系自洽性,还是对其他剧种的渗透能量,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余从在《戏曲声腔》中对“明清俗曲(弦索)声腔系统”有这样的看法:
“东柳”一枝,我认为就是明清俗曲系统,也就是弦索腔系,它属小曲而非南北曲,但形成戏曲声腔和剧种,则对昆、弋多所吸收、借鉴。曲调众多而又不似昆、弋体制谨严。因此,我认为它既是一个腔系,又是一个可以从它的众多曲调中生发出新腔系的群体。[28]余从《戏曲声腔》,载《戏曲声腔剧种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年版,第128 页。
路应昆也认为:
“曲调众多”、来路纷杂,确实是被称为“俗曲”(弦索)的这堆东西的实际状况,而且其中的不少曲调也确实能“生发出新腔系”,因此在研究者面前便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把这堆东西说成“一个腔系”似乎太笼统、太简单化,但要说这个“群体”中还包含了不同的腔系,那么那些腔系又应该怎样划分呢?[29]路应昆《戏曲声腔研究70 年回顾与反思》,《戏曲研究》(第111 辑)2019 年第3 期。
目前,山东戏曲界倾向于将柳琴戏、五音戏、茂腔和柳腔归属为“肘鼓子系统”,将柳子戏、大弦子戏、罗子戏和乱弹归属为“弦索系统”。[30]参见李赵壁、纪根垠主编《山东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洽的归类,虽然柳琴戏、五音戏、茂腔和柳腔是从肘鼓子开始的,但是,“柳子腔”作为腔调在其中的占比并不多,这些剧种也多唱【耍孩儿】【山坡羊】曲牌,如五音戏里有【娃子】和【羊子】,柳琴戏里有【八句娃子】和【十二句羊子】,而这两个曲牌属于弦索腔系的“五大调”。弦索腔系中的剧种虽然也唱“柳子腔”,柳子戏也因唱“柳子腔”而获得柳子戏这一剧种名称,但是柳子戏却以【黄莺儿】【山坡羊】【锁南枝】【娃娃】(又称【耍孩儿】)【驻云飞】 “五大套曲”为主要腔调。而肘鼓子系统中的柳琴戏、淮海戏、泗州戏又同属于拉魂腔系。此外,这些剧种中的许多腔调,还具有积极吸收其他声腔,以及生发新腔调的活力。因此,笼统、简单地归属“腔系”,不仅其行为值得商榷,也与各个剧种“多腔共和”的现实不符。笔者认为,根据当下许多剧种的实际情况,对于山东诸声腔,可采取民族音乐学“悬置”的方法,暂时不作腔系分类,只保留昆、弋、梆三个腔系的说法。
——以2010-2020 年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