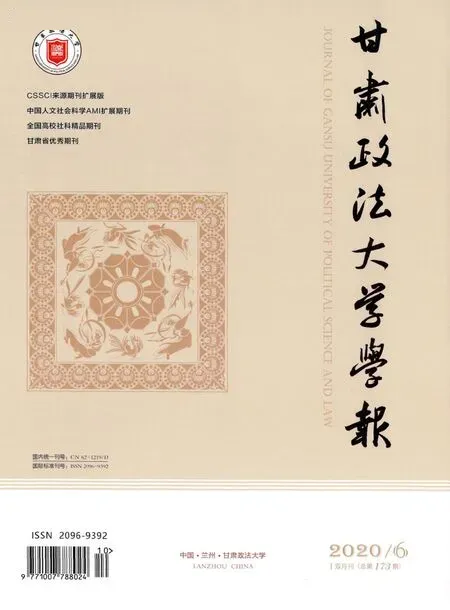侵权法上的获利返还制度
——以《民法典》第1182条为中心
石佳友,郑衍基
对于中国法来说,获利返还并非一个陌生的概念,与之相关的规定散见于中国法律的多个领域,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公司及证券法律体系中规定的 “归入权”;〔1〕如 《公司法》第148条规定,对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与勤勉义务的法律后果,即所得收入收归公司所有。另一类是在侵权法律体系中,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体现在相关条文中,最为典型的当属 《侵权责任法》第20条以及知识产权法中的损害赔偿条款,这些条款大多采取按受害人损失、侵权人获利、支付合理使用费及法定损害赔偿、酌定赔偿的顺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2〕如 《著作权法》第49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然而在实践中,获利返还往往被法官轻轻带过,致使这一制度难以发挥其制度功能。
2020年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 《民法典》第1182条对 《侵权责任法》第20条进行了重要修改:“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这一安排显著提高了获利返还救济在我国侵权法体系中的地位,但笔者认为若希望真正发挥获利返还的制度功能,对于其适用模式的深入讨论仍有必要。
本文所讨论的获利返还救济旨在将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的主观获益返还给受害人,因此该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加害人所投入生产要素的影响,如销售渠道、经营规模等因素。就侵权领域而言,该数额可能高于或低于依客观方式计算的受害人损失 (如合理许可费形式的损失计算)。
一、获利返还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在司法实践当中,获利返还制度在侵权领域,尤其是在 《侵权责任法》所划定的侵犯人身权益情形中并未能得到足够广泛的适用。综合分析相关案例,其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障碍:可操作性的缺乏以及适用范围的严格限定。
(一)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缺乏可操作性
获利返还制度在司法适用中最大的障碍为其可操作性的缺乏。《侵权责任法》第20条仅提出返还 “利益”此种计算赔偿数额的方式,其本身及相应司法解释并未对此概念及范围进行明确界定。而在现实中,商业行为的利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该在何种程度上考量被侵害权益对于加害人所获 “利益”的影响将成为每一个法官都必须解决的问题。明确标准的缺失使法院在面对获利返还数额的确定这一问题上出现多种回应,如在知识产权案例中,有的法官通过侵权产品销售额及平均利润率的核算来确定 “获利”,〔3〕参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6)温民三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书。有的则尝试对侵权行为进行类型区分,并根据场景不同采取不同数额确定的方法。〔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民申2632号民事裁定书。而在人格权侵权的情境中,法官在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20条时更是倾向于向第三句 “逃离”。〔5〕也有法官意识到 《侵权责任法》预防功能的重要性。在 “王希维诉昆山时光医疗美容肖像权侵权”一案中,二审法院强调了 “商家以营利为目的侵犯明星肖像权的现象较多,为达到遏制侵犯公民肖像权行为的社会效果”,相应调高赔偿数额。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苏05民终10576号民事判决书。
因此,获利返还救济在司法裁判中的论证成本较高,且法官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享有较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所以在相关纠纷中法官对于酌定赔偿数额具有明显的偏好。〔6〕王若冰:《论获利返还请求权中的法官酌定——以 〈侵权责任法〉第20条为中心》,载 《当代法学》2017年第4期。在大量裁判实践中,关于赔偿数额确定的说理部分一般都较为简单,大多论证仅说明原告举证时证据之缺乏或损失及获利无法确定,其后便综合考虑各因素,如被侵害权利类型、侵权性质、被告的主观过错酌定赔偿额。〔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民再384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民申1803号民事裁定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湘知民终260号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19)内民终47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沪民终63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知民终85号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2019)新民终36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皖民终246号民事判决书。此种裁判方式较为粗放,不仅无助于法律实践的经验积累,也不利于社会大众根据法律调整自身行为。
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其请求获利返还最主要的障碍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 《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受害人需要举证加害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在缺乏对方配合的情况下,受害人一般难以获得证明利润数额所需的财务数据。〔8〕参见缪宇:《获利返还论——以 〈侵权责任法〉第20条为中心》,载 《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面对无法证明侵权人利润总额即难以获得相应赔偿的风险,受害人在提起诉讼时便更多将希望放在精神损害赔偿等举证更为主动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上。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已有调整举证责任分配的尝试。〔9〕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京民终332号民事判决书。
(二)基于立法的局限:适用范围的严格限制
就侵权法而言,获利返还制度的适用范围被严格限制于知识产权及人格权侵权领域。《民法典》第1182条虽然不再强制规定适用顺序,但是调整了适用范围。
以人格权侵权为例,从 《侵权责任法》第20条的条文表述来看,其在人格权侵权中的适用要求此类人格权内含财产利益。对于名称权、肖像权等商业操作已颇为成熟的权利类型,这一论证并不困难,〔10〕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8)沪01民终8636号民事判决书。然而对于名誉权等正常情况下难以进行商业利用的人身权益,〔11〕对此学界仍存争议,如刘言浩指出 “若人格权本身不具有商业价值如名誉权,则不能成为不当得利之利益”。参见刘言浩:《不当得利法的形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司法实践同样希望通过 《侵权责任法》第20条加强对侵权行为的威慑性,如北京市一中院在一起案件中判决一媒体的不实报道侵犯了受害公司的名誉权,并适用该条款确定赔偿数额。〔12〕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01民终8410号民事判决书。另可参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9652号民事判决书。由此可见,《侵权责任法》第20条可通过进一步的解释获得广阔的适用空间,而其中的获利返还作为一项具有阻吓作用的救济手段,更是可以在广范围内得到适用以体现侵权法的预防功能;目前这种明确限制的立法模式虽使其适用范围十分明确,但同样可能导致保护范围过于狭窄,〔13〕参见朱岩:《“利润剥夺”的请求权基础——兼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载 《法商研究》2011年第3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获利返还的制度功能。
二、获利返还制度的域外经验
基于相关国际共识,〔14〕《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第45条第2款规定:“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均在知识产权领域认可获利返还救济或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将加害人侵权获利纳为考量因素之一。然而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观察,就获利返还救济的一般规定及其司法实践而言,各个国家及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一)通过侵权损害赔偿的途径:法国、比利时及 《共同参考框架》(DCFR)
法国及比利时并不认可 “获利清除”的概念,但两国法院认可在 “评估对遭受金钱损失的受害人有权获得的赔偿金范围时,应考虑违法者通过非法手段已经获得的利润”〔15〕欧洲民法典研究组、欧洲现行私法研究组编著:《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5卷、第6卷、第7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23页。。比利时法院就曾在一起出版物侵害人格权的案件当中,将有过失的出版商因侵权行为所获利润纳入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考量当中,以使判决具有一定的阻吓作用。〔16〕U.Magnus,Unification of Tort Law:Damage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47.此外,法国侵权法的改革草案希望通过归于公共资金的民事罚金 (amendecivile)以应对侵权法威慑功能不足的问题。〔17〕法国的 《卡特拉草案》本希望通过广泛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应对诸如肖像或名誉适用、知识产权侵犯、商业领域的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的 “盈利过错”问题,但对此法国各界存在极大争议, “实务界多持反对意见,消费者团体保持中立,理论界则似以支持声为主”。李世刚:《法国侵权责任法改革——基调与方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68-69页。也有法国学者支持对受益型侵权行为进行整体规定并制定关于获利返还的一般条款,以体现侵权法对多元立法目标的平衡。〔18〕Michel Séjean,Chapter6:The Disgorgement of Illicit Profits in French Law,in Ewoud Hondius& André Janssen(eds.),Disgorgement of Profits:Gain-based Remedies throughout the World,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5,p.130.
而欧盟 《共同参考框架》在第六卷 “造成他人损害的非合同责任”中的第VI-6:101条将获利返还规定为救济手段的一种,并赋予了受害人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但此选择权须 “在合理的情况下”方得行使,即受害人本可通过与侵权人同样的方式利用被侵害权益并获得相当的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仅当法官判断完全不符合此情形时,其才可以滥用为由拒绝受害人的这一主张。〔19〕同前注 〔15〕,第715页。
(二)通过不法无因管理的途径:瑞士、我国台湾地区
根据 《瑞士民法典》第28a(3)条关于自然人人格权侵权诉讼的一般规定,受害人有权准用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要求加害人返还侵权利润。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于2006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法官认为受害人应当证明加害人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利润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大幅降低了对于因果关系及获利的证明标准。此外,法院还在此案中通过举轻以明重的逻辑思路确定 “准用无因管理”不要求 “侵权人代表受害人行为”,即该规范可适用于受害人不可能实行侵权人行为的情形。〔20〕Thomas Kadner Graziano,Comparative Tort Law:Cases,Materials,and Exercises,Routledge,2018,p.485-488.
依据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在擅自利用他人权益获利的情境中,可能产生三个可主张的权利基础,即不法管理、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于不法管理下受害人可主张返还加害人的主观获利,于不当得利下可依通说主张受侵害权益的客观价值返还,于侵权行为下可主张客观价值之损失。〔21〕姚志明:《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88-90页。
(三)通过不当得利返还的途径:奥地利
奥地利承认行为人不能从其不法行为中获利的一般原则,利用他人财产获益的情形可适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041条请求 “获益”的返还,〔22〕同前注 〔15〕,第725页。因为该条款为规定基于给付以外的不当得利的一般条款。〔23〕同前注 〔11〕,第124-125页。然而,对于此种救济不当得利与侵权损害的界限并非如此清晰,如根据奥地利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特别规定,适用获利返还 “要求被告方存在过错且损害的严重性应与法律制裁一致”。〔24〕同前注 〔15〕,第725页。
(四)英美法系的返还法体系
从英国返还法的体系来看,返还可分为两种类型:不当得利返还和不法行为返还。而不法行为返还项下存在三个子类:侵权行为返还、违约行为返还、衡平法中的不法行为返还。〔25〕肖和平、霍政欣:《英美债法的第三支柱:返还请求权法探析》,载 《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3期。因此,英国在一般意义上承认获利返还,但其适用要件仍交由侵权法调整,即侵权行为本身可以产生两个救济性权利,“放弃侵权之诉”这一诉因并不真正意味着侵权行为被豁免,而是原告在赔偿请求权与返还请求权之间做出了选择。〔26〕参见 [英]皮特·博克斯:《不当得利》,刘桥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英国学者沃特森 (Stephen Watterson)认为基于得利的救济还未形成一个通用的适用模式以及明确的边界,其发现在不同类型权益受侵害的情形下,法院对获利返还救济提出严格程度不同的构成要件。〔27〕参见Stephen Watterson,Chapter3:Gain-based Remedies for Civil Wrongs in England and Wales,in Ewoud Hondius&AndréJanssen (eds.),Disgorgement of Profits:Gain-based Remedies throughout the World,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5,p.45.
而第三版 《美国返还与不当得利法重述》第3节明确规定了 “任何人不得从其不法行为当中获利”,且根据第39节的规定,这一原则看似只有 “故意不法行为”这一适用范围的限制,然而实际上其通过特别条款将此救济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几种特定的不法行为。〔28〕参见王利明:《债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26页。
三、获利返还制度的法理基础
获利返还来源于 “禁止非法获利”的古老原则,这一原则早在罗马法时期便得以确立并同样为现代社会所认可,〔29〕同前注 〔28〕,第524页。其他国家法学实践中存在着类似的表述,如在Jegon v.Vivian(1870-1871)的判决中,Hatherly法官明确指出:“This Court never allows a man to make a profit by a wrong[…].”See Ewoud Hondius&AndréJanssen,Disgorgement of Profits:Gain-Based Remedies Throughout the World,in Martin Schauer&Bea Verschraegen(eds.),General Reports of the XIX 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omparative Law,Springer,2017,p.115.但为明确其适用模式,还需要对两方面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一是剥夺加害人获利的必要性;二是将侵权获利赋予受害者的合理性。
(一)获利返还救济的必要性:困境及现有法律制度的不足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各类侵权的行为成本不断降低,加害人所得大于受害人损失的情形也时有发生。〔30〕之前张新宝将获利返还责任归于侵权责任请求权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例外,即 “请求权越界”问题,并认为 “以上 ‘越界’属于特别规定,而且仅仅适用于 ‘实际损失’或 ‘损害’不易确定的案件,这种扩张相对于整个侵权责任法来说仅占很小比例。”笔者认为现实情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参见张新宝、郭明龙:《侵权责任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载 《私法》2008年期。当加害人预估其获利大于受害人损失时,侵权将会是更 “合理”的选择,这就等于加害人可以强制买断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此结果无疑与 “禁止非法获利”原则相悖。
对此,我们首先尝试从现有民法体系中寻求解决途径:或基于不当得利请求 “返还”,或基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 “赔偿”。若 “得利”或 “损害”的概念无法囊括加害人的主观侵权获利,则获利返还因其剥夺加害人侵权获利的效果而具有补充传统民法体系阻吓作用不足的价值。
1. “获利”不同于不当得利一般规则中的 “得利”
不当得利的历史可追溯至 《十二铜表法》,〔31〕该法第7表第10条规定了若果实落在邻居的土地上,果树的所有人有权将其取回。在此基础上,罗马法学家们发展出了 “请求返还诉”(condictio),但并未就此形成统一的制度,〔32〕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29-830页。古罗马法学家Pomponius也仅在学说层面提出 “自然公正要求任何人不得损人利己”的法谚。〔33〕同前注 〔11〕,第1页。经过多年的发展,不当得利法也趋于稳定,并发挥着两个基本功能:一是 “矫正欠缺法律关系的财货移转”;二是 “保护财货的归属”。〔34〕王泽鉴:《不当得利》(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因此,不当得利关注对利益分配结果的矫正,以 “归属说”为理论基础,〔35〕同前注 〔13〕,第139页;[奥地利]海尔姆特·库奇奥:《侵权责任法的基本问题 (第一卷):德语国家的视角》,朱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5页。欧洲各国对此亦基本形成共识。See Nahel Asfour,Wrongful Enrichment:A Study in Comparative Law and Culture,Hart Publishing,2017,p.30-43.其不同于损害赔偿的衍生权利性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为原权,其起源于 “事件以及虽有不当但属合法的事实行为或者法律行为”。〔36〕和育东:《非法获利赔偿制度的正当性及适用范围》,载 《法学》2018年第8期。
因此,依照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则,其返还范围取决于法益的归属划分。通说认为,当受益人无法通过返还原物的方式承担不当得利返还的责任时,受益人应返还价额将依被侵害权益的市场价值确定,〔37〕同前注 〔28〕,第466页;同前注 〔8〕;同前注 〔13〕,第140页。亦有学者认为 “不当得利制度之目的,应以客观的计算标准为妥。但若遇特殊之情形,适用客观之计算标准有失公平时,亦可采用主观的计算标准。”同前注 〔11〕,第397页。其代表加害人非法获利中的原告权益价值部分;而 “获利”为加害人通过被侵害权益与自身生产要素的结合获得的利益,代表非法获利的增量价值部分,〔38〕同前注 〔36〕。直接归入受害人的权益归属内容并不妥当。境外实践也与此类似,如德国民法规定,擅自利用他人财产而构成不当得利时,受益人应依照该利用行为的客观市场价值进行赔偿。〔39〕同前注 〔15〕,第1003页。
2. “获利”不同于侵权责任中的 “损害”
侵权损害赔偿中的 “损害”概念与 “获利”同样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就传统侵权法而言,其以 “完全赔偿”为原则,赔偿数额是以受害人损失为基准的;而获利的计算以加害人的状态为起点,希望以此遏制侵权行为发生,两者对于侵权事件的观察角度迥异。〔40〕同前注 〔13〕。此外,在传统侵权法体系下,受害者同样受 “禁止不当得利”的约束;若获利大于损害,则从表面上看,获利返还救济与该原则相悖。
因此,获利返还救济实质上兼具不当得利及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则特点,相当于在不当得利的基础上通过侵权损害赔偿的违法性理论扩大了利益返还范围。相较于传统损害赔偿法对于过去实际损害的关注,这一制度聚焦于如何有效预防潜在权利侵害上,体现了对于侵权法立法目的的重新审视与平衡。〔41〕[德]格哈德·瓦格纳:《损害赔偿法的未来:商业化、惩罚性赔偿、集体性损害》,王程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二)受害人 “得利”的正当性:不同的论证路径
对于侵权获利的归属,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如在德国联邦法院审理的 “卡罗琳娜公主案”中,法官们选择通过大幅提高精神抚慰金数额以将加害人利润转移给受害人;〔42〕同前注 〔13〕。而法国的 《民事责任改革草案》选择通过民事罚金将其纳入公共财产。〔43〕参见法国司法部:《民事责任改革草案 (2017年3月)》,李世刚、刘曦编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第三届中法民法典研讨会论文,2018年11月,第380-381页。相较于将此部分利益交给国家,笔者认为,将其返还给受害者更为合理,对于这一观点,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论证路径:
1.双方联系的视角:拟制信托与不法无因管理理论
拟制信托义务违反的理论以构筑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特别联系为基础,如英美法中将义务违反拟制为信托义务的违反,〔44〕同前注 〔36〕。如前述 《瑞士民法典》第28a条对 《瑞士债法典》中无因管理相关规定的准用。〔45〕Thomas Kadner Graziano,supra note 20,p.485-488.支持者们认为,既然在无因管理人是善意的情况下,其通过管理行为所获收益都需要交给本人,更不用说侵权行为人通过侵犯他人权益、恶意管理他人权益所获利益了。
特殊关系的拟制对于获利返还来说是一个较佳的论证基础,但考虑到我国在侵权法领域以救济手段的形式构建获利返还,且未与无因管理相互动,则除非立法变更,此种论证路径对于侵权法中的获利返还仍显不足。
2.矫正正义的角度:受害人权益的获利可能性
库奇奥为 “利润返还”寻找的规范基础是 “在狭义上虽然此种利益的归属不能赋予丧失利益人,但应当可以认定一个效力减弱的归属,即加害人侵害了法律原本赋予受害人的获利可能,并且加害人自己享有了该潜在获利。”同时,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加害人实施了一个客观上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的要件以保持法律关系的平衡。〔46〕同前注 〔35〕,海尔姆特·库奇奥书,第41-45页。温里布同样强调不法行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构筑的是一种双向联系,因此救济本就不应当仅考虑一方,无论是受害方的损失还是加害方的得利。〔47〕Ernest J.Weinrib,Corrective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19.侵权双方的关联关系于Palsgraf v.Long Island Railroad 的判决中有所体现。See Benjamin C.Zipursky,Palsgraf,Punitive Damages,and Preemption,Harvard Law Review,vol.125,No.7(May 2012),p.1760-1771.
3.分配正义的角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平性
第三种思考路径倾向于从分配正义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即何者保有侵权获利更符合正义原则。基于资本为劳动之凝聚这一前提, “原告权益价值是凝积在原告权益上的 ‘在先劳动’的价值,增量价值是凝积在被告所投入生产要素的 ‘在后劳动’的价值”。因此侵权获利的分配问题实际上是立法者的价值取舍问题。〔48〕同前注 〔36〕。
从这一视角来看,获利返还救济将随着法官在个案当中对于权益保护价值的不同评价而呈现不同结果,此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英国对于获利返还救济难以形成统一的适用模式的现象。
4.将利润归于国家的不恰当之处
《民通意见》第131条虽规定了国家可收缴通过不当得利获得的 “其他利益”,但根据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上的初步查询,此语句极少在司法实践中得以适用,〔49〕丁宇翔法官指出在裁判实践中确实存在法官认为不当得利的不法原因是与 “本案有关的违法行为”进而需要进行制裁,因此判决收缴非法所得的情形。参见 《民法典合同编分则草案立法研讨会实录 (下)》,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19年10月18日,http://www.civillaw.com.cn/gg/t/?id=36132。学界对此也颇多批评。〔50〕参见霍政欣:《中国不当得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载 《求索》2006年第2期;傅广宇:《“中国民法典”与不当得利:回顾与前瞻》,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最终,《民法典》并未吸收 《民法通则》中与国家收缴相关的条文。此外,国家参与至涉案利益的分配不仅可能对民事诉讼体系带来冲击,同时对法官的中立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合各论证路径,相较于国家收缴的方式,更为合理的方式是将侵权获利归属于受害者,并根据受侵害权益的不同通过适用范围或数额确定方式进行调整。
四、获利返还司法适用的展望
如前文所论述,获利返还司法适用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概念界定模糊以及适用模式不明确造成的。因此,下文将从适用范围、构成要件以及具体数额确定三个方面进行阐释,以展望民法典生效后获利返还制度司法适用的前景。
(一)适用范围
首先,我国以特别条款的形式对获利返还的适用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然而此种规范模式能否满足现实需要?
中国学界对于获利返还进行研究的学者大多主张扩张其适用范围,如王利明主张从独立的债的类型高度构建获利返还请求权,使其适用于侵害人格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情形。〔51〕同前注 〔28〕,第530页。在境外法学界,有法国学者支持以一般条款规定获利返还,因为通过侵害他人权益获利的情形发生在民法各领域。〔52〕Michel Séjean,supra note 18,p.123.德国学者海尔姆斯尝试通过统一标准界定可适用获利返还救济的故意侵权行为,即判断权利人是否本可通过自己实现该权利带来的获利机会而侵权行为额外剥夺了权利人利用此权益获利的机会。〔53〕Tobias Helms,Chapter12:Disgorgement of Profits in German Law,in Ewoud Hondius& AndréJanssen(eds.),Disgorgement of Profits:Gain-based Remedies throughout the World,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5,p.222.
《民法典》第987条关于恶意不当得利人返还责任的规定可否视为我国获利返还的一般条款呢?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从其行文来看,其与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182条第2项存在相似之处,而根据学界通说,此处的 “赔偿损失”解决的仍是不当得利体系内返还范围的确定问题。〔54〕同前注 〔34〕,第272页。举例来说,如果被占有财产的孳息因恶意占有人的故意或过失而发生毁损时,那么除了返还其因占有该财产而获得的利益之外,其同时须赔偿此类可得利益的损失。〔55〕同前注 〔28〕,第471页。由此来看,该条文与获利返还赔偿范围的确定存在差异,立法仍可再进一步,通过明晰的界定避免法条之间可能的竞合。
国内外法学界未就获利返还的适用范围达成共识,因此,我国对此的谨慎态度可以理解。不同于其他民法权益,知识产权的易受侵害以及对其强化保护的必要性、人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损害赔偿的威慑不足足以证成适用获利返还的正当性。〔56〕参见张家勇:《基于得利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规范再造》,载 《法学》2019年第2期。然而,与其以此严格限制获利返还的适用范围,还不如采取开放式列举的规范模式,其后在裁判实践中严格限制扩大解释,由此可为该救济留出适当的发展空间。
(二)构成要件
有学者基于 《侵权责任法》第20条,认为获利返还的构成要件应包括加害行为及其不法性、加害人获利、侵权行为与加害人获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侵权人主观状态的恶意、侵权获利超越了受害人损害。〔57〕参见孙良国:《人身权侵权获益赔偿的构成要件及其适用——兼评 〈侵权责任法草案 (三审稿)〉第20条》,载 《法学》2009年第12期。另可参见前注 〔28〕,第528-529页。亦有部分学者认为获利返还不应当从侵权法的视角进行观察,而应基于不法无因管理或不当得利考量其构成要件。〔58〕同前注 〔8〕;同前注 〔11〕,第229页。
然而,观察角度对获利返还构成要件的影响十分有限,如尽管利润返还请求权在奥地利民法中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但在具体适用中其同样对加害人的过错有所要求。〔59〕同前注 〔15〕,第725页。正如前文所论述,获利返还很难被完全纳入传统民法的任一体系中;在认可其独特性的基础上,笔者将依我国立法传统借助侵权损害赔偿构成要件作为分析框架。
就获利返还的适用,笔者认为应先后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可否适用获利返还请求权,二是返还数额的确定,类似于英国的首先确定民事责任的成立,其后再对救济进行具体评估的实践。〔60〕Graham Virgo,The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Restit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438-439.
侵权法相关条文规范并未对获利返还的构成要件进行异于一般侵权行为的描述,然而在实践当中,由于获利返还救济的独特性,学界对其构成要件主要产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争议:
1.损害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请求获利返还时,权利人对于损害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转化为加害人的获利及其与侵权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并因此产生两个问题:
首先,是否要求受害人证明实际损失? 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部分国家如日本会要求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作为适用获利返还救济的前提。〔61〕参见朱冬:《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救济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123页。笔者认为此种裁判思路有待商榷。举例来说,当媒体擅自报道他人隐私时,多数受害人不会有通过公开此信息用以获利的意图,则此要件将大幅限制获利返还的适用场景。综上,笔者认为获利返还请求不应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前提。
其次,是否也采取侵权法对于一般侵权的证明标准? 笔者认为在审查获利返还请求权是否成立时应采取相对较低的证明标准,即仅要求受害人证明加害人未经其同意或许可即利用其人身权益或知识产权,同时依据一般社会经验,加害人从中获得一定的 “利益”且该获利与被侵害权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62〕此处对于 “利益”应做较为宽泛的解释,如前文提及的瑞士联邦最高法院2006年审结的案件中,法官们明确指出获利并不一定应理解为销售数据的增长,报道使媒体保持其读者数量的长期影响同样可以证成侵权行为导致了媒体的获利。Thomas Kadner Graziano,supra note 20,p.485-488.更高的证明要求可放在确定应返还数额的阶段,并通过举证责任的合理调整使双方当事参与到获利的证明当中。
2.侵权人的过错
对于过错,有的学者主张获利返还应当同样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63〕参见杨立新、林旭霞:《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民法保护》,载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英国法〔64〕同前注 〔15〕,第725页。及《共同参考框架》同样未对此做特别的要求。〔65〕同前注 〔15〕,第714页。而有学者考虑到这一救济的惩罚色彩,认为应当以加害人恶意为构成要件之一。〔66〕同前注 〔56〕,第70页;See Tobias Helms,supra note 53,p.222.此外,亦有学者认为加害人过错应对获利返还的数额而非成立产生影响。〔67〕朱岩认为 “在具有主观过错和客观违法性的加害行为时”,无论利润是否依旧存在,均要求侵权人承担完整的获利返还责任;而在 “仅具有客观违法但无主观过错的情况下”,可在现存侵权获利的范围内进行获利返还。另参见前注 〔13〕。
笔者认为,获利返还针对的是部分情境下传统民法对于不法行为阻吓、预防作用不足的问题,其可能高于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额固然会使其带有 “惩罚”色彩,但获利返还与惩罚性赔偿相异,其确定依赖于可预见的计算标准,〔68〕同前注 〔41〕,第136页。而无需由立法机关通过设定倍数等方式进行 “刻意干预”。
因此,与其在获利返还请求权成立的层面因加害人过错程度低而否定其适用,不如在确定应返还数额时将此作为考量因素之一,如此更符合通过 “动态系统论”进行衡量与调整的合理性。〔69〕[奥地利]海尔穆特·库齐奥:《动态系统论导论》,张玉东译,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此外,在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实践中提高对加害人过错的要求,且加害人过失侵害他人权益以获益的情况相对较少。因此笔者认为,在获利返还请求权成立的层面上,受害人仅需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
综上,就获利返还请求权的成立,受害人仅需证明加害人未经其许可或同意利用其人身权益或知识产权并获益,此行为与加害人获利具有一定关联性,且加害人具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状态。
(三)获利返还数额的确定
1. “侵权获利”的基本概念
加害人从不法行为中获得的全部利益 (或称 “营业收入”)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加害人投入的成本,以及双方投入的生产要素共同结合所产生的全部利润。
根据专利纠纷司法解释,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根据侵权人是否完全以侵权为业而采取销售利润或营业利润两个不同标准。〔7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0条第2款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根据会计学理论,销售利润的数额为与被侵害权益相关商业行为的收入减去相关成本 (包括产品制造、市场推广等费用,以及与之相关的赋税及其他费用)后所得的差额,而营业利润是在此基础上再减去组织管理相关的费用。〔71〕参见张元光:《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笔者认为侵权获利应在销售利润的基础上再进行必要的扣减,但此处扣减的管理、财务费用应与侵权行为具有直接联系,且应由被告承担证明此联系,德国及日本同样采取此实践。〔72〕Tobias Helms,supra note 53,p.225;同前注 〔61〕,第136-137页。侵权获利概念的明确可为之后的讨论提供基础。
2.因果关系的调整:以被侵害权益的作用为基础的类型化区分
学界关于应返还获利的确定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或直接采实际利润而不考虑对侵权人花费的各种成本予以利润补偿,〔73〕其将应返还的非法获利区分为两部分价值,“即原告权益所对应的价值,以及被告投入生产要素所贡献的增量价值”。同前注 〔36〕。或希望对不同要素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准确分割。〔74〕同前注 〔28〕,第539页。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应返还获利与被侵害权益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从实际考虑,仅在极理想的情况下,双方投入的各生产要素对于利润的作用能够被分离得如此精细,在司法实践中做此要求并不现实。〔75〕同前注 〔61〕,第124-125页。美国法官勒尼德·汉德 (Learned Hand)曾就此做出一项经典论述,即技术分摊的问题本质上是无法回答的,任何一项发明都是在以往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此要求对旧知识与新知识的贡献进行数量上的划分通常是不可能的。〔76〕Cincinnati Car Co.V.New York Rapid Transit Corp.,Circuit Court of Appeals,Second Circuit,August 1,1933,66 F.2d 592,19 U.S.P.Q.40.而在人格权侵权领域,这一问题只会更加棘手。
其次,被侵害权益对于加害人获利的影响并不一定是线性的,消费者对于某项产品的购买欲望有可能仅由其几项重点特性所决定,而这种主观欲望更是难以预估的。退一步来说,即便可以通过市场调查等手段得出一个粗略的结果,此类手段的实施也只会成为举证方或者法院难以承受的负担。
再次,若在被侵害权益作为加害人侵权获利行为核心内容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仍对利润进行分摊,则实际上加害人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生产因素的投入获得部分利润,进而相较于侵权前加害人因缺乏核心要素而无法利用手中生产要素获利的情境,实施侵权行为的选择对于加害人来说依旧更有利,则此种处理方式依旧可能成为加害人强行从受害人获得 “许可”的工具。且相较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随意确定利润分割比例的现状,通过类型化区分将一部分无须讨论分摊比例的案件分流出来,可适当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以及法庭的论证成本。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在适用获利返还时对因果关系要求进行适当调整,以使其与该救济的立法目的相契合,并在侵权行为威慑与保障行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77〕参见唐雯:《受益型侵权中获利剥夺的性质及适用——基于获利剥夺请求权独立的思考》,载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笔者认为可通过适当的类型区分实现此点:法官可依据受害人权益对于加害人获利的必要性确定是否考虑加害人所投入生产要素并对获利进行分摊,且受害人应就其被侵害权益的重要性承担举证责任:
(1)若受害人被侵害的权益构成加害人当时获利行为必不可少的 “实质内容”,此时受害人可要求加害人返还全部所获利益而不因加害人投入的生产要素进行分摊,例如未经许可对他人隐私的报道,他人的隐私构成该则报道必不可少的实质内容,则受害人有权就双方投入的生产要素共同结合所产生的全部利润请求返还。另外如在专利权侵权的情况下,若侵害受害人专利权的零件为加害人生产产品的核心零件,则受害人应有权就该产品收入减去加害人投入直接成本之外的全部利润主张返还。
(2)若受害人的侵权利益并非加害人当时获利行为的必要部分,而更多发挥如广告宣传等辅助作用,则在受害人请求返还加害人主观获利时,需要综合考虑各因素对于获利的贡献,对相关利润进行必要分摊再确定应返还数额。此类别的侵权行为主要包括未经许可使用他人肖像、姓名等进行广告宣传、擅自使用他人专利作为生产产品非核心部分等。而关于具体分摊比例的讨论,境内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对此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如日本通过专利技术的“寄与率”对侵权获利进行相应分摊,〔78〕参见管育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判定中专利贡献度问题探讨》,载 《人民司法》2010年第23期。我国亦有根据专家鉴定意见确定专利技术贡献率的实践。〔79〕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5)沪一中民五 (知)初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沪高民三 (知)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此外,还可考虑参考合法获得相关被侵害权益使用权的合理费用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对获利进行分配。
就境外实践来看,此种类型化区分亦有前例。如美国法院在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司法实践发展过程中发展出了 “全部市场价值规则”,即 “当产品的全部价值可归因于专利技术对产品局部的改进时,可以按产品整体的利润计算赔偿。”因此,受害人便首先需要证明被告未经许可利用的专利技术构成侵权产品市场需求的价值核心,此时受害人有权要求因侵权所获得利润的百分百返还;而在无法证明此点的情况下,法院将考虑涉案专利对于侵权产品整体价值的贡献度以确定获利返还的比例。〔80〕参见和育东:《专利侵权赔偿中的技术分摊难题——从美国废除专利侵权 “非法获利”赔偿说起》,载 《法律科学》2009年第3期。此外,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若发现所侵害的专利部分与产品在一般情况下为不可分离的整体的话,同样会要求加害人承担全部利润的返还责任而不考虑专利技术的 “寄与率”问题。〔81〕同前注 〔78〕。
3.应返还数额的提出:举证责任的分配
前文对于侵权获利概念的界定以及获利分摊的区分处理的论述,为应返还数额的确定提供了大致的规则框架。而根据此框架进行具体数额确定时,最重要的便是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如加害人的相关会计记录对于确定侵权获利的数额十分重要。然而,受害人本身并无资格获得此等会计资料,而加害人并不会主动提供对其不利的资料,甚至会在提供该资料时进行调整和选择,这也将使其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从以往的裁判实践来看,传统的举证责任分配使受害人在适用获利返还时承担了过于沉重的举证责任,进而使获利返还的制度目的难以实现,对此进行适当调整无疑是必要的。
实际上,对方当事人掌握案件关键证据,却由于双方处于对立立场上而拒绝积极配合取证的情境并非获利返还诉讼所独有,此时原告可通过证据披露制度请求法院协助,其规范基础为《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2条第1款以及 《新证据规定》的第45至48条。〔82〕《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第112条第1款:“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对上述规则进一步具体化。而在侵权人拒绝提供相关证据时,法院可依据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12条第2款规定要求其承担拒绝提供证据的不利后果,如在 “本田诉力帆专利权侵权案”中,力帆公司便因其拒绝提供涉案产品相关财务数据而承担了对其不利的赔偿数额确定方式。〔8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2条第2款:“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需要明确的是,在请求证据披露的情况下,原告依旧承担着证明加害人获利数额的举证责任。即便被告拒绝配合,原告仍需要通过相关信息对被告的侵权获利进行合理估算,这些信息包括合同价格、同类产品价格、行业平均利润率等。而在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相关材料或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况下,法院便可基于证明妨害,依据原告的主张及所提供证据确定侵权获利。与之相对,在被告配合提供相关材料的情况下,被告可主张不存在侵权获益或者侵权获益低于案涉权益的合理使用费,也可对原告的计算方法提出质疑并就与侵权行为直接相关的成本费用提出扣减。
在此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下,双方有望在相同证据基础上对侵权获利数额进行计算,并随后就应返还数额的具体确定进行法庭辩论。
对于原告来说,其应当对被侵害权益在侵权获利行为中发挥核心作用承担举证责任,该证明责任的完成意味着侵权获利不再在双方之间进行进一步的分摊;而若因加害人经营方式等因素,由此计算出来的侵权获利较低的话,原告可以请求通过客观获益的方式计算应返还数额,即应支付的许可费用。司法实践应支持原告在获得充分信息的基础上选择对的救济方式。〔84〕See Graham Virgo,supra note 60,p.438.
对于被告来说,其应当证明的是在可进行利润分摊的情况下,自身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对于利润的作用 (如人力资源、生产设备、营销渠道、其他零件费用等)以确定分摊比例,被告承担分摊比例的举证责任意味着推定侵权获利全部来源于被侵害权益,若加害人无法证明其他利润形成因素的作用,则侵权获利即为应返还的数额。此种安排不仅是由于加害人对侵权获利信息的掌控,同时也能更好地起到遏制侵权行为的作用。〔85〕同前注 〔61〕,第125-127页。此外,将分摊比例交由当事人双方举证证明能够使法院从因果关系及分摊比例确定的泥沼中脱身,同时也适当限制法官在这一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更突出其中立裁判的角色。〔86〕同前注 〔77〕。
4.应返还数额的确定:基于动态平衡的调整
对于法院来说,在前述双方当事人举证及法庭辩论的基础上,其还应综合考虑各因素对最终数额进行确定。无论当事人双方如何对应返还数额进行证明,侵权行为与侵权获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得到十分清晰的证明,各生产要素的贡献程度更是难以被完全量化,因此前文所述仅能为当事人双方的举证提供框架并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的限制,而法官始终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在个案中实现利益平衡。此立场同样体现于 《瑞士债法典》的相关条文中。〔87〕《瑞士民法典》第五编债编第42条第2款修正案 (2017年4月1日)规定:“如果损失或损害的确切价值难以被精确计算,法院应当运用其裁量权,根据事件的正常进程以及受损方所采取的措施来予以确定”。
加害人的过错程度便应当在这一阶段被法官纳入考量因素的范畴当中。虽然部分学者依旧坚持侵权损害赔偿的完全赔偿原则,认为加害人的主观状态不应对损害赔偿数额的界定有所影响,〔88〕参见程啸:《侵权行为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0 页。但完全赔偿原则本身已引发越来越多学者的反思,〔89〕参见王磊:《完全赔偿原则与侵权损害赔偿之反思与构筑》,载 《法律科学》2019年第4期;郑晓剑:《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之检讨》,载 《法学》2017年第12期。且较之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获利返还制度因其对于侵权法预防功能的强调而更具特殊性;再者,我国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考虑加害人主观状态,如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0条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因素之一,又如北京高院在相关裁判指导文件中明确指出可根据侵权人的主观恶意调整获利返还的计算基础。〔90〕《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8.6节: “通常依据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润计算‘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若在案证据证明侵权人存在明显侵权恶意、侵权后果严重的,可以直接依据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营业收入计算其违法所得。”
综上所述,在双方举证的被侵害权益对于获利影响、加害人所投入生产要素的影响、行业的一般情况等基础上,法官可综合考量加害人过错、侵权行为对于加害人未来运营的积极影响等因素,依据动态平衡的思想以及侵权责任制度的价值框架,最终在个案中确定应返还数额。
(四)结论
通信技术难以阻挡的发展趋势也使对知识产权、人格权等无形权益的侵害难度不断降低,获利返还制度作为一种具有更强威慑和阻吓作用的救济方式对于此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效果,这也是为何在国际范围内获利返还制度频繁引发各国学者讨论的原因。
在此背景下,《民法典》第1182条对于 《侵权责任法》第20条在措辞行文上的调整,无疑是具有进步之处的,其将获利返还制度从死板僵化的适用顺序中解放出来,赋予受害人以选择权,同时保留了法院根据审理情况确定应返还数额的适当裁量权,切实地提高了获利返还这一救济方式在侵权法中的地位。而考虑到 《民法典》在民法体系中的基础作用,这一进步也有望成为侵权法领域获利返还救济的基础规则之一。同时,这一编纂方式也与 《共同参考框架》等示范法律文本的规定保持一致,与国际民法学发展的大趋势相契合。
但同时,亦有学者不希望获利返还制度的进步仅止于此,比如王利明对于以独立的债的类型构建获利返还制度的呼吁,或者前文提到的学者们对扩大获利返还救济适用范围的期望,或者通过引入不法无因管理等制度以将获利返还纳入传统民法体系的建议,由此可见学界在获利返还这一问题上离达成共识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笔者认为,就 《民法典》对于适用范围的限制而言,立法者们谨慎的态度可以理解,即便这种态度可能被解读为过于保守。笔者亦在前文讨论过通过开放式列举的方式适当保留获利返还制度开放性的处理,毕竟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法典》为保持其庄重及稳定不会有过多的修改,因此保证 《民法典》一定程度上的先进性是必要的。然而,就现状来看,我国现有民法体系所采取的特别条款规定模式也已基本覆盖了获利返还可能适用的领域,如除侵权法之外的信托法、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领域。而就获利返还救济并未覆盖的财产权侵权领域,虽有学者提议可在司法实践中对不当得利进行一定扩展以达成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平等保护,〔91〕《中欧民法典国际研讨会实录 (四)》(吴至诚助理教授发言),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s://mp.weixin.qq.com/s/o2-I_xPf AJqejZTY5AECeQ。但同样可以基于权利区分保护的理论暂不在侵犯财产权的语境下考虑获利返还救济,〔92〕和育东指出应 “按照物权、知识产权、财产性人身权的顺序,越靠后的权益越适宜适用非法获利赔偿制度”。同前注 〔36〕。这也并不应被视为此种安排的漏洞而仅是立法政策上对现实状况进行考虑后得出的结论。再者,此种安排的合理性也可体现于前文所论证的获利返还救济正当性基础的多样性上:这一救济本质上很难为单一法律领域的一般条款所容纳。
而即便 《民法典》未来确实需要根据现实情况扩张获利返还救济的适用范围,其仍可以通过编纂特别法规乃至司法实践的发展等方式得到扩展:中国立法者对于 《民法典》的期望是让其成为如同 《法国民法典》一般 “活着的法典”;毕竟,法典的成功颁行仅是法律发展的中间阶段,法律的发展并未毕其功于一役,恰如德国民法学家温德莎德所谦逊指出的:“一部法典只是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时刻……它只是洪流中的一波涟漪而已”。〔93〕Reinhard Zimmermann,Codification:The Civilian Experience Reconsidered on the Eve of a Common European Sales Law,p.379.法典的生命力更取决于未来的司法适用进程。
而对于获利返还制度的体系位置问题,立法者选择将其置于侵权责任编当中,亦有不少学者争论这种体系安排是否合理。前文业已论述获利返还制度本质上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以及侵权损害赔偿等传统民法体系之间的差异,因此,从根本上来看,获利返还请求权很难被完全归于民法任一传统体系当中,而最多只能作为侵权法、不当得利法、无因管理法任一部分的延长或作为独立的责任基础存在,库奇奥认为获利返还制度处在侵权责任法与不当得利法两个法律领域都未调整的中间过渡地带的观点便明确表明了此点。〔94〕同前注 〔35〕,海尔姆特·库奇奥书,第45页。目前情况下,将获利返还单独提取出来作为一个章节的条件并不成熟,至少在适用范围上会面临如何对落入保护范围的权益进行统一定义的困难。〔95〕温里布便曾对此进行尝试,其认为该救济应适用于具有对世性以及可处分性的权利。但即便如此,他也承认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无法被此定义所囊括。Ernest J.Weinrib,supra note 47,p.125-146.因此,既然将获利返还纳入任一体系均只能作为例外存在,那么这一问题的讨论本身便失去实质意义。与之相比,如何构建获利返还的适用模式以使该制度真正在司法实践当中发挥其作用的讨论更具必要性,和育东提出的通过明确获利返还制度正当性和基本原则的方式讨论该制度体系的构建便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这也是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实现的价值之一。
——以《民法典》第1182条前半段规定为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