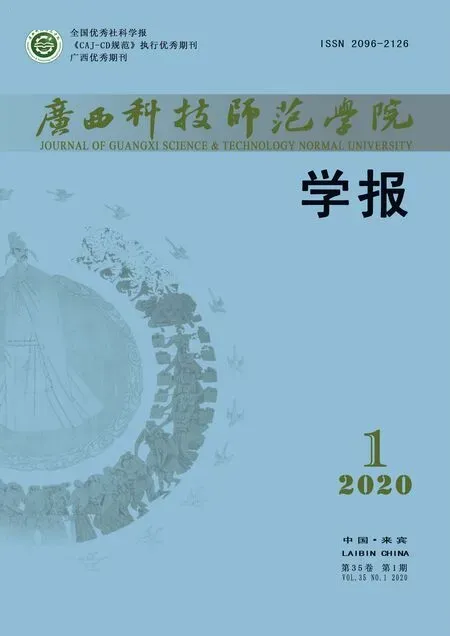论智慧法院建设中的新型法治人才培养
李忠颖,林 双
(温州大学法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信息技术发展也日新月异,而大数据的有效应用,使得各行各业出现了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标志的革新浪潮,其中裁判体制也不例外。智能裁判是指在裁判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裁判效率、准确率的新型态的裁判方式。其存在于多个领域,例如人工智能辅助体育赛事的裁判、人工智能辅助交通违规的判定等。以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为例,智慧法院作为智能裁判实践层面的表现形式之一,于2016年被列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中阐明其含义:“智慧法院是人民法院充分利用先进信息化系统,支持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实现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组织、建设和运行形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作为智慧法院建设的核心部分,前者为智能法院建设提供数据量支撑,后者则利用数据形成智能分析、预测、预警和决策等功能。而智慧法院再利用大数据实现对当前形势科学判断和对未来形势准确预判,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依据[1]。
一、智能裁判与智慧法院的建设困境
(一)法治人才培育的缺失
部分学者认为建设智慧法院依赖于先进的信息化系统,因此偏向于研究信息化系统在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的利弊及如何适用调整的问题。然而,智慧法院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任素贤庭长认为:“智慧法院的本质是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是人的智能现代化,而非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替代人的智能。”[2]正如哲学中所说,思想的载体必须是人脑,而不是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所以,从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这一前提论证,即可得出裁判的主体必须是人的结论。
从目前我国传统法治人才培养存在诸多弊端的现状中,可窥视出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仍然缺少对法治人才培育的重视。首先,是缺乏对学生法治思维的培育,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难以形成独立的裁判思维。传统法学教育以学院式的课堂讲授为主,老师作为课堂的核心,学生大多作为被动接受知识的一方,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传统课堂讲授的最大特点之一就在于学生专注于书本的知识,以是否掌握书本内容为考核重点,而没有专注于学生法治思维的培养。其次,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法治人才的培养都不能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接轨。如中国政法大学,其设有法学实验班(六年学制,本硕连读)、卓越人才培养班、学术型的本科班、互联网智慧法学班等不同类型的培养模式,但互联网智慧法学学习仅仅将其作为特色课程,而不是法学的普及课程。又例如,近年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将优势特色学科方向确定为“人工智能+法学”,秉承学科建设带动教学教育的理念,同步开启探索未来法治人才培养转型,带领学生深度体验真实案件调解与互联网案件审理新挑战。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将“人工智能+法学”设置为优势特色学科是借助其与杭州互联网法院合作的平台优势,借助浙江电子商务与大数据科技发展的地利优势,依托互联网法院线上审判与法学院多端口接入视频教室的设备条件。但对于当前我国大多数的高校而言没有上述的条件支持,也就难以为学生提供“互联网+”法治人才培养的平台。
(二)运用初级人工智能存在风险
信息系统的智能性并不能论证其辅助案件裁判的正确性,无论是多发达的人工智能,在使用上都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人工智能与法律机制的结合,是法律逻辑从文字符号向数字代码的转换。这意味着司法裁判的核心特点必然表现为:依赖于机器代码来定义和计算人们需要遵守的规则和违反规则的结果[3]。况且现今作为人工智能开发基础的法律数据基本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裁判文书,但上网的裁判文书数量可能只有审结案件50%[4]。左卫民教授认为,我国智慧法院的欠缺原因之一就在于法律领域并不拥优质且海量的法律数据资源且法律界并未形成合适且高效的大数据算法[5]。以“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案”为例,在此案中,被告埃里克·卢米斯(Eric Loomis)对自己参与飞车射杀的罪名供认不讳。在被关押期间,卢米斯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的答案输入到了COMPAS(这是由一家私人持股公司开发的一款风险评估工具,为威斯康星州惩戒部门所使用)。主审法官最终对卢米斯判处了较长刑期,主要原因是该黑盒子风险评估工具对被告的评估结果是“高风险”。被告卢米斯对这个判决提出了强烈质疑,理由是该评估过程过于隐匿。该案的主要争议即为风险评估系统给出的评估结果是否具有权威性。不过,法院发布意见表明其试图缓和在当前审判中对大数据算法风险评估的热情,向法官提供判刑前调查报告的同时,也提供“书面建议”,提醒裁判法官这些评估的危险性,但这种警示和建议不太可能引起法官对该风险评估提出有意义的质疑,因为它忽视了法官缺乏对风险评估工具中自身风险予以评估的能力[6]。尽管后来最高法院认为该评估不侵犯被告的正当程序权利,但该案仍旧给人们一个启示:当裁判者无法对于辅助系统给出的评估报告以权威性判断时,该裁判就有不被服从的风险。
(三)存在裁判者迷信人工智能的可能
辅助系统过于智能的话,将会产生裁判者过于迷信的问题,裁判者会不可避免的陷入锚定效应,即是指在不确定的情境下,判断与决策的结果或目标值向初始信息或初始值即“锚”的方向过度接近而产生估计偏差的现象[7]。例如本文提及的COMPAS系统在对具体的犯罪行为进行评估时,因为犯罪嫌疑人是男性,所以认定其风险为高,而因为犯罪嫌疑人是女性由此认定为其犯罪风险低,这种评估事实上真实存在但却与我们审判原理相背离,审判时要注重一个人在具体案件中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以“性别”来做区分。即便大数据所呈现的是如此的计算结果,也应当交由法官依据个案来做相关的考虑,一旦法官欠缺评估辅助工具的能力时,其有极大概率采用该评估结果,这就是具体案件中的锚定效应。但具体的案件应当具体分析,当前人工智能无法在这一方面做到专业的地步,因此辅助系统存在的风险就需要信息化的法治复合型人才来掌控。司法裁判作为一项经验性和价值性兼具的复杂作业,应当坚持法官的主体性和裁判的独立性,避免“智能主义”与“数据主义”对法官自由意志的侵蚀[6]。
二、新型法治人才培养进路
要建成智慧法院,必须倚赖法治人才的参与,目前我们还没有提出一套比较有系统性的培养人工智能法律的方案[5]。上文所述种种困境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智慧法院的建设乃至我国智能裁判的发展。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原有的各学科之间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各学科之间的融合逐步深化,因此建设智慧法院必不可少的就是会操作、应用智能系统的法治人才,能够根据快速更新的智能信息系统进行自我知识的更新。此外,综合世界高等教育的考虑,未来的人才培养标准还应具有创新性与国际化等相关特点[8]。
综上,根据我国目前信息化发展的进程结合法治人才的特点,可以得出新型的法治人才是既能掌握法学理论又有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做支撑的复合型的法治人才[9]。可预见的是,未来在我国的司法实务界,对这种“互联网+法律”人才的需求量将非常庞大,我国应设计专门的人工智能学院或研究院来系统性的培养相关人才。目前专门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的学院还很少,可列举的如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学院[1]。而未来在智慧法院的招聘考试中,可另外再增加关于“互联网+”的相关科目,让有志于进入智慧法院的准法官都能储备有“互联网+”的相关基础知识。有了复合型的法治人才,配合“高精尖”的智能信息系统,以“人”为核心,以“系统”为辅助,构建起智慧法院的核心体系。如此,智慧法院服务于人工办案的宗旨将得到体现,智慧法院的建设进程将会不断加快,并且其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也会得到相应的解决。
当前我国运用在司法实务上的仍为初级人工智能,尚未完全交由人工智能依据大数据运算进行审判,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多是比较初级的庭审语音识别、证据校验、电子卷宗生成等初阶技术性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运作,未来则会逐渐的往辅助量刑智能辅助审判系统迈进。因此,未来我国的智慧法院所需要的人,还应具备综合处理实践问题的能力,须通过“法学+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智能应用法学学习,让法律人明确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技术构造[10],才能有效与正确地判读与应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所给的计算信息。另外,法律数据资源必须再经过一段长期时间的积累,才能聚集信息成为充分的数据库[12],同时,还必须等待诸多的法律科技公司,开发更多的法律知识图谱来更为高效地构建法律人工智能算法,形成符合我国法院法官判案思考的裁判模型,由此作出裁判结果建议时,才能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