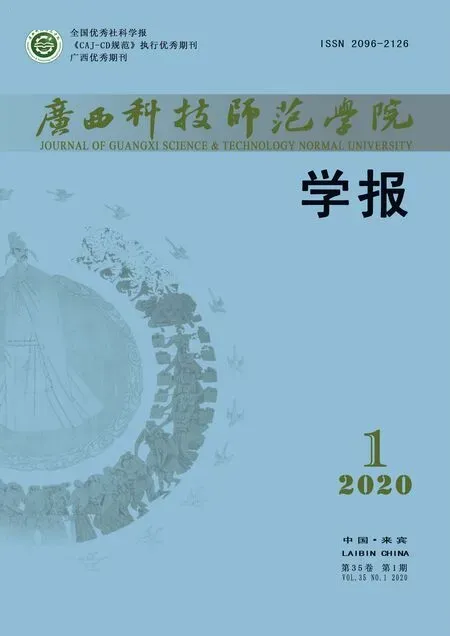论孟子“浩然之气”的内化及其“德性”显现
聂 磊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
孟子“浩然之气”最早见于《孟子·公孙丑上》。有学者认为其思想渊源来自于稷下黄老的“精气说”[1],我们认为“浩然之气”是孟子的独创。对孟子“浩然之气”的研究历来为学者所看重。以往的研究者大都从孟子心性论的角度出发,重点阐释心性的关系;但却忽视了“浩然之气”的内在逻辑及其“德性”显现。因此,对“浩然之气”的内化及其“德性”显现的认识,仍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本文拟从孟子“浩然之气”的内涵、孟子“浩然之气”内化的“内在逻辑”、孟子“浩然之气”的“德性”显现三个方面进一步阐释孟子的“浩然之气”。
一、孟子“浩然之气”的内涵
孟子认为,“浩然之气”的描述“难言也”,即“浩然之气”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描述的。孟子又解释说,“浩然之气”作为一种气,他是“至大至刚”,用正直去培养它且不加损害,则会充盈于天地之间,作为一种气它是与义和道相配的。孟子说:“浩然之气”的产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2]215。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培养“义”之“行”,即如何践行“义”。
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有着什么内涵呢?孟子从“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和“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两个方面作出回答,即分别从气的形态特征和气的内涵特征来回答“何谓浩然之气”。依照孟子的回答,我们可以探究“浩然之气”是属于“至大至刚”的这种物质之气或者说是自然形态之气,还是属于一种精神状态的气象之气呢?从孟子自己的回答来看,“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2]215,孟子认为用正直去培养它,且不加损害,则会充盈于天地之间。对于能够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气,是什么样的气呢?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的气象之气,是一种精神境界达到某一高度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气象。这样的气象是脱离不了客观物质之气的,是具有一定的根源性的;这样的气象是客观存在的,是能够为别人所感知的。如孟子见梁惠王所说“望之不似人君”;黄庭坚称赞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程颐评价程颢“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入其人也,如时雨之润”。冯友兰第一次见蔡元培先生“光风霁月的气象,整个屋子都是这种气”[3]。这些都可以说明气作为一种气象时,是可以感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浩然之气”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并且是能够为人所感觉到的主观精神状态的气象之气。
(一)“浩然之气”的内涵
“浩然之气”是内在于主体的还是外在于主体的呢?我们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浩然之气”作为一种主观精神状态时或者说作为人生境界的气象之气时是内在于主体的。当“浩然之气”这种气象又能够为我们感知到并且去追求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时,这时“浩然之气”可以说是外在于主体的。然而,对“浩然之气”的追求是一种过程,无论是内在于主体还是外在于主体的,都是不能孤立的去谈它是否是内在于主体或外在于主体。当二者同时显现时则是一种过程,我们对人生境界或精神状态的追求也不能静止的孤立的看问题。
(二)“浩然之气”的特征
从孟子的自我回答中,“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在这段表述中,出现了两个“其为气也”。孟子对“浩然之气”内涵的解释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浩然之气”的形态“至大至刚”以及养成之后的状态“充塞于天地之间”,来说明的。第二个方面孟子是从“浩然之气”的本质内容“配义与道”来解释的。“至大至刚”是从“浩然之气”的广度和深度来解释的,具有坚毅、不屈不挠、正直的品质特点,孟子无形之中把“浩然之气”升华了,同时也把“浩然之气”内化了。孟子由其形态、状态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扩充到品质、内涵的升华,使得“浩然之气”得以内化。“配义与道”用来具体阐释“浩然之气”的内在要求,也可以说是本质内容。“浩然之气”要“合于道”“合于义”,与道与义相符合。朱熹对此解释为“义者,人心之制裁。道者,天理之自然”[2]215,“言人能养此,气则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2]215-216。由此,从道的规律性与义的目的性来解释“配义与道”更加符合孟子的本意。朱熹对“配义与道”的解释虽然强调人心的约束性和天理的至高性,但其落脚点仍然是“行”,最后才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性,也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道与义的契合,在行为上符合“义”的要求,同时也符合“道”的客观规律。
作为客观规律的“道”和主观追求的“义”二者的统一性,正是孟子所要阐释的“浩然之气”,因此孟子说“配义与道”。同时孟子也提出“舍生取义”用来说明“浩然之气”,是孟子的“浩然之气”的最高表现,也是对“义与道”最高践行的表现。这是“浩然之气”在人格精神上的体现,也正是孟子所要追求的“浩然之气”。蔡元培这样说“浩然之气”:“一言以蔽之,仁义之功用而已”[4],这句话可以说是对“浩然之气”的本质进行了说明。由此可以理解为“浩然之气”是“仁”的外化。
二、孟子“浩然之气”内化的“内在逻辑”
孟子“浩然之气”内化的“内在逻辑”是在论证“浩然之气”与勇气的关系中逐步显现的,“浩然之气”的内化是在“浩然之气”内涵的基础上逐步升华的。我们可以从孟子与公孙丑的对话中缕析出关于“养勇”的方法,进而论述孟子与告子观点的根本区别;又从二者对于“养勇”方法的分歧入手,从而提出“不动心”的区分,进而论述孟子的“浩然之气”是如何内化的。在下文中将具体分析“浩然之气”内化的“内在逻辑”。
孟子与公孙丑的对话是分析告子和孟子分歧的重要材料。我们从二者论述“不动心”的差别以及他们二人是如何看待“不动心”就可得知二人的观点。通过分析对话,我们认为告子的“不动心”是“不得于言,无求于心,不得于心,无求于气”“持其志,无暴其气”的[2]213。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告子认为“不动心”的方法是“持志”,他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2]213。这虽是孟子所说,但当公孙丑问及告子的不动心和老师孟子的不动心有什么区别时,我们可以看作是告子的“不动心”的旨意。告子认为“不动心”不需要求助于气,只需要强制其心,使心不动就可以达到“不动心”。这样的“不动心”与孟子所要达到的“不动心”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告子提出的“不动心”是带有被动色彩的,孟子并不赞成这样的“不动心”,因此,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也是孟子对“不动心”做出的进一步解释,同时也是孟子对告子的正面回应。告子的“不动心”并不是人所主动涵养,而是被动的涵养的,受到某种压迫时的反应。这样的“浩然之气”并不是主动的涵养,更不是以道和义作为最高原则的气。本质上的区别在于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的背后有着道与义。
孟子将道与义作为“浩然之气”的重要支撑,是孟子将“浩然之气”内化的重要一步。孟子以道与义作为“浩然之气”内化的逻辑前提,是孟子对心性学的贡献。从孟子与公孙丑讨论“不动心”的方法,提出“养勇士”的方法再到“气”的提出,最后孟子提出“浩然之气”来对“不动心”作出定论式的回答,这都是孟子“浩然之气”内化的内在逻辑。那么孟子如何来对待勇气与“浩然之气”呢?这样的“气”与“浩然之气”是否有相同的地方呢?从气的性质状态来,二者都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的气象之气,但是我们是否就可以因此说“浩然之气”是勇气呢?从孟子的回答看是不可以的。虽然在性质上相同,但在本质上却不同。“浩然之气”的本质在于其“浩然”,在于其“塞于天地之间”。可以理解为“浩然之气”是人与天地的关系,换句话就是人与宇宙的关系。孟子在无形之中已把“浩然之气”升华了,升华到超越普通意义上人与人的关系。在境界上与孟施舍的“守气之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浩然之气”是可以使人在整个宇宙之中感到无所畏惧,进而与天地万物相交融,超越于天地万物又复归于天地万物,最终回归到本然之状态。孟施舍的“守气之气”是勇士之气,是人在战斗之中或侠客之中的一种勇气,是无法立于天地之间的气。或者说,是具有一种莽夫之勇的气。这两种“气”有着本质差别,上文所说的“不动心”的本质差别在于“浩然之气”的内在道义。这样的“气”与“浩然之气”都是心的外化显现。但是两者的内在支撑不一样,这才是最大的本质差别。在《论语·述而》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2]164这样的勇气孔子也是极为不赞成的。这样的气看似是“浩然之气”实则匹夫之勇,没有智慧可言。孟施舍的“守气之气”更向是暴虎冯河之勇气,“浩然之气”与孟施舍的“守气之气”在本质上的差别则是“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义”是两者本质的差别,也决定了境界层次上的高低差别。内在道义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二者的本质差别就在于是否符合道义。孟子“浩然之气”内化的内在逻辑经过道义的升华,是具有了道和义的内在原则,并以此为前提作为支撑。因此,孟子“浩然之气”是道与义的升华,“浩然之气”可以充斥着整个天地之间。
三、孟子“浩然之气”的“德性”显现
“浩然之气”经过内化之后必然有所显现,孟子认为“浩然之气”的显现就是“德性”的显现。“德性”一词最早见于《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2]36在《说文解字》对德解释为:“德,升也”[5]。这里可以看出德的本意是升华,升华到一个高度之上的东西。东汉郑玄认为德性是性至诚的体现,德性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本性的自然流露。“德性”是如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呢?“浩然之气”与“德性”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孟子养成“浩然之气”的途径是我们探究“德性”显现的重要方法。
孟子从三个方面具体阐释养成“浩然之气”的途径。首先是“反求诸己”。孟子认为当“爱人”“治人”“礼人”时都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结果,这时就需要“反求诸己”。通过反思自我,从“反求诸己”来养“浩然之气”。其次是“求其放心”。孟子把“仁”比作“心”,把“义”比作“路”。孟子通过对人心的比喻提出“求其放心”。孟子认为“养气在于养心”,他是把仁义的作为追求,把本心作为道义。最后是“存夜气”。孟子认为“夜气”是觉知人的良知。孟子所说的“夜气”其实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夜气”即人心的良知。孟子认为把灵魂深处的“良知良能”培养壮大,渐渐养成“浩然之气”的气象,才能养成“浩然之气”的人格。
“浩然之气”养成的途径是“反求诸己”“求其放心”“存夜气”。养成“浩然之气”有着如何显现呢?孟子认为“浩然之气”内化的显现就是“德性”。“德性”就是“浩然之气”内化于心之后的外化于行的显现。这样的显现是一种升华的内在的表现,把“浩然之气”升华内化为一种内在人格。我们通过对“浩然之气”的养成,来提升出一种内在德性化的气质。“德性”不是简单的内在品德修养,而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如孟子所言:“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2]246这样的内在自我约束不依靠别人,也不是由外界来强迫我要达到某种高度修养,而是一种自我内在的“德性”约束。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德性,谓性之至诚者也”,“至诚”这是一种内求的品性,外在能让你达到“至诚”吗?答案是否定的。孔子也明确提到:“我欲仁斯仁至矣”[2]134,“‘仁’是一种思想,而能具体实践‘仁’的人就是仁者”[6],强调这样一种内在性,内在的自我追求是不能由外“烁我”的,只能依靠自己内在才能达到由“行仁义”到“由仁义行”的内在自我“德性”的自我完满寻求。
追溯上文“浩然之气”的内涵可知,“浩然之气”是一种主观精神之气,是一种抽象的外在于人而又内在于人的气质。“浩然之气”既高于个体的人,又由个体的人所表现,同时具有超越性。孟子“浩然之气”从本质上来说是儒家修养论,落脚点是人的“德性”。孟子说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2]265孟子通过对“诚”的分析提出“诚”是天的法则,做到“诚”是人的法则。“诚”的中心内容是“善”,“思诚”的中心内容是“明乎善”,也就是“尽心”,也就是恢复和保持“良知”“良能”。孟子从“诚”和“思诚”分析,进而达到“尽心知性”。上文提到“德性,谓性之至诚者也”,“德性”是达到“善”的高度时所显现出来的。孟子认为“‘诚’是真实无妄的,是天道的运行规律,又是一种道德体验的状态,是对本心良知的最终根源——对‘天’的一种虔诚、敬畏之情”[7]。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诚”是一种对本心良知的追求,与我们所说的“德性”有着深切的关系,可以说“德性”则是“至诚”的显现,孟子“浩然之气”所要达到的状态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德性”。“浩然之气”是由“思诚”进而“明乎善”所显现出来的,并最终又回到浩然之气本身,显现为“德性”。
总而述之,在笔者看来,孟子“浩然之气”内化是通过对浩然之气的本质即“仁”的外化功用的阐释来说明的。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道义所生,他将道义作为内化的内在逻辑。同时,他指出“浩然之气”的仁义本质和“德性”归属。孟子通过“诚”把“浩然之气”与“德性”联系到一起,他认为“诚”是“天之道”,“德性”是“性之至诚”的显现。通过对“诚”的追求达到“浩然之气”,并最终显现为“德性”。这个过程既是“浩然之气”内化为“德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德性”显现的过程。
——论阳明学派对告子思想的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