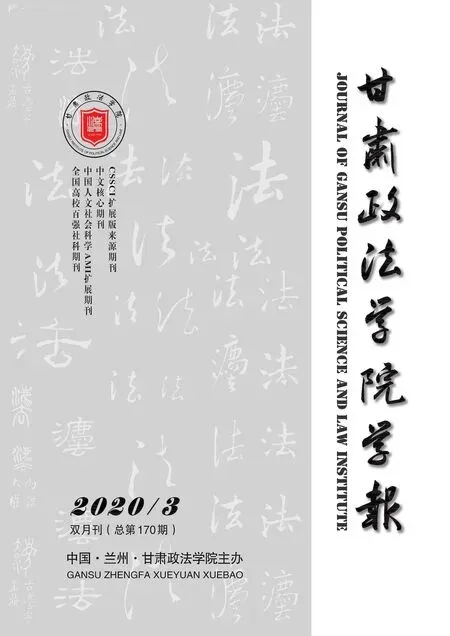对待给付风险与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夏 平
一、问题的提出:对待给付风险负担一般规则是否没落
比较法上违约责任体系构造的立法方案,多见于三处,即以不履行的原因为划分基础,将债务不履行分为迟延履行、履行不能等给付障碍类型,(1)1930年施行的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27条规定:“债务人不为给付或不为完全给付者,债权人得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得请求损害赔偿。”这一规定并未遵从《德国民法典》关于给付不能与给付迟延的二分法,而是增加了“不完全给付”作为第三种债务给付障碍的形态。将不完全给付作为除给付不能、履行迟延之外的第三种给付障碍原因是学术文献中的误读。参见陈自强:《不完全履行与不完全给付》,载《北航法律评论》2013年第1辑。此为原因路径。以不履行的效果为划分基础,一部分规定损害赔偿请求权,另一部分规定合同解除权等,此可称为救济路径。(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版,第477页。典型的采救济路径的国际契约法文件有《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采原因路径的契约法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除此以外,还有兼采两种路径的混合进路模式的法律文件,如《联合国销售合同公约》(CISG)、《德国民法典》。所谓混合进路体系是在《合同法》中规定一般违约责任抽象规定的同时,又根据给付障碍的原因再次进行二级分类,从而使违约责任体系走混合进路体系。在违约责任体系构造上,我国《合同法》原则上系以法律效果为核心的救济路径。(3)解亘:《我国合同拘束力理论的重构》,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这体现在《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了义务违反类型的上位概念,即通过“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统一了违约责任类型。那么,有疑问的是,我国《合同法》违约责任体系是否完全抛弃了以原因路径为基础的给付障碍类型而单纯采救济路径,抑或采混合进路模式。
在原因路径下,履行不能制度系给付障碍法的核心。然而,在救济路径下,其已不再是独立的损害赔偿范畴,而仅是义务侵害下统一损害赔偿责任中的一种从属情形。持混合进路的学者认为,给付不能是一个在逻辑上为必要的给付障碍法范畴,全然没有给付不能,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4)杜景林、卢谌:《给付不能的基本问题及体系建构》,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6期。但因为其论据仅局限于履行请求权界限问题,而强制履行也可以纳入违约救济中,(5)王洪亮教授认为,继续履行请求权就是债的强制履行力,而非违约责任,但其具有违约救济的效果。参见王洪亮:《强制履行请求权的性质及行使》,载《法学》2012年第1期;韩世远教授认为,继续履行也是违约责任,不仅债权人可以主张,债务人也可以主张继续履行以排除债权人的其他违约救济方式。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760—761页。故而亦有学者反对混合进路。支持单纯救济路径的学者认为,债务不履行制度当中,原本由德国法上的“履行不能”所承担的功能,一部分被统一到“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当中去,一部分被融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中,还有一部分被不可抗力所替代。因此,“不能履行”仅仅承担着较为次要的功能(第110条第1项排除实际履行请求权)。(6)柯伟才:《我国合同法上的“不能履行”——兼论我国合同法的债务不履行形态体系》,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由此产生的疑问是,原因路径中履行不能所承担的制度功能能否全然被现有“救济路径下的给付障碍法”所吸收?
功能是一切比较法的出发点和基础。拉贝尔曾说:“如果我们希望在比较各个制度的特征中一起说明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我们就必须首先认识各个法律秩序之间的内部关系。”(7)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77—79页。根据德国给付障碍法中的二重理念,债之效力分为原给付义务请求权和次给付义务损害赔偿请求权。原因路径下的违约责任体系处理履行不能时,由风险负担规则(8)普通法上将风险负担中的风险分为物之风险(periculum rei)及债权之风险(periculum obligationis),基于在后者无法辨识其到底指给付风险或对价风险,已为德国学者所扬弃。参见Fikentscher, Schuldrecht, 7.Aufl., 1985,§67/III.处理原给付义务消灭问题。质言之,给付风险负担规则处理给付义务的消灭问题,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处理对待给付义务的消灭问题。给付风险与对待给付风险均属于给付不能范畴,致力于在履行不能后,恢复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平衡。(9)Vgl.Westermann in:Erman,BGB,15.Auf.2017,§326Rn.1.遗憾的是,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履行不能时对待给付风险负担一般规则。其原因在于,我国《合同法》受到《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影响,加之学者主张《合同法》第107条的违约责任应采严格责任原则。而无过错责任体系下的契约责任不存在给付义务与损害赔偿义务二元体系。履行不能不会导致原给付义务的自动消灭,只会因“不履行合同义务”引起替代损害赔偿违约责任的产生。因此,契约理论若不在区分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履行不能和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履行不能,那么风险负担制度的适用领域也就彻底丧失了。(10)解亘:《日本契约拘束力理论的嬗变》,载《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或者在不以过错乃至于归责事由为归责原因的法律体系中,若出现以归责与否作为风险分配基准,乃体系违反。(11)陈自强:《民法典草案违约归责原则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因此,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是否没落,取决于我国的违约责任体系的构造模式。而比较一个法律制度应从制度体系出发研究其制度背后的思想与功能。是故,仅在明晰制度之间的内部关系后,才可讨论功能的可替代性问题。在合同法中,履行不能制度系确保合同各方利益均衡的风险分配制度。现有解除制度与损害赔偿规则能否均衡各方利益,应是理论界就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是否消亡议题的关键所在。
就履行不能中的对待给付风险所承担的制度功能,能否被现有制度所替代。管见以为,此处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所处理的对待给付义务消灭问题可否为救济路径下的解除规则所替代;二是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在我国违约责任体系下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即可明晰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是消解在单纯的救济体系路径中,抑或隐含在混合进路里。
二、解除规则能否替代履行不能中的对待给付风险
(一)对待给付风险中的自动免除规则
自动免除规则也称当然免除,是指通过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来免除对待给付义务。其背后的法理是双务合同中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的牵连性理论。《德国民法典》第275条和第326条第1款是关于履行不能时给付义务和对待给付义务的自动免除规则(Ipso—iure—Erlöschen),该规则并无合同自动消灭之意。(12)Vgl.BeckOK BGB/H.Schmidt, 50.Ed.1.5.2019, BGB§326 Rn.7.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的给付不能规则(第225条和第266条)同样也只是规定给付不能是给付义务和对待给付义务的法定消灭事由。但我国学者在讨论履行不能或风险负担时有两个误区,一是将自动免除规则理解为合同自动消灭;(13)韩世远教授曾建议在立法论通过自动解除的方式结束合同关系。将客观原因履行不能视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既然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这时让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从反面讲是赋予其权利保持合同效力,而这样做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故自立法论而言,通过自动解除的方式结束合同关系,或许更好。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648—649页。崔建远教授则在其文中对此反驳认为给付义务被排除,合同自动地、当然地归于消灭的后果会导致合同处理没有章法。参见崔建远:《风险负担规则之完善》,载《中州学刊》2018年第3期。二是将自动免除规则理解为自动适用。自动免除规则的自动适用在买卖合同或租赁合同中因标的物毁损、灭失时较常见,即价金自动免除。但是在人身给付不能或费用过高给付不能时,需债务人以此为由提出不履行抗辩,给付义务方消灭。债务人提出抗辩前,单纯满足人身给付不能与费用过高给付不能的事实构成,不能自动适用给付义务的自动免除规则。依据双务合同的牵连性理论,对待给付义务当然也不能自动免除。
除自动免除规则外,债权人也可以在债务人提出履行不能抗辩之后,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26条第5款解除合同的方式免除自己的对待给付义务。这就是我国学界关于风险负担规则与解除权二元模式与一元模式之争焦点所在。(14)具体论述参见周江洪:《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邓志伟、张平:《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的竞合》,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其中一元模式应指废除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统一适用合同解除制度;二元模式是债法维持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二元模式的意义更多的是体现在“不可分之债中的部分不能及不可修复瑕疵给付不能中”。如在互易合同纠纷中,甲以其生产设备与乙仓库中的煤达成交换协议。嗣后因意外事件,生产设备中的一小部分标的物毁损灭失,乙可以通过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自动免除与此对应的对待给付义务,即减少煤的交换量,也可以通过一部解除来免除部分给付义务。若乙订立互易合同的目的是腾空仓库,其本身就无意通过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当然免除与“部分不能”所对应的对待给付义务,来减少互易合同中与该标的物价值相等的“煤的交换量”。该类合同在客观上即使可分,也应视为不可分之债。部分不能是指可分标的有部分无法履行的情况。部分履行取决于部分履行对债权人是否有利益,若毫无利益,则可以全部解除;反之,若尚有利益,不可全部解除。即使部分履行对债权人尚有利益,未致使合同根本违约,但若对待给付义务不可分,抑或对待给付在客观上可分,但债权人将交易标的视为整体,也不可部分解除。(15)赵文杰:《〈合同法〉第94条(法定解除)评注》,载《法学家》2019年第4期。比如上述案例中债权人将仓库中的煤炭视为一个整体,即使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客观上可分,也不可部分解除。因为自动减少部分煤的履行义务对他无利益。反而可能还会对此支付仓储费。此时乙可以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整体解除合同。又若该案中生产设备不是部分毁损、灭失,而是出现细微的质量瑕疵且其不足以导致全部合同目的丧失,此时乙不能解除合同,其可通过自动免除规则减少相应的对待给付价值。但瑕疵担保在损害赔偿中是无过错责任,债权人可以通过替代损害赔偿获得救济无需适用自动免除规则,所以,在无过错责任体系下,有学者认为风险负担规则无存在的必要。此点俟于第三部分再为详述,此处不赘。
通过自动免除规则与法定解除权并存设置,立法者使债权人在个案中可以自己进行如利益衡量,从而选择最有利的救济方式。在可分之债中,自动免除规则和一部解除均可适用。当部分不能时,债权人可以通过这两种手段免除自己的对待给付义务,并参照相关减价规则减少自己的对待给付义务。(16)Vgl.BeckOK BGB/H.Schmidt, 50.Ed.1.5.2019, BGB§326 Rn.34.在不可分之债中,因债权的不可分性,即使部分履行不能,债权人亦可以选择解除权,消灭整个合同。自动免除规则并不消灭合同,此时,就合同继续履行抑或合同被解除,取决于债务人对部分不能是否具有可归责性。(17)Vgl.MüKoBGB/Ernst, 8.Aufl.2019, BGB §326 Rn.24.因为,在“可归责于”债务人的部分不能情形下,债权人完全可以继续履行其全部对待给付义务,然后请求债务人履行不能部分的替代损害赔偿责任。债权人亦可以选择自动免除规则或一部解除(《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5款),然后通过减价方式取代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18)参见《德国民法典》第326条第1款后半句,在部分不能的情况下,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可以适用第441条第3款的减价计算调整对待给付与部分给付的价值关系。我国有学者在探讨减价权的性质与实现时认为减价和损害赔偿属于择一的关系,无法并行主张。(19)吕双全:《减价救济之定性与实现的逻辑构成》,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3期。这里的损害赔偿应属替代损害赔偿,不包括简单损害赔偿。也有学者在论述减价权的性质与实现时认为若买卖合同领域的损害赔偿奉行无过错原则,减价难觅特殊的制度功能。(20)武腾:《减价实现方式的重思与重构》,载《北方法学》2014年第3期。此时相当于间接否认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的存在。但减价若因无过错损害赔偿原则而丧失其适用空间,为何在租赁合同履行不能时,立法者却又规定了减价。事实上,买卖合同履行不能中的减价来自双务合同中价金风险规则。根据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的牵连性理论,部分履行不能时,对待给付义务可以参照减价规则免除相应的价值。《德国民法典》的价金风险负担规则旨在履行不能时赋予债权人更多的选择权,其可以从解除、自动免除规则及替代损害赔偿这些救济措施中,进行自由组合以取得最优解。(21)德国法律通过三个层次分配履行障碍风险。第一个层次为原给付义务是否消灭,第二个层次为是否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个层次为是否产生解除权。参见王洪亮:《试论履行障碍风险分配规则》,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二)解除规则处理履行不能的困境
我国法律中未规定对待给付风险负担一般规则,对待给付义务能否自动免除,尚存争议。抛开风险负担规则的存废之争,假如债权人只能通过解除权免除自身的对待给付义务,那么其只能从《合同法》第94条寻找请求权基础。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合同法》第94条第1项关于不可抗力的解除规则处理价金风险。(22)王轶:《论买卖合同中债务履行不能风险的分配——以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考察背景》,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或者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4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解除规则处理。(23)同前注〔2〕,第532页。但《合同法》第94条第1项和第4项对于解除的发生事由,或者强调不可抗力,或者强调一方存在可归责的事由,从中不难发现,这两项内容并不能涵盖所有履行不能的情形。因为《合同法》第110条履行不能之事由并不限于可归责于债务人之给付障碍,还包括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客观事由,即不可抗力和其他客观事由(甚至第三人的行为)。履行不能的类型有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行合同,如不可苛求人身给付,根据《旅游法》第65条赋予旅游者解除包价旅游合同的权利,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有因客观原因不能履行合同,如《保险法》第58条保险标的发生部分损失;其他因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显失公平不能履行合同,如《保险法》第52条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上述履行不能之特殊情形自然可以置于《合同法》第94条第5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之下。但实践中存在很多双务合同类型,如互易合同、包价运输合同等,其并无明确法律规定。当该类合同发生履行不能时,法官又当如何适用法律?在包价运输合同纠纷中,承运人甲与托运人乙签订包价运输合同,运输合同履行前,因意外事件导致部分货物毁损灭失。就运输合同而言,承运人甲不能完全运输托运物,乙又不能减少运费的支付。此时,乙可否解除合同?我国也有学者提出将《合同法》第110条履行不能纳入《合同法》第94条第5项予以处理。(24)刘凯湘:《两岸合同解除制度之比较研究》,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17年第3期。但正如上文所述,第110条在救济路径下承担的是实际履行救济的功能,并无处理对待给付义务风险的功能。此外,《合同法》第110条从文义上也未赋予债权人解除权。虽然该观点不可取,但也间接说明我国《合同法》第94条欠缺处理履行不能的一般解除规范。
履行不能可归责于债务人时,是否免除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并不会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债权人可以通过替代损害赔偿来弥补债务人不能履行时的履行利益。但在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履行不能时,因债权人不能主张替代损害赔偿责任,其就需要在继续履行合同抑或摆脱合同的继续履行中进行利益衡量。双务合同多通过合同解除、风险负担规则来调整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履行不能,其实质是在当事人之间进行风险分配。(25)我国有学者将给付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的免除规则从风险负担中脱离出来,单独视为履行不能制度。其逻辑是风险负担规则从属于履行不能制度,但履行不能制度既调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也调整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的履行不能。而风险负担规则只调整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参见于韫珩:《论合同法风险分配制度的体系构建》,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4期。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分离。遗憾的是我国合同法总则既无风险负担一般规则,也无履行不能时的一般解除规范。结果导致在不可修复的瑕疵给付或在不可分之债中,债权人将不得不面临以下困境:首先,在不可分之债中,债权人并无容许合同部分解除的意愿存在,合同自不得部分解除。若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导致部分不能,债权人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得不继续履行合同,且无法获得替代损害赔偿。债权人继续履行合同,相当于承担因给付不能所带来的不利,而该对待给付风险本应由债务人承担。其次,在不可修复的瑕疵给付中,若合同利益尚未完全丧失,债权人同样不得解除合同,就不得不接受这一不可修复的瑕疵标的。由此带来的不利益显然仍然由债权人承担。《合同法》第94条因无履行不能的一般解除规范,自然无法处理上述问题。综上可知,现有《合同法》不可以通过“不可抗力”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全然替代履行不能时风险分配之功能。虽然合同法总则未对履行不能类型规定一般救济措施,但合同法分则第231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减少租金、不支付租金或者在“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解除合同。该条旨在确定租赁合同中的风险负担规则。(26)胡康生等:《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其完整地诠释了债权在履行不能时的救济措施,即减价、免除对待给付义务及解除。但是合同法分则关于租赁合同在履行不能时的补充规范并不能解决其他合同类型履行不能时的问题。为使债权人在其他合同类型中免受继续履行合同所带来的不利益,能否通过在第94条中增设履行不能法定解除事由的一般规范来弥补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范的缺失?
(三)重构履行不能作为法定解除事由的一般规范
合同法分则和特别法上的法定解除权规定大大扩张了合同任意解除权和法定解除客观事由的规定,为抽象出《合同法》第94条之外的解除一般事由积累了大量的素材。(27)陆青:《论法定解除事由的规范体系——以一般规范与特别规范的关系为中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在法定解除事由规范体系的整合中,可否不考虑对债权人利益造成的严重程度,只依履行不能作为合同解除事由的一般规范。对此,也许会有反对者认为,不考虑“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于赋予债权人任意解除权,会妨碍契约信守原则。笔者认为可以从三点加以反驳:首先,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并不是证成解除权突破“契约信守原则”的正当性理由,而仅仅是合同补充解释的依据。(28)同前注〔15〕。在突破契约严守原则上,存续上牵连性是对待给付义务与给付义务同消可能的正当化基础,效率考量是证成法定解除权必要性的关键理由。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实现需要其承担损害发生及范围的证明负担,亦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其次,立法者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弥补解除相对人的契约利益。如《合同法》第405条,“不可归责于委托人的事由,导致委托合同解除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又如《保险法》第65条旅游未开始或结束前,旅游者因个人原因解除包价旅游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最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含义是债权人的期待利益根本无法实现。但合同履行有无意义抑或客观交易目的是否不能实现,更多的在于当事人的判断。在立法政策上肯定履行不能作为独立的法定解除权事由更能体现私法上的意思自治。
重构双务合同中依履行不能作为独立的法定解除权事由,并非一家之言。《德国民法典》第326条除第1款规定了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自动免除规则后,还在第5款规定了债务人依据275条无需为给付时,债权人得解除合同的规定。法律委员会对德国债法现代化中引入第326条第5款给出了以下几点理由(29)Vgl.Westermann in:Erman,BGB,15.Auf.2017,§326Rn.19.:首先,除了对待给付义务的自动免除规则外,债权人还可无需通过设置期限即可解除整个合同的效力。其次,债权人在部分不能或不可修复的瑕疵履行中应当赋予债权人解除整个合同的权利,即使该履行不能不可归责于债务人。虽然该理由有异议,但具有以下强有力的论据:①债权人在不知给付障碍的原因时,就可以通过设置宽限期限并与期限无果后解除合同。毋庸说,债权人在无需设置期限的履行不能中,也应拥有解除合同的机会。②在瑕疵补救履行中,尚且存在解除的救济措施,在不可修复的物上瑕疵中同样应存在解除措施。(通过第326条第5款的解除权可以排除第323条第5款第2句非重大瑕疵不得解除合同的限制)③当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既不可以被自动免除,也不能通过一部解除理论消灭时,债权人需要通过第326条第5款的解除权获得救济。最后,债权人可以通过该解除权及时从附随义务中解脱出来。虽然大部分附随义务随着主给付义务的消灭而消灭,为防百密一疏立法者还是做了这一兜底性规定。在解除权方面,德国法律给予债权人以极大的自由,即使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不履行,债权人也可以解除合同。但对可归责于的债权人的履行不能,债权人不得行使解除权。(30)Vgl.BeckOK BGB/H.Schmidt, 50.Ed.1.5.2019, BGB§326 Rn.33.限制债权人对待给付义务的免除不仅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326条第2款对待给付风险负担特别规范中,同样也规定在第323条第6款一般不履行合同的解除权中。对待给付义务的免除在风险负担规则与解除权规则中保持一致的构成要件,也体现了法律体系的一致性。
无论是弥补我国现有法律的漏洞,还是从比较法上分析,重构履行不能作为法定解除权事由的一般规范具有其合理性。而且通过在合同法总则中增设履行不能法定解除权一般规范,更能保证合同法与特别法在体系上的协调与一致性,也更能体现出一般规范对法定解除权规范体系的指引作用。于此,在对特别法中的规范进行解读时,就是对一般规范在特定领域的延伸和展开。但即便如此,对待给付风险负担是否全然无价值亦非毫无争议。日本在债权法改正的议论过程中,有学者建议将风险负担规则连根拔除,因废除风险负担规定有时对债权人保护不周而未被采纳,如债务人行踪不明,解除意思表示时无法送达;解除权不可分无法解除;解除权行使期间等。(31)陈自强:《合同法风险负担初探》,载《北京航天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三、损害赔偿能否替代履行不能中的对待给付风险
针对第二个问题,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在无过错责任中构成体系违反。因为风险负担指在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而致标的有瑕疵、灭失或不能使用的情形,该给付之价值的风险应由谁负担的问题。(32)黄茂荣:《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76页。与此类似的定义还有,风险负担指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时的不利益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或由双方当事人合理分担的制度。参见崔建远:《风险负担规则之完善》,载《中州学刊》2018年第3期。或风险负担乃对不可归责于合同双方当事人事由所引起的损失进行责任分配的制度,不以适用违约责任为前提。参见江海、石冠斌:《论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5期。由该定义可知,风险负担是可归责性损害赔偿之外的损失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分配的问题。所以风险负担规则与过错损害赔偿责任可以是两个独立的制度。但无过错责任中不存在“可归责与否”的认定标准,只要债务人“未履行”即构成损害赔偿责任,所以无法与风险负担规则并存。我国《合同法》因受CISG的影响,被认为采纳的是无过错责任且无风险负担一般原则,只在合同法分则中有若干规定。我国若以《合同法》并无风险负担一般原则为出发点,而适用分则中的特别规定,解释论上或许最为单纯,但学说对风险负担的定义及阐释,只能被视作与法律适用无关。若认为《合同法》也有风险负担一般原则,而属于《合同法》的内在体系,则就需在《合同法》现有违约责任体系中形成一个兼容并蓄的风险负担原则。(33)同前注〔31〕。
(一)严格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及现实困境
在我国《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针对是否借鉴原德国法上履行不能规则产生了争议,立法者最终采纳了公约的做法。《合同法》没有简单确认自始不能导致合同无效,而是吸取公约的经验,以“违反义务”作为确定债务人责任的依据。(34)王利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我国合同法的制定和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这就建立了包括履行不能给付障碍类型在内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违约责任体系。有学者将《合同法》第107条“以结果为导向”的违约责任解释为严格责任。债权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时,债务人仅证明自己无过错并不能免除自己的损害赔偿责任,还需满足《合同法》第117条中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方能免除责任。《合同法》第107条中的违约责任与第117条免责模式被认为是受到CISG的影响。CISG第45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原理来自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双方担保其对合同义务的履行。该责任并非基于过错,而只是由于不履行合同(担保)义务而产生责任。(35)韩世远:《中国合同法与CISG》,载《暨南学报》2011年2期。这种不要求具备可归责事由——“过错”,以单纯的违反约定即构成违约责任称为“严格责任”,进而影响到了我国 《合同法》的起草。(36)梁慧星:《从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但该影响是否足以否定以“过错”为基础的损害赔偿制度,不无争议。
从笔者考察的学术文献中,自严格责任提出以来一直遭受学者的质疑。有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加以反驳,认为严格责任对于国际货物买卖是适宜的,但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国内的各种交易情况。因为国内法适用于一切民事主体,各类主体的交涉能力、注意能力并不一致,如果像公约那样用商人的标准要求劳动者、消费者,时常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37)崔建远:《严格责任?过错责任?》,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有从归责原则的历史发展方面加以反驳,认为严格责任并非国际合同法的立法趋势。我国《合同法》弃过错责任而选严格责任,实际上是逆流而上,完成了向古典意义上严格责任的回归。(38)李清亮:《合同法归责原则探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有从严格责任体系与过错责任体系比较上加以反驳,认为即使继受一个完整的严格责任体系,严格责任相比于过错责任并不具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一个完整的严格责任体系和一个完整过错责任体系在法律适用的结论上几乎是相同的。(39)王洪亮:《试论履行障碍风险分配规则》,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也有从我国司法实务中的判例入手还原违约归责原则的实际适用状态加以反驳,认为真实的裁判逻辑正在向过错归责原则回归。(40)孙学致:《过错归责原则的回归——客观风险违约案件裁判归责逻辑的整理与检讨》,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5期。总之,无论从学理上还是实践中,严格责任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更毋庸说,通过严格责任体系否定风险负担规则的存在。
在严格责任体系中,债务人对履行结果承担的是担保责任。美国合同法契约责任理论是以损害赔偿为原则,强制履行则仅于损害赔偿方式不足以救济债权人时,方能透过衡平法院之斟酌,例外性地采取强制履行以资救济。(41)Oliver Wendell Holmes, Jr.The Common Law(Edited by Paulo J.S.Pereira & Diego M.Beltran, MMXI,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School).Typographical Society, 2011.p.266.因此,债务人在履行不能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法定免除事由免除债务人之损害赔偿义务。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是,我国法律只对不可抗力所致的履行不能免除损害赔偿责任。而无论是英国的合同受挫原则,还是美国免责抗辩事由,都比我国的法定免责事由广。(42)同前注〔38〕。即使单从不可抗力免责事由出发,韩世远教授在对CISG第79条免责事由研究后,发现我国《合同法》上的不可抗力与公约相比,被限定的更严格。(43)韩世远:《中国合同法与CISG》,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2期。公约中的不可抗力重在“不可控制性”,其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不能预见,二是不能避免。但是我国《合同法》117条对不可抗力的定义,将上述两种类型作为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申言之,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三者需同时存在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进一步限缩了免责事由的范围。如果在将我国《合同法》第107条的违约责任理解为严格责任,那么其损害赔偿责任比英美法系,甚至是CISG都要更严格。如此加重债务人负担是否有违公平之法理念,颇值深思。
所谓无过错责任体系下的担保允诺思想,其实质是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风险分配做好约定。换言之,将契约看成是契约双方当事人对未来种种履行障碍所引发之风险的分配。(44)同前注〔10〕。其价值判断是意思自决下的风险分担更符合私法自治的理念,法律只在当事人不可预见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法定风险分配,仅作为补充。与无过错责任体系相比,过错责任体系其实并不排斥当事人自治。背离过错原则之情形一方面可以表现为责任严格化,另一方面可以表现为责任减轻。而责任严格化或责任减轻均可依合同发生,也就是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45)杜景林、卢谌:《德国民法典全条文注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条,第183页。另外,过错损害赔偿制度自始也不排除“意思允诺”下担保思想的存在。原《德国民法典》第282条“对给付不能是否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所致有争议时,举证责任由债务人承担”,该条确定了给付不能时的过错推定责任。同样,该法条背后也隐藏着在真伪不明时的(非过错责任的)担保。(46)普维庭(Hanns Prütting):《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页。这一担保思想体现的是,当债务人不能履行时,应为债权人设置一定的信任前提: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那么他在不能履行的原因真伪不明时,他有意识地承担了风险。拉伦茨认为,在民法典第282、285条中隐藏着“一条对履行的担保”。(47)Vgl.Larenz, Schulderecht,Bd.I,13Aufl., S.343.这一见解与《联合国销售合同公约》第45条中的允诺担保思想均来自合同当事人的意思允诺。两者皆从担保角度出发,加重债务人的契约责任。那么由此带来的反思是,公约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原理未必非要从否定“过错归责原则”来解释,也可以从举证责任的范畴角度出发。当损害赔偿的事实构成真伪不明时,由债务人承担举证责任即可。
从目前合同法的国际发展趋势来看,目前并不存在单一的合同风险分配因素。(4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交流的不断加深,促进了一系列国际性公约及契约文件的产生,也推动了过错责任体系的发展。我国本属大陆法系,过错归责原则既合乎国民心理和社会观念,也是长期以来从法学理论界到实务界的一贯做法。因此,与其在学理上改弦易辙,不如考察大陆法系在CISG公约的冲击下,对其过错责任采取了哪些修正措施。
(二)过错责任原则的正当性
我国《合同法》虽无明文规定过错责任原则,但是第107条也并未否定过错责任原则。在考察以“结果为导向”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中,发现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均未抛弃过错责任原则。
首先,德国在债法现代化中,通过义务违反统一了债务不履行类型,并构建了以结果为导向的一般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在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方式上基本统一为过错责任原则。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债务不履行规则并没有采用单一的过错责任原则,而是采用了一种混合的体系,即第276条的过错原则和第279条的担保责任相结合。但是2002年的《债法现代化》将第279条删除,并相应的修改了第276条第1款。对于自始不能的情形,新债法第311a条第2款将其确定为一般过错责任,而不再是之前的担保责任。担保责任被明确抛弃,因为它会导致在“公正的视角下”无法令人信服的结果。(49)Vgl.Claus—Wilheilm Canaris, Die Reform des Rechts der Leistungsstörungen, JZ2001,insb.S.506.
虽然在卡纳里斯的影响下,过错原则被保留下来,但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立法者抛弃“不履行”概念,选择道德解释论意义层级上的“义务违反”作为统一损害赔偿的上位概念,过于关注债务人错误所为之情事谴责,忽略了私法所关注的首先应是利益侵害。(50)马丁·舍尔迈尔:《〈德国民法典〉 中的履行障碍法:过去与未来》,朱晓峰译,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6期。这里的利益侵害指债权人基于债务关系有权期待的物事,也即基于债务关系产生的期待利益。因此,为了保证债权人的期待利益,立法者也对“过错的基准点”作了弹性的修正,使得债权人可以在履行障碍中尽可能地获得替代损害赔偿。在自始履行不能时,有人认为,债务人违反的是先合同义务,即债务人并未查明自己的给付能力,也未告知债权人潜在的履行障碍。(51)Vgl.Lobinger, Die Grenzen rechtsgeschäftl.Leistungspflicht, 2004,S.273ff.从这种角度考虑,损害赔偿责任仅仅涉及消极利益的损失。因为债权人的利益损失可能会如此衡量,即若债务人履行先合同义务,债权人将注意到给付障碍的存在,继而不会签订合同。但是立法者允许债权人在自始不能中可以主张替代损害赔偿责任,那么不履行的责任基础就必须建立在合同有效成立之上。(52)Vgl.Medicus, in: Prütting/Wegen/Weinreich,BGB, 5.Aufl.(2010),§311a Rdnr.16.这里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来自债务人的给付允诺,债务人在自己的给付允诺中承担了对自己给付能力的担保责任。该担保责任的范围是债务人担保给付障碍不存在。若债务人对担保的给付障碍知情或基于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应当对给付障碍知情,债务人就需承担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53)Vgl.Canaris, in:Festschrift.f.Heldrich,2005,S.11ff.(25ff).给付允诺的担保责任是有限的,其可以从当事人的意思中推测出来。(54)Vgl.Canaris, in:Festschrift.f.Heldrich,2005,S.11ff.(29ff).需注意的是,这里担保责任基础虽可以回溯到当事人固有的给付允诺中,但不意味着,债务人承担的是无过错(不取决于过错verschuldenunabhähgige Einstandspflicht)的担保责任。第311a条第2款中的担保责任是区别于无过错的担保责任的特别担保责任。就自始不能中的可归责性而言,因为在缔结合同前,债务人并不负有维持给付能力的义务,也不负有阻止给付不能之障碍事由的义务。所以,债务人仅仅负有了解自身给付能力的义务。(55)Vgl.Canaris, JZ 2011,499(507).债务人可归责性的基准点取决于,他是否在缔结合同时对给付障碍知情或因故意、过失而不知情。因为在自始不能损害赔偿责任中,债务人的过错基准点不是债务人的行为,而是给付障碍之原因。此外,其损害赔偿的范围还受给付允诺思想的限制。因此,虽然《德国民法典》自始不能损害赔偿责任与统一损害赔偿制度均属过错责任但立法体例上系相互分离的。
在嗣后履行不能时,原给付义务因被《德国民法典》第275条排除而不存在,自不构成义务违反。因此,立法改革中曾有人建议修改“义务违反(Plichtverletzung)”为“不履行(Nichterfüllung)”,但是这样一来,不履行概念无法涵盖保护义务的违反。所以,立法者并没有采纳学者的这一建议。(56)Vgl.Begr.RegE, BT—Dr 14/6040, S.134.德国债法改革之所以弃“不履行”而选择“义务违反”,是因为债务关系中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张。(57)传统德国民法中由债务关系产生的义务只有给付义务。债务关系产生之义务的狭义化,使权利的保障受到威胁;义务的狭义化,也是造成积极违约、缔约过失这些早已打上德国造烙印的给付障碍类型却长期游离在《德国民法典》损害赔偿之外的根本原因。参见刘青文:《论义务违反——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在德国新债法中的统一》,载《中德法学论坛》2006年第4辑。另外,“不履行”概念在德国发生了范式转变,其被学者界定与给付行为关联且不在被理解为与给付结果相关联。同前注〔50〕。为了解决嗣后履行不能中不存在“义务违反”的问题,立法者在第283条第1句中用“援引”一词来适用第280条损害赔偿一般条款中的构成要件。“援引”一词在方法论层面上是指该条款是能够“准用的”而不是直接适用。(58)Vgl.Larenz/Canaris,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Aufl.(1995), S.82.申言之,通过“援引”第283条清晰的表明因嗣后不能而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在可归责的情况下产生替代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取决于“义务违反”的存在。(59)Vgl.Begr.RegE, BT—Dr 14/6040, S.142.借此立法技术,避免“义务违反”与“不履行”这一术语争议。有观点认为,第283条(履行不能中的替代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是一个多余的条款,他和第281条中的替代损害赔偿并列设置,不具有独立意义。(60)Vgl.Palandt/Sprau, BGB, 69.Aufl.2010§283 Rdnr.1.该观点应给予反驳。首先,第283条的功能是扩大第280条第1款中义务违反的构成要件,而不仅是局限于无需设置宽限期这一特别要求。(61)Vgl.Looschelders: Unmöglichkeit und Schadensersatz statt der Leistung, JuS 2010, 856.虽然第281条在有期限的给付义务中同样允许放弃宽限期的设置,但是该条规定不适用履行不能。(62)Vgl.Looschelders, SchuldöR AT, 7.Aufl.(2009), Rdnrn.602.其次,第283条改变了“可归责性”的基准点。第281条替代损害赔偿责任中,债务人需对不履行或瑕疵履行负有“义务违反”责任。但履行不能中的给付义务是不需要履行的,所以不履行不是此处替代损害赔偿的原因。第283条中“可归责性”的基准点是给付障碍的发生,即债务人对嗣后履行不能中给付障碍的发生负有责任即可。申言之,债务人此时不是对嗣后履行不能中的“不履行”的行为负责,而是对引发“不履行”的障碍负责。(63)Vgl.Looschelders, in:Festschr.f.Canaris I,2007, S.737ff.(741f.).
《法国民法典》中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责任的核心条款是第1147条,该条同样没有提到过错,但可将所谓“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之语解释为当然包含了当事人的过错。(64)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367页。关于这里的“过错”,我国学术界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过错要素是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一种为过错要素是严格责任下的免责事由。(65)《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暗含着过错思想。在许多合同债中,被告的过错并不需要举证证明,被告不履行债务的过错是被推定的。参见崔建远:《合同法应当奉行双轨体系的归责原则》,载《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该条从文本上也可以解读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严格责任。只要存在债务不履行或迟延就足以使债务人承担责任,而债务人只有通过证明债务不履行是由于“不可归咎其个人的外来原因”造成的,才能免除责任。参见柯伟才:《债务不履行归责原则之对立与融合》,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这一差异性解读,关键在于如何协调给付允诺思想与过错要素。法国本土学者德莫格经过研究揭示“合同过错的证据”与“按照债的目标来进行的区分”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也就是说,合同过错的证据与区分方法之债和结果之债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的基本思想就在于,要“查明债务人允诺的是什么”“债权人可以合理期待什么”。(66)弗朗索瓦·泰雷等:《法国债法契约篇》,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108—1109页。质言之,如果是手段债务,那么债权人就要证明债务人没有尽到应尽之谨慎;如果是结果债务,那么债务人不履行其允诺就已经足以推定其有过错,他只有在证明存在外部原因阻碍其履行债务时才能推翻这个推定。法国通过手段债务与结果债务的区分,在未放弃过错推定的前提下亦可以协调其与给付允诺中债权人的合理期待的关系。
综上所述,从比较法上考察,无论是通过弹性的过错基准点,还是手段与结果债务的区分,在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方法上,大陆法系并未抛弃过错责任原则。早期英美法系的绝对责任原则,因受到大陆理论的影响,也逐渐吸收了过错归责原则。如美国合同法的错误原则、诚信原则、善意原则、不法契约原则、共同过错原则、合理预见原则、减损原则等规定以及相关判例,全都贯穿了过错责任原则的精神。(67)喻志耀:《过错责任:民法的基本归责原则》,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英国法中“过错要素”通过默示条件的方式被隐藏于免责事由当中。(68)同前注〔65〕,柯伟才文。虽然严格责任中同样需考虑过错因素,但与其将过错因素视为严格责任下的免责事由,不如放到过错责任下,通过过错推定的立法技术,更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在司法实践中,以过错为归责事由的运作,已构成法律工作者法律意识的一部分。就笔者考察的关于违约损害赔偿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中,不难发现过错责任原则的存在。(69)相关检索判决书的案号有:(2001)民一终字第29号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最高院认为海南高院判决依据公平原则,法律适用错误,判决显失公平,本案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处理;(2002)民一终字第4号关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最高院认为,一审判决未体现过错责任原则,应予纠正;(2016)最高法民申1493号关于委托合同纠纷中,最高院认为债务人对此明显具有过错,违反合同约定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17)最高法民申2377号关于其他合同纠纷中,最高院认为某某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应按照过错责任原则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就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方面,审判者对债务人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阐释中也多是基于大陆法系的行为理论,而非英美法系中的默示条款。这一审判思维的形成除了来自法律传统的长期培养之外,在判决中进行道德层面上的过错阐述,也更符合人民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法律意识的培育乃多年积累的成果,并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与习惯相符合。奉行过错责任原则最契合道德伦理。(70)同前注〔65〕,崔建远文。风险分配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之外,道德伦理仍然在其理念中占据重要地位。区分善恶而决定违约责任的有无,仍然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三)过错责任及与风险负担规则的兼容
法律解释乃解释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平井宜雄认为某一观点的妥当性,必能经受最大限度之批判,使有价值可言,因此其主张必须透过“论证”,由“讨论的广场,于对论与反论中,获得真理。”(7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8—99页。通过上述论证分析可知,我国损害赔偿责任不应采严格责任。从法律解释上看,《合同法》第107条只是通过“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这一上位概念统一“原因路径”下的各种给付障碍类型,并确立了“以结果为导向”的违约责任体系,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体系下单纯的义务违反并不足以构成损害赔偿责任,此时还需要考虑债务人对义务违反是否具有过错或给付障碍的发生原因是否具有过错。在违反主给付义务方面,过错责任在过错推定的立法技术下,其与严格责任并无太大差别。因为,过错有被客观化之趋势,债务人是否具有过错,从义务违反这一客观表现上就可以加以判断。债权人只需证明债务人结果上的“未履行”——即构成义务违反,就足以推定债务人有过错。此时,过错责任和基于“未履行”的严格责任并无差异。在违反从给付义务方面,义务违反就是判定过错的标准,债权人证明违反从义务也就是需要证明对方有过错。过错推定技术在这里起不了作用,但为了与CISG公约保持同步,德国学者亦通过其发达的解释理论重新解读第276条第2项中的过失(未尽交易上必要之注意),过失之非难以危险的预见可能性及损害结果之避免可能性为前提。如此一来在举证责任方面,相对于债务人证明自己主观上无过错或已尽所有注意,当事人若能证明瑕疵起因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的客观情况而生,更有免责机会。这样一来,采客观化过失之过错原则与公约第79条第1项免责事由之判断所差无几。(72)Vgl.Schlechtriem/Schroeter,Internationales UN—Kaufrecht,5.Aufl.,2013,Rn.644.转引自陈自强:《民法典草案违约归责原则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我国继续贯彻过错责任原则自然也不会与CISG公约发生抵触。
在诉讼中,对给付障碍的发生原因是否具有过错的考察,不同于严格责任。在严格责任下,只要给付障碍符合法定免责事由即可免除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在过错责任中,履行不能的原因是基于不可抗力的影响抑或该客观风险由债务人所致,往往需要法院来裁量。我国司法实务中,法院在适用不可抗力免责规则时,立足于对债务人是否“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与“不可克服”的主观状态的审查上面,即债务人是否履行了注意义务、是否采取了合理措施。(73)孙学致:《过错归责原则的回归——客观风险违约案件裁判归责逻辑的整理与检讨》,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5期。这充分说明我国判决趋势更倾向于过错责任原则。另外,由《合同法》第117条“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可知,审判实务中若要免除债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需辨别“不能履行合同”是在多大程度上因不可抗力影响所致,而非债务人原因。所以,无论是从《合同法》第117条的规定还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审理思路,我国《合同法》中的损害赔偿责任更易解释为过错责任原则。况且《合同法》第110条中保留了履行不能制度下消灭原给付义务功能,而该条只有在给付障碍法的二重理念下才予以考虑,在严格责任体系下无需考虑排除原给付义务,只需考虑来自给付允诺思想下的损害赔偿义务的免责事由即可。
由于现存的《合同法》分配履行障碍风险的规则并不合理,所以如何构建与损害赔偿责任兼容的风险负担规则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上所述,就体系而言,风险负担规则并不与“以结果为导向”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相冲突。为实现平衡分配履行障碍风险的目标,法律体系内部应视为存在风险负担一般规则。因为,我国《合同法》买卖合同部分存在风险负担规则的相关规定,而且根据《合同法》第174条,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所以,不难推知,其他合同可以类推适用买卖合同中对价风险负担规则。德国债法现代化后,民法虽保留了风险负担规则,但修正了原《德国民法典》第282条中给付不能中的“可归责与否”要件。修正后的风险负担规则并非全然以过错为基准,一方面在给付风险负担规则中,就债务人给付义务的消灭,不考虑债务人的过错,另一方面在对待给付风险负担规则中,就债权人对待给付义务的豁免,反而考虑其过错。(74)Westermann in:Erman,BGB,15.Auf.2017,§ 326Rn.1.台湾学者在论述履行不能中的风险负担规则时限于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情形,(75)台湾学者在论述给付不能类型时,如一时不能宜限于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情形,始论为给付不能,盖在可归责与债务人之情形,应论为给付迟延。参见黄茂荣:《债法通则2,债务不履行与损害赔偿》,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45页。但德国新给付障碍法并未拘泥于“不可归责”这一归责事由基准点。(76)债务人在一时给付不能中,虽不构成给付迟延责任,但如对一时不能具有可归责性,依然承担债权人因此产生的损失负担简单损害赔偿责任。参见 MüKoBGB/Ernst, 8.Aufl.2019, BGB § 275 Rn.153.我国《合同法》第110条在排除债务人的履行义务时,同样不以归责与否为要件。债务人违约导致的合同履行不能,抑或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事由引发的合同客观履行不能,债务人均可以免除自己的给付义务。风险负担规则处理原给付义务消灭问题上将风险负担分为给付风险与对待给付风险的价值意义在这里得以凸显。在给付风险负担的规范体系中,给付障碍无论归责与否,债务人均可以免除自己的给付义务。在对待给付风险负担的规范体系中却存在“基本原则——例外突破”的基本结构。(77)刘洋:《对待给付风险负担的基本原则及其突破》,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其中基本原则指的是对待给付义务自动免除规则,此时意味债务人承担对待给付风险。例外突破体现在,交付行为完成后或可归责于债权人的因素等导致履行不能时发生风险移转,即原由债务人承担的对待给付风险转移给债权人承担。
修正后的风险负担规则不仅与过错责任体系下的损害赔偿责任具有一定的兼容性,而且充分考虑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均衡。首先,德国民法中一般限制债务人的解除权。所以,给付风险中的当然免责规则(自动免除给付义务)不以过错为要件,可以充分缓解对债务人的苛责性。而且,即使在可归责于债务人事由时,债务人通过给付风险负担规则免除自己的给付义务,债权人的解除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因此受到影响。(78)同前注〔45〕,第275条,第183页。其依然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替代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解除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反之,立法者虽赋债权人于履行不能时的选择权,但其通过过错要件限制债权人行使该权利。即可归责于债权人的履行不能,债权人不得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自动免除规则及替代损害赔偿请求权。另外,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并非在履行不能时当然消灭。通过这一规定,在履行原因不明时,债务人可以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防止债权人不作为及观望的态度。立法者在履行不能时设置风险负担自动免除规则、损害赔偿规定及解除权实现了体系内部履行障碍风险之平衡分配的目标。
过错推定的立法技术与风险负担规则的双重设置,是对契约信守理念的贯彻。于债务人一方,其虽通过风险负担规则中给付风险免于现实之给付(自然法则上的给付义务),但仍需审查其是否构成替代损害赔偿责任。于债权人一方,其可以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在替代损害赔偿、风险负担规则中对待给付风险(减价或当然免除)、解除权等救济措施中自由组合,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救济措施,避免裁判者的恣意裁量,剥夺债权人的选择权不利于债权人契约利益的周全保护。
四、结论:法律中隐含对待给付风险负担一般规则
救济路径下的损害赔偿责任相较于原因路径,虽满足了法律面目的简约和统一,却使现存的违约责任一般条款过于抽象。通过在救济路径下进行给付障碍类型的二级划分,可以审视救济路径的不足。在对待给付义务的免除规则中,《德国民法典》采价金风险负担规则与法定解除权二元立法模式,旨在给予债权人以自由选择权。其可以在履行不能中就解除、自动免除规则、替代损害赔偿、减价这些救济措施进行自由组合取得最优解。我国《合同法》受CISG的影响,法律条文中并无价金风险一般规则,仅有特殊价金风险规则。对待给付义务自动免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多通过减价及损害赔偿的计算中予以直接适用。简言之,对待给付风险负担一般规则在实务中可以直接适用。风险负担一般规则是基于双务合同的牵连性理论,体现了交换正义的思想。该一般规则虽未写在法律中,但可将其视为法律内部体系中的“法条形式原则”。(79)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3—355页。借此,风险负担一般规则与违约责任方式相互结合,为履行障碍风险分配提供多元化手段,从而对债权人起到周全保护。
通过与原因路径下履行不能功能做对比,不难发现:不可抗力并不必然导致履行不能,也不必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更不会如某些学者所言可以替代履行不能之中的部分功能。因为履行不能除由不可抗力或可归责的违约行为所致之外,还可以由其他客观事由引起。在解除制度中,《合同法》第94条保留了迟延履行的违约类型,却遗漏了履行不能的解除规定。从现有的规则中不足以解决履行不能下的各种情形,对此需创设履行不能一般解除规范。只是创设一般解除规范后,是否能完全排除风险负担规则依然是有争议的,有时可能对债权人保护不周,如债务人行踪不明,解除意思表示无法送达;解除权不可分无法解除;解除权有行使期间限制等。现有的损害赔偿制度在合同履行障碍风险的分配上并不合理,尤其是在其他客观原因所致的履行不能时,因无法通过不可抗力免责,不能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故而,损害赔偿责任应贯彻过错原则,但过错的基准点并不局限于债务人的给付行为,还有给付障碍的原因。
总之,在现有救济路径的法律框架下,区分各种义务违反的具体构成形态有助于分析其相应的法律效果。(80)朱晓喆:《瑕疵担保、加害给付与请求权竞合》,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另外,混合进路的意义也体现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需证明债务人违约的具体事实构成。债权人主张法定解除权需证明下列要件事实:债务人给付不能、拒绝给付、给付迟延、瑕疵履行致期待利益落空、违反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致无法受领或期待债务人的继续履行。所以,从举证责任的视角看,无论是法定解除权的事实构成,还是损害赔偿责任的事实构成,在统一违约责任下进行原因路径的二级划分均有其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