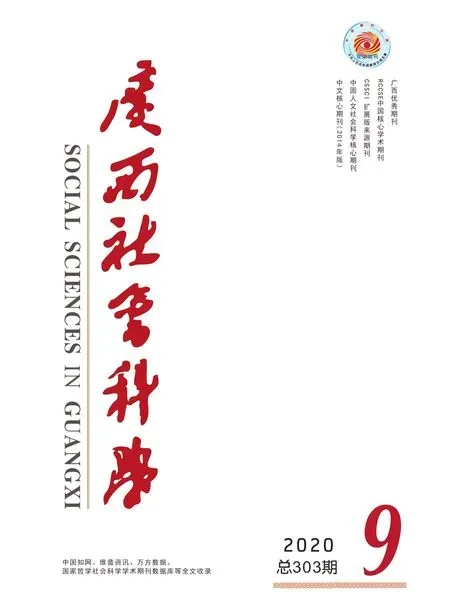重塑“寓言”:林纾《伊索寓言》翻译中的双重改写及其动因
周慧
(1.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上海 200083;2.湖南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由林纾、严培南及严璩合译的《伊索寓言》①本文在进行文本比对时所采用的译文版本为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的《伊索寓言》光绪二十九年五月第四版。但为征引方便,本文所引译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亦参照庄际虹编校的《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本》。此外,由于林纾《伊索寓言》中的寓言没有标题和编号,本文以每则寓言的开头一句作为该寓言的标题,同时因旧版书均一页两面,不便标注页码,本文所引《伊索寓言》中的篇目均不再标注具体页码。是继《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之后又一部广受欢迎的林译作品,一出版即被多次重印。它在《伊索寓言》汉译史和中国寓言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第一部由中国人自主翻译的《伊索寓言》汉语全译本。“伊索寓言”之名自此确定,“后来译者,遵之勿替”[1]。此外,它还触发了《伊索寓言》在民国时期的广泛流传和“中国寓言的复活”[2],“寓言”一词也因之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而被相继使用。
目前,学界对林纾《伊索寓言》的翻译问题展开了不同层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没有确切的底本作为参照,只能就译文的文本内容和某些文本特征进行概述性的分析,无法进一步归纳和整理林纾《伊索寓言》的翻译特征,并作出解释。为此,我们需要将研究建基于细致的文本比对与分析之上,分析译者作出种种翻译决策的原因以及可能影响这些决策的社会、文化因素。正如王宏志所言,“只有通过对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以及译文本身的研究和分析,才可能准确掌握译者在进行这主观裁决时的种种考虑因素”[3]。本研究借助微观文本分析与宏观外部研究并重的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研究视角,参照日本学者沢本郁马在林纾《伊索寓言》底本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对林纾《伊索寓言》中的翻译特征及改写动因等问题进行重新探照。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行为主体根据自身的社会地位及观察视角,用以建构包括物质、社会及精神世界的一种符号学手段,它既受到社会各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建构着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系统和信仰体系[4-5]。因此,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话语使用者,出于不同的动机或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语言手段和话语策略再现或建构同一社会事实,以达到传递意义、参与社会实践和行使权力的目的。批评话语分析的这种研究理念,为我们透过翻译文本考察译者的翻译动机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和研究方法指引[6]。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译本中改写部分的文本特征,以探求译者在翻译时所持有的某种动机或倾向,并结合其价值取向及所处的历史坏境,对造成这一动机或倾向的原因作更深入的探究。
一、林纾《伊索寓言》翻译中的双重改写
通过文本比对,林纾对《伊索寓言》原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写,其改写主要体现在内容和叙述模式两个层面。
(一)内容上的改写
就内容而言,林纾对原文所做的最明显的改写体现在其额外添加的“畏庐曰”案语以及对原寓体和寓意的改写上。在再现原故事时,林纾根据其所欲添加的案语对原寓体进行改写;在呈现原文寓意时,根据案语对原寓意加以改述,甚至删去与案语相矛盾的原寓意。
1.添加案语。林纾在《伊索寓言》全书187条寓言之后添加了案语,这些案语短则数言,长则数行,甚至有的在篇幅上大大超过了故事部分。如以“贵人以巨资为大剧场”“一人畜斗鸡二”“百舌之鸟”“理学家出行岸上”等句为开头的寓言,多为对社会现状的批判和对时事政局的规切。有的案语是对原故事寓意的进一步引申和阐发,如“就乳之羊”一则的原寓意为“暴君总能为暴政找到借口”,林纾进一步引申该寓意,认为强国对待弱国亦是如此:“弱国羔也,强国狼也,无罪犹将取之,矧挑之耶?若以一羔挑群狼,不知其膏孰之吻也?哀哉!”有的案语是对原寓意的否定和批判,如“大橡见拔于风”一则的原寓意为“委曲求全”,林纾在案语中却将该寓意完全推翻,批评被原文所肯定的小草“风来即偃,因得自全”的行为,赞扬原文所否定的“与风鏖而见拔于风”的橡树,称其为“独立之英雄”,只是需要“培基而固根”,并呼吁读者“不当效小草之偃伏”,否则将“终身屈于奴隶”。通过添加案语,林纾抒发了渴望救国保种、自强自立、变法求新、合群向学、反抗外侮、勿忘国仇的爱国热忱。
2.根据案语改写寓体。如“病狮且死”一则,原寓言讲述年老体弱的狮子在相继受到野猪和公牛的袭击后,又遭到来自驴的羞辱,无力还击之下,只得吐出“I have reluctantly brooked the insults of the brave,but to be compelled to endure contumely from thee,a disgrace to Nature,is indeed to die a double death”[7]的悲叹。原文中,病狮的独白是整个故事的寓意所在,表达了宁可被勇者冒犯,也不愿被无能之辈侮辱的寓意。林纾在翻译这句话时,将其译为“吾竟被辱至此耶?辱甚于死,吾垂死而翻得辱,殆两死矣”,且在寓言后添加如下的案语:“畏庐曰:有志者,视辱重于死,乃垂死而仍不愿辱,则真有志者矣。今乃有以可生之人,故以死自待,听彘辱之,听牛辱之,且至忍辱于驴,何也?”如此一来,林纾巧妙地将原句中“勇者的冒犯”和“无能之辈的侮辱”置换为“辱”与“死”的对比,从而强调“与其受辱不如赴死”的观点,使故事内容契合案语中“有志者,视辱重于死”的观点。
3.根据案语改述寓意。如“匠者求材”一则,原文讲述樵夫用所伐橡树树枝制成斧头楔子,反过来劈裂橡树的故事,并通过橡树的哀叹,揭示“由自己所造成的不幸是最难忍受的”这一寓意。林纾在翻译时,不仅将原寓意“Misfortunes springing from ourselves are the hardest to bear”[8]译为“故自伐其国,其伤心甚于见覆于敌”,还在其后添加了案语:“畏庐曰:嗟夫!威海英人之招华军,岂信华军之可用哉?亦用为椓杙耳。欧洲种人,从无助他种而攻其同种者,支那独否。庚子以后,愚民之媚洋者尤力矣。”由此可见,林纾透过橡树反被“以吾枝为杙”的斧头伐而裂的故事,揭示庚子事件中威海英人雇华军以“攻其同种”和庚子事件之后愚民更加崇洋媚外的悲哀。林纾在翻译原寓意时通过将原文中表泛指的“misfortunes(不幸)”具体化为“自伐其国”的不幸,并添加“甚于见覆于敌”一语,从而表达自己对这类现象的深切哀痛。
4.根据案语删除寓意。如“村人见驼而惧”一则,原文讲述人对体形庞大的骆驼由害怕到轻视,最后竟让一个小孩去控制这头骆驼的故事,揭示“熟悉足以消除恐惧”的寓意。而林纾在翻译时并没有将原寓意“Use serves to overcome dread”[9]译出来,只在故事后添加案语:“畏庐曰:一西人入市,肆其叫呶,千万之华人均辟易莫近者,虽慑乎其气,亦华人之庞大无能,足以召之。呜呼!驼何知者,吾腆然人也,乃不合群向学,彼西人将以一童子牧我矣。”由此可见,林纾无疑是希望借身形庞大的骆驼最后却反被一小孩驯养的故事来唤起国民的忧患意识,号召大家通过合群向学来改变命运。显然,原来的寓意已无助于这种论述,因而被删去。
(二)叙事模式上的改写
就叙述方式而言,林纾会将原故事对话中的间接引语改为直接引语,有时甚至将原文中的非对话性内容改为对话或角色独白的形式,通过添加细节使故事情节更加合理,将一些无法从外界明显观察到的情节加以简化或删去,删去原文故事中的预叙提示语和叙述者对所述故事的干预,以及运用概述的方式简化故事情节。通过在形式上将原寓意并入原寓体,以及在句中使用凸显叙事者叙事干预的词汇和句式等方式,林纾将原寓意变为叙事者对于所述故事的评论。
1.着重使用对话体。林纾在再现原寓言故事时,着重使用对话的形式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将原文中的间接引语改为直接引语、非对话性内容改为角色对话,借故事中角色之口来点明寓意。如“蜂与鸟并飞”一则,原文为“The Wasps and the Partridges,overcome with thirst,came to a Farmer and besought him to give them some water to drink.They promised amply to repay him the favour which they asked.The Partridges declared that they would dig around his vines,and make them produce finer grapes.The Wasps said that they would keep guard and drive off thieves with their stings.”[10]林纾在翻译时将其中“besought”“promised”“declared”和“said”之后的间接引语都改为以“曰”开头的直接引语:“蜂与鸟并飞,求饮于村人曰:‘苟饮我,我必报君。’鸟曰:‘君植葡萄,吾以啄掘地,令土质松动,果必大硕。’蜂曰:‘我为君司侦,盗来,吾必螫之。’”译文中对话形式的使用,制造了一种真实的现场感,给读者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增加了故事的生动性和真实性。又如“有业磨者”一则,原文讲述磨坊主与其子欲赶驴去集市变卖,一路上听从各种赶驴意见,却最终在途中失去驴空手而归的故事。原文的寓意由故事叙述者在文末点出:“Upon this,the old man,vexed and ashamed,made the best of his way home again,convinced that by endeavouring to please everybody he had pleased nobody,and lost his Ass into the bargain.”[11]林纾在翻译时,将叙述者的陈述译为故事角色磨坊主的自我慨叹:“业磨者大恨曰:‘吾惟欲徇人意,四易法而终丧其蹇。甚哉,欲求人悦之难也’”,由业磨者之口道出寓意,使所欲阐述的道理更具感染力。
2.补充细节使情节合理。例如,“牧羊者,易而饲驴”一则讲述一位牧羊人在放驴吃草时,不意间遭遇仇敌,欲带其驴逃跑,驴却以即使被抓新主人也不会给它多加一副驮篮为由,不愿随他逃去的故事。原文开头只将故事背景简略交代为:“A Shepherd watched his Ass feeding in a meadow.Being alarmed on a sudden by the cries of the enemy,he appealed to the Ass to fly with him,lest they should both be captured.”[12]林纾在翻译时译为“牧羊者,易而饲驴,复纵驴以食人别业之纤草。寻闻其仇语于墙外,防为所得,乃捉驴鬣,趋急遁。”通过添加“易而饲驴”“纵驴以食人别业之纤草”以及“寻闻其仇语于墙外”等信息,林纾除使牧羊人“饲驴”这一行为变得更为贴合人们的生活经验外,也使牧羊人在“饲驴”时突然遭遇仇敌这一情节变得合乎逻辑,使故事更为合理与可信。
3.简化或删去无法从外界观察到的角色行为。如“狼欲求食于人”一则,原文讲述狼欲披上羊皮混入羊群以便饱食,不料却反被牧羊人错认为羊而宰杀的故事。原文一开头即交代了狼披上羊皮的动机所在:“Once upon time a Wolf resolved to disguise his nature by his habit,that so he might get food without stint.”[13]而林纾在翻译时,将该句简单译为“欲求食于人”,从而把无法从外界观察到的狼的内心盘算,即希望通过伪装掩饰来轻松饱食,加以简化,变为只是对其意图的简单交代。类似的例子还可见于“鹰伏卵于危橡之柯”一则,原文讲述与鹰、野猪同住一树的猫通过诡计诱使鹰、野猪互相惧怕,导致两者都不敢离家觅食,最后均被饿死的故事。原文在讲述猫实施诡计时说:“When night came she went forth with silent foot and obtained food for herself and her kittens;but,feigning to be afraid,she kept a look-out all through the day.”[14]林纾在翻译时,只简单译为“猫夜出取食,窃啖其子”,删去了原文对猫“假装害怕”以及“密切观察”的心理和神情的描写。他通过这样的改动,将叙述者置于一个客观的观察视角,从而增加所述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4.删去预叙提示。如“村人见鹰为人所获”一则,原文讲述鹰被农夫救下后回来报恩,引农夫远离危墙的故事。原文在交代故事时插入了一句对于后来情节发展的预先提示:“The Eagle did not prove ungrateful to his deliverer”[15]。林纾在翻译时则将该句删去,只译原文的故事叙述部分:“村人见鹰为人所获,心怜其羽毛,开笼放之。鹰一日见村人坐于垂陨之石,疾下以爪扑村人,取其顶上所戴之物”,使故事得以依照自然时序展现在读者眼前,从而赋予了故事更强烈的真实感。
5.运用概述简化情节。林纾通过概述的叙事方式对原故事中烘托寓意作用不大的次要情节加以简化,使整个故事在保持情节完整的同时,显得更加凝练、重点突出。如“有胶雀于野者”一则,原文讲述捕鸟人意欲捕鸟却不小心反被脚下毒蛇咬伤致命的故事。原文的寓意由文末捕鸟人之口点出,但在这之前,原文对捕鸟人一系列准备捕鸟的动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A Fowler,taking his bird-lime and his twigs,went out to catch birds.Seeing a thrush sitting upon a tree,he wished to take it,and fitting his twigs to a proper length,he watched intently,having his whole thoughts directed towards the sky.While thus looking upwards,he unawares trod upon a Viper asleep just before his feet.”[16]林纾在翻译这段用以引出寓意的铺垫性文字时,将原文对捕鸟者具体捕鸟动作的描述加以简化,用概述的方式译出,只保留了基本情节:“有胶雀于野者,闻画眉鸣树颠,举胶竿徐进,误蹴毒虺。”如此一来,林纾将译文的故事变得简洁、凝练的同时,也加快了译文的叙事节奏,使叙事重点转移至用以点明寓意的捕鸟者的话语之上,从而凸显了寓意。
6.删去叙述者对所述故事的干预。例如,“蜂觐于帝居”一则讲述了蜂后请求朱庇特赐其刺以刺死那些前来取蜜之人的故事。当朱庇特得知蜂后的要求时,原文对朱庇特有如下一段描述:“Jupiter displeased,for he loved much the race of man;but could not refuse the request on account of his promise.He thus answered the Bee……”[17]林纾在翻译时,只将该段话简单译为“帝不悦,曰……”删去了原文中对“帝不悦”原因的解释。如此一来,通过删去原本内隐的叙述者直接出面干预叙事的语句,林纾在译文中大大降低了叙述者对于所述故事的干预,保持了叙述的连贯性,并且使故事的叙述变为一种“客观”的展示,从而让读者获得犹如亲历旁观般的真实感。
7.显化评论性叙事干预。虽然在再现原文故事时,林纾会尽量让叙述者保持内隐,不干预故事的叙述,但是在翻译原文寓意时,林纾却会通过使用诸如“嗟夫”“哀哉”“宜哉”“殆真愚哉”“故”等带有评论性色彩的词汇或句式,以凸显叙述者对故事的评论性干预。例如,“麑谓其母曰”一则在叙述完小鹿和母鹿间关于母鹿何以身体各项条件都优于狗却仍然怕狗的讨论后,道出“No arguments will give courage to the coward”[18]的寓意。林纾则将这句寓意翻译为:“观此则积馁之人,虽力助之,又恶能益其勇?”通过添加“观此”和使用反问句式,林纾令原本貌似客观的哲理总结变为颇具主观色彩的价值评判,从而使原本内隐的叙述者由幕后走向前台,凸显了叙述者的干预行为。
二、林纾《伊索寓言》的改写特征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就内容层面而言,林纾所添加的“畏庐曰”案语无疑充当了整部寓言的意义权威,其会根据这些案语对寓体和寓意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就叙事方式而言,林纾在再现原文故事时倾向于采用顺序的叙述方式,注重通过角色对话来推动情节发展和点明寓意,以及保持叙述的连贯性和故事情节的合理性,使叙事张弛有度、重点突出。经过这些改写,林纾在凸显《伊索寓言》教化色彩的同时,也增强了它的纪实感,提升了它的权威性。
(一)凸显教化色彩
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主要是对生活经验以及处世哲学的总结和升华,但是经过林纾的改写,整个译本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教化色彩。例如,在“就乳之羔”“狼博兽”“群兽野集”“野驴与狮盟”“狼取人羔”等则,林纾就在案语中发表了自己对当时国际关系的见解,认为强国犹如贪婪的饿狼吞灭成性,强国与弱国之间无所谓邦交可言,强国即便是对弱国温言和语,也只是自恃弱国无法与其抗争的虚伪表现,弱国必须独立自强、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又如,在“冬蚁出曝其夏取之栗”“骡夫挟一驴一骡”“妪嗜酒”“狮入村舍”“一少年喜挥霍”等则,林纾认为善谋国者须行善政,在平日就需注重储才与练兵、严备广储,不可以疲军搏强敌、浅谋图幸胜。在“野兽鳞集”“三牛共牧”“有一父而育数子”“村人见驼而惧”“贵人以巨资为大剧场”“燕方春依人而巢”等则,林纾引入“卫生”“群”及“公法”等概念,认为救亡之道在于向西方学习以融通中西之情,号召国人合群向学,倡议加入公法,学习欧西的胎教及保婴之术。在“一人畜斗鸡二”“匠者求材”“角鸱诏群鸟曰”“鹿谓其母曰”“胡桃植于道周”“蛇穴于周廊之下”“群㹀合谋”“二雄鸡相斗”“葡萄既熟”“病狮且死”“老松一日笑荆棘曰”“狐绝溪而过”等则,林纾则敬告国人勿为欧人所利用,须明种族异同之辨,停止内斗,变法改良,奋起反抗外侮,合力保家卫国。林纾通过添加这些极具个人思想特色的案语,将自己对时局的见解和批判、对西学和维新的渴求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倾注到这部《伊索寓言》译本之中,使该书呈现出浓厚的教化色彩。
(二)增强纪实感
古希腊《伊索寓言》属于fable型寓言,而fable型寓言所叙述的故事一般不会在现实生活或自然界中发生,具有高度的虚构色彩[19]。林纾通过对原文叙事模式的改写,赋予了这些故事较强的纪实感。首先,在再现原故事时,林纾注重故事情节的逻辑性与合理性,尽量通过补充细节的方式使故事的发展符合当时人们的认知与生活实际,从而赋予所述故事真实感与可信度。其次,林纾在改写过程中着重使用对话体,并通过概述的方式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在保持故事情节完整的同时,将叙述的重点始终聚焦在对话之上。而对话作为最常见的一种场景,因其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基本相等,能营造非常真实的现场感[20]。再次,林纾在再现原故事时注重呈现只能从外界观察到的角色行为,删去或简化原文中对角色的心理等描写,保持叙述者的内隐,只让其以旁观者与记录者的姿态出现,不介入故事的发展之中,从而使故事的叙述以第三人称限知的视角展开,形成一种客观讲述的效果。此外,林纾还注重按照事件实际发生的自然时序开展故事的叙述,删去原文中的预叙提示,使故事展现出一种如历史叙述般的客观意味。通过改写各种叙事模式,林纾让原本充满虚构色彩的《伊索寓言》变为颇具实录意味的“客观”叙述,增强了故事的纪实感。
(三)提升权威性
作为fable型寓言,《伊索寓言》的寓意往往是寓言的故事部分,即寓体所寄托意旨的归纳或总结,而林纾在翻译《伊索寓言》的寓意时,通过使用带有评论性色彩的词汇或句式,将原本对道德观念或真理的总结变为来自故事叙述者的带有价值判断的批评或议论,使原本内隐的叙述者由幕后走向台前,凸显了叙述者的存在与干预。在译本序言中,林纾通过将《伊索寓言》的作者伊索和当时在中国大热的斯宾塞相并举的方式,把伊索打造成为欧西的大哲学家。而在“富人大置酒以延客”一则中,林纾更明确地指出该则寓言中前面的评论实为伊索所作,从而将伊索置于故事叙述者的位置。如此一来,通过凸显故事叙述者的评论性干预、赋予叙述者以权威的身份等方式,将《伊索寓言》变为欧西大哲学家伊索的所见、所闻和所评,从而极大地提升《伊索寓言》译本的权威感。
此外,在添加案语时,林纾选择将案语以“畏庐曰”的形式引出。这些以“畏庐曰”为开头的案语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中国传统史传中,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等,用以“卒章显志”的论赞。如此一来,林纾不仅将自己的案语置于译本的核心位置,更令这些案语有了一种犹如“君子曰”和“太史公曰”般褒贬论判的效果,从而赋予案语及《伊索寓言》如史官论断般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三、林纾改写《伊索寓言》的动因
林纾为何会通过改写来凸显《伊索寓言》的教化色彩,增强该书的纪实感和权威性?本研究结合林纾的价值取向、社会身份和文学旨趣,并兼顾当时的历史脉络分析林纾改写《伊索寓言》的原因。
(一)价值取向感召
林纾添加“畏庐曰”案语,并根据案语改写寓体和寓意来凸显《伊索寓言》的教化色彩,极有可能是其想将该书改造成一本符合自己训蒙理念的新式学堂启蒙教科书。
林纾训蒙理念的形成和他自身的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密不可分。林纾早年的生活环境以及与福州船政局进步维新人士的交游,使他很早就萌发爱国保种之心,而他“二十六年村学究”的训蒙经历又让他把实现改良维新的实践场域设定于学堂之中。1897年初,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的“论幼学”专章,受其影响,林纾于同年在至交魏瀚的资助下刻印发行了仿白香山讽喻诗《闽中新乐府》以“课少子”[21]。在这些诗中,林纾抒发爱国之情,抨击时病,并和魏瀚一起对传统启蒙方式进行反思。林纾认为“强国之基在蒙养”[22],儿童教育关乎民族之振兴,但是“儿童初学”,若“骤语以六经之旨”,会令其“悟性转滞”[23],所以他提出以儿童喜爱的歌谣来说明道理的启蒙方法[24]。魏瀚亦在《新乐府序》中指出“蒙养得失,系国之强弱”,并倡导学习欧西东洋的训蒙方式:“训导必取其浅明易晓者,渐渐引以世事,又渐渐入以国事,鼓其英气,令胸中洞然于天下大势,故视国之仇若己仇,视国之利若己利,国日以强,人亦日以勇”[25]。可见,在林纾和魏瀚看来,训蒙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救国人才。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学习西方的训蒙方法,先引以世事,后入以国事,如此才能培养出理想的救国人才。
(二)社会身份牵引
林纾在《伊索寓言·序》中交代该序写于“光绪壬寅花朝”的五城学堂。五城学堂为晚清北京第一所官办新式中学堂,林纾自1901年11月2日该学堂创办伊始即已在其中任教,为汉文总教习,其合译者严君潜亦同在该校任职,为西文分教习[26-27]。根据林纾于序中“日举数则”“经月书成”的回忆,可推断林纾《伊索寓言》应译于光绪辛丑年(1901年)与壬寅年(1902年)相交之际,而这个时间极有可能就是林纾和严君潜初入五城学堂之时。因而林纾是以学堂教习的身份翻译《伊索寓言》的。此外,林纾《伊索寓言》在出版时,是以少年汉文教科书的面貌被推介的[28-29]。而《东方杂志》创刊号中“商务印书馆出版国文类教科书”广告里对《伊索寓言》的介绍为“林君并逐课附加案语,发明真意”[30],也从侧面证实林纾翻译该书时身为学堂教习的社会身份。
根据林纾的训蒙理念和执笔翻译时的教习身份,以及其在《伊索寓言·序》中对该书在欧人启蒙教育中所起作用的介绍——“欧人启蒙,类多摭拾其说,以益童慧”,可推断林纾在翻译时确有将该书作为学堂启蒙用书加以使用的倾向。但是要将该书打造成像《闽中新乐府》那样符合林纾以培养儿童爱国意识为旨归训蒙理念的教科书,还需向其中补充一块“入以国事”的内容,而这极有可能就是林纾选择改写《伊索寓言》以凸显该书教化色彩的原因所在。
(三)文学旨趣指引
如前所述,除在内容上对原文进行改写外,林纾还对原文故事的叙述模式加以改动,其原因极有可能是林纾在再现作为fable型故事的《伊索寓言》时,在叙述模式上采用了一种融《庄子》寓言、柳宗元寓言以及秉承史传笔法的志怪小说等各体之长的混合叙述模式,以赋予和增加这本理想启蒙教材纪实感与权威性,从而更好地协助自己实现于学堂中改造社会的救国抱负。
为提高这本理想启蒙教材的经典地位,林纾在《伊索寓言》的序中介绍该书时,即将该书视为类似《庄子》的“寓言”:“伊索为书,不能盈寸,其中悉寓言”,之后马上对《伊索寓言》与《庄子》进行比较,得出《庄子》固然精妙,但是与“得之阅历”的《伊索寓言》相比,“于蒙学实未有裨”的结论。如此一来,林纾在无形中将《伊索寓言》拔高到了与《庄子》等同的高度,但是要想让《伊索寓言》真正获得如《庄子》般极具感染性的说服力,还需要学习《庄子》的论述方式。因此,林纾在翻译时广泛运用《庄子》“伪立客主,假相酬答”的对话体来达到后者“藉外论之”的目的,从而赋予和提高《伊索寓言》中的故事真实感与可信度。
《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多以动植物为主角,难免会令当时的晚清读者误以为这是一本专事调笑的谐谑故事集。林纾也在《伊索寓言·序》中表达了类似的隐忧——“有或病其书类齐谐小说者”。林纾向来注重文体,且对韩柳文寝馈其中甚久,他深知要想令看似虚诞怪妄的内容更好地为读者所接受,必须在行文上制造出一种庄重感,认为“凡事之愈猥琐者,行文须愈庄重”[31],正如他在点评《柳州罗池庙碑》时所言:使读者不敢斥为齐谐,正以行文庄重也[32]。《伊索寓言》“诡托草木禽兽之相酬答”的内容已无法改变,为避免读者将该书斥为“齐谐”,林纾极有可能想到了借鉴同样记述神异之事却秉承史传笔法之志怪小说的叙述模式。在古代,志怪小说多被认为是有事实依据的纪实之作,常被归入史部“杂传”类,其叙事模式也深受史传影响[33]。史官为追求真实性与可信度,在叙事中通常采用一种有限的全知视角,立于故事之外去观察故事人物的言行举止,对人物心理最多只作简单交代,较少介入故事情节发表议论,从而令所述故事尽量如生活原貌般得以呈现。史传的这些叙事特点都深深影响了志怪小说的叙事模式[34]。林纾在再现原故事时,亦注重保持叙述者的内隐,不让叙述者对故事进程进行干预,会删去一些不可知的情节,并强调故事的逻辑性,令故事得以如实际发生般一幕幕呈现在读者眼前,从而赋予所述故事史传般的纪实感。
林纾一生推崇秦汉、唐宋古文,在古文家中尤其推重韩愈和柳宗元,曾直言“余生平心醉者,韩、柳、欧三家”[35]。林纾不仅对柳宗元古文评价甚高,对他的寓言亦颇有研究[36]。柳宗元的寓言多为规切时政、讽刺世态之作,且其寓言大都采用“先叙事后议论”的论述体例,将重心放在故事之后的论说之上,正如林纾所言:“柳州每于一篇寓言之中,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37]。在不同体裁的寓言作品中,柳宗元通常会以旁观者的姿态对所述故事进行点评和议论,抒发的虽为一己之胸臆,却给人一种冷静客观的感觉,十分具有说服力。此外,柳宗元多以史传笔法写寓言,往往会在寓言后以“柳先生曰”来展开评论,营造出一种如史传般客观、权威的效果。柳宗元寓言的这种论述特点无疑给林纾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在《伊索寓言·序》中介绍伊索时刻意提及了韩愈用以纪念柳宗元的《柳州罗池庙碑》一文,还在翻译时将原寓意变为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的来自旁观者伊索的批评与议论。此外,他也选择用“畏庐曰”来引出自己对所译寓言的评论。林纾从柳宗元寓言中撷取的这些元素使他得以为《伊索寓言》赋上一层冷隽犀利的权威感。
Basil Hatim和Ian Mason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作为“文本处理者”的译者会介入翻译的过程,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及意识形态对原文进行“过滤”,并将他们的知识和信仰注入对文本的处理中去,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文[38]。林纾在翻译《伊索寓言》时,亦会根据自己的志向抱负与价值取向对原文内容和叙事模式进行双重改写,将《伊索寓言》变为一本符合自己训蒙理念的理想启蒙教科书的同时,更成功地把原本充满虚构色彩、用以揭示道德教训的fable型寓言改造为如史传般真实可信、极具权威感的社会讽刺寓言,从而实现于学堂中改造社会的救国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