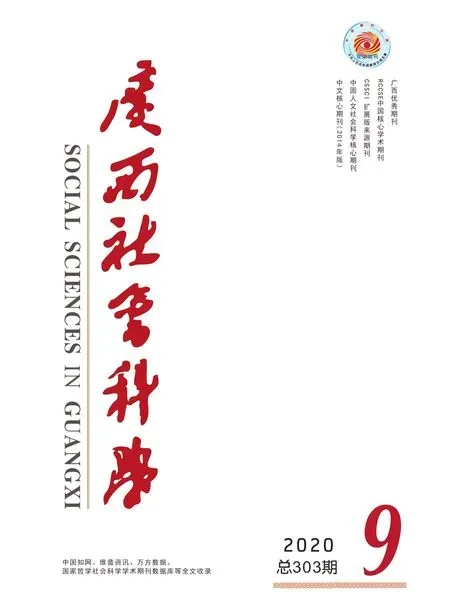百年来清史写作典范的历史迁移及挑战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作为距今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成为史学界十分关心的朝代,仅仅2018年,就有超过3000篇论文,60余部专著问世[1]。清史研究繁荣的标志之一,是通论性清史著作的大量出版。近年较有影响的通代史论著中,以海外学者的成果而言,就有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中的《海与帝国:明清时达》、增井经夫的《大清帝国》、“哈佛帝制中国史书系”《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等系列著作问世,国内的研究者也相继推出“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中国大通史:清朝卷》等。清代断代性历史著作的持续升温,使关于清代通史性写作模式的探究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将百年来的清代通史研究做一回顾,可清晰见出清代通史写作典范的变迁及其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
从20世纪20年代清史馆开馆起,已然形成清史写作的两种基本模式:一种为传统史书模式,如《清史稿》《清通鉴》;与此同时,通俗性的章回式等著史模式也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如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黎东方《细说清朝》等[2]。另一种是受西方学科体制影响的现代学院史著模式,如《清史要略》《清史讲义》。两种清代通史的写作模式均有其生命力,且互相交织缠绕。传统史书写作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仍促成《清代全史》《清史编年》等著作的推出;而章回体的通俗写作模式则在民间吸引最广泛的群体,高阳关于清代历史的系列小说广受欢迎;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影响下的《清朝那些事儿》等系列通俗著作也大行其道。至于《清史讲义》等则影响到《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等一系列著作。两种不同的清史写作模式互相竞争,迄今未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
就在中国本土近代以来的清史书写模式互相竞胜之际,新的挑战应时而来。世纪之交,《剑桥中国史》及史景迁系列著作的问世,揭开了海外叙事史学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序幕。其书与哈佛帝制中国系列历史书、日本讲谈社中国历史丛书一道,风行中国,可视作欧洲、美国、日本等清史写作模式对中国近现代清史书写的挑战。
百年来,中国的清史书写典范经历两次重要迁移,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以传统史书典范为基础,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以现代学院式史学论著书写为典范,及至21世纪以来,遭受西方新史学书写模式的冲击。西方史学著作的优势,与其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回归叙事”热潮紧密相连。在那场历史书写的大讨论热潮中,一部分西方历史学者认为“历史是残缺不全的知识”,“写历史更像是写小说”,有趣与好奇成为重要的写作原点和目的[3]。“回归叙事”令西方新史学著作具备很强的可阅读性,从而俘获大批读者。在新的冲击面前,中国史学界如何回应,其成功的经验如何,其失败的教训又在哪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清史书写模式何以应对时代危机,完成第二次典范的迁移?以下本文且从李学勤、朱志坤两位先生主编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中的《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一书论起。
一、十字路口的清史写作模式:从《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说起
《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一书为复旦大学教授冯贤亮著作,于201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醒目的推荐语为“传统与现实的历史二重奏、开启近代社会的曲折探索”,显示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特性。然而其特殊的现实关怀究竟体现在何处?是该书所针对的主要问题直面现实,可“古为今用”,为今日某些社会问题开药方么?仔细阅读该书,并不能寻觅出该书所谓的“历史二重奏”。试看该书各章节,分别为:顺治开国;康熙大帝;盛世景象的“另一面”;雍正朝的政治;雍正的思想与信仰;乾隆盛世;和珅及其时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傀儡皇帝;最后的帝王。
初读之后可判断:该书前半部分类似“帝王将相家谱”,后半部分则是近代史教科书外加西方新史学对清代皇帝的叙述。何以如此?仅从章节设置而言,是书显然沿袭孟森《请史讲义》而来。孟森《清史讲义》分“总论”与“分论”两编,其于分论部分所设章节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咸同之转危为安。各章节中,也以帝号纪年为线索,勾勒此一时代历史事件。然而,其内里却与孟森《清史讲义》差别较大。如《清史讲义》特重政治事件、职官、赋税等政治史、经济史方面内容,仅仅开篇即花费大量笔墨介绍八旗制度,而《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却只在“顺治开国”一章中以不到400字的篇幅就将八旗制度介绍完毕[4]。如此短小的篇幅介绍,不能令人明了八旗制度原委,也无法据以理解满洲何以兴起,并灭亡明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忽视传统职官、制度等内容的《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却在论述“傀儡皇帝”光绪时,用大量笔墨记载慈禧对“庚子西狩”的回忆,其大部分史料采择自德龄《光绪泣血记》。德龄(1886—1944年)尽管曾服侍在慈禧身边,但她这部回忆性质的著述却是文学作品,且是在“庚子事变”数十年后的追忆。从记忆史的角度去理解晚清变革在公众中的印象固然可以,但将其作为采信史料编入史学著述,显然非传统中国史书写作所容纳。
在“盛世景象的‘另一面’”一章开头,《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在论述庄廷鑨“《明史》案”时如是开篇:“康熙即位的当年,上海黄浦江东住着一位在县衙里作吏员工作的人,叫姚廷遴,当时他三十五岁。因去年的大饥荒,这年春天米价暴涨,百姓生活颇为困难……”[5]这种由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起笔,遥遥而来切入正题的笔法,显然别有借鉴。与上文对照言之,《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一书的内在写作出现一定程度的文本断裂,某种程度上说其历史书写存在一定程度的“失控”。我们不禁要问,在传统史书书写模式之外,《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还借鉴了哪些传统,令其呈现出如今十分“怪异”的面相?
熟悉近年风行中国的史学著作的人,不难发现,这种写作模式很大程度借鉴史景迁的作品。史景迁《曹寅与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等著作在中国公众史学有着广泛的受众。史景迁的写作常常以优美的文笔、精巧的构思,综合多种写作策略,在史料与想象之间游走。“在一种自觉的程度上将文学手法融入其历史写作之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是给历史情节还原出更为丰富深广的时代语境,同时对受众造成更具情感冲击力的影响。”[6]史景迁这种笔锋带有感情的历史叙事写作,激活中国历史的故事性一面,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如《儒林外史》有内里的相通[7],故令中国读者耳目一新又易于接受,产生广泛影响,也促使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反思自身的历史写作模式。中国的清史研究者由此不得不思考写作如何面向公众的问题,即清史研究在学术化表达与公众传播上应如何取得有限度的平衡。
中国史学界应对历史书写模式的转变,不止发生在清史研究领域。樊树志所撰写“重写晚明史”系列著作同样是对新时代历史写作呼吁的应对。海外新的历史书写模式挑战并冲击中国的历史学者的历史写作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典范性的里程碑意义,因其意味着“从以社会科学导向的、以‘确定事实’、‘解释事实’为最终目的的历史研究,转向了以‘人文关怀’为导向的历史研究,并将治学重心转向以文学化的技艺‘描述’历史,传达历史学家的学术见解”[8]。这就能解释《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何以在一章节之内一面讲传统的职官、制度,另一面却必须以一个历史故事衔接另一个故事,以“讲故事”的形式调动整体的章节运作。这种杂糅的笔法,使得传统的历史书写模式产生裂缝,从而发生历史写作难以“榫合”的疏离情况。
清史写作模式至此走到十字路口。往前一步,是既能吸收海外新史学历史著作的叙事性,又保持传统史书书写模式的知识性,但若借鉴不得法,则恐流于“四不像”。既不能像孟森《请史讲义》那样提供言简意赅的历史知识,又无法完全像史景迁《王氏之死》那样自如地在史料与合理想象之间游走。倘若不幸如此,在新一轮海内外清史著作的竞赛中,中国清史学者在公众接受层面的竞争中恐又将落于下风。故此,处于十字路口的清史书写模式,有必要重新追溯中国旧有的史学书写模式,并充分剖析海外史学写作模式的运作机理,从而为新时代的清史写作树立新的典范。
二、清史书写典范的世纪变迁:从“传统模式”到“学院模式”
中国传统的官修史书模式在清朝灭亡前后,继续发展。清朝历代帝王的实录等,均是典型的传统史书。但真正意义上清史书写典范仍然首推《清史稿》。
《清史稿》纂修于1914年至1927年之间,起初馆长为赵尔巽,继任者为柯劭忞,参与修撰的学者包括王树枬、吴廷燮、缪荃孙、张尔田等近百人。修成之后,共计五百二十九卷,除去目录外,“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三十五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尽管其事未竣,称为初稿,但“《清史稿》是学清史的人的基本参考书”[9]。《清史稿》的巨大影响足以见出其为中国清史书写“传统模式”的典范。其典范性主要体现在:其一,修史者采取传统纪传体模式,体例与传统史书一脉相承。其二,由于与修者多为清朝遗老,故多颂美清朝统治,以帝王为线索串联整个朝代兴衰。其三,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清代国史馆底本、诸种实录、圣训、方略、会典、则例、方志、碑传及其他档案均予以采录。不少人因而忘却《清史稿》也是史书,而将其作一手史料加以采用。故《清史稿》作为官修史书,虽未列为正史,实际上却具有正史的权威性影响。其四,其语言多为文言文书写,与传统史学一脉相延。以《清史稿》为代表,中国传统的史书书写还有纪事本末体、演义体等,如《清史纪事本末》《清史通俗演义》等,均在民国年间问世。这些“传统模式”的清史著作具备完善的朝代知识、鲜明的王朝正统观念,在学界和大众间均具备广泛影响。近年备受瞩目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成果《清史》预期也将主要以这种书写模式呈现。
如果中国近代史仍然遵循传统的王朝模式演进,则清史的“传统模式”仍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晚清以来乃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朝代鼎革、风云激荡的时代,呼唤新的史学。晚清时期西学的引入,令传统的历史观念和书写模式遭遇新的挑战。梁启超最先揭橥“史界革命”和“新史学”。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等著作中,梁启超抨击中国传统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认为旧史学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反映出“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上的革命朝气”[10]。梁启超等人高扬的“史界革命”旗帜,正中旧有史书之弊端,不过其言论早于《清史稿》,象征性影响大于实质上对史书“传统模式”的抨击。但梁启超的言论毕竟开启了中国“新史学”的先河,从此中国的历史书写眼光不再“唯上”“唯帝王将相”,“新史学”成为20世纪初中国史学引人注目的一股动态势力。
1904年,清朝废除科举,陆续兴建各类学堂等机构,整个国家的现代学院体制逐步建立,旧有的治学方式、历史教育开始全面被取代,这真正给清史“传统模式”以致命打击。首先,清史写作的平台发生变化。新的高校体制逐步建立,以学院制为依托的专门历史研究工作逐步取代传统的史馆工作模式。同为清朝遗老,汪荣宝、孟森等人登上高等学校的讲台,讲授清史;而赵尔巽等人孤坐清史馆,实际上使其史学特色失去传承基地。其次,受西方学科体制影响,章节体论述逐步取代传统的史书写作与讲授模式。正是受历史教学影响,早期《清史讲义》等著述都是研究者在高等学校讲学,将课程讲义结集成书的。面对新式学堂的学生,如何梳理清代历史,显然非传统零散的史料可以满足。研究必须体系化,讲课也必然条理化,于是现代章节式的论述逐步抬头,而论文著述的研究范式也同步确立。最后,五四运动以后,受“科学”与“进步”观念的影响,历史学的科学化潮流势力日张。李大钊、何炳松、李璜等人均致力于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11]。科学化表达重在论文,又与现代大学体制息息相关。伴随“科学”观念在知识阶层的渗入及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逐步确立,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和书写也逐步转移到学院之中,清史写作的“传统模式”越发难以为继。此种历史写作的变迁也是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一部分。关于这一过程,学者左玉河有简练概括,其云:“古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在官学及书院,现代学术研究中心则移至近代大学。晚清以后仿效日本、欧美而创建之近代大学迅猛发展。近代大学乃为迥异于传统太学、国子监、翰林院之新式学术机构,实为近代知识生产与传播之专门组织。越来越多的学者被吸收到近代大学体制中,大学教授构成传授知识与研究学问之主体。教授、院系、学科、图书馆、实验室、评议会、出版基金、学报及学术会议诸元素所构成之大学制度,使近代大学与专业研究院所一起,赫然成为现代学术研究中心。”[12]清史书写的平台从史馆、民间逐步集中到学院之中,历史研究者也从政府职员、民间学者集中到学院中的教授和学者身上。于是,清史书写的“学院模式”应运而生。
清史书写的“学院模式”最早以日本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为代表,其书1914年即已出版,影响甚大。不过,限于各种原因,孟森《清史讲义》仍更具典范意义。根据尚小明的考证,孟森在北京大学曾四次讲授清朝开国史,三次讲授明清史,其《明清史讲义》是逐步修订、增补完成的。“现在看到的《明史讲义》是1936年印行的最后定本。而《清史讲义》乾隆以后部分,是孟森1935年后增补的,并且增补的部分并没有作为‘明清史’课的内容讲授过。”[13]从中可见,“学院模式”下诞生的清史著述的基本特点:第一,其书多由课程讲义而来,经过多次修订才最终得以完成。第二,其读者面向最初拥有较高知识水准的知识分子,涵盖钱穆所称“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的主要群体。这就使其读者面向相较“传统模式”的史书稍有择取,即其受众的知识水准既略高于《清史通俗演义》的群体,又不如《清史稿》受众那么小。第三,受课程教学影响,其书多列章节标目,条分缕析。优势在于体系完备,适合议论与分析;而弊端则在往往不重叙事,而多在知识与历史观念的灌输。第四,其语言表达逐步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与“新文化运动”有内在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利弊优势因中国社会大众普遍识字率并不高,还能隐伏不彰。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普遍阅读水准的提高、公众历史需求的提升,这种书写模式的优长和弊端均被放大。
整个20世纪,清史写作的基本典范主要就是由“传统模式”逐步过渡到“学院模式”。当然,这种典范的迁移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简单的取代关系,而是两种模式长期交织、缠绕,共同丰富中国现代的清史研究和普及。然而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大量清史著作的写作重心从“传统模式”向“学院模式”倾斜。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叶,清史书写的一些显著性变化业已完成,大略可归纳为:学院式通史写作取代传统史书的编撰;清史研究主要为学校学生服务而忽视社会大众;对知识性与研究深度的探寻超越对历史事件和叙事的陈述;白话文表达取代文言文论说;学院式史书在学术金字塔中取得高于演义体等传统模式中普及类著述的优势地位……这一系列变化标志中国旧有清史书写模式发生重要变化,即写作典范发生迁移。
三、“新清史”与清史书写“海外模式”的利弊
尽管20世纪中国的清史写作在形式上完成“传统模式”向“学院模式”的典范性转变,但其内在的视角与方法、关切的领域及基本论述内容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基本上以政治和事件为主要线索,以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等为支线推进,这种单线模式的“教条化”,也为21世纪以来海外清史书写模式的风行一时提供了机遇。诚如葛兆光所言:“中国通史,基本上会以政治史为主要脉络,因此,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历史叙述中总是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他领域大体上只是依附在这个主轴上。尽管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和《中国史绪论》开始,中国通史写作就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历史叙述的方式,但总体变化似乎并不大。”[14]而以《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为代表的清史著作,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叙述的单线模式,而采取双线乃至多线论述,政治与事件不再居于绝对的主流位置。这与近些年国际史学研究界的新变化有关,其中最为突出的推动力来自新文化史研究[15]。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可清晰看出,环境气候、性别医疗、社会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等国际历史学界风起云涌的诸多新领域均得以有效引进,使海外清史著述呈现别样格局。
清史书写的“海外模式”的突出表现还在于其从全球史的角度关注清王朝。罗威廉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认为近年的清史研究出现了三个重要转向,即“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欧亚转向”。在“社会史转向”中可清楚窥见宗族、亲属、性别、日常礼仪、书籍等内容被增添其中,这在传统中国历史著述较少涉及。中国学者对清代历史中习焉不察的内容视为寻常,而在“本质与建构、想象与叙述、后殖民与后现代,以及帝国与国家、国别与区域、物质与文化、疾病与性别等,五花八门的新观念、新角度、新方法”[16]的重新审视下,传统的清史研究亟待重新审查。与研究视野的全球史关照相呼应的,是海外清史著述特别注意同一时间段,欧洲、美洲及东亚其他国度发生什么,这种开阔的世界史视野是中国传统清史著述较少涉及的。与此同时,近年关于“新清史”的论述中,欧美研究者认为,“清王朝能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的关键,主要原因不在于‘汉化’,而在于他们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文化政策。透过整合各种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维持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地区,清朝统治者将帝国打造成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17]。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向,令西北、东北边疆以及蒙古等边缘地区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对满语等多语种文献的关切也拓展了研究的视野,而该研究的新鲜度及可拓展性也吸引大批研究者和公众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新清史”既调整传统史书关于清朝的论述,也使海外清史著述具备新的价值观依托。尽管我们知道,“新清史”论述有海外诸多各有指向的政治因素驱使,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能动摇清朝“汉化”的基本结论(后文对此还有论述),但其造成的巨大影响则毋庸置疑。近年中国清史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争论即围绕此方面而展开。
清史著述的“海外模式”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原因在于其视角、方法及叙事手段均具有极大自由度。在基本的历史发展和框架内,国内以往多认为“清朝作为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腐朽与堕落的”等基本观念被打破。海外清史著述对“清朝之于中国现代疆域、多民族融合国家的建构具备极大意义”的论断被肯定。此外,在海外清史著述中,还可发现:清朝不再被视作没落的封建王朝和被列强瓜分的对象,而是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帝国,与大英帝国等同步崛起,不过帝国在现代转型中遭遇了阻碍,但却具备强大的内生力。近年西方史学界对中国晚清史的“冲击—反应”模式也发生转变,而认为清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是中国历史自身发展顺理成章而诞生的。这些鼓舞人心的历史观点的提出,使清史书写的“海外模式”迸发强大思维自由度,再加上其叙事性笔法,因而不仅在学界受人瞩目,也在公众层面造成很大影响。
从“中国如何应对西方世界”到“在中国发现历史”,海外史学界逐步否定了清朝乃是停滞不前的封建帝国的观点,而趋向于认为清帝国已经酝酿了诸多现代社会的因素。从社会组织、社会动态等社会史向度论述,清帝国获得更多社会史的阐释。此后,美国的清史研究出现文化史转向,显得更为异彩纷呈。环境、物质文化、视觉与图像、出版等新兴研究领域的成果也被吸纳到海外清史著述中[18]。清史著述的“海外模式”因而别具与时俱进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将学界最新成果涵括其中,因而具备持续更新的生命力。
然而,影响广泛的“新清史”及其勾连相关的清史“海外模式”却并不能称为中国清史写作的第二次典范迁移。海外学者论述背后隐含的政治、学术和思想背景均值得重估。诚如周群指出:“极少数学者对西方学术思潮缺乏应有的警惕,将国外历史虚无主义在清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变种引入国内,有意无意地与以‘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内陆亚洲’等为核心概念的所谓西方清史学派进行‘对话交流’,影响清史研究走向。”[19]消解清史著述中的政治与时间为中心的线索,固然可以丰富清史论述,增添新的趣味和材料,但清史论述“中心”的丢失和“边缘”的过分强调,使人难以把握清朝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主线。清史论述的“碎片化”,一定程度上使人不免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担忧。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清史写作典范的中国气象
20世纪的清史书写典范,由“传统模式”转向“学院模式”,使清史著述步入科学化的大潮,清史话语权从史馆、民间逐步集中到学院,清史论述也日趋精密、深邃。由此也标志中国清史著述“现代转型”的初步完成。但在应对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背景下,学者们不仅在国内对清史书写权力展开话语争夺,还将与海外学界竞争。论述不仅要在研究的深度上推进,也须在普及的广度上下功夫。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学研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重估,以应对新近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潜在危机。一言以蔽之,清史写作须完成新一轮的典范迁移,以满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需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如何继承中国清史书写的“传统模式”及“学院模式”、应对“海外模式”的挑战,成为摆在今日清史写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而新一轮清史写作典范能否确立,也与能否有效呼应国内对清史著述的需求以及应对“海外模式”的挑战密不可分。
清史论述的“海外模式”尽管取得一些成就,在边疆与内亚视角、性别与权力、环境与书籍等领域有值得称道处,但在其纷繁的解释之中,存在重要的阐释危机。清朝是不是中国历史王朝的一部分、是不是“汉化”的王朝?民族融合是不是清朝的主流?鸦片战争是一场特殊的贸易战吗?诸如此类问题,清史著述的“海外模式”往往将问题复杂化,虽作出诸多阐释,却回避最核心的是非判断。其在阐释上的迷失导致“新清史”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却也暴露出其充满“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当代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以各种丧失知识公共性的阐释形式表现出来,注定无法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公共文化成果。”[20]清史著述的“海外模式”因此亟待纠正。
清朝作为距今最近的一个历史王朝,是构筑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一环,也基本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疆域。清朝的重要性,令清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从清代发展、演化而来的,有的或多或少可以找到清代的影响因子。尤其是一些涉及边疆、民族和宗教的重大现实问题,甚至与清代有着直接联系。”[21]有鉴于此,清史著述的新时代典范必须能够回应当代问题、解决历史难题。清史著述的“传统模式”累计大量可信的一手史料,值得继续夯实与挖掘。如冯尔康先生所言:“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22]但是“传统模式”不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其不足之处。有鉴于此,具备理论深度的清史书写“学院模式”仍应该予以坚持。不过在坚持追求研究深度与论述的专精时,应该吸纳传统史书中“演义”“通俗”的一面,使研究不只成为象牙塔的专属,而能广泛普及,在社会上造成普遍性影响,并进一步将海外清史著述的读者群接纳过来。
清史著述的“海外模式”可作为“异域之眼”,为中国清史新典范的确立提供“异己”的文明滋养。对于这种文化上的吸纳,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变迁》一文中早已指出:“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今则全球若比邻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国,其文明皆已灭,故虽与欧人交,而不能生新现象。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23]梁启超以平等的情怀与开阔的胸襟呼吁国人吸纳西方文明,并预言在吸收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即将迎来新的辉煌时代。梁启超的总体判断有其合理性,但在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西方不断泛起“文明冲突论”“本国优先论”,显示其局限乃至狭隘的一面,故西方学者的学术及政治的这种隐含因素也不应忽略。这就要求在创造清史书写新典范时,在吸纳西方清史著述的写作形态的过程中,一些基本的价值底色应当坚持,一些原则性的历史基调应当坚守。即“在当代历史书写中务须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重返阐释的正确历史观为价值诉求,充分整合并吸纳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优秀理论资源,以科学的态度、方法和标准展示史实的真实现场,澄明思想的演进谱系,回归历史的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从而在当代历史书写中真正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以历史的至真达成文化的至善”[24]。
20世纪中国清史写作典范的迁移经过艰辛的探索,其曲折历程显示历史写作与国家历史变迁息息相关。而其间典范的互相交错,也丰富历史写作的形态。如“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即将推出的《清史》即是上述两种典范的结合。在典范的迁移过程中,清史研究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总体上是在回应中国历史书写自身的问题。而21世纪以来西方清史书写带来的挑战,促使我们重新回到全球史,不仅从周边看中国,还应从中国观照全球。显露国际化视野的清史论述的“典范”,将不仅是中国吸收海外的历史研究与书写样式,而且也是中国的历史经验与书写,“反哺”欧美乃至整个海外。那么,新的中国清史论述的模式不妨称为“中国本位模式”。
20世纪中国清史著述从“传统模式”到“学院模式”的转化,与西方大学体制及科学、进步等观念引入中国密不可分。这种新的写作模式的引入,可用制度变迁的机制加以解释,即与制度变迁中的“跨域移植”与“功能新构”十分相似。它们意味着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一种新的机制被引进另一领域,随后与新环境产生作用,形成新的功能和结构。而清史书写典范即将走向“中国本位模式”,则意味其已进入“催化反应”阶段。也即“新构建的功能反馈到其他领域中,与这些领域中的制度和做法相互作用,催化这些领域中连锁反应和质变,推动新组织制度的创造和兴起”[25]。在清史研究的新的历史碰撞和交融中,清史著述的“中国本位模式”不仅因应“海外模式”的挑战,也一并应对改造清史书写单向度的吸收机制,而创造性融合“传统模式”及“学院模式”,以国家级的《清史》为标杆,将清史书写的世界格局作新的改造。
清史著述的“中国本位模式”的完成意味着新一轮典范迁移的成型,其迁移过程意味着中国清史学研究成果开始服务全球。事实上,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清史研究积累的丰硕成果,在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社会需求时,也必将在全球史框架中将中国历史的“清代经验”释放到海外,造福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