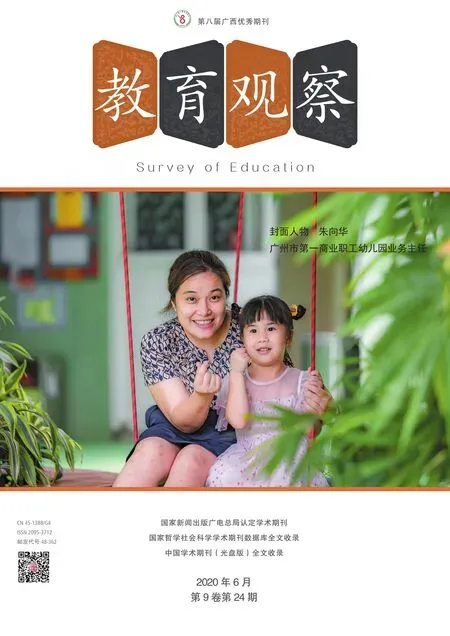儿童敏感期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异化与回归
章 威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一、儿童敏感期理论的知识体系
敏感期是生物生长过程中的某一特殊时期,在此期间,生物对某些事物的感知程度达到顶峰,其相应的身体机能也急速发展。[1]敏感期理论已成为现代儿童教育的理论框架和实施儿童教育的实践基础。基于对生物的长期观察,杜佛利斯提出“敏感期”概念,他认为,所有的生物都会在其幼年时期经历一个短暂而特殊的时期,在此期间,它对某些事物的感受性达到最大,此后该现象将几乎不再出现。立足于杜佛利斯的理论,蒙台梭利将敏感期与儿童期特征和现状联系起来,提出儿童敏感期理论。经过洛伦兹等人的强化与推广,儿童敏感期理论不断得到解读、论证与归纳,迄今为止,教育学者普遍认同儿童敏感期理论,还有学者提出要“捕捉儿童敏感期”的口号。[2]
在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中,每一种心理品质和能力都有其发展敏感期。基于儿童敏感期理论的知识体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原理:第一,儿童的身心发展存在敏感期,即在某个具体的年龄阶段,儿童各方面的发展呈现出敏感而迅速的特征,儿童在该时间段更容易习得知识与能力。第二,这些敏感期的存在给教学实践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和内容支撑,在此基础上,教育界形成了一套针对该时期的教育措施和计划,形成了对儿童教育教学的独特理解。[3]第三,不同敏感期的内容特征存在极大差异,但敏感期发生的年龄阶段存在时间上的交叉重合,即儿童敏感期仅存在于固定的一个时期。
二、教育实践中儿童敏感期理论的异化
在现今教育实践中,教育界已普遍接受“为儿童提供有准备的环境,让儿童从中获得身心发展”[4]的观点。在实践层面,教育者为儿童创设了有准备的、适合儿童成长的环境。[5]由于儿童敏感期是科学研究的成果,人们相信它的科学性,因此儿童敏感期理论能够对幼儿教育提供一定的指导。然而,儿童的成长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特点,儿童敏感期理论不能解释所有的儿童成长现象。在现实教学中,存在将儿童敏感期具体化、精确化乃至教条化的现象,这与教育目的背道而驰,导致出现新的教育问题。
(一)忽视对象的整体性,教育目的预设化
学前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儿童是兼具自然性与社会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生命统一体,儿童的成长过程是复杂且丰富的。有些教育者在异化了的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将儿童的各个发展阶段简单地划分,且划分得过于绝对和精细,强调敏感期的暂时性[6],其功能在于帮助儿童获得某些机能或特性[7]。同一年龄阶段的儿童有不同的表现,对同一内容也有不同的理解,儿童敏感期是否存在顺应逻辑秩序的形成过程?教育者在实践操作中如何准确地划分敏感期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儿童敏感期理论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儿童?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验证。
有些教育工作者在异化了的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用预设、统一的目标要求每个儿童,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教师无法深入儿童的世界,无法倾听那些儿童带着生命原始冲动的声音,导致教育过程流程化、肤浅化。如今,在预设教育目标观影响下,超前教育现象比较普遍,考试内容决定教育目标是学校的常规操作,教育逐渐功利化。生命的发展不应该受限定。如今,成人所坚信的对于儿童的热情与爱正在不知不觉地扼杀儿童的个性,揠苗助长式教育带来的成就不会长久。[8-10]
(二)统一教育时间,教育内容客观化
以统一时间为基准对儿童进行教育,是儿童敏感期理论的核心。然而,异化了的儿童敏感期理论认为,儿童存在认知能力发展的快捷通道,敏感期被错过或被破坏都会导致教育的失败,且这种失败常难以补救甚至不可补救。[11-12]在“抓住儿童敏感期”的命题下,一些教育者陷入了对敏感期的盲目追随中,一批打着科学旗帜、极具功利性和效率性的早教机构疯狂抢占学前教育市场。在此状况下,教学过程结构化、教学方法模型化,导致教育内容脱离实际、教学过程按部就班、教学器具简单,儿童生命内在的和谐与秩序被破坏,儿童丧失了想象的乐趣和创造力。作为衡量和考察儿童生长发育的标准,儿童敏感期能否作为衡量儿童发展的唯一尺码?儿童敏感期是不是适宜可取的时间标准?儿童敏感期是否能够完整反映生命的本质?这些问题还有待商榷。发展性是生命的本质特征,儿童的发展有自己的节奏,没有统一的发展步伐,儿童的成长不应该被抽象的规定约束,儿童更不应该沦为成人计划的被动承受者。然而,异化了的儿童敏感期理论将儿童的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让儿童的成长绝对化了。
在异化了的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教育主题被教师预先设定,并组织起来,儿童被放置在该系统中,如同生产线上的流动产品,被机械装置无意识地操纵。教育内容的客观化、流程化,加上看似科学的解释,使儿童行为沾染了“真理”的味道,这样培养出来的儿童日趋一致。教育的内容应该抓住儿童生命的内在动力,不应是成人提前设计的单一知识体系。[13]当儿童的成长时段与成人的计划表挂钩,异化了的儿童敏感期理论在其中演化为一种知识霸权,教育内容的规范化和程序化成为必然结果,导致教育脱离营养丰富的自然土壤,儿童的多样化感知被剥夺、成长被搁置,这样培养出来的儿童,难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7]
(三)外控教育过程,教育方法模型化
在异化了的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过程是外控的,在外控教育理念的支配下,各种教育信条和纪律将儿童标准化,奖惩等手段精密地安排着儿童的每一分钟,儿童被塑造成成人理想的模样。有研究窄化了儿童敏感期,将儿童敏感期逐步细分为语言、动作、感觉等多种类别,这种细分的本质是限定,是对儿童生命发展时间的人为划分与恣意控制。[14]在这样的限定下,教师的教育技术精湛与否、教师素养的高低,对儿童的发展都无法有所影响,教育难以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
在异化了的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方法是模型化的,它引导人们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结构模型努力寻找一套符合要求且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对儿童进行统一且有阶段性的训练,教育过程简单化和模式化。立足于不同的敏感阶段,家长或教师会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期待能够引导儿童形成与其敏感期相适应并发生深度互动的联合。因此,儿童被安置在特定的环境中,其异质的天性被强制纳入统一发展轨道,其自主自立的品性无法保持,成人通过不断的训练,将儿童内在的、生成性的和复杂的异质生命属性转化为统一发展趋势,将生命的多样性归结于趋同性。从这一层面上看,儿童教育方法中的引导性不过是一个人为设定的流程,教育的无效性因此产生。
教育的意义在于它将儿童与外在世界联系起来,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实现身心与环境的协调。外在的教育目的不应该成为教育的指挥棒,儿童的主体性应该被尊重,教师要根据儿童的兴趣和经验把潜伏在儿童身体内部的能力引出来,释放儿童无限的发展潜能。[15]
三、教育实践应回归儿童敏感期理论的本质
社会生活中的节奏和标准固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对节奏和标准的过分追逐是与生命的自然发展相冲突的。教育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儿童应该从中获得健康和快乐,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井然有序、朝着同一方向过着“复制式生活”。
(一)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应满足儿童成长的需要
教育应保障儿童按照其特有的节奏和张力成长。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要关注儿童的生活体验。儿童的精神生活与成人不同,儿童对世界万物寄予着特殊的感情,持有独特的观点,教育者应尊重儿童成长的本能需要,把神话、童话交给儿童,允许他们自发地游戏、歌唱。[16]
儿童的成长需要生活体验的支撑,统一的敏感期时空内,儿童可能对成人安排的教育内容不感兴趣,无法保持较长时间的注意力。儿童往往对那些被成人视为无足轻重的事物产生好奇心并积极探索。事实上,正是那些在成人眼中“无聊”的行为引导着儿童积累生命成长的必备经验,一旦儿童的这种兴趣受到忽视,儿童内在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将受到伤害。[17]那些企图用成人的观点和情感对儿童进行控制的思想是不可取的,基于此类思想衍生出的教育行为是违背自然的行为,会打乱儿童的成长节奏,泯灭儿童的特性,阻碍儿童的健康成长。
(二)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应尊重儿童成长的差异性
在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需要尊重儿童成长的差异性。儿童成长的差异性通过个体的纵向积累和创造表现出来。生命的成长不是时间和数量上的简单累积和增加,而是一个充斥着无限可能和希望的、不可逆的差异化运动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儿童的成长与表现需要教育者用积极的、发展的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儿童成长的差异性也通过儿童群体的横向比较表现出来。已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同龄儿童之间,个体的生长状态也带有显著的个性特征,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的生命时间表。因此,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应该立足于儿童生命个体的差异性与特殊性,满足儿童的个性化需要。
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要引导儿童生命潜能的发展。理想的教育是使人树立超越现实的理想并将其付诸现实[18],儿童期特有的开放性、生成性与未完成性为实现理想教育提供了现实条件。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的任务应该是激发儿童的无限潜能,引导儿童实现生命的超越与完善。教育者首先应该看到儿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在某些不为成人重视的领域,智慧的幼芽也许正悄悄萌生,这需要教育者善于观察并对其进行积极的唤醒与引导。其次,教育者应该重视儿童创造性的发挥,营造创新文化,提高教师创造意识,激发幼儿兴趣。最后,教育者应该营造自由的教育氛围,儿童能够自由地决定活动的时间、地点、方式,自由“是教育的核心,是儿童的权利,不容侵犯”[19]。
(三)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应遵循儿童成长的自然节奏
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应尊重并匹配儿童成长的自然节奏。生命有机体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时间大纲,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确保儿童的生长发育。儿童成长的自然节奏需要通过感知经验体现出来,生命活动像一场包含过去、携带现在并走向未来的巨大时间之流。[20]生命的时间是流动的、生成的、多样化的,不同的生命之间和同一生命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存在差异,且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多重影响,表现出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特征,展现出独特的节奏与张力。教育时间与儿童成长的生命时间匹配,是教育活动对独特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义的肯定与尊重。因此,教育要允许儿童充分运用自己的天赋与能力,按照自己生命的内在时间有条不紊地发展和成长。反之,如果儿童被外在精确的时间框架束缚着,其特有的生命成长将不能有序展开,教育往往适得其反。
实现生命的平等对话,是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教育的必然途径。如今,在儿童敏感期理论指导下的教育,节奏越来越快,“被教育”“被发展”是儿童成长的常态,无论教师运用多少启发式教学法,体制化的教学过程中儿童总是被动消极的。[21]教育者要看到儿童处于未完成状态,具有不可遏制的自由性和活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生命之间的交流、对话与融合构成教育的生命。[22]一个好的教师在教学中是有所节制的,不会过度输出自己的想法,并能为儿童的自主构建提供充足的空间与条件,让儿童在与环境的深入互动中逐渐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