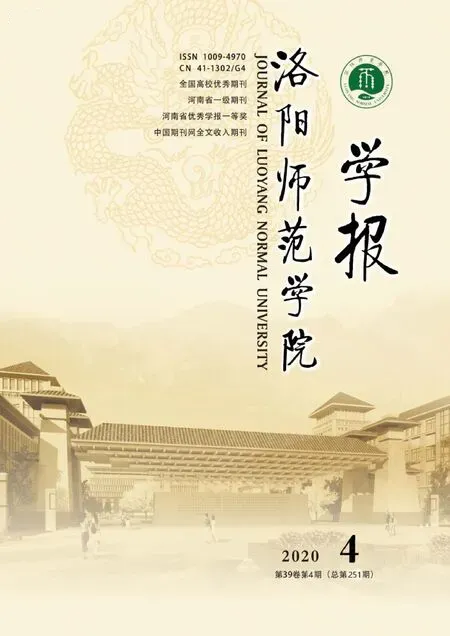“议程设置功能”在五四文学中的理论显现
杨 筱,封兴中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一、前言
五四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既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也得力于大众传媒的发展。五四时期的大众传播主要是依靠纸质传媒来实现的,如报纸、期刊等。这些纸质传媒,作为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的重要工具,对五四文学的发生、发展、传播、接受具有重大意义。正如王富仁所说: “中国现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其本身就是与文学媒体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现代印刷业的发展,没有从近代以来繁荣发展起来的报纸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1]
“议程设置功能”是研究大众传播效果的理论假说之一,最早见于《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是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珀尔希尔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2]194
这一理论作为一种传播效果的理论假说,在很大程度上与五四文学的传播发展历程相契合,并且贯穿于这一时期的作家创作和期刊的创办刊发之中。一方面,这是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传播主体与媒介的目的性显现,这一时期的传播主体(即作家)与媒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设置“议事日程”来强化事件,建构起受众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不断强化民众对于周围“大事”的关注,强化受众的导向需求,以达到启迪民智、解放思想的效果。另一方面,“议程设置功能”同样贯穿于五四文学受众的接受过程之中,受众对传播主体与媒介设置的“议题”的高度关注能够促进信息的快速传播。五四时期家国意识的觉醒以及新式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现代思想烛照下的新青年,他们时刻关注着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发展,这种关注恰与五四作家与媒介的导向高度一致,从而在接受层面促进了五四文学的传播与发展。可以说,五四文学的传播集中体现了“议程设置功能”这一大众传播的效果。本文通过对传播主体、媒介、受众、“议题”四部分的概述来阐释五四文学与大众传播的紧密联系,进而在跨学科研究的意义上丰富对五四文学的研究。
二、传播主体的“议程”设置
五四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多秉承 “启蒙主义”的思想,正如鲁迅所说: “说到为什么作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综观鲁迅的文学创作,从1918年发表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到《阿Q正传》《祝福》《故乡》《社戏》《孔乙己》《风波》, 以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杂文等,无不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一方面,揭露封建礼教对人的残害。另一方面,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以达到对“立人”——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追求。可见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有着明确的“议题设置”的,是为改良人生而进行创作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传播主要就是通过对“议题”的设置来实现其发展的,不论是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还是创造社的“为艺术”的追求,皆是将文学的创作与传播设置在一个有目的的框架之中,以使文学摆脱旧的范式,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问题小说”的作家们往往在作品中提出“社会议题”,如冰心反映封建家庭摧残人性的《两个家庭》,庐隐反映女性生活的《海滨故人》,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以及王统照的《微笑》,等等,都直指现实。但是由于问题小说作家缺乏经验,往往以“爱”和“美”的方式对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此外,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群将目光放在乡村生活方面,并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对国民劣根性及封建习俗进行了批判。创作社代表作家郁达夫也在《沉沦》等作品中描写了作为“弱国子民”所遭受的情感压抑,寄予的是作家对国富民强的殷切期盼。
知识分子在诗歌、散文、杂文、戏剧等领域的创作与传播同样彰显着“议程设置”的功能。尤其是杂文,批判性较强,且与现实联系紧密,“议题”设置效果明显,有鲜明的目的性。如鲁迅的杂文集《热风》取材广泛,有对封建家族制的批判,有对“国粹”的取舍与批判,也有对麻木灵魂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还有许多作家将杂文作为陈述时事的武器,刘半农发表《实利主义与职业教育》来反对当时流行的“实利主义和职业教育”,钱玄同在《回语堂的信》中反对非人道主义观。五四时期的诗歌、散文相对来说多是“主情”的,以抒发作家主观情绪为主。如周作人的散文,注重对生活情调的美的发现。郭沫若、湖畔诗人的诗歌多是直抒胸臆,无所计较,但他们作品中的情感同样具有精神指向,主要包括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于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追求。在戏剧领域,五四时期两个重要的戏剧团体——民众戏剧社和上海戏剧协社,都倾向于“写实的社会剧”和面向民众的戏剧艺术,显示了不同作家在五四时期共同的追求。
最后,需要强调一下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这场“双簧戏”正是五四知识分子自觉运用传播策略推动新文学发展的有力证据。它充分显现了“议程设置”的过程。首先,复古主义思潮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然而并未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意见,这是“议程设置”的前提。其次,正是由于有反对的声音,钱玄同才将各种反对意见总结归纳起来,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信,再由刘半农写复信一一予以批驳,这便是对于“议题”的着重介绍与宣传。再次,便是“议题设置”的传播效果,两信同时发表,名为《文学革命之反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可见,五四文学的传播与发展,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学思潮,都是知识分子自觉运用“议程设置功能”理论传播策略的结果。
三、媒介的“议程设置”——环境再构成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2]195环境再构成,是指传播媒介对于信息的选择是有目的的取舍活动。传播媒介会依据自己的需求或者刊物的侧重点进行筛选,进而对他们认为重要的部分进行整理,最终以“报道事实”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五四文学刊物作为传播媒介的一种,在进行传播时也会有所侧重,进行取舍,发挥媒介环境再构成的作用。
五四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据统计,1921年到1923年间,全国出现的大小文学社团共40余个,出版文艺刊物50多种。到1925年,文学社团和相应刊物激增到100多个。[4]如由沈雁冰全面革新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小说月报》,又相继创办了《文学旬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创造社的主要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新月社的主要刊物是徐志摩于1926年接手的《晨报》的副刊上开辟的《诗镌》,作为他们的代表性刊物,此后又创办了《新月》月刊、《诗刊》和《学文》。此外还有语丝社的《语丝》周刊、莽原社的《莽原》周刊。浅草社刊物有《浅草》季刊,而且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出过《文艺旬刊》。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北大新潮社也办有自己的《新潮》杂志。还有作为新文学重要阵地的《新青年》杂志。这些刊物作为五四文学传播的重要媒介,都在以自身的力量建构着五四文学的传播环境。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原《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六义”作为对青年的寄语: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此“六义”同时也是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对于发刊内容的要求与把控,体现了《新青年》这一媒介的主观选择,以及对营造 “科学”与“民主”环境的追求。在《新青年》杂志周围集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皆以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为己任进行创作和发表。《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皆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进而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新青年》从第四期第四卷便开始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稍后《每周评论》《新生活》《新社会》《民国日报》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从而形成了杂文创作的浪潮。杂文专栏的纷纷设立,可以说是媒介出于构建环境的主动选择,毕竟杂文篇幅较短,且与时政联系紧密,适合用作社会批评的武器。
《小说月报》作为五四文学的另一重要媒介,在1921年以前曾是鸳鸯蝴蝶派的基地,主要刊发描写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茅盾在1921年接编之后对其进行了彻底的革新,正如《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介绍的那样: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小说月报》不再刊发以游戏或消遣态度进行创作的作品,将表现社会问题、新旧冲突的作品作为选择的重点。《小说月报》发刊标准的重新定义,以及文学作品的刊发传播为受众设置了新的关注点,创造了有利于建构现实的传播环境,这也是它成为五四文学传播重要阵地的原因之一。
四、受众的认知与导向需求
麦库姆斯和肖提出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效果显示: 大众传播对于“议题”的强调程度与受众对于“议题”的认知程度之间有着一致性。大众传播对于“议题”愈强调,则受众对于“议题”的关注和了解愈多。
五四文学作为唤醒“沉睡的国民”的第一声巨响,它不遗余力地抨击封建社会与专制礼教对国民的残害,希望能够以文字为武器来影响受众的认知,从而达到思想启蒙的效果。虽然在五四文学发展初期,反对的声音络绎不绝,但是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与社会政治、经济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五四文学得到了广泛传播,受众的认知不断被影响,思想得到解放,文学语言、文体、观念得以革新,广大民众也开始觉醒,并一步步走向进步与发展。
五四文学的传播之所以能够对受众的认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离不开受众自身对于五四文学设置的“议题”的关注。受众的认知与媒介的导向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可以达到高度一致。五四时期,民众身处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虽然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彻底去除封建礼教、封建意识,外患仍然存在,这些因素都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所以对于受众来说,国家与社会的稳定、民主政权的建立便成为受众关注的“议题”,这同样也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问题小说的热潮便是作者与受众关于“议题”契合程度较高的例证。一方面,作家关注着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并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期引起受众的注意。另一方面,受众以文学文本的形式接触社会问题,这也成为他们了解社会和接触社会问题的途径之一。
虽然五四时期的新式教育,培育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独立思想,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新式青年;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对于时代发展或者社会变革都能有着清醒且正确的认识。多数人在混乱的年代里迷茫不定,没有方向,他们作为受众并不能确切地对信息进行选择,于是五四文学的传播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导向需求”。这一概念是一些学者在研究“议程设置功能”理论产生的原因与条件时提出的。他们认为,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渴望了解的课题,但是外部世界丰富而驳杂,无数信息充斥其中,我们无法选择应该关注或者重视的信息,大众传播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导向,帮助我们进行判断与选择。对于不确定的受众来说,五四文学为他们提供了对信息进行选择的倾向性暗示,五四文学作品中对于爱情自由、个性解放、民主的追求,以及对封建意识、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能够使受众确定自己的关注点并形成自己的认知,这正是大众传播发挥效果的方式,也是五四文学能够促进思想解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五四文学“议题”关键词与传播效果
“议题”的筛选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集中的“议题”报道与关键词的设立会加强对受众的影响程度。五四文学作品作为传播的文本,是一定信息的载体。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议题”关键词: 国民性批判、反封建、个性、爱国主义、感伤情绪等。
从1917年发起文学革命开始,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就主张将文学视为改良社会人生的工具,在现代“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借文学启迪民智,促进思想解放。国民性批判与反封建是五四文学创作主题中的应有之义,有着高度的理性批判精神。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作品对于麻木、冷漠的国人形象的刻画,对封建陋习的揭露,都渗透着对国民性的思考与启蒙的理念。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五四文学的主调,五四知识分子受过先进的教育,更有着对国家富强的期望与寄托。闻一多的《红烛》《死水》是以一名民族战士的姿态高唱着爱国主义的诗歌。郁达夫的《沉沦》以一名在日青年的身份,强烈企盼着国家的富强。
五四时期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开端,也是历史的转折期。在这一时期,广大青年与知识分子开始觉醒,自觉追求“科学”与“民主”,然而对于未来出路的探索却是充满迷茫与曲折的。所以,这一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表现出苦闷感和孤独感。如鲁迅的《伤逝》直击知识分子出走后的现状。冯沅君的《隔绝》、王以仁的《孤雁》等表现知识分子追求的痛苦与矛盾。总体来说,五四文学传播设置的“议题”以思想启蒙为导向,有着爱国主义、个性解放、反封建的追求,还有些许感伤情绪的传达。
这些“议题”作为大众传播中的信息的一部分,传达的并不仅是知识或消息,而且包含着特定的观念和价值,它们不仅是告知性的,而且是提示性或指示性的。[2]112正如李普曼曾指出的那样,信息环境能够通过制约人的认知与行为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些“议题”的设置最终是通过建构现实来显现其传播效果的。这些“议题”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以媒介为支撑,产生了深远的传播效果,对文学的发展以及社会诸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五四文学传播带来的是文学语言、观念、内容形式的解放与革新。在语言和内容形式上以白话为主,摒弃了传统的文言文和文学格式,广泛吸收、借鉴外国文学样式,使文学更加适用于现代生活。同时,五四文学以启蒙为己任,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介绍与推动下,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运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研究五四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文学的发展与大众传播之间的紧密关系,五四文学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大众传播效果的发挥。在五四文学传播现场,不论是五四知识分子的目的性选择、媒介的环境再构成、受众的认知与导向需求,还是具体的“议题”关键词,都是大众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具体体现。实际上,无论是五四文学抑或现今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大众传播,跨学科地运用传播学的知识来研究文学,能够打破学科壁垒,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从而获得不一样的结论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