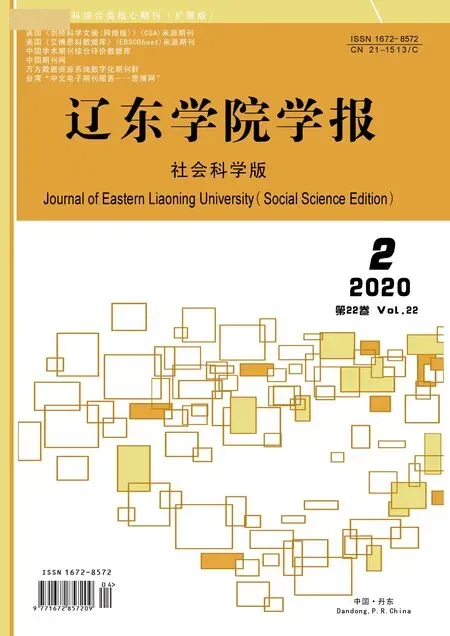坪内逍遥的诗学理论与老庄思想
潘文东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坪内逍遥(1859—1935)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在1885—1886年间以九个分册陆续出版了他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神髓》[1],在书中作者批判了当时日本小说充满着封建道德说教和情节胡编乱造的弊病,指出小说的任务在于描写人情,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空间。这部著作在文学史上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明确提出“小说是艺术”的文学主张,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较早地从美学层面对小说的艺术性进行的探讨。日本学者龟井秀雄认为这与美国著名小说家兼文艺评论家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43—1916)1884年在《小说的艺术》(TheArtofFiction)一文中正式提出这一观点几乎在同一时期。由于坪内逍遥实际撰稿应该在1884年以前,所以时间上可能甚至比西方还要早[2]3。坪内逍遥希望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艺术之美,这样小说将来一定会成为“最大的艺术”[1]32。《小说神髓》理论的实验性小说《当世书生气质》出版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而名噪一时。同时坪内逍遥毕业于当时日本的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毕业后在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任教,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青年,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艺术创作、审美等方面的诗学理论深刻影响了明治时代的青年才俊,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了日本近代文学发展的中坚力量。1891年前后,坪内逍遥在《早稻田文学》等杂志上陆续发表文章,提出了以“没理想”为中心的诗学思想,得到当时学界的极大反响,还引起了与著名文学家森鸥外的文学论战,称为“没理想论争”。根据坪内逍遥本人叙述和一般评论家的研究,艺术“无目的性”“妙想”“没理想”等思想大多来源于西方的诗学体系,但如果我们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其中明显带有东方诗学的特征,尤其老庄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在坪内逍遥诗学理论建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
《小说神髓》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从其结构来看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碎片化的小说批评,而是逻辑严密的文艺理论著作。在“绪论”后面的第一章是“小说总论”,集中讨论了艺术的功能和本质、“小说是艺术”等基础理论问题。坪内逍遥指出“所谓艺术(美术)原本不是实用的技能,而是以娱人心目、入其妙神为其‘目的’。由于入其妙神,观者自然感动,忘记贪吝之欲、脱却刻薄之情使之乐于其他高尚之妙想。这是自然的影响,不可说是艺术的‘目的’。”[1]27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否定了当时主流诗学体系下艺术具有为道德、宗教服务的功利性目的的传统观念。
我国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一般都认为艺术首要的就是道德教化的功能,例如《论语》中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文以载道”的思想长期统治着中国文学,虽然中国也有“诗缘情”之说,在历史上也有很多阶段出现了一批批浪漫主义文学家,但是在儒家思想占有统治地位的中国始终成为不了气候。西方传统社会的审美观也与之相似,例如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诗歌具有“净化”“陶冶”的功能。古罗马的贺拉斯则要求“寓教于乐”。真正明确提出艺术是无功利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鉴赏判断是毫无利害,在审美过程中,“每个人必须承认,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3]41艺术和审美中的无功利思想逐渐被欧洲很多文学家接受,虽然现在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坪内逍遥从西方的具体某位文学家或思想家受到影响,但当年坪内逍遥可以在东京大学图书馆看到从英国进口的原版学术综合杂志来了解西方思想界的动态[4]414。当时英国的文艺界,唯美主义运动正不温不火地展开着,这种文艺思潮反对艺术的功利性,提倡纯粹的艺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因此这样的文艺思潮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或者说“时髦的”文艺理念引入日本国内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提倡艺术的无功利性也不是西方人最早发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子、庄子已经有类似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了。老子认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虽然这并不是老子专门针对艺术和审美提出的,而是对整个宇宙的看法。他认为要使人心保持虚静的状态,才能观照宇宙万物的变化的本原——“道”。这个“道”也就是艺术的本质,它是完全远离人类的实际功利的。庄子对艺术的无功利性有着更加丰富的解释,其中一则寓言是这样的:“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5]546(《庄子·田子方》)庄子认为只有心灵不受功利束缚、达到自由无碍境界的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内篇的第一篇是“逍遥游”,反映了他希望自由自在地在宇宙间翱翔的理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5]14“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5]21,“得至美而游乎至乐。”[5]539所谓“逍遥”就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无所挂碍,而“游”就是去除了一切功利心,任凭心灵自由活动。这种理想也是坪内逍遥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坪内逍遥从东京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像他的同学一样走上仕途,而是甘愿从事较为自由的职业——教师。他的同学或好友也多次请他担任一些行政工作,他都谢绝了,他的一生都尽量与政治保持距离。坪内逍遥原名坪内雄藏,又名勇藏,他在《小说神髓》和一些文章中自称“逍遥”或“逍遥子”,很好地反映出老庄的思想对他的影响。
二
坪内逍遥对艺术的本质有很多表达方式,其中最多用到的是“妙想”一词。例如:“由于入其妙神,观者自然感动,忘记那些贪吝之欲、脱却刻薄之情,使之乐于那些高尚之妙想”[1]27,“其妙在乎通神,使看者不知不觉中如神飞魂驰般感得幽趣佳境,此乃本然之目的,乃艺术之为艺术也。然以其气韵高远、其妙想清绝而提升人之素质只是偶然的作用”,“人类脱离野蛮时代起就无不以风流之妙想为娱、无不爱高雅之现象”,“看一看那些蒙昧野蛮的民族,一味沉湎肉体之欲而不懂得以妙想为乐。”[1]28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坪内逍遥所认为的艺术的“本义”(本质)是通过“娱人心目”使欣赏者“自然感动”或“神飞魂驰”,以“高尚之妙想”为乐。因此艺术创作或审美中追求“妙想”也就成了艺术的终极目的或归宿。而与此相近的表现方式还有“幽趣佳境”“气韵高远”“高雅”“妙神”“美妙之情绪”。日本的诗学深受中国影响,很多审美范畴、概念、术语也多来自中国,这些词汇的语义比较含糊,相互之间的区别或联系也不够清晰,而且由于时代不同或使用者不同又产生了不同的意义,这也许是东方诗学体系的特点吧。我们如果把上述术语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有些是名词性的,如:趣、境、气、韵,而有些是形容词性的,如:幽、高、佳、雅、美等。当然也有一些词兼有名词和形容词的性质,如“神”“妙”等。这是一套东方式(中国)的审美话语体系,与西方美学体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系统,所以两者在很多地方不一定有相对应的东西。中国的诗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它是融入在东方的哲学本体论之中的。在中国的哲学本体论中,最高的范畴是“道”。《老子》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6]73“道”是原始混沌的,它可以产生万物,没有意志没有目的的,它既不是客观(物质)也不是主观(精神)的。道是根本性的而由于“道”的运作产生了“气”,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6]233“气”可以看出是“道”的机能的体现,所谓“气韵”就是“道的本体”的运作的表现。艺术和审美中的最高范畴经常用“妙”“神”来表达。在《老子》中有多处用“妙”字来表达的,它的意义可以从以下段落来体会,“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6]73(《老子》第一章)“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6]129(《老子》第十五章)这个“妙”字可以说是《老子》的诗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在西方美学体系中,“美”是最高的范畴,而老子认为美是相对的,两者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6]83(《老子》第二章)因此“妙”是要高于“美”的上位概念。汉代以后,“妙”被广泛使用在艺术和审美领域,出现了“妙悟”“妙赏”“妙心”等范畴。
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所用“妙想”也是当时美术界常用的术语,例如大内青峦在《大日本美术新版绪言》“杂记”中明确指出:“严沧浪论诗特拈提‘妙悟’二字,王阮亭云诗尚‘神韵’,皆谈所谓美术之妙想也。……毕竟画与诗互有长处,诗难以言尽之处画为之,画难以写尽之处诗可自在言之。共谓唤起超天真而惊造化之妙想。”[7]17同时,《小说神髓》第一章“小说总论”中提到的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1882年曾在日本美术协会的前身“龙池会”做过演讲,大森惟中对演讲进行了整理并把它翻译为日语,以《美术真说》的书名出版。他把费诺罗萨有关“美”应有的特性也翻译为“妙想”。虽然当时文化界各人对“妙想”的内涵也许有不同,但这个词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较为通行的词汇了。
三
在《小说神髓》中坪内逍遥也借用了当时文化界通用的术语“妙想”来表达美的本质,在文本中作者反复强调美的本质是“娱人心目”“以妙想为乐”“使看者不知不觉中如神飞魂驰般感得幽趣佳境”,因此“妙想”首先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同时它还具有审美的愉悦性、提升审美主体精神境界的超越性等特点。虽然作者在“小说总论”中反复声明艺术和审美也有实际的功用,“这是自然的影响,不可说是艺术的‘目的’。”[1]25-26这里似乎存在着前后矛盾,而且在《小说神髓》第三章“小说的主眼”,作者提出小说的主脑(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描写人情,小说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必须揭示“人生的大机关”“人生的奥秘”等,和作者在《小说神髓》第一章中阐述的艺术和审美的无功利性无目的性有着较大的裂痕。坪内逍遥也许意识到这个矛盾,所以他在《小说神髓》第四章“小说的种类”后面加了第五章“小说的裨益”,强调小说的“裨益”是小说自然的结果而非作者主观刻意所为[8]。
虽然《小说神髓》总体来说理论上还是说得通的,但其中的缺陷还是使得理论不太圆满,因此坪内逍遥试图通过丰富其理论加以阐释。二叶亭四迷在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影响下创作了写实主义小说《浮云》,他根据俄国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的美学理论撰写了论文《小说总论》,而别林斯基的美学理论来源于黑格尔美学。二叶亭四迷指出“凡有形(form)则其中有意(idea)。意依形而现,形依意而存。”[9]404他主张以“实相”(现实社会)写出“虚相”(世界的真理、本质)。坪内逍遥这个时期基本认同了这些观点,他在《小说神髓》再版时特意在书的末尾加上了一段声明,说现在的观点已与书中不同了,以后有机会加以披露云云。此后,坪内逍遥在演讲或发表文章时开始使用“美的真理”、idea等说法。
进入19世纪90年代,坪内逍遥负责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文学科教学和学科建设,虽然也发表了一些小说,社会反响不是特别强烈,同时他又积极参与日本的戏剧改良运动,所以逐渐放弃了创作小说。他尝试通过引进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戏剧改造日本的戏剧。莎士比亚戏剧的博大精深给了他极大的启示,1891年10月《早稻田文学》创刊号上刊登了坪内逍遥的《〈麦克白评释〉绪言》,文中提出了他对文学创作和评论的观点:“评释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如实按照文中字义、语法评释,再加上修辞分析;另一种对作者的本意或作者的理想进行发挥、批评和评论。就我来说,我采取第一种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完全按照读者的心来解释。因为他的杰作是容纳‘万般的理想’的作品、犹如不知底部深浅的湖。而且它可以广泛容纳众多理想,而它本身是‘没理想’的。这和造化自然相似。钟的声音、花的颜色因听者和观者而异。造化的本体是无心。若要赞美莎士比亚,可以赞赏其刻画人物性情活动技巧之高明,其比喻之妙、其想象之妙、其构思之妙可以说空前绝后。但是如果要说其理想如大哲学家之高明的话,让人难以接受。而正是他的‘没理想’才应该称赞。”[10]180-187当时坪内逍遥为了着手戏剧改良和指导学生演戏,对莎士比亚和日本江户时代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进行研究。《早稻田文学》杂志创刊的目的是刊登与学习有关的内容,所以坪内逍遥发表论文的初衷对学生课外学习的补充。但是这篇文章遭到了森鸥外的批判,他在自己创办的杂志《栅草纸》上发表《早稻田文学的没理想》等文章对坪内逍遥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引发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没理想论争”。森鸥外指出:“逍遥以纪实为宗旨厌恶谈理、提倡‘没理想’,而我对此难以认同。逍遥的‘没理想’的论点是由于他没看到世界上不仅存在着一个‘现实’(real),还充满着‘想’(idea),当我们好好观察理性界、无意识界时,可以发现那里有先天的理想。例如:听钟声的时候有人听出了无常、有人听出了快乐。但是从中感到美也是一种。或者这里看到美丽的花,有人看出了悲伤、有人看出了喜悦。但是也有人感到了美。在这里,从钟声和花中感到美的并不是因为耳朵好好听、眼睛好好看的缘故。而是因为那个人有着感觉美的‘先天的理想’。”[11]森鸥外所援用的理论是德国先验唯心主义哲学家爱德华·冯·哈德曼的美学理论,这在当时非常新奇,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反响。其实两人在正式开始论战之前已经就相似的问题各自发表了文章。1890年12月坪内逍遥在《读卖新闻》发表《小说三派》、1891年1月在《读卖新闻》发表《不知底部深浅的湖》、1891年5至6月发表《梓神子》等文章,森鸥外对此发表了《逍遥子的诸评语》。其后两人不断发表文章围绕“纪实”和“谈理”进行论战。
其实坪内逍遥所谓的“没理想”并不是中文意义的 “没有理想”,据他在《辨“没理想”的语义》(坪内逍遥《早稻田文学》,1892年1月)中解释说“没理想”并不是“无理想”也不是“不要理想”,而是“没却理想”,即隐藏作家主观意见,使文艺作品像大自然一样成为能够容纳“万般理想”的载体[12]177。坪内逍遥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没理想”的典范,他指出之所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与自然极其相似,并不是说他描写的事件人物与实际的相同, 而是说他的作品在读者心中无论如何解释都酷似造化。人们可以试着看一下自然。以谦虚平淡之心来看,自然只是自然,也就是“自然而然”,不见有偏向善恶的任何一方。坪内逍遥在有关“没理想”的论文中反复强调“自然”“造化”,这些关键词在《小说神髓》也频繁出现,如在“小说的主眼”中作者借用日本将棋的棋子做比喻来描绘人生和世界:“着棋者就是造化翁,棋子好比是人。造化的着法是不可思议的,与观棋者的想法大不相同。”[1]62坪内逍遥在论述如何达到“没理想”的时候总是用“自然”“造化”来描述,因此准确把握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就是解开“没理想”的重点。
从坪内逍遥的文本中“自然只是自然”的用法来看,很明显深受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169按照一般说法,“道”可以姑且视为宇宙的本体。“道法自然”就是宇宙的运行法则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坪内逍遥的“自然只是自然”中,前一个“自然”可以理解为大自然(宇宙),后一个可以理解为自然而然。莎士比亚的作品达到了与自然宇宙相齐的程度,因此,坪内逍遥认为他是人类空前绝后般伟大的文学家。
“造化”虽然是自然的别称,从其字面意义来说就是“创造化育”之意,用来如称呼“自然”就是因为自然有自我创造化育的机能。《庄子·大宗师》:“今以一天地为大鑪,以造化大冶。”[5]190(现在把天地当作大熔炉,把造化作为大铁匠)虽然这里的“造化”仍然是自然宇宙(或者本体、也有学者认为是“道”),但语义着重在于自然的自我创造化育的机能。逍遥认为造化之本体是无心。莎士比亚的杰作颇与造化运作很相似。上至富于审美见识之学者,下至一知半解者都极力赞赏他的作品,其中一个原因是听到前人极力赞赏所以就不假思索接受了这种观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度量极其广阔,能容纳众人的嗜好,犹如自然风光能愉悦万人之故。由此可见,坪内逍遥所说的“没理想”确实不是“没有理想”,相反是能够容纳更多的理想(寓意),如自然宇宙那样无限丰富。在与森鸥外论战过程中,坪内逍遥也确实觉得“没理想”的说法不够严密,所以他在辩论中承认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方便”。
虽然坪内逍遥的诗学思想中有很多来源于老庄思想,但是进入明治时代,日本社会整体上崇尚西方文化,东方的诗学体系被认为是过时的、前近代的。在“没理想论争”中,森鸥外也抓住这一点加以攻击,他批评坪内逍遥使用这些佛教老庄的词汇,意义似是而非、混沌暧昧,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教色彩。因此坪内逍遥尽量回避阐明自己的诗学理论来源于老庄思想,而标榜自己的这些诗学思想来自西方的文学思潮,他在《没理想的由来》一文中列举了自己的思想来源于丹纳、波斯奈特、爱德华·道登等西方众多的文艺理论家,尤其他特别引用了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爱德华·道登(Edward Dowden,1843—1913)在著作《文学的解释》的一段。“很多伟大的作品,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并不能学到一点儿东西,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正如我们进入大海,我们沉浸在大海中,波浪击打着我们,我们欢笑,我们精神焕发,微风和海水包围着我们。共享这自由和无拘无束活力的就是我们所热爱的大海。在吟唱着神秘圣歌的大海中,我们获得了健康和快乐。”[12]295-296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像那汇聚着全人类丰富多彩精神的浩瀚大海,而这些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精彩评论使坪内逍遥找到了东西方诗学的契合点,领悟到了艺术的真谛。坪内逍遥在担任早稻田大学文学科负责人时就一贯主张“和”“汉”“洋”三种文化融合。在其诗学思想占有中心地位的老庄思想崇尚“虚空”“逍遥”“自由”,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近代西方诗学思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西方近代诗学是在追求个性解放等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然而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殊途同归是很自然的,而且在明治初年思想空前自由的气氛中,东西方诗学的融汇又激发了新的创新,使既具有世界意义又保持民族特色的日本近代诗学思想为日本近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