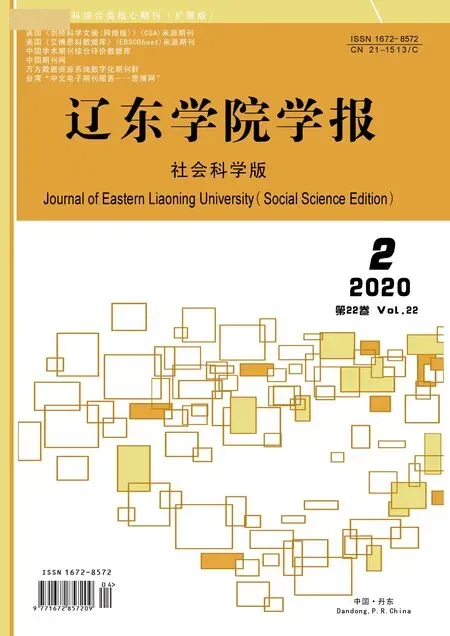当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与传统乡土精神的重塑
——试论《望春风》的主题意蕴
韦 露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阳 550025)
格非由早期的先锋叙事逐渐向传统回归,从“三部曲”中对梦的乌托邦的追寻,到《望春风》中的精神返乡,格非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现实生活,并对现实情状作出文学性的回应。他以知识分子的睿智,为我们展现了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笔墨字间里透露着一个学者对文化传统陨落的隐忧,直至《望春风》的出版,他对乡村的这种饱满的情绪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望春风》全书以主人公赵伯渝的记忆流动为线索结构文章,采用中国古典叙事艺术中“列传”的方式,编排主人公“我”记忆所到之处儒里赵村的各色人物。故事讲述了20世纪中后期江南儒里赵村50年间的人事变化和历史兴衰,在大大小小70多位人物命运的叙述中,为我们呈现了江南水乡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步步走向衰落的过程。
在他们的故事里,混杂了时代的变迁,命运的反转,揭示了他们人生的无常。在小说文本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农耕文明孕育下的乡村伦理失调,道德信仰崩塌,权力被资本裹挟。格非寄予在《望春风》中的不仅仅是对于故乡和个人乡村生活记忆的回望,小说还对当代农村人伦关系的异化和政治权力的更迭进行了揭示,展现了乡村社会越来越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当先的价值观等现实景象,传达出作家对社会变革时期乡村社会伦理危机的焦虑和忧思[1]。在对造成这一系列现象背后原因的批判反思中,格非又试图从精神层面告诉人们,在资本金钱的价值观社会中,我们该如何坚守淳朴、宽容、勤劳的优良传统。
一、告别故乡:诗意的回望
中国的乡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是一个熟人的社会,个体的日常活动主要围绕着农业生产而进行,由于要面对常变的自然和经营琐碎的农事,农民自发地形成了互帮互助的默认契约关系。费孝通将其定义为“差序格局”,指的是由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有等差的次序关系,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他用水波来比喻道:“中国乡村的格局犹如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2]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农村是以家庭为沟通方式所构成的熟人社会,个体行为受到道德观念的自觉约束和规范。历代以来,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促使这一传统发展到现在。格非的《望春风》写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借助文学想象对故乡的人事进行了深情的回望,并试图通过回望,向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乡村伦理文化,作文学性的告别。
(一)诗礼故乡的人性美
旧中国的农村,存在着许多可贵美好的人性,它们频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像废名、王鲁彦、沈从文等一批乡土小说家,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文学作品,将乡土中那些美好人性书于纸上,试图重铸具有生命韧性的民族精神。格非的《望春风》也是如此,它以诗意的笔调记录着朴实大地上的美好人性,为根植于中国乡土之上的民族精神多了一份深层的解读。
小说中,儒里赵村沿袭着善良的人性与淳朴的民风,村民们因为生活需要,邻里之间互相帮助,联系紧密。例如从小是孤儿的赵德正,村民们可怜这个苦命的孩子,每逢有了吃的,都会分一点给他,在村民们的贴补下,德正靠着吃“百家饭”长大。再如被村民们认为是掌握了“天机”的算命先生——父亲,尽管这种职业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但父亲仍能化解人们心中的郁结,是村民们天命靡常时的生活期冀。父亲曾对“我”说过:“人其实都非常脆弱。当他遇到大的灾难和不幸而无力承受的时候,就需要有个人来替他扛着,并给他最后的安慰,让他安时顺变。他可能压根就不信,但他还是需要一个安慰,好把自己的苦难交出去。”[3]78父亲于人们而言,并非只是算命那么简单, “父亲”的职业和为人得到了大家的尊重, “父亲”生活智慧和生活经验得到了村民们的肯定。
儒里赵村在历史的洪流中还展现着巨大的包容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标准超越了时代、阶级、政治等限制。例如独臂的国民党前军人,在这里是会讲故事受孩子们喜欢的“老菩萨”;革命时期的老特务,在这里是受人尊敬充满智慧的算命先生;会弹古琴的风流妓女,在这里却是受人照顾的娇弱妇人等,它包容了许多在特殊时期不同受过伤的灵魂。“远亲不如近邻”成了儒里赵村最质朴的伦理认同,清纯质朴的人伦关系形成了他们彼此的情感凝聚。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外来的政治因素曾给这个村庄带来过冲击,但无一都被它传统文化诗一般的宽厚平和思想所化解,它按照自己的固有的生存逻辑,繁衍生息着。例如小说中的“文革”和“土改”,没有血腥暴力和残酷批斗,非常平和,宗族邻里的关系依然和睦如宾。再例如像高定邦、赵德正等村委干部,他们不仅受到了共产党新时代新思想的教育,同时也承袭了乡土精神中修仁行义的儒家思想,正是二者的兼而有之,使他们在做好一个好干部的同时,也努力维护着乡村几千年留下的乡常伦理。无论是德正还是“父亲”,抑或是高定邦等辈,他们身上的从容、仁义、宽厚,无疑都是传统乡土精神的潜移默化。
正是这些善良美好的人性,在传统文化的浸染中,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尤其是那困境中展示出的善良与淳朴、宽厚与慈爱、平和与仁义,犹如黑暗中的一盏灯,将粗糙的山村装点得诗一般的宁静与雅致。
(二)历久弥新的爱情美
爱情是文学创作常见的母题,它见证着人间最纯真的感情、最温暖的怀抱、最宽广的胸怀。因此,它一直以来都被作家抒写着。《望春风》里表现的是乡土之间微妙细腻的爱情。它简单朴素而又恒久忠贞,它不浪漫却总也相濡以沫。
《望春风》中柏拉图式的爱情,发生在梅芳与高定邦之间。梅芳是小说中豪言爽利的女人,从对“我”父亲的讥讽,到和德正、春琴的作对,都显示出了她的精明强干和伶牙俐齿。但面对爱情的她,却是小心翼翼。在流言蜚语中,她嫁给了高定国。在高定国爱上教书知青小付后,提出与梅芳离婚,“她终于明白,自己当年之所以会嫁给高定国,或许仅仅是为了离定邦更近一些罢了。”[3]264对终于弄清楚自己爱的人的梅芳,命运却跟她开了玩笑。在她离婚后,高定邦为了避嫌,匆忙找了一个寡妇结婚,两个人就这样错过了一辈子。但无论经历过多少非议,在梅芳的后半生,她总是坚定地站在高定邦的身后。比起现代人不能够在一起就老死不相往来的爱情观,梅芳和高定邦式的柏拉图恋爱更显得弥足珍贵。
其实人类最真挚的感情莫如自然而然而成、相濡以沫而居,就像晚年的赵伯渝和春琴一样。春琴从小被认为是“灾星”,她的存在使家里失去了男丁,她的母亲为了延续香火,于是在“父亲”的说和下,春琴嫁给了大她十几岁的赵德正。她曾因为“父亲”对我有过一段时间的怨恨,后来却将对弟弟的爱转移到了“我”身上,对我严令有加,“随着年龄渐长,对于春琴那些有道理或蛮不讲理的命令,我从来没有反抗过。我知道,顶撞、违拗的结果,无非是加深了我对她的依附而已。”[3]309当赵伯渝开出租发生车祸时,被送进医院的他,想到的唯一亲人便是春琴。这时,他才意识到,他和春琴,“在终于走投无路、对糟糕的命运仍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时候,都把投奔对方作为自己不假思索的选择。”[3]388常被命运捉弄的两人,面对生活却像喝白开水般从容,心底里散发出的善良人性极其相似,正是二者心性的契合,才有后来相依为命的同居。他们的爱情没有感人的山盟海誓,却像是久经离别后重逢的老夫妻,你懂得我艰难,我理解你苦楚。春琴和赵伯渝的爱情经历,充分体现了乡土间自然而然的理想爱情,与现代年轻人以物质为前提的爱情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生存而活,为抵抗不幸的命运而活,却又坚守情感的底线,对情感怀有敬畏之心,王曼卿是独特的一个。她有着“逢人配”的称号,从早年被赵孟舒从扬州买回来,到后来与赵德正、高定邦的来往,最后晚年与鱼佬柏生的相守,她以身体为资本,来换取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生存权力。在《望春风》中,小说以童年时期赵伯渝的视角,对王曼卿那所神秘花园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它不仅是儒里赵村男人们梦寐以求之地,更是对不懂世事的“我”、礼平、同彬之辈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当赵礼平试图用积攒了很久的钱去博得王曼卿的 “可怜可怜”时,不料却遭受到了她拼命地反抗。可见,在不公的命运前,王曼卿依然坚守着基本道德底线,在她身上散发着一位女性为了生存而有的倔强生命毅力。
格非对江南历史的书写,撇弃了20世纪70年代末伤痕文学对苦难历史的那种揭示,而是对历史给予了正面非荒诞化的描写,《望春风》中的儒里赵村不再像古华笔下的《芙蓉镇》那样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构陷与伤害。格非是以温情诗意的笔调,叙述了苦难时期人与人之间难得的尊重,让我们在文本里得到了对国家民族痛苦创伤记忆的补偿和慰藉。
二、指向现在:温情的批判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常常成为作家需要肩负的民族忧患意识。而每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总或多或少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历史的扉页上扫落几许污渍,却又总不免重新粘上新的尘埃。因此,正当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时候,作家以自己锐利的眼光关注着这个风云激荡、蠢蠢欲动的时刻,细致入微地窥视到了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某些阵痛。
(一)失去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乡的现代化发展一直是现实主义作家们关注的重点,迟子建的东北黑土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以及格非的杏花江南,这些记忆里的空间开始成为他们的文学挥毫之地。与大多数的乡土小说家一样,《望春风》的书写模式也是关于离开与坚守的乡土小说模式,透露于其中的是格非更加理性和辩证地看待现代化问题。
在现代化这条路上,中国没有哪一个乡村可以置身于世外桃源,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悄然变化着,最明显能够感受到的是农民在一点点地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其实,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3]352在小说《望春风》中,儒里赵村也未能幸免不卷入时代变革的洪流中。来邢桥镇看“我”的堂妹金花说:“早些年,生产队的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现在村子里几乎没什么人种地了。这也难怪,一年忙下来,累个半死,一亩地只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谁愿意干?大家都忙着办厂。”[3]167随着一栋栋厂房的建立,曾经大家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新田长满了荒草,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原来产出的粮食曾养活了这附近几个村的人。后来,来自福建的蒋姓老板看中了儒里赵村这块宝地,他联合着赵礼平采用非常手段将村民们赶了出去,儒里赵村终于在哀叹声中完全失去了土地。
比失去土地更严重的,是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也正在逐步失去。例如,“赵礼平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加盖了几间房,在那里办了一家五金配件厂。高定邦出面阻止,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婶子指着鼻子好一通大骂,最后,定邦也只得由他们去了。”[3]423亲情、乡情,此刻在金钱面前也不过是筹码高低的问题而已。再如,见异思迁的雪兰,在知道“我”母亲的权势不再可以为她带来后半生的衣食无忧时,毅然地选择和上海的技术工人在一起,传统婚姻所秉持的不离不弃和同甘共苦已不再适用于雪兰,雪兰的出轨不仅是乡村传统伦理道德观被扭曲的体现,更是传统婚恋受都市消费主义文化侵蚀的体现。雪兰这样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她父母的指责,反而是默许甚至支持她对婚姻的不道德背叛。这更加说明了,雪兰的出轨不是个例,而是乡村逐渐沦落,伦理秩序日渐崩塌,资本成了一切权力的准则后的结果。
其实乡村失去的远不止这些。《望春风》里懂得察言观色的“算命先生”不会再有人来继承;蕉雨山房里赵孟舒的古琴声再也不会余音回荡;私塾先生赵锡光的三尺讲台也落满了尘埃。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传统技艺、儒家风骨、诗书礼教等等这些曾经构成儒里赵村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东西,也在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到来而逐渐消失。
(二)离开
当《望春风》书写的历史跨越到当代时,温情的叙事渐渐透露出作家对整个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反思与内省。当今农村社会,市场经济正在加速发展,世世代代依靠土地的农民不再坚守土地,更多的农民选择外出工作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随着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优良的乡土伦理道德逐渐失去,同时,正直、善良、淳朴等美好的人性也在土崩瓦解的乡土社会中渐渐离我们远去。
其一,正直的离开。例如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村民在梅芳的带头下为龙英死去的孙子讨说法时,赵礼平却用了50万就平息了这场讨伐,也因为这笔巨款龙英家遗忘了刚死不久的孙子。赵礼平在他们的口中,也变成了“赵董事长”。为了答谢村民们的帮助,龙英家大宴宾客,可是却独独没有邀请梅芳。儒里赵村变成了那个不再为了集体荣誉“有事一起上”的村庄,村民们最后一次以“集体”名义的声讨,也被金钱收买。当初走在最前面,带领着大家为龙英鸣不平的梅芳,在龙英看来却是“越活越糊涂”,梅芳因此还遭受了村里人的刻意冷落,在唏嘘和孤独中度过了晚年。
其二,善良的离开。吃百家饭长大的赵德正,后来成了被村民们理所当然利用着的村干部;为村子开挖水渠的大队书记高定邦,一心想造福百姓,却被奸商赵礼平利用,只用一天,水渠变成化工厂的排污渠,直接污染了村里。高定邦为此大病一场,当他拄着拐杖站在风渠岸边,望着两岸新栽的塔松时,想到自己曾经的努力被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金钱的魔力让这个年迈的老干部既惊叹又失落,感慨万千的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仿佛看到了古老的儒里赵村的明天。当整个村庄被污水污染时,没有人责怪罪魁祸首赵礼平,反而认为是高定邦将村子变得臭气熏天,害他们不得不搬离这里。
其三,淳朴勤劳的离开。在南京工作的同彬,成了村民眼中的 “城市人”,他给人们讲他在城里听到看到的各种奇闻逸事时,他的新身份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村民们被现代文明带来的新奇所感染,城市被描绘成了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古老的伦理和权威不再具有吸引力,铜臭味替代了充满人情味的淳朴民风。村民们不再在地里辛勤的耕种,大家一窝蜂地开始办工厂,由于受技术销售等问题的影响,大多数厂倒闭的倒闭、被收购的被收购,好逸恶劳的风气愈演愈烈。
随着正直、善良、勤劳等这些美好品质的离开,村庄的功能及其在历史积淀中构建的“传统集体”制度正逐步发生蜕变,乡村开始出现精神内核溃散的境况。
(三)改变
在《望春风》的尾声中,格非通过赵伯渝归乡后的见闻,讲述了儒里赵村在失去土地后悄然发生的嬗变。权力意识、金钱意识、土地意识等都在颠覆着传统认知,飘荡在儒里赵村的上空。它们有的令人触目惊心,有的令人痛心疾首,有的却又令人无比心酸。
首先,随着“集体共同感情”瓦解的是个体意识行为的改变。寄托着农民对生活和未来希望的土地没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逐渐退出乡村社会,取而代之的是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因为污水的排入,土地被开发商看上,儒里赵村最后集体搬迁到了朱方镇的平昌花园小区。此时的故乡,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这里臭气熏天,每个人都在忙着搬迁,墙角屋檐到处都堆放着废弃的瓦砾,荒掉的土地上被村民胡乱地栽种着密密麻麻的果树,他们期望的不是春回大地,而是可以获得尽量多的赔偿款。春琴的儿子龙冬不务正业,喝酒吸毒;小斜眼、高定国一类则巴结赵礼平,一起来愚弄村民等等,没有了乡土伦理无名力量的约束,个体的行为规范在法律触碰不到的地方混乱无序。
其次,乡村基层权力也在悄然改变着,权力从德高望重人手里,移交到了资本家手中。曾经那个带领着村民将赵德正从公社武装部救下的高定邦,晚年却指挥不动几个人去开挖水渠,最后好意被赵礼平利用。在见证了赵礼平花钱在一夜之间就把水渠修好后的高定邦,也终于承认“小武松说得没错,时代在变,撬动时代变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也在变。在亲眼看到金钱的神奇魔力之后,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所谓的时代是一本大书的话,自己的那一页,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人翻过去了。”[3]317乡村基层权力的更迭,体现了资本对乡村传统伦理价值的侵袭。
与此同时,人伦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例如,曾经差点被赵礼平强奸的少女赵丽华,在赵礼平飞黄腾达后,成了村里的议论对象,在村里人冷嘲热讽的议论中遭受着精神折磨。父慈子孝的价值观早已被人们忘记。当赵礼平在儒里赵村能够呼风唤雨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把自己的父母放在眼里,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也没能在身边守护。晚年春琴被媳妇虐待,受尽折磨。资本和话语权力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尊严、贞洁、荣誉不再使人们引以为傲,资本主导的乡村,人们唯利是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存在于利益之中。
《望春风》通过对儒里赵村从纯朴秀丽的往昔到现在变为四分五裂,最后只剩下一副残骸的全部过程描写,温情地批判了当下乡村社会为了经济利益,强制性的拆迁土地,并且在追求物质基础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体谅到农民对于乡村情感的诉求,也没有安置好农民由于拆迁带来的情感困惑等问题。不仅如此,小说文本中还体现了由于现代人难以满足的金钱观,从而导致的贪污腐败、官民社会对立、官商相护、贫富分化严重、底层农民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等一系列社会现象。
三、期许未来:心灵的归途
将心灵安放,把希望寄托,是文学赋予读者的阅读期待。无论是诗意的过去,还是孑行的现状,都幻化为一种审美理想,这正是《望春风》所展示的未来。
(一)精神归乡
黑夜无论怎样漫长,白昼总会到来。格非并不是要用《望春风》留住故乡,恰恰相反,小说从一开始就隐约地展现了一个即将衰败的乡村。相比于过去的追忆,格非更加注重的是当下和未来。正如当代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所说:“作家何以能思考普遍的人的状况,首先在于他面对和思考现在;一切有意义的历史关怀,都是现在的投射。”[4]格非在《望春风》中实现了对过去的告别,以文学的方式慰藉自己对故乡的感情,同时也表达了对当下的隐忧,并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之下,努力寻求一条恢复中国乡村精神的途径。
《望春风》展示出精神归乡的第一步便是对乡情乡音的期盼。命运的无常,让赵伯渝不断地流离失所,最终年过半百的他和春琴,终于在同彬夫妇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便通庵居住。新珍、梅芳、银娣她们最终也来到了便通庵生活。正如主人公赵伯渝所说,“慢慢地,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带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会离老家更近一些。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我只不过是在频繁地变更工作,漂泊无着,而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我暂时还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乡之路。”[3]453我国哲学家唐君毅曾说过:“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5]
第二步即是精神返乡。当乡土伦理溃败、消逝,村庄文化溃散、解体时,于大多数人而言,真正的家乡只能存在记忆之中。赵伯渝说:“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我们两个人,你,还有我,就是这个新村庄的始祖。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3]393精神归乡是现代人面对实体乡村解体的无奈之举。其实,每一个灵魂都有一个故乡,从故乡开始出窍,又回故乡寄宿,然后在故乡里腐烂……现实中的漂泊与辗转,只是离不开肉欲之需,物质仍是决定精神的,尽管华灯璀璨的城市街道催生了繁华,可只有故乡的宁静才让人身心流连。
(二)乡土精神的重塑
格非对乡土的叙述极具个人化倾向,《望春风》中所描写的农村,与当今学界文坛的主流观点不同,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文化大革命”,都没有对儒里赵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并且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还体现出了许多人道主义精神,这种内化到普通农民身上的儒家仁爱的凝聚力,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里暗流涌动着,成为那个风云变幻社会里的一缕春风。格非企图通过《望春风》来重述一直以来被人们曲解的传统乡土精神,以及被神化了的文学想象空间。
如何重塑传统精神?赵伯渝的“精神返乡”给予了重要的启示。赵伯渝在面对反转无常的生活情态时,他总是坚忍而平静地承受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与打击,坚持自己心中平淡的理想,所有的这些都因他心中有一份对家乡执着的热爱而得到稀释,在他的内心深处永远潜移默化着深沉的还乡情结,在没有希望的废墟上渴望着春风的到来。格非曾说过:“《春尽江南》写完以后,我很长时间被结尾处的悲伤气氛所笼罩。鲁迅先生曾说过,如果说希望是虚妄的,那么绝望同样是虚妄的。差不多同一时间,我开始考虑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社会,那就是重新使绝望相对化。”[6]格非所说的“绝望相对化”,其实就是精神返乡。
格非营造的理想主义精神通过《望春风》传递到每一个渴望归乡而又不能的普通人心上,为他们在纷杂的社会给予了如何坚守乡村传统人文精神的回答,格非用华夏历史告诉我们,这一种精神存在于乡土之中。几千年来,乡土精神是在农民长期的农业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它是由价值度量、道德尺度、情感方式、风俗习惯等构成的精神规范,并体现为乡风民俗、村法家规和信仰信念等,它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和教育着人们,是国家和百姓得以繁衍生息的精神支柱。就像许多生活在乡土中普普通通的人们,他们可能认识不了几个字,甚至一辈子都是文盲;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多么的富足,然而,他们却有着现代人所缺乏的自力更生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并且总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并起着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理想信念是中国乡村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生存哲学,它包括修身立节、善良敦厚、平和坚韧、兼爱无私等等,有时候甚至还可以是一种面对苦难生活的默默承受与坚守。格非在《望春风》里便是借“父亲”、德正、赵伯渝、春琴等人身上坚守的淳朴、仁义、善良的精神,来反观和警醒世人。
《望春风》的深层主题意蕴不是对过去做痛苦的回望,而是在现实的基础上,糅合了理性和感性的叙述,以“精神返乡”为契机,以从农耕文明中培育出来的乡土精神为基础,从而构建起理想化的诗意生存空间。
结 语
21世纪以来,许多作家带着强烈的社会意识和使命感,完成了对民族未来构建的自我想象。格非在《望春风》中的精神归乡之旅,揭露了现代工业文明给中国乡村带来的冲击,并通过文学想象给予了现代人如何坚守乡村传统精神与生存智慧的启示。长期的乡村生活经验所衍生出来的智慧不是宗教和迷信,更不是阻挡人全面发展的障碍,相反,它却是当代人在五光十色社会中的镇静剂。尽管曾经旧的生产经验不再适用于现在,但善良、美好的人性却依旧如故,“父亲”“母亲”、德正等人留下来的凝结了传统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人生经验,仍旧是我们在感到忧愁和困惑时的心灵寄托。乡村生命形态万千各异,所传达出来的生活经验也内涵丰富,它是中国农民历朝历代沿袭下来的底层生活哲学,是现代人在惶恐不安的世界,追寻的精神与肉体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