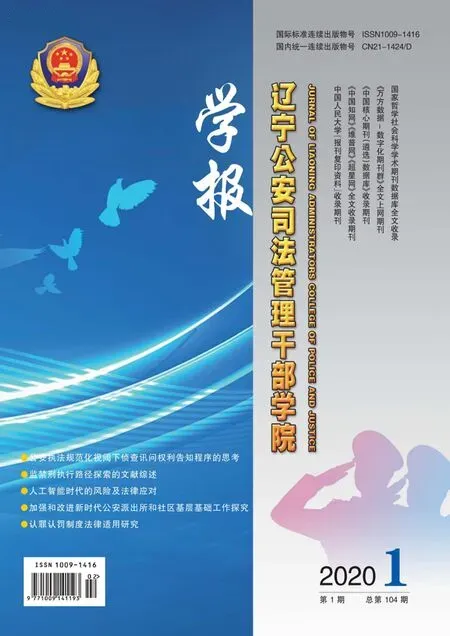L省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研究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调研组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辽宁 沈阳 110033)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以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1)《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2/23/content_5367953.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9月20日。金融稳定与健康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全局,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据统计,商业银行在我国社会金融资产总量中占比超过80%,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中心和主体,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起着决定性作用。商业银行信贷是市场资金流动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使得大量的金融风险汇集在商业银行体系。在经济下行环境下,商业银行体系本已承受巨大的压力,一旦出现严重侵害银行权益的重大犯罪,由于市场的连通性,极易诱发大规模的连锁反应和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协助商业银行排查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调研组对2018年以来L省检察机关办理的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案件进行了全面调研。
一、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总体情况
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是指以商业银行作为对象,侵害商业银行财产、妨害商业银行正常经营的犯罪,主要包括高利转贷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骗购外汇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贷款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等8个罪名,以及涉银行信用风险的诈骗、合同诈骗案件。虽然信用卡诈骗罪也以商业银行为犯罪对象,但由于此类案件主要是因个人小额透支而犯罪,虽然案件数量多,但数额较小,一般不易引发银行信用风险,因此未列入本次调研范围。
(一)案件持续高发
2018年至今,L省检察机关受理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案件230件439人,批准逮捕106件138人,起诉136件227人,不起诉32件61人。案件数量占受理经济犯罪案件数量的2.1%。其中2018年上半年受理79件145人,批准逮捕36件44人,起诉44件111人,不起诉9件19人;2018年下半年受理80件160人,批准逮捕42件52人,起诉43件67人,不起诉6件15人;2019年1至7月受理71件134人,批准逮捕28件42人,起诉49件99人,不起诉17件27人。
(二)案件涉及罪名集中
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主要涉及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贷款诈骗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三个罪名,这三个罪名的受案数达到全部案件数的94.3%。其中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151件,占65.7%;贷款诈骗罪35件,占15.2%;违法发放贷款罪31件,占13.5%。
(三)案件地区分布集中
L省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D市、J市、L市、C市等四个地区,其中D市66件,占28.7%;J市20件,占8.6%;L市20件,占8.6%;C市19件,占8.3%。贷款诈骗案件主要集中分布于F市、D市和J市,其中F市8件,占贷款诈骗案件总数的22.9%;D市、J市各5件,占14.3%。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案件主要集中分布在D市、C市和L市,其中,D市57件,占37.7%;C市17件,占11.3%;L市14件,占9.2%。
(四)涉案银行类型集中
从涉案银行类型看,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案件数量较多,其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87件,占37.8%;股份制商业银行55件,占23.7%;大型国有银行40件,占17.3%;城市商业银行38件,占16.7%。
从涉案具体银行看,民生银行、中国银行、朝阳银行、邮储银行案件较为集中。其中,民生银行共29件,中国银行10件,邮储银行7件;朝阳银行8件。
(五)犯罪手段表现集中
从受案数量最多、对银行资产侵害最大的贷款诈骗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来看,犯罪分子的手段表现相对集中。其中在贷款诈骗罪中以使用虚假证明文件为手段实施诈骗的12件,占贷款诈骗案件总数的33.3%;使用虚假经济合同诈骗的10件,占28.6%;使用虚假产权证明作为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进行诈骗的7件,占19%。在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中,以虚假证明材料骗取贷款的共124件,占82.1%;以虚假合同骗取贷款的共73件,占48.4%;改变贷款用途的共51件,占33.7%。
(六)涉案金额巨大
2018年至今贷款诈骗、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涉案金额总计为1672619.2217万元,造成银行损失共计771126.8877万元。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的案件3件,占两类案件总数1.6%;超过1亿元的案件7件,占3.8%;超过1000万元的案件16件,占8.6%。其中城市商业银行涉案金额1041962.1500万元,损失166735.2752万元;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涉案金额540646.092万元,损失537368.8994万元;股份制银行涉案金额27710.9983元,损失15520.0424万元;国有大型银行涉案金额47565.4061万元,损失47269.4061万元;其他金融机构涉案金额16460.2930万元,损失6020.2930万元。
二、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暴露的主要风险
(一)部分小型农村金融机构风控失效
部分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缺乏风险意识,违规进行所谓创新业务被骗,造成巨大损失,远超自身可承受的范围,进而影响主发起行的经营(2)根据银监办发〔2014〕280号《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村镇银行公司治理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主发起行应书面承诺牵头组织对村镇银行的重大风险处置,确保村镇银行持续稳健经营。主发起行应与村镇银行签订书面流动性支持协议,制定风险处置预案,并报村镇银行属地监管机构备案。”,容易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如陆某、罗某诈骗案,2015年末陆某、罗某为了偿还自身欠款,借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预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之机,在洽谈入股过程中,提出帮助某联社开展票据业务盈利的经营方案。在某联社自身无能力开展票据业务的情况下,2016年1月至5月间,二被告人利用其掌控的多家公司开具的没有资金保证、没有兑付能力、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作为底层资产,诱使某联社先后出资购买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骗取某联社人民币36亿9千余万元。据查,某联社注册资本仅为2亿5千万元。
又如张某甲、张某乙合同诈骗案,2014年6月至2015年8月,张某甲、张某乙与某村镇银行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由银行为其提供垫付资金。2014年7月至2017年7月期间,张某甲、张某乙指使员工冒充客户身份信息、编造虚假交易数据,将虚假交易数据发送给某村镇银行,骗取某村镇银行垫付资金12亿2千余万元,用于购房、买车、置地等支出。据查,某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仅为1亿元。由于被骗损失巨大导致兑付困难,该村镇银行最终被主发起行接管。
(二)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导致个别企业铤而走险
银行贷款作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控制风险是银行发放贷款的重要考量因素,往往会要求贷款企业必须提供固定资产抵押或者其他企业担保,并且相关手续繁琐,造成了企业融资需求与银行融资渠道狭窄、门槛过高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为达到银行贷款要求,不惜通过骗贷手段获取银行资金。但在当前整体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企业经营风险骤增,一旦发生风险事件导致贷款无法偿还,造成银行经济损失,贷款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就会暴露。如于某贷款诈骗案,于某为了其使经营的加氢公司获取经营资金,注册了10余家空壳公司向兴业银行、工商银行、个人及小额贷公司借款,至案发尚未偿还的欠款达到7000余万元,于某及其控制的公司名下的资产均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
(三)银行对于贷款用途的审核管理存在漏洞
行政监管部门为了约束企业贷款用途,防范企业将贷款投入国家政策或法律调控的领域,在相关规定中明确要求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在贷款时必须说明贷款的具体用途,并对于特定用途有明确的限制,但通常情况下许多企业贷款时其贷款用途并不明确或者贷款用途不符合银行的相关要求;在贷款使用过程中,也常常因为市场及自身经营情况的变化改变贷款的用途,最终导致贷款实际用途与申请贷款时并不一致。一旦贷款出现逾期,贷款人的相关行为往往会被司法机关依照骗取贷款罪追究刑事责任。据统计,以虚假合同和虚构贷款用途的手段骗取贷款案件占所有骗取贷款案件数量比例高达82.1%。如裴某骗取贷款案,裴某以他人的名义虚构购销合同,在某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一笔200万抵押担保贷款,宣称用于购买白落叶松方木。获得贷款资金后,裴某将贷款用于偿还其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贷款和给工人开支,到期未能偿还,给某村镇银行造成257.5681万元经济损失。
(四)银行对内部人员的管理机制存在缺陷
虽然银行内部对各类业务操作规范均有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未完全落实。部分金融机构为了追求业务量和经济利益,随意放宽申请人条件,简化申请手续,甚至帮助申请人伪造申请材料,相关内控、风控制度流于形式;部分私营企业的经营者轻信银行业务人员的宣传,为获取贷款伪造销售合同、物权抵押登记等贷款材料,以至于触犯刑律。据统计,在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和贷款诈骗罪的案件中,内部人员涉案的比率高达39.7%。
(五) 惠农贷款被违法套取,影响惠农政策实施
为扶持农业发展,L省对于涉农贷款提供了贴息、免抵押等优惠政策。不法分子为获取不法收益,通过收集农民身份证、虚构贷款用途等方式套取惠农贷款转作他用,影响了惠农政策的落实。2018年以来L省共发生此类案件22件,其中D市16件、C市3件、F市等3个城市各1件,被套取资金7010.1807万元,造成损失6118.1655万元。D市虚构海参养殖案件较多,其他地区则虚构猪、牛养殖类案件较多。如毛某骗取贷款案,毛某编造“公司加农户”与农户合作养猪的虚假贷款理由,以40余名农户的名义,在某信用社骗取无抵押惠农贷款827万元。
三、 办理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案件主要争议问题
(一)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的目的认定存在争议
实践中如何掌握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认定标准存在认识分歧。2018年至今,L省因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被判无罪的案件两件,占经济犯罪无罪案件的14.3%,还有多件案件因检察机关对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意见未得到法院认可,被改判骗取贷款罪。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和《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两个规范性文件予以规范,但两个文件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均采取了推定的方法,即以客观行为推定其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按照司法解释设定的认定路径,实践中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也往往采取推定的方式,导致司法机关容易忽视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考察。只要客观行为符合相关解释的规定,并实现了支配贷款的目的,不调查贷款用途及不能还款的原因,径行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仅以客观行为为依据推定行为人主观目的的方式,有客观归罪之嫌。另外,实践中司法机关还容易忽视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考察、评价,把合法取得贷款后产生占有目的的案件作为贷款诈骗罪处理。虽然对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是否对于构成贷款诈骗罪具有影响,学界尚存争议(3)否定论者认为:“对于行为人合法获得贷款,到期后拒不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形,如果行为人还实施了转移资金、抽逃资金或者隐匿财产等客观行为,可以据此得出行为人之目的在于逃避归还银行贷款,成立贷款诈骗罪。”参见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484-486页。肯定论者认为:“对于行为人合法取得贷款,事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采取诸如隐匿财产、销毁账目等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其论述依据有二,一是,事后故意违背行为和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二是,占有财产后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此时目的是免除债务,不是所谓的“事后故意”,此时不是贷款诈骗的故意,而是普通诈骗罪的故意。”参见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534页。,但是从现实案件处理的合理性来看,区分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确有必要。首先,贷款诈骗罪与诈骗罪是特殊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两罪的区别仅在于犯罪对象不同。诈骗罪要求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产生在实行行为之前,按照刑法体系解释的一般原则,不应在对于贷款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作出与诈骗罪不同的解释。其次,如前所述,司法实践中往往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采取推定的方式,如果承认取得后产生占有目的的行为可以构成贷款诈骗罪,往往会导致不当地扩大贷款诈骗罪的打击范围,将因经营不善等原因最终无法偿还贷款的贷款民事纠纷作为刑事犯罪处理。再次,如不区分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限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必须产生在实行行为之前,会让一些在贷款时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案发后积极返赃的案件,因具有事后的返还行为,导致对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困难。
(二) 对于骗取贷款罪“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存在争议
《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的骗取贷款罪,将“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构成本罪的限定性条件。2010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将骗取贷款罪的“重大损失”规定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其他严重情节”规定为“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此《规定》确立的标准虽然给司法机关办案带来了便利,但是也带来了处罚范围过大的隐忧。由于对于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其他严重情节”与“重大损失”之间为并列关系,只要符合其一就构成本罪,如仅以骗取贷款的数额考量,不考虑是否造成实际损失,就可认定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会导致大量在贷款过程中具有虚假陈述,但已经偿还贷款或者具有足额抵押等未造成银行损失的行为被作为骗取贷款罪处理。现实中,商业银行有采取刑事手段快速高效回收贷款的内在动力,从而积极检举贷款企业;司法机关由于害怕放纵犯罪,不愿主动将没有造成实际损失的骗取贷款行为排除在刑事处罚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L省骗取贷款罪的高发、多发。虽然传统观点认为骗取贷款罪侵害的法益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1],那么以欺骗手段获取贷款的行为,即使没有造成银行的实际损失,也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是对金融安全的破环,应当使用刑法予以规制。但是从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待商榷。首先,刑法保护的法益应当是一种具体实在的社会利益,而不应当是一种抽象空泛的秩序。如果不考虑实际损失,仅仅将抽象的“金融管理秩序”作为本罪的法益予以保护,将不当的扩大本罪的处罚范围。其次,将刑法作为维持金融管理秩序的首要手段,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对于金融管理秩序的维护与管控,应当区分民事纠纷、行政违法与犯罪之间的界限,激活民事、行政方式解决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作用;刑法应作为最后手段,仅对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适用。不应当让没有危及信贷安全的所有瑕疵贷款行为,都可以被以保护金融秩序之名纳入犯罪规制的范围[2]。对于没有实际损失的金融管理秩序,直接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运用刑法手段加以规制的做法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三) 对银行内部人员犯罪行为的定性存在争议
在骗取贷款或贷款诈骗的过程中,内外勾结犯案的比例高达39.7%,但如何对涉案的银行工作人员定罪处罚,实践中存在诸多分歧。有人认为协助外部人员贷款诈骗的银行内部人员应当以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统一定性。这种观点主要依据在于内外勾结犯罪的决定性因素是利用具有特定身份者的身份便利,这一特征决定了整个犯罪性质。在内外勾结案件中,银行内部人员在相关的业务办理过程中与外部人员相互串通,虽然外部人员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但内部人员并不存在错误的认识,没有被骗,不符合诈骗罪的基本要求,相关行为只能根据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与财产性质定罪[3]。有人认为对内外勾结共同实施金融诈骗的行为应统一定性为相应金融诈骗罪[4],即以贷款诈骗或骗取贷款罪追究银行内部人员的刑事责任;也有人认为内外勾结贷款诈骗的,应当以主犯的行为性质定罪,既有可能构成职务犯罪,也有可能构成贷款诈骗罪,此观点也得到了司法解释的支持(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的财产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还有人认为内外勾结的贷款诈骗,无论参与人的身份为何,也不管参与人如何分工,本质上都是共同完成刑法上的同一犯罪行为,一行为同时触犯了多个法条构成多个犯罪的,是“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理[5]。正是由于上述不同意见的争论,使得司法机关处理相关案件时往往会产生疑虑,容易导致放纵对银行内部人员的定罪处罚。调研中发现,在内外勾结的骗取贷款和贷款诈骗案件中,涉案的银行内部人员作为犯罪处理的不足50%。
(四)对于民营企业融资类案件逮捕标准把握尺度过严
2018年至今,L省检察机关因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案件起诉227人,批准逮捕138人,即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高达60.8%。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多为民营企业或其经营者涉案,过高的逮捕率将严重影响涉案企业的正常经营,个别企业甚至因为经营者被长时间采取逮捕措施使得经营陷入停顿中。2018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规范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的11个执法司法标准,其中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要严格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防止“够罪即捕”“一捕了之”。对不符合逮捕条件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应当依法不批准逮捕;对有自首、立功表现,认罪态度好,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民营企业经营者,一般不批准逮捕;对符合监视居住条件,不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可以不批准逮捕”。如何在处理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案件过程中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降低民营企业融资类案件的逮捕率,减少案件的查办对于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是检察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防范治理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的对策建议
在打击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坚决落实“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要求,将案件办理与法律监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结合起来,协助监管机构排查风险隐患,将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办案人员要修炼内功、提升能力,为党和政府的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保障与智力支持,为经济发展的大局助力护航。
(一) 树立检察工作为经济发展大局服务的理念
打击各类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活动,保障经济平稳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是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金融业各类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并存以及交叉发展,使经济关系、经济利益关系日益复杂,机械地套用各种制度规定已难以客观、准确、科学地判断复杂社会经济行为的性质。因此,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树立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理念,坚持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标准、犯罪构成要件标准和是否有利于维护经济平稳发展、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标准结合起来,从整体上对相关案件进行系统、综合的评价。
(二)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问题
只有解决相关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问题,才能给市场活动参与的各方明确规则、划清底线。既要防止放纵犯罪,诱发金融风险;也要防止规则模糊,导致打击面不当扩大。
1.对于贷款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调研组认为:(1)加强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搜集工作。绝不能因为实践中直接证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一定的困难,就忽略对相关证据的收集与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所有诈骗类犯罪共同的主观关键要素,是决定是否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关键要素。(2)准确把握“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在运用推定的方法认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以下原则问题。一是要主动查清行为人是否通过实施贷款诈骗罪的法定行为而将贷款转为自己控制。如果实施了贷款诈骗罪的法定行为,并且最终出现不能归还贷款的结果,并且能够排除这一结果并非由于正常的市场风险或者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客观因素造成,那么可以认定行为人具体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但是如果行为人在客观行为上不符合法定的贷款诈骗罪行为要求,即使出现了不能归还贷款的情况,无需再考察不能偿还贷款的原因,不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要主动查明行为人在贷款时的经济状况,是否具有还款能力或可能性。还款的能力和可能性既包括行为人在贷款时的财产情况,也包括按照行为人的计划、拟使用贷款资金经营所产生的预期利润等客观情况。如果这些客观情况可以证明行为人在贷款时根本不具有偿还贷款的能力,并最终出现了不能归还贷款的危害结果,就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与此相反,如果根据行为人贷款时的经济实力以及贷款使用预期获得的利润具有归还贷款的可能性,仅仅因为市场风险、意外事故、被骗、不可抗力等原因无法归还贷款的,则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要主动查明行为人是否将贷款用于不切实际的高风险投资或犯罪活动,比如参加外盘的高风险期货交易、没有实际经营的高回报投资等,导致血本无归;或者因赌博、高利贷等违法犯罪活动被查处的,应当以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四是要主动查明案发后行为人是否具有隐匿、转移财产等情况;无法说明资金去向或拒不说明资金去向的,一般也可以以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五是要主动查明行为人是否有逃避债务、隐匿行踪的行为以及原因。实践中,银行无法联系到贷款人的原因多种多样,并不能据此简单推定行为人具有逃匿废债的行为。有的行为人因为债权人的极端讨债行为不敢露面,有的行为人因拖欠工资而躲藏,有的行为人因家庭内部纠纷而逃避,只要行为人不是为了逃避偿还银行贷款,即使一时无法联系也不应认定为逃匿而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3)建立对非法占有目的推定的反证体系。要赋予嫌疑人提出反证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充分考虑推定的例外情形。只要嫌疑人提出的反证确实存在,就应当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比如贷款人因暴力催讨而逃匿,企业经营者为了提升企业形象进行“高端消费”等就不宜认定行为人逃匿或挥霍贷款,进而认为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对于骗取贷款罪“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问题。(1)要坚持以造成“重大损失”作为骗取贷款罪定罪处罚的必要条件。骗取贷款罪保护的法益是银行贷款资金的安全,因此其损失也只能以贷款资金作为对象,并且这种损失必须是已经发生的直接损失,而不能是可能发生的间接损失[6]。(2)要将“其他严重情节”与“严重损失”作同类性解释,将未造成实际损失的行为排除在刑事处罚之外。对于此问题,其他省市如浙江、重庆等地都已经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对案发后主动偿还,避免银行损失的案件作出罪处理,合理界定本罪的处罚范围(5)浙江省公检法《关于办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根据刑法规定,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一审判决前偿还的,可以从宽处理。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数额超过人民币一百万元不满五百万元,但在侦查机关立案前已偿还信贷资金,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或者行为人以自有财产提供担保且担保物足以偿还贷款本息的,可认定为刑法第十三条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作为犯罪处理。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数额超过五百万元,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可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客观危害,如行为人在授信、贸易背景、贷款用途、抵押物价值等方面是否存在多环节或多次实施欺骗手段,有无给其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等案件具体情节加以确定。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二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的“重大损失”。”。对于其他省市的有益探索,L省也可以积极借鉴。(3)准确界定本罪的行为方式,合理界定本罪的适用范围。如单纯改变贷款用途、在贷款过程中夸大自己的还款能力、受银行工作人员诱导作出错误陈述的行为均不应包含在本罪的处罚范围之内。
3.对于对银行内部人员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调研组认为,绝不能因为对于如何定罪存在认识分歧,就放纵对相关涉案人员的惩处。在对相关案件的处理中,应当坚持司法解释规定的“主犯决定说”,即在一般情况下,对内外勾结共同实施贷款诈骗的行为应认定为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一是因为这种行为符合内外勾结共同实施金融诈骗的行为性质。内外勾结共同实施贷款诈骗的行为既有骗的一面,又有职务侵占或贪污的一面,具体表现在利用了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经手、管理、处置金融机构资金的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但“骗”的行为是通过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经手、管理、处置金融机构资金的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发生的作用。相关犯罪之所以能够成功,“骗”是“外因”,而“职务便利”则是“内因”。因此,将内外勾结共同实施金融诈骗的行为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是符合其行为性质的。二是以此原则处理,符合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相关原则,减少实践中的争议。三是以职务侵占罪对内外勾结共同实施金融诈骗的行为进行量刑,可能会比用贷款诈骗罪对其进行量刑轻,但不应为了达到重判被告人的目的,而把本质上为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作为相应金融诈骗罪处理。四是在少数的内外勾结贷款诈骗犯罪过程中,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其在犯罪过程中与一般主体无异,不具有职务犯罪的性质,那么即使有银行内部人员的参与,也应当仅以金融诈骗犯罪追究参与者的责任。
(三)努力实现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案件过程中要努力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一是要创新办案模式,探索建立“两必听”的办案制度。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案件过程中,应当听取被害单位和相关政府监管部门的意见,了解各方诉求。对于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社会危害性大的案件,要研究如何把查办案件和化解风险、追赃挽损、维护稳定结合起来,防止引发次生风险。要注重风险评估预警,努力做到依法处置、舆论引导、风险防控“三同步”。二是要更新办案理念,尝试建立“清债减责”机制。对于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案件除了要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外,更重要的是要协助被害金融机构追赃挽损,防范金融风险。在办案中建立有效的“清债减责”机制,根据犯罪人员弥补被害单位损失的比例和程度,适当减轻其刑事责任,如对完全避免损失的骗取贷款等犯罪,可以考虑不作为犯罪处理,以充分调动犯罪人弥补银行损失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改变侦查过程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一押到底”的办案方法,通过灵活变更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为犯罪嫌疑人处理相关财产弥补银行损失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全面发挥检察职能。防范金融风险不仅刑事检察要一马当先,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也要协同发力。民事检察要重点监督超期审理、明显超标的执行和查封、消极执行等违法情形,协同审判机关攻坚“执行难”,监督促进穷尽执行手段,保证合法债权得以足额、及时实现,依法打击逃避金融债权的虚假诉讼等行为,保护合法金融债权;行政检察部门要对在民事检察监督中发现行政机关在金融监管中存在的缺位,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维护良好金融秩序;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要针对骗贷案件中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等危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问题,依法进行公益诉讼检察监督。
(四)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是督促商业银行强化内控机制。从案发情况看,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犯罪案件往往和银行内控机制不严密切相关。绝大多数涉案银行存在着相关内控机制失灵、失效,内控规定流于形式,相关业务工作人员缺乏风险防控意识,参与、配合相关的犯罪活动等情况,从而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检察机关要通过执法办案协助相关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相关的内控机制,加强内部人员的培训,堵塞内外勾结的制度漏洞,消灭犯罪滋生的土壤。针对典型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制发检察建议,监督相关银行将问题整改情况向检察机关反馈。二是督促金融监管机关依法履职。检察机关通过案件办理发现的监管漏洞应当向监管部门发出预警,提示监管部门对相关问题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对于监管部门怠于履行、不正确履行自身职责造成国家、集体及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检察机关要积极履行检察监督职权,督促相关部门堵漏建制。三是重点打击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大股东、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员利用自身权力的犯罪行为,依法与有关部门一道严惩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金融腐败行为,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五)积极参与金融风险的综合治理
要以综合治理的模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检察机关在履行指控犯罪职责的同时,要加强与银保监会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与配合,使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有效衔接,形成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合力。一是加强与地方金融管理局、银保监局、人民银行、公安经侦等部门的联系,强化“两法衔接”的工作机制,建立、完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工作交流机制,确保重大信息及时通报。对于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与各机关统一意见,研究制定稳妥的工作方案,实现刑事案件办理与防范金融风险双同步。二是加强金融法律知识的普法宣传。针对企业经营者、银行工作人员加强银行业务合规教育,防止相关人员误触法网;针对新出现的犯罪情况和趋势通过公开庭审、新闻报道、专题讲座等方式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社会整体的金融风险防控意识。三是做好金融风险防范调研。办案部门要实行调研、综合、办案三位一体的审查模式,加强检察数据收集和研究,挖掘犯罪规律、制度风险和管理漏洞。对于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制度性问题,应当及时形成专项的报告,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并向当地党委报告,为打好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