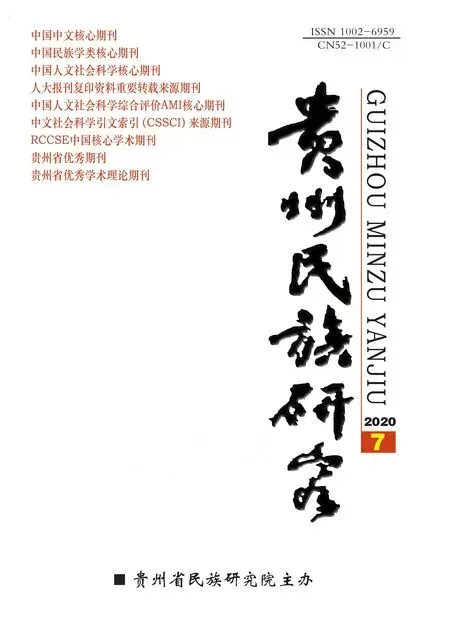《汉民族史记》 的人类学视野
丁苏安
(广西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汉民族史记》的横空出世,为泱泱汉民族树立了一块523万字的历史丰碑。主编徐杰舜先生,以50年的学术积累,20余年的团队研究,5年的奋笔撰写,把中国的汉民族研究推上了一个学术高峰。
《汉民族史记》的学术内涵极为丰富,黄振南教授撰写了《〈汉民族史记〉成色说》 (《南宁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一文已有论及,但笔者拜读之时,却被这套鸿章巨字中无处不在的人类学视野而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历史还可以这样书写!大有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一、人类学结构论视野:创立板块结构模式
人类学的结构论试图从杂乱无章的现象中寻找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结构,其最终目标是从结构认识事物的本质。
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颠覆了中国二十四史传统的述史方式,形成了以历代王朝的框架为坐标的结构模式。但是,凡事都有个度,如果机械地把民族史塞进王朝的框架里,会把一部部好端端的民族史弄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更有甚者干脆视汉族史为中国史,中国史就是汉族史。由于认识的混乱,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对中国史的研究十分热衷而趋之若鹜,而对汉民族史的研究长期冷淡且视而不见,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民族的历史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的状态。对此,徐先生早在大学求学时就看在眼中,急在心里,暗下决心要为汉民族树碑立传。1999年,《文汇读书周报》曾发表新华社著名文化记者孟凡夏的文章:《为汉民族树碑立传的人——访徐杰舜教授》,表露了徐先生的这个心声。
在徐先生50余年的治学生涯中,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汉民族史书写结构的探讨和尝试。读过徐先生的成名作《汉民族发展史》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的人都清楚,当年,徐先生打破历代王朝框架为坐标的模式,在探索按民族发展规律书写民族史的初期,尝试建构了起源—形成—发展—特征—文化的板块结构模式,首次打破了王朝框架为坐标的结构模式,获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尤其是他关于汉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很快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认同,2008年4月被斯坦福大学邀请在“汉民族研究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主旨讲演;2012年《汉民族发展史》 被冯天瑜先生收入《中国专门史文库》,同时,也获得了社会的积极认同,2016年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汉族”条,就采用了徐先生在《汉民族发展史》中所表达的观点。
徐先生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汪国真的成名诗《热爱生命》曾说:“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从1992 年到2019年的27年间,徐先生“风雨兼程”,先后率领学术团队完成了汉民族研究的三级跳,即《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五卷本《汉族风俗史》 (学林出版社,2004年) 和九卷本《汉民族史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的三级跳。正是这三级跳的最后一跳,积50年之学术功力,一跳而登上了汉民族史研究的巅峰。
结构论是人类学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重要工具。在《汉民族发展史》的基础上,徐先生的《汉民族史记》又以历史、族群、文化、风俗和海外移民的板块结构,建构了汉民族的恢弘历史。正如他在《汉民族史记·卷首语》中所说:“传统结构模式没有历代王朝框架的束缚,众所周知,《史记》所开创的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的专题结构,就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从而使历史的编撰灵活机动,收放自如,不仅可使历史生动起来,更可使历史的叙述深刻起来了。所以我于1989 年在《中国民族史新编》的《自序》中就提出:‘中国民族史的编写必须突破历史王朝的框架,按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去编写。’[1](P4)为此,我们这次编撰《汉民族史记》,正是按照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继承汉民族的史学传统,运用传统结构模式,将汉民族史的呈现分为发展史、族群史、文化史、风俗史和海外移民史五个专题。”[2](P5)
徐先生的这个做法,获得了冯天瑜先生的赞誉,他在《社会科学报》 上撰文说:“徐君的《汉民族史记》追迹《史记》的结构方式,突破王朝述史的框架,按汉民族经历的丰富性、多样性部勒篇什,在比较舒展的框架内放手编写,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文化繁富的一个大民族树了碑、立了传,实属难能可贵。”[3]
可见,正是人类学的结构论打开了徐先生的“脑洞”,成就了《汉民族史记》的辉煌。
二、人类学整体论视野:书写述史的新文本
表述问题是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如何书写历史?也就是说如何建构和呈现汉民族的历史?二三十年来,徐先生动足了脑筋。他认识到整体论是人类学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论和重要工具,是“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4]。
那么,如何书写汉民族史?徐先生在《汉民族史记·历史卷》(上)中,从整体论出发,以汉民族的五帝时代、起源时代、形成时代、发展时代的逻辑结构,书写了汉民族述史的新文本,向世界呈现了汉民族上下5000多年的历史长卷。
更有意义的是,徐先生并非就汉民族研究汉民族,而是把汉民族置入中华民族的整体视野之中,使人们从他的叙述中,不仅可以清晰地认识汉民族浩浩漫漫5000多年的历史路线图,还可以清楚地明白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为什么是汉民族的历史原因。所以,徐先生在本卷的结尾,自然而然地把浩瀚的汉民族史汇入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之中,他说:“对于古老的汉民族发展来说,如果说两汉是其幼年时期,隋唐是其青年时期,明清是其中年时期,近代则是其老年时期。这是民族发展规律之使然,从清王朝前期即开始的满汉融合,满族汉化,历经267年(1644—1911年)最终并没有彻底完成,其根本原因是世界变了,时代变了,一个长期封闭自守的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民族概念的引入和应用,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高涨,从此改变了中国民族交融的大方向,中华民族这个雪球,开始在中国滚动。汉民族将与中国所有其他的民族一道,凝聚和交融在中华民族之中!”[2](P446)《汉民族史记·历史卷》 (上)的述史方式,构成了一个从汉民族的五帝时代到起源时代,继而到形成时代,再到发展时代的独具特色、自成系统的述史新文本。
三、人类学区域论视野:建构汉民族区域史的体系
区域作为人类学解读人类文化的方式,是人类学的重点研究范畴之一。周大鸣曾说:“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区域研究则是以民族志为基础的一种提升,或者说是对民族志的超越。”[5]早在20世纪末,徐先生就开始关注汉民族区域的研究。从1996年12月开始,历时3年,其成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在人类学泰斗费孝通先生“要重视和加强对汉民族的人类学研究”题词的鼓励下,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此,一个汉民族研究的“雪球”滚向世界,其所提出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20年后的今天,在研究和撰写《汉民族史记·历史卷》(下)之时,徐先生在《总后记》 中说:“从历史演进的实际出发,以区域为边界,分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七个区域,分别展示了汉民族在这些区域形成和发展的生动态势和精彩过程,正是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时期所形成的族群互动、磨合、整合和融合,才形成了汉民族历史发展的丰富多彩。这一幅又一幅的地域历史画卷,可使人们从纵深上认识和了解汉民族的历史及其多元性和多样性。”[6](P577-578)从而构成了汉民族区域史的体系。这就应了田阡所言:“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要在国际学术前沿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发生学的方法,以现实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探讨特定历史形态和地理形态中文化发生的根源与基础、发生的过程与规律、发展的环境和走向,就……需要一些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引领能力的分析单位和框架。”[7]这对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生态差异的汉民族史的表述是完全必要而不可缺少的。
所以,《汉民族史记·历史卷》(下)对汉民族区域史体系的建构,生动而真实地呈现了汉民族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同时,又存在一体多元的在线状态,充分展现了汉民族来源的多元性、文化的多样性、历史的多彩性。赵巧艳在评论黄土文明研究时曾说:“对中国人类学乃至世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显著方法论贡献就是区域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和在黄土文明研究中的具体应用。”[8]那么,徐先生对汉民族区域史体系的建构也是“区域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典型应用”[8]。
四、人类学族群论视野:对汉民族的族群结构进行分析
族群(Ethnic group) 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研究人类共同体的重大发展,90年代通过乔健和陈志明两位先生的引介传入中国学术界。徐先生作为早期的践行者,不仅于1999年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中引入了族群论,并“发现族群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文现象,即族群是有结构的,尤其是对历史悠久、人次的研究时,其族群结构的特征就凸显无遗”[9](P1)。于是,他初步分析了汉民族的族群结构,还于2002年在《民族研究》上发表了《论族群与民族》一文,按中国话语的逻辑,将族群概念概括为“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在此,他特别指出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为族群,还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10]。此文一出,族群概念的使用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正因为有了这样深厚的学术背景,所以,近20 年来,徐先生为了研究汉民族的族群结构,以行万里路的精神和毅力,除西藏外,走遍了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各地,感生态环境,考民情风俗,查方言俗语,搜资料文献,以语言、族群形成和人文特征的叙述结构,在《汉民族史记·族群卷》(上)(下)两卷中,以100余万字的篇幅,考察和研究了东北的沈阳人、大连人、长春人、哈尔滨人;华北的河北人、山东人、山西人、北京人、天津人;华中的河南人、湖北人、湖南入、江西人;华南的广府人、客家人、闽南福佬人、平话人;桂柳人、高山汉、疍民;华东的上海人、南京人、徐州人、苏州人、镇江人、徽州人、安庆人、杭州人、宁波人、绍兴人、温州人;西北的关中人、陕北人、宁夏人、天水人、河西人、河湟人;西南的四川人、云南人、贵州人、屯堡人等41个汉族族群。其中有大的族群,如山东人、山西人、上海人、北京人等;也有小的族群,如高山汉、疍民、屯堡人等。但无论大小,均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在徐先生的笔下,汉民族的族群个个活色生香,生动有趣,如侠义忠诚又恋家恋乡的河北人,好汉、好客和好礼的山东人,朴实厚道、勤俭耐劳、外向内敛的山西人,京味、善侃、傲慢的北京人,草根、混搭、乐呵的天津人,敢为天下先、崇商重利、嗜食生猛海鲜、讲迷信重意头的广府人,重商贾善经营、以家族为核心、漂洋过海闯世界的闽南福佬人,聚居城镇、随遇而安、诙谐乐天、“死仔”义气的桂柳人,以舟为居,萍踪无定,民间信仰,庞杂多样的疍民,古道热肠、怀旧情结、平民意识的南京人,敢做敢为、有情有义、南北交融的徐州人,柔情似水、气质高雅、心灵手巧的苏州人,聚族而居、兴师重教、左商右儒的徽州人,天堂情结、悠闲安逸、文质彬彬的杭州人,求心求实、师爷风范、水乡风韵的绍兴人,冷娃性格、刀客文化的关中人,尚武出将、南北相融、重教重男天水人,盆地意识与天府心态、“格老子”与摆龙门阵、“粉子”与“耙耳朵”并存的四川人,坝子情怀,知足常乐,融而未合,分而未化的贵州人,仪式社会、军人气质、以孝为先、明朝遗风的屯堡人。凡此等等,举不胜举。面对这些鲜活而多样的汉民族族群和族群文化,人们又不能不惊叹所有这些族群无不对汉民族保持着高度的认同,使人们“在体验汉民族‘一体多元’的多彩在线和多元结构之中,深感汉民族的‘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真是世上最巧妙而又精当的民族结构和民族认同。一方面是历史悠久而结构复杂,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多姿而高度认同。这样,在汉民族的生命‘马拉松’中,孕育、凝聚、磨合、整合和融合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6](P579)
重要的是徐先生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的族群分析,按不同的类型,对其族群结构做了解剖和分类,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就像X光机的透视作用一样,不仅可以从结构的深层次上认识民族的整体性,还可以从结构的可变性上把握民族过程。这无论是对认识汉民族滚雪球从多元走向一体,还是以此为示范,认识中华民族也会滚雪球从多元走向一体,都是极具参考意义的。所以,《汉民族史记·族群卷》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不啻是一个学术创新。
五、人类学文化论视野:对汉民族的文化演进作解读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在人类学的视野里,文化就是人和人的一切行为方式的表达。所以“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呈现是其重要的表征”[6](P579)。汉民族虽有极丰富的文化样态和极深厚的文化传统,但十分遗憾的是学术界有多种版本的“中国文化史”,也有一些“中华文化史”,甚至许多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文化史,偏偏没有一部“汉民族文化史”。其中之原因当然如前所述是人们在中国与汉民族之间画了等号所致,在此无须多言。
重要的问题是汉民族的文化如何呈现,汉民族的文化史走的又是什么路线图?据我所知,徐先生从1992年《汉民族发展史》出版以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对此,他有三点反思:
一是回顾了1992年《汉民族发展史》中对汉民族文化的呈现。 《汉民族发展史》 从琴、棋、书、画;吃、穿、住、用;民族礼仪;民族节日;民族戏曲;民族武术;民族医药;民族工艺;汉民族文化的象征——泰山、长城、大运河9个方面,横向地描绘了汉民族的文化图像。但这种图像呈现缺乏历史的纵深感。
二是反思了1999年《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中对汉民族文化的表达。其从多元的视角,将汉民族文化的呈现分为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七大区,分别呈现了各区汉民族的历史、族群和文化。这种多元态势的表达,虽然展示了汉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结构和态势,但仅就汉民族的文化史而言,不仅缺乏整体性的观照,仍然缺乏历史的纵深感。
三是考察了近二十年来国内汉民族文化研究的动态,区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云贵文化、川渝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东北文化、齐鲁文化、江浙文化、赣徽文化、湘湖文化、甘青文化、海派文化、京派文化、三晋文化等研究蜂起。在这种汉民族区域文化的热流中,我们曾设计将汉民族的文化史以区域文化的形式来呈现。但仔细一想,这仍然克服不了以往的研究缺乏历史的纵深感的缺陷[6](P580)。
经过反复斟酌,徐先生在《文化视野:汉民族文化史分期纲要》一文中提出了汉民族文化史分期的五项原则:要注意中国历史对汉民族文化史的观照,要注意汉民族文化史与中国文化史的区别,要注意汉民族文化史在中国文化史中的位置,要注意汉民族本身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与汉民族文化史的关系,要注意把握汉民族文化本身发展变化的生命规律[11]。最后决定从纵的方向上呈现汉民族文化及文化史,看来,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策。这个决策,使徐先生的《汉民族史记·文化卷》一下子突破了中国学术界各种文化史的包围圈,从而创立了“汉民族文化史”新的表达形式。
在徐先生《汉民族史记·文化卷》 (上)(下) 两卷,也以100余万字的篇幅,考察和研究了从先秦到民国,汉民族上下5000年的文化史。更难能可贵的是,徐先生深入研究,勤于思考,精于概括,善于提炼,对浩瀚的汉民族文化史,以文化底蕴、文化凝聚、文化定型、文化融汇、文化变古、文化重建、文化开新为关键词,建构了文化底蕴,汉民族文化的来源;文化凝聚,先秦华夏民族文化的构建;文化定型,从秦到汉汉民族文化的图像;文化融汇,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汉民族文化的图像;在以文化变古,从北宋到南宋汉民族文化的图像;文化重建,从元到明汉民族文化的图像;文化开新,从清到民国汉民族文化的图像七章的结构,在纵向的视野中,勾勒了汉民族文化史发展的轨迹和路线图,把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连绵五六千年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汉民族的文化发展、演进和融汇的图像,动态地、有历史纵深感地呈现给了读者[6](P580)。
徐先生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发生、起源、形成、变异、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如同一个生命体,有孕育期、发育期、成熟期、衰弱期。汉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连绵、人口众多的民族,其文化史也必然悠长、起伏、多彩、多变,在世界上应该是唯一的”[11]。所以,他在撰写汉民族文化史中牢牢把握住汉民族特有的文化表达,如在论述春秋战国华夏民族文化的汇聚时,从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的经典化;仁者爱人:伦理道德的人本化;玉不去身:玉器文化的人格化;出礼入刑:法律文化的法制化;教之春秋:史学文化的多样化;大象无形:文学文化的明道化;天人合一:信仰文化的世俗化等7个方面展开,每一项都是汉民族文化的独具表达[12](P240-285)。
还需要提及的是,徐先生对汉民族文化史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读后使人不得不击节叫绝。如道家何以会在汉代脱颖而出而成为汉民族本土宗教的问题,徐先生另辟蹊径,从儒道对峙切入,他认为:
儒家虽尊,但并非“罢黜”了“百家”,正如杨清虎有《论故“罢黜百家”其实是融合百家。但为什么同样具有吸纳和融合“百家”,在政治上强过道家的儒家没有蛻化而成儒教,反而是弱于儒家的道家脱颖而出了呢?关键是道家眼睛向下,扎根民间;儒家眼睛向上,迎合上层。在理论上比较,从帛书《道德经》 可见儒道理论的对立:儒刚而道阴。儒家思想讲求自强不息,大同思想、内圣外王之学,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主张,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3]的心态,无不反映出刚健有为、奋进不止的精神,大有“天下者,我的天下”的气概,政治意识极强;而道家思想清心寡欲,见素抱朴,渴望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主张无知、无为、无欲、不争,贵柔、守雌、主静,纯任自然,泯灭主体能力,崇尚自然高远,鄙弃狭隘功利主义,强调的是一个“静”字[14](P413)。……于是,道教的创立者抓住、借用、发挥、膨胀了这些思想,使“道”成为至上神[12](P414-415)。
“道家眼睛向下,扎根民间;儒家眼睛向上,迎合上层。”徐先生一语点明了道家之所以能成为汉民族本土宗教,而儒家不能成为汉民族本土宗教的根本原因。此说有根有据,深入浅出,又接地气,且抓住了儒道不同之关键,不能不令人叹服。诸如此类的论述,在《汉民族史记·文化卷》中俯身可拾。如变:古今汉字的转折点;秦兵马俑:汉民族古代雕塑的巅峰之作;“变土为金”:从原始瓷到真瓷;汉乐胡舞:汉民族歌舞艺术融会的高潮;学派林立与人格建构:理学成熟;平民宗族:宋代汉民族乡村社会的转型;从楷书到宋体:稳定了汉字千年的字形;从《史记》 到《资治通鉴》 的大变古;从“六艺”到“四部”:汉民族学术文化的追根溯源;学科蜂起:汉民族学术文化的转型,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地域、语言、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构成的,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汉民族史记·文化卷》所展示的文化图像中,可见“汉民族的文化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江大河。这条大江大河从史前、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元到明、清到民国一路奔腾而来,使人们共享了一次心灵的巡礼。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15]文化史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徐先生娓娓道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历史生命力,感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历史胸怀,感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历史定力,感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多元张力,感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多彩魅力,感受到汉民族文化的灵魂呼唤”[12]1。正因为《汉民族史记·文化卷》 形塑了汉民族的灵魂,才使《汉民族史记》超凡脱俗而可成为鼎扛之大作。
六、人类学离散论视野:描绘汉民族走向世界的路线图
令人惊异的是徐先生的《汉民族史记》竟然有一卷“海外移民史”。我作为徐先生指导的硕士,由于具有较好的英文基础,有幸成为他撰写此卷的学术助理。
离散(Diaspora),既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亦是当今存在的社会现象。人类字学的离散论是近20 年移民研究的新理论,刘冰清和石甜认为“二战后,关于离散的研究不仅仅是关注犹太人,视野范围也扩大到了美籍非裔、海外华人以及因为持续战乱所流离失所的亚美尼亚人,讨论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家园故土与客居他国的族群的关系,扩大到了第二代与故国的想象,因为劳动市场的开拓而引发的迁移等等。新的用法则涉及分离的任何类型,包括诸如中国人的贸易离散,或像土耳其人和墨西哥人的劳动迁徙离散。”[16]郝国强则认为“离散是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新人口现象”,但“总体而言,国内外离散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有待继续深入”[17]。
其实,徐先生早就开始关注族群的离散研究了。原来早在《汉民族发展史》出版之后的20世纪90 年代,徐先生就为当时研究汉民族史没有包括海外华人、华侨而深感遗憾[6](P582)。此后,他心中一直记挂着这件事,并一直默默地进行着学术准备。机会不负有心人。2015年,徐先生开始撰写《汉民族史记》就把“海外移民史”专列一卷,以还三十年前许下的心愿。
在徐先生眼中,汉民族不仅是中华民族视野中的“凝聚核心”,而且还是全球视野中的“太阳民族”。正是“凡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看今天的世界,五大洲何处无华人?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天涯何处无华人?汉民族真可以堪称永不落的‘太阳民族’了。”[6](P582)在《汉民族史记》中,徐先生以汉民族海外移民的萌动时期、汉民族海外移民的开启时期、汉民族海外移民的初发时期、汉民族海外移民的曲折发展时期、走向世界:汉民族海外移民的大发展时期五章,近60万字的篇幅,向人们描绘了汉民族走向世界的路线图。
由于是汉民族海外移民的开端之作,徐先生牢牢地抓住了三点:
一是把与汉民族移民有关的学科,如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航海学、灾害学和外交学等学科打通整合在一起,抓住民族史、移民史、航海史、造船史、灾荒史、外交史、华侨华人史、佛教史等与汉民族移民有关的部分,努力打通,实现跨学科的交融和整合,来建构汉民族的海外移民史。
二是用大历史的视野,把汉民族的海外移民置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思考“安土重迁”的汉民族为什么会从江河走向海洋?为什么会冒百死,反海禁,下南洋?为什么又会从南洋下西洋而走向世界,如《易经·系辞下》所云:“致远以利天下”。成为一个对世界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太阳民族”或“海洋民族”。
三是借华侨华人史的学术高地,尽力吸收华侨华人史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汉民族海外移民史记》的内容,使之有血有肉而可立于学术之林[6](P583)。
这种脑洞大开,“不二法门”[3]的创新之举,呈现了汉民族2000多年波澜壮阔的海外移民史,真正是难能可贵。为还20多年前许下的心愿,徐先生在《汉民族史记》的卷首扉页上赫然写上了“献给全球华人”5个大字!正如王华博士所言,展示了徐先生“开阔的视野,伟大的胸怀”[18]!
七、结语:满园春色关不住
人们常用“春色满园关不住”来形容春天的生机盎然。其实,我们翻开《汉民族史记》,黄灿灿的带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标志的护封,红彤彤的精装封面上印有一个大大的墨黑“汉”字,大气之势扑面而来。翻阅各卷,时不时地感受到浓浓的人类学味道和意韵。难怪此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类学会会长郝时远先生和中国民族学会会长杨圣敏先生的鼎力推荐。郝时远先生说:
徐杰舜先生能够成就这样一部汉民族史记的鸿篇巨制,是他几十年来笔耕不辍、深入思考、不断积累的结果,他先期的《汉民族发展史》、《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和《汉族风俗史》等研究成果,都是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就,由此也奠定了他在汉民族历史研究中的权威学者地位[19]。
杨圣敏先生说:
该书不仅淋漓尽致地向读者生动而形象,深刻而朴实地展示了汉民族惊天动地的历史和文化,也寓意深切地向读者明示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伟大历程的艰难和漫长,这是一般民族史著作很难有的境界和很难达到的高度[20]。
《汉民族史记》厚重而深邃,全面而系统,多彩而生动,以百科全书式的视角,向世界呈现了一个从历史深处走来、阳光而伟岸的汉民族,将汉民族史研究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它既是一部有规模、有分量、有深度、有品位的里程碑式的汉民族通史,又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汉民族专史。当然,《汉民族史记》的价值和意义现在可能还难以充分显现,还需要在历史的“酒窖”中慢慢发酵,慢慢彰显。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言:
《史记》能夠成就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巨著,依靠其建立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位一体”的结构模式。……徐君的《汉民族史记》 追迹《史记》的结构方式,突破王朝述史的框架,按汉民族经历的丰富性、多样性部勒篇什,在比较舒展的框架内放手编写,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文化繁富的一个大民族树了碑、立了传,实属难能可贵。徐君把他的学术历程比喻成“马拉松”。这个研习汉民族史的“马拉松”跑了半个多世纪,堪称“在崎岖小路上攀登不畏劳苦,今天,终于到达了又一座高峰,这是值得载入学术史的事。
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云:“天若有情天亦老”。说的是倘若上天也有感情,也会随着岁月蹉跎而老去,也指自然法则是无情的。徐先生自己在《总后记》中也深有感触地说:
《庄子·养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确实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度的,而知识是没有限度的,以有限度的生命去追求没有限度的知识,就会弄得很疲困;既然这样还要去汲汲追求知识,就会弄得更加疲困不堪了!说实话,虽然五年来研究和撰写《汉民族史记》的经历,使我深深体验到了“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的疲困不堪,但吾初心不改,能为伟岸的汉民族,为“太阳民族”或“海洋民族”的全球华人,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吾心不悔
俱往矣!我们今天能读到满满人类学味道的《汉民族史记》,真应该为徐先生的“吾心不悔”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