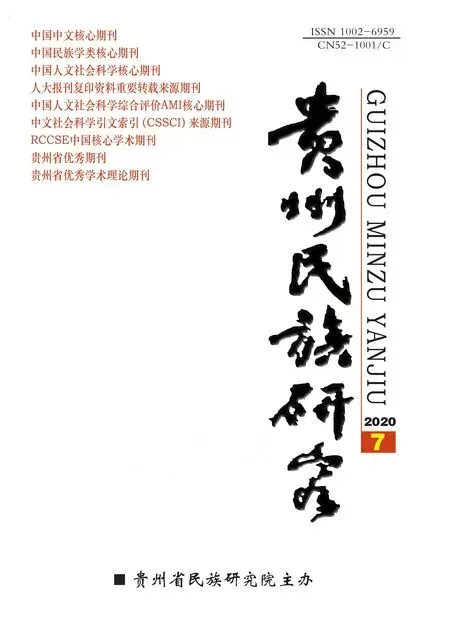回归传统 超越传统
——评徐杰舜主编的《汉民族史记》叙事取向
朱炳祥
(武汉大学 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最近,徐杰舜教授主编的《汉民族史记》出版了,这是一部在汉民族研究上史无前例、内容丰富、体系宏大、具有创新性和时代意义的鸿篇巨制,共分九大卷,洋洋523万字。这部著作的叙事有一种强烈的回归与承继传统的取向;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回归,也意味着在时代的语境中对传统的超越。
《汉民族史记》对传统史学叙事传统的回归取向是明确的,徐杰舜教授在“卷首语”中说:
如何呈现泱泱汉民族的历史?是按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中,中国史学界所形成的通史范式来呈现?还是按太史公司马迁所开创的汉民族史学传统结构模式来呈现?我们反复斟酌、反复实践、反复比较,在历时近五年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近代通史范式的刻板性、束缚性和浅薄性,越来越体会到传统结构模式的生动性、开放性和深刻性[1](P4)。
中国传统的史学叙事体例主要有3类,一是以《左传》 为代表的以年代为线索编排历史事件的“编年体”;二是以司马迁的《史记》 为代表的“纪传体”;三是以事件为主线编排的“纪事本末体”,如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在3类叙事体例中,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影响最大。《汉民族史记》对于传统史学叙事模式的推重与回归,特指对司马迁《史记》叙事传统的回归。
在中国历史的书写中,传说孔子所作的《春秋》开辟了一个传统,即依据经典文献书写历史,其特点是“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 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2](P119)孔子的学术态度非常严谨,“疑则传疑,存而不论”,而司马迁则将中国历史源头追溯到五帝时代,撰写了《五帝本纪》,其贡献在于,他将当时人们认识的历史追溯向前延伸了几千年,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源头。也正因为将历史向前延伸到足够的长度,并且找到了源头,司马迁才能在追踪原始时代黄帝以来历朝轨迹演变的过程中,发现“王迹之兴”的政治史的宏观变迁规律。司马迁“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即汉代)”“略推三代,录秦汉”“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P818),他发现,原始时代后期的“五帝时期”是依靠权威建立统治这样一种“德治”社会管理与控制的模式,虞夏“积善累功,德洽百姓”,汤武的“修仁行义”,皆为对五帝时期“德治”传统的承继[4](P123)。也就是说,原始时代的黄帝到夏商周,所强调的治理天下的经验是“善、德、仁、义”传统。但是到了秦代,这种“德治”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秦襄公至秦始皇之前的这段时间,强调了“德”与“力”的并重,并且重心放在了“力”上,如“蚕食六国”就是“力”的表现。但这仍可看作是“量”的变化。而到了秦始皇时代,则彻底改变了原始社会依靠权威统治的“德治”传统,重新建立了一种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传统。这是“质”的变化。其后,陈涉“斫木为兵,揭竿而起”自称王,继之刘邦、项羽起义进而到西汉王朝的建立,为正是延续了秦始皇所建立的专制传统,形成了“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即由下层阶级以“力”(武力) 直接夺取天下的新规律。而在追溯中国历史源头并且探索中国历史发展变迁规律的同时,司马迁又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得以产生的基础与本根,这个基础与本根就是五帝时代创立并延续到夏商周三代“德洽百姓”“修仁行义”的传统。因此,概括说来,《史记》叙事最基本的贡献在于对于中国历史源头的追溯、对于历代王朝兴衰成败规律的探索以及对于中国文化之根的发现。
《汉民族史记》承续了司马迁向着历史源头探索的坚定意向并有所拓展。如果说司马迁对于汉民族文化源头“五帝时代”还仅仅是作为“传说记忆”来书写,或者说仅仅是一个推论;那么《汉民族史记》则证实了“五帝是一个历史时代”,并且进一步确定了“五帝时代的坐标”[1](P151)。虽然这一看法并非徐杰舜教授首倡,但是反复辨析当代诸多学者的各种相同或者相异看法,对浩繁的古代文献包括在传统上不受重视的“纬书”在内的众多典籍材料相互参证,结合考古材料与田野材料的实证,进而从中抽绎出合乎历史真实且具有内在逻辑的结论,坐实了五帝是“历史事实”,则是徐杰舜教授主编的《汉民族史记》的当代贡献。
如果说“坐实”历史源头较之“推论”历史源头显示了当代研究对于传统研究的超越,那么,梳理上古至现代的5000年民族历史变迁规律相较于梳理上古至汉代大约3000年“王迹之兴”的变化规律,则又体现了另一种超越。我们现在习惯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比喻成一条龙,那么这条龙应该是一条完整的龙,也就是它是一条“有头、有尾、有中腰”的龙,五帝时代正是一个龙头。司马迁大胆地推测出存在着这一个龙头,但由于他生于2000多年以前,故而无法判定这条龙的形态特征。而在当代,这条龙经历了5000年的成长,它从“潜龙勿用”之龙,到“见龙在田”之龙,到“或跃在渊”之龙,再到“飞龙在天”之龙,有了各种发展变化,已经显示出更为完整的形态学特征。既然已经确定了“龙首”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么在5000年的历史中,这条龙如何延伸发展,如何摆动龙躯,如何神游天下,都应据其踪迹进行言说。于此,《汉民族史记》将民族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汉民族的起源时代、汉民族的形成时代和汉民族的发展时代。起源时代,其主源有二:炎黄与东夷,支源有三:苗蛮、百越和戎狄。形成时代,时间从夏代开始,直至汉代,时间延续了1000年。发展时代,时间从魏晋至近代,其间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这是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大发展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宋元明清时期,这是民族继续交融与汉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近代汉民族新发展时期,显示出满族汉化、中国民族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转向等特征。总之,《汉民族史记》显示出了汉民族从远古走向近古、从近古走向近代的整体历史过程的变迁,同时显示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所形成的汉民族的基本特征。
进一步说来,《史记》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司马迁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司马迁采用将田野材料、民间谱牒与典籍相互佐证的新方法,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历史学家的目光。司马迁重视田野调查、重视民间文化,进行实地考察,在田野调查中他发现各地的“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5](P6)。与此同时,他还重视民间文化的谱牒。当时,正统的儒家的观念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他们不屑于传述流传下层社会的谱牒。司马迁则不同,他把《五帝德》 《帝系姓》 《世本》等一大批谱牒利用起来,与《春秋》 《国语》相互佐证与发明,使史学大大地扩充了史料的来源,这才使他有可能追溯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找寻到中国历史文化的本根。
《汉民族史记》有着明确的史学与人类学双重学科意识,其在田野调查方面成就尤其突出。徐杰舜教授兼具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深厚修为,他对于《汉民族史记》的设计,整个九大卷中的许多卷都是运用田野分类法去串联历史材料的。双重学科的叙事视野,这个《汉民族史记》与《史记》的相通之处,很容易被找到;深一步说,还涉及到徐杰舜教授所推崇“专题结构”的叙事形式问题。我们在初读《汉民族史记》时,或许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写的是汉民族史记,那么紧扣着汉民族的历史问题写作就可以,也就是说,《汉民族史记》的“历史卷”是符合本题的,而后面的篇幅更为巨大的“族群卷”“文化卷”“风俗卷”“海外移民卷”并不与本题切合,似乎应该将这四个部分共七卷的内容融合到“历史卷”中去。解释这一疑问,就是解释《汉民族史记》整体叙事的匠心独具。从田野调查出发,所形成的必定是一种“专题结构”的民族志形式,而《史记》的编撰体例,全部都是“专题结构”的叙事形式。徐杰舜教授对此说明道:
传统结构模式,没有历代王朝框架的束缚,众所周知, 《史记》 所开创的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的专题结构,就具有开放性特点,从而使历史的编撰灵活机动,收放自如,不仅可使历史生动起来,更可使历史的叙述深刻起来。为此,我们这次编撰《汉民族史记》,正式按照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继承汉民族的史学传统,运用传统结构模式,将汉民族史的呈现分为发展史、族群史、文化史、风俗史和海外移民史五个专题[1](P5)。
设置汉民族史的发展史、族群史、文化史、风俗史和海外移民史这5大块,是《史记》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的专题结构的继承。不过,这里接踵而至的又是一个疑问:《史记》专题结构叙事体例的核心是“纪传体”,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的主要部分是人物传记,而这个最重要的特点在《汉民族史记》中却似乎并没有得到继承,因为在523万字的巨著中,甚至没有一篇是专写某个具体人物的,这又怎样解释呢?
在我的理解上,徐杰舜教授的“五卷分类法”正是对《史记》“纪传体”传统的历史回归与当代超越。《汉民族史记》将《史记》“纪传”中作为“个体”的人物承继下来,并转换为作为“群体”的人物。《历史卷》中对于“炎黄”“东夷”“苗蛮”“戎狄”的四分类,《文化卷》中对于“炎黄”“东夷”“苗蛮”“百越”“戎狄”的五分类,与《本纪》何其相似!《族群卷》更是一个很好的体现,该卷列出了汉民族的7个分支族群:东北族群、华北族群、华中族群、华南族群、华东族群、西北族群、西南族群,这种分类有似于“世家”分类的拓展。每个族群里边又分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如沈阳人、河北人、山东人、湖北人、湖南人、客家人、上海人、关中人、四川人等共43个人群,这种分类又与“七十列传”的面目相似。因此,司马迁《史记》对于“个体”的纪传仍然由《汉民族史记》继承下来并转换与拓展为“群体”的纪传。而《文化卷》《风俗卷》亦有类于“十表”“八书”的专题结构形式,其内容亦有相通之处,它们同样记载了汉民族的历史大事与各种文化典章制度。至于《海外移民卷》,则既可以看作是《史记》中关于域外文化交流零星记载的承继,又可以看作是新的时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汉民族史记》叙事之所以出现强烈地回归传统的取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近代以来受西方史学影响的叙事方式的一个深刻反省。徐杰舜教授很不满意中国民族历史的近代叙事模式,他要从这个框架中解放出来:
近代通史范式弊端不少,其往往以历代王朝为坐标,刻板地把历史按朝代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一般重政治轻文化,往往写成了朝代更迭史,束缚了历史学家的手脚和思想,从而使历史浅薄地蜕变成为帝王将相史。……反思民族史的研究。由于解放以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受中国通史研究方法论的影响甚深,在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中,一般独立专章、专节叙述某朝代的民族及民族关系。因此,除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通史已包括了中国民族史,没有必要再赘述,而忽视或轻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外,更重要的是无视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把民族史的内容套在中国通史历史王朝的框架中,使民族史成为了中国通史的附庸[1](P5)。
受西方史学叙事影响的中国通史叙事范式举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6]为例。第一册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原始公社时代、夏商时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政治史事、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的演变和文化思想状态。第二册收入了秦汉至隋的统一时期,分别叙述了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十六国、东晋和南朝、北朝时期各王朝的兴亡、经济状况、文化概况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化。第三册、第四册是隋唐五代时期,同样从政治兴亡、经济状况、文化状况三个固定模式对各个时期与各民族进行叙事的。在民族史方面,则可以举出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7]为例。这部书就是将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这四个汉族来源、东胡系、肃慎系这两个满族来源以及匈奴系这一回族来源,套在“秦以前”“汉至南北朝”“隋至元”“明至民国”这四个时期之中来叙写的。再如与民族史相关的“风俗史”同样也是这样。如晁福林的《先秦民俗史》[8]关于“风俗”的八个分题“饮食”“服饰”“居住”“交通”“氏族、宗族与人名”“礼俗”“岁时节令”“信仰与宗教迷信”全部整齐划一归入了“原始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诸历史时期的框架之中。《汉民族史记》 的确彻底摆脱了这种近代通史叙事范式的“刻板性、束缚性和浅薄性”,塑造了该书叙事的“生动性、开放性和深刻性”的特征,从而证实了徐杰舜在《汉民族史记》的叙事取向上既回归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创新,足见徐杰舜汉民族史研究50余年的匠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