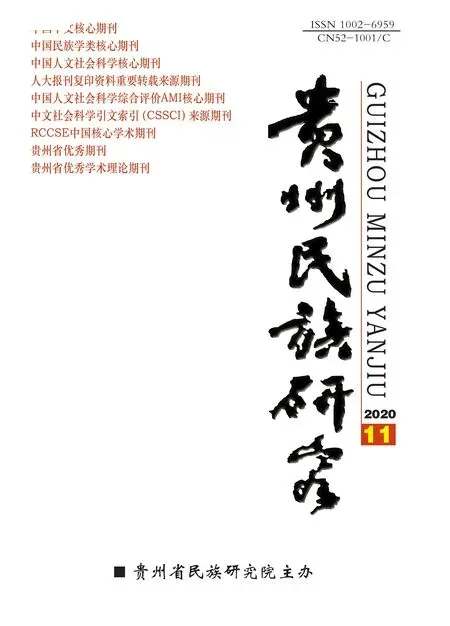白族学者杨琼《论语案》的价值与思想方法初探
杨志明
(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民族文化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500)
一、杨琼《论语案》的经学史价值
经学应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需要而生,它既是一种学术传统,更是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自上(中央) 而下(地方) 贯彻和自下而上认同的重要思想纽带,因此直至清末民初仍盛行不衰。就此而言,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对象,理应囊括内地和边疆在内的全国古往今来的重要经学成果。然而时至今日,边疆民族地区的经学成果,不仅极少有学者问津,未被系统研究,更没有被纳入众多“中国经学史”论著研究和叙述的视野。无论从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学术严谨性,还是从其政治敏锐性来说,这都是不小的疏失。
古籍资料显示,云南的经学初兴于明代,且以辑刻儒家经典和内地学者的注解为主,是学习阶段;云南学者自著经学成果的大量涌现,在清代和民国初期,是创作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自明代至民国,云南学者辑刻和自著的经学成果有近80 种250卷之多。其中,辑刻原著及内地学者注解的有20种145卷以上,云南学者的自著有56种190 卷以上。对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经学,对弥补中国经学史既有成果研究内容的缺失,这都是一笔数量可观的宝贵财富。
再深一层看,云南经学同内地经学一样,也经历过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标志这一转型的典型成果,当以大理邓川杨琼、滇南石屏袁嘉谷、昆明呈贡秦光玉等人的著作为代表。秦光玉的经学著作漫及《尚书》 《礼记》 《论语》 《孟子》《学庸》 (《大学》 《中庸》合称),以捡择章句阐发其义理,时兴历史和现实的感悟为特点,故通以“郄视”(管窥) 为名,显得比较零散。袁嘉谷流传至今的经学著作,最重要的有3部: (1)《经说》 先论“经”之称名、传承和作用,再分《易》 《书》 《诗》 《春秋》 (含左氏、公羊、谷梁三传) 《礼》 (含《周礼》 《大戴礼记》) 《论语》 《孝经》 《孟子》诸部捡择经史和章句义理而论,前者是比较完整的专论,后者则是感悟性的散论; (2) 《诗经古谱》 为残篇著录; (3)《讲易管窥》纵论《易》之起源与完成、流传及古史进化观,是最有新见创意的系统之作。
杨琼以专治《论语》见长。民国四年(1915年) 秋,杨琼著成《论语案》四卷,请云南巡按史任可澄、政治文化名人赵藩、学务处总参议陈荣昌作序、题辞,随即付与开智公司印刷后分赠各校师生及戚友参阅,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对杨琼的《论语案》,任可澄的评价是:“钩稽群经,抉择诸史,复时采泰西学说与孔子之说相印证,于以校量其纯骏,别白其异同。凡朱注所未尽者,辄引伸而发明之。虽其说间不免于附会牵引,要能旁参曲证,以自申其旨。即起前贤而难之,或未能胜也。”赵藩称:“其紬绎故训,间发新理,或感触时事,或藉镜欧西,大要取便学子所易领解,而亦可以备一时之参证。知通人必不执诂经家法,以相绳也。”陈荣昌简评为:“析义甚精,持论甚正,实足为后学之津逮。”这些评价总体上是中肯的,但较为笼统,且偏于《论语案》的义理创见一边,未能揭示其关注社会、通经致用的思想初衷。
细考杨琼的《论语案》,从思想方法看,我们认为其最显著的价值和特点,是兼通“四书五经”,通过章句与全体通贯、经论与史事兼顾、考训与义理同治、中学与西学互鉴、通经与致用联袂的诠释,系统阐发《论语》的经义及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思想方法与朱熹《论语集注》等古注很不相同,是颇有时代气息、社会担当的一种系统创作,故细论如次。
二、章句与全体通贯
杨琼对《论语》的注解,虽20篇俱全,且各篇及其中章次的顺序不变,但并非每篇逐章解析,而是有所捡择地进行侧重阐发。为避免其捡择性的注解失之“随兴”和零散,保证《论语》原著蕴意的完整性,杨琼采取了以《论语》各篇完整的某章为中心,将其与《论语》 其他相关篇章“内联”、与儒家其他经典相关篇章“外联”,且“内联”与“外联”相互通贯的诠释方法。
“内联”方面,如对《论语·公冶长》“雍也仁而不佞”章,杨琼就联系《论语》 的《学而》《子路》 《宪问》 《里仁》 《先进》诸篇相关章节进行诠释,称:“夫子尝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曰‘刚毅木讷,近仁’,曰‘有言者,未必有德’,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曰‘是故恶夫佞者’。是仁则不佞,佞则不仁,其判然矣。”这就充分说明,强调仁厚(“仁”) 与巧辩(“佞”) 不相容,主张君子应该仁厚持身而不齿巧辩,是孔子的一贯思想,而不是偶发之论。
“外联”方面,如对《论语·子路》“子路问政”章孔子所答“先之”“劳之”“无倦”,杨琼又联系《大学》 《诗·鄘风·定方之中》 《礼·月令》 《易·乾象》 相关章节进行诠释,称:“此章,夫子示子路为政之道,只‘先’‘劳’‘无倦’四言耳,而其理无不赅,玩之最有趣味。先之者,道之以德,如‘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是也”;“劳之者,如‘星言夙驾,税于桑田’‘周视原野,修利堤防’是也。无倦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指出孔子关于为政的一贯思想,是强调执政者要以身作则、勤于政事、无怨无悔地砥砺奋进。
“内联”与“外联”通贯方面,如对《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章,杨琼按语:“今读《论语》,以觇夫子之道,章章各有不同,即一章中亦各有不同,似乎万殊,而究其大本大原,则无非一理。琼于‘一以贯之’句,解之曰:‘夫子心中浑然一团全是理,发出来千头万绪全是道。’”而这个“一以贯之”的“道”“理”,就是为学之道、君子之道、成圣之道,亦即《论语·学而》中孔子所谓“学而时习之”之道,《论语·里仁》 中曾参所谓“忠恕”之道, 《中庸》 所谓“中和”之道, 《大学》 所谓修己安人(内圣外王) 之道。故,杨琼于《论语》首篇《学而》首章“学而时习之”,按语称:“此章,开宗明义,夫子只提出一个‘学’字,而不明言所学何事,是亦教人用心推想,不肯一语道破,以为学者择善固执”;于《论语》第二篇《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按语:“此章,‘学’字最宜注意。空空说一‘学’字,到底学些甚么?朱子解之曰:‘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夫大学之道,其纲领多端,非可以一言括者。然则可以一言括者,其惟圣乎!圣人可学而至也,人皆可以为圣人也。‘志于学者’,犹云以学圣为目的也”;于《论语》第四篇《里仁》“吾道一以贯之”章,按语:“此章‘吾道一以贯之’,要说成圣人之心浑然一团全是理,行出来千头万绪全是道,方合彼《中庸》所谓‘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又于《论语》 末篇《尧曰》 末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按语:“《论语》 首章‘学而时习之’至‘不知不愠’,而曰‘不亦君子乎’,末章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此深有意,盖学期于为君子”,“《论语》首末皆以归重君子,其记者之微意乎!”
这种思想方法,与对《论语》作逐章逐句孤立解释的朱熹《论语集注》等古注明显不同,更能揭示《论语》各篇章旨的通贯性和孔子思想的体系性。
三、经论与史事兼顾
《论语案》在解释孔子关于孝道、为政、君臣关系、人情与法理之分、儒家与道家的不同、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守礼的重要性、富贵与贫贱的去处(chǔ)、“仁”的事功和心术二义、举贤任能的关键、国家兴衰之理、孔道(儒教) 传承的纲脉等问题的论述时,往往征之史事,以彰明其义理,突出其意义。其所引史事,基本出自“五经四书”及《史记》和前后《汉书》等正史。
如,于《论语·学而》所载:“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杨琼就先总其义为:“此章,夫子示有国者以治道之本”,在引《司马法》 《尚书》 《诗经》相关论述予以申述后,又引史“以事验之”,说:“舜之端拱垂裳,文之陟降左右,敬也。魏文侯之期猎,卫商鞅之徙木,信也。唐尧之茅茨土阶,汉文之一衣数汗,节用也。 《益稷》 之股肱群臣,《康诰》之赤子斯民,爱人也。三代之蒐苗狝狩,皆于农隙,筑城作室,役以冬时,使民以时也。大抵敬信是节用、爱人、使民之本,而敬又是信之本。”“端拱垂裳”“文王陟降”两说分别出自《易》和《诗》;“唐尧茅茨土阶”“汉文一衣数汗”俱载于《史记》;“魏文侯期猎”“卫商鞅徙木”分别见于《战国策》 和《史记》, 《益稷》《康诰》 为《书》 之篇;“三代蒐苗狝狩”事见《春秋左传》。
又如,于《论语·雍也》 所载:“子谓子夏曰:‘女(汝) 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杨琼引申其旨为:“此章夫子之警子夏处,正为千百世后之学人发其病状,而药石之”,并引史事以证明其说:“若夫后世记诵辞章之习,但溺于辞章,以干利禄,设心固已左矣,而复盗名欺世,腼然以儒者自居。如汉之公孙宏,晋之殷浩者流,此真小人矣。甚又若宋之王安石,清之袁枚,则俨然与君子为敌。人或非之,则且肆其文才以拒谏饰非,使人之言之者不能以相难,此则小人之甚者。”公孙宏事迹见于《史记》,殷浩事迹见于《晋书》,王安石事迹见于《宋史》,袁枚事迹见于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和朱庭珍《筱园诗话》。这一引史申述,既符合《论语·里仁》中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界定,更是对孔子原意的细化理解:“小人”之中又有图利不顾名的“真小人”,和既图利又争名的“伪君子”(“小人之甚者”) 的重要区别。
经论与史事兼顾的思想方法,不仅使《论语》原有义理更明确、细致,也使杨琼对《论语》义理的阐释显得更加平实、更有历史深度。这与宋、明道学家对《论语》的诠释重理论思辨的取向明显不同。
四、考训与义理同治
考据学重文献内容的“事实”考订,训诂学重文献的词义、语法译解,杨琼长于文字学,有专著《形声通》 《肄雅释词》,故其《论语案》对《论语》的诠释,由重史事而至考据、训诂便自然而然。杨琼对《论语》章句义理的考训诠释颇多,这里仅举数则以见其治学的严谨、细致。
《论语·泰伯》载:“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对泰伯“三让”,有朱熹主让商、二程(程颢、程颐)主让周而史无定论。杨琼支持朱熹之说,并以考据学细加论证。其论证为: (1) 《论语·泰伯》记孔子之言:泰伯、文王之时,“(商之) 三分天下(周) 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夫!”是“明谓让商”。(2) 泰伯、文王之时已具备克商夺位的条件,但他们仍“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为”,故孔子称“泰伯之至德为让商可无疑”。(3) 如泰伯之让为让周,则其仁义仅及于“父子兄弟之间”,而只有让商,其仁义及于“天下国家之际”,才足以与孔子称其有“至德”相称。(4) 所谓“民无得而称”,是因为周人未有天下之时,商人编纂的史籍不会记载周人的圣德,由此亦见泰伯之让是让商。(5) 《春秋传》 (《左传·僖公五年》) 称“泰伯不从,是以不祀(嗣)”,所谓“不从”,即“不从太王剪商之志”,泰伯之让为让商更无疑。杨琼对朱熹观点的支持性论证周密细致,再征之史籍相关记载,泰伯“三让”为一让季历,二让文王,三让武王,均在周克商而拥有天下之先,则可确断泰伯之“三以天下让”为让商。
《论语·乡党》 详记孔子执摈之事,有人据《史记·孔子世家》,考订《乡党》所记为(鲁) 定公十年(公元前509年) 夹谷之会时事,杨琼则据周礼知识否定这一解释,认为这是“不知会礼有相而无摈,宾礼有摈而无相。此言摈,则非相可知”。这是说,定公十年(公元前509年) 夹谷之会时孔子已摄行相事,按上古礼制,孔子执摈之事绝不会发生在此时。又,朱熹《论语集注》引宋代学者晁说之的“孔子定公九年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间绝无朝聘往来之事。疑使摈、执圭两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尔”为说,杨琼则认为:“细玩语意,系与前后文一律,皆是记者从旁摹拟而纪实焉者。则安知非左氏、史迁所失载哉?”这是据语言分析而怀疑古代学者的通识,并疑及儒经、正史的记载有缺失。
《论语·阳货》记载孔子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说,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又注引:“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朱熹以“义理(天命) 之性”兼“气质之性”解孔子所谓“性相近”之“性”,程子则认为这里所说的“性”,只能作“气质之性”解,而非关“义理(天命) 之性”(“性之本”)。杨琼支持程子的解释,同时赞同宋儒将人性区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并追问“一‘性’字,何为有二说”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此,宋儒的解释思路是形而上学(义理思辨) 的,而杨琼则另辟蹊径。他以汉字构造和使用的类型(“六书”) 学为据,解释说:“性”有二义,“以会意言,性从心生”故有“义理之性”,“以假借言,则假生为义”故有“气质之性”。进而,又以儒经相关论述为据,证明孔子、孟子、 《中庸》 论“性”均有“会意”与“假借”二义。这就为宋儒的人有二性说提供了语源学补证。
可见,考据、训诂与义理结合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使杨琼对《论语》的诠释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实说、新见。
五、中学与西学互鉴
晚清至民国初年,西风东渐日烈,杨琼生活在那个时代,又曾被委派到日本考察学务,兼习师范一年有余,对西学有较多接触和了解,中西文化比较于是成为杨琼诠释《论语》的重要视角。《论语案》涉及中西社会、风俗、文化、政教、哲学、科学、教育、军事的论述随处可见,而其认识和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
一是认为中国重伦纪,精神文明优胜,西方尚功利,物质文明优胜,二者之间有“守本”与“逐末”的根本差别。如,杨琼对《论语·学而》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的按语为:“今泰西之俗主于兼爱,其于孝弟之伦置而不讲,以此推行,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其何道之能生哉?”在《论语·学而》“子张问十世可知”章的按语中,杨琼说:“今泰西之俗男女平等,自由结婚,始而苟合,终而苟离,夫妇之伦未立,父子因以不亲,根本拔矣。”在注解《论语·雍也》篇时,杨琼对“(子) 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的按语是:“今世之法律家,必参权利于义务之内,以遂人民之欲望,是先获而后难也,将使举世争夺,而真性漓矣,焉得仁?”对“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按语是:“今之外国列强,可以作齐观也;其尚功利,喜夸诈,不殊乎齐也。今之中国,可以作鲁观也;其事伦纪,守礼义,不殊乎鲁也。虽外国富强,中国贫弱,不足为得失也”;对“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的按语是:“近世欧洲之政策,其博施济众之政策乎……此固我国之所宜师法者也。特其近于墨氏兼爱之教,其于一本之义有所亏缺,势必至于根本不固,枝叶随以枯槁,事有余而心不足,仁道转为之阏窒焉。”所谓“墨氏兼爱之教”,即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功利思想;所谓“一本之义”,即儒家由“亲亲尊尊”而“仁民爱物”的道义主张。
二是认为孔教可与西学相通。如,杨琼在《论语案·为政》中认为,西方哲学自康德合笛卡尔唯理论、培根经验论“二派而一”之后,便与儒教传统的“知行合一”主张相通;在《论语案·里仁》中认为:“西人论理学(逻辑学) 之演绎、归纳法”与儒家的“格致工夫”相同,“演绎者,即一理而演绎于万理;归纳者,由万理而归纳于一理”,因此与孔子所谓“‘一以贯之’正相发明”。又如,在天人观方面,杨琼认为《论语·宪问》所申明的执政者“尚德”、勤政,而不“妄冀膺符受箓”, 《季氏》 所讲的“国家兴衰迟速之理,皆由人定以胜天,非由天定以胜人”,“亦即近世天演学家‘优胜劣败’之谓也”;在教育学方面,杨琼认为西哲苏格拉底所谓“产婆法(启发式教学)”、培根所谓“器械法(灌输式教学)”与儒家声教相似,而裴斯塔若吉的“直观法”则与《论语·阳货》所载“子曰:‘予欲无言’”所强调的身教相似;在伦理学方面,杨琼认为《论语·子张》所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既“与《大学》 格致诚正之理互相发明”,“然即泰西之心理学,亦可以证明之”,因为“心理学家言,人之一心分为知、情、意三种,而道德之作用在意志”,“知”即“博学切问”“格物致知”,“意”即“笃志近思”“诚意正心”,“以此观之,心理学亦仁学之谓哉”。杨琼甚至在《论语案·尧曰》中指出:“孔道之传,又分经学、文学、理学三大部别……今泰西又有科学、哲学诸名目,将与我孔子之学相沟通,则又当有集中、西之大成者起而继焉。”后来果然有现代新儒学涌现,印证了杨琼的洞见。
三是认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是“中体西用”的“大同”之世。在《论语案》 的《为政》 和《雍也》 两篇,杨琼分别总结说:“人道进化之理,斯宾塞尔尝发明之。彼西人且必变其无伦纪之俗,而进于有伦纪焉,斯臻进化矣”;“外国一变至于中国,中国一变至于大同。夫孔子之所谓道,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所谓“外国一变至于中国”,是说西方应当转变其重功利和物质文明的传统,向中国重道义、重精神文明的核心价值观靠拢;所谓“中国一变至于大同”,则是说中国在坚守孔教仁义之“道”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应像西方一样大力发展经济、军事、教育,补足富强济众、法制禁私之“术”。
杨琼抑西扬中的阐释,无出于当时“变器不变道”的保守观念,是对物质文明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对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以“硬实力”相竞争的残酷现实的轻视,因此不免有空悬道德理想之失。然而,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行为若无道义指引、公德制约,其后果又是极其危险、不堪设想的。因此,杨琼之失,不在强调道义,不在标举道德理想,而在将道义的理念和原则锁定、固化为孔教(儒教) 的礼义制度设计。
六、通经与致用联袂
杨琼治《论语》的根本目的,不在考训文辞、征之史事、鉴之中西以澄明玄学义理,而在通经致用,突出孔教的现实意义和救世功用。因此,《论语案》对《论语》各篇章的诠释,几乎都以指明其章旨的现实意义为结语。
比如,《论语案·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章的结语为:“大抵格致天算之学(按:指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西人较中国为精,若夫哲理名言之蕴,中国较西人为精,未可以轩西而轾中也。”对《乡党》所载君子的服饰,杨琼在指出中国重五行、礼制,西方重生态、适便之后,总结说:“此古今、中西之不同,不必泥古而病今,亦不必重中而轻西也,时而已矣。虽孔子在今,亦惟损益之,以随时而已矣。”于《子路》“樊迟请学稼”章,杨琼指出孔子的本意是强调君子当以修己安人、引领政治世风为首务,而不是钻研和从事物质生产,因而以“焉用稼”拒斥樊迟,但在结语中杨琼又补充说:“特樊迟之意,虽失之浅陋,然在今世犹可通。”并在《子路》“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章的按语中,详述“今西国陆军”的兵种、学制盛况后,指出:“今若以一日不教之民,而使之战,岂非以卒予敌,弃之如遗哉?”这是看到了传统儒学的轻视物质文明和军事科技之失,而暗示儒学亟需开创出富民强国之“术”。
又比如,对《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尧舜也与”章,杨琼在按语中指出:“上古之治,任人而不任法”,“近今之治,任法而不任人”;“任人之治,上古可,近今不可;任法之治,近今可,上古不可。何也?上古人心浑噩,相见以诚……近世人心机变,各遂其私,不可以恃人。卢梭曰:‘国家之名,乃由人民合群结约而成。’此《民约论》之意也。夫孟子固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又是在强调社会、国家的治理必须德治与法治并举。对该篇“子曰:‘有教无类’”章,杨琼按语说:“今西国与日本,皆谋教育普及。日本以一岛国,人民不过二千余万,而其学校林立,至有三万数千所之多……以此观之,夫子‘有教无类’之言,与外国之理亦合。吾国可不急谋教育普及乎哉?”
由此足见,杨琼《论语案》的思想方法,既与沉醉形上义理、内圣工夫的理学(道学) 路向不同,也与执意社稷疆场、百姓日用的实学取向有别,更与彻底否定儒教传统的自由主义、西化思潮迥异,是一种既有义理思辨,又有社会关切,更有国故情怀的近代经学的特殊形态。
———无锡泰伯墓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