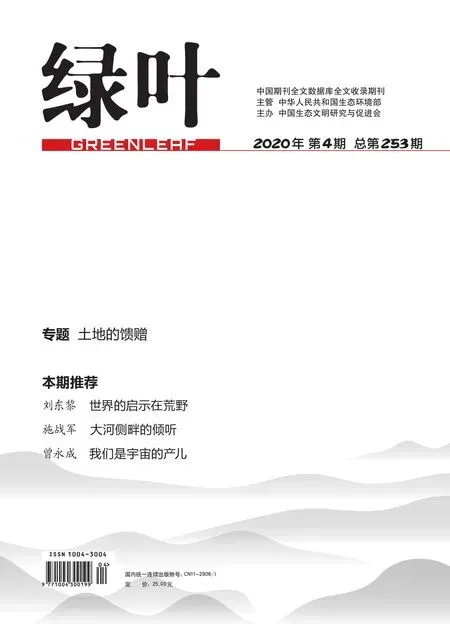湛江行吟(组章)
◎梁永利
走在雅致的家园
一
偶然记住了一句广告语:粤西越美。在我的心里,越美的就是湛江。
湛江的美,不在于有多少胜景,不至于像明信片一样,一叠叠风光,装靓了,让人渴望到此一游。
湛江的美,是不经意间的流盼;是小家碧玉的风情;是有气度的雅致。
我不再想把红绿蓝的色彩挡在我行走的前方,因为湛江的本色,沉实、自在,还有那么一点野趣,我的生活因之优雅!
世事荒荒,常常扪心自问,能优雅吗?如若上班一族,公务缠身;如若家庭主妇,烦于菜蔬残毒;如若骄骄学子,择业何方?诸多的负累,心重意沉,谁能借一方仁山智水,谁能指引一处小径,给你释怀,给你闲看花开,静观云起?
有的!我借给你一款新新的湛江。在一个早晨,与你把持迷雾笼罩的绰约;在一个黄昏,与你轻啜海湾景色酿成的红酒,那份恣意,那般芳香,一定会把你的郁郁愁情消解开来。
二
走在湛江的古埠头,遇见一口水仙井。看看在百年时间里涌出的清凌之水,它避开了咸风腥雨,那苍桑,一袭心头,我的凝视自然回到了故旧的宁静。水有何欲?自漫自流,它不作声的放任,带着几分轻狂,如书风草色,打点些许时光,我还能再介意生存的困惑吗?
走在湛江的绿道,我希望下着轻雨,在雨中有油纸伞的相逢。你看到了吗,小雨点数着湛江行走的脚印,深深浅浅里有探寻,有追问,有向往。
湛江是水做的。东海的钢龙在兴云了,西海的蔗林在结雾了,赤地千里换了绿妆,当我吸过清风的甜味,心空已被湿润擦亮。
我时常,借着细雨,享受湛江的柔情。斜竹间,噼里啪啦,疑是惊兔飞鸟,小女狐仙。我想着浪漫,想着野趣,这仿佛旷世的情结,放在生活之途,怎不是安闲?
安闲断不能无趣,陪心爱的人读书,学琴,饮茶,听雨,闻香,湛江太合适不过了。旧时,周作人先生的雅致,料想北京是不能满足的。如今,北京的茶肆又那么喧杂,没有湛江的温婉清雅。我想,周老先生,在天有灵,过来湛江一遭,陪你喝一杯不求解渴的酒,小吃不求饱的点心吧。
三
行走湛江,最让人赏心的也许是它的红树林吧?在市区观海长廊就有一大片。走近它,你一定能获取生命的原始冲动。因为它的胎生,你会想及人与自然生存能力的契合,相比之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自身功能渐渐地弱化了,但红树林不是,它即便穿越了千年时光,它的内生能力越发逢勃。看它的根系,奇形怪状地呈现着,这些气根,葳蕤着它生命的繁衍。红树林总是维系一片和谐的天地。化石岩边,小红蟹举起大拇指,指挥着它的队伍;弹跳鱼爬在树上,凸出的双眼,转晕了花花的碎光;海螺的行动最是迅速,一有动静,倏地钻进泥里;吹水泡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来,此起彼伏地让人生奇;只管前行,而忘记了海天一色的景趣,一群白鹭在树枝上面盘旋,给观海的人们带来湛江的一片祥和。
长廊观海已经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在那里,习以为常的海风,会把你的肺掏空,生长在银沙与海的边缘的红树林,又将绿色的养料补给你,充实你,你拥抱生活的情愫一定在大地流行。
我在湛江慢生活着,把一天当两天三天过。要命的浮躁是权欲有加者的事,与我何关?我在慵懒中用点功,我在用功中也偷点懒,谁教我九万里悟道,终归田园诗酒?是湛江,是盛满我雅致情怀的家园。
东海岛,请给我坚硬的诗情
在一场铁骨与柔情的赛场上,回荡着我海螺般的呼唤。这是湛江的钢铁“梦之队”,为东海岛打下了一枚纪念的钢桩。我呼唤的风,没有腥咸;我呼唤的雨,穿过井架,与红土地上的炽热,相互交融。
新一代的工人,整装碧海深情,仿佛熔炉淬火,目光是火辣辣的。他们看到钢轮一样的朝阳,在康庄大道上奔腾,拴不住惊喜和原浆的幻象,千万吨空间,同样等待着我和东海岛初恋的井喷。
东海岛,请给我坚硬的诗情!这个热季,给远航的船乘上了翅膀,南国新港响起湛江号的笛声;给海风系上刀锋,削除一些藏在礁石里的杂质,红树林的领地,开阔了一片海,我与小鸟依然排演青春的礼赞。
有了钢铁,我们的江,掀高了立体的水;
有了钢铁,我们的岛,伸出了森林般的臂膀。
水的高度,是创造财富的难度,但我已熟悉钢花飞溅,是水与火的洗礼。
去掉平庸 、萎缩,每一根都神经注入铮汉的骨气,臂膀伸出了 ,它如钢板将柔软压实,海上钢城又锃亮多少曙光?
我需要从银沙上练习顽强,让一年几趟的台风从胯下溜走,狂风吹不尽的,是我思想的金矿。从此等着一盏灯点燃,我爱坚硬的誓言。
我需要钢铁的哺育,习惯吐酸的胃,学会消化一串串铁骨头。
我记得 ,从一本书开始,我吸收了钢铁的营养,呵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东海岛让我看到了心仪的答卷。
南三写意
从祈祷的罄声中醒来,我的南三梦系上了用一挂水珠做成的金链,泠泠作响。它藏着昨日星辰的瞩目和今朝露水晶莹的遐想。
来回弯曲的水道,我舍不得岛上人家的眷恋,冷不丁冒出一句令人向往的俗语——“寿比南山”来。是啊,这南三不就是南山?
我善意的比方,已闯进当地方言的趣味里,三不是山,山也是“三”。这是何等相似的心音回归!
“山”与“三”权当海岛人寄望美好的谐音吧。
“寿比南山”与其说寿山,不如说松树,不如说梦想。寿是人们日子的叠加,或平或淡,或风或雨,老了比不过松树的挺拔;即使是南山的松树,也会有千年的枯萎,断不如拥有一颗善心,在海岛看潮起,看花开!
今年的七月,我记住了家乡海岛的清凉,一场风魔过后,海吼沙飞的景象,悄悄地静下来。
水火二重天的历劫,展示了人们坚韧的意志。
意是自然给予南三海岛的画景。
志是眼前开拓故园的一腔心愿。
我不敢小觑南三岛含情的等待,当全力打造国家级滨海旅游示范区的规划出台后,她的因缘,她的际遇,通过南山大桥这只大手,再次牵引了人们的目光。
看看,俗世的喧嚣终不能浸染她的风韵,走在阡陌间,方方水塘,她广阔的胸怀,融汇氤氳,飘渺于轮回之中,是海风吹出的和畅,白云刷新的纯净,烟雨孕育的精魂,这山这水,显出了她的灵性。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印顺大德弘愿而来了!结缘于海岛上的交椅山。他以海南南山寺弘法的威严,亲手置下菩提树,发起一方善心,拟把这里修建成祈求和平的圣地,观音文化的福田。
交椅山在南山诸岛中最高。其实,高也不过是海拔三十余米,而它却应了“有仙则名”的诗句。
此山留仙。附近村民常在更深夜澜时,听到了空谷之声,有如南风尽日的瑶琴,猿鸟满山低吟;有如北窗下的秦筝,清愁绵绵,盘旋林中;月光清冷,树影婆娑,隐约里仙女飞袖,掩过海岛的上空。这祖辈相传的故事,充满着神秘的色彩,让人认定交椅山非同一般。
说得也是!当我来到田头墟的陈氏小宗时,交椅山的神奇因陈瑸认宗的传说广为流传。
陈瑸是出生在雷州市附城镇南田村,他与南三岛有何牵连?
这得从陈瑸高中进士说起。田头墟的陈氏裔孙、作家陈济华给我讲了一段民间故事。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陈瑸中进士后,回到家乡雷州南田村拜祭先祖。当他跪拜下去,神台上的神主牌就一个个倒了下来。陈瑸当时甚感疑惑,就问他母亲。母亲告诉他:“你虽然是在南田村出生,但你的根却在南三岛的田头村。”
原来,陈瑸的母亲怀了他之后,还未待陈瑸出世,他父亲患了一场大病,不久,就撒手人寰了。苦于生计,母亲怀着身孕,回到娘家雷州南田村。不久,陈瑸便在南田村出生了。
自那时起,陈瑸就许下一个心愿:有朝一日,一定要到南三岛来寻根。
陈瑸曾先后两次来到田头村,但田头村的进士和秀才有一大筐,村中的长老以为,陈瑸那时的官职不算什么,不怎么看得起他,于是,就有点骄横地对陈瑸说,田头村也是从乾塘村迁出来的,那里才是大宗,你应该到那里认宗归本。可陈瑸到了乾塘村,乾塘村长老又说,你是田头村的后裔,你还是回到田头村去为好。就这样推来推去,气得陈瑸叫苦不迭。
陈瑸又返回南三岛田头村,在田头村东北的交椅山上狠狠地踩上了三脚板:有你田头村,就没我陈瑸公,有我陈瑸公,就没你田头村!他刚说完,交椅山立时飞沙走石,眨眼之间矮了一大截。此后,田头村的风水就真的慢慢衰败下去了。田头村的风生水起,交椅山的确是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从地形来看,交椅山如一只待飞的凤鸟。自古以来,它的啼鸣是东边海浪遏云的回响,人们的各种传说,不无证明自然界的神奇。在这里,我感觉到了南三岛的旧形与新势,波光与树影,阳刚与阴柔,这相对应的生存法则,会呈现出亘古的和谐。也许印顺大德的行愿,是基于自然的造化与南三人的福德,不然,这刚启动的设想,何以借菩提见性南三示范区的宗教文化?
我从南三的行政区所在地田头墟到交椅山,不用半个钟头。沿着小沙路,我轻轻地拨开路边青葱的草蔓,来到菩提树旁,视野顿觉空辽:远观东海岛钢铁基地吊架云耸;近见池波不惊,鹭鸟低翔,呈现出一派凤鸣南三的仙境。
此时此刻,你不能不佩服南三示范区管理者的远见,通过打造文化园,筑巢引凤,这凤又正待势而飞翔,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凤鸟是百鸟之王,凤有向阳、秉德、高洁、示美、喻情等神性。印顺大德于此筑山鸣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天涯。从海南的南沙到湛江的南三,道途不远,却是南方岛与岛的相约,天涯与海岛的倾情。在这自然的馈赠与击赏中,超越生死之海,正见能量,止恶行善,成就未来,这怎不是一种使命呢!
当我踏上南三岛的那一刻,南三人诚信、直谅、大义的美德就萦绕在耳边。
南三拥有了自己的功德,南三大桥可以见证!
南三谱写了前进的乐章,环岛交通可以见证!
南三描绘了生活的畅想,新村崛起可以见证!
这就是南三岛穿珠串玉的丰姿,将南三的海岛文化集合,这就是南三写意的梦想。
也许梦想很小,小成别致的新楼,小成山野的花儿,小成恒河的砂砾,在一刹那间,小成我你的会心微笑。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南三的水月云天啊,有50公里的联围大堤接连着,这是一幅创造人间奇迹的画轴,以交椅山的文化幅射,南三正如一位出浴的少女,唱出了建设家园的心声。
如果你有开拓生命的勇气,你有青春岁月的那番创业激情,来南三吧!听听这里涛声的呼唤,和我一样,留下拥抱南三的写意与幸福的时光!
邦塘村怀想
我到邦塘村,并不是为了寻根,因它的根基太浅,在雷州半岛腹地的小凹坑上,除了听见几声牛哞狗吠,面前的古瓦残墙,倒让我想起了人间世兴替中的漠然。借明清两代70多位文武官员的威名,换来“传统宗法观念的缩影”的称号,其愚忠尽孝的意识,荫庇宗族的心态,像一枚钉子一样击进我心灵深处,它用四百年的斑绣,腐蚀了我淡淡的愁绪。这斑绣贴在民居的土墙上,层层叠叠,勾勒出时间闪过的影迹,偶尔也脱落了游人的惊奇。
来的人不多,多的是古屋,共一百余座,堪称古民居博物馆。单是李光祖一家就拥有四条巷道,十多座屋宅相连,有7进,呈回字形,有72间房子,84扇门,大小天井24个。没有古建筑知识的人,懒得去想象它屋内雕刻的优美和吉祥的动植物图案的清晰!反正,轩子里、断壁外全是红荔黄皮簇拥着。有了果香,历史与现实就有了味道。
趟完“廉让间”“中和”两条石板巷,邦塘村的前情往事,如它后坡上的山稔花,绽放了小小的诗意,又如一丝浮云的遮盖,我的心扉萌发了几许童真。于是,我学会了对远方的思念,学会了等待当那一丝浮云飘走,我就会等到它一潭池水边的嫩绿,它的清香。当然,有时候等待是那一枚钉子钻入身心的痛快,让心灵结痂后悄然掀开了的期盼。
多年以来,邦塘村成为城里的月光停留的一个驿站,它的蛙鸣仿似雷州歌,给一缕新芽或是一剪燕影歌唱。抑扬顿挫里,抹去张家李屋的蜚短流长。我走在熟悉的小道上,看到了一抹久违的春色。心里想着,只有在这里,诗人的油纸伞,才会结起丁香,世俗的负累才可释怀。我怀旧的情愫也许受伤了,而归家的方向不会迷失。
静坐在学堂的石凳上,喜欢手捧着南坡先生的诗卷,轻尝着他思乡的情怀,以及他一介儒士培育后学的风范。那一年,一顶红木轿子抬举着李绍绎归来,整葺了学堂,从此,一册册散装的雷俗,演绎着南坡先生的故事。如今,邦塘是名城雷州的民俗村,但其民俗不及民风。它的静雅,用无声的细涓来表达;它的朴素,用村边的古槐来展示;它的纯洁,用燕语来吟哦……
我抚摩着它的一片红瓦,我爱上了它悄然改变的容颜。几条小巷,黄沙已盖着它的苍老,兴许有世人不愿窥视到的落魄。但这落魄正是明清才子的印记,当今村民乐业的心情才是悠闲。
不再踏上了它的石级,不再欣赏它班驳的灰雕,只是一室书香、半亩方塘、些许桑麻、加上鸡鸣田舍的日子,把我推进了一种难忘的境地,我苦心种植的诗行,在乡风的吹拂中高高地飘扬。
在邦塘村,我为自己学识的浅薄而愧疚,为听不惯粗言俗语而不安。我在雷州本土文化的滋补中,激活了所有的失落,若让诗心在邦塘村出轨,我一生中的些许幸运是否在邦塘村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