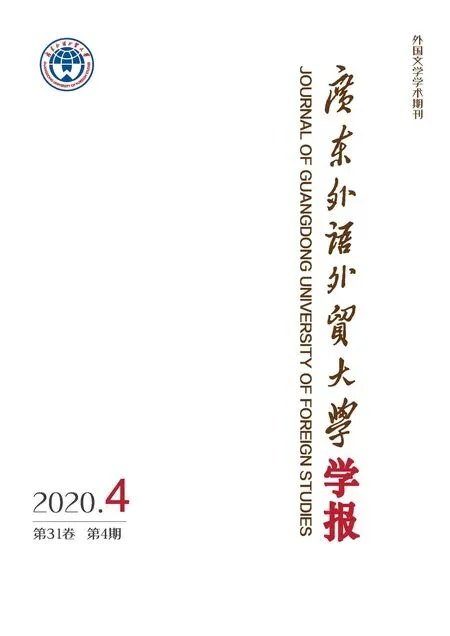中西诗学精神的暗合
——梁宗岱诗学新论
魏国岩
引 论
晚清以降,西学涌入,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思维模式与西方多元的诗学体系发生了激烈碰撞,迸发出绚烂的火花,梁宗岱诗论就是万千花朵中较为夺目的一朵。对梁宗岱的学术研究从一九七九年香港文学批评家璧华编撰《梁宗岱选集》的抛砖引玉,到二○○三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纪念梁宗岱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再到二○一三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办的“纪念梁宗岱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掀起了梁宗岱研究的热潮,时至今日仍有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梁宗岱诗论研究相关成果是丰硕的,其代表学者有黄建华、文学武、曹万生、张仁香、陈太胜、栾慧、许霆等人,在梁宗岱象征主义诗学、纯诗理论、契合论、比较诗学、诗学精神等方面做出了有力探索,为我们用中国传统诗论与西方诗论交的叉视角去剖析梁宗岱诗论构建方式,挖掘他的诗论根源提供了基础与启示。梁宗岱的诗论,是在中西方诗学文化相互融合的环境中建立起来,注重“借助比较鉴赏中外诗风”(黄建华,2003:128),在充分理解中西方诗学精神精髓的同时,也找到了中西诗学精神的融合之点、暗合之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说到:“梁君几乎才认识我们底文学,便体会到那使这文学和现在艺术中最精雅最古老的艺术相衔接的特点”(梁宗岱,1984:188)。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诗学体系中,寻找共通点,发现二者的沟通之处,从而展开深入的诗学研究,是梁宗岱诗论的重要出发点。“他以比较文学的眼光、融通中西的意识看待一切文学”(栾慧,2014),努力地寻找着中西诗学的“融合点”(孙玉石,1999:156),进而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有力而可靠的支撑,引导中国新诗健康发展。
“妙悟”与纯诗的“共相”
“妙悟”一词最初见于东汉曾肇的《长阿含经序》:“晋公姚爽,质直清柔,玄心超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9:9)。自魏晋南北朝开始成为佛教中被广泛运用的专业术语,加之中国士大夫多与佛家道家学者交流密切,有的本来就“身在佛中”,在思想上必然受到禅宗和老庄思想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作为禅宗的“妙悟”说,逐渐进入了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对“妙悟”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妙悟说”,“妙悟”成为一个极富中国传统特色的美学命题。
纯诗理论是源自西方的诗学观点,是现代主义诗论中具有“双重身份”的一个概念,其一方面涉及了诗歌的本质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了诗歌的形式问题,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纯诗关于诗歌本质的问题。纯诗是什么?马拉美主张“呼吁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强调“作诗应该运用话语捕捉那即将消逝的出神入迷的心灵状态”;穆木天在《谭诗》中根据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要求,首先打出了“纯粹诗歌”的理论大旗,认为“纯诗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诗是潜在意识的世界”(陈惇、刘象愚,2000:136)。
梁宗岱则认为,纯诗与“妙悟”有着共通之处。他说:“严沧浪曾说:‘大抵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不仅作诗如此,读诗亦如此”(梁宗岱,1984:10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纯诗讲求的是内心“感悟”、“妙悟”和“灵感”,作诗是一个心灵探寻的过程,这符合中国传统诗学轻逻辑重感悟的特点。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改变了我们写作的语言方式,白话诗歌也涌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从历史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但新诗作为新生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诗的散文化主张降低了“诗的门槛”,诗的“平民化”主张导致了“诗艺”的简化与退步,缺少了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诗也就没有“妙悟”的存在,诗歌如果不去“散文化”,将很难继续发展下去,结果必然是诗的衰亡。梁宗岱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这个严重的问题,所以他要竭力地宣扬他的“纯诗”理论,他提出了诗是什么、如何提升诗性的问题,呼唤诗艺的回归。梁宗岱倡导诗歌内容与形式不能肤浅直白,要具有诗的特质,要运用象征的“手腕”,要具有含蓄性和暗示性,要充分用色彩和音乐来表现,给接受者进行体悟和发挥想象的空间。他试图通过对“纯诗”的倡导,来呼吁具有“妙悟”特质的好诗出现,以此来捍卫诗的形式特征和本质内涵。
“纯诗”理论是梁宗岱诗论中的核心概念。温儒敏(2005:216)认为:“从批评史上考察,与其把梁宗岱视为象征主义诗论的译介者,不如说他是‘纯诗’理论的探求者”。这十分准确地说明了“纯诗”理论在梁宗岱诗学中的重要地位。梁宗岱在《谈诗》《论诗》《新诗底纷歧路口》等相关文章都有关于纯诗的论述。他认为:“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梁宗岱,1984:95)。梁宗岱认为要做纯诗,诗人应该超越自我主体,回到自然,去捕捉刹那的灵感,一首好诗,是外物刺激后偶然得来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创造出来,要通过外在的表象世界的暗示,去发现生命中的哲理。他对纯诗的界定充满了玄幻和神秘,认为艺术创作离不开灵感的恩典,这种感悟可能以“闪现”的方式出现,转瞬即逝。但同时他也强调,灵感的光顾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到生活中去、到大自然中去、到爱人和孩子那里去感受生活,感受美好,去发现生活中的美。梁宗岱认为纯诗最好的表现方式就是象征,象征具有暗示性和隐晦性和神秘性,因此要求接受者必须具有感悟能力,需要读者或批评家注重对音乐和色彩的体悟,来激发我们的官能,去参悟和还原所暗示在作品中的灵感。假如没有“感悟”,即使作品在艺术独具匠心,具有“艺术手腕”,那也称不上是一首好诗。梁宗岱的诗学观倾向于唯美的纯诗情的感受,十分强调感观世界的外在形式的审美功能。可以感觉到,梁宗岱的纯诗论,是诗人对内心世界的表达。
梁宗岱的诗论深受瓦雷里的影响,他对纯诗理论的这个特点能够较准确地把握,针对纯诗的这一特质做出了较为丰富的阐释,并以此为融合点,实现了中西诗学精神的融会与贯通。梁宗岱赞成严羽的“禅道”和“诗道” 在“妙悟”方面的共通之处,他引用王国维的“古今来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之三种境界”的论述,用“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来描述“妙悟”的内涵,细细品来,非常贴切妥当。这正是因为纯诗需要“感悟”的特性,决定了纯诗必定超越原作者的创作初愿,发挥其更大的暗示力和弹性,也因为心灵的沟通没有界限,无论作品是感性的或是理性的,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是虚幻的还是现实的,都能够通过心灵的桥梁进行融会贯通。梁宗岱对文学接受中“妙悟”的强调,与纯诗的“暗示性”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传统诗学观对他的熏陶与影响的结果。而恰是在这种沟通与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误读”,才使中国传统诗学中的“妙悟”说与西方诗论中的“纯诗”理论,建立起了“共相”的关系,丰富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空间。
“兴”与象征的共通
中国传统诗学中的“兴”在甲骨文、金文中是群体合力向上举物之象。郑玄注《周礼·春官》说“兴者,托事于物”。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朱熹在其《诗集传》中的定义比较精当,他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托事于物”是指诗人将所要抒发的意愿不直白的道出,而是通过其他事物或意象来暗示。在中国兴的运用一般并不是独立,常常有兴与赋、兴与比并用,这样更能发挥出兴的作用,这样会使兴句的暗示作用更加突出。“兴”在《诗经》中有广泛应用,如《关雎》是以水鸟相向和鸣起兴,喻君子和淑女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自己的智慧,与劳动生活相结合,创造了“兴”的艺术手法。
“象征”源于古希腊文,原是“信物”的意义,随着生产生活的需要后来演变成一种标识、暗语或仪式的代名词,渐渐发展为用某种符号或标志物来传达某种观念、含义,通俗地讲就是用有形的事物来指代无形的意义,使其具有含蓄性和暗示性。查尔斯·查德威克的《象征主义》一书认为:象征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从柏拉图开始就关注到了象征,诗歌成为人们表达和探寻现实与理想的工具后,因着象征具有“储蓄性”和“暗示性”,也就成为了文学必不可少的表现手法。黑格尔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象征问题,他说广义上的象征是发端于东方的,而象征的特殊涵义却是在近代法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才赋予的。黑格尔将象征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1)象征是一种符号;(2)象征的本质具有双关和模棱两可性的;(3)象征不是比喻”(王泽龙,2008:39)。
中国较早关注“兴”与象征相通特点的是闻一多,他认为:“西洋人的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相当于《易》中的‘象’和《诗》中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中作为风情诗的风,必须带着伪装,所以诗人的语言中,不能没有兴。象与兴实际都是隐”(闻一多,1993:232)。闻一多把“象”和“兴”放置到了诗学理论的位置,这是他的创新之处,其重要意义更在于他率先看到了中国传统诗学中的“兴”和西方现代诗学中的“象征”的共通之处,但象与象征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闻一多这里有偷换概念的问题。周作人(1972:68)说:“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让我说一句陈腐话,象征是诗的最新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我们上观国风,下观民谣,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较赋与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周作人认为“兴”也有模糊性,不只是比的依附,是有实实在在的意义的。周作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关注到了“比”与“兴”的关系,为象征拓展了类比的项,强调象征是中国古典诗论的一部分。但并没有深入地分析西方诗论在象征的本质含义上与“兴”的区别。
梁宗岱是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重要开拓者,深谙象征之道,“象征主义在其诗学体系中呈现出网状的结构,其精神几乎触及到他的每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文学武,2010)。梁宗岱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结合他对西方诗论的深入体悟,对兴与象征做出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与阐释。他赞同刘勰对“兴”的解释,梁宗岱(1984:66)认为:“《文心雕龙》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义。’所谓‘微’便是两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表面看来,两者似乎不相联属,实则一而二,二而一。象征的微妙,‘依微拟义’这几个字颇能道出”。他将“依微拟义”视为象征的奥妙之处,也意识到了“意象”与“拟义”之间有关系。接着引了《诗经·小雅·采薇》、杜甫的《登高》、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细致地阐释了象征的含义,最后总结说:“所谓象征是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出神底瞬间看风的遥遥的宇宙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世界”(梁宗岱,1984:69)。梁宗岱由对“兴”的解释来引申出对象征的诠释,让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切入点十分恰当,进一步明确象征作为一种符号具有暗示性的特征,给象征下了通俗易懂、十分精当的定义。
朱光潜与梁宗岱的“象征”之辩一直是学术热点,梁宗岱(1984:64)说:“朱光潜根本的错误是把文艺上的‘象征’和修辞学上的‘比’混为一谈”。接着亮出观点:“我以为象征与《诗经》里的‘兴’颇近似”(梁宗岱,1984:66)。我们不难看出,朱光潜是以西方的“理”为核心来阐释象征观的,而梁宗岱是以中国的“情”为核心来说明他的象征观。正是因为朱光潜对西方美学的深入理解和认同,才使得他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阐释他的象征观和美学意识的。而梁宗岱是以中国传统的诗学精神和美学意识,来表达他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象征观,梁宗岱找到了中西诗学在“兴”与象征方面的暗合之处。这一点上,梁宗岱的努力确实要比闻一多、周作人的定义更接近到象征的本义。
“真”与宇宙意识的暗合
“真”与“善”“美”同是中国传统美学命题。中国首提“真”的是老子,后由庄子进行了集中的阐释,深化了“真”的美学内涵,将“真”升华到中国传统美学的层面。《庄子·渔父》有言:“真者,精诚之至也” (胡仲平,1951:308)。“真”从字面上理解是“伪”的对立面,是事物的本质,是宇宙的本真世界。在这里梁宗岱所强调的“真”是“心灵之真”。在梁宗岱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强调:“真是诗的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的最高与最终的实现”。梁宗岱把“真”作为诗唯一的“根”,作为衡量诗的最高标准。他说,一首好诗最低的标准是要让接受者佩服他的艺术手法,再高一层次的便是让读者感受到它是有生命的存在,而最高层次的好诗是让接受者感受到了它的生命,但却忘记了他的艺术手法,梁宗岱把这三层称做:“纸花”“瓶花”和“生花”(梁宗岱,1984:95)。可见探寻“真”是梁宗岱诗学理想的追求,他所强调的“真”是形式与内容合一的双重“真”实。同时,梁宗岱还强调诗要与现实生活密切的结合起来,他认为,诗人必须有十分丰富的人生阅历,才能获得珍贵的“妙悟”与“灵感”,才能写出有生命的诗。梁宗岱把诗人的性情与诗歌的创造结合起来,强调诗歌的形式不只是内容的载体,同时也是反映诗人性情的一面“镜子”。徐剑(1998:1)称梁宗岱为“本真诗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文如其人”,梁宗岱相信什么样气质的诗人,自然会写出什么样风格的诗。因此,如想达到诗歌形式上的“真”,诗人必须要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和精神内涵,丰富自己的想象,净化自己的心灵。
“宇宙意识”是象征主义的重要概念之一,马拉美就有较强的“宇宙意识”,并将宇宙与诗歌的关系作为拯救诗歌的有效手段,他说:“我理解了在诗歌与宇宙之间的内在关系,为了使诗歌保持纯洁,我有意要将它从梦和偶然之中解脱出来,使之与宇宙的观念相并列”(董强,2005:130)。这种思维将诗歌置于“形而上”的层面,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象征主义认为,诗人是被上帝选中的人,他拥有认识和传递神秘的使命与能力,把诗歌和诗人的责任神圣化了。
梁宗岱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较深,谙熟象征主义的宇宙意识,所以他的诗论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亦回避不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他所谈到的“宇宙意识”也是中西诗学精神上的一个共通点,这种宇宙意识既带有中国传统诗论的感悟式的审美直观,又不乏西方象征主义的神秘的元素。在《李白与歌德》一文中,梁宗岱倡导诗歌创作应探寻宇宙的玄机和生命的奥义,认为中国唐代诗人李白与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宇宙意识极其相似,这种宇宙意识表现出了优秀的艺术作品具有的相通性,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流露出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真”的终极体现。梁宗岱的“宇宙意识”是充满了对“人”的本质的思索,是对人性的一个探索。对时间的思考是宇宙意识必然涉及的问题,梁宗岱十分喜欢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这正是因为陈子昂对时间观念的认识和其宏大的宇宙意识。梁宗岱喜爱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仅是因为这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时间的存在和时空的变迁。陈子昂和孔子捕捉到了“刹那”的妙悟,使刹那成为了永恒,“禅”境顿生。这正是梁宗岱诗学精神所探寻的“真”的境界,从终极层面上来说,哲学意义上的“真”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宇宙意识”实现了统一 。
“物我两忘”与“契合”的融通
“物我两忘”是中国古典美学概念,语见沈约《郊居赋》云:“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沈约,1995:5)。其意源于《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傅璇琮,1999:72)亦指创作时艺术家的主体与创作对象的客体浑然为一而兼忘的境界,诗人进入这种体验境界时,直觉会处于亢奋状态,灵感涌动,在这种状态下能创作出奇思妙想、浑然天成的艺术作品。中国古代诗论家非常注重的创作主体与外物的统一关系,一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艺术家的才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才能创作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契合”兴起于法国象征主义,是西方诗学重要的审美范畴,波德莱尔和爱伦·坡是“契合”论的先驱。契合论受到了波德莱尔推崇,是其象征艺术的核心,《契合》是他《恶之花》中一首十四行诗,诗中把自然比喻成一座神殿,芳香、色彩、音响相互融合感应,形成了“幽暗与深沉”的“象征的森林”。他认为人与自然、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人的感官之间都存在着感应连通的关系。“契合”有三层含义,首先是通感或联觉。指人的感觉器官功能之间体验的交融、互换。感知事物普遍性,万物都来自同一个本源和宇宙的奥秘,但因人的不同感官的作用,呈现了不同的世界。其次是外在物质世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之间的交互与感应。指人的感官在受到外在事物的刺激作用下,而唤起的思想或情感,达到从外物的感应,而进入精神世界。最后是精神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同一。指人的直觉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世界。这种对直觉体验的重视和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艺术注重感悟的感知方式极为相近。
中国对“契合”的译介并不一致,先后被译作“交响”“交错”“应和”“感通”等,这些近义词间有着交合和连通的共性内涵,也都合情合理,但梁宗岱给了最为恰当、正确的翻译“契合”,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契合”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其理论内涵与“物我两忘”有着相通和相似之处,很容易让中国诗人所理解和接受。中国传统诗学中,从诗歌创作到接受,“物我两忘”的例子不胜枚举,能够将味觉、触觉和嗅觉等官能作用吸纳到诗学领域,注重色、香、味等刺激对产生美感的重要性,达到“万化冥合”的效果。西方象征主义注重将“物”进行区分,并通过表象与本质构建艺术世界,这实际上是“物我合一”的思想。梁宗岱认为“契合”有形与神,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同一性。这一点与波德莱尔强调“契合”是人的感官与内在的心灵、人与宇宙万物融合的主张相似。
梁宗岱谙熟象征主义诗学,对象征主义诗学核心内容的“契合”给予了正确的定位,他说“契合”乃“象征之道”(梁宗岱,1984:71),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他在《象征主义》中对这“契合”进行了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契合体现了“生存是一片大和谐”(梁宗岱,1984:73)的观点,是主客体、人与自然的同一和通感,是一种形神两忘的无我的境界。在这里梁宗岱对主体与客体关系进行了理性的阐释,“我们消失,但是与万化冥合了。我们在宇宙里,宇宙也在我们里:宇宙和我们的自我只合成一体”(梁宗岱,1984:76)。他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来阐释“契合”,认为“契合”不只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还是“景即是情,情即是景”,他指出“心凝形释,物我两忘” (梁宗岱,1984:67),才是象征的“最高境”,也就是“契合”。梁宗岱还用“形神两忘”“真寂”“万化冥合”等老庄哲学思想来解释波德莱尔的“契合”。“情景交融、物我两忘”的“契合”论,也正顺应了东方“天人合一”的精神法则。他立足于中国传统诗学观点,在审美方式上接受象征主义契合论,从而找到了中西诗学精神在“物我两忘”与“契合”之间的融通点。
梁宗岱对契合诗学进行了的本土化消解和民族化的重构,他对契合阐释的独特之处在于,以精熟为基础,运用“我”与“物”的整体关系来阐释这个诗学理念,在将“契合”中国化过程中即展现了对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继承,又体现了对西方诗学的吸纳,确立了独特的“契合”诗论观。
结 论
综上所述,在西方诗学接受过程中,梁宗岱诗论表现出了对西方诗学中国化、民族化的重构特色,体现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主导作用与自觉性,也蕴含着对传统诗学现代化的努力与实践。中国传统诗学精神与西方诗学精神本是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文化背景下孕育发展的。原本并列平行的两条线,被现代主义诗潮的浪花摔打出了相连接的“交合点”。正如梁宗岱(1984:35)所说“中西两种诗学在彼此的共相增补更新了对话的‘他者’”。踏着前人的足迹,梁宗岱细致地发现了这些“交合点”,并结合自身中外的学术经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同时也对中国传统诗学中相关的理论进行历时的梳理,分清源流,理清脉络,为我们新诗的发展找到理论之基,指明努力方向,虽说这种“交合点”的搭建有些薄弱,但作为一种交叉视野的尝试,其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