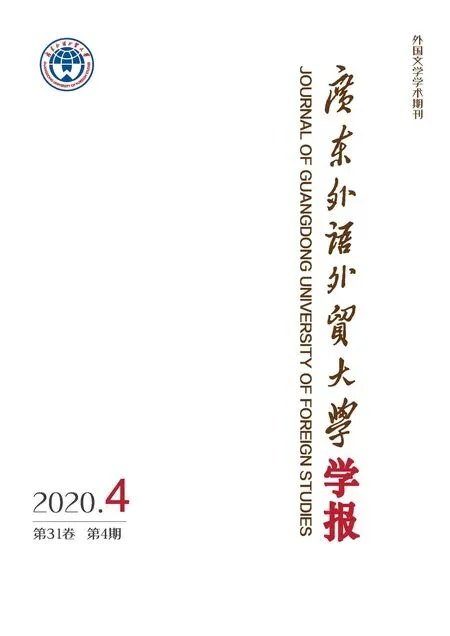论《奇鸟行状录》中的自性实现及女性他者
许静华
引 言
在荣格(2018b:111-113)关于心理学与文学关系的阐释中,将文艺作品的创作模式分为心理模式和幻想模式两大类,指出“心理模式的作品的素材来源于人类的有意识的生活”及“自觉的人类经验的领域”,而幻想模式的艺术创作素材则是“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奇异的事物”,“是一种超越人类理解力的原始经验”。荣格同时非常重视文艺创作过程中作者的“内省”活动,认为在阅读和欣赏文艺作品的过程中,读者和欣赏者对作品的内部心理反应也是一种内省,如果作品和读者的内省能产生共鸣,其震撼的力量就会勃然爆发——“艺术创造和伟大艺术对我们造成影响的秘密在于这种重新陷入分享奥秘的状态”(荣格,2018b:133)。村上春树(Murakami Haruki, 1949-)的作品尽管不乏晦涩难懂之处,却能在全世界收获为数众多的读者,其原因就在于他运用“幻想模式”的创作手法,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理性所难以解释的、人类心灵的共同体验,并始终着眼于人的精神危机,致力于寻求精神救赎。在《奇鸟行状录》(1995)中,村上春树着眼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与心理重建,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深入探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体现了其通过“幻想模式”创作深入集体无意识层面以触发读者内省式阅读的文本张力。
《奇鸟行状录》主要讲述主人公冈田亨在妻子离家出走后陷入自我认同危机之中,试图通过回顾与妻子间从关系融洽到产生隔阂的始末来寻求重建夫妻关系的途径。其间,冈田亨被动地卷入了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之中——打来色情电话的神秘女郎、失手导致男友车祸死亡的笠原May、通灵者加纳马耳他、“意识娼妇”加纳克里他、帮助占卜师本田交付遗物的间宫中尉、赤坂肉豆蔻、肉桂母子等,聆听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记忆叙述。这些发生在不同时空(诺门坎-满洲新京-东京)的故事中共通的“暴力性”以一种超验的联系将冈田亨夫妇卷裹于其中。一筹莫展的冈田亨下到枯井中苦苦思索,在几位女性的“指引”下,最终放弃原本超脱、疏离的立场,并在与暴力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背负的职责,重建自我认同。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春树借通往无意识界的“枯井”、驱动世界/体制运转的“拧发条鸟”等“幻想模式”下的意象,将历史与当下、个体与他者关联起来,从纵向(历史)-横向(他者)对主人公的经历与抗争展开不同维度的观照。
该作品问世之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于一九九六年获得了日本第四十七届读卖文学奖,并得到该奖评委大江健三郎的肯定。中外学者对该作品的解读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其一,对作品中的历史叙述、暴力书写以及村上春树“转向”的关注。黑古一夫(2008:148)、林少华(村上春树,2014:序)、尚一鸥(2013:162-185)、戴玉金(2019)等着眼于《奇鸟行状录》中的历史叙述,认为村上春树试图通过追寻暴力的源头,揭示现代的“恶”与历史的密切关系,进而表达所有人都负有与“时代之恶意”展开斗争的历史责任,体现了其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实现了村上春树的创作态度从“超然”到“介入”的转变。杰·鲁宾(2012:182-215)分析了《奇鸟行状录》与《寻羊冒险记》两部作品在指涉战争历史、暴力传承等方面的互文性。张小玲(2014)聚焦于《奇鸟行状录》和莫言的《檀香刑》中的“暴力”叙述,分析作品的“暴力”表现及内涵。其二,对作品中“战争记忆”重构与日本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的阐释。杨炳菁(2009:132-150)、刘妍(2016:122-152)等指出,作品通过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共同构建了当代日本战争记忆,体现了村上春树对自身国家的历史认识所表现出的复杂的情感焦虑;但与此同时,村上春树通过对个体记忆中历史的叙述,营造出虚无的历史观,在某种程度上消泯了人们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李立丰(2015)、王海蓝(2017)认为,作品中的“满洲叙事”凸显出战后日本流行文学中少见的“二战史观”,但村上春树的历史反思并未完全摆脱日本后现代文学强调体制与个人宿命对抗的表达范式,是为了借伪满这一“他者”反观当代日本社会体制中固有的弊病,而对于作为个体的日本人“被害性”的强调客观上消减了对作为整体的日本的“加害性”的认知。
不难看出,先行研究多从小说中的暴力书写、历史叙述以及通过“战争记忆”“满洲叙事”重构日本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等角度来解读《奇鸟行状录》,这些着重于历史纵线的解读尽管突出了村上春树反思历史、关注日本当下现实的社会“介入”立场,却忽视了小说对横向他者及主人公的精神危机、自我重建方面的着墨,淡化了村上春树对个人成长及人的精神困境的关注。根据荣格的个性化(individuation)理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趋向“精神完整性”(totality of the psyche)的自然的先天倾向,视统一人格/自性实现为个人发展的最终目标(杨韶刚,2017:8)。在理解个性化理论之前有必要对荣格的无意识原型论加以简要说明。荣格认为无意识包括个人无意识以及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的各种本能及原型的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为带感情色彩的情结,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原型(荣格,2018a:5-6)。这些原型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阴影、人格面具、阿尼玛和阿尼姆斯、自性等。其中,自性原型能潜在地把一切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内容和心理特征都结合在一起,使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杨韶刚,2017:42)。也就是说,个体心理发展存在着一种自然驱力,在这种驱力的作用下,自性原型将精神的各种非自我方面(包括阴影、人格面具、阿尼玛/阿尼姆斯等原型)加以认知、区分和整合,使之成为一个心理上不可分割的整体——自性实现,这一过程又称为人的个性化过程。如上所述,小说的主人公在婚姻受挫后自我认同产生动摇,被迫重新审视自己与妻子的关系,进而反思自己的存在价值。
婚姻挫折与自我认同危机
村上春树此前的作品始终以“迷失与自我追寻”为导向,探讨经历精神创伤后防御性的、封闭的自我。主人公们往往遵循“不交流、不干涉”原则,通过刻意地与他者保持距离来维系自我的独立性,借区分自我与他者、强调个体的独特性来构建自我身份认同。《奇鸟行状录》的主人公冈田亨沿袭了村上春树前期作品中“超然”、愤世嫉俗、人际关系疏离的性格特征——与家人没有联系,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朋友,大学毕业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却自嘲为“比跑腿学舌强不了多少”,缺少职业上的自我认同感。在辞去法律事务所工作后,他感到茫然和一种“麻痹感”——“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盯视招聘广告的时间里,我开始产生某种常有的类似麻痹的感觉。自己现在到底在寻求什么呢?往下到底想去哪里呢?或者不想去哪里呢?对此我愈发糊涂起来。”(村上春树,2014:66-67)
冈田亨的边缘化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妻子久美子可以说是他唯一主动选择的交际对象,通过与久美子的结合,他得以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并与社会建立起最小限度的联系。然而,尽管与久美子经历了相识、相爱到结为夫妇,他始终无法在真正意义上理解她。在共同生活的六年间,尽管他对妻子的脾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其情绪波动时尽量采取适当的方法安抚她,却无法理解其情绪背后的真实原因。这位关系亲密伴侣对冈田亨来说同时又是最大的“他者”,令他时常体验到疏离感。在某次争执之后,躺在久美子身边,他不禁自问自己对这个女子究竟了解多少:“何时我才能把握其全貌?莫非到老都对她稀里糊涂,并稀里糊涂地死去不成?果真如此,我这进行中的婚姻生活到底算什么呢?同这为并不了解的配偶朝夕相处同床共寝的我的人生又算怎么回事呢?”(村上春树,2014:36)可见,与妻子关系的隔阂甚至令他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妻子的不辞而别使冈田亨陷入焦虑和混乱之中,其自我认同也濒临崩溃,他试图理解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的原因所在。
就在冈田亨为婚姻危机苦恼不已、找不到出口的时候,他的身边陆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笠原May、加纳马耳他姐妹、间宫中尉、肉豆蔻母子等),向他诉说各自的记忆与故事,冈田亨逐渐被动地“参与”了他们的人生。与此同时,通过对这些“他者”的投射,在他们的故事中感受到与自己不同程度的关联,促使冈田亨在深入地省察自身的基础上审视与他者的关系。
妻子的出走使得冈田亨从无视他者到正视他者、“参与”他者,这一转变体现了村上春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联”的深入的思考。村上春树视小说创作为“自我疗愈”的一个步骤,在执笔《奇鸟行状录》时,村上春树深深感到此前“超然”(detachment)的创作手法已无法支撑日渐庞大的叙事架构,唯有通过“介入/参与”(commitment)——即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才能进入下一个“疗愈”阶段;尽管这种“参与”存在着种种不确定性,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首先必须通过深入自身内在的“掘井”作业来实现(河合,1999: 79-85)。村上春树指称的这一探索自身内在、以期最终在某处与他人连接的“掘井”过程,正是荣格(2018a:20)所描绘的“我于其间体验自身之中的他者的同时,非我之他者也体验我”的过程,是个体透过意识表层深入个体无意识领域,最终抵达人类所共同的集体无意识的基盘的过程。荣格认为,“人际关系有益于个性化过程的原因在于,通过它们,个体可以用投射的方式与无意识的许多方面发生联系”(杨韶刚,2017:213)。村上春树将“参与”他者作为构建自我之重要手段的思考,正与荣格通过对他者的投射来实现自我的个性化过程的理论异曲同工。
值得一提的是,冈田亨所采用的“战斗方式”不是直接与藏匿久美子的绵谷升对峙,而是下到井底,深入观照自己的内心。他为何采取如此曲折而不着边际的做法呢?在小说的开头,村上春树刻意设置了一些具有共时性的意象,暗示着夫妻间共同拥有的情感基盘的动摇以及危机的迫近——刚结婚时捡来养的猫的失踪;撮成两人婚事、两人的监护人占卜师本田老人之死;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拧发条鸟”的出现。冈田亨下到空屋的枯井中冥想,貌似极其偶然的选择,实际上是遵从了种种与无意识相联系的意象的指引:久美子命他到没有出口也没有入口的巷子里找猫,因为猫是他们共同经营的美满婚姻生活的见证;本田老人曾预言“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空屋院子里意欲展翅的石雕鸟,可视为“拧发条鸟”的化身。这一切都指向了那口枯井——寻求答案的唯一入口。
除了妻子久美子外,冈田亨周遭出现了多名特立独行的女性,他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她们的人生。福嶋亮大(2010)称冈田亨身边这些谜一般的女性为“宿命的女性”,认为“在她们的入侵下,主人公失去了固有的明确的轮廓,最终不得不面对外界的暴力记忆”,“这些宿命的女性不仅将主人公从内部带到外界,又让他从外界回归内部。主人公的犬儒主义由于她们的入侵而被打破,他的唯一的存在场所只能是她们所在的空间了”。 在此,这些女性可视为冈田亨深入观照自我的“他者”,是他人际关系中必须加以认知、区分、同化的对象。
女性他者与自性实现
荣格(2018a:20-50)在《作为心理关系的婚姻》一文中写道,每个男子心中皆存有一个不灭的女子形象,这一形象是无意识的,是人类生命机体原初起源的遗传因子,可谓女性所有祖传经历的烙印或原型——阿尼玛,这一形象往往无意识地被投射在所爱的人身上,是强烈吸引或者厌恶之情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原型体现在女性身上则是阿尼姆斯。阿尼玛具有情欲和情绪化的性质,阿尼姆斯则本性理智(荣格,2018c:192-193)。阿尼玛原型使男性无意识地将女性理想化,一旦这一幻想在现实中遭遇挫折,便会造成男性的心理危机。区分、整合阿尼玛原型能促使男性内部成长和转换,走向个性化/自性实现。
以下着重以久美子、笠原May和加纳克里他这三位女性对冈田亨的个性化过程带来的影响,来阐释主人公迈向个性化的过程。
(一)阿尼玛的投射——久美子
久美子是冈田亨决意改变此前与社会及他者疏离关系的契机。在初识久美子并与之相处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不曾有过的息息相通之感——“就像两个微小的光点在无边的黑暗中并排行进时对方都不由自主渐渐靠向一起那样的感觉”(村上春树,2014:253);两人的相知打开了彼此紧闭的心扉——“我因之得以逐渐理解她眼睛捕捉到的世界的姿影,并得以向她慢慢讲述自己眼中世界的样态”(村上春树,2014:257)。在了解了久美子曲折的身世后,冈田亨决心要守护她不再受到伤害;而婚后两人合力构筑的“我们的家”更成了彼此精神的归依。久美子可视为冈田亨无意识中阿尼玛的投射,通过与久美子结合,他得以确立全新的自我认同。
久美子自幼在外婆的抚养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即将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忽然要将她接回,这导致外婆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一边对久美子百般疼爱,另一边又出于愤恨而暴力相向;幼小的久美子由于强烈的恐惧和不安,以解离的心理防御机制维系精神的正常秩序,关于那段时间的记忆完全失去了(布莱克曼,2011:41)。回到父母陌生的家中,久美子孤立无援,唯有温柔善良的姐姐成了她的慰藉。然而不久,姐姐因意外而死,她再次陷入悲伤与孤立之中。尤其是在她发现哥哥绵谷升对姐姐扭曲的爱恋之后,她对所谓“家人”的厌恶与恐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急于摆脱这个虚伪、冷漠的家庭。
由于从童年时代起经受的来自家人的冷漠和背叛,久美子对人性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父亲的残酷无情、母亲的虚荣、哥哥的阴暗狡诈,都令她对有着同样血脉的自己感到厌恶,无法产生积极的自我认同,同时也以冷漠的“人格面具”武装自己。与冈田亨相爱使她获得了与宿命抗争的勇气,平静的婚姻生活使她暂时忘却了过往的不幸。然而当她意外怀孕,这种宿命式的恐惧再次袭来,她对家族血统的恐惧导致她选择瞒着冈田亨堕胎,而剥夺一条无辜的生命又加深了她的罪孽感,内心的“阴影”开始蚕食久美子的自我,将其一步步拖入黑暗之中;加之绵谷升的推波助澜,久美子最终陷入了崩溃状态。然而她内心仍然渴望救赎,通过化身为“电话女郎”,向冈田亨发出不易分辨的求救信号。
冈田亨对两人共同经营的婚姻家庭感到自足,因此,久美子的离去使他陷入了自我认同危机之中。久美子是冈田亨尝试去理解、接纳的最亲密的“他者”,通过追寻消失的久美子,他得以深入观照自身个体无意识中的阴影及阿尼玛,进而逐步重建自我认同。
冈田亨下到枯井中苦苦思索,回溯并确认自己与久美子结成的纽带,这一纽带形成于共同对抗绵谷升一家的过程。两人婚后生活中唯一的裂痕是妻子瞒着自己堕胎——久美子对两人爱情结晶的扼杀,既是出于对自身的否定,也是对婚姻家庭的不信任,这使冈田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他选择了压制自身的悲伤和愤怒,延续表面风平浪静的婚姻生活。这一被压抑的情绪投射到了他在出差地的一家小酒馆偶遇的一名歌手“吉他男子”身上,作为余兴表演,男子用蜡烛烧手心向观众演绎“痛苦的共感力”,那种痛苦的感受与“流产手术”引发的创伤莫名地纠合到一起。以至三年后在东京街头无意间见到这名歌手时,冈田亨忍不住尾随他,同时感受到一种无从化解的“带有悲凉意味的愤怒”,最终演变成为用棒球棍痛殴“吉他男子”的暴力事件。这一偶然事件使他觉察到自身的暴力性——源自对抗以绵谷升为代表的暴力性的冲动,这无形中又与本田伍长、间宫中尉、肉豆蔻的祖父等人对抗历史的暴力遥相呼应,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暴力的漩涡。他放弃了随加纳克里他远走克里特岛的计划,决意正面迎战将自己及所爱之人的人生推入深渊的暴力性。基于一种近似于命运共同体的连带感,冈田亨将久美子内心的阴影同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夺回久美子同时也是冈田亨与自身阴影对峙、整合自我的必经之路。
(二)阴影的投射——笠原May
对于冈田亨而言,十六岁的少女笠原May无疑是个奇特的“他者”。笠原微微跛足,用硕大的太阳镜掩盖眼角的疤痕,浑身上下洋溢着与年龄不相符的不羁与豁达,将自身严严地隐藏在“人格面具”之中。她谈及“雨蛙一般枯燥无味”的父母和在假发公司兼职时充满幽默感的言论,让人觉得她是个玩世不恭的女孩。在最初与冈田亨谈及的话题(六根手指和四个乳房)中,透露出她渴望了解世人对“不同寻常”的态度,由此可窥见她深知自己的“不同寻常”,渴望得到理解。在逐渐熟识以后,笠原对冈田亨坦言自己内心中有一坨“烂泥”,有着强烈的“摧毁的欲望”,希望能切开“死亡的内核”一探究竟。其实青春期的反抗、破坏欲望并非不同寻常,然而她却得不到包括父母在内周围所有人的理解和引导。在因恶作剧失手造成男友的死亡之后,笠原堕入了自我否定的“阴影”之中。她心怀内疚却无法寻求原谅,在她身上出现了复杂交错的多种心理防御,她最终选择放弃校园生活,去到偏远的假发工厂,用纯粹的手工劳动来磨炼自己,通过自我退行寻求内心的救赎(布莱克曼,2011:85)。
笠原的言行举止时常令冈田亨困惑不已:在初次见面时就涉及畸形、死亡等奇妙的话题;在冈田亨面前表现出毫无防备、亲昵的态度;当冈田亨待在枯井底沉思的时候偷偷撤走绳梯令其身陷险境……笠原如林中精灵般不可捉摸、善良却喜欢恶作剧的种种性情丰富了冈田亨对女性的认知。另一方面,在笠原身上,冈田亨看到了久美子的身影,其错手害死男友之后的悔恨及自我否定、一蹶不振,与久美子选择堕胎后的心理变化极其相似。从某种意义上看,笠原是冈田亨无意识中的阴影的投射,他将自己对久美子情感移情于她,以同情、包容的姿态接纳了她内心中“烂泥似的东西”,正如他决意全盘接纳久美子内心的阴影一样。
笠原在山区工厂劳动时曾给冈田亨写过七封信,从中能读出其心理转变的过程:1.在深山中的假发工厂默默劳作,感受体力劳动带来的单纯的满足感,体验到一种普遍的人际联系。将自己投射到普通的女孩身上(遥远的东南亚国家蓄着长发的女孩们、在工厂中劳作同时幻想着结婚及新生活的女孩们),逐渐靠近了“本来的自己”。2.对冰封湖面上的“鸭子人”的描写,体现了她对内心“烂泥/阴影”的超越,象征着与自己和解、迎来内心平静的渴望。3.赤裸地跪立于月光之下泪流满面,以忏悔的姿态省视内心,认同内心的阴影。
冈田亨通过“倾听”,间接地“参与”了笠原的人生;在他的“参与”和启发下,笠原得以从内部打破壁垒,逐渐实现了对消极心理内容和积极心理内容的同化,重建自我认同。笠原处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界线还没有完全固定,所以格外敏感”(川上未映子,2019:169)的阶段,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想要摧毁一切的欲望”,这可视为一种消极的情感被深度压抑之后逐渐堆积、转化为内在暴力性的一种表现,笠原的自我还不足够强大,未能疏导这一内在暴力性,导致其向外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男友的死亡),自己也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通过对笠原这一他者的观照,冈田亨意识到了“暴力”的双向性,必须树立一个强大的自我以对抗来自外界及自身内部的暴力性;同时,通过对笠原的间接“救助”,冈田亨意识到自己的信任和包容起到了消解暴力性的疗愈作用,更坚定了寻回久美子的决心,最终得以辨识出久美子的求救信号。
(三)引领者——加纳克里他
川上未映子(2019:173)评价到,村上春树的很多作品常常将女性这一存在视为巫女性质的,让女性承担巫女式的职责;女性描写大多作为男主人公异化的入口或契机。从这层意义上看,女性他者可视为引领主人公进入潜意识界、逼视自我的重要契机。在这部作品中,加纳克里他对于冈田亨而言正是这样一名“引领者”的角色。
加纳克里他由于天生特殊的生理机制,长年忍受各种各样“肉体上的痛”,在二十岁时,她由于不堪忍受而开车自杀,然而自杀未遂却意外地使她失去了一切疼痛感。为了还债,加纳克里他当了妓女并被迫加入了卖淫团伙。本来在性方面没有任何感觉的她,在一次接客(绵谷升)过程中遭到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非现实意义上的“强奸”,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在从事灵媒工作的姐姐加纳马耳他的帮助下,加纳克里他成了一名“意识娼妇”。
初遇加纳克里他时,冈田亨惊讶于其独特的装扮(六十年代风格的装束、妆容以及红塑料帽),对她作为“意识娼妇”的身份也困惑不已。在梦中、在异界的“208房间”(作为久美子的替身),冈田亨多次与加纳克里他交合。他无法理解这种带有“巫术”色彩的交合的意义所在,但意识到加纳克里他这一异质性他者将自己与现实中及历史中的某种“暴力”连接到了一起,其暴力的根源指向了妻兄绵谷升。加纳克里他的他者性还体现在引导冈田亨重新审视与妻子的关系,进而重建自我认同的作用上。妻子久美子在性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然而在其要求分手的信中却提到自己无法遏制地陷入性饥渴中,通过和不同男人的交媾来填补内心的空虚。这一告白令冈田亨感到屈辱、愤怒的同时,对苦心经营的夫妻关系的意义以及自我存在的价值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与加纳克里他的交往促使冈田亨正视久美子面临的痛苦与困惑,将目光投向导致其沦落的暴力性外因,并为之挺身而战。
由此可见,加纳克里他对冈田亨而言是双重意义上的他者,其一,连接现实与历史、意识与潜意识的媒介,引导冈田亨透过种种表面意象深入暴力的核心;其二,从克里他的经历以及以性为媒介传达的信息的启示下,冈田亨得以重新审视与妻子的关系,对久美子的性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剧烈的内心冲突逐渐采取了接纳、包容的态度。
如前所述,个性化是一个把包括阴影、人格面具、阿尼玛/阿尼姆斯等精神的各种非自我方面加以认知、区分和整合,使之成为一个心理上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过程。冈田亨将无意识中的阿尼玛投射到妻子久美子身上,在遭遇背叛、离弃之后,该如何克服心理危机,使消极心理内容(阴影)与积极心理内容同化,则是他面临的最大的难关。通过回溯与久美子之间的纽带关系,接纳笠原May的“阴影”,并在加纳马耳他的“引领”下,他逐渐走出自我边缘化的状态,正面迎战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中“恶”的代表绵谷升。《奇鸟行状录》分为贼喜鹊篇、预言鸟篇及捕鸟人篇三部,前两部可视为冈田亨遭遇磨难并竭力克服心理危机的过程,对应于认知、区分各种无意识原型的过程;到了第三部,通过主动迎战邪恶,在各种力量及意象的帮助下,冈田亨以较强大的“意识自我”不断同化“自性”中的各方面,逐渐形成了平衡和统一的人格,亦即个性化。
结 语
本文以《奇鸟行状录》主人公冈田亨遭遇婚姻挫折后的自我认同危机以及其对人际关系中他者态度的转变为着眼点,结合荣格的无意识原型和个性化理论,分析主人公如何通过对女性他者的观照,摆脱现实中及精神上的危机、重建自我认同的过程。主人公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形形色色的人的人生,在此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普遍联系的暴力性世界,自己与妻子久美子所面临的危机仅仅是庞大的暴力性机制中的一环。在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中,久美子、笠原May和加纳马耳他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他者”,是主人公无意识中阿尼玛的投射对象。他在“猫”“本田老人”“拧发条鸟”的指引下,通过“枯井”这一神秘入口,直面自身的阴影;通过打破疏离化的人格面具,整合阿尼玛原型促成自身内部的成长和转化,走向自性实现。
纵观村上春树自《奇鸟行状录》以来的作品,尽管主人公置身的环境各异,所面临的困境林林总总,但最终总能归结到主人公经过艰苦的自性探索,迈向自性实现这一主题。在这一过程中,人际关系遭遇危机,尤其是与亲密对象(妻子、挚友)间关系产生裂痕的情节占了很大的比重。例如《奇鸟行状录》中冈田亨与久美子的婚变、《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及他的巡礼之年》中多崎作遭受的多次“背叛”、《刺杀骑士团长》中妻子的外遇等等,无不给主人公的精神、心理带来巨大的创伤。而真正的故事则始于背负着如此创伤的主人公是如何重新找回精神上的安宁,如何通过艰难探索走向自性实现的过程。村上春树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在于,他始终着眼于人的精神危机,致力于探究人的自性实现及精神救赎;用幻想模式的创作素材,通过纵横交错的“历史”叙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难以用理性阐释却符合深层心理逻辑的人类心灵的共同体验。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