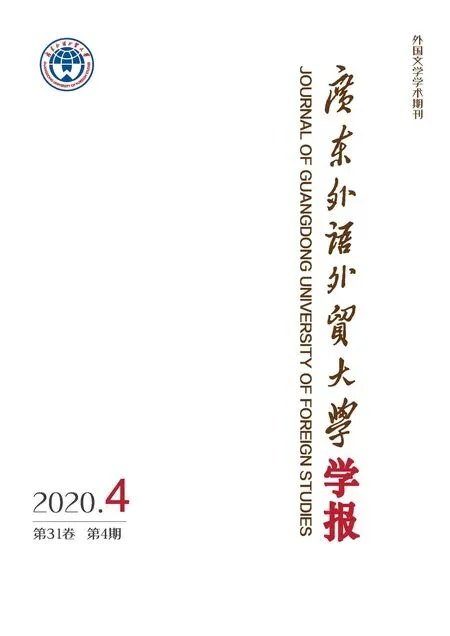论布伦嘉伯小说《鸦片战争》的神化书写
张秋
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作为文学母题对德语文学产生影响的历史由来已久,卫茂平在其所著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中,详细梳理了自骑士文学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德文学关系。文学作为反映社会进程的一面镜子,德语小说中的中国书写实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德语作家对中学西传过程中,中国知识的文学加工和再思考。
自二十世纪上半叶起,德语文学中对中国知识的加工兴趣不减,名著纷呈。一九一六年,阿尔弗里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发表了被誉为“第一部表现主义小说”的《王伦三跳》(DiedreiSprüngedesWang-lun),该小说是以中国清朝真实存在的人物王伦以及白莲教起义的历史事件为文学底本。自此,德语文学对中国知识的加工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儒、道哲学的译本。作为新的起点,“德布林将中国哲学从学术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Schuster, 1977: 168)。就在次年,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创作了题为《万里长城建造时》(BeimBauderChinesischenMauer)这一堪称中国书写中的珠玉篇什。与《王伦三跳》关注中国哲学的立场不同,卡夫卡的中国书写借由“长城”这个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对“西方文化中流行的‘中国神话’”进行释读与解构(周宁,2002:94)。
第三帝国时期,德语作家聚焦中国哲学、历史的兴趣依然不减。流亡中的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创作了多部戏剧和诗歌,融合了作者对庄子、孔孟、墨子哲学思想以及对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理解,表达了作者的社会批判立场。同一时期的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则创作了以中国为虚拟场景的小说《彬,北京之行》(BinoderDieReisenachPeking)。与布莱希特的重心不同,在《彬,北京之行》中,中国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不仅是主人公口中的“梦中的古老国度”(Frisch, 1964: 75),而且是主人公寻找自我、探索内心和追寻归途的起点。北京则成为无法实现和难以企及的象征。
从上述概览中不难发现,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作家对于中国知识的接受情况可能截然不同,其大致可以视为两类:中国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但文本本身书写的并非中国故事;而另一类文本的作者则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兴趣,创作了赋有典型中国哲学色彩的小说。
有论者认为,“直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仍不涉及个体,因为在这之前,中国更多是被作为一个集体或群体来对待”(Zhu, 2015: 55)。此时,中国只是德语文学中代表陌异性的“象征(Metapher)”(Lange, 1986: 341),而破冰的情况出现在一九七八年。然而,这样的观点却值得质疑。中国人作为个体出现在德语文学中的情形应远早于一九七八年。如果我们的目光不局限于上述被广泛研究的作家和作品,则会发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语文学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中国小说尚未受到中外研究界的足够重视,对这些文本的研究将改写学界得出的固有结论。
本文所聚焦的奥地利作家鲁道尔夫·布伦嘉伯于一九三九年发表的历史小说《鸦片战争》(Opiumkrieg)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文本。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春林(Tschun-lin)便是以个体的身份出现:他既是虎门销烟的主导官员,也是践行改革思想的实践先驱。作者对春林个体性的塑造,使其不同于以往德语文学中儒、道思想信仰者的固有形象,而成为事件中独立的个体。本文拟对这部在中德文学关系领域中被长期忽视的小说作深入的文本细读,以文本中的孔子与吕洞宾的神化对立形象为切入点,详细稽考文本中的中国知识来源。通过梳理孔子与吕洞宾形象在中学西传中的嬗变,管窥布伦嘉伯对中国知识的思考和改写以及其独特的文学书写立场。
《鸦片战争》:一部被忽视的中国小说
在近二十年的德语文学研究中,布伦嘉伯的历史小说《鸦片战争》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布伦嘉伯最富盛名的作品是于一九三三年发表的《卡尔与二十世纪》(KarlunddaszwanzigsteJahrhundert),该小说具有鲜明的“新客观主义风格”(Hughes, 2009: 206)。而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往往仅是在论述《卡尔与二十世纪》时顺带提及,作为对作家创作情况的补充一笔带过。
《鸦片战争》一书延续了作家写实和具象性的行文风格,布伦嘉伯在扉页上赫然标示:“该小说中的事件进程、日期、统计数据以及所引用的文件内容皆遵循历史”(Brunngraber, 1939)。小说以一八一六年,即嘉庆二十一年的中国广东为切入点,描写了主人公春林的一生。春林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如小说结尾处咸丰皇帝的太子所言,“您(春林)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Brunngraber, 1939: 326)。布伦嘉伯用细腻的笔调再现了嘉庆到咸丰皇帝统治期间的清朝。其语言详实,无论是对当时的街景、饮食、服饰、习俗,还是对官员、科举制度以及史实的描写都非常真实。具象性的写作风格不仅使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说的可信度,便于德国读者迅速进入到“大清帝国”这个陌生的场景中去。此外,小说的具象性也透露出了作者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作者对鸦片战争这个历史事件做了严肃的思考,使小说成为作者思想的载体。通过对中国知识的接受与改写,布伦嘉伯恰如其分地将历史和虚构融合在一起,书写了一部具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中国小说。
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这部小说曾经历了被禁、解禁、再度被禁和解禁的曲折历史。在发表当年该小说就再版了五次,随后的二三十年间又多次得以再版。二十世纪不同年代的评论家对其解读截然不同:由于布伦嘉伯在小说中表现出对英国的敌对态度,同纳粹德国的政策一致,因此在发表初期被纳粹视为“宣传手段之一”(Freundlich, 1995: 16-19)。然而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中,意识形态评判家更倾向于不将布伦嘉伯与纳粹宣传混为一谈,因为不能仅凭布伦嘉伯对英国的敌对态度,就将其与纳粹政权联系在一起。
更值得注意的是,布伦嘉伯在《鸦片战争》中,对中国古代神话人物进行了丰富的阐释,这是在其他以德语书写的中国小说中,不曾重点关注过的对象。布伦嘉伯对神话人物的摹写凸显了一个新的维度,即历史人物的神化。作者树立了经过神化的孔子与吕洞宾之间的对立形象,并对道教祖师吕洞宾进行特殊的艺术加工,展示了中学西传过程中,中国知识的嬗变,且透露出作者对西传中学的思考与其真实的社会政治立场。
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神化
布伦嘉伯在小说中对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作了丰富的阐释。从“广义神话”(袁珂,1996:68-76)的概念来看,这些人物既包括仅存于传说中的上古神话人物,即狭义神话人物,也包括经过神话化的真实历史人物。
布伦嘉伯在小说中提及仅存于神话传说的上古神仙伏羲和盘古。此外,多次写到观音,称其为“女神(Göttin)”(Brunngraber, 1939: 42-57),并描写了观音的救世形象。作者对观音性别的认知与佛教典籍有较大差异。在佛教典籍中观音具有随类应化的本领,可以化现为三十二种不同的身份。但大多数是以男性身份出现,《华严经》便称其为:“勇猛丈夫观自在”。但在唐朝之后,观音的形象的确因妙善公主的传说逐渐趋于女性化。这一点在西方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中有所体现,郭实腊(Karl Gützlaff)在其著作《开放的中国》(ChinaOpened)中就把观音描述为“慈悲女神”(Gutzlaff, 1838: 198)。同时,郭实腊也对观音救苦救难的形象进行了转写:“观音……,救护之神,在佛教众神中占据非常高的地位”(Gutzlaff, 1838: 220)。郭实腊著有大量介绍中国的著作,并在欧洲广为流传,《鸦片战争》中甚至提到了“郭实腊”其名(Brunngraber, 1939: 316)。因此,作者极有可能是从郭实腊的著作中获得了关于观音的信息。
除了上述几位神话人物,布伦嘉伯主要描绘了两位经过神化的历史人物,即孔子和吕洞宾。历史人物的神化一般被认为是“原始神话时代结束以后,奴隶制社会的人们在神秘宗教观念的支配下,对于始祖和其它为家族(民族)事业发展有特殊贡献人物的神化而形成神话故事的过程”(赵沛霖,1991:119)。神化一词在德语语境中也有类似的含义,指的是“将人拔高到神或者半神的地位”(Boak, 1916: 293)。在这个过程中,人具有了神性,其事迹也变得非凡,从而出现了人格神化的现象。
在《鸦片战争》的第一节中,作者就明确指出了孔子神化的情况:“……春林踏入了供奉礼教之父的大殿。……这里没有那位被神化了的人的画像,只有一块名牌,环绕四周的是161位智者、尊者以及孔子弟子的牌位”(Brunngraber, 1939: 16)。
布伦嘉伯的创作应当受到了当时汉学家和汉学热潮的影响,他将孔子定位为“被神化了的人”(Vergöttlichte[r]),其来源可从西方译者对孔子“头衔”的翻译中寻找到蛛丝马迹。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在其德译本中称孔子为“智者(der Weise)”(Schott, 1826),而英译本中则多称为“中国哲学家(Chinese Philosopher)”(Giles, 1898)、“圣人(The Sage)”(Macgowan, 1889; Smith, 1900)或“孔夫子(Confucius)”(Legge, 1861; Legge, 1877; Smith, 1900)。德国学者裴德思(Thorsten Pattberg)在其著作《神圣的孔子》(HolyConfucius!)中,对孔子头衔在德、英译本里的翻译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从其研究结果来看,自硕特一八二六年的译本到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所译的《论语》问世前,十七部译作中有十部将孔子的头衔译作“圣人”(Pattberg, 2011: 31-42)。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如此翻译并无不妥。而对于圣人一词的理解,不同的译者也有不同的洞见。
但在这些译作中,只有卫礼贤在其一九一○和一九一四年的译本中将“圣和圣人”与“神和神的”(Pattberg, 2011: 42)联系在了一起。卫礼贤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对中国思想在德国的传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他一九一四年翻译出版的《论语》中,卫礼贤直接称圣人为神,或将圣人描述为“通过启发成为具有神圣权威和心智力量的神”(Wilhelm, 1914: 60),明显具有人格神化的含义。卫礼贤的翻译与小说中布伦嘉伯对孔子“被神化了的人”的描述不谋而合。在其他汉学家的译本中均未出现圣人与神的对应关系。由此可见,卫礼贤的译本应当影响了布伦嘉伯的创作。
其次,从广义的视角来看,历史人物的神化也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思想的认知有关。奥地利学者科林·罗斯(Colin Ross)在其研究著作《新亚洲》(DasNeueAsien)中,曾论述人的神话化问题。罗斯认为,“在遥远的东方,此岸与彼岸并不是两个完全割裂的世界。它们更多是相互交错的,人们也可以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世界之中。……普通人在死后可以被神化,并作为神圣的死者对活着的人产生影响”(Ross, 1940: 38-39)。从罗斯的观点中可见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生死观以及人格神化的理解。由于生死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明晰,一些特定历史人物可以同时作为人和神而存在,他们被后人供奉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孔子在中国本土尚经历了“圣化”和“神化”的过程。可见孔子的神化倾向随着儒家经典的德译传入德国,并在德语文学创作中得以再现。
孔子与吕洞宾:神化人物的对立
(一)孔子:文人志士的侧写
在《鸦片战争》中,孔子与主人公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学识层面。春林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熟知孔子之言。他志在入京为官,最终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这都是清朝文人志士的理想化侧写。春林从小接受的孔子形象就是经文人志士神化之后的孔子,孔子不仅被称为至圣先师,还成为参拜的对象,赶考的学子都希望能受孔子保佑,一举中榜。
布伦嘉伯笔下的春林形象一方面符合当时清朝的真实情形,同时也引入了典型的西方元素。春林既是熟读孔孟之书而走上科举之路的十六岁年轻人,又是一个富有现代反思精神的改革先驱。小说中,春林曾与他乳母的女儿荷似经历了一场悲剧性的爱恋,春林曾对她说:
……如此一来我父亲更容易给我安排一门门第相当的婚事。我们民族所想的也非完全正确。你可能觉得我同你在一起,是违背了我父亲的意图。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孔夫子说过,孝顺父亲是第一位的,但这不是说为了父亲的生意,而是要传宗接代。你也可以为我家传宗接代,为什么你生的孩子就不如知府女儿生的孩子珍贵呢?这总让我想到蛮夷说的话,婚姻中尤其是对孩子而言,最可贵的就是父母之间的爱。(Brunngraber, 1939: 64)
从春林的话中可知,由于所受的儒家教育,春林愿意孝顺父母,遵循父父子子之道。小说中,布伦嘉伯巧妙安排春林在科考中阐释“康熙《圣谕十六条》(SechzehnguteRegelndesweisenKaisersKang-hi)”(Brunngraber, 1939: 44)的情节设置并非偶然。“敦孝弟以重人伦”是《圣谕十六条》的第一条,它“将以往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孝’放在第一位”(高薇,2019:107),以教化百姓。春林对孝道的认可,是作者对儒家文人志士的理解与描写。但更重要的是,春林具有一定的反思精神,尤其对金钱联姻和门第观念心存质疑。春林的思想相当先锋,他认为婚姻中最重要的是爱情,而非门当户对。这一点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仍具有一定的批判力度。春林不排斥西方先进观念的输入,是一个思想开化的儒家学士。在布伦嘉伯笔下,一个传统与现代思想交织的立体人物跃然纸上。
(二)吕洞宾:实践精神的来源
然而,春林身上的反叛精神和批判性思想不再属于孔子。从小说一开始,春林身上就隐隐体现出现代性的抗争思想,并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通过离家出走达到高潮。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春林离家的行为经过了深思熟虑。这次出走丰富了春林的实践经历,让他挣破封建家庭的桎梏,最终成就其历史性功勋。
值得注意的是,在春林离家时留下的书信中,出现了一位推动他从文人学者到改革先驱这一重要转变的关键性人物,也是德语文学中十分罕见的道教形象——吕洞宾。布伦嘉伯在书中给予吕洞宾很高的评价:“我(春林)不畏惧陌生与远方,因为在我看来这充满了希望,我深信,在永垂不朽的吕洞宾的注视下,我将周游四方,我不仅要成为一位思想家,更要以实践家安身立命”(Brunngraber, 1939: 67)。
春林从孔子那里汲取知识,却从吕洞宾身上获得实践精神。布伦嘉伯不仅直接称吕洞宾为“神(Gott)”(Brunngraber, 1939: 43),还将其与实践家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形象加工与我们平日对吕洞宾的认知有较大的分歧。在中文语境中,吕洞宾通常与谚语“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联系在一起。他既是道教全真派祖师,也是八仙中的一位。宋徽宗尤为推崇吕洞宾,在宣和元年封其为妙通真人。因此,吕洞宾的神化不仅是民间信仰,也有官方的参与。
一方面,吕洞宾同孔子一样,既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神化的对象。这一点在布伦嘉伯塑造的吕洞宾形象里有所体现。但另一方面,吕洞宾作为实践家的记载在德译典籍中却无据可查,作者对吕洞宾的塑造实则展示了他对中国知识文学性的转写:
春林拘谨地走到八仙之首吕洞宾的塑像前。吕洞宾不仅以创作名言警句而著称,同时还是官阶很高的统帅,……简而言之,这是一位孔武有力的男人,用他骑士的双腿脚踏实地……。春林担心自己未来只能成为一位清醒的思想家,而不是真正的实践家,这样的忧虑让他在吕洞宾的神像前鞠了一躬。事实上,春林在这里只许了一个愿望:他希望自己不仅懂得思考,而且能付诸实际行动。(Brunngraber, 1939: 43)
从这里可以看出,春林的志趣从一开始就与孔孟之道不同,其效仿的榜样是作为实践家的统帅吕洞宾。在作者笔下,吕洞宾地位崇高,不仅有超过孔子的势头,而且成为与孔子思想家形象所相对立的实践家。
在神明吕洞宾的驱动之下,春林希望增长见识,“他分别在商船和战舰上漂泊了两年”(Brunngraber, 1939: 168)。“他的思想确实变得成熟起来,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健全的世界观了”(Brunngraber, 1939: 168)。春林游历大江南北,看遍世间百态,这些宝贵的经历“全部汇入他的心灵,使其变得更加深刻,如此一来他以一种新的、谨慎而渊博的成熟姿态重新回到书本之上……”(Brunngraber, 1939: 169-170)。在外漂泊两年之后,春林参加了会试并高中榜首,成为刑部的七品官员。自此,春林开始了仕途,终于有机会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预示了春林不再只是一位精神富有的学士,还能为危机四伏的国家出征打仗。小说中,春林多次向皇帝进言,并指出走私鸦片的国民只看重眼前利益,对禁烟令视而不见的官员更是欺上瞒下、中饱私囊。此外,春林还敏锐地察觉到英国人走私鸦片的政治目的。最终,他在三十四岁时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作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
从春林的实践经历来看,布伦嘉伯对吕洞宾形象的化用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吕洞宾并非像老庄一样是道家中最正统、经典的人物,德语著作也较少关注吕洞宾其人。吕洞宾广为流传的形象是诗仙、酒仙和道教全真派祖师。其乃“神仙”这一认识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记》:“时人皆知吕洞宾为神仙”(李裴,2007:66)。卫礼贤在《金花的秘密》(TheSecretoftheGoldenFlower)中,也仅介绍了吕洞宾修道的形象(Wilhelm, 1931: 5-6)。其二,布伦嘉伯突显吕洞宾的实践家身份,在其他的德语中国小说或中国典籍的德译本中均无可查。因此,作者对吕洞宾的塑造不仅是他对中国知识的改写,而且赋予了春林和这部中国小说以新内涵:社会的改革并不能只停留在思想层面,朝堂上的口舌之争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处于存亡之秋的大清需要春林这样的人实践他的改革思想。春林践行的不仅是销烟这件事本身,更多的是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对时人只图眼前名利的痛心以及对改变等级社会、官员腐败和国家动荡现状的责任心。这一切的改革都需要实践,而布伦嘉伯将春林实践精神的来源安排在了吕洞宾身上。
孔子与吕洞宾,这两位分属于儒道两家的神化人物,从思想性和实践性上被对立起来,其中吕洞宾所代表的实践精神尤其受到推崇。如此的塑造大致有二:首先,这与布伦嘉伯的政治立场不无关系。作者出生于一个无产阶级的家庭,自青年时期就亲近社民党。他社会民主的立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创作的立场,社会需要民主的改革,等级制度应该遭到废除。因此,他笔下的春林具有同样的社会批判精神。春林驳斥权贵联姻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立志禁烟,并希望推动清朝重回繁荣。然而该小说发表于一九三九年,正值纳粹统治时期。亲近社会主义的作家无法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明言他的立场,选择“经典人物”作为春林效仿的榜样容易暴露作者真实的想法,从而遭禁。相反,陌生的“中国神仙”不容易暴露作者真实的意图。纵观中国典籍德译的情况,吕洞宾鲜少出现,只有卫礼贤在《金花的秘密》中,对明清扶乩托名吕祖所作的《太乙金华宗旨》做介绍时,提及吕洞宾(Wilhelm, 1931: 3-10)。因此可以说,布伦嘉伯站在他的政治立场上,借春林之手,假吕洞宾之精神,实则想要隐晦地表明他本人的世界观:社会充满暴力和不公,人与人的平等被摧毁。这样的社会需要改革,而改革不仅是口头之争,更需要实在的行为。
其次,布伦嘉伯对吕洞宾的化用也并非毫无根据,在中国的书写文本以及民间口传文本中,吕洞宾是书写神仙鬼怪之词的诗人。借助归属于吕祖名下的著述,可以管窥吕洞宾的面貌。吕洞宾是贴近于市井生活和劳苦大众的平民神仙,他深受下层人民喜爱,代表了世人皆平等的思想。吕洞宾的这一特点在其创作,或假托于其名下的诗词中均有所体现。虽然他的创作主要围绕修道炼丹,但他劝说时人修道时多讲方法,而非区分人的等级。吕洞宾的主旨意趣多在对世俗生活的批判,尤其是批判世人忙忙碌碌,只图眼前名利的行为。例如在《沁园春》(五)中,他写道:“多谋转使多愁,恰似吞他名利钩。看日前些子升沉事,把天机丧尽,不肯抽头。蜂为花忙,蛾因灯逝,只恁迷前忘后忧”(吕洞宾,1994)。从其所作的诗词来看,吕洞宾确实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精神。因此,也有论者认为,“吕洞宾词居《唐宋全词》所收神仙鬼怪词之首。其词是丹道理论的艺术宣传品,同时含有较为强烈的批判精神”(许兴宝,2002:29)。
吕洞宾这一具有社会批判思想的神仙形象,被布伦嘉伯化用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春林承载了吕洞宾的批判思想,对时人沉迷于鸦片和乐于从鸦片交易中获取利益的行为深表痛心,并下定决心即使为国捐躯也要清除鸦片。春林具有先见性和现代性的目光,他不仅看到英国文明和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指出鸦片交易背后的政治目的:地大物博的清朝成为“英国要发展商贸关系甚至是侵略扩张的重要对象”(李英全、齐远飞,2017:20)。然而,布伦嘉伯对吕洞宾的化用并没有止于春林的思想层面。春林敢于人先,在受到层层阻碍的禁烟运动中践行自己的先锋性思想。尤其是鸦片走私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时,禁烟不再是大快人心的事:“他(春林)的出现至少让三类人感到不安和反感——每一个吸食鸦片的人,每一个贩卖鸦片的人和每一个同谋的官员”(Brunngraber, 1939: 230)。
综上所述,作者借吕洞宾形象的化用以及对孔子和吕洞宾形象的对立塑造,在小说中构建了吕洞宾经神化后的实践家形象,并使之成为主人公春林效仿的对象,让春林用其一生来践行社会改革的思想。同时,作者也洞察到变革可能产生的后果。小说后半段春林的流放预示了改革需要牺牲。但在最后,布伦嘉伯安排咸丰皇帝的太子将流放的春林接回京城,并对春林三十五年前的改革决议表达了委婉的认可。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视为作者寄托于社会改革的希望。
无独有偶,约七十年后在汉学家玄英(Fabrizio Pregadio)主编的《道家百科全书》里,作者对吕洞宾的社会批判精神做了较详细的总结:“吕洞宾的名号被用以传达对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批判声音。那些有时藏于回文和属以其名的诗词出现在寺庙的墙上,书写着对官员不公和贪腐的谴责。宋徽宗时期,佛教徒遭受诋毁和迫害时,也借吕洞宾之名来传达他们的思想”(Pregadio, 2007: 713)。这番总结回应了布伦嘉伯在《鸦片战争》中赋予吕洞宾的社会批判精神。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众多以中国为主题的小说中,布伦嘉伯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在对中国历史人物的摹写中突显了一个新的维度:对历史人物的神化。孔子和吕洞宾,这两位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经过布伦嘉伯神化的处理,被赋予了高于人格的神格。布伦嘉伯对小说中涉及的“神”都有精准的定位,其丰富而详实的知识来源可经考证。从布伦嘉伯的用词和理解来看,汉学家郭实腊以及卫礼贤的译作对其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对郭实腊以及卫礼贤译作的接受之上,布伦嘉伯还对孔子和吕洞宾的形象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孔子作为思想家的代表,在小说中与社会批判实践家的代表吕洞宾形成了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对立关系集中体现在主人公春林的身上,他作为极具智慧的清朝学士,熟知孔孟之道,但又充满批判精神和实践意识。春林一边驳斥社会的迂腐之处,一边投身于社会改革之中。在他的身上,吕洞宾所代表的实践家精神占领上风。实际上也折射了作者的意图,即社会需要变革,变革需要实践,实践必定会有牺牲。但这个过程中,人却应该是平等的。
布伦嘉伯透过历史人物神化这个视角对鸦片战争和社会变革做了严肃思考。这部文学性与社会价值兼具的文学文本展示了中学西传过程中,中国知识被接受、改写以及在文学文本中再现的情形。历史小说《鸦片战争》是对中国历史事件严肃的文学思考和加工,其接受过程经历了从“支持纳粹”到“反法西斯”的复杂变化。而“历史人物神化”的阐释维度丰富了德语文学的中国书写。作为一部既具文学性又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小说文本,《鸦片战争》应引起学界新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