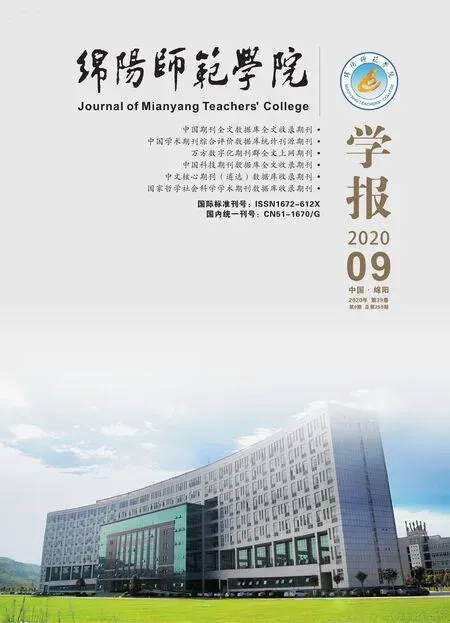再造“革命”:论《活着》中的采风者与苦难叙事
徐家贵,罗文军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长篇小说《活着》的“苦难”主题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正如余华所说:《活着》写的是“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1]3,这是一本再现苦难的小说。甚至,在自序中,他还讲到自己为了真实地再现福贵的苦难生活,将第三人称叙事改为第一人称。但颇有意味的是,文本所呈现的并非全然如此。余华声称改变人称是为了让福贵自己发声,但他却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双重叙事者的结构,即福贵不是第一叙事者,而是由一个第一人称的第三者“我”来间接地打开福贵的嘴。那么,为什么余华不让福贵自己开口讲话,反而要引入采风者“我”来替福贵发声呢?事实上,余华本人并没有意识到“采风者”的引入对文本造成的影响,既往研究多对此进行赞扬,将这一结构视为余华本人的形式创新,认为采风者“我”是余华的缩影,其功能是“这部小说的记录者”[2]116,或者“我”的引入是为了设置“一个充满历史悖论的历史环境”[3]128,形成反讽性的叙述效果。然而当立足于“采风者”来重新解读《活着》时,小说苦难叙事的“苦难剥离”被呈现出来,由此重现了9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以“文学”来实现“苦难”与“革命”的再造,进而深入到新时期知识分子、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采风者”的形象功能与错位
《活着》中采风者“我”的叙事功能被放大,而形象功能却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从“采风者”本身出发,不难发现采风者职能的颠倒和身份的错位,由此带来的是苦难叙事的苦难剥离。
中国“采风”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周天子“采诗”以观民风;至汉代,有了专门的采诗之官,“王者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4]40。之后,“采风”成为保存文化和艺术创造的重要形式。可见,“采风”这项活动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而作为采风活动的执行者,自然也兼具了这种属性。小说中的采风者“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是“收集民间歌谣”[1]2。显然,这里的“采风”仍然属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采风”,而“采风者”在中国传统意义上肩负着“搜集”、“记录”和“整理”的使命①。反观小说,文中的采风者“我”却颠倒了传统采风者的职能。采风者“我”看似是一个传声筒,只是忠实地“记录”福贵的苦难生活。但是小说中,这个记录者首先筛选了记录的主体,进而才开始记录和讲述。文中的采风者“我”对乡下的其他老人和其他的故事都不感兴趣,在发现福贵的乐观与特别后,进而才对福贵感到好奇,愿意听福贵讲故事。这里,“整理(筛选)”先于“记录”与“搜集”,采风者“我”在文章的开始,就主动选择了要讲谁,讲一个什么故事。福贵是被选择的对象,而不是他自己表达的结果,苦难的生活是被筛选之后的结果和满足采风者好奇心的故事。
从叙事者“我”的身份来看,首先他的职业是“采风者”;其次,在和福贵的对话中,他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城里人”;第三,追溯“采风者”的历史起源,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除了任命专门的采诗之官,在民间还有专业的采风者进行采风工作。到了近代,这类采风者的范围不断扩大,知识分子成为其主力军,比如“文化馆”和“群众艺术馆”的工作人员等②。由此可见,这个到乡间收集民谣的“城里人”的第三重身份,应当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奇怪的是,知识分子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肩负着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人,才能算作知识分子”[5]。而文中的“我”却表现出一个二流子的形象,“我”对自己及其职业的描述是一个“会讲荤故事会唱酸曲的人”[1]3和“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1]2。由此可见,采风者“我”的心理和身份之间存在严重的错位,而这种错位不仅仅表现在心理上,还表现在行为上。如小说中对采风者“我”的形象有这样一段描述:
头戴宽边草帽,脚上穿着拖鞋,一条毛巾挂在身后的皮带上,让它像尾巴似的拍打我的屁股。我整日张大嘴巴打着哈欠,散漫地走在田间小道上,我的拖鞋吧嗒吧嗒,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仿佛是车轮滚滚而过时的情景[1]3。
显然,这样一个“二流子”的穿着打扮和我们通常所讲的“城里人”“知识分子”根本不搭边。事实上,在福贵和“我”的对话里,福贵得出“我”是城里人的身份后,自己觉得很是“得意”,因为觉得别人看不出来,只有自己看出来了。可见,采风者“我”虽然是城里人,但在小说中表现的并不是一个城里人的形象。其次,采风者“我”明确说到自己在乡间所做的事情,如傍晚到农民屋前看看女人,和男人聊天;晚上走夜路时看男女偷情;和一个赏心悦目的农村女孩调情等,这些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知识分子会做的事情。
这里,采风者“我”从严肃的知识分子形象变成了一个二流子形象,自身的严肃性被消解,看似严肃的故事之下充满了反讽和滑稽,在采风者“我”自身严肃性被消解的过程中,福贵真实的苦难生活也变成了采风者口中的调侃故事。
二、“采风者”的叙事嵌套
由于采风者“我”的介入,福贵第一人称的苦难生活成为了这个第一人称第三者的回忆。也正因为如此,采风者“我”看起来可靠的故事,实际是一种不可靠叙事,《活着》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苦难再现,而是采风者“我”的苦难再造。其次,从余华本人来看,他对采风者“我”介入文本的理解也局限于叙事功能,而对文本内容所起到的作用缺乏清楚的认识,所以余华本人也需要成为我们审查的对象。由此,小说文本就形成了“福贵——四十多年后的福贵——十年之后的采风者——余华”三层嵌套的叙事结构。
第一层嵌套,即四十多年后的福贵讲述自己的一生。余华认为“时间的方式就是福贵活着的方式”[1]11,“现在”的时间只出现在一开始,福贵的“生活”被设定在“过去”(一个夏天的午后),“苦难”则设定在“过去的过去”(四十多年前)。这里,福贵“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6]29,福贵通过“回忆”将自己的苦难转化为生活,在过去的时间中福贵呈现出积极的状态,如福贵和采风者“我”相遇时,他“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十分生动”[1]6;“我”请福贵讲述自己,他“显示出喜悦之情”[1]127;而讲述到妻子被迫被接走和龙二被枪毙的时候,福贵居然“看着我嘿嘿笑了”[1]34。当时间回到“过去的过去”,福贵的生活却充满了颓败。小说开始,福贵输光了家产,他“脑袋里空空荡荡”,想“拿根裤带吊死算啦”[1]21;后来有庆死的时候,福贵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道,“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1]126。显然,“主体回忆的真实性是不可靠的”[7]308,通过“时间的宽窄”比较,福贵的感情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过去”的生活呈现出乐观,“过去的过去”的苦难呈现出颓败。福贵通过“回忆”将自己的苦难转化为生活,但正如余华所说,“生活是不真实的”[8]181,看似的真实不过是通过“写真实”的方式进行的再造。
在第二层嵌套中,余华引入了采风者“我”来讲述福贵的苦难,文本结构呈现出“中国套盒”的模式③,既往研究者则将其称为“双重叙事者”的叙事机制。然而,正是由于这一机制的设置,福贵的生活进一步转变为了采风者“我”的故事。小说开篇是一个夏天的午后,采风者“我”遇见了老年的福贵,听他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故事由此展开。“叙述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独裁的过程”[9]71,这里,采风者“我”实际是整个小说的控制者,掌握着小说的话语权,然后在每一次福贵的苦难到达高潮的时候骤然出现。表现在文本结构中,则是采风者“我”的故事与福贵的故事不断地交替出现,四次中断将小说分为五个部分,共同建构起了《活着》的故事框架。在故事框架中,采风者“我”将福贵的生活故事化。这个第一人称的第三者“我”看似解决了余华的写作困境,也间接地帮助了福贵发声。但是新的问题产生:福贵自己确实发声了,只是他讲的却不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采风者“我”口中的故事。很明显,这与余华的目的背道而驰。经过时间的拉开,我们发现人称的转变成为了一个幌子,这个第一人称的第三者“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余华的问题,福贵的“声音受到视角限制”[10]23,反而产生了新的遮蔽。小说给我们一种幻觉,使用第一人称“我”就代表了福贵自己在发声,但事实上福贵的生活不是“自述”,而是“他述”。
更进一步,从“采风者”到余华的第三层嵌套,则出现了质的变化,即口头故事变成了书面文字。口述历史是“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11]5,福贵的生活表现为声音故事,经过采风者“我”的口,仍然停留在声音之上。这种口述的方式是属于大众的,但是余华将声音转化为了小说文字,文字是精英阶级的④。实际上,采风者“我”的职责是将口述故事文字化、历史化,使故事以一种历史的方式呈现出来⑤,然而余华代替采风者“我”承担了这个职责。余华对素材(采风者的故事)进行整合、加工和转化,使言语变成了文字,将口述的故事书面化、经典化和小说化。《活着》是一本主题先行的小说,余华的创作表面是在为福贵发声,实质则是“作为规则、符号以及通用的措辞等融合而成为一篇特殊文本的一个‘空间’”⑥。所以,虽然余华想要记录福贵自己真实的生活,但是由于叙事的嵌套,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活却是虚构的小说。由此,福贵的话语从口述走向了文字。在这个过程中,小说以“代言”的方式完成了话语权的转移,即农民(福贵)的话语权彻底地转移到了知识分子(余华)的手上。而“代言的言说方式更多地立足于知识者社会价值的实现”[12]8,余华想真实地再现福贵的话语,但事实上这不过是在知识分子的语境中再造农民话语。
三、苦难叙事的“苦难剥离”
简言之,三层嵌套叙事构成了福贵开口说话的全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实质上是福贵从“自说”到“他说”的过程,背离了余华创作时人称转变的初衷,这种背离在小说中表现为苦难叙事的苦难剥离。
在第一层叙事嵌套之中,“回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不是重新制造过程中被动的反应,而是一个新的感知生产性的行为”[7]113。小说给我们一种想象的错觉,福贵的苦难生活是幸福的、满足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嵌套的感情线中,采风者有意让读者只关注表层的糖衣,而忽视里层的苦涩。四十多年后“乐观”的福贵,其实是采风者记忆之中的福贵。由于记忆产生的不稳定、损失和后知后觉,福贵的苦难在记忆中流失。其次,在时间的艺术里,本来“只有叙述者才知道全部故事”[13]114,但是由于时间的“宽”(四十多年)、“窄”(一个夏天的午后)使得单一的时间线被打破,让正在遭受苦难的福贵和讲述苦难的福贵穿越时空,同时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人们在“过去”的时间中了解福贵的生活,并建立起安全的心理预期,再带着“过去”的眼光回到“过去的过去”。所以福贵无论如何遭遇“苦难”,时间已经被剧透,苦难的撤退就这样潜伏在时间的“宽”“窄”之间,正如余华所说:“是时间的神奇让我完成了《活着》的叙述。”[1]11
而在第二层叙事嵌套之中,出现了两层故事,即年老的福贵讲自己的故事,十年之后的采风者讲自己与福贵的故事,而“讲”就“意味着事件的真实性在讲述中被消解”[14]19。在表层故事中,福贵的苦难生活是满足采风者“我”好奇心的故事;在里层故事中,福贵的苦难生活则处处充满了故事性的偶然,如福贵拿钱去给自己的母亲请大夫,偶然的好心导致的结果却是被国民党大兵抓壮丁。这类因偶然导致的苦难在小说中比比皆是,特别是死亡的偶然在重复的死亡中达到戏剧化的高潮,如县长的女人生孩子难产,却只有有庆的血型合适,最后有庆却因为输血过多而死,当县长找来的时候,福贵又惊讶地发现县长居然是当年的战友春生。实际上,底层的苦难不在于其苦难的连续性,而在于底层生态的脆弱性,一个偶然事件就可以轻易地改变福贵的命运,所以故事的嵌套将福贵的生活故事化,让他“活下去”。那么问题随之而来,余华为什么要将福贵的生活处理成“故事的故事”呢?既往研究一般将其作为叙事方式的创新,其实不然。在这里,作者进行了两次拉开,一次是生活与故事的拉开,另一次是故事与故事的拉开。这两次拉开使苦难变成生活,生活转变为故事,由此形成两个空间,即话语空间和故事空间⑦,十年之后的采风者“我”作为叙述者在话语层运作,而十年之前的采风者、年老的福贵和年轻的福贵则作为人物在故事层(包括里层故事和表层故事)运作。所有的苦难通过故事传递,故事又被话语再造。话语在传达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隐藏生活、扭曲生活,苦难在故事中自然地失真。
到第三层叙事嵌套,知识分子再造农民话语,福贵扮演着余华为他选定的角色,并在余华为他创造的苦难中展现高尚。然而,“文学就是这样,它讲述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作家没有意识到的”[1]6,福贵的苦难在自己重复的讲述中不断复现,又在不同人的讲述中被反复审视,由此构成复杂的话语权力网,“这些话语中的每一种又构成了各自的对象,并且对它进行了加工,直至将它彻底改观”[15]34。所以,余华在展现苦难的时候,同时也消解了苦难,有意的文本形式实验潜在地解构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总的来说,在三层叙事的嵌套和剥离中,第一层,福贵的苦难被自己解构,形成苦难主体的苦难剥离;第二层,采风者“我”将福贵的生活故事化,形成叙述主体的苦难剥离;第三层,知识分子(余华)再造农民(福贵)话语,形成创作主体的苦难剥离。三个主体分别“去苦难”之后,导致了“事物真实性的遮蔽和扭曲”[16]17,时间成为叙述的动力,苦难的现场与生活离间、生活与故事离间、故事与小说离间,三个时空重复地推进交织,话语的力度和真实性被不断消解,福贵的苦难成为加工洗练之后的小说读本。余华想要写出的是“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民表现出独立(而不是借助知识分子话语)的面对苦难的本色”[17]42,然而文本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却是一个温情脉脉的老人,是这个老人苦难剥离之后的生活。
四、知识分子与再造“革命”
通过“采风者”的再解读,不难发现余华通过知识分子再造农民话语,再造了福贵的苦难生活。这种想象性的“再造”,其实质是以知识分子话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而非文本表面的民间立场和平民立场。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与文本相反的现实生活,即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旁落。
“我国的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18]60,但是到90年代,学界却掀起了“告别革命”的思潮。事实上,“革命”的内涵⑧极其丰富,早期“革命”指的是“时间或空间上旋转循环运动”;14世纪时,“革命”逐渐具有了政治内涵,从“循环运动”演变为“政治叛乱、起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革命”具有了现代的内涵,即“恢复人原本(Original)就应有的权力”,同时包含“创建新秩序”和“颠覆旧秩序”的意义⑨。而到中国近代,毛泽东明确了“革命”的内涵,即“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19]17这一主张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直到90年代,李泽厚、刘再复率先提出“告别革命”的呼声,此时要告别的“革命”针对的是“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指的是“用群众性的暴力活动来破坏、打倒、推翻、摧毁现存的事物(包括人和物)、制度、程式等等”[18]288。余华在告别“革命”的时代书写苦难,刻意回避了传统创作里“革命”化的主题和人物,这本身是有意识的对“告别革命”的一种回应。这里,“革命”成为一种象征,“革命”与“政治”相连,文学表面的“去革命化”,其实质是“去政治化”。然而苦难叙事的苦难剥离则带来了新的矛盾,余华想要告别“革命”却无法真正地告别。前者是因为“采风者”的介入,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解构了苦难;后者则是因为余华再造“苦难”的同时再造了“革命”,这两组矛盾在显意识和潜意识两方面共同构成了作者复杂的内心世界,正如余华的自我警醒:“文学不是空中楼阁”[20],它与现实与时代密切相关。由此,延伸出以下两个问题:“再造苦难”与“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知识分子、文学与革命之间存在着一个怎样的互动?
首先,在战争年代,苦难生活与革命现实密切相关,二者是共生的关系,所以在再造“苦难”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 “再造”了“革命”。同时,由于底层的脆弱性,导致整个群体相比于其他群体,更多的被置于受害者的位置上。回到小说来看,在内容上,《活着》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极大,横跨了20年代到90年代。在叙事的嵌套和剥离中,不难发现苦难、战争和革命贯穿了福贵的一生,“革命”影响着福贵的命运,福贵一辈子经历了两次国共战争、三次土地改革、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所以与作为知识分子的余华不同,福贵作为社会的末端,他更多的是革命的受害者,被迫承受“革命”所造成的“苦难”,如国共战争时,福贵上街买药,却被抓了壮丁;而在形式上,福贵在被“代言”的过程中,重新获得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作为个人的“主体性”,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象,在“革命苦难”的话语里,苦难不再是“个人独立承担的自由意志中不能抽身不能遗忘的罪责”[21]40,而“被容纳于民族和国家的宏大叙事话语建构中”成为“集体记忆”[12]71。余华在潜意识中通过这种想象性的叙述为福贵代言,将中国近现代革命进程与福贵的苦难生活结合在一起,隐秘的革命和显性的苦难必然相伴而生,“苦难”的再造背后是“革命”的再造,这种再造的“苦难”使得“苦难”不再是高尚的理由,而“革命”成为了苦难的源头。
其次,90年代“告别革命”的实质,就是要“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而“再造革命”背后的诉求是知识分子的“再政治化”。仔细审查余华的创作观念,不难发现其观念有明显的转向,即从一开始的“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22]到人物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1]7。可见,余华在一开始是没有给人物说话的权利的,他试图将话语权给福贵,但看起来并没有成功。文本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阶级关系网和权力场,在这个权力场之中,底层无法发声,所以由知识分子代言,这种“代言”的方式实质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本身无法祛除,反而通过小说叙事(文学)的形式凸显出来,余华讲述的是一个底层人民受难的故事,“苦难”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革命”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代以来,“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23]11,并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知识分子在潜意识中通过再造“苦难”来再造“革命”,实际上是将底层受难的社会问题,转化为了文学创作中的“革命”问题,又以表面的“文学革命”再造遮蔽了现实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种遮蔽体现出的正是9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乏力,以及他们应对时代变迁时的复杂心理。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宣扬平民立场、人的文学,但多数仍持有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泽厚、刘再复等人;而在文革之后,他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也是“民众”的一份子,不再以启蒙者的姿态高居不下,而是自诩是民众的一份子。显而易见,造成这一心态转变的原因是60年代的“革命”,“革命”既给了知识分子极高的话语权,同时也在文革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伤痕。文革后,“苦难”成为“革命”的隐喻,“革命”成为“政治”的象征,知识分子想要摆脱“政治”的阴影,在现实中却无法摆脱。90年代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以余华的《活着》为例,通过“再造苦难”和“再造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
五、结语
简言之,“书写苦难”是余华的创作意图,告别“革命”(去政治化)是时代的重大议题,苦难的再造显现出无法告别“革命”的困境,这种复杂的关系在小说中以一种既呈现又解构,既解构又再造的状态,通过“文学政治”的结构呈现出来,形成一种“合目的的反目的性”。由此看来,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特别是《活着》中苦难叙事所展现出来的问题的转化,就此而言,我们确实还需要反复回到文学,回看历史。
注释:
① 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工作,在我国由来已久。民间文学的工作者在采风时,其原则与步骤是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其中,“整理”包括了筛选、分类和归纳等内容。参看钟敬文编:《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164页。
② 对采风者身份的考证主要分为官方和民间两条线,但是无论是官方和民间,段文识字是基本要求,而识字的人多是知识分子,如钟福民《采风对民间民族艺术的影响》和许英国《关于我国民间文学最早的收集活动:采风的探讨》之中,以文献的方式进行考证,最后得出采风者知识分子的身份。
③ 中国套盒模式,也称“嵌套叙事”“俄罗斯套娃”或“俄国玩偶”,这种结构往往会造成小说中的叙述分层,参看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4页。
④ 口述史是围绕人民建构起来的历史,这种模式不同于以往精英知识分子书写的历史,它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参看[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⑤ 对采风者的职能(包括历史职能和文化职能),参看钟敬文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164页。
⑥ 这种特殊的文本空间也可作为一个融合并记录盛行于特定文化时期文化观念、无序组合及权力结构的“场所”(“作者与作者身份”词条),参看[美]M.H.艾布拉姆斯、[美]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的《文学术语词典:第10版》,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⑦ “故事空间”指的是事件发生的场所和地点,“话语空间”指的是叙述行为发生的场所或环境。参看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⑧ 对“革命”内涵的多重解读,参看李怡:《多重“革命”内涵的重合与混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札记》,《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⑨ 对“革命”这个观念的的历史发展,参看“Revolution(革命、大变革、天体运动)”条目。[英]雷蒙·威廉斯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57-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