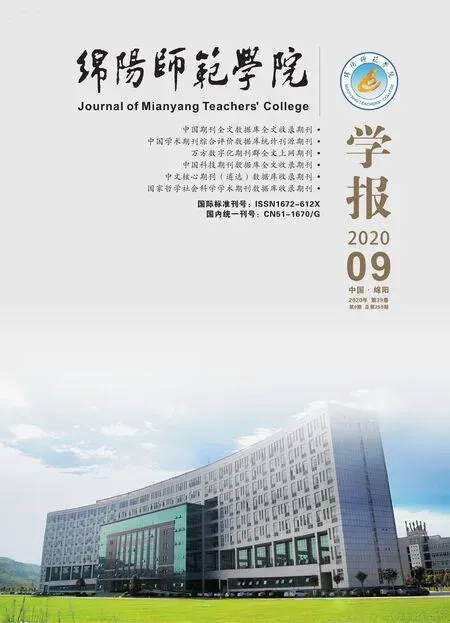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情感书写中的启蒙话语建构
鲍昭羽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23)
情感书写历来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占据着不容小觑的位置。从《西厢记》的书简传情到《红楼梦》的孽海情天,从《牡丹亭》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到《断鸿零雁记》的“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无一不显示出情感叙事在文学话语中的巨大力量。进入到现代文学的启蒙话语中,如何安放情感,变成人从未成年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关键。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成为通向自由与平等的必经之途。郁达夫在《沉沦》中对异性的呼喊,胡适于《终身大事》里与传统婚姻方式的决裂,都显现出“五四”一代常常将情感解放作为自身启蒙的先决条件。但问题在于,情感解放的复杂与艰辛不是一句口号式的宣言可以涵盖的。情感,作为一种人的本能体验,常常与欲望纠葛缠绕,形成难以挣脱的情欲漩涡;而理性,身为启蒙中的核心因素,会不会跟带有某些非理性特质的情感体验相冲突,也成为个体启蒙进程中的一大问题。回溯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或许可以厘清启蒙话语下个体情感无处安放的困境,还原那些被“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宏大口号所遮蔽的繁复与艰难。
一
意图解放个人情感的“五四”一代作家们率先扬起了批判封建传统的大纛,他们以揭露传统文化对人情感的压抑作为整个启蒙话语构建的起点。中国传统情感观念的最大问题在于将情与欲等同,故而常常在节制欲望的同时否定情感。《说文解字》中将“情”解释为“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字源上说明了古人对“情”的体认。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主张“礼以养情”[1]57,实则就是将情与欲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随着宋明理学的逐步发展,“情”干脆为“欲”所取代,成为儒家眼中不断膨胀的洪水猛兽,因而才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说法。殊不知,情与欲需要分而视之。欲即欲望,是人的本能反应与原始冲动,若不加节制确实可能衍生出贪念、执念、恶念;情感由欲望而生,却又超越欲望成为心之所向,本身即包含着对原欲的净化。不懂得“以情节欲”“借情抗礼”,使得传统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始终处于灰色地带,即使在反抗礼教的话语中,也没有获得其应有的合法地位。对传统礼教的抗争也因而常常流于纵欲放荡,并无多少情感上的解放。在这样的情欲观念下,一部分人拼命压抑感情、成为封建贞操观的傀儡,也有一部分人一味以发泄欲望来追求快感,因而形成了情感的畸形压抑和欲望的变态释放这两种极端的精神走向。“五四”作家对封建性的批判恰始于此。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和单四嫂子都是情感被压抑乃至剥夺的典型。她们处于中国乡村那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却孤立无援,得不到半分情感的慰藉。作者赋予了她们寡妇和母亲的双重身份:寡妇的身份使得她们失却了妻性的温柔与贤淑,转向母性的宽宏与慈爱,孩子的意外失去却又剥夺了她们为人母的身份。情感在寡妇和母亲这两重身份中的双双失落终是将她们一步步推向无望的深渊。《祝福》和《明天》或许可以看成是一个故事的两种写法,如果说《明天》重点叙述的是作为寡妇的单四嫂子如何失却母亲这个身份的,那么《祝福》的侧重点就在于讲述祥林嫂是如何从一个现实的寡妇变成了心理上的寡妇。生活的种种贫穷、困苦、动荡和不幸虽然常常给祥林嫂带来麻烦,但却始终没有击垮她。真正击垮她的是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贞操观,它根深蒂固又如影随形,牢牢地把改嫁后的祥林嫂绑缚其中。旁人对祥林嫂不洁的指责和生怕死后身体被劈成两半的恐惧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祥林嫂终是没有摆脱夫权制下不平等的主奴意识,陷入到一种画地为牢的局促中。在她这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已不再是外在的规范,而是内在的约束。她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寡妇,对情爱无望,向夫权低头。更可悲的是,当母爱——这个唯一符合礼教的女性情感归宿也被整个社会所扼杀时,她们最后的感情出口亦被死死堵住。当她们的孩子死于天灾和人祸之后,“明天”再也不会到来,个体的情感在那个封建闭塞的社会里终是归于幻灭。母亲身份的失落成为女性情感湮灭的终点。这一点在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隐藏在“典妻”罪恶背后的,是女性被当成生育机器的事实。个体的情感与渴求统统无足轻重,人成了可以被交来换去的物品,即使是所谓符合礼教规范的个人情感也被弃置不理。春宝娘所展现的是一个女性在夫权制下情感世界节节退守却终究退无可退的悲剧命运。她们如鲁迅所言,是“老中国的儿女”,“本来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2]332。当最合乎自然人性的母爱都被封建社会撕扯得支离破碎之时,传统情欲观对人情感的压抑已然到了畸形的地步。
除却情感的失落,变态欲望的产生成为封建传统压抑下情感的另一种极端走向。一群表面上“三纲五常”、实则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封建卫道士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固执地维护着纲常伦理,视情欲为洪水猛兽,常常在世风日下的感叹中忧心忡忡,俨然把自己摆在一个道统继承人的至高位置上。然而讽刺的是,他们的心中也常常有着对情欲的隐秘渴望,性意识时不时不受管控地冒出头来,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肥皂》中四铭老爷对于“买块肥皂,给孝女咯吱咯吱地遍身洗一遍”[3]51的反复强调,《高老夫子》里高尔础讲课时目力所见的女学生乱糟糟的头发,都是鲁迅从心理描写的角度去揭露这些封建卫道者禁不住冒出头来的性幻觉与性心理。明明被异性所扰乱,却偏偏装出一副批驳世风的虚假嘴脸,这种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割裂使得他们的情欲无法得到正常的宣泄,反而逐渐流于猥琐。一面是“男女授受不亲”的绝情禁爱,一面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殖崇拜,两种观念的对立和共存催生了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他们活在欲的宣泄中而忘乎情的存在,因而进一步造成了情欲观的扭曲。《高老夫子》结尾处对高尔础在打完第二圈麻将,终于觉得世风好了起来的描写,就是鲁迅对这类伪君子最大的讽刺与鞭挞。
以批判封建情欲观作为整个现代文学情感书写的起点,是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的口号相互映衬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高举“人的文学”的大旗,反对“非人的文学”,他提出的是人最原始、最基本的问题,即如何发现人、“辟人荒”的问题。他在文中明确地为“人”下了一个定义:“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4]。这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去理解人,着重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属性与合理欲求。《人的文学》中所发现的“人”既要求“灵”(精神生活)的合理性,也要求“肉”(世俗的、肉体的)的合理性,是灵肉合一的人,是符合人性人道的真人。于是,将个人从漫长的历史轨道和驳杂的社会体系中抽离而出,构建成一个“不为君而存在,不为父母而存在,晓得为自我而存在”[5]5的个人,成为这一时期的启蒙要务。“五四”文坛的作家选择以反封建反礼教的形式实现情感的释放与人性的解禁,实质上是在启迪中国人从奴隶意识中走出,抛却“灭人欲”的伪道德观和剥夺情感权利的“节烈观”,从而摆脱灵肉分离的畸形生存状态。破旧方能立新,只有卸掉历史传统的重压,才有可能正视人的问题,诞生真正的“人的文学”。
二
从封建传统中突围出来的一代人,大声疾呼着自由与解放。他们以婚恋自由为口号,以情感解放为旗帜,一路向着理想中的启蒙圣地高歌猛进。从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到庐隐的《海滨故人》,甚至到二十年代末《莎菲女士的日记》,都呈现出恋爱至上的叙事倾向。其中的主人公无不将爱情看作是人生至圣至洁的大事,企图以爱情的获得来摆脱现实的困境、实现个体启蒙。情感解放成了知识分子启蒙的捷径。然而,对个体解放的大肆宣扬和个人情欲的过分释放常常使得人的情感陷于迷乱。郁达夫、丁玲等人的作品都讲述过一个在欲望的左右奔突中无法找寻到“情”的故事,显示出不加遏制的欲望对个体的启蒙具有怎样摧毁性的力量。
郁达夫笔下早期的“零余者”具有相同的形象特点:既漂泊孤寂又渴望慰藉,既感伤忧郁又愤世嫉俗,既空虚沉沦又自我谴责,总之,他是一个永远无法与周遭环境相融合的边缘人。他们以追求爱情作为治愈自己种种心灵困境的良方,所以《沉沦》中的主人公才会发出“不要知识,不要名誉,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所要求的就是爱情!”[6]24的大胆呼号。这种宣言无疑是划时代的,它是对旧时代“谈情色变”现象的猛烈冲击,是对所有言行不一情欲行为的赤裸嘲讽,是他们那一代人对所谓“启蒙”的直观认知。可惜的是,《沉沦》这一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并没有懂得爱、收获爱,他们虽试图打破传统情欲观,却时常被伦理道德的鬼魅所缠绕,仍未破除情欲一体的思维方式,造成了情感启蒙的一次迷失。《沉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在自己所作的小说里把自个儿想象成一个多情的勇士,幻想着与邻家寡妇女儿的传奇故事,可现实中的他却怯懦、胆小,既无法承认情的萌发,也不能正视欲的骚动。所以才会对自己的生理反应充满恐惧和自责,而对欲的拼命压制又带来了对情的过分警惕。他见到迎面而来的女学生“呼吸就紧缩起来”[6]22,在喜欢的旅馆主人女儿的面前“总装出一种兀不可犯的样子来”[6]35。这种对情的遮掩与隐藏使得人的情感无法正常地生长与释放,从而逐渐滑向变态的欲望,这才有了主人公的偷窥与窃听。“零余者”们在欲望中迷失,归根到底是因为无法真正地认识“情”之一事,始终混淆情欲、等同情欲,难以逃脱传统情欲观的影响。此时的情感解放有如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因为缺乏理性的节制与恰当的体认,一时之间泥沙俱下,绝望与希望并存,灾难与光明同在。
到了二十年代末,情感书写中对情与欲的区分变得鲜明起来,现代理性的形成使得人们开始以审视的目光看待情欲,但情、理、欲的复杂纠葛依旧难以避免。这在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较之“零余者”们,莎菲在感情上更勇敢、更积极。她主动追求姿容俊美的凌吉士,却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对方卑劣的灵魂:凌吉士的爱情就是肉感的享受,他的世界中既无高尚的欢欣,也无深切的痛苦。于是,莎菲陷入一种新的困境:爱一个人,究竟是爱他的躯壳还是爱他的灵魂?在情感的选择中,究竟是从理断情还是尊崇本心?她无法处理这种对立与撕裂,所以日记中才会充满沉沦和自责这两重声部。沉沦是欲的难以遏制,而自责则来源于理性对欲望的审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凌吉士的迷恋与自身的爱情诉求是怎样地不相符。她所渴望的感情是了解、是慰藉,正如她自己所说过的那样:“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7]4这样的情爱观是真正意义上现代的情爱观,是个体摆脱了夫权制下的主奴对立意识后对爱情本身的叩问。如果说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们还是受着传统情欲观荼毒的先行者,那么丁玲笔下的莎菲已然是一个有着现代思维和现代困惑的新女性。她所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以理性战胜欲望,从而获得情感启蒙的棘手问题。理性的发展与本能需要之间的冲突,是此时个体启蒙所面临的巨大难题。结尾处莎菲的独自南下究竟是逃离还是新生,终是一个连作者自身都无法解答的谜题。然而,这盘难解的棋局在郁达夫那里已不再是困扰。此时的郁达夫为自己的“零余者”们找到一条情感的出路,变得游刃有余。
写于1932年的《迟桂花》,一洗郁达夫早期小说中的躁动与混乱,转向了平和与节制之美。时值中年的老郁,也像《沉沦》中的主人公一样,面临着情感的骚动与欲望的流窜。浓艳的桂花气味在不经意间激起他的性冲动,翁莲圆润丰满的身材也令他浮想联翩。不同的是,老郁选择将自己的内心波动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而不再是刻意的隐藏和压制。他的剖白与忏悔获得了翁莲的谅解、包容乃至某种情感的回馈。与其说翁莲是小说中一个温柔质朴的女性形象,倒不如说她是一种象征。她是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外在客体,如迟桂花一般,既激发了主人公的欲望,又在激荡过后以其纯真圣洁克制并升华了欲望,达至灵与肉的平衡。一种平和节制的感情也随之产生,即包含着关怀、慰藉与怜悯的兄妹之情。翁莲的清澈、率真与无邪是自然的具化,体现出郁达夫在以理性节制欲望的过程中是如何向自然求助的。空山秋夜的沉默,林间晚钟的幽幽,莫不让人肃然起敬。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自然不是民间原始的自然,而是理性过滤后的自然,是启蒙话语下知识分子对乡村诗意世界的想象。乡村不再是鲁迅笔下那个需要被启蒙的空间,反而成了人们安放心灵的居所。
郁达夫借助这样一个想象中的世外桃源,终从情感的沉沦中突围。理性以约束和塑形的方式实现了情欲的升华,成为此时启蒙话语构建的核心因素。梁实秋就曾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力陈理性的重要地位:“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能包括的是几样的成分?)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种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8]这与“五四”时期的自然人性论已有所差异,强调的是理性在启蒙过程中的指导意义。“五四”时期,一众作家关心的是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呼吁的重点在于“肉”的解放,即个体生命欲望的释放。他们还来不及进一步展示个体内心深处的冲突,也尚未思考欲望的大解放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和危机。而梁实秋对情与理之间关系的这种理解,是对人性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认知。理性约束情感,情感遵从理性,只有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才能呈现出健康的生存状态。这一方面是发现了理性在个体启蒙中不容小觑的作用,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唯理是从,真的能够走上启蒙的康庄大道吗?这成为情感书写中又一个需要被反复叩问的观念。
三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除却以进化论的观点去理解人、理解生命,还有不少作家选择去展示生命的另一面。他们突破意识层面,大胆地挺进潜意识层面,渐渐发现理性不是万能的。情感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以旁逸斜出的姿态,与理性相悖,构成一种非理性的存在。
在这一过程中,弗洛伊德学说的涌入影响甚大。1921年7月,朱光潜就在《东方杂志》上介绍过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1922年12月,谢六逸所译的日本松村武雄的论著《精神分析学与文艺》开始刊发,更为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学与文学的关系。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下,施蛰存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他的《梅雨之夕》就讲述了一个小职员在落雨的黄昏时分所产生的种种绮思。它展现出的是主人公情感世界的难以捉摸:个体的复杂情感偶尔会从日常生活中叛逃出来,向那个理性之外的世界探探头。那么,这种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情感闲逛是否构成对理性的怀疑与挑战?它与理性之间究竟能否共存共生?这种意义上的情感解放会不会与以理性节制情感的启蒙诉求相冲突,从而形成情感书写对启蒙话语的一种冲击和悖反?再一次,情感因其难以条分缕析的繁复形态,构成了启蒙话语下的又一重困境。
许地山的小说《春桃》和夏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就书写了情感选择的两难,呈现出两男一女的情感书写模式。春桃因战乱与未婚夫李茂走失,在劳苦的底层生活中与另一男子刘向高相互陪伴、扶持;《上海屋檐下》的杨彩玉曾叛逃家庭,与革命者匡复相爱,后因匡复革命失败被捕,迫于生活压力与其昔日好友林志成同居。面对前夫的突然出现或归来,两个女人都陷入到一种情感的撕裂之中。她们既怀揣着对前夫无法割舍的情丝,又与现在的同居者有着不可斩断的日常情感。春桃要三个人一块儿住的决绝,杨彩玉不舍得任何一个人离去的啜泣,都是在情感的复杂超出了理性的规范时所发出的叹息。作家们一方面将这种情感书写置于苦难的叙事中,增添了情感困境的厚度与深度;一方面又以牺牲的精神化解冲突,从而彰显出人性所蕴藏的无穷力量。
这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两重感情并不是来源于个人情绪的闲逛或出走,而是来自于情感的流亡甚至是流放。她们都是被抛入到生活的困苦之中的,战争的到来、革命的失败,构成了生命的苦难。苦难由此成为她们情感书写的起点。所以她们的情感困境不会像《梅雨之夕》中的那样似有若无,也不会像凌叔华《酒后》所呈现的那样意趣盎然。她们的情感撕扯本身就包含着一种难以抵挡的生存苦痛,展示出生活的沉痛与生命的厚重。而作品中两位男性的选择则使得这种情感困境由对立走向调和。他们都愿意以自我的牺牲成全对方,不再拘囿于自私自利的个人情爱。《上海屋檐下》的匡复重又投入革命的洪流中,《春桃》里三人同居、互帮互助的家庭组建模式,无一不突破了狭隘的爱情书写,为情感的走向找到了一个更加宽大宏阔的出口。人与人之间的怜悯与理解迸发出强大的人性光辉,克服了理性与情感两者间的紧张关系,达至一种新的平衡。日常生活中枝枝蔓蔓、难以厘清的非理性情感转化成一种审美情感,里面充满着自由与美。这类作品,尤其是《上海屋檐下》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时,西安事变的爆发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了一批关押已久的犯人。不少归去来兮的革命者都面临着昔日情感的困扰。匡复、杨彩玉与林志成的故事更是直接取材于戏剧界人士宋之的、刘莉影和魏鹤龄之间的经历。这类作品的意义倒不一定在于说明革命的无坚不摧或是包容万物,其珍贵之处在于体现了危急时刻人情人性所迸发出的强大力量。正是有了这样的情感书写铺垫,路翎才会在四十年代《财主底儿女们》中,让他笔下的主人公蒋纯组,在临死之际、在中国最为困苦之时,摒弃那颗躁动的心,真正地收获爱情、同情与理解。
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现实中被压抑了的情感,显示人性的复杂所带来的强大生命力,是情感书写中启蒙话语构建的另一个维度。它本身即包含着对启蒙的反思与丰富。启蒙不仅仅需要理性的引入和发展,更需要情与理的相互促进和激荡。否则,人们便会被工具理性所异化,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那样成为理性的奴隶。人性而非理性,一跃成为启蒙话语的核心要素,进入到文学场域中,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话语中情感突围的关键所在。这样的核心话语转变在梁实秋那里表现得格外明显。二十年代末的梁实秋还在高举理性的旗帜,然而到了三十年代与左翼文学阵营发生争论时,他转而推举“人性”。这里的“人性”不再侧重于理性,而是指向了人的情感,构成与左翼文学阵营所提倡的“阶级性”的尖锐对立。他在《文艺批评论·绪论》中说:“文学就是人生最根本最严重的情感之完美的表现。恋爱的力量,义务的观念,理想的失望,命运的压迫,虚伪的厌恶,生活的赞美,这种种都是古往今来的文学杰作的根本素质,而这种种又都是人性的最重要的成分。”[9]1“人性”的第一要义不再是理性,情感也不必一味向理性低头。梁实秋对于“人性”概念理解的滑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启蒙话语的不断转变。
情感书写,就这样在困境与突围两种状态中不断反复,揭露出情感解放本身所携带的巨大“麻烦”。可也正是在这些接续不断的麻烦和风波中,二三十年代文学才得以勾勒出一条从情欲分离到以理节情再到情理激荡的情感解放路径。伴随着对情、欲、理三者关系的反复书写,启蒙话语的核心要素也在不断发生转变。与“五四”一代作家反封建反礼教的情感书写起点相对应的,是人的自然属性的挖掘与解放;而当欲望泛滥成灾危及健康情感的产生时,理性被大规模引入并置诸领头羊的位置之上;但情感对理性的冲撞又常常提醒人们修正对世界的认知,唯理是从变成了一个可疑的伪命题。以审美情感的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泛人性”成为启蒙的灵丹妙药。由此,情感书写在自身的流变与发展中形成了从提倡自然欲求到推崇理性再到尊重人性的启蒙话语构建,完成了对启蒙的实践、反思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