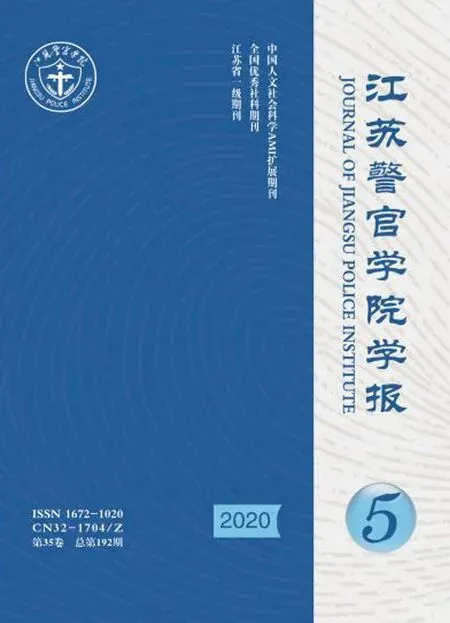作为回溯侦查认知模型的摸底排队
顾 君
摸底即“摸清底数、摸清底细”;排队即“逐个核实、甄别”。摸底排队长期以来被界定为一种常用侦查措施,这是从侦查行为视角对侦查经验的总结,其关注的是侦查工作组织实施的样态。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学界对侦查的认知停留于对侦查外在行为过程的描述,未能进行必要的理论抽象,而认知模型是对侦查认知进行理论化描述的工具。伴随侦查信息化实践,侦查认知正在发生某种流变,由于侦查认知模型这一基础性理论的缺失,造成传统侦查与信息化侦查理论的某种割裂。从认知视角看,摸底排队是对侦查实践认知样式的提炼,它能描述和解释侦查认知的结构和过程,指引侦查认知的实践;能够预测并解释信息条件下侦查认知中出现的新现象和趋势。因此,作为侦查认知模型的摸底排队具有必要的理论解释张力,是贯串传统侦查与信息化侦查理论的认知基础。
一、摸底排队侦查措施定位的缺陷
(一)无法解释摸底排队对其他侦查措施的总摄现象
在摸底排队的实施过程中,基于特定情势必然大量使用其他措施。比如普遍摸排的过程中,了解核实相关情况时必然要通过询问、辨认、查阅档案资料(信息库)等方式进行;摸排过程中发现可疑人员要常规性地实施搜查、讯问;遇到可疑人员(不限于本案嫌疑人)逃跑通常要采取追缉堵截等紧急措施;鉴别特定对象与案件的关系离不开检验鉴定;锁定摸底排队的范围很可能需要技术手段的支持。尤为重要的是,由于摸底排队的终极目标是发现嫌疑人,那么所有其他侦查措施的使用均服务于摸底排队中的某个具体认知目标(子目标)的实现,且这些侦查措施的使用有着认知逻辑上的内在条理性。在此意义上,摸底排队总摄其他侦查措施。
(二)对摸底排队起始节点的解说不能自洽
按传统理解,摸底排队以对案情和嫌疑人的分析判断为基础,也即确定侦查方向与范围是摸底排队的逻辑前提。然而,在侦查初期,侦查人员所能掌握的案件情况往往是有限的,很可能无法第一时间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只有在经过普遍摸排后才能获得更多案件信息,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由此看来,摸底排队并非以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为前提,有时反而是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的必要手段。
(三)对摸底排队的终结节点解说不清
在侦查学教科书中,通常将侦查认识过程分为寻找发现嫌疑人、认定犯罪嫌疑人两个阶段。其中寻找、发现嫌疑人阶段的方法就是摸底排队,而该阶段以确定重点嫌疑人为终止,这似乎是说确定重点嫌疑人是摸底排队终结的标志。然而,重点嫌疑人并不等同于侦查认定的嫌疑人,认定嫌疑人仍需要围绕重点嫌疑人生活背景寻找其他更有效的条件(证据)以服务认定需求,该阶段工作仍属于摸排的性质。
(四)无法解释摸底排队的条件和侦查方向在内容上的重复
侦查方向的确定是侦查认识活动中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侦查方向在实践中被称为是“侦查工作的锋芒所向”,在语义上这一概念是虚指,只有在具体的案件侦查中才能获得其内容上的实际表达:针对具备特定条件的人开展侦查工作。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差异,但其实质内容与摸底排队的条件一样,表达的都是嫌疑人应当具备的某些特定条件。两者在内容上的重复从逻辑上看,可以理解为摸底排队是侦查方向的实践展开。而这正凸显了本文的主题,摸底排队不仅有行为层面的经验意义,更有着认识论层面的深刻意蕴。
二、摸底排队措施定性的原因
(一)侦查认识理论研究中僵化的教条主义认识论
当前,侦查认识理论停滞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立场的复述,直觉性地判断侦查认识是一种回溯性的认识活动,并将回溯侦查简单地解说为是从犯罪结果回溯其原因的认识活动,既没有分析侦查认知过程的一般样式,也没有从回溯逻辑的角度揭示侦查认知的特点及界限。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实践中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以意识为中介的客观对象与主体行为的互动过程,是一个感知—思考—行为—反馈的循环过程。受当时科技背景所限,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仅以阐明主体与客体的宏观关系为己任,思辨、原则地考察了人类心智产生与发展的路径,而未能由宏观层面深入至微观层面,进而探索客体刺激在认识主体内如何转化为各种心智形式(如意识、观念等)的动态过程”①朱宝荣:《认知科学与现代认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真正科学的哲学,在于其唯物主义立场、辩证法贯彻和实践论皈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向一切科学技术开放的,现代认知科学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因此,对侦查认识的理论研究应呼应不断发展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对侦查认识的研究深入到侦查员内在的认知过程中去。
(二)侦查认识理论研究中的唯理主义取向
唯理主义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可靠知识不是来自经验,而是从先天的“自明之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当前侦查认识的理论研究基本上起始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认识论立场的复述,辅以侦查经验的陈述,似乎侦查认识的具体知识是从这些认识论原理中演绎出来的。唯理主义取向的研究进路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侦查认识理论的实践品格,导致侦查认识理论与侦查实践的脱节。
哲学认识论对具体学科的认识理论有着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具体学科需要在哲学基本立场、观念、方法的指导下基于本学科的具体经验进行相关的研究。如果说哲学认识论是从宏观角度探索个体认识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侦查认识理论则应立足于侦查实践,从微观角度研究侦查认知的过程及其机制的具体规律。洛克认为:“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是导源于经验的。”①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66页。经验不是唯理主义演绎的结果而是人类实践的结果,其在性质上属于“知道如何”的知识。在哈耶克看来,其是人们基于“理性所不及”的某些一般规则行动的结果。②[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波兰尼则将人们行动中所拥有的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称为隐性知识。③杨郁娟:《论侦查隐性知识》,《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因此,对于摸底排队这一侦查实践的经验结晶,理论研究的目标在于竭力阐释“知道如何”背后的“知道那个”以及“知道为什么”,将隐性知识显性化。
(三)侦查认识理论研究中的行为客观主义范式
受限于心理学研究的一般进程,对侦查认知的研究长期被行为客观主义研究范式所统治。行为客观主义的研究重点是人的外在的、可观察到的行为,排斥考虑人的内部所发生的心理过程,因此,行为客观主义无法提供对人的内部心理过程的观测,也无力构建关于认识机制的一般理论,它实际上沦为一种机械反映论。相应地,侦查认知往往表现为从现象直接到“不言自明”的结论,对侦查认知的研究呈现为对侦查经验的阐述或脱离内在心理过程对思维方法的研究。
现代认知心理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人的内部发生的心理过程上,放在人对外界信息的内部加工过程上。相较于传统心理研究领域的内省法和行为客观主义分析,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研究视角转换的问题,更有赖于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为核心的方法论范式的革新。它将人的认知视为信息加工的流程,将人脑视为“黑箱”,从信息的输入输出关系上,来把握心智结构和机理,模拟人的认知过程。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得对侦查认知的内在心理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成为可能,侦查认识理论的研究迎来发展契机。
三、摸底排队的认识论意蕴
(一)作为系统认知过程的摸底排队
1.认知目的有机性。在侦查实践中,具有某种特征的(嫌疑)人员是一个条件性的集合,并非是侦查工作的直接对象,并且其具体身份也处于未知状态,是需要寻找确定的目标。这些嫌疑目标的发现,需要通过某些“与案件有关的人、事、物”作为认知的中介而实现,他们是需要寻找确定的次级目标。也即查明嫌疑人的认知总目标基于侦查认知的逻辑衍生出一系列不同层级的子目标,呈现为认知目标的树状图。其中的每一个子目标都是关于条件的集合,也是侦查认知的目标集(或解空间),而每个解空间都意味着一组摸底排队工作。嫌疑人应具备的条件内在规定了“由事到人”“由物到人”“由(关系)人到(嫌疑)人”等侦查认知的进路(即侦查途径),侦查中的一系列摸底排队行为是基于侦查认知逻辑的有机组合。
2.认知过程的整体性。现代认知心理学主张将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作为整体加以系统研究。因为系统论揭示,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其实质是说系统整体具有系统中部分所不具有的性质。④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传统侦查理论研究将侦查认知过程割裂为认知心理视域“对案情的分析判断”与行为视域“开展侦查工作”两个不同层次,这是对实践的某种误读。首先,从内在意识过程与外在行为的关系看,摸底排队行为不过是服务于侦查认知的一种反馈方式,即通过行为获取信息,从而印证认知判断或是提供决策依据。其次,虽然摸底排队的条件是现场认知得出的结论,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对象之所以能对理解者呈现出意义,主要是由于它具有某种“理解前结构”,这是理解、解释之所以可能的先决条件。①陈中立等:《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也就是说,侦查员关于犯罪的“理解前结构”指引着现场认知,即筛选何种信息、如何加工信息和得出何种结论。因此,案情分析和开展侦查两个认知阶段基于共同的有关犯罪的前设叙事,即观念体系、思维前提和思维假设等,当试图从信息加工过程探索侦查认知领域时,这两个认知阶段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摸底排队映射犯罪的内在表征
1.案情是犯罪的表征单位。侦查认识围绕着案情进行。案情除了表达案件的具体情况之外,还表达从各具体案件中抽象出的某种“一般结构”。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观点,知识在人脑中的存储和组织形式或者说知识在人脑中的呈现方式,称为知识的内在表征,知识表征有内容和形式之分。②梁宁建:《当代认知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因此,犯罪表征是反映犯罪的知识,是犯罪通过信息中介转化为人脑中与其相应的映象或观念形式。其中,案情是犯罪内在表征的单位,按照故事结构理论的观点,正是借助于这种“一般结构”,侦查员才能有效地理解和处理其他具体案件。③陈永明、罗永东:《现代认知心理学——人的信息加工》,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5页。
2.案情是基于案件要素的关系结构。考察摸底排队条件中的“时空条件、因果关系条件、作案工具条件、知情条件、痕迹物品条件、赃物条件、特殊技能条件、反常表现条件、前科条件、特征条件”等常见条件,其实强调了三类关系:其一,犯罪事件的时空关系。时空是客观实在的基本属性和维度,犯罪事件是对作案人连续性社会活动中一个特定时空片断的标记,犯罪事件同时也就标定了犯罪各要素的时空属性。时空属性既是循线追索犯罪各要素历时性过程的维度,也是鉴别或认定犯罪要素的重要标准。其二,作案人与痕迹物品的关系。痕迹既能反映人与物的特征,也能反映人的某些特定行为。作案工具条件、物品条件、赃物条件表达的是历时性过程中作案人与特定物的所有、获取、伴随、处置等具体行为或关系状态。其三,作案人的犯罪行为与其连续性的日常生活行为之间的联系。该联系又有两种情形,一是作案人日常行为的习惯性所规定了的某些犯罪行为中的具体特征,如特殊技能条件、前科条件;二是作案人的某些日常行为或事件如因果关系条件、知情条件、反常表现条件,与犯罪事件紧密相关。
3.案情是案件要素在时空维度动态过程中的关系结构。世界万物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案件构成要素中的人与物也有着各自的线性轨迹和际遇,并与社会环境不断发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互。在侦查认知中,时空要素首先被理解为标定犯罪事件的时空坐标,由此,基于案件各要素历时性的连续动态过程,形成更为复杂的关系网络,案情呈现为以犯罪主体事件为基础的、不断发散的各关联事件系统。而侦查员的中枢控制系统基于目的导向,对上述客观图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适,即以作案人为中心,把握作案人与痕迹物品、作案人的犯罪行为与其连续性的日常生活行为之间的联系。
(三)摸底排队隐含的侦查元认知策略
1.从摸底排队看侦查认知中的问题解决。一般说来,在回溯侦查的模式中,已知的情况是现场的各种现象,即犯罪人行为的直接损害结果及对客观环境造成的各种变化。根据犯罪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回溯推理判断现场“发生了什么行为”,但并不能依据某种因果律从犯罪结果中直接推导出“行为人是谁”或“谁实施了这一行为”。侦查实践将问题表述为“嫌疑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又藏身何处”,即侦查方向和范围的确定。认知科学认为,问题表述的适当性将影响问题解决的难易程度。侦查实践中的命题置换,使得问题求解得以可能。这种置换发生在侦查理性认知之前,是侦查员基于“理性不及”的“默会之知”,属于侦查元认知策略。由于这些尚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在位阶上的优位性,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侦查实践的基本方式及特点。
2.摸底排队是对回溯侦查式样的提炼和抽象。从认知思维看,“问题解决的实质就是在自己头脑中所构成的关于外在世界的心理模型进行的一系列操作活动,当了解外在世界时,问题就解决了。”①刘爱伦:《思维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在侦查认知思维下,犯罪现场的认知实际上是横向搜索犯罪事件时空,从结果现象摄入案件具体信息,将犯罪表征中抽象的要素及其关系具体化;侦查方向的确定实际上是纵向搜索关联事件,判断并优选关联事件,寻找知情人,由此确定可疑人、事、物与案件的关系并明确嫌疑人,这实际上是横向搜索关联事件的过程。而认定作案人,主要是针对嫌疑人进行纵向搜索以获取证据的过程。摸底排队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认知作用,是对回溯侦查式样的提炼和抽象。其一,摸底排队广泛适用于对案件中人、事、物的认知。摸底排队可以表述为“穷尽具有某种特征的对象并从中识别出特定对象”。检材在样本库的同一认定,其在方法形式上表现为摸底排队;而对作案人行为方式的判断、理解痕迹现象之间的关系,侦查员往往需要依据经验穷尽其可能的原因,从中确定符合现场整体情况的假说。其二,摸底排队是侦查认知中的定位技术。侦查认知始终穿梭于历史构建与现实实存之间,案件要素在现实中的本体需要经摸底排队确认,围绕该具体要素的案情关系才能具体化,才能追溯其与案件的进一步关系。摸底排队在形式上是在犯罪表征关系网络中的定位技术。其三,摸底排队是侦查知识和经验的组织方式。虽然痕迹物证知识是现代侦查学发展的主线,但侦查认知是综合运用专门知识与一般生活经验的结果,这些一般生活经验是回溯推理中“通常被省略的前提”②[波]齐姆宾斯基:《法律应用逻辑》,刘圣恩译,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页。。如果说痕迹物证技术是提供物(痕迹)的特殊性及痕迹与具体行为关系的知识,那么一般生活经验主要解决物(痕迹)与案件的关系、痕迹(对应行为片断)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案件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经由摸底排队最终确定。摸底排队链接着不同领域的知识,是对侦查知识和经验的组织方式。其四,摸底排队的成效决定侦查认知的实际可能性。犯罪这一历史事件的信息发送及其获取方式不外乎痕迹物证、共时空知情人及档案资料。由于痕迹物证知识已然系统化,能否摸清底数、底细,是否有效地逐个核实、甄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侦查认知的实际可能性,摸底和排队是这种侦查认知样式有效性的内在要求。
四、回溯侦查认知的方式和特征
回溯侦查认知整体上可描述为:在犯罪表征的指引下,从结果现象摄入案件具体要素及其关系信息,沿着犯罪关系网络节点,次第有序地搜索作案人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寻找、处理、利用信息,由信息驱动的认知过程,而每一个认知节点都依赖于寻找和鉴别信息(即摸底和排队)的组合使用。因而,摸底排队在认知机制上表现为寻找与鉴别(认定)两种功能的组合,它们以一种交互的方式整合在侦查认知活动之中,侦查认知过程表现为寻找与鉴别两个环节。
(一)寻找环节
与标准的穷举法相比,摸底排队过程中的每一个目标集(解空间)中,具有某些特定特征的对象的具体身份是未知的,是需要寻找的确定的目标。在此意义上,马忠红教授将寻找性界定为侦查认知的本质特征。③马忠红:《侦查的本质及特征》,《人民检察》2004年第8期。该环节的认知表现出鲜明的特征。首先是搜寻策略的高度指向性。侦查中的寻找并非是一种漫无边际的行动,犯罪的关系表征犹如现象世界复杂迷宫之中的线路图,它始终引导侦查思维有选择地关注并解读繁杂的现象信息,评估其是否与犯罪事件有关及其在犯罪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侦查方向隐含着一种高度建构的搜寻策略,探索那些可能产生稳定信息交换的、并导向作案人的关联事件,侦查员心智在侦查认知过程中不断进行着目的导向的调校。其次是在控制基础上的循线追踪。侦查建构的搜寻策略并不必然能得到正向反馈的结果。对象的底数能否摸清决定着侦查认知的实际可能性,而这是由社会整体的科学治理水平决定的。毕竟公安的治安控制不过是“维持其他社会机构所不能干预的无纪律空间的一种‘间隙纪律’和‘元纪律’”①[法]米歇尔·福科:《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9-241页。。
(二)鉴别(认定)环节
侦查中的鉴别在实践中常被称为“综合审查评断”,其认知方式是一种印证模式。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印证模式已经取得了规范上的合法性。②左卫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将“逐个核实、甄别”简单归纳为排队,未能准确地表达这一认知过程的特点。侦查中的鉴别不仅要鉴别对象身份及其与案件的关系,还需要核实证明本身的可靠性,其认知要求及复杂程度超过同一认定。首先,证伪(排除)法是印证的重要方法。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的证明活动存在两种维向,即证实主义进路和证伪主义进路。③[英]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编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页。侦查中的印证既不能简单视为“建立假说—论证假说”的证实过程,也非不断推翻修正假说意义上的证伪过程。在侦查认知的具体机制中,排除法有着重要的认知意义。其次,“有罪怀疑”是侦查员思维方式中必然的倾向性特征。侦查认知中由于痕迹物证事实上的稀缺性和隐匿性,势必引发寻证中的定向注意力,从而产生心理暗示效果,使“有罪怀疑”的思维定势得以强化。再次,印证机制理论上的完美依赖于犯罪行为与痕迹之间某种理想型关系的预设,但现实中由于犯罪留痕行为方式、留痕条件、认知条件和能力乃至破坏风险等多方面的限制,痕迹物证极度稀缺。司法实践中,过高的诉讼证明标准和合理证明机制的缺乏,有时倒逼侦查机关“技术性地制造出虚假的印证”④左卫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在诉讼证明认知转向的背景下,合理的诉讼证明规则必然表现为对侦查认知机制中合理的方式方法的确认和规范,毕竟“证明原则在逻辑上先于证据法而存在,而且,还为其提供了许多潜在原理。”⑤[美]特伦斯·安德森、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证据分析》,张保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6页。
综上所述,摸底排队是侦查的实践经验,是人们基于理性所不及的某些一般规则的行动结果,它是一个系统的认知过程和方法体系。由于能否“摸清底数、底细”,是否“逐个核实、甄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种侦查认知样式的可能性及有效性,与其说“摸底和排队”是对某种方法的描述,毋宁说这是侦查认知样式有效性的内在要求。因此,摸底排队是对回溯侦查认知样式的提炼和抽象,反映回溯侦查的认知方式及特征,从认知视角看,摸底排队是回溯侦查的认知模型。而侦查工作组织、实施的具体样态,不过是侦查思维方式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形式,时代变迁背景下,侦查实践形式正发生着某些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