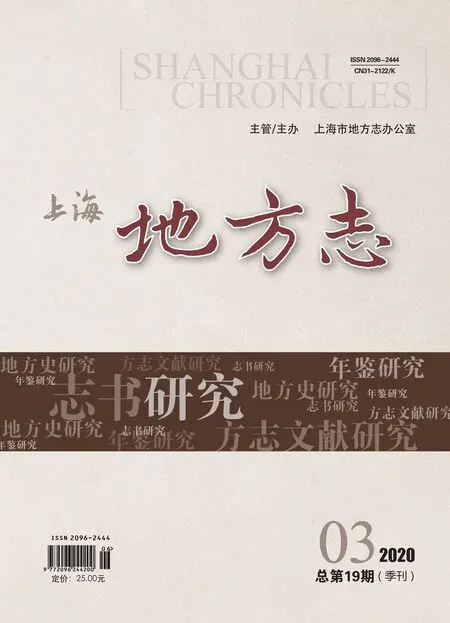方志学历史源流
陈 畅
在对方志学展开深入研究时,必然要对方志学本身的发展历史予以探讨,必然要涉及到方志学的历史源流问题。弄清方志学的历史源流,不仅是纵向系统地研究方志学孕育产生及其后发展历程的需要,也是深入研究方志学各阶段背景、内容、特点等,从而正确地把握方志学内部发展规律,进而对方志学的未来发展进行预判并可以作出相应调整的需要。①许卫平:《试论方志学的分期问题》,《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以下凡出该文者皆简称《试论方志学的分期问题》。
一、学界对方志学历史源流的已有探讨
中国地方志编修历史悠久,而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的产生和发展却落后于修志实践数百年,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和滞后性。但这并未妨碍历史上和今天的志家学者为“方志学”建设发展而努力,并未妨碍志家学者为“方志学”在学科之林居一席之地作出贡献。
“方志学”一词始见于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然而,早于梁启超提出方志学名词的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已经萌芽和成型,并于民国时期及以后走向发展和成熟。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其发展总的趋势是螺旋式上升的,与中国社会历史同进步共发展,这在学界已是共识。
有关方志学的历史源流问题,学界已有探讨。复旦大学巴兆祥在刊发于《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3期上的《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一文中,开篇就指出“他们有的从纵通向阐述,有些则按时期论述”。②巴兆祥:《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3期。以下凡出该文者皆简称《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巴兆祥本人则以学科学理论为指导论述方志学学科发展脉络。
(一)从纵通向阐述方志学发展脉络
笔者理解:所谓从纵通向论述方志学发展脉络,一是着重研究方志学史上各种理论、各种流派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二是研究各个历史阶段的方志理论成就和志家学者的成就,及其承上之作用启下之影响;三是梳理方志学发展的来龙去脉。
主要从纵通向阐述方志学发展脉络的学者及其代表作包括:许卫平《试论方志学的分期问题》(《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把方志学分为古代方志学、近代方志学、现代方志学三个发展时期。王广荣《试论我国方志学研究的历史与发展》(《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1期),将方志学发展分为宋到清的雏形孕育、民国时兴起、20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完善三个时期。张航、王艳《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轨迹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认为方志学理论萌芽于宋元明、成形于清、成熟于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发展和全面繁荣期。韩章训《论方志学发展历程》(《新疆地方志》2016年第3期),认为方志学萌芽于汉唐、初创于宋、发展于元明、成熟于清、独立于民国。佘广和《近百年来中国方志和方志学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际》2001年第1期),评述了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方志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学术成就等。
(二)按时期论述方志学发展脉络
笔者理解:所谓按时期论述方志学发展脉络,即着重研究方志学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特征的、较长时间的某一段历史时期的理论发展状况、理论创新、成果得失,以及立足该段历史时期对方志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予以探讨等。
主要按时期论述方志学发展脉络的学者及其代表作包括:洪焕椿《南宋方志学家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通过对范成大等6位志家学者的研究,得出结论——方志学已于南宋时形成。许卫平《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在叙述民国时期志书编修和方志学研讨热兴起的基础上,认为学科意义上的方志学开始形成。饶展雄、程慧《明代方志与方志学的发展》(《广东史志》1996年第1期),简要介绍明代方志编修和方志理论研究的成就。许卫平《近代方志学分期探论》(《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根据方志实践与方志理论研究的特征变化,将近代方志学的上下限分别定为清光绪中后期和1956年。许卫平《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扬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卷第1期),主要论述晚清时期方志编纂的创新和方志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廖晓晴《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32卷第1期),主要阐述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发展状况,并分析其创新之处。刘柏修《方志学科建设研究综述》(《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10期),主要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的10种构想以及学科体系的构成依据和特征。许卫平《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上、下)(《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2期、2006年第1期),在将现代方志学分为孕育待兴、探索、中挫冷落和新兴发展四个阶段基础上,进一步对现代方志学处于这四个阶段的发展状况、成果得失等进行分析。沈松平《试论民国方志诸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黑龙江史志》2006年第8期),主要论述民国时期方志实践与方志理论对传统方志学的继承与创新。姚金祥《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浅说》(《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1期),对近30年来学界有关方志学学科体系方面的研究予以综述。曾荣《新视角、新思路与新趋势:近代方志转型视域下的方志学研究述论》(《广西地方志》2016年第4期),主要从近代方志转型视角下梳理方志学的研究现状,并就方志学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探讨。
(三)以学科学理论为指导论述方志学学科发展脉络
20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新学科集群般涌现,以学科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学科学”(又称“科学学”)随即诞生。按照学科学的理论,学科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子系统或是大学中的一个专业建制;一个学科的成立,必须具备“特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时代的必然产物”“学科创始人与代表作”“精心营建的理论体系”“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五个最基本条件。
巴兆祥在《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一文中,把学界有关方志学的历史源流问题的已有探讨,划分为“从纵通向阐述”和“按时期论述”两类,而自己则有别于这两个角度,另辟蹊径地尝试以学科学理论为指导来论述方志学学科发展脉络。
在学科学理论指导下,巴兆祥依据学科学五个最基本的评判条件,对方志学学科发展脉络得出结论:清乾嘉时代传统学术意义上的方志学形成;民国时期是现代学科的建构时代,方志学也随之开始现代转型;20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转型后的方志学全面升级。
学界对方志学历史源流的已有探讨,综合观之,笔者认为:从纵通向阐述和按时期论述,基本都属于是对方志理论本体的总结与探讨;巴兆祥的以学科学理论为指导论述方志学学科发展脉络,相较于前二者,更具有学术研究性和学术研究意义,因为学科学本身就是学术研究发展的产物。
二、方志学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流向
对方志学历史发展阶段作出划分,是探讨方志学历史源流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基础。而学者们恰是对这一划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甚至对方志学成型之说保留意见。学术鼓励争鸣,笔者认为:影响方志学历史渊源和发展流向的因素有很多,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影响因素才能确保探讨和研究方志学历史源流的科学准确性。
影响方志学历史渊源和发展流向的因素,大的方面主要有:
一是,方志学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其产生和发展主要是由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规律所决定的。
二是,方志学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受到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期以及同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其他方面内容的影响。如受到当时学术意识和研究范式的影响;又如方志记述内容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编纂方志需要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撑,这些学科也对方志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三是,方志学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又具有自身的稳定性,通常迟缓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的变化。
四是,纵观方志学发展史和方志发展史可知,方志理论尤其是方志学的产生和发展,较其自身的物化表现形态即方志的出现和发展,具有明显的缓慢性和滞后性。但是,方志学一旦出现和创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方志编修实践及其成果的影响;反之,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又将给予方志编修实践以理论指导,进一步促进精品佳志的出现和地方志工作的发展。
下文中,笔者依据上述影响因素,同时借鉴学界对方志学历史源流的已有探讨,首先对方志学历史渊源和发展流向作一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进而在每一发展阶段重点分析方志学就其内部实质情况看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所呈现出的明显特征以及对方志学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等。
(一)南宋前期,方志学的雏形出现
中国的方志理论,从目前的史料看,大致始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序志》借用汉荀悦的史学主张,“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①[宋]范晔撰:《后汉书·荀悦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而提出地方志“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②[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序》,巴蜀书社1984年版。
至北宋,地方志书转向定型发展轨道,方志学也随之发展。元丰七年(1084年),太常博士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卷首序中写道:“方志之学,先儒所重,故朱赣风俗之条,顾野王舆地之记,贾耽十道之录,称于前史。”①[宋]朱长文纂:《吴郡图经续记·序》,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朱长文在此提出了“方志之学”这一名词,同时留下了方志之学为“先儒所重”这一讯息,实属可贵。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留下较多的理论阐述。
南宋之前的方志学理论,多散见于序跋之中。因地方志书大多散佚,理论阐述详情亦不得而知。而在整个南宋时期,方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时人对方志的理论思考也逐渐成熟。虽然南宋时期没有出现专门的方志学理论论著,但此时的理论思考已涉及方志学理论的核心——本体论与编纂学的基本层面,如方志起源、性质、功能及修纂人选、体裁、体例、编纂原则和方法等。总之,方志学理论尤其是理论核心在南宋时期已经产生,方志学的雏形在南宋前期已经出现。
方志在元代的发展,一是表现在并非远小于宋的修志规模;二是加快了的志书形式演变速度;②注:在目前可考的元代所修190多种地方志书中,方志多达140多种,即使是与南宋相比,也占绝对优势。在北宋所修的143种地方志书中,地记有12种,图经有58种,图志有4种,其他有47种,方志有22种。图经居首位,方志仅居第三。在南宋所修的262种地方志书中,地记有12种,图记有21种,图志有13种,其他有10种,而方志则有206种。南宋时,方志种类开始跃居首位,并远多于第二位的图志。参见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三是更突出地表现在创立了新的方志种类即“一统志”;③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了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扎马剌丁“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的建议,命扎马剌丁、虞应龙等负责纂辑“一统志”。五年后纂成,共755卷,定名为《大一统志》。元成宗大德初年,此志又重修,由孛兰盼、岳铉主其事,于大德七年(1303年)重修成,共1300卷,定名为《大元一统志》。元顺帝时,令刻印此志传世。四是元大德二年(1289年),农学家王祯将自己任安徽旌德县知县时修纂的6万多字的《旌德县志》试用木活字印刷,“不一日而百部齐成,一如刊版,始知其可用”④[元]王祯著:《王祯农书》(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亦在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方志发展和前朝理论成就基础上,元代的方志理论研究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元代虽仍无志家学者专门著作,但在方志序跋之中多见理论主张和观点。如:燮溥化在《乐安县志序》、黄溍在《东郡志序》、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序》中对方志的起源、性质以及作用,对方志收录范围和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冯福京在《乐清县志序》中强调“事不关于风教,物不系于钱谷,诗不发于性情,文不根于义理,皆一切不取,定为传信之书,庶非无益之作”⑤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3页。,明确指出了方志严格的收录标准,并说明其与志书质量的关系。此外,元代志家学者对志书体例、章法、类目设置、内容排列、材料剪裁、文字校正以及鞭恶扬善笔法等亦有探讨,并开展了方志批评。
明代以降,方志编纂的范围更加广阔,方志类型更加多样⑥注:除总志和府、州、县、镇志之外,还创修了通志和边关志。、体例和所记内容更加丰富⑦注:明代方志记载丰富,引用原始档案较多,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地理建置、经济物产、政治生活、军事制度、风俗、人物和文化著述等提供了大量文献支持,这是学界公认的。。有更多的志家学者开展理论探讨,对方志学理论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夫志,史之翼也”,⑧[明]童潮主修:《九江府志(嘉靖)·序》。已不满足于简单地将志书比附史书,而是多方面、多角度地辨析史志关系;“经之以天、纪之以地、列之以人”,⑨[明]杨鸾主修,秦觉主编:《云阳县志(嘉靖)·修志义例》。不止于将方志与《周官》《禹贡》联系起来考述源流,而是进一步认为方志是各类古史在体例和内容上的融合;不仅将“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⑩[明]刘鲁生:《曲沃县志(嘉靖)·序》。作为修志宗旨,而且注重订立凡例,通过将修志之所忌书于序言、凡例中,通过总结修志弊端等以明编纂之宗旨和原则。⑪黄燕生:《明代的地方志》,《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
(二)清乾嘉时代,方志学成为传统学术中的“专门学问”
巴兆祥在《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中分析清乾嘉时代的方志学:当时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方志编纂展开的,对方志性质、源流、功用的论述仅属零星阐发、片言只语;当时学者还没有意识到要去构架一个方志学的理论体系(即便是章学诚也如此),更没有意识到要在朱长文“方志之学”基础上提出“方志学”这一名词与概念。①《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简单讲,巴兆祥认为,乾嘉方志学大致属于“方志编纂学”。
笔者赞同巴兆祥观点,也赞同其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从学科的角度看,乾嘉方志学还只是论及了方志学科的主干而已,尚未形成体系。但是,笔者也想强调一个事实:没有构架一个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体系的意识,这不是乾嘉学者的学术素养问题,而是当时中国传统学术意识与研究范式大多如此所致。②注:乾嘉学者的方志学研究范式,或借助序跋、凡例,如李绂《重修临川县志序》;或以书札,如朱鹤龄《复沈留侯论修志书》;或撰写专文,如章学诚《地志统部》等。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历史时代的问题,是社会整体学术水准和学术环境的问题。
然而,笔者更想强调的是,虽然此时的方志学大致属于“方志编纂学”,但它已经成为传统学术中的一个学科门类,已经成为传统学术中的一科“专门学问”。
乾嘉时代,方志编修取得巨大成就,“各省、府、州、县皆以修志相尚”,③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以下凡出该书者皆简称《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编修方志约有1434种④庄威凤:《<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编著辑要》,《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10卷第4期。。而且,大批硕学之士——杭世骏、袁枚、全祖望、齐召南、戴震、王昶、章学诚、钱大昕、焦循、李文藻、毕沅、段玉裁、姚鼐、谢启昆、洪亮吉、武亿、李兆洛、汪中、孙星衍等纷纷投身各地的方志编修,出现“志多出硕学之手”⑤《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5页。局面。如全祖望等修志一、二部者比比皆是;更甚者如章学诚,主修、参修《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湖北通志》《广济县志》等十几部。
这些硕学之士,大多在经学、地理学、史学、谱牒学上有独到建树。他们视方志编修为“著述大业”,开始以自身的学问所长,从多方面多角度思考方志理论,积极开展方志学术研究。无疑,这是一个专业学者身上的学术素养和学术意识的自觉体现,是乾嘉学者的行为必然。章学诚所撰《文史通义·外编》被赞“集传统方志理论之大成”。民国梁启超在对中国地方志的编研发展情况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以后,甚至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在梁启超看来,章学诚将方志的概念由“地理书”改造成“一方之全史”,将方志的功用扩展为“专以供国史取材”,进而提出设立志科、保存资料等富有创新精神的建议,达到了构建方志学理论体系的高度。⑥曾荣:《论近代方志学的渊源与转变》,《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0期。
与前朝相较,乾嘉学者对方志理论所做的进一步探讨,不仅表现为探讨方志属性、起源、功用、体例、编纂方法以及修志人员素质等问题;更是表现为对方志性质、纂辑与撰著、体例因袭和创新等问题有所争鸣,以章学诚、李绂等为代表的历史派和以戴震、洪亮吉等为代表的地理派的形成是其中的典型表现。有关方志学研究的各分支科目,亦随之开始衍生出来。总之,乾嘉学者虽未构架出一个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体系,但传统时代方志学知识体系还是成功地被呈现出来了。
(三)光绪后期和民国时期,建构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盛
自乾嘉时代至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方志学无论在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体例内容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未突破方志编研的旧轨;同时,理论研究的领域仍很狭窄,方志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并无大的改观。总之,就其内部实质情况看,方志学研究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光绪后期,方有转变。民国时期,更是开启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方志学研究,传统学术中的“专门学问”开始尝试向现代方志学“独立学科”转变。①曾荣:《近代方志转型的视角:梁启超与方志学新论》,《沧桑》2014年第5期。
1.光绪后期,开始突破方志编研旧轨,摆脱旧志封建色彩
许卫平《试论方志学的分期问题》认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社会进化论的思想方法,以及近代科学技术文明,都对方志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光绪后期,方志学的研究开始挣脱封建社会的羁绊,显露出新的风貌。当然,许卫平是以古代方志学、近代方志学、现代方志学来划分方志学的发展阶段的,他所说的“显露出新的风貌”是指显露出他本人所划分的方志学“近代时期的风貌”。
在光绪后期倡导的乡土志编纂中纷纷强调“其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使其爱国,必令自爱其乡始”②[清]杨承泽:《泰安县乡土志(光绪)·序》。,“并激发其竞争之思想”③裴晃:《奉贤乡土地理·例言》。。这就突破了旧志编修主于资政统治、驯化臣民和供史籍取材等要旨的藩篱。近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亦开始主张,以新的思想指导志书编纂。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刘师培提出:要创编一种新方志。新方志的任务主要是推进乡邦政教和教育后人。新方志为“讨论国政之资”,要“激发爱土之心”,要注重经济、物产、技术及实业方面的记述等④[清]刘师培:《编辑乡土志序例》,《国桦学报》1906年第9号。。一些志家学者亦有类似的论述。这正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在方志学领域的影响与渗透。
光绪后期开始,方志记述较多地增加了“同光新政”以来出现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开始较多地反映民生实用方面的内容。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蔡元培《重修上虞县志例言》主张对旧志要“有因有革”“师古者得其意,不必袭其貌”,摒弃了章学诚修志开端必冠以“皇言”“恩泽”二纪的定式,提出仿《华阳国志》以地篇居首。在这一时期的不少志书中都摒弃了以往旧志卷首“天章”“恩纶”“宸翰”“巡幸”之类的内容。有的志书把“天章”内容按类分载到艺文门目中。可见,光绪后期所编修方志已开始摆脱旧志的封建色彩。
2.民国时期,开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方志学研究
晚清民初时,西方“分科治学”理念与学科分类法传入中国。如钱穆所指出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这个客观标准,指的是相关的学术机构与学科共同体建立起来。此时,中国的现代学术有了新的评价体系。在“各部门学科,均须以科学方法整理之”的学术背景下,志家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方志基础理论、方志编纂、方志理论发展史、方志发展史、方志批评、方志整理等方面探索建构现代方志学学科体系。正如曾荣在《论近代方志学的渊源和转变》一文中所指,“在西方分科理念的影响下,时人致力于方志学理论构建时,已经涉及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这一重要议题”。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方志学研究正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这一点在目前学界基本已达共识。方志学由传统学术中的“专门学问”开始尝试向现代方志学“独立学科”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方志学”学科名称得到学术界承认和使用,传统方志学迈向现代方志学走出关键一步。
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首创“方志学”这一学科名称。与此同时,梁氏还借用章学诚的方志编纂理论,阐释方志学学术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
其后,“方志学”这个学科名称,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使用。学者纷纷以“方志学”为名发表论著。如于乃仁《方志学略述》、李泰棻《方志学》、王葆心《方志学发微》等。1931年,顾颉刚、朱士嘉发表《研究地方志计划》一文,在给出方志定义后论述为什么要研究地方志,研究地方志的先决条件,地方志的研究层次、研究方法等①顾颉刚、朱士嘉:《研究地方志计划》,《社会问题》1931年第1卷第4期。。尽管此文通篇未提“方志学”一词,但实际上已对方志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作出阐释。1942年,吴宗慈发表《论今日之方志学》,“汇记一地方古今纵横之史迹曰方志,研究此汇记之史迹,应采用如何方法,乃适用于今之世,曰方志学。”②吴宗慈:《论今日之方志学》,《江西文物》1942年第2卷第2期。吴宗慈对“方志学”的界定更加明确。
(2)理论研究问题的范围被拓展和深化,方志学论著层见迭出,学者开始尝试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
民国时期,方志理论研究已经包括方志基础理论、方志编纂实践、方志发展史、方志理论发展史、方志批评、方志整理等问题。有关这些研究问题的论著,巴兆祥《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一文中有专门列举。另一引起笔者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整理了方志目录,而且甚至有很多专书出版。如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万国鼎《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任凤苞《天春园方志目》等。
1935年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篇章形式系统阐述方志名称、起源、发展、性质、功用、价值、地位等③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1936年王葆心撰成《方志学发微》,导源篇从地理学、史学、经学、文学各个学科角度考察方志的历史根源。④王葆心:《方志学发微》,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注析本1984年版,第246页。1938年甘鹏云《方志商》刊行,从修志实践出发系统论述通志编修的义例、凡例等问题,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修志理论和指导方法。⑤甘鹏云:《方志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59页。李泰棻《方志学》、黎锦熙《方志今议》、邬庆时《方志序例》、寿鹏飞《方志通义》、瞿宣颖《志例丛话》、吴宗慈《修志丛论》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方志学理论专著。据统计,1913年至1948年,另有方志学研究相关论作423篇⑥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民国时期,不仅方志学论著的数量在1949年前的方志学发展史上绝无仅有,而且更重要的是建构了方志学学科的一些基本术语——方志学、方志学界、方志名称、方志种类、方志性质、方志功用、方志取材、方志体例、方志源流、方志修纂、方志派别、方志整理、方志目、地方志、版本、参考书等。
个别学者甚至已经在论著中开始尝试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泰棻14章63节的《方志学》和傅振伦8篇19章的《中国方志学通论》。李傅二人所尝试构建的学科体系,都包括方志名称、方志价值、方志发展、章学诚方志学、方志批评、方志编纂等内容。不同之处在于:李泰棻以方志基础理论、方志批评、章学诚方志理论为铺垫,重点研究方志如何编纂问题;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的内容尽管较简略,却增加了方志种类、方志弊病、方志派别、方志整理等项,各篇章内容也较为平衡,其所构建的“方志学”学科体系更全面更系统。
(3)专业学者群稳定形成,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被运用,方志学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的现代科学性有了保障。
“五四”以后的民国社会,“竟言整理国故,表扬国粹”,于是“方志之书,颇引起学者之注意。”⑦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自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以下凡出该书者皆简称《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些原本从事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研究的学者,也纷纷将学术视野投向方志学,常在《东方杂志》《学风》《建国学术》《禹贡》《清华学报》等学术刊物、馆刊、报纸和学报上“发为论著”且“时有精义”①《中国方志学通论》自序。。顾颉刚、谭其骧、万国鼎、于乃仁、寿鹏飞、余绍宋、刘复、张维、张其昀、朱士嘉、傅振伦、庄为玑、王以中、瞿宣颖、甘鹏云、王葆心、胡朴安、胡行之、洪焕椿、方国瑜、邓之诚、蒋梦麟、卢建亮等学者,更是将方志学列为自己主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可想而知,这些学者的学识优势,对现代多种学科知识和理论的运用,进一步推进了方志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民国学者在方志学研究中,除承袭传统研究范式即“通过序跋、凡例、书信”之外,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主要以“学术文章”的形式发表见解,且有综述性论文、专论性论文等,形式新颖。
“从1911年到1949年,共发表方志学论文384篇。”②林衍经:《方志学广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如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东方杂志》1924年),瞿宣颖《志例丛话》(《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1号),傅振伦《方志之性质》(《禹贡》1934年第1卷第10期),万国鼎《方志体例偶识》(《金陵学报》1935年第5卷第2期),朱士嘉《方志之名称与种类》(《禹贡》1934年第1卷第2期),沈炼之《方志体例和内容的演变》(《地政月刊》1935年),王以中《地志与地图》(《禹贡》1935年第2卷第2期),王葆心《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论评》(《北平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1936年第56、58、60、61期),庄为玑《方志研究刍议(附泉州志综)》(《厦门大学学报》1936年),黎锦熙《方志今议(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图书季刊》1939年新1卷第2期),于乃仁《方志学略述》(《建国学术》1940年第1期),瞿宣颖《方志余记》(《中和月刊》1943年),寿鹏飞《方志本义管窥》(《国学丛刊》1947年第14卷第30—44期)等。
(4)成为大学教育科目,方志学学科地位被奠定。
傅振伦、瞿宣颖、顾颉刚、吴宗慈、朱希祖、黎锦熙等学者,在北平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西北联大开设方志学课程。课程或名为“方志学”,或名为“地方志”“方志实习”等。傅振伦秉承章学诚应“创办志科”的指导思想,第一个在大学开设并讲授方志学课程。
方志学走进大学课堂,成为大学教育科目,是方志的社会影响扩大之结果,是民国学者努力建设之结果;同时也真切地反映出方志学学科体系得到学术界认可、方志学学科地位上升的客观事实。
三、方志学成为成熟完善的一大学科尚欠东风
不同于传统方志学和民国时期开始的尝试向现代方志学“独立学科”转变,1956年后,社会主义新方志学产生;改革开放后,地方志事业更是全面发展,不仅出现两次全国性的修志热潮并形成大量修志成果,还出现了影像方志、数字方志的新形式和方志网站、方志微信公众号等新载体。新时代背景下,方志理论研究繁荣兴盛起来,并成功吸纳新的学术研究元素,方志学“独立学科”的建构得以全面升级。
可以说,方志学在改革开放后成为“独立学科”,这一观点在学界已无异议。但笔者认为,方志学预成为如历史学、文学等成熟完善的一大学科,仍欠东风。
(一)1956年后,社会主义新方志学产生
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编修传统在一些地区开始传承延续。但从建国之初至1955年这段时期,方志学虽然在应用研究方面不无起色,但其发展总体上处于冷寂局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政府还无力顾及方志编研,新的修志队伍亦未建立,纵有志书偶尔成稿,也往往出于民国遗老之手,且体例和内容都难脱旧轨。
这一状态于1956年开始转变。方志在编研方面,开始呈现出一些本质性的变化。主要原因和表现如下:①《试论方志学的分期问题》。
一是,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共八大召开,中国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形态意义上的方志学即社会主义新方志学,遂有了转变产生的社会形态基础。
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视,专家学者的呼吁,1950年代中后期,方志编修传统在全国范围得到恢复,并掀起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研的第一个高潮。方志学学科也随之推动发展。
自1956年起,在随后的两三年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纷纷倡议重新编修地方志。如《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第7版刊载全国人大代表王祝晨《早早动手编修地方志》一文;《人民日报》1957年3月13日发表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等委员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的联合发言《继续编纂地方志》。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等一批志书,并选辑其中部分内容转发与会的领导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同时毛泽东还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同年8月9日,周恩来指示:要系统整理县志,把各地地方志中有关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的资料整理出来,古为今用。周恩来要求国家档案局抓好修志工作,并委托曾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主持其事。
三是,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编写新的地方志”列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的十二个重点项目之一,②注:一说1956年。参见邱新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沿革(1958—2002)》: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副秘书长高德介绍,这个《方案》后来并未正式公布,从他保存的《方案》(草案)看,正式形成的时间是1957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1956年。并从具备条件的市、县开始,逐步推广,计划在十年内全国大部分市、县编修出新方志。1958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后转入中国科学院),对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包括科研工作意义重大。这就拉开了社会主义新方志学兴起的序幕。
四是,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贯彻落实马列主义基本思想和要求,倡导用新的思想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指导新志编修、旧志整理应用以及理论研究等。此举对方志学的科学发展方向,产生了积极影响。
五是,1956年起,学界开始探索有关社会主义新方志学发展方面的理论研究,方志学研究渐趋活跃。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及成果开始出现,如金毓黻《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傅振伦《整理旧方志和编辑新方志问题》、吕振羽《一封关于地方历史研究的书信》、王重民《中国的地方志》、陈正祥《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等。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957年)系全国第一部方志联合目录,洪焕椿《浙江地方志考录》(1958年)系国内第一部区域方志研究之作,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1962年)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方志考录性著作。这些开创性的探索研究和“第一”,对社会主义新方志学的学术起步具有标志性意义,尽管有些尚不深入,甚至略显粗浅,但并不影响其对日后整个“新中国方志学术70年”具有重要价值。③潘捷军:《“志”存高远:新中国方志学术70年》,《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5期。
此外,学者们就新方志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问题予以探讨,表现出时代特征。如1956年金毓黻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一文,论述方志价值、新修地方志的内容和体例、新修志书篇目等,赋予其时代新意。金氏在“社会”门中列“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生活动态”等类目,开始吸纳马列主义基本精神。方志学分支科目的研究工作亦开始起步。如1956年至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开展方志应用研究,从全国志书中摘录三千六百万字,汇编成《方志综合资料》《地方志分类资料》《地方志物产》等,共计六百八十册。
(二)改革开放后,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已无异议,要成为成熟完善的一大学科尚欠东风
梅森《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立项准入时机成熟》,从四个方面探讨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依据:近代化以来,中国学术和学科的细化裂变必然促使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方志的历史地位是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历史基础;方志活动的学术积淀是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学术基础;方志资源的广泛利用是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的社会基础。巴兆祥《基于学科学视角的方志学学科构建源流》指出:20世纪80年代,总结性方志成果出现、学科体系日渐完善丰满、专业学者群规模更大稳定性更强、学术著作堪称经典、专业性学术共同体和学术阵地建立、理论研讨会常态举行、方志学扎根大学课堂等,都标志着改革开放以后的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
如果说民国时期方志学学术成就大大超越了过往,“方志学”学科名称得到学界承认和使用、方志论著层见迭出、专业学者群稳定形成、现代学术研究范式被运用、方志学进入大学课堂等几大主要表现,昭示方志学开始尝试向现代方志学“独立学科”转变;那么,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各高校的历史学系、图书馆学系、档案学系“常态化”开设方志学课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各层级方志学人才教育全覆盖,学术共同体建立,学术研讨会“常态”举行,研究范式向成熟学科看齐,总结性方志成果问世以及较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体系被公认等,则标志着方志学现代转型后成功实现“全面升级”。
但是,笔者想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方志学还没有出现转折性发展,就其内部实质情况看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民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方志基础理论、方志编纂、方志理论发展史、方志发展史、方志批评、方志整理等方面积极建构学科体系。但是,从实际效果看,还存在两个重要缺陷,一是除方志编纂和方志整理两方面的成绩最为显著之外,其他方面尚显单薄;二是缺乏专门的学术阵地,大学里的方志学课程也多属临时开设。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方志学,只是实现了“全面升级”而已,最大的进步也仅在于解决了民国时期的缺陷。实事求是地讲,相较于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的变化,方志学表现出了一定的“迟缓性”。
改革开放后,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方志学学科历史问题,尽管其书写还较为单一、不成体系,但毕竟是这一方面的有益尝试。许卫平《试论方志学的分期问题》(1992年)、《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1995年)、《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上、下)》(2005年、2006年),刘柏修《方志学科建设研究综述》(2004年),姚金祥《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浅说》(2014年),韩章训《论方志学发展历程》(2016年)以及梅森编著的《上海方志研究概要》(2004年)都对方志学学科历史问题有所探讨。
根据学科学理论,对学科发展历史的书写与否,是考察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准。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改革开放后的方志学,已如历史学、文学一样成为成熟完善的一大学科?答案只能是——尚欠东风。一个成熟完善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定位、发展思路及方向等,以区别于其他学科。方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无异议,但要想成熟与完善,仍需要顶层设计,仍需要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架构来统筹理论发展方向,仍需要进一步在体制机制、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有更大的建树。①《史志学刊》2018年方志理论专项研究课题组:《近20年来方志学学科建设研究述略》,《史志学刊》第4期,2018年。总之是,其任也重、其道也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