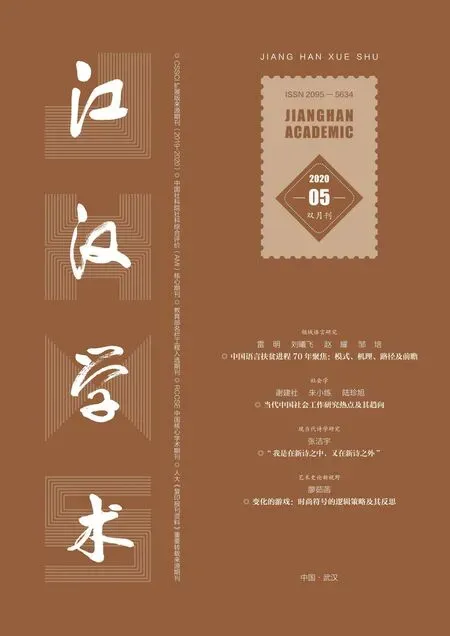“语言诗化”与“窗”
——论林庚在创作与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
张 颖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在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作者由新诗创作转向旧体诗创作或者其他文学研究领域的大有人在①,但在新诗已经取得合法地位之后,从旧体诗有意识地转向新诗,而且终其一生坚持在古典与现代的穿插融合中创作新诗,并构建出独特的新诗理论,却唯有林庚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洪子诚先生曾说:“林庚是诗人。但他是写‘新诗’的诗人。是能写好旧诗但坚持写新诗的诗人。而且还是到了晚年仍倾心于新诗的诗人。”[1]“写新诗的诗人”这个名称包含了“为诗一辩”的急切感,也似乎唯有此能准确地标明林庚在文学创作上的身份。穿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唐诗研究、楚辞研究、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之间,林庚“由‘学’而‘诗’,从‘诗’到‘术’”[2],充分体现出了他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互动之间构筑诗学的特征。这种互动关系的成果,是著名的“节奏音组”“典型诗行”“半逗律”“九言诗”等新诗概念的阐发,但不可否认的是,林庚的格律诗实验在新诗历史中后继乏人,不仅如此,后人一般认为林庚在1930年代后期创作的两本格律诗集在艺术特色上并没有前面两本自由体诗集那样鲜明。而根据林庚对新诗的整体设想,新格律诗才是未来新诗发展的方向,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似乎值得追问,从其“学”“诗”“术”的互相缠绕中或许能够寻求到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本文试图从其核心诗学观念出发,钩沉林庚在新诗创作中的内在脉络,并于学术研究的多重纠葛中理出其背后的思维模式,最终考察他在多重身份互动下的核心诗学理念,在此基础上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探索角度。
一、“语言诗化”与一种迷失
林庚的一系列古典文学研究在古典文学界获得了极高评价②,但他的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却一直伴随着质疑与论争。早有戴望舒评价其写作是“用白话文写旧体诗”[3],后有穆木天认为林庚的诗集中“现实主义的成分,是相当的稀薄”[4],穆木天当然是在褒义上使用“现实主义”一词,这些评价似乎奠定了林庚诗作被否认的基调。但同时,俞平伯认为“他不赞成词曲谣歌的老调,他不赞成削足适履去学西洋诗,于是他在诗的意境上,音律上,有过种种的尝试,成就一种清新的风裁”[5]。废名对林庚的诗更是激赏:“在静希的《春野与窗》无声无臭的出世的时候,我首先举手佩服之,心想此是新诗也,心想此新诗可以与古人之诗相比较也,新诗可以不同外国文学发生关系而成为中国今日之诗也。”③当代有研究者指出:“他的新诗写作脱胎或者说分蘖于旧诗写作的经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他的成功的写作,主要原因却不在旧诗的影响,而是在接受旧诗的影响的同时,能始终立足于新诗探索的基点,并且有意识地运用一些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方法技巧,对这些影响进行主观处理,使其在现代性艺术的洗礼之下,实现某种富有意味的现代性转换。”[6]林庚的格律诗实验成功与否我们暂且不论,但单纯的新旧比附确实会简化他在吸取历史经验中所作的努力。
考察林庚一生的新诗探索姿态,明显可以看出他试图从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中呼唤出一种仍然可以行之有效的普遍法则,在“现代性转换”这一视野之下所寻求的是一种委婉的、抒情的方法,在“继承”与“转换”这两个维度中,试图规避由暴力性的革命所带来的反作用,而达到一种温和的过渡。“语言诗化”这个概念便是这一普遍法则的具体承载物。在新诗理论与古典文学研究中,林庚将其作为连贯新旧的核心理念予以多次阐发,其核心是诗的语言问题。联系到林庚由自由体新诗转向格律体新诗时的时代背景,正是早期新月派的新格律诗实验的瓶颈期,自由体新诗“要么成为分行的散文,失去诗的艺术特征;要么回避散文,在远离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7]165,此时林庚开始意识到回顾古典诗歌的重要性,“中国文学史事实上乃是一个以诗歌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它,对于探寻诗歌美学的奥秘,诗歌语言的形成过程,都是理想的窗口和例证”[7]161。现实的契机④与探索的动因相结合,在新与旧之间寻找一种和谐的过渡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出路,而林庚所追寻的诗学核心理念也在这种不断的反顾中呼之欲出。
“语言诗化”到底具有什么含义?在林庚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系中,“语言诗化”是古典文学被向前推动的核心动力,“诗化”的本体物质是“语言”,通过某种转化,化普通的语言为诗的语言。林庚指出,“诗化”是诗歌语言“突破生活语言的逻辑性和概念的过程”[7]163。在现代诗歌研究历史中,“诗化”往往与“非诗化”同提,那些新诗创立初期“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8]在构成了破旧立新的资源的同时,也被后来者不断批评。他们所言的“诗化”毋宁说是“新诗化”的意思,相比于林庚的“语言诗化”概念,其含义更专一。“诗化”仍然具有其背后的逻辑性,“诗化”后的语言要给人带来新鲜感,但是不能完全脱离人的想象范围。如何在“诗化”的同时,既保证语言的创造性,又保证逻辑的合理性,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林庚的研究中,古典诗歌“语言诗化”“具体的表现在诗歌从一般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它自己的特殊语言”,这仍然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证:“突出的表现在散文中必不可缺的虚字上,如‘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在齐梁以来的五言诗中已经可以一律省略。……这是一个高水平的提炼,乃成为语言诗化发展中的一个标志。”[9]将一般语言(散文语言)中不可或缺的虚字去掉,打破语言的逻辑性,却仍然不影响读者的理解,这是“语言诗化”一个重要的跨步。除此之外,在诗行、语法、词汇上,“语言诗化”分别有不同的要求,林庚每每根据古典诗歌在这几个维度的“诗化”经验,来提示新诗语言相关维度的“诗化”需求。
诗行的“诗化”是指古典诗歌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的发展过程,“今天我们缺少的正是相当于五七言那么既严格又简单的诗歌形式……我们缺少的正是这个建行的基本规律”[10]。所谓“建行”,不是指行与行之间,而是一行之内,字数的增减所引起的节奏变化。林庚设想的是,如果能够探索出一种“普遍诗行”,将之应用于大多数诗人的创作,那诗歌的普及将不是难事。“普遍诗行”不仅与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关,其核心还是为了将现代语言能够以一种接近人们生活的方式普及开来,以达到如唐诗一般脍炙人口的地步,缓解新诗目前的困境。从具体的方案实施来看,“普遍诗行”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关键问题在于林庚的“普遍诗行”与古典诗歌的差别很微妙,在极度排斥“旧诗”的新诗人们看来,这无异于诗的复古。因此林庚一面坚持实验,撰写理论文章,一面开始寻求折中的办法。
“半逗律”“节奏自由诗”便都可以说是折中的产物。借着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探讨民族形式问题的契机,林庚正式提出“九言诗的‘五四体’”这一诗行概念,“九言诗的‘五四体’最接近于民族传统,也最适合于口语的发展;我想‘民族传统’与‘口语的发展’应该是今天诗歌形式上最主要的问题”[11]。从建行问题到民族传统问题,看似不太相关,其实正符合了林庚一直以来的思想观念,即“普遍诗行”背后所隐含的诗歌愿景。至于“九言诗”与古诗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在成型的七言诗基础上随意增添两个字,而是根据“半逗律”规则,重视生活当中的话语习惯与白话文中新的“节奏音组”的出现,将之规定为上五下四的“五·四体”。从根本上来说,林庚考虑的出发点是语言从文言变为白话文之后诗的现代性问题:“从中国诗歌史上看来,文言曾经是古代诗歌的理想语言,五七言也曾经是古代诗歌的理想形式。但是无论是文言或是五七言,对于今天的诗歌说来,就都不如对于古代诗歌那么理想。”[12]因此“让群众用自己生活中的语言,在更为理想的诗歌形式中充分自由的歌唱,追求比五七言更为理想的诗歌形式是完全应该的”[12]。当诗行上寻找到“九言诗”或者折中的“节奏自由诗”这种诗体,新诗的诗行便彻底从旧诗中脱胎出来,成为能够容纳新时代、新思想、新语言的载体。换言之,正如齐梁以后的五言诗,“九言诗”成为新时代“语言诗化”的一个标志。
在古典诗歌中,语法诗化建立在五七言形式成熟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便是将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飞跃性、交织性等特点充分释放。语言的飞跃性“通过诗歌语言跨度上的自由,解放了诗人的冥想力与思维敏感的触角”[9],而词汇诗化主要是“诗的新原质”的发现过程,“我们写诗因此就正如写诗的历史,因为我们每发现一个新的原质,就等于写了一句诗的新的历史”[13],而新诗的语言从文言变为白话,单音字变为多音字,字数增多之后就更要通过拉大诗歌语言的跨度,“摆脱散文与生俱来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使语言中感性的因素得以自由地浮现出来”[14],否则便成为分行的散文,诗意全无。
当代诗人臧棣在探讨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时提出:“从语言的同一性出发试图弥合古典诗歌与新诗的断裂(或称差异)的可能性究竟是怎样的——它是一种切实的建议,还是一种似梦的幻想?”[15]可以看到,在林庚的研究中,不管是变化了的时代,还是变化了的语言,其背后的文字仍然共同依托于同一个汉语传统,因此在原理上,新诗的诗化与古诗的诗化并不是一种完全断裂的关系,反而可以借鉴其内里最核心的机制。与此同时,“语言诗化”虽然能够成为一项普遍原则被应用于新诗当中,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正如戴望舒所言:“林庚先生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大森林中一样,好像他可以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然而他终于会迷失在里面。”[3]这种“迷失”在日后林庚的创作中是事实存在的。从林庚的古典文学研究与新诗创作,也即“学”与“诗”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林庚的古典文学研究对他的新诗思路形成了一种合围之势,在“语言诗化”这一普遍原则的统摄之下,新旧诗似乎连成了一线,同时新诗本身所应该具有的“现代性”则被无意识地忽略了。在新旧文学极度“断裂”的背景下,这种温和转变显然更符合林庚对“诗”的态度。林庚的诗学理论与新诗创作在这种连续性的视野中得以建构,这一方面有利于规避革命性动作所带来的破坏性,同时也就有可能在这种反向中过犹不及,虽然如此,“语言诗化”并没有在当下完全丧失活力,仍然对诗的创作具有反向上的启发性。
二、“窗”与格式之间
从“诗”发展到“术”(具体的新诗理论),林庚进行了多番理论探索,“诗”与“术”的联系看似紧密,但往往鸿沟也就在这里发生,理论与创作之间的龃龉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关键是要深入林庚自身的思维与观察角度,理清创作与理论之间的生成与游离关系。林庚在1930年代出版了四部诗集,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由诗到格律诗,不仅是具体的诗学实验,也是一个诗学理想的追寻过程。从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到,这种诗学理想的追寻过程是相当曲折的,困难在于新格律诗如何在真正意义上保证语言的自由,如何在“诗化”的基础上不走进古诗的死胡同,如何使多种因素在诗中得到调和,成为林庚所追求的“自然诗”,而民歌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非常关键的资源,缓解了自由与格律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北平情歌》为中心,可以考察前后时期林庚写作的转变。一改《春野与窗》中的自由体诗风格,《北平情歌》几乎是严格的格律诗实验。为什么要取名为“北平情歌”,林庚说到,“据说写诗是要生活丰富的;而自己这一年来,除了上课堂教书外生活便如一张白纸;然而依然有这样不算太少的一些短诗,虽然如此平淡,已不能不感谢是这古城的赐予了”[16]。纵观集子中的诗歌,北平的风景占据主线,可以作为古城赐予诗意的证明,但更重要的或许正如林庚自己道出的,因为现实生活的平静,反而在读书、教书、文学研究等学术活动中寻找到了更多的情绪共鸣。这些情绪与现实如何构成林庚写作的背景,又如何参与到其创作中,要从诗人主体形象,以及意象等内部因素去考察在表面的形式试验背后复杂的逻辑。
《诗成》这首诗在林庚的所有创作中具备“元诗”特征:
读书人在窗前低吟着诗句
微雨中的纸伞小孩上学去
秋来的怀想病每对着蓝天
纸伞上的声音乃复趣有佳
“诗成”这个诗题颇有意思,全诗并没有写一位诗人如何写诗,而是勾勒了一幅场景。读书人低吟着的诗句是已成的古诗,还是自己正在写作的作品,我们不得而知,第二句是一幅实景,一二句结合起来看,是写作者站在高处随意俯瞰到的一幅场景。但三四句从视景转向内心,“怀想”以及对纸伞上声音的遥想,才是真正的“诗成”过程。所以这首诗可以理解为林庚心中对诗人形象以及写诗动因的一个解释:一个足不出户的读书人,借着一扇窗观望秋天的景色,遥想风景中的声音,写成诗,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过程。
如此看来,“窗”在“诗成”过程中具有格外重要的作用。“窗”是林庚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前一部诗集就命名为“春野与窗”[17],而在《北平情歌》中,“窗”一共出现了22次,最多的时候在同一首诗里出现3次。通过对这些诗的分析可以发现,诗人所站立的地方总在窗内,也就是一种从内向外的视角,诗人借窗户去关注外界的事物变化,诗意的产生很多时候都是从诗人的眼睛看向“窗”开始的。“窗”在林庚的心目中成为了一个触发诗意的“装置”,只要一看见“窗”,马上就会“目击成诗”。实际上“窗”外的景物在不同的诗中可以变化为多种场景,比如“低低的小窗下淅沥未曾停”(《弹琴》);“窗外冰冻了天井”(《冬之曲》);“读书人窗下该有着什么点缀着秋来”(《秋来》);“窗前静静的每一个下午日影与风声”(《窗前》);“窗外寂静的我的园子里门在哪里呢”(《夏之深夜》),等等,“窗”可以说是诗人在平静的读书生活中了解外界事物的一个触媒。
其实在这之前,自由体诗集《春野与窗》中,林庚就写过一首以“窗”命名的自由诗,这首《窗》则更加深入地刻画了一个独坐窗下的读书人静坐想象的过程。而且林庚对这首诗十分重视:
《窗》共写了整整三天;这三天我把所有杂念都丢开,将心沉在这一件事上;除了到处走走外,人便整个的陷入沉思了;这样平均每天约能完成一节;到了第三天的夜间才算写好了最后一句。……独写《窗》时精神异常愉快;我不断的把七八行诗变成两行,一行,到有一句可以用时仿佛才可以喘过一口气来,接着便仍又写下去,我开始觉得在一种新的风度的尝试中,能够把自己用毅力安顿在长时间的追求里,忠实的完成了它的欣慰。[17]
从1933年到1934年10月这个时间段内,《窗》的写作可以充分说明林庚转向格律诗的动机与原因。写作时间的加“长”,诗行的不断精炼,最重要的是“能够把自己用毅力安顿在长时间的追求里”时所体验到的一种“一种新的风度的尝试”,这种创造的愉悦成为推进后面更深入的实验的动力。《窗》本身并不是一首格律诗,所谓的精炼主要是指情绪的锻炼,同时,“不断的把七八行诗变成两行,一行”,这种减缩也是“诗化”的过程。
吴晓东曾研究过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其中“居室”与“窗”在现代派诗歌中反复出现。“如果说居室是‘人们在无穷无尽的空间切出一小块土地’,‘窗’则意味着这一封闭的内在空间与外界的联系。”[18]在林庚的诗中,“‘窗’作为有限与无限之间的人为的界限在此趋于消泯,这使林庚能够‘随便的踏出门去’(《春天的心》)。正是这一句‘随便的踏出门去’,构成了现代派诗歌至为难得的一个诗品”[18],将窗内与窗外世界的互通看作是林庚浪漫诗品的体现这一点切中肯綮。周作人曾在《五十自寿诗》中写到:“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窗下世界似乎成为了现代诗人们的一个庇护所,窗下的艺术世界到底能不能成为现实的庇护所这一点,在战火频仍的现代中国已经得到了否定的证实,但依然有许多人到窗下去寻一张“平静的书桌”。因此,“窗下”这个位置在现代文人们那里确乎具有一种张力,可以反映出他们在“入”与“出”之间的紧张状态。而回到林庚身上,“窗”与其说是一个意象,不如说是连接诗意与形式之间的一个装置,他在“窗”与诗的“格式”之间构造了某种精神联系。
“窗”是打通室内外的媒介,而“窗框”则是一种对外面的风景的规约。窗框类似于看电影时的荧幕,林庚在探讨“诗的韵律”时就拿“荧幕”做过比喻,他首先指明不同的荧幕形状会影响观者的观看感受,而这就类似于自由诗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然而大自然却是不要我们觉得有什么形式的,它是要我们简直不知怎么的就接受了它;自然诗像它,乃也要一个使人不觉得的外形;而这便是韵律。便是正如那电影上永远用一个一致的幕”[19],窗框正如荧幕一样,“一致的幕”就类似诗的形式,它是通向外界景物的一个窗口,而它长久固定的形状,使得窗下的诗人丝毫没有觉出束缚,这便是“普遍诗行”所能够达到的同样的效果。
“窗下的读书人”是林庚对自身作为诗人形象的揭示,同时他在“物”与格律之间所搭建的这种精神联系也给我们以启示。在“诗”与“术”之间,这种内在脉络并不容易被发现,尤其是在林庚的创作中,有许多扭结状态对我们的理解构成了障碍。《北平情歌》就表现出林庚在古典与民歌、口语之间的某种扭结。不可否认,集子中的很多诗尚有浓厚的古典影子,一方面是意境上的化境,另外就是具体意象的采用,如“ 夜 ”“ 晨 ”“ 窗 下 ”“天 空 ”“ 落 花 ”“ 墙 外 ”“游 子 ”“牧野”“童年”等,还有某些短语句子的使用,如“夜半角声里”(《秋深(一)》);“吹遍了人家”(《秋深(一)》);“画角的哀愁”(《秋深(二)》)等。这些“五字”短语常出现在“十五字”诗或稍微长一些的诗句中,源于新格律诗实验容易不自觉地袭用古典诗歌中现成的诗句,林庚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似乎也可以证明“迷失”的出现是很容易的。
然而也可以注意到,像《情歌》这种明显具有民歌情调的句子,也出现在林庚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其前期自由体诗也有《洗衣歌》一首,明显模仿了民歌。林庚尤其注重民间文学对诗歌发展所起到的解放作用,在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林庚认为每当正统诗歌进入宫廷变得繁缛整饬,离人民越来越远时,民间流传的各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诗句反而充满活力并经久不息。因此当诗歌之路走到僵化与末路,不妨借鉴民歌的经验。具体到新诗创作中,类似于陕北民歌“青线线蓝线线蓝格英英采/生下个蓝花花实是爱死人”,所提示的可能正是继“五七言诗”之后新诗形式的新方向,类似于林庚所实践的“十一行诗”。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诗歌在西化与古诗之间是一种折中的形式,林庚取法民间,与1940年代延安诗人们的创作并不一样,文人色彩更浓,并且对民谣也有更多的转化。
综上所述,《北平情歌》中的新诗实验,古典意象与意境占主导地位、口语试图融入其中、民歌带来解放,这三种因素形成了林庚初步试验新格律诗的基本面貌。到《冬眠曲及其他》中的四行诗,似乎终于找到了一种合适的诗体,以《北平自由诗》为例:
当玻璃窗子十分明亮的时候
当谈笑声音十分高朗的时候
当昨夜飓风吹过了山东半岛
北平有风风雨雨装饰了屋子
这首诗语言流畅,一改之前格律诗中明显滞阻的情绪,显得畅快清晰,情绪丰富。而这样的诗作在林庚的整个格律诗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林庚转到厦门大学任教,十年时间,时代环境瞬息万变,林庚的活动重心慢慢转向了学术,但诗的写作一直没有中断,甚至专门开设写作课以练习新诗。建国后,在新诗民族形式讨论中,林庚更加深化了之前的格律诗理论,而这一切都与他这十年间的古典文学研究有着深刻的关联。
三、延伸或者转化
在创作上林庚更多表现出一种恬淡闲适的风格,尤其是早期的自由体新诗,有学者甚至认为,“在本质上,林庚的诗是传统的中国诗的内容的,也是一个优美的闲雅的中国气息的诗人,很少有染到近代世界性的观感”[20]。但是林庚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显然必须要纳入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历史进程之中,现代学术与古代学术的差别除了研究方法上的不同,最重要的是一种研究视野与格局上的转变。林庚的文学史研究相比于一些具有严谨的学术化风格的文学史有更多的诗人色彩,在对作品尤其是诗歌作品的理解上往往别有新意。更重要的则是林庚提出的一些文学概念,比如:“布衣感”“少年精神”“盛唐气象”,这些概念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也对我们更生动地理解文学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林庚的新诗理论中,有一些与古典文学研究有比较明显的联系,如“半逗律”就是从《楚辞》当中直接获取的经验。这种联系非常直接,往往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一些更抽象的概念。细细考察这些概念的使用,会发现与林庚对古典诗歌的理解密不可分,也就是说,除了“语言诗化”作为连接新旧诗的核心线索,林庚对新诗美学特色上的认识,也包含了古典诗歌中转换过来的经验。
以“深入浅出”“狭”“偏激”等词语为例,林庚所说的“深入浅出”是一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就唐诗来说,“唐诗的可贵处就在于它以最新鲜的感受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启发着人们。它的充沛的精神状态,深入浅出的语言造诣,乃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完美的成就”[21]。诗歌发展到盛唐时代,语言获得了充分的表现力,唐诗能生动、深入地体现出人们的生活,其普及与流传程度也达到最高。从语言学的角度,唐诗或许不是最复杂精微的语言,但从美学的角度,唐诗的语言因其“深入”的同时又能“浅出”,最能将美的文字与新鲜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在林庚的新诗理论中,“深入浅出”的语言特色是涵纳在“普遍诗行”这一愿景之中的艺术特点。“深入”“浅出”是不可分离的,单向度的“深入”或者“浅出”最终都会走入“狭”。“自由诗好比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一面冲开了旧诗的约束,一面则抓到一些新的进展”,“然而在这新进展中一切是尖锐的,一切是深入但是偏激的;故自由诗所代表的永远是这紧绝的一方面”[19]。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创的新诗而言,极度的暴力断裂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林庚此处言明的“紧绝”,“紧绝”是“深入”的,同时也导致了“偏激”。而对“偏激”的警惕,就来自于他研究古典文学的经验。
经过盛唐之后,韩愈、孟郊等人所代表的“苦吟”时代到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这种“深入”实际上就是“诗歌落潮的征兆”[22]219,“为了不甘心于这样一个落潮,杜甫过去曾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到了韩愈就发展为追求那奇特的、生疏的、惊人的语句上的表现”,而这种追求无异于“追求着一根远离开自然道路的魔杖”[22]219。之后的创作离生活越来越远,诗歌高潮慢慢被词、曲、小说所取代。这根远离开自然道路的魔杖虽然“指顾之间,便出现一个浓郁缤纷的世界”[22]223,但“它却是离开自然的离开现实世界的神秘的语言”[22]223,“艺术性与现实性”不能统一,最终在程式化中趋于僵化。这就是一味“深入”最终导致的灭亡结果。“人们乃需要把许多深入的进展连贯起来,使它向全面发展,成为一种广漠的自然的诗体。”[19]林庚提出的“自然诗”,就是结合了“深入”与“浅出”两个方面的全面诗体。在“自然诗”中,“明朗性是诗的一种美德”[23]。
从语言上的特点,到一种美学上的追求,“深入浅出”实际上不仅是林庚针对新诗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他心目中对新诗所能达到的成就的一种期许;对新诗越写越狭窄,越写越散漫的警惕。要避免单向度的深入,否则就会走向晦涩;既要抓住刹那的情感,也要捕捉永恒的无限。“深入浅出”看起来简单,却是唐诗能够在艺术上臻于顶峰又能历经千年仍然引起新鲜感的核心要素。如果更具体地来看,“深入浅出”又不仅仅是一种美学的追求,也是林庚理解诗歌形式与内容之关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语言诗化”或许可以看做一种“深入”,同时,结合形式上的“浅出”(普遍诗行的产生),将能产生林庚心目中理想的新诗。
除所述三个概念之外,林庚在新诗理论中还会时常使用一些古典诗话概念,“质”与“文”就是一例。
诗坛到了长久的“文”的阶段后,乃渐渐的丧失其质,而留下一个空洞的形式,亦即是学的文了;这便轮到诗坛的衰歇。于是又需要一个质的时期。不过从前的求质没有今日自由诗的彻底,故如晚唐人打开的局面,到后来只演变成诗,终非诗的全部。⑤
林庚将“质”理解为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之下感悟到的某种诗意,它是刹那间新得的感情,具有“惊警紧张”的特点,是个体所感悟到的思想与感情;而“文”是这种感情经过蕴藏之后发抒出来的,更加具有普遍性,有“从容自然”的特点,平常的好诗基本处于二者之间。但相对来说,一首诗的成功与否在于“文”而不在于“质”,这是一种完成了的自然、谐和、均衡。而“质”并不是不重要,只是真正的好诗是将“质”消化融入“文”中,变成一个成熟浑融的整体。林庚对“质”与“文”的理解,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古典文论中文质彬彬的观念借助诗歌史的支撑,它着实可能在一定层面回应人们在自由和格律上两相拉扯的困局,不是从技术构成上,而是在美学意蕴上,重建中国诗歌在打破旧有的诗歌体制后的文与质的张力关系”[24]。不管是“深入浅出”,还是“质与文”,诗歌必须处理好刹那的感情与形式的束缚之间的关系,这其实就是新诗格律问题的内在本质。
古典文学研究对林庚的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他“能够自如地出入于新诗创作与古典诗歌研究之间,二者并行不悖甚至相得益彰、相互激发”[25],以一种现代视野去重新审视古典诗歌的同时,古典诗歌的美学与语言特色也真正构成了新诗发展的资源。其实除开这些具体方面的互相联系,更能反映出其关联本质的是内化于林庚自身生命的一种精神底色。林庚对唐诗“深入浅出”这种美学特色的概括,以及对“自然诗”理念的伸张,都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与其说林庚所追求的是一种抒情化的“纯诗”,不如说他追求的是一种艺术的本质。艺术“是超越性的,艺术的感受刹那而永恒,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能使我们超越有限直面无限的宇宙”[7]164,这种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是林庚进入文学领域的初衷,也贯穿了他整个“学”“诗”“术”的探索历程。
四、作为一种“诗品”
“艺术的超越性”使人超越有限的时空抵达无限的宇宙和历史深处,人的心灵通过艺术便获得了这种超越的能力。在这种认识之上,林庚认为“陶渊明所以说读书不求甚解,正可为这般经生说法。不求甚解原是艺术的态度,因为一切艺术的语言原不是逻辑的语言所能尽的,艺术把人带到原始的浑然的境界,才与生命本身更为接近”[26]。沉浸在诗歌中获得最原始自然的生命感受,不加雕琢的、纯然的生命体验,我们可以将这种具备抒情色彩的人生追求称之为一种“诗化”的人生态度。
从“学”“诗”“术”三方面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来看,林庚的生命姿态与思维方式都是在这三重维度中产生的。一方面是“诗化”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就是思维上的跳跃性。“诗化”的人生态度是对诗歌抒情性的重视,对人生诸多方面积极乐观、天真质朴的追寻。他对“盛唐气象”的推崇出于其“博大的胸怀”,对建安风力、少年精神、布衣情怀的重视也源于此。这种“诗化”并不全然代表着乐观,林庚并没有忽视占据了人生一半的忧患,但他仍然更倾向于昂扬向上的这一面。林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批判时,仍然继续写诗、撰文,不断完善自家独创的“布衣感”“少年精神”“盛唐气象”[27]就是一例。作为生命态度的“诗化”和作为诗歌语言的“诗化”虽然在具体内涵上有所区别,但在核心理念上是共通的。“语言诗化”是为了使新诗创作能够“于最平实的生活中获得那原始的活力”[28],为了诗歌语言本身的特性能够不受拘束地“解放”开来。而生命态度的诗化所直接导向的就是一种思维与行为上不受束缚的天真的解放。
另一方面,“跳跃”既是诗歌中的形式技巧,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必须主动地凝聚力量去跳”,“可能唤起我们埋藏在平日习惯之下的一些分散的潜在的意识和印象”[29]。这种思维方式对林庚的新诗创作与古典文学研究都有影响,在创作中作为一种具体的技巧被林庚广泛运用于新诗之中。在对诗歌格律的探索过程中,林庚更加强调“跳跃”的重要性。他在最早实验四行诗时说:“自然诗的声韵不只是形式本身的悦耳,且有时也可辅佐着诗意。”[30]韵律不仅构成了诗歌的形式,同时还是一种诗意的钩沉。这种诗意其实就是韵律构成的节奏感所带来的想象跳跃唤起来的,“它的有规律的均匀的起伏,仿佛大海的波浪,人身的脉搏,第一个节拍出现之后就会预期着第二个节拍的出现,这预期之感具有一种极为自然的魅力”[31]。从思维自主的跳跃到由节奏去帮助思维的跳跃,从而达到更加广漠的自由。正因此,诗歌的格律在林庚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探索,他“通过格律问题在思考诗歌内容与形式以及风格之间的关系”[32]。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跳跃”则变为一种抓主潮的研究方式。林庚认为只有抓住了“主潮”,我们对文学历史的理解才不会偏离根本。这样就导致一些细微方面在林庚的文学史研究中或许会被忽略,比如“深入浅出”的语言特色或许并不符合所有唐诗的写作特点⑥,但林庚在“诗国高潮”这一观念的统摄之下,将之概括为唐诗最主要的美学特色,并以此来反思新诗语言的问题。可以看出,“学”“诗”“术”给林庚带来的是一种扩展性的生命体验,在这三个维度中,林庚能够融合各方面的差异,寻求其中具有延伸性的共同特质,使其几个向度(新诗、唐诗、楚辞、文学史)的构建都充满诗性与活力。尤其是其中的新诗,不再是单向度的发展,而成为带有历史延伸性的文体。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相得益彰、相互激发之间,其中所隐含的矛盾性是对林庚的新格律诗探索产生质疑与肯定这两种极端相反的态度的原因。
从新诗自身的发生来看,新诗与旧诗互相割裂是既成事实,无论在语言,还是在审美追求上,新诗与西方资源都比新诗与古典资源具有更深切的联系,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明是商籁体(Sonnet)在新诗中的影响程度远比“九言诗”要高。对林庚的新格律诗实验,历史上具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戴望舒就直观地认为“四行诗”是“新瓶装旧酒”[3],而与这种否定林庚的探索完全相反的观点是,“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33]。这种肯定或许是以对新诗西化的质疑为前提的。
如果不考虑他人的观点,仅仅从林庚自身的诗学体系内部出发,林庚确实并非在一种完全的现代性视野下来进行古典诗歌的研究和新诗理论探讨。一方面,林庚对古典诗歌的赏析往往带有本身作为一名写作者的会心,但其解读更倾向于一种“诗话”式的点评,很少掺杂西方理论。另一方面,林庚的新诗理论建基于一种“诗化”的人生态度,这种对生命“浪漫性”的追求往往大于林庚构建的格律诗学体系,即我们在探讨林庚构建的新诗理论时,必须时时兼顾林庚对诗的纯粹性、抒情性的重视。因此有学者认为林庚的文学史论述可以说是陈世骧等人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先声[34]。
新诗资源的驳杂与本身边界的扩展,都导致新格律诗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式微,“由于格律在本质上,是诗歌中通过重复、回旋或呼应而形成的一种语词现象,它实现的既是字音的相互应答,又是情绪的彼此应和,因而毋宁说,自由诗的‘格律’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一种特别的韵律和节奏。也就是说,谈论自由诗的‘格律’,其实是谈它的变动不居的韵律和节奏”[35],这种将一种硬性的格律要求变为对个性化的韵律和节奏的追求,显然更加符合新诗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林庚的诗学体系中,“语言的诗化”具体为“词汇”“语法”“句式”三个方面的“诗化”,虽然也将“诗的新原质”纳入了考虑范围,但总体而言仍然很难冲破“格律不是束缚”的魔咒。当然就新诗自身而言,林庚所追求的“自然诗”对诗的“明朗性”的重视,仍然是值得反思和重视的观念。
林庚作为“学者型诗人”与“诗人型学者”,在“学”“诗”“术”三个维度中均建构起独特的研究与写作体系,除提供了一种具体的知识建构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三重维度的互动与回旋构成了一种特别的现象,对我们以此重新认识新诗扩展的活力有重要意义。纵观林庚在新诗创作与文学研究之间长达一生的互动,如果说没有一颗赤子般对诗的真心,便很难在争议与波折之中坚守本心。尤其是体现在林庚本人身上的浪漫诗品,是他一切文学活动的基础,“边城”心态[36]等等都只是暂时的,“窗下的读书人”才是一幅永恒的画面。这种浪漫诗品,不仅是林庚人格上的精神底色,也是穿行于创作与研究当中的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诗品”存在的新诗人林庚,不管其探索最终有没有起到影响新诗发展进程的作用,都提供了一种在中西之间,在断裂之下努力构建新的诗体的经验,这种“诗品”或许才是新诗曲折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质。
注释:
①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周作人从写出“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杰作”到后来的杂诗写作,俞平伯后期转到旧体诗写作与《红楼梦》研究,胡适转向“整理国故”,程千帆转向古代文学研究等。
② 这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尤其是对《中国文学史》的评价,其中叙述的诗化特征与其他特点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了研究界的认可。可以参看王瑶、朱自清等人的评价。
③ 日后废名在《谈新诗:林庚同朱英诞的诗》一文中又强化了这一观点。
④ 1931年,林庚毕业之后辗转到大学任教,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这个契机促使他更加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古典诗歌。
⑤ 解志熙在收录时有所校对,此处沿用解志熙校对过的文本以便阅读。具体参见书中第121页注释④、⑤。解志熙:《林庚集外诗文辑存》,《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4月第1版,第121页。
⑥ 在2018年10月于北京举办的“四十年代的国家想象、地方经验与文学形式”学术研讨会中,冷霜提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