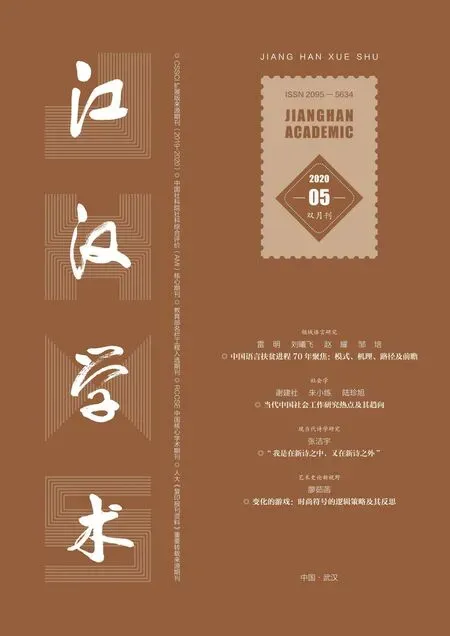日常审美体验与陌生化公共艺术
王洪义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上海 201620)
从最初在户外设置艺术品到现在的社区艺术活动,国际公共艺术的发展趋向是从街区到社区、从精英主导到大众参与、从专门观赏活动到日常生活景观。从审美角度看待这种艺术类型的成长,可知人类社会正经历从艺术审美到日常生活审美的巨大转变①,公共艺术在功能和形式上随时代而变迁正是当下日常审美思潮中的一种类型化反映。
有关日常审美中“美”的概念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为关于“什么是美”的问题一直是美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此处难以详论。但对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经历的审美体验而言,至少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是身体感觉,即当我们的身体感官受到外界刺激时,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刺激的存在,比如烘烤食物的气味,皮肤接触冷热温度的感觉,被按摩或撞击的感觉;这些感觉也可能源于自身活动,如跑步、切菜、使用工具等。人们对这些感官反应是否纳入审美体验范畴会有不同看法,但许多当代艺术正是依靠这种身体反应才得以完成,如包括烹饪、饮食和观众身体参与的行为艺术。另一个有关“美”的问题是它的敬语(honorific)属性,这导致“审美”一词通常会在积极意义上被使用,审美活动也会因此被视为一种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体验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在艺术审美活动中(如观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或聆听一场精彩的音乐会)所能获得的强烈的、积极的审美体验,与日常生活中一般对象或活动对我们的影响不是一个等量级,因为后者是平常的、特征不明显的或因过于熟悉反而熟视无睹的,很难给我们以心灵的震撼。还有一些物体和现象给我们的感官反应甚至是丑恶的、可怕的,足以冒犯和干扰到我们。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假如日常生活中的对象和活动都是常见的、普通的、平凡的、例行公事的,我们如何能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审美体验而不仅仅是日常反应呢?
西方日常美学理论(Aesthetics of the Every-day)对此给出解答,那就是实现日常审美需要陌 生 化(defamiliarization)、陌 生 感(making strange)或光晕(casting an aura)②的介入[1]。这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为应对生存需要,只能基于实用主义立场进行判断和付诸行动,这样的人生过程会让我们忽略日常对象和活动中的审美潜力,而一旦我们以一种不同的态度或感知方式去体验它们,我们就能在最普通和最常见的事物中体验到美的存在。而若想获得这样的对日常事物的艺术审美体验,最好的办法是让日常事物以陌生化面貌出现,因为被陌生化的日常事物就不再是日常事物而成为了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这种通过陌生化手法变日常事物为艺术表现的手法,正与当代公共艺术为大众日常生活提供艺术审美对象的目标相一致,因此陌生化方法也就自然成为当代公共艺术的主要创作模式之一。那么在这个公共艺术创作模式中包含了哪些具体的陌生化创作手法?通过陌生化手法改变日常事物平凡属性以获得审美体验,是否意味着日常生活中平凡事物本身并无审美价值?下面我将结合日常审美理论对当代公共艺术中的陌生化创作现象略加介绍,也对日常审美与艺术审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个人初步看法。
一、作为创作模式的“陌生化”
这里说的“陌生化”,是指原本很熟悉的日常事物由于形式或功能上的改变而让人感觉不熟悉、异样甚至惊骇;而所谓“日常事物”是指以艺术为审美中心的理念中所不包括的审美对象和活动(看展览、听音乐会不算日常生活),即被普遍认为与艺术审美毫无关系的日常生活内容,如为满足吃穿用住等基本生存需求的事物和活动,如炊具、卫生工具和劳动工具等物品,或者吃饭、梳洗、穿衣和清洁等日常活动,当然也包括并非频繁发生的活动,如聚会、体育赛事、假期、婚礼和旅行。总之,“日常生活”就是指那些超越个人和文化差异的人类普遍活动。这样的生活内容,往往有重复、常见、普通、平淡、人尽皆知、缺少刺激等特征,因而对置身其中的人缺乏明显的感染力,与我们在艺术审美体验中所能获得的惊险刺激和美轮美奂有明显差距,这也就是人们通常不会将日常生活视为审美对象的主要原因。
但有一点也需要注意,是日常生活中不但包括那些大量存在、按部就班、缺乏艺术性的普遍活动(如饮食、穿衣、洗漱等),也包括未必频繁出现却被普遍认为是有艺术性的日常活动,如节日庆典中的多种审美考虑、家居内外的装饰美化或出席重大活动的服饰礼仪等,这些虽然也属于日常生活内容,但会更偏重审美而不仅仅是实用的考虑。由此可见,我们的日常生活本来就是由看似不同但实际上互有关联的两类活动构成的,一类是以实用为主导的功利性活动,另一类是以审美为主导的非功利或次功利活动。我们不妨把日常生活看成相互联系的两端,一端是从务实和利益角度看到的世界,另一端是有意识地从审美角度看到的世界。对后者而言,即便是在看起来与审美无关的日常普通事件中,也存在着获得审美体验的可能。这是因为,对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审美体验或进行审美活动而言,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审美对象是否存在,而是我们面对日常生活的立场和态度,是“态度决定一切”,即“日常审美的问题不是指这个物体的形式美或不美,而是要追问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什么关系使对客体的这种特殊体验变得美”[2]。在提香(Titian)的油画《丹娜伊和黄金雨》(Danae and the Shower of Gold,1550’s)中,宙斯化身的黄金雨,对丹娜伊来讲是爱情的象征,但对丹娜伊身边的女佣来讲则是天上掉下来的硬通货。由此可见,如果只依据实用主义立场感知日常生活,眼前能看到的恐怕都是普通平凡之事,自然就会忽视日常生活中所存在的审美潜力。因此,对日常审美体验来说,最核心、最重要的,不是它包含哪些特定的对象与活动,而是我们观察它、认识它的视角和心态。这也就是美学态度理论(aesthetic attitude)所阐明的,在理论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审美体验对象。况且,对不同的思维主体来说,日常生活所显现的面貌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还会因为不同的职业、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而格外明显——假如我居住在五星级景区里,那么景区风景对我来说就是日常所见,而并非千里迢迢赶来还要购买昂贵门票的游客眼中的奇山异水;假如我的工作是博物馆里的清洁工,那么观看伦勃朗画作也不过是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艺术专家们所理解的意义非凡的艺术观赏活动。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计算概率,恐怕所有人间事物都可以包括在日常生活范围里。所以,如果仅从具体事物和人的活动上看,我们其实很难判断什么是日常生活什么不是日常生活,也没有人能开列出日常生活所能包含的所有事物的清单。最普通的生活经验也能告诉我们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某事某物对某一类人可能是艺术性的审美活动,对另一类人却只是日常生活,反之亦然。就像种菜对郊区农民来说是日常生活,但对城市居民来说可能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因此他们会付费去参加包含种菜内容的旅游项目(如去植物园工作一天)。难得,罕有,会带来陌生感,而这种陌生感,恰恰是将日常生活事物转换为审美体验对象的枢纽机关。
作为艺术创作模式的“陌生化”,是通过改变熟悉事物的外观形态、功能用途或生存语境,有效去除基于实用考虑而丧失审美情趣的人类精神惰性的一种常用手段。它能够击碎人们面对实用且熟悉的事物所产生的习以为常或熟视无睹的消极反应,激活人们面对日常事物的新鲜感和探索欲。20世纪初期俄罗斯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是通过“陌生化”手法实现的,他们认为“陌生化”是与日常生活的“自动化”体验相对立的,它是艺术家有意识地对文本施加日常偏离的过程[3]。宗白华也说过“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像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像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4]。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陌生化是要打破日常感受的定式,冲破习以为常的认知惯性,“创造性地损坏习以为常的、标准的东西,以便把一种新的、童稚的、生气盎然的前景灌输给我们”[5]。当代艺术创作中有很多艺术家采用使熟悉事物陌生化的手法,取得点石成金、变废为宝的艺术效果。其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杜尚(Duchamp)名作《泉》(Fountain,1917),通过改变语境(将小便池从卫生间移到展览会)和去除实用功能的方法,让熟悉的事物出现陌生面貌,从而改变事物的性质:生活用品成为艺术品,生活事件成为艺术事件③。
二、公共艺术中制造陌生化的几种艺术手法
可以说,无论什么流派的视觉艺术都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别无二致,都是一种有意识地对现实生活的修正、改变乃至抽象,而在艺术中实现陌生化的目标,就更需要使用偏离常态和夸张变形等形式手段,对人们司空见惯的平凡事物进行艺术加工处理,才能让平凡事物显现出不平凡的光辉。从制作技术层面上说,对平凡事物进行艺术处理就是要从形式上对原型进行改造,这也是陌生化艺术创作模式的要义。可以说,没有形式改造就没有陌生化效果,没有陌生化效果就无法引导人们从艺术审美角度认识日常事物。况且,对日常事物是只有形式可以改造,内容是无法改造的(艺术家可以为画中的天使加上翅膀,而真实的人物是不会有翅膀的),因此,对日常事物的外观形式进行加工处理从而改变其常见性质而产生陌生化审美效果,是完成陌生化艺术的不二法门。下面将简单介绍几种在公共艺术中较为常见的陌生化创作手法,用以说明陌生化创作模式下的日常事物已不再有日常性质而是成为艺术表现对象,这也是本文标题中“陌生化公共艺术”的语义所在。
(一)改变形态
也就是常说的“变形”,一般是指在仿佛某种力学作用下出现的物体形状或体态的改变。这是艺术史中最常见的制造陌生化美感效果的手法,几乎出现在所有艺术大师的作品中,其变形程度的强与弱,或者变形方向上的积极与消极,则与时代、地域、民族性、流派、个人趣味等有关。如著名南美艺术家费尔南多·波特罗(Fernando Botero)的公共艺术作品以“胖”著称,超常肥胖的体态让作品中的人物和动物产生幽默感。德国英吉创意小组(Inges Idee)的《下一步!》(Next step!2017)是一个12米高的年轻学生行走像(图1),鞋子和腿被极度拉长变大,但躯干和头部仍然保持12岁儿童的常规比例;这个有卡通特征的校园儿童形象作为所有学生的榜样出现在校门口,他充满自信、迈着大步走向世界。

图1 英吉创意小组:下一步!2017年,德国慕尼黑
(二)改变体量
生活中万事万物会各有各的体量,不同体量的设定与实用需求有关,通常是固定的,轻易不会改变,因此人们会形成对司空见惯的事物固定体量的认知,也就不会格外关注它的审美意义。但如果有艺术家明显改变了日用品的体量,将普通物品极度放大或缩小,就会使人因意外而获得惊喜,也能提醒人们对身边日常事物有所关注。这种借助改变日常事物的体量而营造艺术审美对象的艺术表现手法,因能带来骇人眼目的视觉效果而经常被艺术家所采用。如欧登伯格和凡·布鲁根(Oldenburg and van Bruggen)的《苹果核》(Apple Core)和草间弥生(Yayoi Kusama)有名的《南瓜》(Pumpkin)都无例外地使用了这种方法(图2、图3)。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的周游世界的《大黄鸭》(Rubb Duck)甚至成了某种公共娱乐事件,其基本创作手法也不过就是把一个简单的动物形体极度放大而已(图4)。而笔者在公共艺术专业的教学实践中也多次使用了这种方法(图5)。

图2 欧登伯格和凡·布鲁根:苹果核,1992年,美国

图3 草间弥生:南瓜,2016年,美国

图4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大黄鸭,2013年,香港

图5 方雪影、钱韵:几何形体,2018,上海
(三)改变功用
事物的功用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存在价值,茶杯用来喝水,钢笔用来写字,台灯用来照明,各有各的实际用途。但按照康德的说法,艺术是无功利之物,所以去除日常生活中平凡事物的实用功能,赋予其与实用功能无关的审美属性,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实用的生活物品变成了非实用艺术品。其中使日常物品脱离生活空间进入公共空间进行陈列的方法,会让观者产生既熟悉又陌生的异样感,从而产生艺术化的审美体验。如英国曼彻斯特公共纪念碑和雕塑协会(Public Monuments and Sculpture Association)将工厂里废弃的内史密斯蒸汽锤(Nasmyth Steam Hammer,1917年设计)竖立在街头:在工厂里被废弃,是因为已失去实用价值,而重新出现在街头,意味着转型为公共艺术作品,功能效用的改变,让曾经的废弃物变成工业城市的历史纪念碑(图6)。中国艺术家宋东的《物尽其用》(Waste Not)通过对中国家庭中大量日常用品的去功用转化,而真正使其在审美意义上实现“物尽其用”(图7)。该作品由其母亲多年来积攒的上万件生活用品组成,包括旧肥皂、烂布头、破损的儿童玩具、过时的书籍报刊、空饮料瓶、锅碗瓢盆等。巫鸿在为此展览写的前言中说到“物的转化”——实用品变成了艺术品,从私人空间转入公共空间,由此使这些平凡无奇的日用品与艺术建立起新型联系[6]。

图6 内史密斯蒸汽锤,1917年设计,1981年移到现址,英国

图7 宋东:物尽其用,2013年,悉尼
(四)改变质感
质感是艺术最为表面的形式(通常与材质有关),改变任何事物的固有质感都能带来明显的陌生感。正如女明星到了一定年龄还是皮肤细腻娇嫩,人们就会揣测她是否做了整容手术;如果橘子皮不是布满褶皱而是光滑如丝,人们也不会认为这是橘子。由此可知,只需让平凡事物改变外观质感即可收到明显的陌生化效果。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小狗帕奇》(Puppy)和《气球狗》(Balloon Dog)使用了不同于原型的材质:用花卉类植物制作小动物形象,用镜面不锈钢模仿乳胶,因而产生了新颖离奇的陌生化效果(图8)。詹姆斯·迪弗(James Dive)在澳大利亚悉尼海滩上制作的《融化的冰淇淋汽车》(Melted Ice Cream Truck),针对全球变暖这一日益严重的现实问题,通过有冰淇淋融化效果的瘫软汽车造型,夸张表现汽车由于高温而融化的特异景观(图9)。虽然这件作品不是真由冰淇淋制作的,但却通过模仿冰淇淋特有的融化形态使作品有强烈的震撼力。

图8 杰夫·昆斯:小狗帕奇,1992年,西班牙

图9 詹姆斯·迪弗:融化的冰淇淋汽车,2006年,澳大利亚
(五)改变语境
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认为任何艺术品都不具备永久的身份,一个事物在某些时候是艺术品,在另外一些时候却不是,该事物是否属于艺术品与其所处时间、空间的语境条件有关。所以我们不应该追问什么是艺术品,而应该追问是何时何地何种条件使之成为艺术品,即便是毕加索的名画,如果不被置于艺术语境中来看待,那么也只是一个物性的存在而并非是艺术品[7]。由此可知所谓“语境”(Contextual)是能决定作品属性和含义的重要外部条件,艺术作品只有依赖于语境才能产生意义,而改变事物存在的语境也就自然会使该事物丧失其原有意义而产生新的意义。就像“祭坛”(Altar)本是供奉神灵的建筑形式,通常会伴随着宗教圣像而设置于教堂或神庙中,但瑞士艺术家托马斯·赫西霍恩(Thomas Hirschhorn)在四个城市中所创作的祭坛却出现在城市的角落中。这些祭坛由蜡烛、鲜花(通常用透明纸包裹)、泰迪熊和填充动物玩具、写有爱心和其他象征的纸片构成,这些日常事物在改变语境后变得无比庄严(图10)。作者在解释创作意图时说,大多数人不会死在广场中央或美丽的大道上,即便是名人也不会死在“中心”,无名者与名人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他要通过这些祭坛的形式、位置和持续时间对纪念碑的地位提出质疑④。毫无疑问,这些临时街头祭坛是由日用品与其所处城市环境共同构成的,变更背景环境的做法使这些低档日用消费品充当了深刻思想的载体。
(六)制造残缺
有关“残缺美”的理论讨论一直存在,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看法,但在艺术实践领域不但没有争论而且早就成为惯例,艺术家们为求新颖效果常常会有意制造“残缺”。最明显的案例是米洛岛维纳斯的断臂至今没有被修复,不被修复的理由是普遍认为各种修复计划都不抵保留雕像的残缺状态更有美感。澳大利亚艺术家彼得鲁斯·史邦克(Petrus Spronk)的《建筑残片》(The Architectural Fragment,1992)安置于墨尔本市维多利亚国家图书馆前面,作品以这种倒塌和下沉的破败形式寓意文明的衰落和时光的流逝,以倒塌的屋檐一角与真实的图书馆建筑的稳固厚重形成强烈对比(图11)。法国艺术家布鲁诺·卡塔拉诺(Bruno Catalano)的《旅行者》(The Travelers)是一件唤起记忆的公共雕塑,以身体中心的巨大空缺的形式,表达每一位旅行者在离开旧地前往新地点时,都会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一部分留在当地。这种大面积残缺的人体样式显然也会让观者感到陌生和奇异(图12)。

图10 托马斯·赫西霍恩:蒙德里安祭坛,1997年,瑞士

图11 彼得鲁斯·史邦克:建筑碎片,1992年,澳大利亚

图12 布鲁诺·卡塔拉诺:旅行者,2013年,法国
以上数个案例能说明“陌生化”已是当代公共艺术的一种创作模式,有多种类型和较为广泛的适用性,在陌生化这个模式下完成的公共艺术作品已经成为连接我们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审美体验的桥梁和纽带。那么为什么与熟悉的日常生活相比,陌生化之物更具有审美价值因而会成为艺术表现对象呢?彭锋论述审美对象的一段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并不像某些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符合某种美的定义(比如比例)的事物就是审美对象。经验告诉我们,很多符合某种比例的事物并不美,而很多不符合某种比例的事物反而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欣赏对象。此外,也不像另一些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符合自身概念的事物(比如一头刚好符合鲸的概念的鲸)就是审美对象。如果一个东西与描述它的概念完全吻合,我们只会说它真而不会说它美。只有当一个事物突破我们习惯描述它的范畴而又吻合或愉悦我们的认识能力时,我们才会发出“美”或“啊”的惊叹。审美不是依据概念(无论是美的概念还是事物本身的概念)来审察对象的认识,而是超越任何概念束缚的体验。审美对象是无概念的,这并不是说审美对象是某种人类迄今为止尚未认识的事物,而是指事物在我们尚未用概念来描述它之前的那种活泼泼的状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审美对象不是某种特别的事物,而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某种特别的状态。[8]
由此可知,经陌生化改造的日常事物之所以能获得新的美学价值,就在于这个被改造的日常事物已超越任何概念的束缚,突破了我们对它的习惯认识,使之从合规则、合比例、合概念状态进入到“某种特别的状态”——陌生化状态,由此才能呈现出活泼和真实的美感。事实上,陌生,就是不合常规和不合定义,就是不为固定概念所包含和描述,它恰恰是任何事物都可能有的某种特别的状态,是让平凡事物脱离平凡、实用事物脱离实用的特别状态,由此才能将日常生活体验转换为艺术审美活动,而我们也只有在面对有陌生感的日常事物时,才能从长期形成的审美疲劳中清醒过来,发现最常见的日用品也可以给人带来意外和惊喜,从而实现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说的“‘审美化’基本上是指将非审美的东西变成、或理解为美”[9]。此外,在这个创作模式中我们还需知道,所谓陌生化不是让人素不相识或无法辨识,而是要让陌生与熟悉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以陌生化面貌出现的艺术作品要同时包含陌生与熟悉两种生活信息,既要前所未见,又要保留平凡事物的基本特征,而不能只有陌生没有熟悉。这样才能符合朱光潜所说的“不即不离”的审美原则,即艺术要与实际生活保持适当距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这样才能用美感的态度去感知事物,用熟悉的生活经验去印证艺术,“艺术的理想是距离近而却不至于消失”[10]。上述这些案例都毫无例外地兼具陌生与熟悉两种状态,所以才获得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
三、陌生化与日常审美
通过陌生化创作模式让人们从日常事物中获得美感的做法,与人类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人们对自己熟悉的事物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但对于陌生事物往往有好奇心理,也常常会被新鲜事物所吸引,所以“人生若只如初见”永远是美好的,“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永远是难免的。尤其在影像媒体霸权和商业消费热潮裹挟下的快节奏现代生活中,在商业资本使用全方位包装手法将日常生活变成景观诱惑的大背景下,大量以复制为生产方式、以平均化为审美标准的大众娱乐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已经成为控制社会群体性审美反应的主要力量,使人们面对熟悉事物时很难有自主判断的可能,在很多时候甚至只能产生一种类似机械化的自动反应。而致力于将日常事物改造为艺术品的“陌生化”公共艺术创作方法,通过对日常生活审美和艺术审美的双重能量的发掘与置换,既能让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得以更新,又能让我们的艺术审美体验与日常生活经验不至于偏离太远,由此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对日常事物的非概念性感知能力,使我们在面对日常平凡事物时不再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从而摆脱受商业力量控制的自动反应式审美,在日常生活对象和活动中获得有新鲜感的审美体验。
能让平凡事物获得“光晕”效果的陌生化艺术作品,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积极和健康的意义:首先,它赋予日常生活对象和活动以震撼的审美体验,由此揭示了在日常生活中被忽视或漠视的平凡事物的美感潜能;其次,它帮助我们摆脱在消费社会中形成的实用主义、等级化和机械化审美定式,打破平凡的、不值得纪念的日常事物与商业化的精英艺术之间的审美级差;最后,它鼓励我们从审美角度认真对待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增加现世生活的满足感而且没有引导奢侈消费的弊端。但这样也带来另一方面的理论问题,即陌生化公共艺术的价值实现前提是传统美学中以不熟悉、非实用的事物为美的理论,陌生化的作用是变熟悉为不熟悉、变普通为不普通、变日常为非日常,这些日常的和平凡的事物是由于不再日常、不再平凡才获得审美意义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熟悉、普通和平常事物的审美价值的否定?如果将陌生化即非日常化作为审美先决条件,那么在我们一生中占比最大的平凡工作和日常生活就会成为审美体验的盲区,会使我们忽略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诸多对象与活动的审美价值,我们就难以获得在日常生活中一定存在且随时出现的以熟悉、普通和平凡为特征的审美体验。因此,如何在打造陌生化审美对象的同时也能保留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之美?也就成了陌生化审美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
西方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将熟悉和普通的日常生活视为一种与刺激性的陌生化体验相对应的、有相辅相成意义的审美体验过程。如芬兰美学家哈帕拉·阿托(Haapala Arto)认为,当这些普普通通的日常凡俗生活为我们提供一个平静、舒适、稳定和安全的生活体验后,我们才有可能享受非凡、紧张和短暂的陌生化审美[11]。美国学者谢莉·欧文(Sherri Irvin)认为那些看似重复、平常、少变化的日常状态,就像家庭生活一样能够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舒适和稳定的条件,平静生活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日常审美意义,也是值得欣赏的[12]。其实凭一般生活经验也可以想象出,假如我们没有普通、常见、熟悉和相对静止的日常生活状态,只有连续不断地、非凡的、紧张的特殊经历,我们是否还能有心情或有条件对陌生化事物给予足够的关注?虽然在一些经典论著中会把平凡的日常生活看成单调、乏味、枯燥、毫无美感可言⑤,但如果从分类而非敬语意义上理解“审美”,就能知道即便是不具备积极的审美品质——刺激性强、叙事结构连贯、主题统一的事物,也未必就不具有审美体验价值,毕竟缺乏连贯结构、散漫、单调和平淡本身,也是可以成为日常审美体验对象的。这是一种以平凡为特征的日常审美体验类型,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休闲活动就建立在这种审美体验基础上。入选《咬文嚼字》2016年十大流行语的“葛优躺”,或许可作为对这种非敬语意义的、消极的、慵懒式审美类型的形象表征。或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美”的理解,应该回到鲍姆嘉通所提出的“美学”(Aesthetics)一词的原初意义,即通过感性获得的经验,无论它的价值是什么。总之,不论是司空见惯的日常审美,还是有强烈震撼效果的艺术审美,都是同一事物(生活本体)在不同方向上的精神展现,它们共同构筑了今天充满矛盾意味的日常生活。而通过陌生化手段将日常平凡事物转变为艺术审美对象的公共艺术创作模式,算得上构造日常生活经验与艺术审美体验连续体的一种类型化手段。
公共艺术的宗旨是为大众日常生活提供艺术审美对象和活动,其发展趋势是艺术与生活的融合。日常生活审美与艺术审美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通过艺术手法营造陌生化效果正是帮助人们从日常审美过渡到艺术审美的运转中枢,其具体操作手法则包含体量、功用、质感、语境和形象完整性的改变等。陌生化创作方法能构造从日常审美经验到艺术审美体验的连续体,赋予日常凡俗生活以新鲜感和刺激性,改变人们对日常事物因熟悉而漠视的惯性思维,有效去除由于审美疲劳而产生的冷漠与消极的体验感,实现以艺术创造抗拒消费社会中自动化、平均化审美体验的社会目标。与日常生活不即不离的陌生化艺术让普通的日常生活不再乏善可陈和黯淡无光,其扩展审美体验范围和人生思想境界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这样做也有理论上的不易周全之处,有可能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中造成对敬语意义上的艺术审美价值的削弱。对此我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所论未周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① “艺术审美”是指以日常生活之外观赏艺术品和参加艺术活动为审美体验,如观画展,听音乐,看演出,其理论基础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日常生活审美”是指以在日常生活之中获得对美的直观感受或经验为审美体验,其理论基础是“艺术等同于生活”(art equals life)。
② Aura汉译为“光韵”或“光环”,是本雅明(Benjamin)在其名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提出的术语,指的是被现代大规模复制技术所消解的独特的原创作品所拥有的神圣性和仪式感。神圣性代表着艺术品不同于世俗物品之特性,是艺术审美的存在基础。仪式感根植于圣像或偶像崇拜仪式中造成距离感的宗教体验,即人们只能在一定距离外瞻仰或膜拜艺术品,而不能将其拥有或占有。一旦艺术品生产方式脱离了这种神圣性和仪式感,转向可技术复制的批量生产,艺术的“光韵”也就烟消云散了。
③ 1917年5月,杜尚和他的两个朋友共同经营的前卫杂志《盲人》(The Blind Man)发表了一篇匿名社论,在解释这种“现成品”时说到三个要点,其中之一是取消一个物体的“有用”功能,使它变成了艺术。见英国泰特美术馆官网介绍:https://www.tate.org.uk/art/art-terms/r/readymade.
④ 见托马斯·赫西霍恩官网介绍:http://www.thomashirschhornwebsite.com/statement-altars/.
⑤ 如黑格尔把日常生活看作是平庸和乏味的,散文气息(prosaic age)是其主要特征。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0-148页。尼采把艺术看成是一种强力意志的形态,认为艺术并非以幸福和情欲为目标,而是以强力为目标。见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