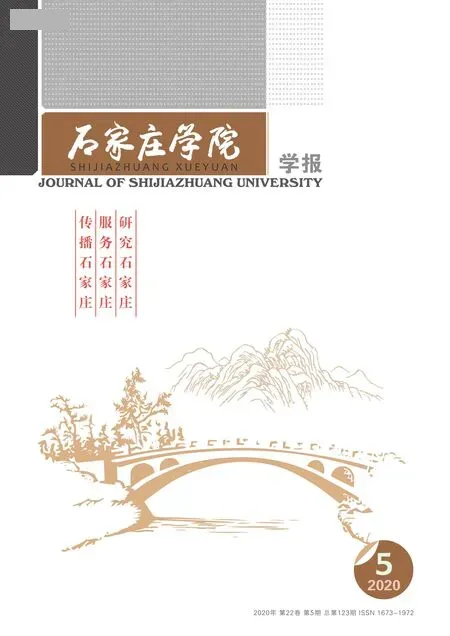从技术统治走向技术民主化
——《启蒙辩证法》的技术观及其后续影响
刘光斌,石夏丽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霍克海默(Moriz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启蒙辩证法》揭示了人类按照征服自然的方式征服人类社会的统治逻辑,探讨了合理性与社会统治的复杂关系,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中形成了“工具理性”范式。后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从不同方面反思和超越第一代“工具理性”范式,在各种理论方案中产生了一条从技术角度延续和超越第一代批判理论的发展方案,最终从理论上引导技术统治走向了技术民主化。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使用技术理性逻辑解释了《启蒙辩证法》的社会统治主题,不同于《启蒙辩证法》的悲观论调,他认为一种新技术理性有望摆脱社会统治困境。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思考影响了芬伯格(Andrew Feenberg),他深入反思了《启蒙辩证法》中的统治主题,并推进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政治主题的研究,他认为人们可以对技术发展作出新的选择,主张把技术发展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最终从理论上实现了从技术统治向技术民主化的转变。从《启蒙辩证法》对技术统治的分析到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策略,反映了《启蒙辩证法》技术观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续影响,也表明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已经扭转了早期《启蒙辩证法》中有关技术统治的悲观论调,对技术发展提出了一种民主化的乐观方案。
一、《启蒙辩证法》中社会统治的工具理性逻辑
《启蒙辩证法》揭示了启蒙要摧毁神话却倒退成为新的神话的主题,人类通过掌握自然规律,推进技术进步并以此摧毁了神话的基础,然而人类在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工具理性逻辑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之中,导致人对人的社会统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统治的合理性与工具理性逻辑紧密地结合起来,呈现出人类遭受统治的现状。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知识和技术是人类摆脱自然控制、获得解放的主要依托。就知识而言,他们指出知识已经成为启蒙的合法性认证,体现了人类的优越性。他们引用培根的观点进行佐证:“人类的优越就在于知识。”[1]2他们认为培根的观点与流行的科学观念相辅相成,启蒙理性得到广泛传播,这是人类获得解放的重要条件,知识已经成为启蒙的合理性,主要采用概念和图景解释世界。就技术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技术是方法,“技术是知识的本质”[1]2。人们通过知识的技术性运用,能够把技术应用于自然以达到利用自然并全面地统治自然的目的。可见,知识并不只是向人们展示真理,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和实现人们的目的,也就是说发挥知识在技术操作中的作用。由此看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知识和技术已经成为启蒙的合理性,社会进化的过程被解释为知识和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相比较于神话的蒙昧而言,启蒙的这种新的合理性以实现人们的解放目标为指向,但其实质只是工具理性的合理性。
在《启蒙辩证法》中,人们用知识取代了神话幻想,推动了工具理性的发展。人们用神话解释自然是因为早期人类没有掌握有关自然的知识,并因此对各种自然现象产生畏惧心理,人类获得了知识、掌握了自然运行的规律就不再惧怕自然。神话以神人同形同性为其理论依据,各种神灵只不过是人“畏惧自然现象的镜像”[1]4。人类用神话解释自然是因为人类无法解释自然现象,从而对各种自然现象产生恐惧心理,恐惧的表达变成了解释自然界中陌生之物的方式。在神话的自然中,人不可能获得自主性,也不可能摆脱自然的控制。人类为了克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广泛应用启蒙的知识和技术,这进一步为人们摆脱神话自然提供了可能,也不断促进了“工具理性的增长”[2]81。可见人类努力去获取知识不是以求知为目的,而是把获取知识作为人类解决难题的手段,是为了实现人的目标,可见启蒙理性就是工具理性,为启蒙奠定了合理性,启蒙理性的发展是为了使人类摆脱对自然的恐惧,为了人的解放。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理性不仅成为人类统治自然的重要工具,而且成为统治人类社会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启蒙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新的神话。由于启蒙的工具理性与神话的统治有着天然的联系,启蒙演化成一个新神话,这形成了启蒙与神话的二元对立及其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疏远神话意味着追求解放,启蒙成为新神话又妨碍人们追求解放。工具理性的应用使人类摆脱对自然的恐惧,使人类统治自然变得可能,与此同时,人们必须从内心接受理性的思维方式,使自己的行为按照规律办事并进行自我约束,于是对个人内在自然的控制变得可能。可见,随着启蒙工具理性的广泛运用,知识和技术的应用也变得越来越普及,统治成为《启蒙辩证法》的主题。具体来说,启蒙工具理性的广泛应用导致人对自然、个人和社会的全面统治。
首先,统治外在自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人类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和规律,自然在人类面前不再神秘,也就失去了魔力,人类利用工具理性统治自然,以统治者自居。马尔图切利(Danilo Martuccelli)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把理性和统治连接在一起的根源就在人统治和支配自然的愿望中”[3]205。随着知识的进步,启蒙工具理性的广泛应用,人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征服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也逐渐地改变了早期对自然的恐惧,人类统治自然变得理所当然。在神话走向启蒙的过程中,原来神话世界中的人与外在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
其次,统治内在自然。《启蒙辩证法》提到人们通过获得知识,便学会了规避自然带来的危险,支配自然变得可能,但付出的代价是造成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分裂,因为现代人是通过控制内在自然来征服外在自然这种方式获得自我的认同,这使得人类在摆脱自然控制的同时陷入到自身控制之中。可见人类并没有摆脱神话的施压,只是控制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个人只有按照规律采取行动,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们把掌握规律看成获取自己生计的手段,人们依据经验直觉行动到依据理性行动,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个人的自我规训过程,人们通过理性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也要求主体行为符合规律要求。
最后,统治社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统治外在自然和统治社会都依据工具理性逻辑,恰如霍耐特(Axel Honneth)所说:“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工具支配过程在社会内部的那种结构与之相似的投影。”[4]50人们用科学对待万物是为了统治自然,统治者只有了解人才能更好地去统治人。由于不平等分工,统治阶级使用作为所有者支配的权力工具,使用暴力威胁直接受压迫的主体服从命令,阶级统治强化了人对人的统治,而商品生产需要大量的生产资料又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关系,对自然的控制与对社会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社会中人对人进行统治的逻辑与人对自然进行统治的逻辑是一致的,即都遵循工具理性的逻辑对待人和物。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出于人的自我持存的生存需要,人们需要工具性地控制自然,同样为了人的生存需要和社会的存在需要,人需要对他人进行统治。总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知识和技术作为启蒙合理性形式的工具理性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和社会之中,解释了工具合理性与社会统治的复杂关系,然而,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没有提供一个摆脱统治状态的出路,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悲观的论调。
二、技术理性转化了《启蒙辩证法》的工具理性逻辑
马尔库塞主要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了与《启蒙辩证法》相似的主题:现代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统治。马尔库塞主要把由技术进步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发达工业社会,并解释了技术理性的统治效应。马尔库塞遵循了“《启蒙辩证法》所开启的思路”[5]211,把工具理性发展为技术理性,以此分析社会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尔库塞开启了批判理论分析社会统治现象的新路径。
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理性的观点来自韦伯(Max Weber)的理性观。马尔库塞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韦伯的理性观。第一,它是经济理性。这种理性以获取更多利益为目的,强调经济生产和活动中的效率。第二,这种理性的基础是抽象活动。抽象的理性体现在对自然和人的可计算、有计划的统治中。第三,被运用于资本主义的各类管理结构中。整个社会科层制度都受理性支配,包括支配物和人的消闲与工作。总之,马尔库塞认为韦伯所说的理性是一个科学中立性概念,体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作为一种形式合理性,用来分析工厂和各类科层制度的运行效率,并实现对自然的控制和促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标准制约整个形式合理性体系,这些技术标准与手段的效率有关,因此,他明确指出:“韦伯所设想的理性,表现为技术的理性。”[6]81工业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主要奉行技术合理性的逻辑,政治领域内的官僚政治体系也遵循工具理性逻辑。马尔库塞指出韦伯的工具理性分析有其合理性,不过由于韦伯把理性视为形式合理性,从而与价值理性无涉,所以无法解释价值问题,但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承载了特定阶级的利益。于是,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应用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产生了统治效应,发挥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遵循技术理性逻辑,再现了《启蒙辩证法》中技术应用及其产生的统治效应。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化机器生产过程中,不仅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的技术性应用成为生产活动中的主要模式,而且人们形成了特定的行为模式。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在生产中应用的后果是,人们按照技术的需要组织起来,人们的行为需要适应技术的需要,导致技术理性变成了一种统治人们的力量。随着生产、社会生活领域中工具理性的应用,技术统治的逻辑在各个领域得以复制。
在生产领域,技术理性的应用产生了对人们的统治,形式上由直接对人们的统治转变为对技术的管理。人需要适应机器生产的需要,在生产过程中人不得不受到机器的控制。政府采取控制机器生产程序、操纵技术组织结构等方式间接地实施政治权力的统治。也就是说,政府只要高效率地利用现有技术,组织生产以及不断提高机器生产效率,那么就能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满足人们对物质等方面的需要,也就增强了人们对政府的忠诚度和认同感。马尔库塞指出:“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7]5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统治变得更加隐蔽,因为统治以管理机器的形式出现,管理者组织和管理好机器便能实现对工人的控制,似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发生了转移,变成了工人与机器之间的矛盾。不仅如此,技术和知识的应用还造成工人阶级内部的严重分化,表现为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职业分层,强化了“蓝领”工人向白领工人转化的趋势,并且通过鼓励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等方式,使工人对企业的认同感增强,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否定意识。按照马尔库塞的解释,技术组织和管理程序实际上体现了特定的利益,统治者不再直接控制被统治者,他们通过组织和操纵技术便能实现自己的控制,从而使得统治的形式变得越来越隐蔽。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已经从生产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领域。劳动力的消费对维护社会的再生产是不可缺少的,只有通过刺激人们广泛参与消费,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得以维系下去。发达工业社会既借助技术进步等方式推动生产,也积极采取措施刺激消费,并把刺激消费视为一种非暴力的卓有成效的统治形式。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不再采取直接的恐怖方式实施统治,代之以满足人们虚假消费的方式,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把社会强加的虚假需要变成自己的需要,人们不仅不会批判这个社会,反而认同这一发达工业社会,这一切离不开技术进步。正如马尔库塞指出:“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7]15或者说,“技术、技术设备及其应用总是与社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技术政治系统发挥作用”[8]。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与统治实现了高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表现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通过技术、机器等实施对人的统治,消费领域不断刺激人们追求过度的虚假消费,满足于技术带来的物质丰裕的消费,而且在政治领域,技术改变了统治的方式,恐怖、暴力统治不再是统治的标配,现代社会通过技术以更加隐蔽、更加有效的方式实施着对人们的统治。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对技术的服从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6]104
总之,马尔库塞解释了社会统治的技术理性逻辑。他说:“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7]15这个观点契合《启蒙辩证法》的统治观。不过,马尔库塞比较乐观,他认为摆脱社会统治并非完全不可能。马尔库塞提出新感性和大拒绝的设想。一种基于审美想象力的新感性有望摆脱社会的压抑,马尔库塞相信感性之解放的重要意义,感性之解放就在于人们的身体之解放,摆脱技术理性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控制。马尔库塞相信人们也可以采取大拒绝反对被控制和统治,“这个伟大的拒绝就是对不必要压抑的抗议”[9]134。大拒绝包括拒绝虚假需要、拒绝延长劳动时间、美学拒绝等,意在恢复感性,拒绝技术理性及其带来的统治效应。至此,马尔库塞摆脱了《启蒙辩证法》呈现出来的悲观论调,指出了摆脱技术统治的可能路径,这为芬伯格从政治层面摆脱技术的统治效应,走向技术民主道路提供了理论启示。
三、技术民主化提供了解决《启蒙辩证法》中社会统治的策略
芬伯格对《启蒙辩证法》和马尔库塞有关技术统治的主题进行了批判。首先,对工具理性的功能进行了批判。芬伯格认为,《启蒙辩证法》是从自我持存的生存论角度分析科学技术和工具性控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工具理性主要是在人追求自我生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指出在物质匮乏的社会中,人们为了自我持存的需要,必然工具性地对待自然和人,这一方面实现了技术对自然的工具性控制,另一方面技术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服务。芬伯格认为《启蒙辩证法》把技术视为一种工具理性,服务于人的生存需要,从而对工具理性进行了功能分析,即技术服从于社会统治的需要。可是《启蒙辩证法》并没有提出解决工具理性统治的策略,正如芬伯格所说:“没有为克服它所谴责的罪恶提供策略。”[10]90
其次,对技术理性的政治批判。芬伯格指出马尔库塞的侧重点是证明科学和技术为阶级统治服务,不过,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并没有像《启蒙辩证法》那样悲观,因为马尔库塞指出了一种解放的可能,一种新的技术实践形式将是可能的,这种形式是通过人类才能意识到的审美需要决定的,正因为如此,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指出了“现代技术的民主潜能”[5]40。也就是说,在马尔库塞看来,发展出一种新技术摆脱统治效应是可能的,人们可以通过参与政治引导技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芬伯格对此作了评论:“他比任何人更加注重把这一问题放到政治讨论的议事议程中来。”[10]22
芬伯格既不认同《启蒙辩证法》中工具理性从控制自然而转向统治社会的主题,认为只不过是“集权主义的启蒙”[5]14,也不赞同《单向度的人》中“单向度”的理论表明技术理性的社会统治主题,而是认为存在摆脱技术统治的方案。他说:“补救的方法不是在精神复兴中寻找,而要从民主进步中寻找。”[5]14芬伯格认为人们不是完全沦陷于技术统治之中,也不必然如《启蒙辩证法》那样悲观,人们可以对技术发展方向作出理性选择,发展出一种新技术政治学。作为马尔库塞的学生,芬伯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政治化的倾向十分赞赏,他继续推进和完善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政治学,提出了技术民主化方案。
芬伯格继承了马尔库塞技术政治思想,又力图改变其技术政治方向。对马尔库塞有关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芬伯格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新的权力系统建立在征服了其人类对象的技术操纵者的力量基础之上。”[10]29-30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坚持认为技术统治是一个政治问题,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单面”社会把技术合理性“扩散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包括休闲、教育、性生活等等”[10]32。芬伯格显然赞同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统治是政治问题的观点,然而他并不赞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必然导致单向度的社会的结论。芬伯格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中指出,尽管马尔库塞指出了技术的民主潜能,然而他的论述太抽象,也没有从实践上解释清楚技术应用中的人类的价值问题。因此,芬伯格指出需要另寻出路,主张通过一种新的技术政治学改变马尔库塞技术政治学的方向,这种新的技术政治学既要把人类价值结合到技术结构中,又能解释具体的实践。
芬伯格认为既不能把技术视为中性的工具,也不能把技术视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而必须把它看成是和其他制度一样是社会的,他认为有必要把技术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不过芬伯格认为今天的政治运动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政治运动,芬伯格认为现代政治学只能看成是一种“微政治学”,因为相关的政治运动都是小范围的,这些政治运动的目的不是从整体上根本性地反抗和改变国家,而只是为了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可见,芬伯格主张的“微政治学”与具体的小范围的政治抗议形式有关,目的是通过改变特定的技术以改善生活环境。这种反抗的政治运动是自下而上的运动。芬伯格强调在技术设计、技术发展战略和运用过程中,利益集团掌握了技术代码,这是有悖民主精神的,他认为所有受到影响的人们都能参与到技术代码的设计与应用中来,这样才能够改变技术系统。他说:“通过来自用户、顾客或受害者的压力来改变特定的技术或技术系统。”[10]43可见,他所说的“微政治学”是体现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技术政治学,对技术系统中的人类主体提出了交往的要求。芬伯格说:“我们正在发现如何作为社会技术系统中的互动者来行动。”[10]46他还认为在技术领域中出现内在的反抗将改变技术政治的发展方向。
芬伯格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的选择和决策深受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强烈影响,在技术发展的结构性中技术对工人、消费者和自然环境的福利漠不关心,这是因为资本家及其代表拥有经营自主权,他们掌握了技术代码。与此同时,正因为这些漠不关心构成了当前技术斗争的背景,技术的传播和官僚行政打开了其他斗争的局面,可以重新设计技术为人类和自然服务。芬伯格认为,以追求技术民主化为目标的技术斗争已经在很多领域发生,涉及互联网、环境、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问题,技术斗争采取了从黑客攻击到诉讼、消费者抵制,再到抗议和示威等手段。尽管这些社会运动与和平、民权、税收等重大问题相比,它们显得软弱甚至微不足道。然而,随着普通人在技术体系中参与技术代码的设计,“技术先进社会的性质正在逐渐发生变化”[11]116。这些代码等同于法规,技术行动必须符合技术操作规则,使之符合人类的需要。芬伯格指出:“我们才刚刚开始对技术进行民主干预。最终的调整可能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11]117对技术官僚思想的抵制构成了一种新的传播形式,这种传播形式植根于技术社会的日常经验,通过改变技术规范间接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从技术和规范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在公众被系统性地剥夺权力的地方展开斗争,以技术规范为基础继承技术系统,改进技术法规,如此一来,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变革引领了一场技术领域的激进改革,这有利于形成民主的技术政治。
芬伯格认为要把技术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发挥普通大众在技术设计和决策中的作用。他用技术民主化理论解释当代社会运动,认为当代社会运动与技术的紧密联系有关,当代激进运动,如环境运动和基于性别的运动等都涉及到技术和其他技术中介系统的斗争,这些争论通过挑战资本主义对技术知识的应用间接地提出了权力问题。芬伯格认为当代社会运动与技术应用紧密相关,技术中介已经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说:“政府官僚机构使用越来越复杂的计算机技术,并且越来越受到模仿市场运作的问责制形式的制约。市场越来越依赖于通信技术,实现全球化,而生产则由高度官僚化的管理层组织。这些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往往会创造一个越来越技术化的社会理性系统。”[11]112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官僚制将其限制性的生活形式强加给有能力为自己利益而抵抗的人民,而来自底层的人民的反抗,尽管可能是局部的斗争,是微政治学,但仍然有利于实现技术的民主化。
四、结论
《启蒙辩证法》的技术观从技术统治走向技术民主化的发展,表明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思想家从技术批判的角度回应了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解释了人们运用工具理性对待自然和人类社会而产生的技术统治现象;马尔库塞用技术理性逻辑解释了单向度社会的统治现象,他认为技术成了新的统治形式,强化了对人的统治。芬伯格指出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今的诸种社会运动及其反抗活动与技术中介密不可分,技术政治学应围绕争夺技术代码而展开各种权力斗争,这需要发挥技术的民主潜能。
《启蒙辩证法》的技术观从技术统治走向技术民主化的发展,反映了《启蒙辩证法》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后续发展的影响。《启蒙辩证法》解释了人们为了生存需要,工具性地对待自然和控制自然,并以控制自然的方式控制了人类社会的现象,从而确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工具理性的分析范式,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后续发展。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进步及其产生的统治效应,再现了《启蒙辩证法》以控制自然的方式控制人类社会的主题。芬伯格一方面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功能分析造成人们无法逃避的统治效应;另一方面他对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进行政治批判,从马尔库塞的分析中看到了技术的解放潜能。芬伯格提出技术民主化方案,实现了工具理性批判向技术民主化的转化。
《启蒙辩证法》的技术观从技术统治走向技术民主化的发展,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从悲观走向乐观的理论发展趋势。《启蒙辩证法》一书揭示了启蒙的工具理性逻辑以及由此解释的社会统治现象,总体呈现出悲观的论调,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分析,最终解释了一个单向度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统治现象,虽然他指出了技术的解放潜能,但总体方案也不够乐观。芬伯格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技术批判传统,提出技术民主化的方案,他对新兴社会运动的分析,表明从下层产生的技术民主运动将是可能的,这从整体上扭转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技术批判立场上的悲观论调。总之,《启蒙辩证法》的技术观从技术统治走向技术民主化,表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展示了一条从工具理性到技术理性,再到技术民主化的发展路径,既反映了《启蒙辩证法》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续影响,也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从悲观走向乐观的规范化理论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