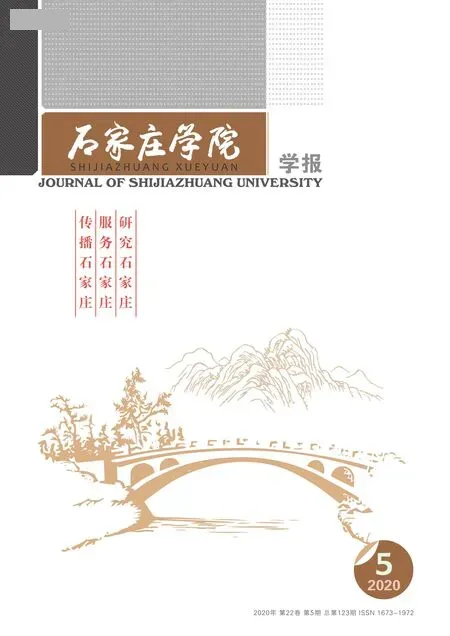明清燕赵府州县志资料来源初探
秦进才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历史是以史料为媒介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史料既是研究的基础,又是研究的对象。史学家的观点随着史料的发现而变化,史料的真实与否直接影响着史学研究的成果。明清府州县志,多是政府组织编纂的官书,是研究明清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是研究明清地方史与区域史的第一手资料。明清府州县志的资料来源,既是编纂方志的基础,又影响着志书的水平,也决定着其价值等。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府州县志的资料来源,既有共性,又有特点。详细剖析每一部明清府州县志的资料来源任务巨大,归纳、升华其认识,更不是短期就能够完成的。笔者只是选择性地对明清燕赵①燕赵,既是国名,又是地名,还是区域名称。作为国名,有战国时代的燕国、赵国,后人合称燕赵,前后疆域有所变化。有汉魏以来的燕、赵诸侯王国,辽朝的燕赵国王等。作为地名,有河北省曲阳县的燕赵镇。作为区域名称,有着不同的用法,有说大燕赵者,以古代燕赵两国的疆域为基础,包括了今京津冀和晋鲁豫辽内蒙部分地区;有说中燕赵者,指今京津冀;有说小燕赵者,指今河北省。本文的燕赵,是区域名称中的燕赵,指今京津冀地区,大致相当于明朝的北直隶、清代的直隶省,又称为畿辅者。府州县部分方志的资料来源稍作探讨,抛砖以引玉。
一、府志的资料来源
明清行政层级体系中的府,为省以下的行政区划,承上启下。府志,是以府辖区为记述范围的志书。府志相对于州县志来说,所涉及的区域广阔、人口众多、事务丛杂,难度比较大,因而不仅志书篇幅较大、编纂耗时较长,而且数量较少。府志的资料来源,不仅因时代而有不同特点,而且创修、续修与重修亦有所区别。
(一)创修府志的资料来源
所谓创修志书,亦称为创辑、创始、新修、始修、首修等。指本地未有志书而修纂者,或是新增志书的门类,或是改换旧志门类名称等,都可以划在创修志书的范围之内。创修志书,有很多已经散佚了,流传至今的较少,并且有些所谓的创修志书并非名副其实。
有些后人视为创修的志书,其实并非都是第一部。如河间府志。就明朝来说,解缙等编的《永乐大典》中引用:“《河间府志》广盈仓,在府治前。”[1]3436说明《永乐大典》所引用的《河间府志》问世无疑在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年)之前。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四《新志》载有《河间府志》,说明此《河间府志》成书于明英宗正统六年(1414年)之前。景泰《寰宇通志》卷二《河间府》中引用《旧郡志》资料,证实旧《河间府志》在明景帝景泰七年(1456年)之前已传世。天顺《明一统志》卷二《河间府》中引用了《旧郡志》与《郡志》,证实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前新、旧《河间府志》已经广为人知。其后,又有所谓知府贾忠修纂的天顺《河间府志》20卷①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六《史部·地理类上》载:“贾忠《河间府志》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只著录了作者、书名、卷数,并没有著录年代。民国《河北通志稿·旧志源流》卷一则著录为:“天顺《河间府志》二十卷。明贾忠修。见《千顷堂书目》。贾忠,山西崞县举人,天顺年知府事,纂修成书。”(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2 802页。)不作任何说明地添加了“天顺”二字,以标明年代。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天顺《河间府志》说法的始作俑者。这种说法被后来著述所沿袭、发挥。如《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五《佚书·沧州地区》载:“[天顺]河间府志二十卷。(明)贾忠修。明天顺年间修。”(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页。)沿袭前人之说。又如《河北省志》第83卷《出版志》第三章《方志出版》载:“《河间府志》20卷,贾忠纂修,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间)成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标注得更为具体。还有2003年《河间市志》五《文化·史志编修》(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页)、《河间文化艺术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等,也是稍有变化地抄录《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的文字,没有作任何考察,都有以讹传讹的嫌疑。,其实,山西崞县举人贾忠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到七年(1462年),都在沧州知州任上,不可能以河间知府的身份来编纂天顺《河间府志》②嘉靖《河间府志》卷一七《宦绩》载:沧州知州贾忠,“天顺二年,自邳州改任。属大水之后,救荒弭盗,历有成绩,赋役均平,听断明允,修城池州治,得膺旌典。寻升河间府知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版,史部第192册第626页。)《明实录·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七天顺五年四月辛未载:“筑直隶河间府沧州城,从知州贾忠奏请也。”(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6 735页。)嘉靖《河间府志》卷二《建置志·城池》载:“沧州城池。自旧沧州迁今治。天顺五年,知州贾忠始奏筑新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2册第421页。)卷四《宫室志·公署》载:“天顺六年,知州贾忠于城东北隅创建厅事及吏舍仓庾,煥然一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2册第454页。)民国《沧县志》卷三《方舆志·建置·仓储表》载:明天顺七年,预备仓,在州治西街,知州贾忠创建。(《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2册第65页。)嘉靖《河间府志》卷五《宫室志·学校》载:彭时撰《重修河间县学记》曰:“天顺七年,山西贾侯忠来知府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2册第459页。)由上述可见,从天顺二年到七年,前后6年,贾忠都在沧州知州任上,不可能以河间知府的身份编纂天顺《河间府志》,民国《河北通志稿》所言与事实不符,后来诸书以讹传讹,亟需更正。。应当是从天顺七年(1462年)至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年)间,贾忠在河间知府任上③嘉靖《河间府志》卷一七《宦绩》载:知府,“贾忠,山西崞县人。自沧州知州擢任。赋性峭直,居河间八年,威行惠流,治益闲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2册第619页。)前引彭时撰《重修河间县学记》曰:“天顺七年,山西贾侯忠来知府事。”康熙《畿辅通志》卷五《城池》载:“故城县城始建莫考。明成化二年,郡守贾忠、知县唐高增筑。”(《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河北》,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册第172页。)嘉靖《河间府志》卷一《地理志·山川》载:单家桥,“成化(十)六年,知府贾忠、滕佐重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2册第407页。)成化十五年,贾忠升为陕西苑马寺卿,不会在成化十六年再修单家桥。康熙《献县志》卷一《地理·桥梁》亦作:“成化六年,知府贾忠等重建,桥之南北竖二大坊。”(清康熙十二年刻本,第13页b-14页a。)可知“十”字衍,当删。嘉靖《河间府志》卷四《宫室志·公署》载:“府治,在府城中正北,然屡经兵燹,仅蔽风雨耳。……成化庚寅,知府贾忠重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2册第445页。)庚寅,即成化六年。嘉靖《河间府志》卷五《宫室志·学校》载:河间县儒学,“成化六年,知府贾忠、同知赵祺、通判诸廷仪、知县史彬合谋辟地重建,庙学焕然一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2册第459页。)《明实录·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辛巳载:“减中长芦盐则例。……河间知府贾忠以则例太重,请为量减,故诏河间、涿州仓每引米减为三斗,保定、天津仓视河间者加五升,延绥仓视保定者加一斗,若折银俱二钱五分。”(第1896-1897页)。成化《山西通志》卷一〇《人物·国朝·已仕》载:“贾忠,崞县人。中正统甲子乡举。除知沧州,升河间知府,又升参议,仍掌府事。”(民国二十二年景钞明成化十一年刻本,第46页b。)时间当在成化十一年之前。《明实录·明宪宗实录》卷一九六成化十五年闰十月辛酉,“升河间府知府贾忠为陕西苑马寺卿”。(第3453页)由上述可见,贾忠从天顺七年到成化十五年,十六年时间在河间知府任上,在此时间内撰写了《河间府志》。前引嘉靖《河间府志》卷一七《宦绩》言贾忠,“居河间八年,威行惠流,治益闲暇”。是抄录程敏政撰《河间府志后序》的“贾君守河间八年,威行惠流,治益闲暇”。程敏政说是对的,即贾忠在任河间知府8年时,撰成《河间府志》,即在成化七八年之际,此后贾忠仍然在河间知府任上。嘉靖《河间府志》不加思索的抄录过来,说贾忠“居河间八年”,则有失考察,少了贾忠在任8年的时间。,与郡倅诸廷仪编纂《河间府志》20卷④明程敏政撰《篁墩文集》卷二一《河间府志后序》载:“河间郡守太原贾君忠及其倅宁夏诸君廷仪,取郡志梓行而走书京师,请敏政序其后。”“然则斯志之行,岂徒以饰吏事夸美观而已,将使夫行部之臣、筮仕之士,不烦于询访咨诹,而一郡二州十六县之事举目可以尽得之,由是而出治无难焉,则二君子有功于斯郡大矣。……诸君赞成此举之力尤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 252册第364-365页。)由此可见,成化《河间府志》是贾忠与诸廷仪合作的产物。嘉靖《河间府志》卷一七《宦绩》载:推官,“诸廷仪,宁夏人。仪有学识,时多宗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2册第621页。)由此可知,诸廷仪也有能力帮助贾忠编纂成化《河间府志》。,又请学者程敏政“为之博采群蒐重加订正,凡古迹、山川、人物、诗文之类,彪分胪列,颇详整于旧云”[2]365。按照成书年代来说,当称为成化《河间府志》,而非天顺《河间府志》。上述几部《河间府志》到明朝嘉靖年间,或收藏在皇宫中,或保存在衙门里,散布在民间者很少,一般人难以见到,或是已经散佚不为人知,但都比人们所认为的创修府志——嘉靖《河间府志》年代要早些。
作为创修府志的资料来源,既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点。
有以传世、民间、方志文献等为资料来源者。如嘉靖十八年(1539年)奉知府郜相命纂辑《河间府志》的樊深认为:“河间,今王畿重地,其在辽金及胜国,戎马驰突,文献灭裂,识者慨焉。后虽有程氏旧刻亦仅成而未备,邝氏家集每欲备而未成,废缺相循,卒为坠典。”由此可见明代人编纂志书时收集资料的困难,樊深对于本文上述编纂的多部《河间府志》了解得不全面。这里所提到的“程氏旧刻”,当是指程敏政参与修订的成化《河间府志》20卷;“邝氏家集”,当是指明代任丘邝璠(1458-1522年)家族编纂河间府志的行为⑤明代任丘邝氏,人才兴旺。邝璠,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任瑞州知府,修正德《瑞州府志》,著有《便民图纂》等书。其弟邝珩,弘治十二年进士,任平凉知府。其弟邝琚,贡士,任馆陶知县,博文藻思,雅尚著述。其弟邝琮,监生,任辽东经历。邝璠长子邝涛,正德十一年(1519年)举人,任桐城知县。邝涛之弟邝澡,正德十四年举人,任解州知州,博学宏才;其弟邝汴,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光禄寺卿,植性静重,积学渊闳。邝琚之子邝灏,正德十二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出为河南提学副使,朴直超逸,优于古作。参见嘉靖《河间府志》卷二三《人物志·任丘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2册第697页)等方志。由上述可见,任邱邝氏有条件、有能力、有时间撰写《河间府志》,并且明清世家大族纂修地方志事例屡见不鲜,但邝氏并未完成此事,因未见其他史料证实,故推测言“邝氏家集”当是指明代任丘邝璠家族编纂河间府志的行为。具体情况,尚待今后发现新材料证实。。樊深认为前人的志书不是不完备,就是没有完成。因为,“瀛而无志犹无瀛也,志而不工犹无志也。嗟予踈陋何以堪此。然又惧夫机会难逢,时焉易失,恐后之慨今无异于今之慨昔也”[3]393,因此承担起了纂辑《河间府志》的使命。樊深广泛寻找资料,“稽诸坟典,质诸谱牒,参之旧辑,摭以新闻”[3]393。也就是搜集、稽考经史子集等传世文献中有关河间府的资料,网罗、辨别家谱、族谱、宗谱等民间文献中的有关资料,翻阅、参考新旧《河间府志》等志书的有关资料①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土志·风俗》载:“人多贵德,俗皆淳朴。旧郡志。衣冠不乏,风俗熙熙。同上。农桑为先,务诗书为要领。郡志。民淳讼简,无强暴相凌之风。旧郡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2册第477页。)由此可见,嘉靖《河间府志》参考了新旧郡志,即新旧《河间府志》。旧《河间府志》,也就是樊深嘉靖《河间府志·河间府志自序》所说的“旧辑”。,收集社会上发生的新生事物、新知识中的有关资料,对于相关资料进行考察,以解决存在的相互矛盾等问题。16个字不多,涵盖的范围很广,从现代的知识体系看,涉及到了传世文献、民间文献、方志文献、口碑资料等,也就是广泛地收集了各方面的资料,构成了嘉靖《河间府志》的资料来源。然后经过“析事类而条理秩焉,肆采择而遗阙补焉,加删存而褒贬寓焉,原利病而民性资焉”[3]393的整理,纂辑成28卷的嘉靖《河间府志》,成为流传至今保存完整而成书时间较早的《河间府志》,被后人视为创修②万历《河间府志》载:“河间郡志,肇刻嘉靖庚子,凡二十八卷。”(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第1页a。)所言“河间郡志”即嘉靖《河间府志》。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一二《人物志·文学》载:“时河间守郜相以郡无志乘,慨然欲修之,举以属〔樊〕深,深成书二十八卷,郡之有志自此始也。”(《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1册第302页。)乾隆《河间县志》卷五《人物志·文学·樊深》载:樊“深成书二十八卷,郡之有志自此也”。(《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1册第713页。)三书均以嘉靖《河间府志》为河间府有志之始,并为现代人所认同,有人说“是志为河间首创志书”(于洪儒《河北省方志概要》,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第89页),有人说“河间古无志,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郜相上任后,‘乃托诸司谏樊君深,爰修次焉。’‘稽诸坟典,质诸谱牒,参之旧辑,摭以新闻。’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修成”。(来新夏主编《河北地方志提要》,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由上述可知,至少明永乐、正统年间已存在《河间府志》,景泰、天顺年间有新旧《河间府志》。成化年间有贾忠等修纂的《河间府志》,但上述《河间府志》,嘉靖年间的樊深有些已经看不到了。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一二《人物志·文学·樊深传》载:“今深书不传,《明史·艺文志》列其目。”(《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1册第302页。)其实,浙江天一阁收藏着嘉靖《河间府志》。是当时的社会条件限制了他们的眼光,产生了所谓创修的说法,不足为怪,但应当认识他们以讹传讹说法的局限。,也起到了创修的作用。
有以传世文献为主、口碑资料为辅者。如表山带河、东西扼晋冀咽喉、南北守燕赵要冲的明代真定府,其山川、财赋、户口、风俗、人物等,散见于诸史的记载中,总括于《明一统志》的记述里,并未有单行本的府志传世。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真定知府唐臣得到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李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瑶的支持,会檄大名府通判雷礼总纂府志。雷礼下功夫,“蒐故实,掇逸遗,参舆论”[4]7。蒐故实,指广泛搜集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历史资料。掇逸遗,即辑集掇拾以前逸遗脱漏的历史事实。参舆论,征求公众对于府志编纂的看法和意见。蒐故实,掇逸遗,主要是说广泛收集传世文献。参舆论,是说注意收集口碑资料。从上述可见,其资料来源是以传世文献为主,以口碑资料为辅。在此基础上,“酌是非,博采精择,以次以辑”[4]7,纂辑成33卷的嘉靖《真定府志》,完成了创修《真定府志》的使命。
有以志稿为主要资料来源者。作为明代左挹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的宣府,没有方志,其兴废沿革以及风俗人物的盛衰之迹无所稽考。景泰三年(1452年)十一月到七年(1456年)九月间,任职提督宣府军务右佥都御史的李秉,撰写宣府镇志稿③正德《宣府镇志》王崇献《宣府镇志后序》载:“贡士范生桓言曰:宣府旧无志,闻诸前辈相传,景泰年有李巡抚者,山东曹州人,创为手藁以诏后人,志之始也。仆闻之不觉怅然兴感。盖李公名秉,先外祖也,已即世矣。”(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第1页b-第2页a。)李秉,除在景泰年间任提督宣府军务右佥都御史外,天顺八年,又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未完成编撰而升迁离去,但由此开启了宣府志的编纂事业。天顺八年(1464年)八月至成化三年(1467年)九月间,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宣府的叶盛,在军政边务之余,撰写了《宣府志序例》[5],编成宣府志稿,并收入了自己撰写的《神祠记》《来恩亭记》《隆庆州学记》《云州义烈祠碑》等相关文章,但《宣府志》稿未刊刻就离任了④正德《宣府镇志》刘健《宣府镇志序》载:宣府,“故无志,兴废盛衰之迹无所于考。成化初,姑苏叶文庄公盛以都宪巡抚其地,始即所见闻裒集之,藁成,未梓行而去”。(第8页b)刘健认为叶盛是开始编纂《宣府镇志》者,当是因为情况不熟悉而然。。叶盛编纂的宣府志稿碾转到了镇守太监孙振之手⑤正德《宣府镇志》徐溥《宣府志序》载:“宣府未有志。成化初,叶文庄公为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尝撰次成编,未行而去。弘治丙辰,巡抚副都御史马君中锡闻而购之,或言故监察御史李经家尝有是藁,为镇守太监孙公振所得,将锓梓矣,会移镇大同,则以授君。”(第1页)马中锡是直接购买到了叶盛宣府志稿或是碾转从镇守太监孙振处得到的,得到的途径有不同的说法,现在很难求得准确的说法,但叶盛稿本为马中锡所得的结果是相同的。,准备刊刻时,因移镇大同而作罢。弘治九年(1496年)四月到十二年(1499年)三月间,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宣府的马中锡,从孙振处得到了叶盛的志稿,因有人随意增损,马中锡在边务之暇修订,“复旧规而加新闻”[6]1b,编纂定稿,并在弘治十一年(1498年)请吏部尚书徐溥、户部尚书刘健为宣府志撰序,似乎《宣府志》问世指日可待①明焦竑辑《国史经籍志》卷三《史类·地里》载:“《宣府志》十卷,马中锡。”(《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16册第368页。)明朱睦撰《万卷堂书目》卷二《地志》载:“《宣府镇志》十卷,马中锡。”(《续修四库全书》,第919册第466页。)《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载,“马中锡《宣府镇志》十卷”;卷八《地理类下》亦载,“马中锡《宣府镇志》十卷”。(第159、206页)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载:“马中锡《宣府志》十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 406页。)上述诸书,虽书名有《宣府志》与《宣府镇志》之别,但都是10卷,都是马中锡撰,似乎可以证明马中锡的《宣府志》或《宣府镇志》已经问世。乾隆《宣化府志》方承观《序》亦言:“宣志,创于前明弘治抚军马公中锡,嘉靖庚申,翰林孙公世芳踵修之。以其后马志失传,惟孙志为州邑所取材。”(《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11册第1页。)实际上,马中锡志稿并未刊行,哪来的失传问题,以上诸记述并不准确。。因马中锡告病归家,又一次留下了宣府志稿本②首先,前引徐溥言“宣府未有志”,刘健曰:宣府,“故无志”,都是说弘治十一年之前宣府未有志书,马中锡《宣府志》的刊行应当解决了宣府无志问题。但正德《宣府镇志》王崇献《宣府镇志后序》载:正德九年,总制宣大军务的丛兰说:“宣府志久未成帙。”“贡士范生桓言曰:宣府旧无志”。(第1页)说明正德九年时,宣府依然无志。其二,一般方志都会有编纂者写的序言或凡例,正德《宣府镇志》,有马中锡请徐溥、刘健撰写的序,而无马中锡写的序或凡例,马中锡的《马东田漫稿》中也不见宣府志序或凡例等。其三,有些著述引用马中锡《宣府志》:“花朝节,城中妇女剪彩为花,插之鬓髻,以为应节。”实际源自于嘉靖《宣府镇志》卷二〇《风俗考·岁时纪略》载:“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城中妇女剪彩为花,插之鬓髻,以为应节云。”(《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9号第226页。)此事不见于与马中锡有关的正德《宣府镇志》。上述可证明马中锡留下的是稿本而非刻本。。正德九年(1514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的孟春和以右都御史总制宣大军务的丛兰,委托兵部职方司主事王崇献,编纂宣府志书。王崇献以外祖父李秉60年前编纂宣府志的行为,产生了“是书若有待焉”[6]2a的使命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编纂任务。因“边地书籍不多,凡事无从考证,姑因旧志笔削成编”[6]2b。这里的“旧志”,不是指刊刻成书的宣府镇旧志,而是指李秉、叶盛、马中锡等人前后相承编纂的宣府志稿,阴差阳错地成为了王崇献编纂《宣府镇志》的主要资料来源,王崇献与宣府贡士范桓、举人杨百之等合作,编成10卷本的正德《宣府镇志》③正德《宣府镇志》10卷,前有弘治十一年徐溥、刘健序,后有正德九年王崇献后序,两者相差16年,这种不合常规的序言,使许多人只看到了徐溥、刘健序,如明人焦纮的《国史经籍志》等而著录为马中锡《宣府志》10卷。其实,书后还有王崇献的后跋。书中内容,不仅有王崇献增加的,如正德《宣府镇志》卷三《墩台》载:“预置墩,预竖墩,以上二座,俱正德九年总制都御史丛兰添设。”(第57页a)卷三《牌碑》载:“皇都得意坊在钟楼南,正德九年,为举人杨百之立。”(第83页a)卷六《宦迹·巡抚官》载:“孟春,字时元,山西泽州人,丙辰进士。正德八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第58页b)而且还有后人增加的,如正德《宣府镇志》卷六《宦迹·巡抚官》载:“郭登庸,字自微,号两山,山西山阴县人,甲戊进士,嘉靖十五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第59页a)卷六《宦迹·续宦迹》载:“巡抚都御史宁杲,字仲升,辽东海州卫人,正德十四年,以左佥都御史巡抚赞理军务。”因此说,正德《宣府镇志》,包括有马中锡宣府志的内容,也有弘治十二年以后马中锡不可能撰写的事情,还有正德九年以后王崇献不可能编纂的内容。因此,著录正德《宣府镇志》,为弘治《宣府镇志》,编纂者为马中锡,虽不是空穴来风,但有不准确之嫌,著录为正德《宣府镇志》,编纂者为王崇献,方符合实际,说其版本是明正德刻嘉靖增修本更准确。。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5帝60余年,《宣府镇志》终于问世,成为创修的宣府志书。
(二)续修府志的资料来源
续修方志,又称续编、续补、续增、续志、续纂、增修、增补、补修、接修等。一般认为在旧志的基础上,拾遗补阙,校谬正讹,接续旧志门类编纂新志,是为续修④如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卷一《凡例》载:“此次修志,其分门别类一遵湘潭公成规,取其条例清釐,意义贯串,令阅者属目瞭然。”“志中所纪星野、沿革、疆域、形胜、山川、城池、公署、坛壝、关隘、水利、邮政、风俗、方产、封爵、仙释等门概无变易,志俱仍旧,其余有变易者逐门增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9册第13页。)上述所言随类附事,体现了续修方志的特点。。如果说创修志书数量很少,那么续修志书应当是明清方志的多数。续修志书的资料来源,多数继承了创修志书的成果,补充了新的资料。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续修志书的格式上相互有差异⑤有的格式上区分得很清楚,如光绪《海阳县续志·凡例》载:“此次重修固宜仍存其旧,而其中间有讹錯之处悉皆更正,与续志分为上下函,凡续采者皆载下函,以便省览。”(《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6册第168页。)新旧内容从格式上、先后顺序上,就分得一目了然。有的分得并非如此清楚。,而资料来源则是大同小异。
有以旧志资料为主、加以核查补充者。如果说人们视嘉靖《河间府志》为创修,那么按照其体例再修《河间府志》就可以说是续修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河间知府杜应芳说:“本府三长俱短,五难是虞,加之期会漙书,棼投猬集,窃有志而未逮焉。为此,合将旧郡志分頖各属长吏,遴萃文学,博诹故老,官给笔劄月资饩钱。缺者补之,纰者正之,信者传之,殽者辨之。通限三旬,汇送本府裁订,勒成此中一书。”至于“道路悠谬之谈,恍愡疑似之语,采摭既隘,挂漏尚多,是不详不核也,责在各属。非所笔而笔,非所削而削,誉毁怵志,史野交讥,是不赡不直也,责在本府”[7]2b。把嘉靖《河间府志》当成了基本的资料来源,分配给各属长吏,由他们分别负责,动员所属的文学、故老等人员,承担起所缺资料的收集补充、谬误资料的考证辨别的任务,知府负责对于资料的取舍删削。如对于入宦迹志的资料规定:“宦迹,宋元以上详矣而备载,高阳横海之类,以若今院道然也。国朝名宦,取生祠口碑为据,无据不录。见任者,止书籍贯以俟论定。”[7]1对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不详的,加以补充。“天津重镇,旧志仅附卫名于静海,而城池公署俱略不载。今另标题备录,俾阅者知津门重地为国家咽喉之区。”[7]2a增加新资料,以反映迅速发展的天津情况。“旧志黜摈仙释,其谊甚正,然《一统志》业备载矣。今续考入,以示点缀。”[7]2b把嘉靖《河间府志》黜摈的内容补充进去。“纂述惟恐不确,故拟议咨诹不厌其详,以昭信也。至绮闻异说,传之可疑,弃之可惜,故裒集《闰谭》附末,亦《西湖志余》之意也。”[7]2b-3a访问咨询不厌其详,即使有些奇闻异说资料也要收起来,集合为《闰谭》,附录在万历《河间府志》中。这样,万历《河间府志》在嘉靖《河间府志》提供的资料基础上,纠正其讹误,扩展实物资料、口碑资料等,有删削,有舍弃,更有所增加,由“旧志八百六十二叶”,增加为“今志九百八十九叶”[7]3a。
有以旧志残本、援经据史为资料来源者。明永乐年间,曾编纂《永平府志》,历经百年已经残破。弘治十三年(1500年),永平知府吴杰告诉行人司行人、郡人张廷纲与滦州学正吴祺:“近得一编,历岁既久,传写舛讹,残缺尤甚,盍为撤旧而维新是图。”①弘治《永平府志》张廷纲《永平府志序》(《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册第15页)。同上书吴杰《永平府志跋》亦曰:“首询郡志,脱略无几。”(第3册第500-501页)所言旧志情况有相同之处。所谓一编,即永乐《永平府志》,因其残破、舛讹,而令张廷纲、吴祺总任纂辑为新志事。并发布文移,“通行所属州县,转行儒学堂印教官,各带老成知事生员,或二名三名,各将州县及境内卫所衙门兴废沿革,与夫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古今名贤碑刻,及诗文等项,有关风教者,逐一公心考校,送府再加评订”[8]24-25。动员各州县学官与生员搜集资料,以备编纂府志之用。张廷纲等“因取史传,参以诸书及古今人物诗章文字有之征者,较其舛讹,芟其?芜”②弘治《永平府志》张廷纲《永平府志序》(《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册第15-16页)。同上书吴杰《永平府志跋》亦曰:“援据经史,搜罗百家所载。与夫稗官小说,参互考订,编摩成集。”(第3册第501-502页)两人所言有相同之处,可相互证明,相互补充。,又“或稽诸载籍,或质诸故老,或参以见闻”[8]492。开阔搜集资料的思路,将传世文献与口碑资料结合起来。对资料进行选择、考证,“旧者存之,新者续之,讹者正之。事之不足信、文之有可疑者,阙之。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削之。凡有禆于风教、有关于政体者,录之。纪其实而违其名,略于今而详于古”[8]493-494。几经努力,终于纂辑成10卷的弘治《永平府志》,成为目前存世最早的《永平府志》。
(三)重修府志的资料来源
重修方志,又称重辑、重纂、新修、新纂等,指旧志,因朝代革故鼎新而重修,或因贯通古今而重修,或因订谬正误、拾遗补缺而重修,或因新资料、新方法而重修,诸多原因不胜枚举。重修是方志编纂中的重要方法③民国《龙游县志》卷首余绍宋《叙例》载:“修志有两法,一为别出新裁全部改譔,一为因仍前志但纂续编。两者相衡,前者难于后者多矣。”(《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57册第5页。)前者当属于重修,后者当属于续修。余绍宋主张,为有些县志编纂者所认同,如民国《长葛县志》卷首刘盼遂《叙例》言:“修志之法有二,一为别出新裁全部改换,一为因仍前志但纂续编。两法相较,前者较后者为宜矣。”(民国十九年铅印本,第1页a。)可见余绍宋的主张化为修志的实践。。有时续修与重修概念混淆④光绪《太平续志》卷首《光绪太平续志凡例》载:“台州六县志书,以戚氏《太平志》为最善。此次重修,其凡例均依前志,略有变改。复增考异、补遗、附录诸目,或以正旧志之失,或以拾前志之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0册第464页。)光绪《太平续志》的凡例虽言:“重修。”书名仍然称为《太平续志》,续修、重修两概念,在他们那里是混淆的。。两者有共同之点,都有时限向后延伸、内容纠谬补缺等,续修中有重修的部分,重修中有续修的内容。相异之处,续修主要在于沿袭旧志门类而延续时限、增补新资料,重修主要在于体例变更增加新门类⑤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首《例言》载:“成都旧志六卷,但分类而未分门,此次重修略仿《四川通志》体例分十三门,以统各类,共成十六卷,多旧志一倍有余。”(《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册第12页。)这是名副其实的重修。。新志与旧志相比,虽然名为重修,仍然沿袭旧志门类者,应当属于续修⑥光绪《分水县志》卷首《凡例》言:“县志肇自前明,至道光乙巳,凡七修矣。分列十门,为卷一十有二,体例精详。此次重修一仍旧制,惟增兵事、殉难、存疑、补遗四条、余悉按类续编,不敢妄作。”(《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7册第9页。)道光《分水县志》正文10卷、首1卷、末1卷,故言“为卷一十有二”。光绪《分水县志》与道光《分水县志》卷次相同,门类多同,故虽言“重修”,实为续修。;即使有续修之名而已经用新体例者,应当归为重修⑦民国《封邱县续志》卷首《叙例》载:“余越园谓:‘修志有两法,一为别出新裁全部改譔,一为因仍前志但纂续编。’吾封旧志于淸顺康时,经王、耿二令相继续修,虽版字漫漶而规模犹存。本志因用后法,将旧志照原本重印,上接耿志,另纂新编。惟相隔二百余年,事迹多致缺略,国制变更,体例亦当改易,爰于采访所得,大体仿效《龙游》,旁参《安阳》、《滑县》、《密县》、《鄢陵》等县续志,裒辑成册,共二十八卷,名曰《封邱县续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1页a。)从旧志原本重印来看,连续修也算不上。从另纂新编来看,体例变更,虽然书名为民国《封邱县续志》,实质上已经是重修了。。在资料来源方面也有比较大的扩展、充实。
有以传世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者。如正德《宣府镇志》以旧志稿为主要资料来源,旧志稿是叶盛“即所见闻裒集之”[6]8b而成,由马中锡“复旧规而加新闻”[6]1b,记录了到明正德年间的情况,为后人保存了珍贵资料,但也有“语时则备而考古则踈”[9]1的弊端。宣府人孙世芳,清楚其中有“方舆仅述法度,未详甲赋,仅存经画,末及所谓大政教号令,且遗佚失裒,又将何所取藉备戒世世耶”[10]9175的问题。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御史栾尚约与孙世芳谈及宣府志事,一拍即合。孙世芳“殚其知识,摉罗惟愽,检索惟勤”,全力以赴,投入编纂。收集“先之往代史书、当朝制册,次之名臣伟议、先儒绪言,又次之幽人所愤谈、译人所袭讲”①参见嘉靖《宣府镇志》孙世芳《宣府镇志序》(《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19号第1页),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一五九《宣化府部》补(第9 174页)。再则,嘉靖《宣府镇志·宣府镇志凡例》载:“志所纪事,多自二十一史中考用。若二十一史外,则汉唐以来诸简册、国朝诸制书,历代儒贤诸文集,以及禆官所述、残碑所遗,亦皆取可传信者补阙漏焉。如或考索未明,则宁略不备,非敢臆度悬断,失本真也。盖深致其慎,以俟来哲云。”(《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19号第5页)与孙世芳《宣府镇志序》多有相同之处,增加了“禆官所述、残碑所遗”,可以互相补充。,作为资料来源。按照传统文献理论看,史书、制册,属于文;议论、讲谈,属于献,再加上“禆官所述、残碑所遗”,均可归为传世文献的范围。对于这些资料,采取“关世道者笔之不病于烦,悖时宜者芟之不病于简”[11]1的处理方法,经过“发以义例,标以要纲,著以条章,断以意见”[11]1的梳理、归纳、规范、升华等过程,编成二十六考、七表、九传共42卷的嘉靖《宣府镇志》,成为资料丰富的名志②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四《宣化府》引用《宣府镇志》一条,引用《宣府志》八条,其中八条来自于嘉靖《宣府镇志》卷八《山川考》,仅有一条笔者未查清楚史源所在。。
有以远则用传世文献与近则用采访资料相结合者。同治十年(187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修《畿辅通志》,并檄命府州县各修方志,先事采访。保定知府李培祜听取《畿辅通志》总纂黄彭年的意见,聘请正在编修《畿辅通志》的栾城拔贡张豫垲(原名惇德,号重斋)主持其事,“因用通志凡例,以纲统目”,因为“官牍年久无存,私家又罕纪载,难在无征”,因此,资料来源,是“远事征于书,近事征于册”[12]1。即距离远的事情,取证于传世文献——书,距离近的事件,取证于档册、采访册——册,书册是重修保定府志的主要资料来源。利用编纂《畿辅通志》的有利条件,编成了纪、事、略、录、传、记6纲42目80卷的光绪《保定府志》。
有以方志文献与档案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者。如天津,始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设卫筑城,继而由卫改州,由州升府,方志也由《天津卫志》而变为《天津府志》,天津在发展变化,天津志书也在与时俱进,由创修、增修而重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设局重修府志,资料来源,“其书大抵取裁于畿辅新旧两志,兼采州县旧志,旁及经史百家撰述。凡夫列圣之天章,累朝之诏谕,方舆星纪之数,风俗物产之详,仕宦政绩之尤,人物科名之盛,河道堤防之原委,屯田盐法之大凡,海防营制之分合,通商租畍之后先,罔不纲举目张,条分件系,洵乎详而能校,简而能赅,殆足以信今而传后矣”[13]2。上述概括地介绍了天津府志资料来源和主要内容。随后具体地说明了资料来源的种类,“今自书籍而外,近年所采厥有数类:曰旧通志、新通志,皆《畿辅通志》也。曰前志,乾隆四年所修府志也。曰州志、县志,总诸州志新旧志名之也。《沧州新志》未刻称州志稿。曰档案、档册,院司以下公牍所出也。曰请旌册,津郡绅士立采访忠孝节义局,汇报院司入奏,所具姓氏事实也。曰采访册,诸州县官属、绅士先后举报入志事宜也。曰测绘册事,使履勘舆地所具图说也。全书所征一一注明,庶便覆审”[13]3-4。由此可见,天津府志资料来源,除书籍——即古代传世文献外,近代主要在于方志文献、档案文献和口碑资料。不仅对全书资料来源有着具体的说明,而且有些卷也注明了资料来源。如“诸志所载以外,兼上采九朝圣训、《东华录》诸书,近事则档案、邸抄居多”[13]11。这是对于《皇言》类资料来源的说明。《天津府志》资料来源,收集广泛,分类细致,著录规范,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历时4年,编纂成了纪、表、考、传4类共54卷的光绪《重修天津府志》,成为天津府志的代表作。
有以传世、档案文献和口碑资料为资料来源者。明清时代,北京作为都城,设立顺天府。先后修纂了永乐、万历、康熙《顺天府志》,这些《顺天府志》草创荒略,没有超过20卷者,与明清时代的京师地位、首善之区不相符合。光绪三年(1877年),筹划编纂《顺天府志》,虽然前有永乐、万历、康熙《顺天府志》等,还要编纂《光绪顺天府志》,虽未冠以重修之名实际上属于重修之列。聘请张之洞担任总纂,撰写了《修书略例》59条,主张宜典核,宜征实,以官文书为据,引书凭古雅者,引书用最初者,群书互异者宜考订,采用旧志及各书需覆检所引原书,引书注明第几卷等,作了细致、明确的规定,并为编纂者所遵循。光绪五年(1879年),开局编纂,聘请名家学者担任编纂事宜。光绪十一年(1885年),完稿。光绪十二年(1886年),刊刻问世。修成了具有京师、河渠、经政、故事、官师、序志等11志,全书130卷350余万字的《光绪顺天府志》,成为明清《顺天府志》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明清顺天府的基本资料。资料来源,则“自群经笺注,地理专书,正史别史,诸子文集,与夫图经、志谱、公牍、访册,于古若今,数十万卷中探讨而出”[14]2。资料来源广泛,涉猎领域宽阔。传世文献、档案文献和口碑资料等相结合,构成《光绪顺天府志》主要的资料来源。并严格考证资料,纠正“修志之弊,非稗贩即沿讹,此则征引必注原书,异同力求一是”,对于“如人物,如官师,文学则所治何经,所箸何书,经济则所兴何利、所除何害,语语征实,不取空文”,“田赋准今,金石证古,类此谊各有当,例取其严”[14]2-3,以求资料的准确性和可信性。书后列《光绪顺天府志恭引》御制、御批、钦定书籍49种,《光绪顺天府志引用书目》844种,两者合计893种,清楚地标明了传世文献资料来源。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引用的清代公文档案,未能一一列出。《光绪顺天府志》的资料来源之广泛,考证资料之严谨,树立了一个典范。
明清府志的编纂,一般来说,创修者前少借鉴,资料不足,经验不多,难以为工。续修者沿袭气息浓厚,特点不明。重修者投入较大,资料丰富,后来居上。如乾隆《正定府志》,“博采群书,网罗散失,正讹十之二三,补亡十之四五,扩充十之六七,名实固殊,体裁亦别”[15]6,与旧志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上述府志的创修、续修和重修,笔者归纳为9种资料来源类型。具体到每部府志,又是由当政者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当地的学术氛围、资料条件,编纂者的学识与投入精力多少等来决定其水平高低、质量好坏的。但相对于州县志书来说,无论是主持编修的知府等官员,还是具体负责纂辑的学者、官员,其学识水平一般要比州县要高些,搜集资料的视野开阔,资料来源的条件也好些,在资料上下的功夫也更大些,因此,在资料来源的广泛性、资料来源标注的规范性、引用资料的准确性等方面水平也就高些。
二、厅州志的资料来源
明清的州,有着不同的行政品级,清代又分为属州(散州)和直隶州。清代的厅,也有着散厅和直隶厅的区别。相应厅州官员也有着不同的品秩。为叙述的方便,本文将厅州志书放在一起论述。厅州志书的资料来源,从创修、续修、重修的角度来看,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创修厅州志的资料来源
有以传世文献为主,辅之以档案文献和实物资料者。清雍正二年(1724年),设置张家口厅(治今河北张家口市桥西区);雍正十年(1732年),设置多伦诺尔厅(治今内蒙古多伦县城);雍正十二年(1734年),设置独石口厅(治今河北赤城县北独石口镇),合称口北三厅,隶属于直隶口北道。新设立的口北三厅未有方志。乾隆七年(1742年),直隶口北道金志章编纂成《口北三厅志》初稿。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宣化知县黄可润奉命补辑增修。黄可润认为,“夫载笔之道,史不能详则辅之以志,志不能详则证之以史。北部兴灭递嬗,干戈相寻,既无有司之执简,唯按以柱下之所藏,而考据于《北史》及辽、金、元之史为多。建置异而疆土不殊,部落分而裔类则一,著其代以烛其事。由北代之录,证以南朝之纪。至近世州邑关镇之旁载,名山石室之留贻,可志者渐备搜而传之。今之志,后之史所资也”[16]23。因口北三厅的特殊情况,黄可润把资料来源的注意力放到了传世文献上,收集了《汉书》《后汉书》《魏书》《辽史》《金史》《元史》等纪传体文献,又收集了《洪武实录》《永乐实录》等明代的编年体文献,还收集了《北征前录》《奉使录》《张德辉纪行》等亲身到过口北三厅者的诗文集、笔记等文献,也收集了《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皇舆图》等地理总志文献,参考了《畿辅通志》《北中三路志》《万全县志》等省通志、路志、县志等方志文献,借鉴了《四镇三关志》《宣府镇志》等关志、镇志的记述,引用了《多伦诺尔同知富德清查册》等档案文献,收录了虞集等撰写的碑刻文献,据不完全统计,引用资料达80余种,有时不仅仅注明书名,还注出篇名。正是在下大功夫收集资料、扩展资料来源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地努力,纂辑成经费、台站、考牧、蕃卫、世纪、杂志等16卷的《口北三厅志》,打造成了创修方志的精品。
有以《明一统志》为主、博采其他资料者。明代成化十一年(1475年),谢庭桂奉命创修隆庆州志,因为明初龙庆州人内迁,永乐十二年(1414年),方移民充实,改名隆庆(治今北京延庆区延庆镇。隆庆元年,改为延庆州),纂修州志,“征文献则载籍散失,怀旧俗则人非土著”[17]2b,无处着手,只得从京师借书于故旧,咨询于故老,“得郡人致仕教谕迟君英家藏赵尚书所遗《伧父集》观之,略知开创之由,继游上谷复得怀来旧志于钦差管理粮储户部正郎昌平马公孝祖所。于是谨遵《大明一统志》为主,旁蒐传记,博采见闻,门分汇别,诠次成编”[17]2b-3a。由上述可知,《明一统志》是主要资料来源,参考了怀来旧志、明刑部尚书赵羾撰《伧父集》等,创修成16卷的成化《隆庆志》。
(二)续修州志的资料来源
明清时代,续修州志占州志的多数,其资料来源大同而小异。
有以传世、方志文献和前人志稿为主者。如冀州志书,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有著录,成化年间,修成《冀州全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知州张景达聘请陕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丁忧在籍的张玺编纂州志,张玺认为:“冀旧有志,多疏略。”“介庵谢翁亦作补遗,讨论精当,惜未脱藁而卒。”因此,张玺“乃本《禹贡》《职方》、列史诸志、《一统志》《真定府志》、州县旧志及各碑籍并谢藁,櫽括以完。予特类萃之耳,间有增损,皆据实录,未敢妄窜臆说,惧失真也”[18]4。广搜博稽传世文献、方志文献和未刊方志稿,博采众长,荟萃精华,编成了天文、地理、人事、人物4大类10卷的嘉靖《冀州志》。
有以方志文献为主而参考其他资料者。如康熙《涿州志》的资料来源,“旧志可存什之五,可删者什之一,可改者什之二,而增入者乃得什之三四重”[19]。方志文献成为主要资料来源,采用者达到70%左右,再增加一些新资料,编成了记述职官、科第、胄监等12卷的康熙《涿州志》。又如光绪《蔚州志》在顺治《蔚州志》、乾隆《蔚县志》、乾隆《蔚州志补》所提供的资料基础上,重新分为表、志、传、记4例,资料择优而取,别成一家。根据资料来源,将人物志一分为四,“以采之正史及贤良祠传、满汉名臣传者为史传,录其全文;采之名人文集及家传、墓志、行状者为集传,节其大要;次以列传,则各志及今采访事实也;又次以列女,则古名媛及今节孝贞烈也”[20]3-4。不按照人物的角色、性别等来分类,而是按照资料来源的体裁来分类,独具一格。广征博采,综合创新,而编纂成光绪《蔚州志》。充分地继承了旧志的成果,也就站到了前人的肩膀上,提高了自己的起点。广泛地收集新资料,合理地分门别类编纂,打下了超越旧志的基础。
有以民间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者。如清圣祖为修《大清一统志》,诏命各府州县选名儒耆旧纂辑成志书以进。冀州知州李显忠,“奉檄以来,访故老而拾遗闻,揖缙绅而搜散帙,俾乖舛悉芟,同异用收”[21]2b。依靠着调查访问收集来的民间文献,编纂成10卷本的康熙《冀州志》。又如祁州(治今河北安国市祁州镇),先后有崇祯、康熙、乾隆《祁州志》传世。光绪年间,因修志不易,决定采访数十年以来近事,分类记之,编纂续志。知州赵秉恒,“出示四乡绅士耆老各以见见闻闻源源录送,而属孝廉〔刘学海〕秉笔焉。历两年之久,裒然成集,余覆加校订,厘为四卷。体例一遵旧志,惟旧志中昔有而今无者汰之,事同而名分者合之,以归简要”[22]172,也就是“爰据四乡所采访者,照旧志以类续之”[22]173。采集民间文献成为光绪《祁州续志》的主要资料来源。
有同一部州志不同时代有不同资料来源者。如赵州知州祝万祉编纂《赵州志》,针对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在前朝者,或博览古籍,或采取诸泐石,正误辨讹,其难其慎已。在近代者,或荐绅先生之公议,或田夫牧竖之传闻,有疑必阙。凡确务扬,不敢过为夸诩,亦不敢轻为淹没。令观者可感、可兴、可歌、可泣,于以兴政教而厚风俗,未必无小补耳。”[23]6b-7b因为时间久远,前朝的档案早已无从寻觅,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忆也已经模糊不清,只能从传世文献和碑刻等实物资料中去搜集。而近代有些口碑资料尚在民间流传,历史人物的后裔尚在,有些家传谱牒还在,口碑资料的可信度比较高。祝万祉针对不同的时代,运用不同的收集方法,寻找方志资料来源,编纂了康熙《赵州志》。其实,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编纂方志寻找资料来源的方法。
(三)重修州志的资料来源
重修州志的资料来源,也不是千篇一律,也是因地因时因人而宜。
有以传世文献与档案文献并用者。形胜甲于河北,地处京师肘腋之地的涿州志书,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知州张逊创修成书①明陆简撰《龙皋文稿》卷八《涿州志序》载:“成化乙巳,锡山张侯时敏擢守是州。侯才美兼人,治有余力。历览井邑,嘅然兴曰:‘美哉川原,而况今日非昔也,顾图志不作,盛际弗彰,曷以共吾职与!’乃聘州学训导唐舜卿及乡进士高鉴辈俾从事焉。”撰成初稿后,“复得户科给事中唐君用思、府博仇君东之为再加雠校,侯亦手诠次之。凡再阅岁而成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39册第281页。)张侯时敏,即涿州知州张逊。由陆简序可知,参与纂修《涿州志》人员的情况以及成书的时间——成化乙巳年的“再阅岁”,即成化丁未、二十三年(1487年)。可订正乾隆《涿州志》等认为“涿志昉于明成化乙巳知州事张君逊”(乾隆《涿州志》卷一《凡例十则》,清乾隆三十年刻本,第1页a)和“涿志初修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知府张逊”(《河北地方志提要》,第215页)的说法。,弘治六年(1493年),刊刻传世②明孙能传、张萱等撰《内阁藏书目录》卷六《志乘部·北直隶》载:“《涿州志》四册,全。弘治癸丑州守张逊修。”(《续修四库全书》,第917册第72页。)《千顷堂书目》卷六《地理类上》载:“张逊涿州志十二卷弘治癸丑修,守。”(第154页)清范邦甸等撰《天一阁书目》卷二之二《史部二》载:“《涿州志》十二卷,刻本。明弘治癸丑修。翰林院陆简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弘治癸丑,即弘治六年(1493年)。这里的修,即成化《涿州志》刊刻问世。。多次续修。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吴山凤出任涿州知州,认为前志疎略,未臻完备,发凡举例,重修州志,“《事迹》创自今志,其余采旧志者十之二三,续增者一二,更定者过半矣”[24]1a。《事迹志》的《正纪》俱采录二十一史。《杂纪》釆用《新书》《隋书》《古今注》《博物志》《列仙传》《旧唐书》《韩昌黎集》《册府元龟》《北梦琐言》《燕云奉使录》等史部、子部、集部文献。《食货志》则取自赋役全书等档案文献,也就是传世文献与档案文献并用。“遗文轶事搜采甚富,而记载繁简条理秩如。”①乾隆《涿州志》沈初书《序》(第5页b)。民国《涿县志》修志同人《序四》曰:“乾隆乙酉,知州事吴公山凤以前志略倡议重修,万卷图书尽供考订,六房案牍足备参稽,考献征文,补残正误,有条不紊,阅者称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26册第3页。)可见乾隆《涿州志》收集资料丰富,为后人认同。编纂成22卷的乾隆《涿州志》,同治《涿州续志》与民国《涿县志》遵循其体例,随事增录。
有以志稿、旧志与档案文献等为资料来源者。赵州志明清时代多次重修,正德《赵州志》以州县分卷,隆庆《赵州志》按门类分卷,体例为康熙、同治《赵州志》所沿袭。光绪年间,编纂赵州志则分为光绪《直隶赵州志》《赵州属邑志》两部志书,改变了体例。光绪《直隶赵州志》的资料来源,以同治年间赵州州判孟传铸编纂的志稿为主,知州孙传栻“出孟稿相示,俾与旧志参酌。缺者补之,繁者芟之,讹者订之,歧异者考核之。复广为采访,续加编辑”[25]296。在孟传铸志稿与旧志稿的基础上,加工修改,择优而取。“今纲序及田赋、风俗、杂考皆用旧志,山川用旧志,形胜论、星野、沿革、疆域、名宦、职官、名臣、仕迹、武功、忠烈、孝义、文苑、方技诸目,序皆系孟稿,略有删订,其余依类增补。”[25]303同时,注意采用档案文献资料,“田赋关国计民生,不宜简略,今遵《赋役全书》及《通志》所载,详注起运存留之数”[25]303。这样,“体例,遵旧志略加变通;纪述,踵孟稿详为补葺”[25]296,纂修成光绪《直隶赵州志》16卷。
有以传世、档案文献与口碑资料等为资料来源者。同治十一年(1872年),直隶设局重修《畿辅通志》,檄府州县各修方志,并先以旧志献通志局备参考。深州知州吴汝纶奉檄纂修州志,制定《采访志书条例》,包括应采书目,采本境名贤著述,采传状碑志,采金石碑刻,采旧志,采邻境志书,考村庄道里,采河道迁徙,采民间习俗,采物产货殖,采族姓迁流所自,考核舆图,采方言,采人物,采旧事,采古迹等16条,[26]509-516每则都有具体要求。如“应采书目国朝官书,如《大清会典》《太清一统志》《皇朝三通》等书,必应详考。其他古书,则《廿四史》《通鉴》《三通》为纲,而唐、宋、元、明各家诗文集及畿辅名贤所著书为辅。前志搜釆简略,往徉挂一遗万,此宜急补者也。又如《太平御览》《事文类集》《渊鉴类函》及一切类书、丛书,苟有一事足资考证,皆应广为蒐辑,冀免贻讥疏陋”[26]509,规定详细具体。采访志书条例16则,涵盖了传世文献、档案文献、实物资料、口碑资料等,系统全面。丰富的资料来源,断断续续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吴汝纶修纂的同治《深州风土记》22卷,跻身于名志之列。
明清燕赵厅州志书的资料来源,从上述创修、续修、重修三个方面看,每一方面又有多少不同的资料来源途径,笔者归纳为9种类型。之所以厅州志书的编纂者采用这样不同的方法,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条件、所担负的编纂任务和前人编纂的志书所提供的基础,这些都是时代和地域的产物,又与具体的方志编纂者的知识水平、学术视野等有着密切关系。地方志是记述当地社情民事的百科全书,有些资料记录在传世文献当中,有些资料保存在民间文献里,有些资料体现在碑刻等实物资料中,还有些流传在当地人的口碑里。纂修州志时,搜集载籍,眼睛向下,深入民间调查、访问、收集实物、口碑等资料,是获取纂修州志资料的重要来源途径。
三、县志的资料来源
县,是中国古代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县志,在中国地方志中数量最多。县志的资料来源,与府厅州志相比,体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资料来源途径。
(一)创修县志的资料来源
创修县志,有些是新建县未有县志者,有些是几百年未修县志,有些是原志已经散佚,有些是原来县志附载于府州志中等不同原因,导致有些县没有传世单行本的县志。上述诸情况存在的县,所修的县志都可以作为创修县志。当然,也有自以为是创修,当时认同为创修,后人也认同是创修,实则不是者,如明崇祯广昌知县刘世治几次询问广昌县志的有无,当时人都说没有,自己也认同②崇祯《广昌县志》刘世治《广昌县志序》载:“广昌之志书,前之有无,皆不可知。”新上任知县刘世治问曰:“‘何无志书?’答曰:‘从来无有’。窃讶而疑之。是邑,壤地虽小,犹是中土文献之邦也,何独于志而无之。无何至境,谒庙毕,有乡之缙绅暨青衿来谒,不佞起而请曰:‘斯亦礼教地也,何无志书?’诸公齐声唯曰:‘原无有志’。一客起而对曰:‘云中,自石晋蹂躏以来,得失不常,典籍散逸,他不尽知,即相近之灵丘亦未有志。’不佞窃自思曰:‘此亦阙典哉。’”(《明代孤本方志选》,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第12册第426-428页。)可见,广昌无志,成为当时广昌人的共识。,所修崇祯《广昌县志》,被人认为是创修,实则不是③康熙《广昌县志·广昌县志凡例》载:“旧志创修自三韩刘公世治,续修自新乡王公佩琦,未及刋布,仅存选举以下四志篇首叙论。旧本岀学博吴公继诚之手,逸本是王公所作。”(清抄本,第1页)清朝人认同崇祯《广昌县志》是刘世治创修。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四《新志》载有:《蔚州志》《广灵县志》《广昌县志》《灵邱县志》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228页)可知,明英宗正统六年(1414年)之前,已经有《广昌县志》,只是广昌人不知道而已,认为200年后所修的崇祯《广昌县志》是创修。。又如万历《涉县志》,也是自以为是创修等①《明清民国涉县志校注》收录的顺治《涉县志》载:明知县李天柱《〈涉县志〉叙》曰:“因究情厥志,闻为阙典。嗟嗟!光[先]余而继治者,岂曰乏人,而竟未有创成以为永久传?夫无志,是无涉也。”(中华书局2008年,第86页)因此,李玉柱编纂了万历《涉县志》。任澄清《增修〈涉县志〉序》曰:“自上党李公创修县志二帙,以存大略。”(第90页)清知县刘璇《纂修〈涉县志〉叙》曰:“上世修志者不可考,及先令李天柱栋宇延乡先生受庵李君辈,采得残断旧草一册,参互考订,著为上下二卷,时万历戊戌岁也。”(第96页)并收录《创〈涉县志〉凡例》(第102页)。由上述,可见李天柱自认为是创修《涉县志》者,后来知县也认同。实际上,在李天柱之前有嘉靖《涉县志》,保存在宁波天一阁者,收录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中,化身千百,传到了当代。。因创修者身份、家庭背景与文化素质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资料来源。
有以传世、档案文献与口碑资料等为资料来源者。如明南宫知县叶恒嵩,要编纂县志,但发现“两汉以下诸书宫之文献,仅记什一于千伯,郡州志已科条之矣,蒐剔其轶,亦无有见于他说,阙如也”,资料极为缺乏。经过编纂者“相助讨论,旁罗往牒,累集成编”[27]2a。往牒,即官府档案文献。邑人刘汀认为,编纂者“披猎载籍,研涉经史,查之乎风谣,谘之乎父老,又广采诸荒垅野迹、残碑断石之中”[27]1a。从刘汀所言看,载籍、经史属于传世文献,风谣、咨询父老等属于口碑资料,荒垅野迹、残碑断石属于实物资料等。以此作为创修县志的资料来源,采用“絜要领,正名实”[27]1a的方法考察资料。创修成地理志、官师志、杂物志、艺文志等9志5卷的嘉靖《南宫县志》。又如邯郸县②2016年9月30日,撤销邯郸县,其辖区分别划归邯郸市邯山区和丛台区等。,是战国赵国、两汉赵国的国都。但明成化以来百余年县志未修。邯郸举人、陕西巩昌府通判张成教,对于“或有谈说古今之务,抵掌而称《赵世家》者,即一时耆旧卒卒罕所置对。此子大夫之所深耻也”,在邯郸知县张第支持下,越境购书,多方征集,“乃复忘其謭昧,为之搜佚典,窜僻闻,谬为诠次,以成叙事之言”[28]1。所谓“搜佚典,窜僻闻”,不是仅仅着眼于从《史记》中汲取营养,“惟夸武灵之雄,侈平原之侠,搤捥相如而揕胸马服,则兹志也是不过谈赵之谱而已,嗟夫!与无志奚殊焉!”而是注重“志者,志其大者也,民之利病,政之因革是也”[28]1。收集邯郸县历史上的重要典故,网罗与此典故相关的诗文著述,以见古今影响,属于传世文献。注意明代邯郸发生的重要事件,与相关碑刻、文学著述联系在一起,属于档案、实物资料。并记述一些亲身经历的事件与熟悉的人物,属于口碑资料。根据上述资料,编成了贤淑志、选举志、杂事志等10志8卷的万历《邯郸县志》,成为了流传至今的邯郸县9志的首志。
有以方志文献与口碑资料为资料来源者。如蠡县无志书,知县李复初,“参之众议以尽其详,质之父老以拾其遗,考之载籍以穷其远,准之《一统志》以定其极”[29]50。集思广益,收集口碑资料、传世文献和方志文献,创修出封域、建置等5卷的嘉靖《蠡县志》。又如元城县(治今河北大名县大名镇,1949年8月并入大名县),历史悠久,向为天雄附郭而无专志。康熙十一年(1672年),朝廷修纂《大清一统志》,元城知县陈伟遵命修志,发布《徵修志启》,申明修县志之意。刊发《□□□修县志告示》,征集资料,“凡属地方城郭、署舍、建置、田赋、祥灾、官师、政绩、选举、科名、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贞士、逸民、仙释、流寓、祠宇、坊表、陵墓、艺文,有关名教,甚切吏治,除启访缙绅、学校外,合行晓谕各村都里耆民老人等知悉,即将所见所闻,据实呈报,务在详确,不得虚诞。的限某月日赴县投递,以便查核,编成全书,申报宪台,刊垂不朽”③康熙《元城县志》卷首《□□□修县志告示》,《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0册第16页。参阅《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册第303页。。修县志告示划出了征集县志资料的范围,并动员人们到县里据实呈报。并“搜郡志摭拾成言,曰质之简编也。询搢衿网罗缺失,曰补之谠论也。采耆旧探讨遐广,曰得之四隅也”[30]7,编纂成“节取于府志者十之六,博征诸民献者十之四焉”[30]16,包括宦业志等6卷的康熙《元城县志》。上述县志的编纂,体现出方志文献与口碑资料为主的资料来源特点。
有以方志、档案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者。如沙河县无志,万历十六年(1588年),知县姬自修以创修县志为己任。万历十七年九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何出光发《为创修县志事》的牌文,督促修纂。知县姬自修“于视事之讌,相与肆考古今传记,博采图经志典,广咨学士父老见闻,参以郡志,间附已意,据事直书,鲜有饰言”[31]2a,“访诸民间得遗藁一帙,其词多附会而事且略弗核”,令教谕王九秋、训导李国士审核编纂,知道沙河县有些事已记载在《顺德府志》中,乃“上请得若干卷,一一准之,而往牒可搜、舆论可采、令甲可按者,蚤夜惟是兢兢焉,务于参伍精而评品定,然后纂入”[31]75b。由此可知,图经志典、《顺德府志》、民间遗稿是其资料来源,又与档案文献、口碑资料等相核查,然后编入到县志中。创修成有典祀志、选举志等8类、分为上下两卷的万历《沙河县志》。
有以旧草志和方志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者。如武安县未有志书,是为阙典。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武安县教谕陈玮等人,“旁搜博采得旧草志一册,事实踈而文亦荒鄙,复究《大明一统志》、彰德郡志、历代史册诸书,及邑之缙绅耆,庶粗得一二之绪余”①嘉靖《武安县志》陈玮《武安县志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册第2页)。嘉靖《武安县志·修志凡例》亦载:“武安旧未有刻志,后得草志书一册,率出于臆见之私而各立门户者也。予夺罔公,文亦鄙俚。余虽不敏,惟以刚直至公为主,稽诸载籍,采诸舆论而后敢纂入,其取咎于人否不睱计也。”(《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册第11页。)既可与上述互证,又可见其史源,以及考察资料的态度。,“名宦乡贤,本诸《大明一统志》、彰德郡志乃载。其去任名宦增入一二,则本诸缙绅士庶舆论,余无所私”,“节孝尚义,曾经褒旌及有司核实以表扬之者,皆足以为世动也,备书”[32]12。由上述可见,旧草志、《明一统志》《彰德府志》以及口碑资料,是编纂嘉靖《武安县志》的主要资料,同时参考了传世文献和档案资料,编纂成了食货志、祀典志等9志4卷的嘉靖《武安县志》,作为武安创修之志,完整地流传到了现代②《河北地方志提要·〔嘉靖〕武安县志四卷》载:“卷4艺文志,今不存。”(第421页)也许南京图书馆藏胶卷未有嘉靖《武安县志》卷四《艺文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册,不仅有《艺文志》,还有罗宏撰写的《武安县志跋》(第143-144页),可知嘉靖《武安县志》有完本。。又如香河无志乘,知县沈惟炳在沈万钶志稿的基础上,“蒐佚典,稽故实,而鳞次之,于郡志得其一,于邻志得其一,于吏牍得其一,时复博咨绅弁,旁诹农樵,久之见闻所摭,渐习渐真,每有得,亟泚笔成录,日记月胪,略具质文之概”[33]6-7。旧志稿、府县志、档案文献,构成了主要资料来源,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创修成兵防志、礼乐志等11卷的万历《香河县志》。再如怀安县明代为卫,无县志。清代改为县,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县殷邦翰等创修县志初稿,雍正年间,知县武一韩续修志稿,怀安县人周昇撰拾遗稿,三稿均未刊。乾隆六年(1741年),怀安知县杨大昆奉檄修志,“发箧陈书,网罗放失旧闻,始就殷、武二稿,讲去其非而求其是,又本之列代史,参诸镇志,参诸通志,参诸原郡邑志,综核纷纭,务在徵疑考信,断以义例”③乾隆《怀安县志》杨大昆《序》(清乾隆六年刻本,第2页ab)。乾隆《怀安县志》钱戢曾《纂修怀邑志序》载:“逎悉意纲罗遗书,于诸闻见,必本诸府志以求其合,必参诸省志以观其通,必要诸历代史传以征信而考疑。”(清乾隆六年刻本,第4页b)可与杨大昆序言相互印证。,以殷邦翰、武一韩等志稿为基础,参考《宣府镇志》等,修成城池、武备等24卷的乾隆《怀安县志》,成为现存最早的《怀安县志》。还有乾隆时,阜平县知县邹尚义,因“邑乘芜缺,无所取征。旧有志稿若干卷,非典要所存,憬然念之,于是采缀省郡志,延询故老,以酌旧稿之去留,正其谬讹而修补其散佚”[34]2。工部右侍郎李宗文说,邹尚义“念天下郡邑皆有志而阜平独缺,遂引为己任,讨旧闻,询故老,搜蠧简,核典实,辑成邑志若干卷”[34]2b。两人所谓“旧有志稿若干卷”与“搜蠧简”含义相同,可见其资料来源,有旧志稿、省志、府志,有故老的口碑资料,志稿、志书占主要部分。并与友人往复商榷,编成乾隆《阜平县志》4卷,也是阜平县第一部传世的县志。由上述可见,编纂县志是诸多县官的心愿,是薪火相传的事业,前人编纂的志稿,为后人提供了基础,后来人继续编纂,实现了前人的心愿。
有以方志文献作为主要资料来源者。如赤城县,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改卫为县,而无专门的志乘。因事久而湮,赤城卫册失传,档案源流茫昧,献渺文微,不利于资料的搜集。再加上“地志之作,创始与续修不同,边陲与内地又不同。续修者踵事增华正讹订谬善矣,然不若创始者之遐搜博考戞戞乎其难之也。内地文献足征,甄综差易,边陲为用武之地,碑版荒凉,父老愿朴,苟非博极群书虚衷体访,未易得其实而纪之”[35]9-10。知县张良标、廖三友先后撰有志藁,事属草创,多有抵牾矛盾。知县孟思谊知难而进,旁搜远绍,“以三路志、《宣化府志》为粉本,而证之诸史,参之名集,通之旁邑志。剔藓剜苔,衔姜拾蠧,乃迟之又久,慬而成书也”[35]15-16,也就是乾隆《赤城县志》的资料来源,“大半取材《北中三路志》《宣化府志》,更以列朝国史、《畿辅通志》、宣属各邑志,与夫名家文说诸集,参考成书”[35]20,着重收集方志文献,作为资料来源,注重各种文献资料之间的互证考察。汲取方志文献、国史与文集的精华,编纂成有建置志、武备志等八卷的乾隆《赤城县志》,成为《赤城县志》的嚆矢之作。又如蔚县,明代为蔚州卫,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改卫为县。“蔚前为卫时无志,即后为县时仍无志,间有附见州志中者,亦多缺略未备。”[36]13使人遗憾,耿耿为怀。知县王育榞以修志为己任,“从向皋先生得明《宣镇志》一部,《两镇三关志》半部,至国朝所修《云中志》则终不可得,乃即两志所载,参以州志之仅存者”[36]13。即以《蔚州志》《宣府镇志》等方志文献,作为编纂蔚县志的主要资料来源。搜集排比,分门别类,“详加考订,互为参稽,权衡务平,笔削唯谨。事必穷其本末,宁详无略;人必核其初终,宁严无宽”[36]13,创修成31卷的乾隆《蔚县志》。
有以档案文献和口碑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者。如清苑县久无志乘,知县李廷宝,“延访询之故老得其一二焉,搜之敝牍得其三四焉,已而考之荒碑、索之野史得其五六焉”[37]304-305。可见资料主要来源于口碑资料、档案与传世文献,笼统地说是“远稽坟典,博综谱牒,旁咨故老,参订师儒”[37]1,据此创修成嘉靖《清苑县志》6卷。又如正统六年(1414年)成书的《文渊阁书目》卷四《新志》载有《宛平县志》①《明实录·明太宗实录》卷二〇一载:永乐十六年六月“乙酉,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命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谕德金幼孜总之。仍命礼部遣官徧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第2 089页)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一《列朝·访求遗书》载:“国初克故元时,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尽解金陵。又诏求民间遗书。时宋刻板本,有一书至十余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贮书,每本以一部入北,时永乐十九年也。初贮在左顺门北廊,至正统六年而移入文渊阁中,则地邃禁严,事同前代矣。至正统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内署诸书,悉遭大火,凡宋元以来秘本,一朝俱尽矣。自后北京所收,虽置高阁,饱蠹鱼,卷帙尚如故也。自宏政以后,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题本》载:“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回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近奉圣旨移贮于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写完一本。总名曰《文渊阁书目》。合请用‘广运之宝’钤识,仍藏于文渊阁,永远备照,庶无遗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5册第114页。)所记与《万历野获编·访求遗书》可以互证。《文渊阁书目》卷四《新志》往字号第一橱书目,载有从《顺天府志》1册到《隆庆州志并永宁志》3册,著录北直隶地区的6部府志,18部州志,130部县志,共计154部志书。这些当是永乐十年(1412年)、十六年,朝廷两次颁布《纂修志书凡例》、“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以后,府州县所撰写的志书,故称“新志”,以与《文渊阁书目》卷四暑字号第一橱书目的《北平府图志》《宛平县图志》等“旧志”相区别。这些书,除了《顺天府志》《隆庆州志并永宁志》标明1册、3册外,其他志书既没有作者、年代,也没有标明卷数、册数。再则,《文渊阁书目》明代并未刊行传世,清代才有抄本、刻本,所载志书深藏于皇宫文渊阁,民间传本很少,故多数明代府州县志编纂者看不到,也就往往与《宛署杂记》作者沈榜一样言“县故无志”了。,而万历十八年(1590年)任宛平知县沈榜的发现,“县故无志,而掌故案牍又茫然无可备咨询。自窃禄以来,随事讲求,因时擘划,或得之残篇断简,或受之疏牍公移,或访之公卿大夫,或采之编氓故老,或即所兴废举坠,捄弊补偏,导利除害,发奸剔垢,其于国家之宪令,非不犁然具备也。而予始求之则无征,自予行之乃始有据”[38]3。上述所言资料,涉猎广泛,既有官方文件,又有民间口碑,更有自己为官施政的措施,主要属于档案文献与口碑资料。利用“退食之暇,杂取署中所行之有据而言之足征者,随事记录,不立义例,不待序次,聊识见闻,用备掌故。久之不觉盈帙,固命吏稍缮之为二十卷”[38]4,命名为《宛署杂记》。“其书始于宣谕、建制,终于遗事、遗文,详于内政、民风、山川、贡赋,而略于人物,究以稗官附焉。惟经费书则备极覼缕,几于隶首不能得”[38]1,虽无《宛平县志》之名,而确有其实,为万历《顺天府志》所关注,为康熙《宛平县志》《光绪顺天府志》等所著录、引用,是现存最早的宛平县志文献。
(二)续修县志的资料来源
续修县志的资料来源,也因地、因人、因时而有所不同。
有以传世、方志文献为主要资源来源者。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丰润知县吴慎,因县志数十年未修,“乃博考群籍,衷诸正史,参之传记与父老之传闻、乡先生之淹雅流通者,下至谚语卮言,有关必录”[39]4,广泛搜集资料。采取“据旧志,删繁补漏,考故增新”[39]1a的方法,以“志乘首重文献”的观念,没有书就借,“史则借观于鲁生凤翥,《畿辅通志》则取资于学校,《使辽录》《北辕录》《金国行程》《方舆纪要》《燕山丛录》《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奉使行程录》《京东考古录》,则得之友朋行笈中”[39]3b。多方收集传世文献。在依据旧志、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纂辑成8卷的乾隆《丰润县志》。
有以传世、档案文献与口碑与实物资料为来源者。如雍正年间,邯郸知县郑方坤自称:“汲汲皇皇,簿书之暇,必勤此事。无论名公硕彦、令典献章,必详必究;即残碑断碣,皆为足据之文;野老农夫,尽属可询之献,弥缝补缀,倘亦千百之什一乎!”[40]1-2张洮称为:“辨劫灰于轶事残编,停杯慷慨;剔剥藓于荒祠废塜,立马踌躇。”[40]190上述所言,资料来源涉及到传世文献、档案文献、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4个方面,编成了拾遗补缺的雍正《邯郸县志》
有以民间文献和方志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者。如肥乡知县李鹏展委派教谕赵文濂纂辑县志,因肥乡县屡遭水灾,书版漂没,书籍散亡,档案残缺,资料缺乏。只得“搜旧家之谱牒,访古庙之碑文,问先贤遗事于子孙,咨月旦乡评于父老,有善率录不以微末遗也”[41]6b-7a,眼睛向下,搜集民间文献资料。“旧志重修,特因原稿少如,修葺本朝人物事迹缺略过多,兹则援据府志益以见闻,误者正之,繁者删之,阙者补之,要期表扬前烈、传信后人。”[41]12a抄录府志中的相关资料,运用档案资料,“职官年代久远,房稿无存,难以编葺,兹从司房抄录”,“赋役,旧志全抄《赋役全书》,历年既多屡奉文裁革,与旧志逈不相同,兹仿府志一以现行事例为断”[41]12b,把档案资料纳入到县志中。赵文濂等人从身边资料收集做起,多种资料并收,编成36卷的同治《肥乡县志》。
有以实地考察收集民间文献为资料来源者。具有特色的县志,不仅仅是传世文献的汇编,也不全靠妙笔生花的行文叙述,而是那个时代面貌的反映,需要编纂者实地考察和民间文献收集。如乾隆年间,永清知县周震荣邀请章学诚主纂《永清县志》,“以族志多所挂漏,官绅采访,非略则扰。因具车从,橐笔载酒,请余周历县境侵游,以尽委备。先是宪司檄征金石文字上续通志馆,永清牒报荒僻无征久矣,至是唐宋辽金刻画一十余通,咸著于录。又以妇人无阃外事,而贞节孝烈于方志,文多雷同,顾者无所兴感,则访其见存者,安车迎至馆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愿至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后接见五十余人,余皆详为之传。其文随人更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42]179。知县周震荣提供了实地考察的条件,编纂者章学诚不辞辛苦,周历县境,实地考察,获得了许多新资料,打破了贞洁烈女记载的僵化模式。又如清广昌(治今河北涞源县涞源镇。1925年改为涞源县)知县杜登春,带人“跋涉山谷,谘诹野老,手摩碑记,移会邻封,笔其山川疆域,制为《广昌县舆图册说》”[43]4,以知县的身份跋山涉水,走访野老以获取口碑资料,手摩碑记以获取实物资料,向邻县调查档案资料,广寻博采到比较齐全的方志资料。再如天津县廪生蒋玉虹,“生平留心文献,以县志自乾隆四年后阙焉未修,立志踵为之。采访阅二十余年,始终不倦。凡故家谱牒,前贤箸述,必思搜求得之。荐绅诵说之言,父老传闻之事,靡不一一记载。每裹粮,操笔砚,徧行荒郊败寺中,遇有残碑断碣,辄掘土浣苔摩挲,辨识且读且录,积年既久,裒然成帙。嘉庆中,知县任衔蕙欲就其稾删润成书,未果行。迨同治续修县志,乃从其家购得据为底本,是以乾嘉之际乡邦掌故尚不至于全湮者,实赖玉虹之力”①民国《天津新县志》卷二一之三《人物三·蒋玉虹》(《中国地方志集成·天津府县志辑》,第3册第384页)。同治《续天津县志》卷一三《文苑·蒋玉虹》亦载:“立志续修,乃采访数十年。故家谱牒,前贤著述,靡不搜求。搢绅诵说,故老傅闻,靡不登记。尝操笔墨、油纸、大便面,遍行荒郊破寺中,剔残碑断碣,辨其字画辄录归。凡志书所应有者,分门编纂,稿本己积数十帙,不厌繁多,惜未成而卒。”(同治九年刻本,第7页b)。两志大同小异,可以相互补充,使其更为完善。。廪生蒋玉虹执著追求,不畏艰难,多方调查,以一己之力收集碑刻、族谱和口碑等资料,聚沙成塔,为同治《续天津县志》打下了基础。还有,枣强知县单作哲,乾隆“壬申,乃徧咨于绅士,令各类叙家传与耳目所闻见者,悉举于籍,以待讨论。复命胥史数辈,分诣村聚录残碑断碣之可辨者,以备参互”[44]1a,在此基础上编纂了乾隆《枣强县志》。上述4人,身份不同,方法相异,但通过社会调查与实际考察相结合,收集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以作为县志的资料来源则是相同的。
有以方志文献、口碑资料为资料来源者。如清嘉庆三年(1798年)十月,广宗知县李师舒,“取县志读之,殊多缺略”[45]1a,并且百余年未曾续修县志。因此于嘉庆七年(1802年),“延故老,咨荐绅,广为采访,详加考证。官师、选举、宦迹三志增补排叙,灿若列眉。尤于人物、艺文二志加意搜剔,盖孝义贞烈之行,为一邑风化所关,而发潜德之幽光,表名贤之事迹,畅风扢雅,鼓吹休明,非文章无以发之,广宗虽微区,固不可忽而不讲也。其余体例悉仍其旧,纲举目张,裒然成集”[45]1b-2a。由上述可见主要增加口碑资料。不仅沿袭康熙《广宗县志》的体例,而且利用其原版增加的新资料再雕刻新版,新旧志版字体明显不同,所增新页版心用“新添”字样标志得很清楚,由此续修成了嘉庆《广宗县志》12卷。
有以方志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者。同治《元城县志》资料的来源比例,是“全志仍旧志原文者十之四,节取府志者十之三,博征群书及采辑民献者亦十之三焉”[46]48,方志文献占到了资料来源的十分之七。考虑到地方志文献容易损失毁灭的状况,抄录沿袭旧志资料,突出了地方志资料连续性的特点,有助于乡邦文献的积累。此种方法有利于保留地方资料,也容易导致新旧方志资料陈陈相因。民国《广平县志》的编纂者也说:“县志自清康熙十五年重修以后迄未续修,文人凋谢,县卷无存。此次采录,得于府志者十之五,得于访闻者十之二,阙而待补者十之三,增辑之责惟赖后贤。”[47]11可见方志文献占到了十分之五。民国年间在以方志文献为资料来源上,与明清一脉相承。上述所说县志资料来源比例未必那么准确,但可以肯定县志的资料来源中方志文献、口碑资料占的比重要比府志大些。
(三)重修县志的资料来源
重修县志的原因并非完全相同,编纂者身份亦且相异,资料来源的类型也非仅是一种。
有以传世文献与民间文献为主者。柏乡县志较早者,笔者目前所知正德《赵州志》以州县各自为卷,卷七即是《柏乡县志》,篇幅不大,内容齐全,但没有单行本传世②县志保存在于府州志中,正德《赵州志》以州县各自为卷是一种类型,还有按门类析书等类型。如嘉靖《威县志》王舜臣《后序》载:知县钱汝冲言:“威虽小邑,亦文献素称地也。顾旧无志,其汇载于郡志者大而略也。”(《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册第528页。)嘉靖《威县志·威县志凡例》亦言:“威县旧无专志,汇载于郡,皆其大者,嘉靖戊子,知县钱术始遵《大明一统志》布列条例,因事比类而增广之,创为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册第547页。)汝冲,即钱术表字。明代威县隶属于广平府,威县志的内容汇载于《广平府志》中。又如康熙《宛平县志·顺天府宛平县志凡例》载:“县旧无志,统之于府志中,以其附郭也。”(《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第5册第1页。)再如隆庆《丰润县志》谷峤《叙丰润志》亦载:“旧无邑乘,凡疆域、山川、人物、政治之迹俱附州志,然亦略矣。”(明隆庆四年刻本,第7页b。)明代丰润县隶属于直隶顺天府蓟州。县志附于府州志的形式相异、原因不同。现在有的县把府州志中的记载辑录出来,如《明清民国涉县志校注》附录了嘉靖《彰德府志·涉县》(第63-72页),辑录出有关涉县的资料。。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创修单行本《柏乡县志》。后来又有续修的万历、顺治《柏乡县志》。康熙年间,魏裔介两次重修《柏乡县志》,分别成书于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十九年(1680年),其序曰:“余于政事之暇,博览载籍,兼考前辈诸老先生文集、近日海内与里中诸君子篇什所及,暨荒草烟榛牌版所存,向偶有遗漏者并收采补入之,而《民社》一志考据典礼,于嘉惠氓黎之意尤慇慇焉。”[48]209-210载籍,指书籍、典籍,又可称传世文献。文集与诸君子集等,刊行者可划入传世文献中,有些尚未问世的稿件,可归为民间文献。碑版,可归入金石,又可作为实物资料。又言:“邑之户口几何?家钱谷几何项?人物之臧否何分?节孝之真伪何辨,何者为文治所系,而诗赋铭传之必详。何者为武备所资,而保甲刍糗之必审。条分缕析,而操觚岂易易哉!”[48]226-227这不但涉及到“诗赋铭传”的资料来源,而且是魏裔介20余年3次增补、编纂《柏乡县志》的亲身体会之言。又言:“是卷参酌诸名公志书,而订以己意。考证史传殆将百家,网罗遗文爰历十载。”[48]233诸名公志书,也包括了由柏乡魏氏三代人编纂的嘉靖、万历、顺治《柏乡县志》。魏裔介父子两代人,不求报酬,自觉从事《柏乡县志》的重编之事,前后历时二三十年,遐搜博稽,资料来源领域之广,收集时间之长,资料数量之多,在《柏乡县志》编纂史上,独树一帜。康熙十九年(1680年),修成了民社志、诰敕志、碑铭志、序记志、诗赋志等10卷的《柏乡县志》。
有以传世、档案文献与民间文献和实物资料为资料来源者。如《定兴县志》,从明嘉靖年间起,历经100余年屡次垂成而废,康熙十二年(1673年)才得以创修问世,又经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续修,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知县张主敬设局,因病解职在家的陕西巡抚鹿传霖邀请掌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晨重修县志,参与义例商榷、志稿鉴定。资料来源,“以熙隆两志为轮辂羹酒,而益以近代之人文国故”①光绪《定兴县志》卷首鹿传霖《光绪重修定兴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2册第193页)此文为幕僚樊增祥代撰,见樊增祥著《樊山集》卷二三《重修定兴县志叙代》。(《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606册第752页。),以康熙、乾隆《定兴县志》作为主要资料来源,广泛收集《周礼》《汉书》《分省人物考》、楼钥《北行日记》、陈僖《燕山草堂集》、陈子龙、杨维桢、李东阳著述等传世文献,注重搜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地理总志文献,注意收集雍正《畿辅通志》《日下旧闻考》《范阳识略》《容城志》《新城志》《安澜志》、府志、旧志、康熙志、乾隆志等方志文献,将墓志、塔碑、神道碑等实物资料抄录入志中,把拓片等实物资料纳入到县志中,收录县册等档案资料,将行状、鹿氏谱、耿氏谱中丞家传等民间文献收入到县志中,将采访册等口碑资料收录在志书中。资料来源广泛,注明来源出处,编成了集成之作的光绪《定兴县志》。
有以方志文献和民间文献为主要资料来源者。如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山东道御史、邑人乔璧星,受临城知县程鹏抟委托,主持续修《临城县志》,“旧志所存,繁以删之,而要无不举,补葺其所不及载□十居其四”[49]2a,可见是以旧志资料为基础,汲取其精华,补充其不及。“凡所纪录,皆蒐往昔残碑断碣与夫长老传记、里巷舆评,不信不载,不公不载”[49]1a,补充的主要是民间文献与实物资料。重修成贡赋志、述考志等7卷的万历《临城县志》,因旧志散佚,此书成为现存最早的《临城县志》。又如道光十年(1830年),南宫知县周栻设局编纂县志,遵循陆陇其《灵寿县志》的程式,参考《畿辅通志》《冀州志》的体例。旧志散佚者多,完整者仅胡景铨修康熙《南宫县志》,但“胡志后距今156年,时代旷隔,搜罗非易。今细心考核各志,以类叙入。《官师》《选举》二志,赖有邑人上舍杜兆震纪录以为蓝本。《名宦》《人物》《艺文》尤难采择,今据邑人齐维藩《椿庭集》及各家志乘实迹可据者参酌编录,惟期弗遗弗滥。其年远无稽者无从搜求,徒滋扼腕”[50]5a。由此可见,体例遵循陆陇其康熙《灵寿县志》后,体例变了,资料来源大成问题,只得以旧志和民间文献为主,编纂成风土志、事异志等12志16卷的道光《南宫县志》。
县志的资料来源,笔者亦分为创修、续修、重修3类进行梳理,粗略归纳为15种类型,既有与府厅州志相同的类型,又有着自己的特点,也就是口碑资料、方志资料所占的比重更大些,在方志资料中,县志稿所占比重比较大,数量比较多,这是县志的特点,因为县的管辖区域范围小些,作为个人有条件收集资料,有时间、有精力,可以撰写出县志稿,这样也就形成了一些民间的县志稿。至于能否有刊刻的机遇,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也是县志的局限,因为宋元以前的那些地方志先驱的著述——记、图经、土地记、风土记等早已散佚,幸运的也只是留下了只言片语,明清人编纂县志只能向传世文献寻找资料来源。再则,许多县域范围内的人物、事件上不了国史,因此,只能以方志文献或流传民间的县志稿作为资料来源之一。
四、明清燕赵府州县志书资料来源概观
编修、编纂地方志书,又称为辑、编辑、纂辑、增辑、重辑、修辑、汇辑、补辑等,既标明了纂修地方志的方法,也表明了志书的资料性质,从侧面说明了资料来源的重要性。明清燕赵府州县志资料来源,上述归纳为创修、续修、重修三大类别,梳理为33种类型,已分别叙述如上,以下再稍作概括性观察,略述管窥蠡测之见。
(一)府州县志书资料来源的共同性
明清时代,府州县志的撰修,是当地的大事,往往会有上下公文的往来,公告民众的檄令、文移,有关方志采访的条例等。时过境迁,这些当时习以为常的告示、檄令、文移等,多数已经销声匿迹,不好寻找,偶尔发现一件也十分宝贵。我们只能从府州县志的序言、凡例等中去查询其资料来源,有些序言、凡例中也没有方志资料来源方面的记载。只能从只言片语中去挖掘有关资料的来源情况,这使得我们对于明清时代燕赵府州县志资料来源的考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我们也只能从这些有限的资料中去分析、去探讨。
从文献类型看,经史子集等传世文献,奏议公牍、赋役全书等档案文献,碑刻、墓志等实物资料,家谱、族谱等民间文献,民间传说、采访调查资料等口碑资料,是府州县志资料来源的共同源头。具体到某种府州县志来说,5种文献不一定全部都有,比重各类志书也有所不同,均是因时因书而宜、因地因人而异。
从记述的时间角度看。对宋元以前的记载,主要依据与本地有关的纪传体正史、诸子、文集、金石碑刻等文献。对明清以来的记载,随着编纂方志的推进,方志文献数量的逐渐增加,方志文献也成为资料来源之一。也就是宋元以前的远事以传世文献和实物资料为主,明清以来的近事以方志文献、档案文献、民间文献、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为主。
从志书的创修与续修看。“大抵始作之难在考古,续志之难在证今。考古者,辨九州之星野,审三代之损益,并数千百年之人物盛衰,古迹存没,非博物之君子弗能至。已成之后,踵而续之,惟在于搜之以勤,取之以慎。”[51]5-6创修与续修方志有不同的难点——考古与证今。创修方志更注重资料的广博,续修方志更需要方志编纂者的谨慎勤奋。创修与续修对于资料来源的着眼点也有区别,创修、重修的府州县志书,更注重传世文献、档案文献的收集,参考实物资料和口碑资料等。续修的府州县志,着眼于增补缺漏、订正讹误,更注重收集档案文献、民间文献和口碑资料。
从收集资料来源的方式来看,多种多样。
有购买、借阅图书资料的方式。这是普遍的收集文献资料的方式。张金吾言:“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52]240读书做学问,首先有书可读,购书、借书、抄书、藏书等是解决无书可读的办法。个人治学如此,官方编修志书更是如此,既要查阅传世文献,也要查阅档案资料等,前提是有书籍、档案可供查阅,然后把有关资料摘录出来,方能收集到相关资料以备采用。上述列举了吴汝纶《采访志书条例》的内容,魏裔介凭籍着自家的藏书,张成教越境购书,谢庭桂借书于故旧,吴慎千方百计借书等,这是一般的收集资料的途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有征集资料的方式。府州县志是官书,主持编纂者是各级政府官员,编纂者有些也是官员——学官占多数,他们也拥有行政资源,因此,很多时候发布告示等征集①除前文已经引用府州县告示等公文外,还有一些,如康熙《续滦志补·世编·滦州为蒐辑志书以光文献事》附《学政条约·一蒐文献》曰:“顷闻郡邑志书多就残毁,有司簿书旁午不暇整顿,百余年间,见闻断绝。吾谓此事惟敎职当专主之,每月督课诸生外使其随意笔录,据伊里中所有菑祥、水旱、风土变迁及一切忠臣孝子、贞夫节妇、高贤耆寿、乡党善人,裒集成帙,敎官汇季申报。本院再加斟酌续成志书,吾将以此定师生之学识取进退焉。”(《清代孤本方志选》第二辑,线装书局2001年版,第1册第3-4页。)这是提督学政命府州县学官督课生员收集本地方志资料。又如孙杰主编《任丘市志》第十八编《杂记·任丘县修志告示》载:“县必有志,将以章往而示来。志必有事,藉以信今而传后。若非博采群言,安能杜撰成卷。所有科条全行昭示,尚祈士庶逐款对。”开列出23项具体内容,“凡所具列,望我任源故家夙耆,掇拾旧闻。老师鸿儒,搜罗往迹。开揭陈言,逐日投县。中有博览广记足资考订者,以礼优隆。中有片善寸长可裨风教者,以类甄录。或逸才隐德人不及知,或音节孤操众所不与,或身兼六艺之长而〔不〕遇于时,或学贯三才之蕴而不屑于仕,俱宜据实呈报,以凭显微阐述”。(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58-759页。)这是县官发布告示征集县志资料。上述两件公文,发布官员身份不同,命令下属收集呈报资料则是相同的。,命令下属机构、人员提供相关资料。征集是明清方志收集资料中使用较多而得心应手的方式,也是地方志编纂中具有特色的征集资料的方式,古今沿用,行之有效。
有社会调查资料的方式。调查古城遗址,调查碑刻资料,调查口碑资料,调查民间文献等。在资料来源相对匮乏时,社会调查方式对开辟资料来源所起的作用更大。明清府州县方志编纂都会运用社会调查的方式,相比较州县志的社会调查资料占的比重大些,采访调查的人员,主修县志的知县,府州县的主要纂修者,以及官吏,都会去调查,更多是由学官、生员等来担当其任务。有时官府支持方志编纂者调查访问资料,编纂乾隆《永清县志》的章学诚,在两年时间内走遍了全县,发现了许多新资料,再加上精心编纂,使乾隆《永清县志》成为了著名方志。反之,得不到行政权力的支持,虽然有收集方志资料的热情和毅力,也很难取得圆满成果。如天津县廪生蒋玉虹,集中精力为《续天津县志》而遐访冥搜,但因为“玉虹一介寒士,力不能多致书卷,又不能征取官牍,但凭耳目所及,随手录存”[53]530,因此,至死也未编出《续天津县志》,但留下了《天津志稾》,为后人编纂提供了基础。
有查阅档案的方式。有时即使收集档案资料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持,行政权力一般也是有范围的,超出了其范围收集资料也很难。清同治年间,通商大臣崇厚聘请前云南盐法道、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提调吴惠元编纂《续天津县志》,在崇厚权力范围内收集资料很方便,但“至必不可不续者,无册可稽,寓书都门与省垣各署详查,迄未见覆,而历时既久势难再待,白于公先付剞劂以俟续补”[54]8b-9a。虽然是奉命编纂,本身也是官员,但其他部门上司不予理睬,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大致归纳为上述4种方式,其他独特的征集资料方式,不再一一列举。
(二)府州县志书资料来源的特点与相互为资料来源
府州县志书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行政层级不同,在资料来源上也就显示出范围不同、追求不同。如多数的府志在资料来源上,收集的范围广、数量多,标注得清楚而规范,相比之下,州县志就相形见绌了。又如府州县志都有以未问世的志稿为资料来源者,从数量上看,县志多于府州志。从编纂者身份来看,县志稿多为当地士绅,府州志稿多为在任、前任官员。这不仅与辖区范围的大小、行政层级的高低、编纂志稿的难易有关,而且是由其编纂者的社会地位、兴趣爱好、经济条件、文化素质、学术视野和知识水平等所决定的。
府州县志,不仅都是一统志、省通志的主要资料来源,而且也以一统志、省通志作为自己的资料来源,府州县志与一统志、省通志在相得益彰的资料互相转化、汲取中,形成了府州县与一统志、省通志在资料来源上的互动格局。
同时,府州县志之间也存在着互为资料来源的互动关系。府志,以州县志书为资料来源之一,如《光绪顺天府志·光绪顺天府志引用书目》中著录了顺天府属州县的39部志书。同样,州县志书中也引用了多种府志资料,本文前面已有多处列举,此不再赘言。州志与县志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上下互动的关系,乾隆九年(1744年),易州知州杨芊,“汇集易、涞、广志书与足迹所周、咨询所获,延宾考稽”[55]2a,编成8册志稿,奠定了乾隆《直隶易州志》的基础。有些府州县志与邻近或其他府州县志也有互为资料来源的关系。这种行政区划不同层级方志资料来源的互动关系,拓展了方志的资料来源途径,丰富了志书的记载内容,强化了保存方志资料的效果。
(三)考察府州县方志资料来源的意义
考察府州县志资料来源,虽然是个小问题,但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其一,府州县志标明了资料的来源,表明言之有据,以证明其可靠性、真实性,并标明了承前启后的发展。方志编纂者爬梳剔理,下大功夫收集了府州县的相关资料,为后人研究府州县的历史、文化、风俗、地理等问题,汇集了资料,提供了线索,有功前人,裨益今人,嘉惠后人,功德无量。
其二,为评价府州县志书提供了依据。什么是价值,价值就是凝聚在著述中的有效劳动。收集了系统而全面的史志资料,旁征博引,考证异同,力求一是,来源标示清楚,说明编纂者下了大功夫,反之,可以证明没有下功夫,或者基本功比较差,搜集不到有关资料。没有丰富的资料来源,没有扎实的学问功底,怎能编纂出好的府州县志,只能是为了应付上司的檄令,凑凑合合地应付了差事,一两个月、三四个月就编纂了一部志书,这样的志书不会有太高的学术价值。从这个角度说,对于资料来源收集的丰富与否直接关系着府州县志书的水平高低和价值判断。
其三,同一部方志不同的资料来源,体现出不同的史料价值。前面已经说过,从府州县志来源种类看,可以大致分为传世文献、档案文献、实物资料、民间文献和口碑资料等不同的来源类别。不同的来源类别,有着不同的史料价值。传世文献,本来已经存在于世,收集到府州县志中,勾勒出本地的历史发展线索,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料线索,为当地收集、保存了系统资料,丰富了乡邦文献,转化当地的精神财富。把旧方志文献有选择地收入到新方志中,保持了前后的历史联系,有助于乡邦文献的积累。上述两种府州县志的资料来源,起到了汇编和保存历史资料的作用,是第二手或多手转引的资料,没有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因此史料价值不高。如研究府州县的秦汉历史,除了明清府州县志提供的秦汉的碑刻、简牍、印章、青铜器等实物资料外,不能以明清府州县志所提供的资料为依据,而仍然需要依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传世文献资料,也就是运用比较原始的文献、引证书籍用最初者等。而收入到方志中的明清档案文献、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等资料来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保存了当时人、当事人的记录,保持了资料的原始性,有些还是唯一的资料记载等。也就是“语时则备而考古则踈”[9]1,原因在于,“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56]843,所以方志新资料,不仅可以起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42]619的作用,而且还会提出新问题,以至于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是研究明清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有些甚至是第一手的资料,史料价值比较高,是研究历史不能替代、不可或缺的资料。
其四,收集的资料来源的多少,不仅证明编纂者是否下了功夫,而且说明该府州县在全国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如果一个府州县志书中,没有纪传体正史的资料来源,也就是说纪传体正史中没有这个府州县的记载,说明这个府州县没有发生过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没有产生过影响中国的著名人物,没有出现过影响中国的著述等,这个府州县在全国哪来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
其五,府州县志中资料来源的多少,也体现着该地人文素质的高低,文风的兴盛衰微,历史意识的强盛微弱等。这既与当地读书人的多少、文化水平的高低、档案资料的完善等有关系,也与当地大家望族的文风、具体人的历史意识有关系。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又有自觉的历史意识者,自己留下了政绩、档案、诗文著述,儿孙找名人撰写了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碑表等传记著述,或者编纂了家谱、族谱、家传等,这些资料,有些就是以作逝者树碑立传的目的为出发点的,如全祖望撰写的黄宗羲神道碑曰:“乃因公孙千人之请,捃摭公遗书,参以《行略》,为文一通,使归勒之丽牲之石,并以为上史局之张本。”[57]213章学诚言:“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①《文史通义校注》卷八《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第882页),又见乾隆《大名县志》张维祺(字吉甫)撰《序》。(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第4页b。)与上述近似的说法,明清时代很普遍,如嘉靖《宁夏新志》杨守礼《重修宁夏新志序》载:“家有谱,郡有志,国有史,人文兼备,法制森然。”(明嘉靖刻本,第2页a。)嘉靖《宁海州志》熊文翰《题宁海州志后》载:“国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谱,其义一也。”(明嘉靖刻本,第3页b。)万历《福州府志》沈秱《福州府志叙》曰:“国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谱,一也。”(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第3页a。)万历《黄岩县志》袁应祺《黄岩县志叙》载:“国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谱,此巨典硕务,可谓无关于政教而尠之哉!”(明万历刻本,第1页b。)乾隆《福宁府志》卷四〇《艺文志·李拔:福宁府属五县志叙》曰:“郡之须志,犹家有谱,国有史,天下之有图籍也。”(《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册第626页。)诸如此类很多,虽然家谱、县志、国史排列顺序,不完全一致,但所表达的意思多有相近之处,可见为当时的共识。有些家谱、县志等的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正史记述,如《宋史》中有些传记就是以被立传人子孙所献的家传、行状等为材料来源的,后来又转化为府州县志的资料来源,为后人研究提供了资料,成为后人编书立传的依据。如本人没有历史意识,没有留下传记、著述、日记等资料,当时也没有撰写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等传记资料,时过境迁,人死灯灭,后来人无法创造历史资料,只能创作传说、神话、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很快地湮灭于历史长河中,怎会变为府州县志的资料来源呢?因此说,方志资料来源是否丰富,也是当地人文、风气的反映。
明清燕赵府州县志书资料来源是个小问题,但这个小问题联系着大世界,不仅直接联系着府州县志的水平高低和价值判断,而且与当地的社会历史、文化、习俗、风气等紧密相连。
(四)府州县志书资料来源的标注方式
明清府州县志书,对于资料来源的标注方式多种多样。
有的在引用文字之前,标示出资料来源。有用大字者,如嘉靖《宣府镇志》卷八《山川考》在引用资料之前用大字另起行,按时代先后标出资料来源的简称,如汉志、晋太康地里志、辽志、金志、皇明一统志、镇旧志等,位置显著,引人注目。亦有用大字加括号标示资料来源者,如乾隆《赤城县志》卷一《地理志·山川志》载:“七峯山〔宣府镇志〕在龙门所城东北百里。西高山〔畿辅通志〕龙门所西二里。又有北高山,在所北二十里。”有用小字者,如正德《大名府志》卷九《古迹志·陵墓·滑县》载:“颛顼陵帝喾陵旧志谓:俱在白毛里土山之阳,有庙同祀二帝。”乾隆《顺德府志》卷六《古迹·邢台县》载:“龙冈在城西北七里。旧郡志载:冈上有井大如轮,光武营军所造。又传:石勒时大旱,佛图澄于冈掘一死龙,济以水乃苏,祭之,龙腾空而起,雨即降因名。考地理志达活泉即是。”这里的“旧志”“旧郡志”“又传”——民间传说,都是用来标明资料来源的,多是用小字双行标注出引文与资料来源出处,亦有用“旧志”双行小字,引文用单行大字者。如万历《保定府志》卷十八《田赋志》载:清苑县,“旧志官民田地二千八十一顷一十五亩一分九厘三毫”,资料来源用小字标示。虽然都是在引文前面标注资料来源,字体有大小之别,行格有单双之分。
有的在引用文字之后,用小字标出资料来源。如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土志·风俗》载:“俗尚祈祷信鬼神。《莫州图经》。人有孝义,士勤经史,以农桑为先务。陈文《(庙)〔府〕学记》。河间之民其气淸厥,性相近。《尔雅》。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韩文。民多豪杰号称难治。本府碑记。卖剑买牛,卖刀买犊。《龚遂传》。进退以礼。《隽不疑传》。”再如万历《河间府志》卷四《风土志·风俗》载:“文武忠孝,代不乏人。密迩齐鲁,渊源洙泗。以上俱《景州学记》。风俗鸷悍,高尙气力。《寰宇记》古渤海地。廉耻成风,志士鼓义。沧州赵叔纪《十咏》。寡求不争,有古人风。元《献州记》。”两者相比较,不仅可以看出后来者资料收集得更丰富,而且可以知道资料来源更广泛,方志编纂犹如积薪,后来居上。乾隆《正定府志》卷二《地理上·形胜》载:“枕中山而挹秀,跨冀野以钟灵。《正定县志》。”光绪《保定府志》卷四十一《古迹录·旧遗址》载:“阳城,在完县东南五十里。旧志。蒲阴有阳城。《续汉志》。阳城故城,在阳城淀西北、蒲阴县东南三十里。《水经注》。”多用小字双行标注出引文,亦有用单行大字者,如乾隆《正定府志》卷九《建置下·邱墓》载:阜平县“吴王太子墓在城东方太口。见旧郡志”。资料来源著录详略不同,上述所列多是书名或篇名,有的则书名与篇名都列上,如光绪《蔚州志》卷十六《列传·马元臣》载:“事母孝,弟贫尽让其产,无难色,乡党诵焉。《蔚县志·孝义》。”同卷《张宪》载:“官至副使。有文武材略。旧志《乡贤》。”同一书资料来源著录,也并非整齐划一,如同是光绪《蔚州志》卷十六,有些也仅著录书名,如《刘傅传》载:“卧病月余,卒。事闻,赐赠荫祀,褒忠祠。《两镇三关志》。”
有既用大字标示资料来源并引用资料文字,又有用小字双行标注出处者。如《口北三厅志》卷四《职官》载:“迭剌部夷离堇〔辽史百官志〕北院大王。初名迭剌部夷离堇。〔国语解〕掌军马大官。太祖分北、南院,太宗会同元年改夷离堇为大王。”“迭票底〔辽史本纪〕太祖元年。耶律曷鲁〔辽史本纪〕太祖八年。”同一书同一卷同一段两种资料来源标注格式并用。
有的在引用文字之后,加重颜色标示资料来源。如嘉靖《河间府志》卷一《地理志·沿革》载:“义成堡见瀛州孝友刘君良传。”“河间古镇,联城数十,总制千里。元河间路教授张英撰《肃宁县李公德政碑记》。”用双行小字加重颜色来标示资料的来源。
上述几种标注资料来源不同的方式,是编纂者根据不同的需要,而采取的不同方式,由此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术特征,体现了府州县志编纂者的学识和编纂态度。府州县志明确地标注了资料来源,提供了按图索骥的线索,方便他人查核和引用。
(五)府州县志书资料来源的局限
明清时代,虽然有些燕赵府州县志注明了资料来源,为后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尤其是随着清朝乾嘉考据的发展,也影响了府州县志资料来源的著录等,向着更加严密的方向发展。由于地方志是官书,编纂方志是个系统工程,参与人员较多,志书成于众手,参加者水平参差不齐,文化素养高低也有差异,责任心大小也很难整齐如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诸多局限。
时代的局限。明清时代,中国是农业社会,文盲是社会的多数人,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低,书籍普及率不高,很多家庭中未有书籍的收藏,也没有公共图书馆,府州县衙门中,保存的传世文献也不多,地方志流传的不多。如康熙年间提督学政蒋超,“所过州县访求邑乘,存者宝如拱璧,失者忧若坠绠”,“兵毁之余,遗编齾翰只字不留”[58]2。州县保存的方志很少,偶尔有保存者,视之为宝贝。又如乾隆年间柏乡知县锺赓华亦言:“柏志创自前令马公写,延庭张公续成之。今所存者,刊于谢公廷瑞,其裁定则魏文毅相国,承先志而继述之者也。”[59]3a作为《柏乡县志》,且不说保存在正德《赵州志》卷七中的《柏乡县志》,就是单行本的还有嘉靖、万历、顺治、康熙《柏乡县志》,仅能看到康熙《柏乡县志》一种。南宫情况也有些类似,“南宫旧志,叶志无存,邢志缺略,邑人卢凤有志十卷,早失其稿,郑宏庆续邢志系抄本,亦无从觅,惟胡志具有全书”①道光《南宫县志·凡例》(清道光十一年刻本,第1页a)。其实,明知县叶恒嵩创修、嘉靖三十八年成书的嘉靖《南宫县志》5卷,即叶志,不仅有传世者,影印本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册,而且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南宫县邢氏求己斋依明本影印为《嘉靖南宫县志》。明知县邢侗续修的万历《南宫县志》13卷,即邢志,其清抄本至今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道光年间都未能看到,后在民国年间叶志、邢志几经努力都找到了。,望都县志也是这样,“创修无考,即明时马志、张志皆遍求莫得,康熙十七年李志初印者,亦且寥寥”[60]8a。很多当地的志书,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有些即使保存下来了,也不为时人所周知,如嘉靖《河间府志》①如嘉靖《河间府志》,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一二《人物志·文学·樊深传》载:“今深书不传,《明史·艺文志》列其目。”(《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41册第302页。)《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载:“樊文深,《河间府志》二十八卷。”(第2406页)把作者名字都搞错了。又如康熙《顺天府志》,《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三〇《光绪顺天府志引用书目》中也没有著录。当地志书编纂者都不太了解当地的志书了,还有更多的人能了解吗?、万历《香河县志》②如万历《香河县志》,《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二二《艺文志一·纪录顺天事之书》载:“沈惟炳《香河志》,未见。卷数无考。”(第6 353页)作为藏书家、目录学家缪荃孙都未见,可能见过的人不会多。民国《河北通志稿·文献志·旧志源流》卷一载:“万历《香河县志》十一卷。明沈惟炳纂修。存。沈惟炳,湖广孝感进士。万历四十六年知县事。是志,沈惟炳因前任沈万鈳旧槀重纂,万历四十八年成书,前有自序。”(第2 780页)清朝大学者缪荃孙不了解的事情,民国学者说明白了。现在万历《香河县志》已被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复制,化身千百。等。有些机构藏书少得可怜,多是私人藏书,因而给府州县志资料来源的收集带来了很多困难。还有,当时也没有现代如此方便的电脑检索、搜索引擎等,检索起来很麻烦,下了很大的工夫,而收效甚微。诸如这些因素,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局限。
有些府州县志书没有标注资料来源,有的标注了也比较粗糙,有些只标明书名或只标篇名,有些在此处标书名,在他处标篇名很不一致,尤其是对于一书有多卷次和篇目者,不利于迅速查找资料来源的出处。
有些府州县志对于同种一书,著录了不同的书名,如在乾隆《口北三厅志》中先后标注了《周伯琦诗注》《周伯琦近光集诗注》《近光集诗注》等三个不同的书名,实际上是一部书,体现出标注的不规范性和编纂者的粗疏之处。
还有些府州县志对于一些资料来源的出处误标或张冠李戴的错标,或诸多方志承谬袭误,或是挂漏舛误,以讹传讹等。
诸如这些,都是我们在运用明清燕赵府州县志资料来源时,要注意的问题,要不厌其烦地核对原文,以减少新的失误。
资料,是地方志书编纂的基础。明清燕赵府州县志的资料来源,是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问题,但又是直接关系着志书的质量、水平和价值等问题。我们既可以从明清燕赵府厅州县志的资料来源中,看到一代又一代方志编纂者,求真求实,讲究证据,殚精竭虑,博览群书,走访耆老,搜集碑刻,努力开拓方志资料来源,博采众长,汇集了众多资料,旁征博引,细致考辨,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增强了府州县志书的可信性、可靠性,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线索,保存了系统的文献资料,提高了后人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前人的局限,除了时代的局限之外,还应当看到难以彻底克服的鲁鱼亥豕之讹等。无论是前人的成功之处和失误之点,都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我们应当接着前人的脚步走,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后人创造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