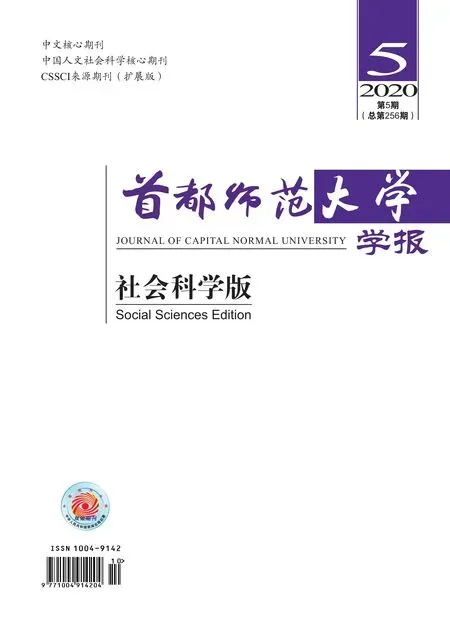以禅喻诗:严羽的诗学思想及其文化旨趣
洪 涛
作为宋代诗话压卷之作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构成其鲜明的学术品格。在“诗禅交涉”的诗学演进历程中,严羽的“以禅喻诗”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以禅论诗”的风尚,开启了“诗禅一味”的源头,更是“将它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使之系统化,理论化”①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5页。。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沧浪别开生面,如骊珠之先探,等犀角之独觉,在学诗时工夫之外,另拈出成诗后之境界,妙悟而外,尚有神韵。不仅以学诗之事,比诸学禅之事,并以诗成有神,言尽而味无穷之妙,比于禅理之超绝语言文字。他人不过较诗于禅,沧浪遂欲通禅于诗。”②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8页。别具慧眼地窥见严羽对于诗禅之论不是如前人简单的概念格义比附,而是努力从形式内涵乃至精神层面双向打通。对此,宇文所安进一步将严羽诗禅关系的讨论细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过程类比,即禅宗修炼与诗歌学习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一种直觉的、先于反思的理解。第二层是状态类比,这一层类比在过程类比的基础上发生在禅悟状态与诗“悟”状态之间。第三个层面指严羽将断定诗悟与禅悟状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合二为一。①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43页。指出二者在目标取向、运思过程与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在这些真知灼见的背后,《沧浪诗话》有些问题依然隐而不彰,值得反复追问。严羽在庞大的宋代文人群体中,因何誉为“求之宋代,独严羽一人,自负识力,此则专以批评名家者”②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在宋人一如江西诗派普遍以禅论诗的风气中,严羽何以自许《沧浪诗话》是“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是“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③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51页。?在笔者看来,严羽以“妙悟”这一“众妙之门”开启了诗学上“绕路说诗”的方便法门,建构了以“妙悟”为方法论,以“兴趣”为特质论,以“气象”为境界论严整的诗学体系。其与江西诗派诸人“以禅喻诗”形似而神异,在某种相同的技术取径上却宣示了完全不同的目标取向,以“反理复情”的姿态展开了重回诗歌抒情本质的深沉求索。
一、妙悟:诗歌方法论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妙悟”应该是《沧浪诗话》带给中国诗学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概念。这一借用佛禅的术语,经严羽的创造性转换,已经成为阐释中国诗歌的重要法门。明人胡应麟即云:“汉、唐以后谈诗者,吾于宋严羽卿得一‘悟’字,于明李献吉得一‘法’字,皆千古词场大关键”。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0页。严羽揆度诗禅,揭櫫“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⑤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将“妙悟”视作会通诗禅的津梁,也明确标明其理论渊源所自。
“悟”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法门。在成佛的修行方式上,佛教史上长期存在“渐悟成佛”与“顿悟成佛”的争论。中唐以后,由南宗慧能开创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逐渐取代了其时以北宗神秀为代表的“渐修”主旨,促成了佛教在中国革命性的转变,使得顿悟一跃成为修行学说的主流。其实在慧能之前,中国佛教的一些学者曾根据印度经典的“十地”的理论,曾提出过“小顿悟”和“大顿悟”的思想。以支遁、道安、慧远与僧肇等人为代表的佛教徒主张“小顿悟”,认为觉悟是一个由浅入深渐进的过程,以七地为分界,七地前未见真性,至七地智慧具足,烦恼断尽,始悟无生法忍。然七地虽然见理,但功行未满,要证得究竟,仍须进修后三地。“妙悟”这一概念,最早出自僧肇《肇论》中的“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⑥僧肇著,张春波校释:《肇论校释·涅槃无名论·九折十演者·妙存第七》,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9页。。对于这种析悟理证体为二的做法,竺道生提出异议,以为此法名为顿悟,实为渐悟,原因在于“理不可分”,入理之慧亦不可分,悟理与体证不可相离,觉悟终极的真理只能一次完成,十地以前皆是大梦之境,一无所悟,到了十地之后的“金刚心”,才体认性空、本无生灭的诸法实相,方可言悟,从而把支遁等人顿悟阶级合二为一,这种学说被称之为“大顿悟”。道生的思想虽然解决了顿悟过程在时间上的完整性问题,但所悟的真如本性仍外在于己,悟与所悟之间判然二分,悟是心悟,所悟是理,只是修习之心契合所悟之理,即道生所谓的“夫真理自然,悟亦冥符”。这样在真俗之间仍然留下一道巨大的鸿沟,有乖真如不二法旨,需要在学理上进一步弥合。这一事关顿悟的根本性问题,到了慧能那里,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慧能将之前悟与所悟心理二元皆收归一心,悟是自心在悟,所悟是自心之性,心性一如,强调的是“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⑦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页。;正因为能悟所悟体一不二,所以烦恼与菩提,凡夫与佛的区别只在本心一念之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既然直了本心即可成佛,在顿悟方式上,也就无需坐禅诵经,无需由戒入定,由定发慧,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只要常行直心,皆是修行。这种顿悟思想与方式的转变,完成了佛教中国化改造,慧能“以一个具体现实的人心去代替一个抽象玄奥、经过佛教学说百般打扮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把一个外在的宗教,变成内在的宗教,把对佛的崇拜,变成对自心的崇拜,一句话,把释迦摩尼的佛教变成慧能‘心的宗教’”①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慧能顿悟观中蕴含的直抵本心、不假修为、圆融无碍、当下即是的思想以及简洁明快、生动活泼的宗风对后来的宗门影响深远,也给唐宋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以极大的灵感。尤其对于诗歌而言,禅悟中的这种非逻辑性、直觉性、主体性等特点与诗歌创作及精神若合符节,使得诗禅交涉逐渐成为中国诗学一道亮丽的风景。中唐以来,诗歌批评中已出现以禅论诗,主要表现为将禅宗的某些范畴运用于诗论,如晚唐五代的诗格在形式上往往借鉴佛教典籍的结构形式“门”,皎然在《诗式》中提到的“量”“作用”和“境”,王昌龄《诗格》中出现的“自性”等佛禅术语②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161页。,但总体而言,还流于简单概念格义。迄至宋代,由于禅宗接受主体身份的微妙变化,农禅日益变为士大夫禅,禅宗大兴文字禅,文人禅悦之风盛行,热衷“以文字为诗”等因缘,以禅论诗更是成为一时风气,因而在诗禅内来关联探索方面要深入得多,其中“‘悟入’说无疑是宋人最富个性、最有创造性且最具生命力的诗歌理论”③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成果。检索宋人论诗,以禅悟说诗不绝如缕,如李之仪谓“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苏轼云:“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即使为严羽所诟病的江西诗派,一样热衷此道。曾季狸在其《艇斋诗话》有一个总结,说“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④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6页。。
严羽于宋人普遍论诗“悟入”风气中拈出“妙悟”二字,还特别标榜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虽不免自矜,但背后应该有其特别用心处。那么严羽的“妙悟”和江西诗派有何不同?
《沧浪诗话》一开篇即开宗明义:“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⑤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以识为主”是理解严羽“妙悟”论乃至其整个诗学的关键,“妙悟”既是严羽诗学方法论,更是其诗学认识论。而在认识论意义上,“妙悟”首先表现为“识”,“识”是“妙悟”的灵魂。那么,严羽的“识”所指何谓?禅宗的“顿悟”是于电光火石一念之间,完成对真如本体的领悟和把握,彻底洞悉佛性。正如赖永海先生所理解的,历史上对“佛性”“天理”“道”的认识和把握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采用“顿悟”“体证”的思维方法,是“因为只要他们所要认识或把握的对象是那种既无形无象又无处不在的‘大全’、‘本体’,就必然会(或者说必须)采用这种突发性、跳跃式和整体性的‘顿悟’、‘体证’的思维方法”⑥赖永海:《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学术月刊》2007年,第 35页。。这样看来,“顿悟”这种思维方式首先意味着对某种整全性根本性存在的领会。严羽将“妙悟”从禅宗引入诗学,也是要解决认知诗歌的根本问题。与“顿悟”是对佛性的彻底领悟相类,“妙悟”是要对“诗性”有根本体认,对诗歌特色有全面深刻的把握,最终由诗指向诗人,这正是严羽“识”的重要内涵。在“以识为主”提法之后,严羽马上给出了“汉魏晋盛唐”他心目中诗歌的典范形态,作为对本色诗歌的具体注解。对于如何培养“识”,严羽认为须做“从上做下”的功夫。具体而言,就是先立大体,法乎其上,渐次熟参汉魏、晋宋、南北朝、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开元、天宝诸家、李杜二公、大历十才子、元和、晚唐、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体会诗歌的风格、气象,熟悉诗体诗法,直观体悟,见出言外之意,从而领悟诗歌的本色。按照这样的接受顺序,学诗者才有可能达到“辨家数如辨苍白”的境界。严羽不是从个别作家作品,更不是从某一个具体技术问题来认识诗歌,而是在历史源流中,从一个整全的视野中领悟诗歌(和诗歌背后诗人)特点,从而达到对诗歌特质的把握。这和江西诗派做法大异其趣。江西诸人悟入诸问题,大体而言,其要旨不外于由字、词而句、篇进而到作品意蕴,重视诗歌技巧,如字词句法、命意起承转合等。如被视为黄庭坚诗学思想整理者的范温说:“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①范温:《潜溪诗眼》,吴文治:《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3页。强调从小处入手,从“一转语”处悟入,着眼于“字法”“句法”“章法”等技巧问题而至于整体把握。这种由局部而整体的把握方式,在严羽看来,是“眩于旁门小法”,能否真正把握艺术之精神,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
严羽自称“从上做下”的功夫“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他关于“妙悟”的讨论中以一系列诸如“大乘/小乘、南宗/北宗、正/邪、第一义/第二义、临济/曹洞、透彻之悟/一知半解之悟、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大历以还之诗”等二元对立概念来说明其诗禅旨趣和价值取向。从严羽以禅喻诗所借用的概念而言,他和江西诗派等宋人并无太大区别,“悟入”“熟参”“活参”“识”等也是宋人论诗常用的话头。但严羽以上述二元对立概念明确宣示了他和江西诸人的分歧所在。他显然将自己所拈出的“妙悟”看成是大乘、南宗、第一义、透彻之悟等等,而将对立的一面推给江西诗派。由于“先立其大”和“目无全牛”这个取向上根本分歧,一切似曾相识的内容都变得泾渭分明。所谓“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问题是,南宗“顿悟”的是大全,严羽这个“先立其大”的“大”何以得见?“以识为主”是否要求“以识为先”?“识”是“生而知之”还是“学而知之”?如果是“生而知之”,“熟参”“活参”就毫无意义,如果是“学而知之”,那和江西诗派仿佛的“渐修”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一者是“部分到整体”,一者是“整体到部分”,那么如何确证对一个时代、一个诗人或一首诗歌在没有对于部分的学习前提下如何直接进入整体的把握?这些问题,和南宗禅曾经在理论和实践中遭遇的困境一样,虽然慧能“顿悟”法门在理论上机法锋利,通透圆彻,但在禅宗实际修行中却会面临诸多挑战。在后来马祖一系演绎中,“即心即佛”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平常心是道”,但如果“道不用修”,“即事而真触类是道”,砍柴担水、穿衣吃饭、屙屎送尿、扬眉瞬目,都成了佛性的显现,如果真是“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那我们如何判定此心是清净的与世俗杂念无染的心,还是自然的与世俗和光同尘的心?类似诘难,使得其在理论圆融彻底时反倒在实践中陷入两难。禅宗史上,对于为什么“顿悟后还要渐修”,神会有一个比喻,说正如母亲生孩子是顿悟,而喂养孩子,身智渐渐成长是悟而后修。这是禅宗“顿悟渐修”的一个解释。神会这个比喻其实也存在问题,如果顿悟是彻而全知,这个后来渐渐长大成人的孩子和曾经的婴儿是同还是异?这和道生对“小顿悟”的批评理路是一致的。为了说明妙悟之后还需“熟参”,曾与严羽一同受学的包恢也用过这个比喻:“顿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体已成;渐修如长养成人,岁久而志气方立。此虽是异端语,亦有理可施之于诗也。”②包恢:《敝帚稿略》,吴文治:《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035-8036页。这可以作为严羽妙悟不废参读的一个注脚。钱钟书先生对此也有一个解释,认为“禅与诗、所也,悟、能也。用心所在虽二,心之作用则一。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然其为悟境,初无不同。且悟即‘造’之至‘深’,如须‘深造’,尚非真悟。宜曰:禅家讲关捩子,故一悟尽悟,快人一言,快马一鞭。一指头禅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诗家有篇什,故于理会法则以外,触景生情,即事漫兴,有所作必随时有所感,发大判断外,尚须有小结裹”③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页。。这是从诗与禅不同性质来看待悟的不同表现,亦属解缚之论。其实诗中言悟,不仅是涉及言筌与诗歌创作性质的问题,主要还是借路说诗的方便法门,得意忘言,不能完全胶柱鼓瑟。严羽借用禅悟概念,强调的也是在对象观照中不离不染,不着名相的态度。江西诗派关于诗歌在认知方式上就发生偏差,视细枝末节为实相。这种执着于形式(如句法、声律等)和技术(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层面的造作,无异缘木求鱼。与江西诗不同,严羽诗“悟”关注的是首先突破理学思想对诗学艺术的负面影响,在一种整全意识中,将被理学禁锢僵化肢解的生命体验解放出来,恢复日常生活世界的活泼的生命情感,“妙悟的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涌动——生命的涌动”④郭建平:《妙悟论》,《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严羽曾问学于包扬,而包氏兄弟原为象山学生,象山殁后,又拜师朱熹,后又背义理之学而归于大慧宗杲门下的临济禅。严羽在思想上或受包氏兄弟之影响,故其理念明显偏向心学和临济一脉禅学。其论诗理念“先立其大”和陆九渊思想如出一辙。与之相对,江西诗派论诗路径在禅宗上接近北宗,在宋代思想谱系也更接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的朱子之学。当然“妙悟”的启发更多应归于临济一脉的大慧宗杲。严羽自己就坦承“妙喜自谓参禅精子,仆亦自谓参诗精子”①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53页。,点出了二者的思想渊源,大慧宗杲曾明确指出:“学道无他术,以悟为则。”针对当时禅林中有些人热衷公案的注解问答,他们轻视“悟”,甚至反对“悟”,大慧对此做了尖锐批判:“而今默照邪师辈,只以无言无说为极则,唤作威音那畔事,亦唤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门,以悟为诳,以悟为第二头,以悟为方便语,以悟为接引人之辞。如此之徒,谩人自谩,误人自误。”②《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八《答宗直阁书》,《大正藏》第47册,第933页下。宗杲反对“是事莫管”“只管守静”避事遁世的“默照禅”,这与禅“悟”必须贯彻在世事之中的精神相违背,它不仅不能激活人们对现实生命的诗意体验,反而还要泯灭这种活泼生命体验的灵性,使其终于湮没无闻。宗杲“看话禅”是恢复禅悟与日常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生命体验活动,一切文字都只是获得这种本真生命体验的符号或工具,保留了禅“悟”生命体验的特性。所以,在精神旨趣上,严羽借用了宗杲“看话禅”强调“悟”的实践体验特性,将其禅学精神化用为诗学精神,以此恢复诗人生命体验的诗意灵性。
二、兴趣:诗歌特质论
妙悟是认识论和方法论,贯穿于严羽整个诗学的全过程,它为了解诗歌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与视域,构成其诗学建构的前提和基础。“妙悟”这种观照方式是整全性的,首先要把握的就是诗何以为诗的本质问题。因而,在妙悟对诗歌具体实践中,顺理成章要对“诗何谓”这一根本问题做出回答。
在《诗辨》的总结性文字中,严羽给出了明确的回应,指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③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在这一段关于诗歌的精彩描述中,严羽正说反说,破立结合,揭示了诗歌的本质及其特性。他以两个“非关”切分了诗与非诗的界线,以“别材”“别趣”提示了诗歌的独特存在。在一种正反对照、兼容并蓄的辩证思维中,引出了他关于诗歌的本质和特性的理解:“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前者是关于诗歌本质的重新确认,后者是关于诗歌特征的独特见解。一些学者将“兴趣”视作严羽的诗歌本体论,这不够准确。“诗者,吟咏情性也”是明确的下定义的句式,是严羽在宋代普遍以理说诗的风气下,复归诗歌的抒情传统,重申坚持诗歌的抒情本质的立场。指出“诗言情”乃诗歌的本质不是严羽创见,但体现的是他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理论勇气和真知灼见。严羽真正的贡献,是在坚持诗歌抒情本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兴趣”这一概念来用以说明诗歌理想的美学特征。
那么,“兴趣”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概而言之,约略有四种:1.认为“兴趣”指诗人的“情性”熔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2.认为“兴趣”与魏晋南北朝以来审美艺术中的“神韵”“气韵”或“韵味”相通;3.认为“兴趣”即是当外界事物有和自己意趣相通之处,便激发了感情,引起感兴,是由于内心之兴发感动所产生的一种情趣;4.认为“兴趣”就是“意境”。④魏彩云:《严羽“兴趣”说研究综述》,《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8期。上述观点各有侧重,而又错综互见。从“兴趣”这一概念的诗学渊源而言,尽管历来兴义难明,但揆其大略,主要还是侧重于心物交感及其美感效应,兴在中国诗学中建立的地位,就是因为后代诗学家使它的精神意向突现,“就是因为它实在表明了诗歌中情意与形象之间互相引发互相结合的几种最基本的关系和作用”①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而“趣”大抵相当于诗歌的韵味,与钟嵘的“滋味”、司空图的“韵外之致”、杨万里的“风味”相近。②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所以“兴趣”这一概念的历史资源中已经内在包含了心物情景交融及其美感效应等因子。从严羽文本理路而言,他是在对江西诗派的批评中确立他的诗学观念。“诗有别材”是从诗歌创作外部素材来源而言,反对的是江西诗派主要从书本到书本的写诗路径;“诗有别趣”是从诗歌创作主体内在精神表现而言,反对的是江西诗派以理为诗的表达风尚。在否定以书为诗、以理为诗的错误看法之后,他重提诗歌的抒情本质。但“情性”本身不是诗,需要有体现诗歌本质的独特表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严羽提出或者说发明了“兴趣”这一概念。
从严羽关于“兴趣”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兴趣”首先体现心物交感,情景交融的创作取向。这是强调诗歌内容层面主客统一,要求诗歌直面社会、直面生活,不能闭门造车、剿袭书本。“感物起兴”是“兴”的中心意蕴。在中国诗歌创作中,“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是诗歌发生学的一个基本解释,由物进而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活水源头。“兴”的普遍规律,正如摆脱江西诗派羁勒的杨万里看来,是“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生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③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门徐达书》,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41页。。严羽眼中的盛唐诸人之所以能形成“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歌特色,很大程度也应归功于“兴”本来就蕴含的这种心物交感,猝然遇合,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品格。直接从生活中去获得诗情诗感,在严羽看来,也正是唐人能写出好诗的原因:“唐人好诗,多是征戌、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④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98页。而反观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习惯从书本里讨生活,寻章摘句,衣冠古人,讲究“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强调“用事”“用典”,舍本逐末,必然导致视野狭隘,性灵干枯,诗道榛莽。在严羽之前,钟嵘就探讨过不同文类的特点要求,批评过当时“文章殆同书抄”作诗风气,提倡“即目直寻”的创作方法:“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⑤钟嵘:《诗品·序》,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页。刘克庄则明确以创作来源区分唐宋,称前者为“风人之诗”,后者为“文人之诗”:“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⑥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3页。不仅诗坛对此风气不满,大慧宗杲对“默照禅”“摄心静坐,事事莫管,……落外道二乘禅寂断见境界”批评的理路也与严羽如出一辙,从中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思想上的影响。
其次,“兴趣”包含诗人主体在情统领下的情、理、意等诸多心理因素的深度融合。这是强调主体感性和理性的圆融统一。严羽坚持诗的抒情本质,以此作为诗与非诗的分水岭,这是他论诗的基本立场。但严羽清楚,诗并不是指纯粹单一的情感描述,它始于情感而又超越于情感,它包括情感而又不局限于情感,诗在吟咏情性之外,还负载着更多的内在诉求。本来,在中国诗歌观念中,除了“诗缘情”之外,历史更长地位更高的是“诗言志”,其所言之志,并非单纯的个人怀抱,而是带有强烈以礼乐精神为核心的政治化、道德化色彩。宋代在普遍以理言诗风气下,有“诗以意为主”⑦刘颁:《中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5页。的提法。“这‘意’或‘志’包括观念、意志、认知、直觉、心绪等多种精神内容,它倾向于平和而非激动,倾向于清醒而非迷狂,倾向于明晰而非朦胧。这‘意’或‘志’不同于唐人那种不可言说的微妙印象和感受,而更多的是主体的理性认识”⑧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页。。宋诗之所以爱说理,爱议论,与唐宋之际读书人身份意识和社会角色意识的变迁有关,“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比唐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宋代士大夫更多是集“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①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同时具备了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和学术主体的特征,比唐人要复杂得多。在角色意识上,由于重文抑武国家政策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宋代士人的价值坐标系中,在政治领域建功立业并非最高追求,能究天人之际、辨性命之理并能身体力行、成圣成贤,才是人生最高境界。“所以诗歌创作对于宋代士人来说主要不是生命体验的呈现,而往往是其主体意识的表达形式,或者是一种技巧和显示博学的方式”②李青春:《唐宋诗的文本差异及其文化原因》,《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5期。。这形成了唐诗主情和宋诗主理不同风貌。严羽生长在宋代,对时代风气不可能完全无感,他很清楚,诗歌中不可能只有情感,情、理、意等心理因素都不可或缺,所谓“诗有词理意兴”。问题是需要分清轻重主次,不只是简单调和情理意,而是如何把理意有效消融于情中而浑然一体,这才是他和江西诸人的分歧所在。所以,他一方面反对片面地以理为诗,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诗不但不排斥理,相反,要达到诗歌的极致,还必须多读书,多穷理。但理在诗中,应该“不涉理路”,不能太着迹,不能“叫噪怒张”,而应如盐在水,如花在蜜,体匿性存,无痕有味。宋诗与唐诗的区别,并非情理的有无,而是情对理安顿的艺术和方式,“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③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页。。理在情中,浑融无迹才是严羽的追求,也是其“兴趣”的应有之义。
复次,“兴趣”最重要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严羽认为,理想的诗歌,如汉魏盛唐之诗,是“词理意兴,无迹可求”,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所以,“兴趣”不仅是一种灵动生命的诗意情感,或者说是一种“心象”,而且还是一种与外在形式紧密相连的对生命情感的诗意体验。④程小平:《〈沧浪诗话〉的诗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从本质来说,它是艺术表现与艺术效果的结合体。⑤许志刚:《严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从艺术表现看,既是事与理消融于“情性”之中,所谓“不涉理路”,不“多务使事”,淡化意理的生硬,消解物事的粗重;又是语言等形式在表现内容时水乳交融,浑然无间,不着名相,不露痕迹,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所谓“不落言筌”。强调文字的不即不离,不粘不滞,正是禅宗“诸佛妙理,不关文字”思想的表现,于相而离相,于念而离念。严羽用“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形容这种境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常见于禅门话语,如《五灯会元》卷七:“我若东道西道,汝则寻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么处扪摸?”⑥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5-386页。这种对语言的随说随扫,不即不离的态度,是为了真正领会无法为语言牢络的真实义。从艺术效果而言,“兴趣”的这种妙合无垠,言简意远,也就是严羽所描述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和钟嵘释“兴”为“文已尽而意有余”的精神一致,也和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引述戴容州的说法相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⑦祖保泉、陶礼天:《司空表圣诗文笺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呈现了一种情景交融、言意俱泯、虚实相生、韵味悠远的艺术效果。这种恍惚迷离的效果,正是严羽通过“妙悟”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审美直觉,将传统意义上被割裂的诗歌内容与形式弥合成一个整体而所呈现的某种不可言说的效应。这一点类似于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苏珊·朗格的“情感的形式”。朗格认为,情感与形式不是逻辑地接合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因此朗格又曾称之为“生命的形式”。这是逻辑理性难以把握的,它只能由艺术审美直觉予以把握。严羽之所以要将“兴趣”说得玄虚迷离,就是因为“兴趣”(情感的形式或生命的形式)无法通过逻辑理性的方法将其予以再现复制,也无法运用分析归纳的方法将其推导出来。触目即真的体验难以言说,只能在惟恍惟惚的个体感受中进行领悟。
三、气象:诗歌境界论
如果说“兴趣”是诗歌的内在特质,侧重于诗歌的内在精神,那么作为其特质的外在呈现,则表现为“气象”。近人陶明浚在评论严羽五种诗法的关系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说诗譬如人的身体,体制如人的体干,格力如人的筋骨,气象如人的仪容,兴趣如人的精神,音节如人的言语,五者既备,然后可以为人。同样,诗歌亦然,五者之长,而后可以为诗。①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7页。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把“气象”视作仪表,贴切传达出了气象之于诗歌的意义。如果将诗歌视作一个生命体,那么其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最终都集中呈现于“气象”,并通过气象展示出来,表现为诗歌的整体精神风貌。叶嘉莹先生认为:“‘气象’当是作者之精神透过作品之意象与规模呈现出来的一个整体的精神风貌,而每一位作者之精神,既可以因其禀赋修养之异而有种种之不同,因之其表现于作品中之意象与规模,当然便可以有种种不同之‘气象’。”②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255页。
“气象”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是“气”与“象”这两个古老概念内涵不断交融演化的结果。其核心概念的“气”源自于中国先秦以来就有气化哲学思维。古代艺术理论有尚气传统,魏晋以后,随着“文以气为主”观念的流布,“气”由哲学渗透进而影响到文学艺术成为美学概念。徐复观先生梳理“气”在中国文化含义演变后指出:“(气)是一种‘生理的生命力’,若就文学艺术而言气,则指的只是一个人的生理综合作用所给予作品上的影响。凡是一切形上性的观念,在此等地方是完全用不上的。一个人的观念、感情、想象力,必须通过他的气而始能表现于其作品之上。……一个人的个性,及由个性所形成的艺术性,都是由气所决定的。”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因此之故,“气象”也正是严羽判断诗人风格差异的主要尺度,是他“辨体”的重要依据。这一点,正如黄景进特别提醒的,“严羽之判断某诗作者是谁或属于某个时代,并非皆用考据方法,而往往是凭主观的鉴赏经验——通常是由观其‘气象’来判断”④严羽著,黄景进撰述:《沧浪诗话》,台湾金枫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譬如他断言“虽谢康拟邺中乐诸子之作,亦气象不类”。毛先舒《诗辩坻》卷二对此作了一个注脚:“灵运乡中八子诗,是拟建安,却得太康之调。”严羽认定前人诗话中陶渊明的作品有可能是李白诗歌的误入,理由也是“体制气象不类”:“《西清诗话》载:晁文元家所藏陶诗,有问来使一篇,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予谓此篇诚佳,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得非太白逸诗,后人谩取以入陶集尔。”⑤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21-222页。
“气象”不但是个人诗歌审美风格的重要依据,更是时代精神风貌的分水岭。严羽论诗的特点,在于他藉由“妙悟”慧眼,拥有了一种从大历史、大视野中整体观照诗歌的能力。这一点,尤其体现于他的“气象”诗学观。叶朗认为:“气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乃是概括诗歌意象所呈现的整体美学风貌,特别是它的时空感。这种整体美学风貌和时空感,既反映诗人的精神风貌,也反映时代生活的风貌。⑥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0页。借之解释严羽的“气象”观十分贴切。严羽认为唐诗与宋诗差别不在于工巧与朴拙等技术层面,它们最为本质的差别在于“气象”:“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唐宋诗如是,盛唐与中晚唐也是如是。在《考证》十九中说:“‘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都是以气象来区分时代。而对于其推崇的诗歌时代气象,严羽喜欢用“混沌、浑厚、难以句摘、不可寻枝摘叶”等来描述,他感慨“汉魏古诗”是“混沌”的,“建安之作”是“不可寻枝摘叶”的,“盛唐诸公”也是“浑厚”的,都具有浑然的特点。“浑”就是元气未分之状,也正是气化哲学中“通天下一气耳”本来意义。这种元气的浑沌状态,有学者概括为四个基本特性:第一,大,是指元气浑厚浩瀚的境界,生发无限的力度。张载《正蒙·太和》云:“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管子·内业》云:“此气也不可止以力。”分别说明元气沛乎塞于天地之间、真力弥漫的大境界和大力度。第二,全,是指元气的浑沦整一、完足无缺的状态。郭绍虞《诗品集解》云:“何谓浑?全也,浑成自然也。”《列子·天瑞》解释“浑沦”云:“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第三,朴,是指万物未蒙、淳朴自然的元气状态。《淮南子·诠言》云:“浑沌为朴。”第四,和,是指元气阴阳交感,自然合和的状态。王夫之云:“阴阳异撰,而其絪缊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①李利民:《论盛唐气象的浑然美》,《江汉论坛》2010年第11期。元气未分的“大、全、朴、和”的特性,也正是“浑”的美学特点。汉魏盛唐诗歌,注重整体篇章的即兴表达,尚未堕入诗歌句法和创作程式技巧的藩篱,强调诗歌篇法的整体统一,而不侧重诗歌技法的讲求,呈现出一派朴拙浑然的美学风貌。严羽反对以“雄深雅健”四字论之唐诗,比之“子路事夫子时气象”,是觉得“健”尚有剑拔弩张,未尽中和浑厚之嫌。推崇诗歌“浑厚”是“妙悟”观的内在精神的必然体现,是打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下一种整全融合观照方法自然的逻辑延伸。这种“浑厚气象”从审美境界上说同“兴趣”也是一致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落言筌”,皆与“气象浑厚”“气象混沌”的涵义相通。
在严羽看来,“浑厚”是诗歌气象重要美学品格,但还不是其心目中的典则。严羽于前代诗歌中,最为推崇盛唐气象。以为“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诗而入神,至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将李杜视作诗歌的极则,是盛唐气象的代表。之所以情有独钟,因为在严羽看来,盛唐诗歌的“气象”不仅有“浑”,而且还兼具“雄”,是“雄浑”。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特别强调了盛唐诗歌“雄浑悲壮”,“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道出了他独推崇盛唐诗之原因所在。正如许多学者所发现的,严羽标举“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水月镜花”的空灵的盛唐“兴趣”,看似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人更符合这种理念,但严羽却青睐李杜而非王孟,是因为李杜更能体现这种浑厚雄壮兼而有之的盛唐气象。在《诗评》中,严羽称“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金鳷擘海、香象渡河”都是出自佛经譬喻。所谓“金鳷擘海”,依《华严经》卷三十六云:“譬如金翅鸟王,飞行虚空,安住虚空,以清净眼观察大海龙王宫殿,奋勇猛力以左右翅搏开海水。”可见“金鳷擘海”是针对李杜诸公气象雄壮而言。“香象渡河”出自《维摩诘经注释》:“香象,青香象也,身出香风。”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云:“香象渡河,亦喻文字透彻之意。……譬如兔马象三兽渡河,兔渡则浮,马渡及半,象彻底截流。”②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77页。故而,“香象渡河”是针对李杜诸公的气象浑厚而言的。
严羽对盛唐气象的推崇背后,是对一种刚健阔大、昂扬奋发、生机勃勃时代精神的追慕。关于“盛唐气象”或“盛唐之音”,正如林庚先生所言:“‘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③林庚:《关于李白》,《光明日报》1954年3月29日。它表现为积极进取的英雄气息、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高昂明朗的思想感情,雄浑壮大的气势力量。李泽厚曾描述:“(盛唐之音)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的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废、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④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早在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先生就敏锐洞见盛唐诗歌“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⑤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3页。相比于盛唐的刚健阔大,宋调整体上转为理性内敛,在所谓文化的造极之际,不免盛极而衰的衰飒垂暮之气。刘子健指出:“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⑥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运、气运直接表现为文运,这使得唐诗与宋诗精神气象迥然有别,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一为少年才气发扬,一为晚节思虑深沉。从其背后,李泽厚先生从中看出了历史文化的盛衰变迁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少喜唐音,老趋宋调,这种个人心绪爱好随时间迁移的变迁,倒恰好象征式地复现着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和它的主角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由少壮而衰老,由朝气蓬勃、纵情生活到满足颓唐、逃避现实的历史进程。”①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126页。宋人学诗,始于晚唐,终于晚唐,三百年一个轮回,透露出某种意味深长的历史宿命感。严羽指点其时诗坛,忧从中来:“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②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7页。如果说严羽论诗“兴趣”诸义主要针砭江西诗派,而“气象”诸义锋镝所指多为江湖诗派。针对江湖诗人学晚唐形成的狭窄窘促、细碎僻涩之弊,宋人俞文豹就表达过类似忧虑和批判:“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技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孪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邪!”③俞文豹:《吹剑录》,《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831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羽批判孟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不能认同韩愈对孟郊的称许,概因孟诗有违严羽心中推崇的刚健正大、青春勃发的盛唐气象。
四、结语:反理复情的诗学旨趣
中国诗歌史,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观念的演变,都将抒情视为诗歌的本质,尽管“诗言志”经过儒家理性精神的改造,带有强烈以礼乐精神为核心的政治化、道德化色彩,但正如清人边连宝在《病余长语》卷六中所指出:“夫诗以性情为主,所谓老生常谈,正不可易者。”哪怕不同历史时期诗歌在“载道”与“言情”之间存在一定的消长起伏,却始终不能背离情这个诗歌的根基。情在中国文化中毁誉不一,表现为思想史上的抑情论与诗学史上的尚情论基本对峙的格局,中国人的情感在思与诗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默契与平衡。这一平衡在南宋理学大兴之后,通过理学对文学领域全面渗透逐渐被打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主导的创作风气和存养心性、复归性理的诗学理念偏离了文学的抒情本质与审美精神,使得传统文化中原本就狭窄的情感空间被严重挤压。这一趋向引起了当时和明清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不绝如缕的反拨。对此,宋人已有“宋诗非诗”的看法,“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辩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④刘克庄:《竹溪诗序》,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745页。。明人干脆断定“宋无诗”:“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焉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⑤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八《潜虬山人记》,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453页。以为造成这种局面,江西诗派最难辞其咎:“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⑥李东阳:《麓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1页。
《沧浪诗话》所展开的“以禅喻诗”是一系列讨论,倡导“妙悟”,标举“兴趣”,推崇“盛唐气象”,正是“说江西诗病”,反对宋诗的理性化、学者化、议论化的风气,回归诗歌抒情之途,正本清源的一种努力,是对其时诗歌困境的一种忧患之思和积极回应。正如前人所谓:“沧浪论诗独为诣极者,匪直识见超越,学力精深,亦由晚唐、宋人变乱斯极;鉴戒大备耳。正犹《孟子》一书发愤于战国也。”①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338页。严羽的“悟”是极力将诗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情感抒情本质,对诗的解缚,归根结底,是对被理学禁锢僵化的生命的解放,恢复生活世界的活泼泼生命情感。谢思炜对此有深刻的见解:“悟入在解释文学或艺术时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在直接的感性形式中来感受人的生命和活动,在语言形式中突破概念指义活动而进入人的真正的生活世界;其次则是在艺术中象在禅悟中那样显现,把握人的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恢复人的本源性的存在状态。”②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5页。解放诗性就是解放人性,回归生机盎然,鸢飞鱼跃的人之本源,只在“有情之天下”中,才能造就一种青春勃发,刚健阔大的时代气象,这或许是严羽对垂暮卑弱的末宋文化的一种深沉忧患和寄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