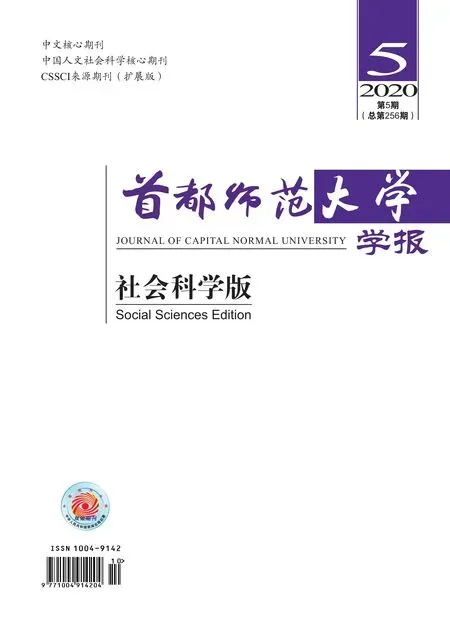兼顾个人与社会
——法国社会主义先驱皮埃尔·勒鲁思想初探
倪玉珍
一、勒鲁:从被遗忘的社会主义者到受热捧的社会主义先驱
在活跃于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众多社会主义者当中,勒鲁(Pierre Leroux,1797—1871)的光芒曾长期被我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等人遮蔽。国内多数读者至多只知道勒鲁是圣西门的弟子和《论平等》一书的作者。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勒鲁的研究主要限于通过解读《论平等》来探析勒鲁的平等观。①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喻名峰、毕金华:《论皮埃尔·勒鲁的平等观》,《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周志成:《“平等幻觉”与“勒鲁平等”的当代意义滤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甚至在法国,勒鲁也遭遇了近一个世纪的遗忘。然而,在法国的七月王朝(1830—1848)和第二共和国(1848—1851)时期,勒鲁曾是一位令人瞩目的社会主义者。他的学说在作家和工人中颇具影响力,维克多·雨果和著名文学批评家圣·勃夫都曾受其影响,著名浪漫派诗人拉马丁将勒鲁誉为“19世纪的卢梭”,小说家乔治·桑甚至自称为勒鲁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热忱信徒。①David Owen Evans,Le Socialisme Romantique,Pierre Leroux et Ses Contemporains,Paris:M.Rivière,1948.勒鲁在工人中的影响力,从他在1848年第二共和国确立后被工人选为布萨克(Boussac)市市长和国民议会议员,可以窥见。勒鲁的学说之所以在当时不仅能吸引无产者,而且能吸引具有自由主义或共和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源于其学说内在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与勒鲁曲折的经历不无关系。勒鲁曾于1821—1822年加入致力于通过密谋起义建立共和国的烧炭党,后又于1824年与其朋友杜布瓦一起创办《环球报》(Le Globe)宣扬自由主义学说。②Jean-Jacques Goblot,Pierre Leroux et ses Premiers Ecrits(1824—1830),Ly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1977,pp.2-3.此后他受圣西门的学说影响,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加入圣西门学派。1831年1月,《环球报》正式成为宣扬圣西门主义的喉舌。不过,勒鲁很快因为反感于圣西门学派建立新神权政治而离开后者创立的圣西门教会。他宣称自己既反对圣西门学派的“绝对的社会主义”,也反对七月王朝时期盛行的“绝对的个人主义”,③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éditépar Bruno Viard,Paris:Desclée de Brouwer,1997,p.156.并试图将圣西门主义的精髓与自由平等的思想融为一炉,探索出一套社会主义学说。对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反思,赋予了勒鲁的学说独特的丰富性。正因为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学界重新发现“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学术转向中,它得到了关注与热议。
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思想界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失望感,促成了一场批判“极权主义”的潮流。④倪玉珍:《法国当代左翼思想变迁述略》,《政治思想史》2012年第3期。不少原本亲苏的左翼知识分子转向自由主义,另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则试图寻找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勒鲁的社会主义学说重获关注。对勒鲁的研究在法国逐渐升温,勒鲁的重要著作也相继得以出版或再版。
尽管勒鲁及其学说受“热捧”,但研究勒鲁学说的高质量专著却很少见。贝尼舒(Paul Bénichou)的《先知的时代》堪称研究法国浪漫主义时期政治思潮的经典之作,但其中只有一章涉及勒鲁。⑤Paul Bénichou,Le Temps des Prophètes:Doctrines de l’Age Romantique,Paris:Gallimard,1977,p.357.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虽大力推介勒鲁,但他本人并不研究勒鲁。维亚尔(Jacques Viard)关注勒鲁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往来,而不重视探究其思想本身。⑥Jacques Viard,Pierre Leroux et les Socialistes Européens,Le Paradou:Actes Sud,1983,p.14.肖巴尔(Armelle Le Bras-Chopard)的《差异中的平等》试图对勒鲁的学说作全面探究,但此书在理论探析的深度上仍显不足。⑦Armelle Le Bras-Chopard,De l’ Egalitédans la Différence.Le Socialisme de Pierre Leroux,Paris: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1986.法国学界为何缺乏研究勒鲁学说的高质量专著?一方面,这源于勒鲁学说自身的不足:中学毕业后因贫困放弃报考大学的无产者勒鲁缺乏闲暇和必要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勒鲁的受关注与法国的政治论争密切相关,因而一些研究带有论战色彩。尽管如此,在国内学界对勒鲁的学说作初步的介绍和探讨仍有必要。勒鲁虽不是训练有素的学院派作者,但丰富的阅历使他得以广泛接触和观察社会现实。此外,正如曾旅居法国的德国诗人海涅所言,勒鲁不仅具有高度的理性思辨能力,而且敏感并富有同情心,⑧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352.这种特质使勒鲁对时代问题具有深刻的直觉和洞察力。勒鲁一生著述甚丰,其著作论题涉及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诸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勒鲁的思想作全面介绍,只限于探析勒鲁关于“社会”的论述。在笔者看来,勒鲁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作的辩证且富有张力的论述,是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二、勒鲁转向圣西门主义:宣告“社会”的死亡与呼唤新宗教
1830年7月,一场革命使复辟的波旁王朝覆灭,七月王朝确立。革命胜利后不久,《环球报》创刊人之一杜布瓦和多数编辑离开该报,只余下勒鲁和圣·勃夫等人苦苦支撑。自9月起,勒鲁开始与圣西门学派接近,继而与后者商讨转让《环球报》事宜。1831年1月18日,《环球报》正式成为圣西门学派的喉舌。①Jean-Jacques Goblot,Pierre Leroux et ses Premiers Ecrits(1824-1830),p.8,pp.16-17.
勒鲁为何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一个自由派转变为圣西门主义者呢?政治局势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七月革命的胜利使复辟时期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然而,在勒鲁看来,七月革命只是使大资产者取代旧的封建贵族垄断了政治,并利用其垄断的权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②Jean-Jacques Goblot,Pierre Leroux et ses Premiers Ecrits(1824-1830),p.23.要理解勒鲁的批评,有必要了解七月王朝确立后法国的政治社会状况。七月王朝延续复辟王朝时期以纳税额确定选民资格的制度,1831年4月的新选举法通过后,法国只有16万余人,即占总人口数0.5%的人有选举权。③H.A.Collingham,The July Monarchy:A Political History of France,1830-1848,London,New York:Longman,1988,p.71.在社会经济领域,七月王朝奉行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这使得少数垄断权力的富人很少承担社会责任。七月王朝政权的这一利己主义特性,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越发显示出其恶果。工业革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在一些工业城市,如里尔、鲁昂、南特等地,工人的贫困、其身体和道德状况的恶化以及童工等问题日益引起公众注意。④André-Jean Tudesq,Restoration and Reaction,1815-1848,trans.by Elborg Forst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76.出身贫寒、当过排字工人的勒鲁深知工人的苦难。出于对七月王朝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无所作为的失望,复辟时期关注“政治”斗争的勒鲁,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⑤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p.98-99.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圣西门学派关于社会重建的学说强烈地吸引了勒鲁。
圣西门学派是1825年圣西门逝世之后,由他的追随者罗德里格斯(Olinde Rodrigues)、昂方坦(B.P.Enfantin)、巴札尔(Amand Bazard)等人组建的。1825年10月,他们创办了《生产者》(LeProducteur)周刊,宣扬圣西门主义。自1828年末起,他们在塔朗纳街举办定期的公开讲授活动,吸引了众多听众。圣西门的学说为何能吸引昂方坦、巴札尔以及曾担任圣西门秘书的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孔德(Auguste Comte)等才识很高的年轻人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圣西门的学说表达了19世纪初法国人普遍感受到的对社会分裂的焦虑,并提供了解决方案。对社会分裂的焦虑主要受到三个层面的事实激发:在政治层面,自1789年大革命爆发至19世纪上半叶,法国始终未能确立稳定的政制,政体不断更迭,政治重组的努力屡遭挫败。在经济层面,工业化及自由竞争的推进,扩大了贫富差距,瓦解了传统的社会关系,激化了社会冲突。在道德层面,启蒙和革命破坏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却未能提供帮助法国人获得道德共识的信条。⑥M.Agulhon,J.Birnberg and F.P.Bowman,Les Socialismes Français 1796-1866:Formes du Discours Socialiste,Paris:Sedes,1995,p.191.这种状况使不少人产生了空虚、怀疑甚至绝望的感觉,这种虚无感同时伴随着内心对信仰和新世界的渴望。拉马丁于1819年说出了一代人的心声:“我们的痛苦,是生在这样一个可恶的时代,一切旧的东西都坍塌了,而新的又还没到来。”⑦Pierre Rosanvallon,Le Moment Guizot,Paris:Gallimard,1985,p.19.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圣西门提出了关于法国危机起源的解释,以及重建社会的设想。他认为,法国之所以在革命后长期陷入分裂与动荡,根源在于领导革命的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对政治的思考并非确立在考察社会事实的基础上。他们忽视对历史和社会的考察,以抽象的自然权利学说为原则指导政治活动。在圣西门看来,实施政治变革需要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适应。①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王燕生、徐仲年、徐基恩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3页、第270页。因而,要弄清法国适宜确立何种政治制度,首先需要考察“社会状况”。他呼吁法国人把运用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实证方法运用到对人和社会的考察上,以便确立“科学的政治学”,以区别于“形而上学的政治学”。②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第259页。圣西门认为,对社会状况的考察不应只限于社会现状,还应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做广泛的历史考察。他对欧洲自11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做了一番历史考察,并得出以下结论:11世纪欧洲的军事—神学封建社会体系正式确立,自11至15世纪,这一社会体系占据了统治地位,实业则处于从属地位。自公社解放运动和阿拉伯人将实证科学传入欧洲以来,实业和科学的力量不断壮大,并得到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保护。自16世纪宗教改革至大革命前夕,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致力于批判军事—神学的封建社会体系。然而,16至18世纪的批判只是成功地打击了旧的社会体系,却未能建立起新的替代物,欧洲陷入道德和政治的混乱之中。圣西门认为,要走出危机,需要从“批判”旧体系转向“建设”新体系,推动欧洲确立实业—科学的社会体系。这意味着一方面要促成实业家掌握世俗权力,另一方面要在实证和科学的基础上确立新的信仰体系,以替代旧神学。③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第264-284页。晚年的圣西门越来越强调确立新信仰体系的重要性。在1825年出版的《新基督教》中,他呼吁创立“新基督教”。这是一种关注未来而非关注来世的世俗宗教。在圣西门看来,“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是新基督教的神圣原则,人们应当按照这个原则,把社会组织得“可以保证最穷苦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得到最迅速和最圆满的改善”。④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三卷,董果良、赵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3-164页。
对勒鲁来说,圣西门对“批判的时代”的批判赋予了他批判七月王朝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圣西门提出的改善最贫苦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状况的社会理想,又给予了他希望和行动的目标。在满怀热忱地拥抱了圣西门主义之后,勒鲁宣告“社会”的死亡,并呼唤它的重生。在1831年9月发表于勒鲁主办的《百科全书》杂志的《致哲人》中,他把不平等但有机的神学—封建社会与七月王朝时期的原子化社会做了对比。勒鲁指出,在6至18世纪的神学—封建社会里,尘世充满苦难和不公,但人们相信来生以及上帝面前的平等。同时,尘世的社会具有“家庭的外表和形式”,即便地位最低下的人,也会感到自己和这个家庭有关联。启蒙哲人摧毁了基督教的根基,把个体从封建社会这个“家庭”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使个体不再感受到与整体的关联,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对旧信仰的破坏使怀疑主义成了普遍的法则。⑤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93,p.91,p.86,p.119.
勒鲁认为,当个体不再能确信什么时,他只是听凭激情和偶然性的支配,只为自己活着,只活在当下。这样的人,只有“自然的自由”而无“道德的自由”。前者是动物的自由,即听从本能;后者是人的自由,它驾驭本能。为了拥有道德的自由,需要一个理想,一个支点。当个体不再知道什么是美德和义务时,他只是在各种激情之间做一个计算,在欲求的满足中寻求幸福,却没有与欲求平衡的力量。然而,当人人都追求自然的自由时,势必相互冲突,陷入战争状态。⑥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p.119-122.这正是勒鲁眼中社会的悲惨景象。在他看来,七月王朝时期的社会利己主义盛行,弱肉强食。掌权的强者奉行“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把自由竞争视为正义的原则本身。他们把耶稣赶出神庙,开始崇拜金银。他们一心只求在竞争中获胜,不再把扶助弱者当成义务,甚至处心积虑地剥夺弱者。⑦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p.90-91.尽管他们是社会的强者,但他们也是不幸的:他们被逐利的欲望俘虏,过着利己主义的生活,“没有伟大,没有多样,没有诗意,受利益的牵制并总是遭到破产的威胁”⑧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185.。工人则沦为为获得一块面包或奶酪而劳动的机器,工人们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绝大部分时间与机器相伴,没有机会发展理性、培育情感、养成道德。①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第37页。当这些不幸的人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面对他们的只是冰冷的刑罚。②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90.
在勒鲁看来,七月王朝的社会已沦为“利己主义者的集合体”,这样的社会,已经死亡了。勒鲁认为“社会”并非“人的简单的集合”,而是“人的总体关系”,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当人与人相互疏离、缺乏相互关联的纽带时,当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失去和谐的统一时,社会就死亡了。③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78,p.133.勒鲁批评那些只看到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繁荣与财富增长,并自以为生活在人类文明顶点的人,只能用“肉体的眼睛”看,不能用“心灵的眼睛”洞察到社会的危机。④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87.
受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启发,勒鲁认为社会的重建离不开宗教的重建。⑤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83.那么,未来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宗教?勒鲁期待的是一种取消了现世—来世二元分立的世俗宗教。他相信圣西门的预言:黄金时代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或来世。⑥Sébastien Charléty,Histoire du Saint-Simonisme,Paris:P.Hartmann,1931,p.31.
1831年1月,勒鲁宣告自己成为圣西门主义者。此时,圣西门教会已存在一年有余:1829年12月,圣西门学派通过选举确认了两位领袖——最高神父昂方坦和巴札尔,成立了圣西门教会。⑦George Weill,L’ École Saint-Simonienne:son Histoire,son Influence jusqu’àNos Jours,pp.39-40.
三、对圣西门教会的反思:勒鲁调和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努力
关于未来的新宗教,刚加入圣西门教会的勒鲁并未形成系统的学说。此时他更多是追随教会的主张。自1828年起,圣西门学派逐渐向教会转变。他们一方面发展了圣西门关于组织实业的学说,另一方面日益强调确立统一的信仰体系。在组织实业方面,他们主张废除继承权,以便取消不劳而获者的特权;同时确立统一的银行体系,由中央银行和一些次级银行集中管理生产资料,并根据每个人的生产能力进行分配。⑧巴札尔、安凡丹、罗德里格:《圣西门学说释义》,王永江、黄鸿森、李昭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七讲、第八讲。爱弥尔·涂尔干:《社会主义与圣西门》,见爱弥尔·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李鲁宁、赵立玮、付德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382页。圣西门学派认为,一旦采取这些措施,实业将趋于繁荣,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和无序状态将逐渐消除。不过,他们认为,仅仅组织实业不足以完成社会重建。只有当实业制度获得统一的信仰体系的支持,社会的统一与和谐才有真正的保证。这个信仰体系不同于传统基督教,它以促进实业和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成员的团结协作为目标。⑨爱弥尔·涂尔干:《社会主义与圣西门》,(同上)第392-393页。
为了论证基督教衰落之后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宗教时代,在1828至1829年的公开讲座中,圣西门学派进一步发展了圣西门关于批判的时代与建设的时代的区分,并使其成为一个明确的理论。他们把人类历史划分为有机时代和批判时代。在前一个时期,共同的信仰把所有个人的活动集中起来,使它们朝向一个共同目标。在后一个时期,共同的信仰崩溃,个人各行其是,利己主义盛行。在圣西门学派看来,基督教居统治地位的11至16世纪是一个有机时代,而自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16至18世纪则是一个批判时代。16至18世纪的批判者对旧社会体系的攻击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由于他们只破不立,又使欧洲陷入道德和政治的混乱之中。要走出这一危机,必须尽快结束批判时代,重建统一的信仰体系。(10)巴札尔、安凡丹、罗德里格:《圣西门学说释义》,第三讲。
在昂方坦的影响下,圣西门学派日益把圣西门晚年写的《新基督教》视为宗教启示,把创立新宗教视为社会重建的首要步骤。他们宣扬泛神论,宣称“上帝就是一。上帝就是一切;一切皆存在于上帝之中……它从物质和精神两个主要方面向我们呈现自身……”由此,曾遭基督教贬低的“物质”的地位得以恢复,它与“精神”同样神圣。科学家对宇宙的研究和实业家的生产劳动因而是神圣的。①爱弥尔·涂尔干:《社会主义与圣西门》,(同前)第390-391页。这种泛神论还倡导人类的博爱,预言人类将不断走向更美好的未来。②巴札尔、安凡丹、罗德里格:《圣西门学说释义》,第293页。Paul Bénichou,Le Temps des Prophètes,pp.280-281.关于社会的组织,圣西门学派设想社会由履行三种职能的人构成:第一种人是神父,他位于社会等级的顶端,因为他对上帝怀有最深厚的爱,并能促成科学和实业的联合及和谐发展;第二种人是科学家,即运用理性去认识万物或者说认识上帝的人;第三种人是实业家,他的劳动是献给上帝的祭礼。一切社会职能皆神圣,因为它们都源于上帝,科学家和实业家也是神父,只不过是较低层级的神父。③Sébastien Charléty,Histoire du Saint-Simonisme,p.58.在最高神父昂方坦和巴札尔看来,在未来的社会中,18世纪的启蒙哲人倡导的个体自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依其对上帝的爱和才能的多寡而定,因而层级较低的人只需服从层级较高的人,整个社会就会达至统一与和谐。④Sébastien Charléty,Histoire du Saint-Simonisme,p.66.
显然,勒鲁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与圣西门教会的等级制并不协调,这个矛盾为他日后与圣西门教会的决裂埋下了伏笔。1831年1月,刚加入教会的勒鲁与几位信徒被派往比利时及法国的一些城市考察工人状况并传播社会福音。此行成果颇丰,他们在比利时创立了一个教会和六个传授圣西门主义的中心,并在里昂赢得了不少皈依者。⑤P.-Félix Thomas,Pierre Leroux,sa Vie,son Oeuvre,sa Doctrine:Contributionàl'Histoire des Idées au XIXe Siècle,Paris:F.Alcan,1904,pp.33-35.然而正当他们沉浸在喜悦中时,圣西门教会却酝酿着分裂的危机。分裂主要源于最高神父昂方坦对婚姻和妇女问题的看法。圣西门学派倡导男女平等,反对天主教对独身的偏好,主张“恢复身体的权利”。然而昂方坦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他认为存在两种天性不同的人,一种是具有忠诚气质的,另一种是喜爱变动的。婚姻适于前一种人,对后一种人来说,婚姻生活不能使其满足,他们往往因此走向谎言甚至犯罪。既然这种天性是上帝赋予的,为何不允许这些易变的心灵随心所欲地改变婚姻状况呢?此外,昂方坦认为,既然继承权不复存在,家庭也不应存在,“自由之爱”就是正当的了。⑥George Weill,L’ École Saint-Simonienne:son Histoire,son Influence jusqu’àNos Jours,pp.96-97.昂方坦的主张遭到巴札尔的坚决反对。两位最高神父的分歧引发教会内部的激烈论战。1831年11月,巴札尔、勒鲁等一批核心成员相继离开教会。⑦George Weill,L’ École Saint-Simonienne:son Histoire,son Influence jusqu’àNos Jours,pp.103-105.
圣西门教会的分裂使圣西门学派趋于衰落和瓦解,同时也促使勒鲁反思圣西门学派的社会重建方案。1834年,勒鲁在《百科全书》杂志发表《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批判了两种学说:“绝对的个人主义”和“绝对的社会主义”。前者认为只有个体是真实的存在,社会只是人们构想出来的抽象概念。它至多只承认社会是个体的聚合或个体订立契约的产物。这种学说崇尚个体自由,反对干预自由竞争,认为政府应当“被限制在最狭小的行动领域里”,充当一个“无足轻重的守夜人”。勒鲁认为七月王朝奉行的正是这种学说,其恶果是强者奴役弱者。正是为了治疗这种弊端,改善贫穷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圣西门学派强调社会是有机体并且优先于个人,并试图重组社会。然而他们最终确立的是“新教皇制”,在他们设想的由少数“先知”引领的社会里,只有极少数个人享有自由,大多数个人不再是“活泼泼的有自由意志的生命”,而是“一块有用的物质”、一个“机械地服从社会”的工具。勒鲁表明他既不赞成绝对的个人主义,也不赞成绝对的社会主义,他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社会学说,以便调和个体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这“两把互相开火的手枪”⑧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p.158-162.。
圣西门学派从批判“批判的时代”开始,最终走向“新教皇制”。对这一事实的反思促使勒鲁重估16至18世纪这一“批判的时代”。勒鲁试图将“批判的时代”及其倡导的个体自由放置在一个新的历史进步图景中加以阐释。他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例如在古代东方,个体被整合进一个等级森严的种性制社会。在那里,不同等级的人被规定了不同的社会职能,社会是统一的,但它是以个体的不平等和不自由为代价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公民享有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以特权的形式为少数公民享有,大量的奴隶没有自由。同时,公民过多地被吸纳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有政治自由而无个体自由。因而,在这一时期,自由和平等的实现很不完全。基督教的出现使人类在追求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一方面,通过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一部分人得以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挣脱出来,到世俗社会之外发展其个体性。①Pierre Leroux,D’une Religion Nationale ou du Culte,Boussac:Imprimerie de Pierre Leroux,1846,pp.62 64.世俗社会与精神社会的二分及相互斗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诞生了“个性与自由”:对世俗社会的专制不满的个人,可以到精神社会里寻求庇护,反之亦然。②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p.201-202.另一方面,基督教宣称的“上帝面前的平等”使“人类的平等”第一次在精神领域获得了承认。在此之前,包括在古代共和国中,只存在社会等级内部的平等。③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第135页。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每个人平等地享有自由这个理想尚无法实现。自从入侵欧洲的蛮族和基督教会共同确立起封建—神学社会体系以来,上帝面前的精神平等与尘世中的不平等并存。基督教会使人陷入“对来世天国的迷信”之中,个人被教导要服从现存的秩序。④Pierre Leroux,D’une Religion Nationale ou du Culte,pp.66-67.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p.81-82.自16世纪开始,伴随着科学与实业的发展,欧洲进入了人类的解放时代。“第一次解放”——新教改革以耶稣和圣经的名义反抗教会,但个人仍服从耶稣的权威。在17至18世纪的“第二次解放”中,个人逐渐完全摆脱传统的羁绊:在科学和哲学领域,否定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权威;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否定了以荷马为代表的权威;在宗教领域,否定了以耶稣为代表的权威。⑤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p.140-141.
那么,16至18世纪是否如圣西门学派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批判和破坏的时代呢?勒鲁认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从始于17世纪末并持续了50年的“古今之争”中,诞生了一个重要学说——人类的进步和可完善学说。这一学说由帕斯卡等人提出,并由孔多塞、圣西门等人加以发展。这个学说构成了新宗教的根基。⑥Pierre Leroux,“De la Doctrine de la Perfectibilité,” Oeuvres de Pierre Leroux,Paris:Louis Nétré,tome II,pp.25-56.它使人期盼未来而非来世,它把个人放置到一个永恒的时间之链中,使个人意识到自己与人类的关联:“人类的精神是相互关联的;在所有人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共通之处;个体的精神在一个由人类的普遍理性培育出来的空间里生活着;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人的精神都是由先前世代的人们的劳作,以及整个人类的协作构建起来的建筑。”⑦Pierre Leroux,Réfutation de l’ Éclectisme,Paris:Librairie de Charles Gosselin,1841,p.44.
由此,在勒鲁的历史阐释中,16至18世纪的启蒙哲学不再是与中世纪传统的决裂,而是人类继承了过去所有世代的精神遗产之后的成果。受到启蒙哲学滋养的现代世界,使“上帝面前的平等”在尘世获得了初步实现:人们不再首先把自己看成某个特殊等级的成员,而是首先把自己看成唯一的一种等级——人类的成员。⑧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第264-265页。勒鲁认为现代人和古代人的一个重大不同是:他仅仅因为具备“人的资格”就可以享有各项自由权利。启蒙哲人和革命者宣称这一点并试图使之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哲人和革命者高扬个人理性并批判旧秩序,并非要颠覆一切宗教,而是为新宗教作准备。1789年的《人权宣言》是新的“人类宗教”(la Religion de l’Humanité)的福音书,而“整个大革命就是一个萌芽中的宗教”⑨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200.。
通过把人类历史阐释为平等和自由在神意指引下不断得到实现,以及人类从相互隔绝到融为一体的进程,勒鲁为大革命的格言“自由、平等、博爱”祝了圣:“它是神圣的,它代表人们追求的理想,它象征-神示的未来……”①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第19页。
为“批判的时代”和个体自由所做的辩护,表明了勒鲁与圣西门教会的距离。为平等祝圣和对新宗教的渴盼,又表明勒鲁与“绝对的个人主义”的距离。在勒鲁看来,个人远非独立于社会,每个人都从社会中汲取了元气与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应当成为被动服从社会的工具。恰恰相反,“社会的完善源于所有人和每个人的自由”。②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p.165-166.既然所有人平等地享有自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那么,应当如何组织社会,才能兼顾自由与平等、个体与社会呢?勒鲁认为,首先应继承人类在16至18世纪的“解放”中取得的成果,承认并保障个人享有的各项自由权利,其次还应确立“社会权力”,由它来负责平等地教育所有儿童,促成公共理性的进步,并组织工业缩小贫富差距。③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202,p.226.圣西门学派设想“社会权力”由少数“先知”掌管。勒鲁则认为,这一设想是对古代和中世纪的宗教组织的模仿。由于现代社会与古代和中世纪的社会已有天壤之别,这种模仿注定要失败。勒鲁认为,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存在着阻碍知识传播和人员流动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障碍,少数杰出的个人——他们往往被称为“救世主”和“先知”——得以支配多数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少数人对知识和权力的垄断逐渐变得不可能,“救世主”和“先知”的预言逐渐被公共舆论取代。那么,在现代社会,谁来充当立法者呢?那就是“由受人民委托的人表达出来的人民的意志”④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p.169-173.。因而,代议制并非像圣西门学派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批判者用来摧毁旧社会体系的工具。相反,它是“进步的永恒的必需的工具,是未来社会的可完善的却不可或缺的形式”⑤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171.。勒鲁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使代议制更加完善。在一个不同质的社会里,相互冲突的利益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朝向未来呼吁进步的,一个是在现状中感到满意的,这是“永恒的政治的二元性”。让这两种利益都得到代表,“谁也不压倒另一个,没有动荡或者以最小的动荡取得进步,越来越走向同质,统一,平等”,这就是代议制政府的目标。⑥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175.
结 语
至此不难看出,勒鲁为何会被一些学者誉为法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先驱。勒鲁试图对圣西门主义做平等化的改造,并在其中加入尊重个体性的元素。这一努力使圣西门主义更能与19世纪中叶之后的时代潮流相适应,从而有助于它保有持久的生命力。在改造圣西门主义的同时,勒鲁也继承了圣西门的重要精神遗产:对社会问题和精神重建问题的关注。和圣西门一样,勒鲁也认为,对政治的理解不应过于狭隘,政治变革不仅仅关乎对政治制度的完善,它还关乎社会的重新组织,尤其是道德人心的建设。缺乏必要的社会团结和良好民情的支持,好的政治制度也难以持存。例如,当议会中的各利益群体缺乏道德共识时,议会政治就容易沦为利益群体之间无节制的争斗和阴谋诡计。⑦Pierre Leroux,Aux Philosophes,aux Artistes,aux Politiques:Trois Discours et Autres Textes,p.195.和圣西门学派一样,勒鲁表现出对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冲突的焦虑,以及对社会统一的渴望。这种焦虑促使他在强调代议制不可或缺的同时,又宣称政治与宗教密不可分。在勒鲁看来,只有当代议政治有了一个宗教根基,社会才不致分崩离析。1846年,勒鲁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倡议法国确立国民宗教。⑧Pierre Leroux,D’une Religion Nationale ou du Culte.不过,这个小册子侧重于论证确立国民宗教的必要性,并未详述国民宗教的信条。从散见于勒鲁各个时期著作的宗教论述来看,他期待确立的是一种世俗宗教。他称之为“新基督教”或“人类宗教”。这种新宗教以人类的进步和可完善学说为根基,以1789年的《人权宣言》为“福音书”,宣扬人类的统一、人类成员之间的平等和博爱。关于新宗教的信条如何产生,勒鲁也未详述。他只是在原则上指出,未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同时也是宗教评议会。它将确立宗教信条,并有权力和义务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统一的宗教教育。勒鲁考虑到,统一的宗教教育保证了社会统一,却有可能压制个体自由。针对这一危险,他提出以下建议:首先,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宗教评议会可以依据人民的意愿,对宗教信条作适时和必要的修改。其次,区分人生的两个阶段——童年和成年。社会对个体的宗教教育只限于童年时期,成年后个体得以摆脱社会的监护,同时成年个体享有的各项自由权利有助于个体抵御社会可能施予的强制。①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p.226-228.
从勒鲁的论述来看,他所说的“人类宗教”更像是一种哲学或政治学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不过,勒鲁学说中包含的宗教色彩,使他在19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退潮、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兴盛之后,开始遭到贬低。此外,1848年6月工人起义遭镇压后,法国的社会冲突激化,勒鲁主张折中调和的学说在无产者中的影响力下降。1852年路易·波拿巴利用军事政变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确立第二帝国之后,勒鲁被迫长期流亡国外。1871年勒鲁逝世后,其学说逐渐湮没无闻。
尽管勒鲁的社会主义学说曾长期遭到遗忘,但它的重获关注表明它并未丧失生命力。勒鲁敏锐地感受到了法国现代化转型期的社会危机。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勒鲁试图调和基督教传统与现代政治原则,调和社会性和个体性,重建社会团结。尽管勒鲁未能提出一套系统的可操作的政治方案,但他为后世的人们继续思考社会问题开启了重要路向。勒鲁所揭示的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力、自由与平等、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始终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正如法国著名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所言,勒鲁的社会主义学说在当今的法国仍具有重要价值,因为他提醒人们:一个仅仅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以生产为本位的社会,是不足以让人们生活得幸福的。②Pierre Leroux,A la Source Perdu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