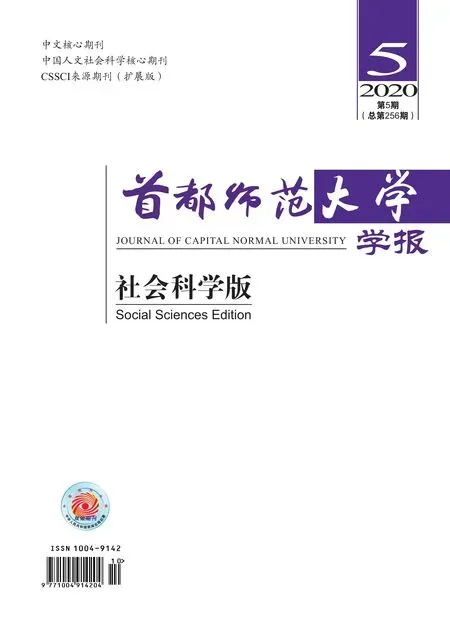从《中日丛报》与《中国丛报》之渊源看早期英美汉学与日本学的伴生现象
尹文涓
《中日丛报》(TheChineseandJapaneseRepository,1863—1865;以下简称《日丛》,英文简称 CJR)是英国19世纪早期汉学家、日本学家詹姆斯·萨默斯(James Summers,1828—1891)在伦敦编辑出版的一份英文月刊。①James Summers ed.,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of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History and Art,Relating to Eastern Asia,London,July 1863-Dec.1865.国家图书馆有馆藏。该刊不仅是西方第一种将中国和日本两国并列作为研究主体的学术期刊、是欧洲知识界第一次将日本从当时汉学概念中的“其他亚洲属国”中单列出来,也与早期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1801—1861)在广州创办的知名英文期刊《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1832—1851;以下简称《丛报》,英文简称CR)有着莫大的渊源关系。②E.C.Bridgman ed.,The Chinese Repository,Canton,May 1832-Dec.1851.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全套20卷本馆藏,国家图书馆有影印本馆藏;关于《中国丛报》作为西方第一种汉学期刊的地位与意义,参见石田干之助:《欧美关于中国学的诸杂志》,唐敬杲译,《学术界》第 1卷(1943—1944年)第 6期,第 44-45页;Elizabeth Malcolm,“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1850,”Modern Asian Studies,7,2(1973),pp.165-178;尹文涓:《〈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英美汉学》,《汉学研究通讯》,2003,no.2,第28-37页。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丛报》的史料价值及其于美国汉学之发肇的意义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但对于其某种意义上的“续刊”《中日丛报》则较少关注。③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见关于《中日丛报》的专门研究,但日本学界对于该刊的价值早有重视,1967年日本雄松堂(Yushodo)出版了该刊影印版,前有编者撰写的长篇前言,介绍了该刊的缘起和在日本研究方面的内容。参见“James Summers,Editor and Professor,”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vol.1,no.1,日本雄松堂影印版,1967。本文拟在简介《中日丛报》创刊缘起、内容体例的基础上,从西方汉学学科史的角度,辨析该刊与《中国丛报》之渊源同异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早期美国汉学与英国汉学的同源发生关系,以及美、英汉学与日本学的伴生关系。
一、詹姆斯·萨默斯与《中日丛报》
(一)詹姆斯·萨默斯生平
詹姆斯·萨默斯为19世纪英国早期汉学家、日本学家、语言学家。1848年,萨默斯前往香港圣保罗学校任教,次年6月,因在澳门天主教活动中的不当行为,引发史称“岑马士事件”的葡—英外交冲突①萨默斯亦译苏谋斯、岑马士。关于此事件的代表性研究参见马锦强:《1849年詹姆士·岑马士事件研究——英澳早期关系一个案》,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于1851年返回英国。
1852年底,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开设“中文班”(China Class),萨默斯被聘为中文班授课,成为英国汉学史上第三位汉语教授。②在此之前,伦敦大学大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于1837年开设英国首个为期五年的中文讲席,基德(Samuel Kidd,1799—1843)被聘任为首任中文教授(1837—1842);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于1847年开设首个中文讲席,费伦(Samuel T.Fearon,1819—1853)为首任汉语教授(1847—1852)。但这两个学院的中文讲席在首任期满后均长期停开。萨默斯的“中文班”课程不仅教授中文官话,还教授若干种方言,深受那些计划赴华的外交官、传教士以及商人的欢迎。兼之此时正值中国和日本被迫与西方建立外交关系之初,在1875年牛津大学开设汉语课程之前,国王学院的“中文班”是当时英国唯一开设常规汉语课程的地方③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为理雅各,任期为1875—1897年;剑桥大学于1888年设置“汉语教授”职位,威妥玛为首任教授。,因而也成为19世纪下半叶英国外交部招收驻华外交官的指定培训中心。以1854至1858年为例,英国外交部招收的22名驻华外交官中有20名是来自萨默斯的这个“中文班”。“中文班”的诸多学生如固威林(William Marsh Cooper,1833—1896)、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庄延龄(Edward H.Parker,1849—1926)、梅辉立(William F.Mayers,1831—1878)、道格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1838—1913)等,后来在19世纪“中英日”三方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萨默斯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多年,其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著作中:《中国语言与文学讲义》④James Summers,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ondon:John W.Parker&Son,West Strand,1853.《约翰福音书》⑤该书是用拉丁字母翻译的《约翰福音》上海方言译本,参见:James Summers,The Gospel of Saint Joh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According to the Dialect of Shanghai,London: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853.《汉语手册》⑥James Summers,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汉语手册》),Oxford:University Press,1863.关于《汉语手册》的代表性研究参见于海阔:《19世纪汉学家萨默斯的〈汉语手册〉及其汉语教学思想述论》,《理论月刊》2013年第5期。《中文基础》⑦James Summers,The Rudim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Dialogues,Exercises and a Vocabulary,London:Bernard Quaritch,1864.《中、日、满文书目汇编》⑧James Summers,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Japanese and Manchu Books,London,1872.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汉语手册》,该书既是一部重要的汉语研究著作,也是一本优秀的汉语口语和书面语教科书。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评价该书为“英国第一部汉语学术著作,是汉语专业学生最有用的手册”⑨德庇时著,王仁芳译:《英国汉学起源与发展——19世纪上半叶》,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259页。。日本的内田庆市教授亦将《汉语手册》列为“西洋人汉语研究文献重要资料之一”(10)内田庆市:《近代西洋人的汉语研究的定位和可能性——以“官话”研究为中心》,国际汉学研究网,2010-04-25。。
1873年,萨默斯应日本明治政府邀请前往他关注已久的日本,在东京开成学校(今东京大学)教授英国语言与文学,于1891年病逝于东京。
(二)《中日丛报》的创办、编撰及运营
萨默斯创办、编撰并任主笔的《中日丛报》,全名为“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of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history and art,relating to eastern Asia”①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of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History and Art,Relating to Eastern Asia,London,July 1863-Dec.1865.,为英文月刊。该刊首期刊印于1863年7月,1865年12月终刊,共29期。和《中国丛报》一样,《中日丛报》也是每卷出齐之后,再合订成卷,前附各期目录及索引。该刊29期合订3卷:第一卷为1863年7月号至1864年6月号;第二卷为1864年8—12月号;第三卷为1865年1—12月号。该刊为大32开本,封面中间以及周边印有“实事求是”“言心声也书心画也”等中文格言,印刷相当漂亮整洁,可见当时在伦敦中文活字铅印已经比较便利。
《日丛》在创刊号中对该刊的内容和主旨作了说明,表示该刊“严格限定”(as a rule)于与“中国和日本”相关的以下四方面内容:
1.关于远东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哲学、语言文学、地理、历史、传记、艺术及人民生活状况的论文(Papers or Essays),原创或译作均可;
2.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学术动态和书评(Literary Notices and Reviews of Books);
3.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要闻综述或重要官方文件(Summary of Events and Documents);
4.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时事新闻杂录(Miscellanea)。②“Advertisement,”CJR,July 11,1863,p.2.
这一方面表明了《日丛》的关注对象是“中国和日本”,而且性质上属于相当严肃的学术刊物;另一方面,这其实也体现出《日丛》的栏目设置,该刊每期内容大体分栏为:Papers(论文)、Literary Notices(学术动态)、Summary of Events(要闻综述)、Miscellanies(新闻杂录)。从该刊现有三卷的内容来看,第一类的“论文”内容占据了该刊的主体,一般每期4—5篇文章;此外“书评”、“要闻”和“杂录”三类的内容,一般都是合编在每期最后一篇文章里,分量大概为每期的五分之一。除了没有Religious Intelligence(宗教通讯)栏目,《日丛》的这个栏目设置基本上是照搬《丛报》。
在栏目编排上,《日丛》也采取了《丛报》后期的体例方式,即目录中不设栏目,标题按序号标以“第一篇”(Art.I)等,每期大概5篇文章左右,约40页。第一卷上标有序号的文章计有66篇,加上编者刊首关于本刊以及汉学出版情况的长文,实为67篇,合计522页;第二卷只有5期,共刊载文章43篇,230页;第三卷上共刊载文章112篇(目录显示为100篇,遗漏2篇),592页。三卷合起来共计222篇文章,不含广告内页,篇幅共计1344页。但目录中的很多文章实际上是重复的,因为该刊采取了将一篇文章分多次连载的方式。《日丛》这种连载的方式,一是篇幅所限,二也是为吸引读者,这是19世纪报刊为保持订阅量的典型策略。
《日丛》的稿件来源主要为三部分:其一是撰稿者供稿,据笔者统计,《日丛》上以全名或缩写方式署名的撰稿者共计有40名,除去其中7名为非主动撰稿(稿件为从其他期刊转载或旧稿重印)外,至少还有33名撰稿者是主动为该刊供稿。其中有英国汉学家德庇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法国汉学家洛图尔(Count d’Escayrac de Lauture,1826—1868)、颇节(M.G.Pauthier,1801—1873),德国汉学家贾伯莲(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z,1807—1874),以及日本学家弗雷德里克·维克多·迪金斯(Frederick Victor Dickins,1838—1915)和萨道义等。第二类稿件来源,是从其他在中国或欧洲出版的报刊及汉学杂志上转载文章,如《丛报》、《泰晤士报》、《亚洲杂志》(JournalAsiatique)、《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中国之友》(FriendofChina)、《德臣西报》(ChinaMail)等。第三类稿件,就是萨默斯本人主笔的文章。19世纪西方出版的这类私人报刊,由于资源问题,编辑往往充任主笔,《日丛》每期的“书评”、“动态”或“杂录”等文章的编撰,均出自萨默斯本人之手。
《日丛》撰稿者的署名方式,要么是署全名;要么是署以姓名缩写如“C.C.”,或身份如“a Medical Officer of the Royal Navy”、“a German missionary”等。除此以外,该刊还有大量文章未署名。不过,以姓氏缩写方式署名的情况,根据其文章内容等信息,大部分可以推断出作者名字。③目前《日丛》上仅一署名为“L.M.F.”的撰稿者,笔者无法推断出其真实姓名。《日丛》第二、三卷上共刊载了该作者的8篇文章,内容主要为关于李白、班昭、屈原等中国古代文学家的介绍,参见L.M.F.,“Distinguished Men of the Tang Dynasty,”CJR,vol.2,pp.19-22.笔者就此请教于方家。譬如,卷二上某篇题为《1843年上海开埠记》的文章,作者署名缩写为“W.H.M.”①W.H.M.,“Reminiscences of the Opening of Shanghae to Foreign Trade,”CJR,vol.2,Oct.1864,pp.79-88.,根据文章内容和当时在华外侨名单,我们可推断作者为麦都思之子麦华陀(Walter H.Medhurst,1823—1885)。
《日丛》在第二期(1863年9月号)封二上刊载过一个订户名单,显示当时该刊一共有订户60人。②“List of Subsribers,”CJR,vol.1,no.2,August 1863,inside front cover.其中包括两名前港督德庇时和文翰(Samuel G.Bonham,1803—1863)、时驻日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1807—1897)、时任上海领事巴夏礼(Harry S.Parkes,1828—1885)、奥斯曼铁路公司主席斯蒂文生爵士(Macdonald Stephenson,1808—1895)、英国皇家海军中国舰队司令阿斯本(Sherard Osborn,1822—1875)③1861年“李泰国—阿斯本事件”之相关人。、著名的鸦片商人颠地(John Dent,1799—1853)、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等。可以说,订户基本上是英国驻华或当时与中国事务相关的政、商、教会界人物。④“The Principal Promoters to the ‘Repository’,”CJR,vol.1,no.4,Oct.1863,inside front cover.此外,《日丛》1863年10月号上还刊登过一份含19名个人和3家传教差会的“本刊主要赞助者名单”(The Principal Promoters to the“Repository”)。除现任港督罗便臣(Hercules Robinson,1824—1897)一人外,该名单基本与订阅者名单重合。而且这其中,又有7人如伟烈亚力、德庇时等,同时也是《日丛》的撰稿者。
《日丛》读者、赞助者和撰稿者3个群体的大面积重合,会导致该刊所能构建的舆论空间相对狭窄。这说明该刊要么内容主题对于当时的英语世界还颇为生僻,要么定价超出一般消费水平,或者兼而有之。
该刊的定价刚开始是每期2先令6便士,整年预订优惠价为1英镑1先令(合21先令)。⑤再加1先令英国境内包邮;该刊还承诺每月3号前发行,以便赶上途经南安普顿港的“大陆邮政”发往美国和海外其他国家。“Advertisement,”CJR,July 11,1863,p.2.参考当时英国阅读群体与消费能力,这一价格显然偏高。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爱丁堡评论》发行量为800份左右,其定价也不过每本5先令(季刊,年订费合20先令),就已经将读者限定为中上等阶层人群。⑥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日丛》这一定价政策显然使得其订阅量非常不乐观,为了扩大订阅量,该刊第4期刊登了一个降价通知,将年订阅费减半,降为半基尼(10先令6便士)。⑦“Reduction in the Price of the‘Repository’,”CJR,vol.1,no.4,Oct.1863,inside front cover.这也就意味着,《日丛》订户如果没有有效增长的话,其订费年收入将不过30镑左右,这笔收入显然不足以维持一份刊物的正常运转。
或许是为了解决该刊运行经费的实际需要,《日丛》还推出了内页广告。起初广告内容多为与中日研究相关的书籍、期刊等。譬如,首刊号封三上的4则广告,第一则是关于萨默斯自己的代表作《汉语手册》,当时该书刚刚刊印,可谓即时推广;第二则广告是关于一份名为《英伦中国通讯》(TheLondon andChinaTelegraph)的期刊,上有售价及订阅方式;第三则是洛图尔的新书《中国回忆》(Memoiressure laChine)预告,广告的语言是法语,声称该书很快将出版;第四则广告也是法语的,是关于巴黎出版的一份学术期刊《东方与美洲研究》(RevueOrientaleetAmericaine)。⑧CJR,vol.1,no.1,July 1863,inside back cover.
《日丛》还尝试过更广泛的商业广告。该刊10月号特意登载了一则广告推广消息,声称“本刊目前已经发行到东亚广大地区,实为广告推送之绝佳媒介。如有需要,本刊编辑还可以将广告翻译成中文刊印”。为吸引广告,编辑还向读者保证:
日本、安南、暹罗这些国家但凡受过教育的人以及新加坡、巴达维亚、婆罗洲、马尼拉、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利亚的中国移民都识汉字,本刊在这些国家均有发行。
中文广告将会大力促进东、西方商业界之间的信任和友好交流,消除贸易的一大障碍。中国和日本有数百万人口,欧洲人可以与他们直接打交道。现在身处汉口这样的中国内陆城市的商人,都可以直接订购英国的商品并顺利收到货物,简直像法国商人从英国购买产品一样的容易。⑨“Notice to Advertisers,”CJR,vol.1,Oct.1863,inside back cover.
至于收费,则是一则5行的广告,翻译成中文收费2先令6便士、用中文印刷再收费4先令6便士,共计7先令,如果以中、英文双语登载则有优惠。(10)“Notice to Advertisers,”CJR.不得不说,萨默斯不仅仅是位中文教授和汉学家,也是一位极有商业眼光和超前的全球化意识的人;当然,这也是当时西方报刊运营机制商业化以及当时英国贸易全球化的某种体现。但显然,“中文广告”和全球购这样的概念对于当时的英国实在太超前,萨默斯此举并没有为《日丛》吸引更多的广告。
不管怎么样,《日丛》在1865年12月发行最后一期后停刊。回顾创刊之初,萨默斯曾满怀希望地表示,如果将来得到更多资助,希望可以将篇幅扩大到64页。①“Notice to Advertisers,”CJR.显然他一直没有得到预期的资助,扩版的愿望也一直没有实现。《日丛》停刊的直接原因,除了经费的困难,其相对生僻的主题显然也不符合西方新闻所谓的大众化趣味(general interest),必然会导致该刊在订阅量和稿源等方面难以为继。当然,《日丛》的命运也有其时代原因,英国自1861年彻底取消印花税之后,一方面是各种模仿美国大众报刊风格的廉价“便士报”蓬勃发展②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第37-41页。;另一方面,报刊很难维持稳定订户,报刊的创办和消失经常可见。可以说,《日丛》之停刊,和当年《丛报》之停刊一样,都是必然。③1873年,萨默斯在伦敦还创办了第一份海外日文报纸《大西新闻》(The Taisei Shinbun)。该报目标读者是留英的日本学生,内容多为欧洲时闻名胜之类,但这份报纸销量不好,很快就破产停办。
二、《中日丛报》与《中国丛报》之渊源
《中日丛报》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之一,在于其自命为《中国丛报》的“续刊”。《中日丛报》“创刊词”开篇即宣称《中国丛报》为本刊之“前身”:
早年在中国居住过的外国人都非常熟悉先前的《中国丛报》(the original Chinese Repository),而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份期刊的标题以及本期的内容,都无疑会让他们回忆起那份可敬期刊的宗旨和风格。鉴于《丛报》在英国并不广为人知,我们有必要先向国内的读者介绍一下本刊前身《丛报》(the former Repository)的风格和宗旨,以便让读者了解本刊的目标和展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广阔领域。④James Summers,“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Scope and Objects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CJR,July 11,1863,pp.1-12.该文署名为“the editor”。黑体下划线标注为笔者所加,下同。
萨默斯开门见山地搬出《丛报》,以及“the original Chinese Repository”和“the former Repository”等措辞,无不是为《日丛》和《丛报》的血缘关系正本清源,声称《丛报》为《日丛》之“前身”、《日丛》为《丛报》之续刊。
接下来,该文简要介绍了《丛报》之始末,并指出:“裨治文博士和卫三畏博士精心编撰的《丛报》,以其长达二十卷之篇幅及其刊载的那些富有启示性的论文和文章,使之足堪为最有价值的参考书籍。”⑤James Summers,“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Scope and Objects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CJR.《日丛》编辑对《丛报》的这一“最有价值”的评语并非虚套,在此后的文章中,读者还会发现《日丛》向《丛报》频频致敬的例子。最有意思的是在1864年4月号的一则书讯中,编辑还不忘特别提示读者,法国汉学家洛图尔在其新著《中国回忆》中对《丛报》的推崇,指出“该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为《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国丛报》”,而且作者“虽然对于前者给予了恰当的称赞,但他认为后者更加详实”。⑥“Notices of Books,&c.,”CJR,vol.1,April,1864,pp.441-442.1864年刊印的《中国回忆》(Memoires sure la Chine)应该是洛图尔该书的首版;后该书完整出版时书名为“La Chine et les Chinois”(Paris,1877)。
《日丛》因而在“创刊词”里顺理成章地表示,该刊的创刊目的,一是为了重印《丛报》上的文章:
《丛报》存本散佚不全,有人曾建议重印《丛报》。重印全套《丛报》固然并不可取,但有理由相信,如果将该刊部分原创文章重新刊印,读者将十分愿意乐见其成并从中获益。本刊一旦获得足够的资助得以扩版,就会每期适量重刊《丛报》上的文章。⑦“Notices of Books,&c.,”CJR.
二是为了“接手”继续《丛报》未竟之事业:
《丛报》那两位博学的编辑在终刊号上曾表示,希望将来有人接手(taken up by other hands)该刊中断的未竟之业;《丛报》所展现的研究领域之广阔,前所未有,他们放弃这一事业,实非得已。⑧“Notices of Books,&c.,”CJR.虽然以萨默斯对广告效用的领会,不排除《日丛》自命为《丛报》续刊有借《丛报》之名为自己正名之嫌。但上文所表达出来的对《丛报》作为一份汉学期刊的认可和继该刊之“绝学”的使命感,同样毋庸置疑。这才是萨默斯以继承《丛报》之“遗志”为己任,并“接手”续办这样一份期刊的重要动机。
当然,最能体现《日丛》和《丛报》之传承关系的,是该刊不仅如前文所言努力延续《丛报》的体例和编撰风格,而且还如其在创刊词中所承诺的那样,重刊了《丛报》上的部分文章。《日丛》上明确注明是重印自《丛报》的文章有8篇(连载以单篇记)。①《日丛》只简单交代转载于某期刊或著作,一般无详细原刊出处。其中3篇为卫三畏所撰,题目分别为《苗族简介》②《日丛》上刊载信息为:“The Miáu-tsz,or Aboriginal Tribes,inhabiting various Highlands in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Proper,Reprinted,with alterations,from the‘Chinese Repository’,”vol.1,Oct.1863,pp.139-149;该文实际上是由《丛报》上两篇文章构成,前半部分是卫三畏所撰的同名文章,后半部分是译文,均载于《丛报》第14卷3月号。Samuel W.Williams,“Notices of the Miáu Tsz,or Aboriginal Tribes,”CR,vol.14,March 1845,pp.105-115;Samuel W.Williams,“Essays on the Justice of the Dealings with the Miáu Tsz,”CR,vol.14,March 1845,pp.115-117.和《日本宗教和近代大事记》以及《日本政治、人民、法律、监狱等》③“The Religious Sects and the Principal Events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CJR,vol.1,Nov.1863,pp.220-232;“Japan:its Political States;its People,Laws,Prisons,&c.,”CJR,vol.1,Jan.4,1864,pp.315-321;Feb.3,1864,pp.350-356.,后两篇分别是卫三畏编译的关于日本问题系列连载文章中的第10篇和第5篇,标题略有改动。④Samuel W.Williams,“Notices of Japan,the religious sects of the Japanese (10),”CR,vol.10,no.6,June 1841,pp.309-319;Samuel W.Williams,“Notices of Japan,politics,classes,laws,prisons&c.,”CR,vol.10,January 1841,pp.10-20.
《日丛》从《丛报》上所转载的篇幅最长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文学常见历史与传奇故事》,在《日丛》上从第一卷12月号到第三卷7月号上陆续分12次连载。⑤“Extracts from Histories and Fables to which Allusions are frequently made in Chinese Literature,translated from the‘Arte China’of Père Goncalves,”CJR,vol.1,no.6,pp.248-254;&c.该文原载《丛报》第20卷(1851年),分3期连载,标题有轻微改动。⑥“Extracts from Histories and Fables to which Allusions are commonly made in Chinese Literary works,”CR,vol.20,no.2,pp.94-105;no.3,pp.122-152;no.4,pp.194-215.该文内容节选自葡萄牙籍遣使会传教士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calves,1781—1841)1829年出版的《汉字文法》(ArteChina),原文为葡萄牙语,由前港督、汉学家包令(John Bow ring,1792—1872)将其节译为英文刊于《丛报》。
除以上文章外,《日丛》上标示重印自《丛报》的文章还另有4篇。⑦“Bootan and Tibet in relation with China,”CJR,vol.3,May 1865,pp.201-208;“Notes on the City of Fuhchanu-Fu,”CJR,vol.3,no.27,Oct.1865,pp.462-464;“Statistics of the Ta-Tsing Dynasty,”CJR,vol.3,no.29,Dec.1865,pp.548-559(CR,vol.12,p.57.);“Names and Area of the Chinese Provinces,”CJR,vol.3,no.29,Dec.1865,pp.559-560(CR,vol.4).但显然,《日丛》自《丛报》转载的文章比其标注出来的要多,譬如,《日丛》1864年9月号上一篇题为《1847年从广州到上海的旅行》的文章⑧“Reminiscences of a Voyage from Canton to Shanghai,in the summer of 1847,”CJR,vol.2,Sept.1864,pp.62-69.,该文没有署名,注释“摘自私人日记”。但根据文章内容以及当时在华活动的外侨情况,可以追溯出作者为裨治文及其刊载于《丛报》上的原文。⑨E.C.Bridgman,“Voyage from Canton to Shanghai,from the journal,”CR,vol.14,August 1847,pp.398-406.
应该说,《日丛》无论是在其抱负和内容上都做到了传承《丛报》。《日丛》在第二卷的一篇文章中,借德庇时之口重申了该刊和《丛报》的关系。这篇题为《欧洲的汉学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by Europeans)的文章,介绍了德庇时新近在皇家东方学会会议上宣读的一篇关于英国汉学界成果及动态的文章,里面特别提到德庇时在文章中肯定了“詹姆斯·萨默斯教授,重新创办(re-establish)了一份《中国丛报》这样的关于中国和日本之期刊”的贡献。(10)James Summers,“The Study of Chinese by Europeans,”CJR,vol.2,no.13,August 1864,pp.26-28.显然当时英国汉学界对于《日丛》作为《丛报》之续刊,是认可的。
值得关注的是,萨默斯何以如此执念于“重办”《丛报》,以及他本人和《丛报》当年所建构的外侨群体的关系。笔者以为,萨默斯本人与《丛报》起码有如下几方面的渊源:
其一,萨默斯应该是《丛报》忠实的读者。一方面,《丛报》是当时外侨群体中影响最大的英文报刊之一,尤其是该刊关于中国及侨民动态消息的报道,对于当时像萨默斯这样身处开埠之初的香港岛的侨民而言,不啻日常生活指南;另一方面,对于萨默斯这样一个具有语言天赋且热心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人,《丛报》也是当时侨民最方便而权威的读本。
其二,《丛报》曾报道过萨默斯。《丛报》一贯密切关注侨民动态,萨默斯甫一抵港,就被录入《丛报》年度“外侨名单”①“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CR,vol.18,Jan.1849,pp.3-9.;自然,《丛报》也没有错过报道萨默斯1849年在澳门引发的英—葡武装冲突事件。《丛报》在报道该事件时保持了相当客观的态度,既肯定了葡方拘捕萨默斯的不合理性,也指出英方武装劫狱并枪杀无辜的野蛮行径。②“Register of the Principal Events Have Occurred in China from Sept.1st 1848 to Dec.31,1849,”CR,vol.18,Dec.1849,pp.669-710.
其三,有理由认为,萨默斯与裨治文两人有直接的交往。萨默斯1851年离开香港回英国前,曾在上海居留。③在《丛报》当年的“外侨名单”中,萨默斯的居住地也从香港变更为上海。“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CR,vol.20,Jan.1851,pp.3-14.据《丛报》统计,1851年居住在上海的西方人含传教士、海员、外交官、游客等共计153人。④这个名单不含少数家眷,但包含部分回西方休养的人。“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CR.这其中受过教育并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感兴趣的“中国学人”(Chinese student)不过寥寥数人⑤“汉学”“汉学家”等词汇的定义到 19世纪末期才固定下来;在此之前,法语和英语中大多以“sinologue”“students of Chinese”“Chinese Scholar”,指代“学习中文的人”“中国学者”。参见拙文《〈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英美汉学》,第 28-37页。;而且,19世纪上半叶在华的外侨群体,一般集中居住且非常依赖于侨民团体关系。⑥萨默斯1849年被扣押于澳门监狱中时,就曾给美国驻粤领事福士(Paul S.Forbes)写信求援,信中提到他与伯驾相熟。马锦强:《1849年詹姆士·岑马士事件研究——英澳早期关系一个案》,第32页。因此,萨默斯在上海期间,极有可能与裨治文交往,而此时正是《丛报》处于停刊风波之际,《日丛》后来在创刊词中所转达的《丛报》停刊之遗憾和“续刊”之愿望,或许正是起因于两人的交际。
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日丛》与《丛报》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表面的排版、印刷来看,《日丛》更为规范齐整。《丛报》早期的刊印是局限于华南沿海的地下活动,条件一直非常简陋;而《日丛》是在当时排印技术最先进的伦敦出版,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从《日丛》封面的汉字印刷质量来看,当时伦敦已经有便利的中文活字铅印。此外,《日丛》的内页还夹杂了一些关于订阅和相关书籍出版的广告活页,这也是欧洲报刊的编辑发行相较于30年前《丛报》创刊时期更为灵活的体现。这是印刷技术和报刊生产机制方面的时代进步,这一进步,也为学术研究的生产、发展提供了条件,包括汉学研究。
但两刊之间最本质的差异,就如两刊标题所明示,是关于“中国”和“中国与日本”的差异。虽然,从内容比例来看,《日丛》上关于日本的介绍并不比《丛报》多;而且,可以肯定《日丛》编辑对于日本的知识和兴趣,很大部分是来自《丛报》,《日丛》上第一篇介绍日本文化的文章,就是转载《丛报》上卫三畏的日本问题系列文章。但是,《日丛》在刊名中将“日本”与“中国”并列,毫无疑问是将对日本的关注放到与中国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欧洲知识界第一次郑重地将日本从“其他亚洲国家”(Other Asiatic Nations)中单列出来,甚至可以说是欧洲“日本学”的开始。
内容上的另一个差异,是《日丛》上没有《丛报》上的一个重要栏目,即“宗教通讯”(Religious Intelligence),而且其他栏目内也基本没有关于传教活动的报道⑦《日丛》上刊载过一些关于教会医疗活动的报道。;虽然从捐资及读者名单看,该刊和教会组织及个人的关系仍然密切。这也使《日丛》免于《丛报》当年曾遭受的“宗教性质”的指责,尽管《丛报》编辑曾反复申辩自身从经费到性质都与教会无关。
三、《中日丛报》与19世纪中叶欧洲汉学
石田干之助曾这样评价汉学期刊对于汉学研究的重要推进作用:“在欧美的中国学,和其他任何学问同样,为日进月累的不绝进步。其所以有这样的进步,各国底学会跟研究所等所发行的关系杂志,继续刊载有力的新研究,实为最大的因素。”①石田干之助著:《欧美关于中国学的诸杂志》,第39页。从 1851年《丛报》停刊之后,到 1890年《通报》(T’oung Pao)创刊之前,这四十年是西方汉学期刊的断裂时期。期间与中国研究关系较为密切且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性期刊主要有:《亚洲学报》(JournalAsiatique,1822—1938)、皇家亚洲文会系统的如《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oftheNorthChinaBranchoftheRoyalAsiaticSociety,1858—1859;1864—1948)、《中日释疑》(NotesandQueriesonChinaandJapan,1868—1870)、《中国评论》(TheChinaReview,1872—1901)等。也就是说,在《日丛》创办之前,勉强算得上“汉学”期刊的只有《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②这个学会及会刊是《丛报》停刊后裨治文在上海所经营的重要事业。学会成立于1858年,裨治文任首任会长,初名“上海文理学会”,1859年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初名为《上海文理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该刊可以说是《丛报》真正意义上的续刊,如果将裨治文为《会报》撰写的发刊词和28年前他为《丛报》写的发刊词相比较,就会发现两刊的主旨和内容设计如出一辙。“Preface,”Journal of the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No.1,July,1858,Shanghai.但该刊在1858—1859年期间只不定期出过四册,1864年才续刊,以季刊年合订卷方式发行。并且在19世纪,该刊所刊登的90%的文章都来自“亚洲文会”所举办的内部演讲活动③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第 80页。,影响不大。如此说来,在19世纪中叶欧美汉学期刊出现几乎长达40年断裂的时期,1863年创办的《日丛》是一个近乎“续存”汉学的努力。
当然,一份刊物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所刊载的文章的分量。《日丛》创刊号首先隆重推出的都是当时已经比较知名的汉学家的文章,第一篇就是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题为《犹太人在中国》的论文④Alexander Wylie,“Israelites in China,”CJR,vol.1,no.1,July 1863,pp.13-22.;第二篇是瑞典汉学家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1819—1954)的《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该书于1854年刊印于香港,是西方人所著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最早著作之一,《中日丛报》连续4期连载重印⑤Theodore Hamberg,“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and Origin of the K wang-si Insurrection,”CJR,vol.1,pp.22-29,pp.53-63,pp.99-111,pp.150-163.;接着两篇正文分别是英国汉学家艾约瑟关于中国科学、文学等方面的介绍和洛图尔的《关于中国的回顾与展望》。⑥Joseph Edkins,“On the Present State of Science,Literature,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CJR,vol.1,no.1,July 1863,pp.29-32;d’Escayrac de Lauture,“Thoughts o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hina,”CJR,vol.1,no.1,July 1863,pp.32-36;August 1863,pp.70-77.
《日丛》上最有分量的汉学文章之一,无疑是1864年9月号上所刊载的法国汉学家儒莲的《〈边裔典〉中的突厥部史料》一文。⑦Stanislas Julien,“Historical Documents relative to the Tu-Kiue(Turks),”CJR,vol.2,no.14,Sept.1864,pp.45-50.该文原标题为“Documents Historiques sur les Tou-Kioue(Turcs),extraits du Pien-I-Tien”,原载于法国《亚洲杂志》(JournalAsiatique)1864年第3、4卷,分5次连载,长达200多页。儒莲该文利用的是《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第130卷“突厥部汇考”的资料,所继承的是其师雷慕沙的西域研究传统。《日丛》刊发此文的时间基本与《亚洲杂志》同步,而且估计拟将其全文连载刊出,因其9月号上该文的末尾写了“待续”(to be continued)。但《日丛》后来却并没有继续连载,不了了之。推其原因,估计是因为该文篇幅太大,而且涉及在当时欧洲汉学界算是较为前沿且偏涩的西域研究,《日丛》编辑人手及能力均不足敷,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发展中的英国汉学与较发达的法国汉学之间的差距。
此外,《日丛》还节译了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的《中国戏剧》。⑧Antoine Bazin,“The Chinese Drama,”CJR,vol.1,April 1864,pp.435-441.《日丛》上还可以找到雷慕沙另一位高足、法国汉学家颇节的文章,即第一卷9月和10月号(1864)上两期连载的《马可·波罗行记》⑨M.G.Pauthier,“A Memoir of Marco Polo,the Venetian Traveler to Tartary and China,”CJR,vol.1,no.3,pp.124-129;no.4,pp.169-188.,由萨默斯译自法文。这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原创文章,为后来颇节于1865年出版的《马可·波罗行记》的节选。(10)M.G.Pauthier,Le Liver de Marco Polo,Paris,1865.该书为首次依据马可·波罗原稿的三种手抄本整理而成,且除异文校勘和说明外,还补充了大量史地注释,在版本学和蒙元史研究方面均很有价值。《日丛》在该书出版前提前节译、登载其内容,可见对当时欧洲汉学界的情况和最新动态非常了解。
从英国汉学的角度,《日丛》上比较有分量的文章是德庇时的《汉文诗解》。①J.F.Davis,“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CJR,vol.1,Jan.1864,pp.291-307;Feb.1864,pp.323-343.《汉文诗解》长文首版登载于1830年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这个版本是介于首版和1870最后增订版之间的一个修订版。不仅如此,在《日丛》上还可以找到19世纪德国知名语言学家、德国汉学奠基人之一的贾伯莲的文章。②贾伯莲又译加贝伦茨、甲柏连孜,其父是有名的满文学家。贾伯莲曾与儒莲一起跟随雷慕沙学习中文,后先后于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任教,毕生致力于中国语法的研究,著有《汉文经纬》(GrammatikderChinessichen Schriftssprache,1881)、《汉语语法基础》等。贾伯莲在《日丛》上发表的文章题为《蒙古语言与文学》③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z,“A Sketch of the Mongo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James Summers,”CJR,vol.1,March 1864,pp.401-410.,其时年仅18岁,估计是他最早的汉学成果。该文是萨默斯自己从德语翻译成英语,这一方面说明萨默斯对欧洲汉学最新进展跟踪密切且颇具慧眼,当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欧洲汉学整体上并不繁荣的事实。
体现编辑对刊物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主动定位和筛选的方式之一,就是长篇连载。《日丛》篇幅十分有限,但以连载的方式刊载过好几篇长文。其中连载时间跨度较长的一篇是英译版《雷峰塔:汉文与白蛇的故事》(Lui-fung Ta,Thunder-Peak Pagoda)④“Lui-fung Ta,Thunder-Peak Pagoda,of The Story of Han-wan and the White Serpent,translated from Chinese by H.C.,interpreter in Her Majesty’s Civil Service in China,”CJR,vol.1,Feb.1864,pp.357-365.,该文在《日丛》上自1864年2月号开始分7次连载,译者署名“H.C.,Interpreter in Her Majesty’s Civil Service in China”。⑤笔者推测这个“H.C.,Interpreter in Her Majesty’s Civil Service in China”极有可能为固威林(William Marsh Cooper,1833—1896)。固威林1852年入国王学院,就读于萨默斯任教的“China Class”,属于英国第一批专业中文学生。1855—1888年先后在厦门、香港、广州、汕头等地任中文翻译及领事。《日丛》上还有一篇作者署名为“C.C.,Interpreter in Her Majesty’s Civil Service in China”的文章,题为《中国的殉夫风俗》(“Suttee in China,”CJR,vol.1,May 1863,pp.457-461.),与《雷峰塔》译文第4次连载前后排版。根据文内“领馆译员”“我们相邻的福州”等信息,结合1865年前后英国驻华人员名单(https://archive.org/stream/bub_gb_YtI9AAAAcAAJ),可以推定这个“C.C.”就是时为厦门使馆译员的固威林。 再由“H.C.,Interpreter in Her Majesty’s Civil Service in China”和“C.C.,Interpreter in Her Majesty’s Civil Service in China”近似的署名习惯,可推两名作者为同一人。据笔者考证,这个《雷峰塔》英译本所据中文底本,就是嘉庆十一年(1806)刊印的“姑苏原本”《雷峰塔奇传》,为五卷十三回章回体小说。
笔者以为,《日丛》上的这个译本应该是白蛇传故事最早英语全译本。白蛇传故事最早的西译本是儒莲的法语译本《白蛇精记》,1834年由巴黎戈斯兰出版社出版。⑥S.Julien,Blanche et Bleue ou Peh ShiéTsing Ki,les Deux Coulouvers-fees,Paris,1834,p.326.同年刊印的《皇家亚洲学会学报》在书评栏目介绍了儒莲的这个译本,认为《白蛇精记》不同于西方以往译介的中国小说,在于其民间流行和迷信特色,而且该书中文版也才新刊印不久。《皇家亚洲学会学报》同时简要概述了法译本的故事内容,且特别强调其内容“只是概述故事,并非翻译”⑦“Reviewed Works:Pe-shi-tsing-ki:Blanche et Bleue,ou les deux Couleuvres Fées,Roman Chinois by S.Julien,”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1,no.2,1834,pp.307-321.,经笔者核对儒莲译本,也确非完整转译。
康提尼·巴黎塔的伊莎拉酒庄建立于2012年,由印度尼西亚人和意大利人合伙经营。除了瓦利尔慕斯卡特和阿方斯莱弗宁,酒庄还种植了黑玛尔维萨和西拉。目前,酒庄仅酿造3款酒:伊莎拉莫斯卡托白葡萄酒、伊莎拉桃红葡萄酒和伊莎拉红葡萄酒。
《日丛》上另外一篇连载时间较长的文章,就是弗雷德里克·维克多·迪金斯翻译的日本和歌《百人一首》,自1865年3月号至11月号分9次连载。⑧Frederick Victor Dickins,“Translation of Japanese Odes,from the H’YAK NIN IS’SHIU(Stanzas from a Hundred Poets),”CJR,vol.3,March 1865,pp.137-139.此外就是分6次连载的《1862—1863年日本使欧官员游记》,为萨道义所译。⑨Ernest Mason Satow,“Diary of a Member of the Japanese Embassy to Europe in 1862-63;A Confused Account of a Trip to Europe,Like a Fly on a Horse’s Tail,”CJR,vol.3,no.24,July 1865,pp.305-312.这两篇译文是《日丛》上关于日本学的重要内容,下文将展开讨论。《日丛》上连载时间跨度最长的文章,就是重印《丛报》上的江沙维的那篇《中国文学常见历史与传奇故事》。该文共收录各种民俗寓言故事、文学典故共计233条,内容非常庞杂如“哪吒”“杏花村”“狐假虎威”等无分类编排,还有一些如“油郎”“遇故人”等①“Extracts from Histories and Fables to which Allusions are frequently made in Chinese Literature,”CJR,vol.3,no.24,July 1865,pp.305-312.,则无论从语言还是文学而言都价值不大。
体现刊物内容与性质导向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编辑本人的稿件。萨默斯本人为《日丛》撰写了大量稿件,除了编写每期最末一栏的“学术动态”或“中日新闻”外,萨默斯还在《日丛》上正式发表过11篇文章,其中7篇关于中国、3篇关于日本、1篇既有中国也有日本;此外,《日丛》上还刊载过萨默斯所译的3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译文。
《日丛》上关于汉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动态以及近事新闻,就主要见于萨默斯本人编写的“学术动态”、“书评”和“中日新闻”里。“学术动态”一栏大多为各种汉学期刊、学会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马礼逊教育协会”等机构的会议记录、报告等。譬如1864年8月号上刊载的《欧洲的中国文学研究》一文②James Summers,“The Study of Chinese by Europeans,”CJR,vol.2,August 1864,pp.26-29.,就报道了德庇时在当年6月“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上宣读的关于英国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动态的报告。《日丛》还刊载过一些汉学家的传记和讣告,譬如第一卷8月号上关于雷慕莎的介绍③“Memoir of Rémusat,translated from the‘Biographie Universelle’,”CJR,vol.1,August 1863,pp.77-84.,以及11月、12月号上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柯恒儒(Henri Jules Klaproth,1783—1835)的传记。④“Memoir of Klaproth,translated from the‘Biographie Universelle’,”CJR,vol.1,Nov.pp.217-220,pp.254-267.柯恒儒是19世纪欧洲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之一,为巴黎满语研究的发展及远东文献的收藏做出了巨大贡献。
《日丛》“书评”一栏最能体现萨默斯对西方汉学整体和动态的把握。以1863年7月首刊号上一则书讯为例,该则消息是关于洛图尔的新书《中国回忆》(MemoiressurelaChine)的预告,广告语言是法语,声称该书很快将出版。⑤CJR,vol.1,no.1,July 1863,inside back cover.不久,在该刊1864年4月号上的“新书介绍”一栏中,编者告诉读者,该书第一部分最近已经出版⑥“Notices of Books,&c.,”CJR,vol.1,April,1864,pp.441-442.笔者推测1864年刊印的《中国回忆》应该是洛图尔回忆录的首版,为节略本,十多年后该书全本才出版,书名更改为《中国与中国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Paris,1877)。,由此可见萨默斯对欧陆汉学界的密切跟踪。
萨默斯甚至还试图编撰一份西方汉学著作书目,题为《关于中国语言和中国的著作》。⑦James Summers,“The Names of Works on Chinese and China,”CJR,vol.2,Nov.1863,pp.167-168.从标题以及文末的“未完待续”来看,萨默斯是计划编撰一份比较全面的汉学书目,就如《丛报》18卷上刊载的汉学书目《关于中国的著述》(List of Works upon China)一样。⑧S.W.Williams,“List of Works upon China,principally in English and French languages,”CR,vol.18,pp.402-444,pp.657-661.《丛报》这个书目是西人关于西方汉学研究的首次文献整理和研究综述,对后来考狄编撰《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在编目体例、学科分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日丛》这个书目的第一部分收录了起自1763年迄于1860年刊出的30种图书,其中大部分为汉语官话和方言学习的各种词典,包括马礼逊的《英华词典》、马若瑟的《汉语札记》、江沙维的《葡汉词典》、裨治文的《广州方言撮要》、卫三畏的《拾级大成》等。遗憾的是,《日丛》这个“待续”的书目并没有继续。
就如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所言,《中国丛报》的作者名单实际上就是当时西方汉学家的名单。⑨Roswell S.Britton,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Kelly and Walsh,1933,pp.28-29.这个评语同样适用于《日丛》,该刊的撰稿者名单,也是一份当时西方汉学家的名单。《日丛》上的撰稿者,有英国的第一代汉学家德庇时、艾约瑟、伟烈亚力;也有美国的裨治文、卫三畏;同时还有当时已经知名的法国汉学家巴赞、儒莲、洛图尔;还有德国汉学的奠基人贾伯莲、早期葡萄牙汉学家江沙维;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日丛》上开始起步的第一代英国日本学家迪金斯和萨道义。如果说《丛报》和《日丛》的汉学家名单有什么差异,应该说《丛报》是对此前的完全整理,而《日丛》更多的是对“当代”,也就是19世纪中叶欧洲汉学的动态报道。
四、《中日丛报》与英国日本学
一般而言,日本学(Japanology)是指日本开国以后欧美学者以翻译与研读日语经典文献为中心,对日本国家、社会与文化自觉开展的体系化、学术性研究。欧美日本学发轫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语文文献学传统,其研究涵括日本语言、历史、文学、宗教、习俗、艺术、音乐和工艺等诸多领域。
萨默斯关于日本的研究应该始于在国王大学教授汉语期间甚或更早,创办《日丛》后,就开始在该刊“学术动态”“杂录”等栏目刊发一些关于日本以及日本学动态的介绍。譬如,《日丛》首刊号就在“通讯”里提到,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的León de Rosney教授,最近新开设了一门日语课程。①《日丛》同时提到,官方对这门课程并不十分支持并采取了监督。“Literary Notices,”CJR,vol.1,July,1863,p.42.此后关于日本研究的动态里,亦多次提到Rosney关于日语教学和出版的情况。②“The State of our Relations with Japan,”CJR,vol.1,Nov.1863,p.242.随后,《日丛》在11月号上全文翻译并刊发了Rosney在开课仪式上的长篇发言稿。该文在概述日本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现状等情况之后,指出随着日本与欧洲政治和贸易往来的日益增加,(欧洲人)学习日语势在必行。③León de Rosney,“Opening Lecture on the Japanese Language,”CJR,vol.1,Nov.1863,pp.203-214.此外,萨默斯还收集了几乎欧洲所有关于西方日语课程、日本问题研究动态方面的信息。从这些几乎琐碎的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欧洲人开设的第一门日语课程、相关出版、学习日语的动机等方面的情况。这些信息的综合,可以说就是欧洲日本学发端之状态。
《日丛》还重刊了卫三畏的《日本宗教和近代大事记》和《日本政治、人民、法律、监狱等》两篇文章④“The Religious Sects and the Principal Events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CJR,vol.1,Nov.1863,pp.220-232;“Japan:its Political States;its People,Laws,Prisons,&c.,”CJR,vol.1,Jan.4,1864,pp.315-321;Feb.3,1864,pp.350-356.,这两篇文章原刊于《丛报》,标题略有改动。⑤Samuel W.Williams,“Notices of Japan,the religious sects of the Japanese (10),”CR,vol.10,no.6,June 1841,pp.309-319;Samuel W.Williams,“Notices of Japan,politics,classes,laws,prisons&c.,”CR,vol.10,January 1841,pp.10-20.在《日本大事记》一文的末尾,萨默斯加了一句编后语,表示“自1841年《中国丛报》上刊载此文以来,日本已经再度打开国门,而且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日本在最近几年迈入全新的历史阶段,过去的时光一去不返(nec prateritum tempus unquam revertitur)”⑥“The Religious Sects and the Principal Events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CJR,vol.1,Nov.1863,p.232.。可见在过去的二十多年,虽然西方与日本的关系已大变,但西方的日本学并无大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卫三畏在《丛报》上的文章仍有价值。
在前期收集和编撰关于日本问题资料的基础上,萨默斯本人撰写的关于日本问题研究的第一篇正式论文出现在1863年12月号上,题为《我们在日本的政策与机遇》。⑦James Summers,“Our Policy and Prospects in Japan,”CJR,vol.1,Dec.1863,pp.243-248.此后萨默斯还撰写过关于日语语法学习之类的文章⑧James Summers,“The Japanese Language and Grammar,”CJR,vol.2,no.16,Nov.1864,pp.151-158;no.17,pp.215-216.,同时还翻译了一些日本诗歌以及《平家物语》的缩写版。客观地说,就像西方第一批汉学家的贡献主要在语言和启蒙方面一样,萨默斯的日本学研究还并不成体系。
萨默斯对于英国日本学的更大贡献,是培养了后来著名的日本学家萨道义。萨道义于1859—1861年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跟随萨默斯学习中文,1862—1883年任英国驻日公使翻译,1895—1900年间任驻日公使,1900—1906年间为驻华公使。萨道义在《日丛》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日本学方面的文章刊于1865年3月号上,题为《日文的各种字体》。⑨Ernest Mason Satow,“The Various Style of Japanese Writings,”CJR,vol.3,no.20,March 1865,pp.140-141.这篇只有短短两页的文章,就是后来成为日本学专家的萨道义的兴趣开始。或许是因为关于日本的研究特别少的缘故,编者特别欣喜,特别为这篇短文写了按语,提示读者该刊此前还刊发过两篇关于日语学习的文章可供参考。(10)其中一篇其实就是萨默斯本人撰写的《日本语言与语法》,James Summers,“The Japanese Language and Grammar,”CJR,vol.2,no.16,Nov.1864,pp.151-158;no.17,pp.215-216;另一篇为《日语习得》(Hints to Students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该文署名为“a Medical Officer of the Royal Navy”(皇家海军医务官),“Hints to Students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CJR,vol.2,no.17,Dec.1864,pp.216-222.萨道义第二篇关于日本学的文章《1862—1863年日本使欧官员游记》(11)Ernest Mason Satow,“Diary of a Member of the Japanese Embassy to Europe in 1862-63,”CJR,vol.2,no.17,Dec.1864,pp.216-222.在《日丛》上分6次连载,但并未完结,最后一篇文末显示“待续”,遗憾的是《日丛》就此停刊。此外,萨道义还在《日丛》上发表过一篇日本人关于鸦片战争记载的英文译文。①“The Fall of the City of Chinkiang-fu,an incident in the Chinese Opium War 1840-1,translated from the Japanese,”CJR,vol.3,no.27,1865,pp.449-452.
虽然萨道义对于日本学的真正发轫是在《日丛》停刊之后,但毫无疑问,萨默斯和《日丛》启蒙了萨道义对于日本的兴趣,并提供了一个发表和交流的平台。1872年10月30日,日本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Japan)在横滨举行首届会议,该学会的成立与会刊《日本亚洲学会学刊》(TransactionsAsiatic SocietyJapan)的刊印是西方日本学专业化的标志性事件。萨道义此时已成长为学会的重要成员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日本地理》的文章。在任英国驻日公使翻译期间,萨道义继续其师萨默斯的使命,在伦敦创办了一份名为《凤凰杂志》(ThePhoenix)的月刊。②Ernest M.Satow ed.,The Phoenix:a monthly magazine for India,Burma,Siam,China,Japan&Eastern Asia,London,July 1870-June 1873.从副标题“amonthly magazine for India,Burma,Siam,China,Japan&Eastern Asia”看,该刊似乎是想继承《日丛》的遗志,并将“东方”进一步拓宽。可惜的是,《凤凰杂志》继承了《日丛》的宿命,在发行三卷(36期)后,也因经费问题停刊。
萨道义还极有可能引领了另外一位英国人对于日本学的兴趣,这就是《日丛》上引人关注的早期日本学家迪金斯。1863至1865年迪金斯作为英国皇家海军军医到日本横滨,期间因为对植物学和日本文化的共同兴趣,他和萨道义成为终身的朋友,后来又成为日本学研究的同道。③1871—1879年迪金斯以律师身份再度到日本,返回英国后,到伦敦大学任管理工作。迪金斯也是英语世界最早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他关于日本文学和文化的翻译及研究成果,可参见其七卷本作品合集。④Frederick Victor Dickins,The Collected Works of Frederick Victor Dickins,Bristol:Ganesha,Tokyo:Edition Synapse,1999.
《日丛》自1865年3月号至11月号分9次连载了迪金斯翻译的和歌《小仓百人一首》。⑤Frederick Victor Dickins,“Translation of Japanese Odes,from the H’YAK NIN IS’SHIU(Stanzas from a Hundred Poets),”CJR,vol.3,1865.书名前作者名为笔者所加,迪金斯在《日丛》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均署名为“a Medical Officer of the Royal Navy”(英国皇家海军军医),下同。迪金斯不仅将“一百首”和歌全文翻译,还用注释简要介绍了作者背景和诗歌内容。但由于显而易见的编辑排版的原因,1865年8月号上的连载将序号“第50首”译诗遗漏⑥Frederick Victor Dickins,“Translation of Japanese Odes,from the H’YAK NIN IS’SHIU(Stanzas from a Hundred Poets),”CJR,vol.3,August 1865,pp.389-394.,因此,《日丛》上的“一百首”实际上只有99首。有趣的是,该文刊载时署名为“a Medical Officer of the Royal Navy”(英国皇家海军军医),但根据Peter McMillan的英译《小仓百人一首》序言里对早期英译日本诗歌的介绍⑦Peter McMillan,One Hundred Poets,One Poem Each:A Translation of the Ogura Hyakunin Isshu(《小仓百人一首》),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可推测这个“英国皇家海军军医”就是迪金斯。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迪金斯的这个英译本是《小仓百人一首》的第一个西文译本,同时也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日本文学作品。这个日本文学英译的“第一”就是出现在《日丛》第三卷1865年3月号上,次年又以单行本刊印。⑧Donald Keene明确指出:“第一篇日本文学英译、迪金斯的第一篇翻译是在1865年3月份;1866年的版本为再版。”Peter McMillan,One Hundred Poets,One Poem Each:A Translation of the Ogura Hyakunin Isshu.这在西方日本学史上,无论如何是一个标志性和里程碑性质的事件。迪金斯在《日丛》上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是《日本幕府首都江户访问回忆录》⑨Frederick Victor Dickins,“Reminiscences of a Visit to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CJR,vol.3,no.23,June 1865,pp.257-264.,其中提到了卫三畏早前的“远征”(10)指日本嘉永六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打开了日本关闭已久的大门,史称“黑船事件”,其时卫三畏任翻译。。
需要说明的是,就像《丛报》上面有诸多关于中国周边国家的报道和介绍一样,《日丛》的内容其实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和日本,上面也有关于周边国家的形势和文化的介绍,譬如关于朝鲜、印度等地的介绍。①“Geographical Notices on Corea,”CJR,vol.3,no.22,May 1865,pp.236-238;T.Braddell,“Trade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CJR,vol.3,no.21,April,1865,pp.161-176.这不仅仅是源于《丛报》的传统,还由于当时西方人关于东亚研究的地域笼统性,对于区域的界定不是那么明晰和强调;也可以说是一种“东方”的殖民视角。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日丛》上的中国观和日本观。同19世纪来华的大多数西方传教士、外交官们一样,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和关注并不等于热爱,萨默斯的中国观也基本是负面的。《日丛》上关于中国人性格或者文化特点的直接介绍不多,但在评价1861年中英外交摩擦的“李泰国—奥斯本”事件时,萨默斯毫不掩饰其对于中国人“欺骗性”的批判:
只有那些不得不和中国官员打过交道的人,才会真正体会到中国人的欺骗性。中国的外交艺术,也就是隐瞒事实,或者是将谎言掩盖在一副忠君报国嘴脸下的艺术,是中国官员修炼多年的功课。②James Summers,“The Lay-Osborn Expedition to China,”CJR,vol.1,Jan.1864,p.321.
相对而言,日本积极配合西化的态度,导致西方人对日本有更好的观感:
日本在行政管理上的活力、在国家安全保障方面的力量,以及相对有限的君权使得权贵能够参与政见表达与判断——或许是这些因素赋予了日本政治上的这种可以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③James Summers,“Introductory Essay,”p.3.
但日本也免不了和中国同被贴上“半野蛮”和“异教徒”的标签,以及相应的殖民者对中、日共同的“义务”和姿态,“光指出中国和日本是半野蛮人(sem i-barbarians),或者从他们宗教的本质而言,说他们是迷信的异教徒,都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了解他们历史的特质”④James Summers,“Introductory Essay,”p.8.。
由此我们发现,正如《丛报》是美国汉学的起点一样,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日丛》可以视为英美专业日本学的起点。从《丛报》早期对日本的关注与报道,到其续刊《日丛》的专门日本研究,可以总结的一个事实就是:早期英美的“汉学”之中包含了对日本的关注和兴趣;《日丛》作为《丛报》之续刊,体现了英美汉学界从“中国学”到“日本学”扩展的清晰脉络,乃至东方学的扩展过程。
结 语
最后,要说明的是,《日丛》出版时间并不长,内容十分有限,其生命力与权威性,与后来的《通报》《华裔学志》(MonumentaSerica,1935—)等专业汉学刊物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一份个人创办的学术期刊,《日丛》的价值或许并不仅限于其汉学研究内容的价值。韩大伟(D.B.Honey)曾经从文献学的角度将西方古典汉学史分为三个阶段:“耶稣会士阶段”、“法国汉学学派时期”和“英美学派时期”。⑤韩大伟著,程钢译:《传统与寻真——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世界汉学》,2005年第3期,第7页。《日丛》更大的意义是,一方面它作为《丛报》“续刊”在西方这三个汉学“时期”之间的传承使命和作用:《日丛》创办期间,正值西方上一份汉学期刊《丛报》停刊十多年之后、下一份专业汉学期刊《通报》创刊前近三十年之际;不仅如此,《日丛》较完整地记录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乃至欧美的汉学界、日本学界在专业化的初级阶段的活力、特点和生成发展机制。如果对该刊订阅者或者赞助者的身份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除了有中国生活经历的这个群体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类别,就是当时欧洲的学院派汉学家、日本学家或者说是东方学家,如法国汉学家洛图尔、时圣奥古斯丁学院东方语言教授 Reinhold Rost、大英博物馆埃及与东方部门管理员Samuel Birch等,这些属于欧洲传统学术范畴中专门领域的学者,他们对中国研究的关注,正是英国汉学走向学院范式的开始。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日丛》与《丛报》的渊源,就如英美两位汉学先驱马礼逊与裨治文在广州十三行夷馆的密切关系一样,体现了美国汉学与英国汉学之同源发生关系。而《日丛》作为《丛报》之续刊,则更是脉络清晰地展现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界从“中国学”到“日本学”扩展的过程。可以说,早期英美的“汉学”之中就包含了对日本的关注和兴趣,后来的西方现代“日本学”,就正是在英美汉学发肇之际,相伴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