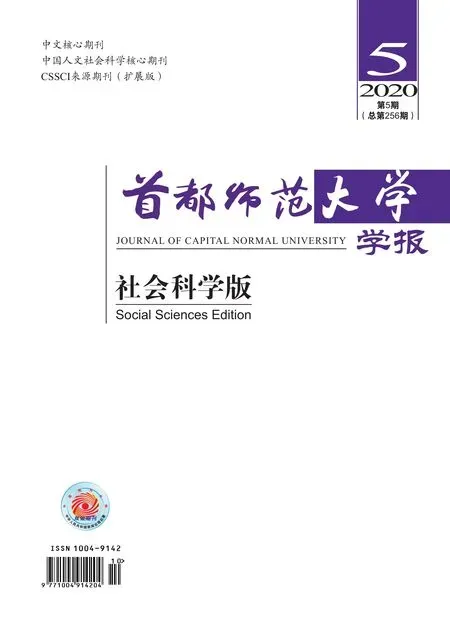古典“德性统一论”与当代情境主义
聂敏里 冯 乐
自1958年安斯科姆发表《现代道德哲学》①G.E.M.Anscombe,“Modern Moral Philosophy”,Philosophy,1958,33(124):1-19.一文始,德性伦理学的当代复兴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在这个过程中,德性伦理学不仅伴随着来自伦理学内部源源不断的批判,同时也受到了其他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巨大冲击,而这一切都使得德性伦理学在这场复兴浪潮中危机重重。其中,“德性统一性”(the unity of virtue/virtues)①“德性统一性”在其历史源头就呈现出多种样态,即多种形式的德性统一论阐释路径。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种:(1)强统一性:这种观点认为诸德性只是“德性”这一概念之下的不同名目,即认为只有一个德性,因此可称为“德性的同一性”(the identity of virtue)主张。其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以及斯多亚学派。(2)较强统一性:虽然承认存在诸种德性,但是认为如果存在一种德性,也就存在其他所有德性,而这一切都通过智慧或实践智慧(明智)得以实现。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3)弱统一性:一个人拥有某种德性就拥有其余德性,但其拥有程度是有限的,即承认主体在德性拥有上存在着不均衡性。其代表是许多现代学者阐释下的“亚里士多德”,例如尼拉·巴德沃(Neera Badwar)的“德性的有限统一性”(the limited unity of virtues)以及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的“评价性知识的统一”(the unity of evaluative know ledge)。(1)、(2)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坚持诸德性之间存在着一个使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那就是“智慧”或“实践智慧”(明智),同时(实践)智慧是具有德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命题尤为引人注目。当代心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们立基于经验观察以及付诸道德直觉来思考伦理问题,因此很难认同传统的德性统一论。相较于苏格拉底所坚持的强统一论的绝对理性主义,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理性和非理性因素都在人的行动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但是,他仍然坚持了“德性统一性”这一基本原则,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在不具有其他德性的情况下具有某一德性。试图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做非德性统一论的论证不符合古希腊的伦理传统,也有悖于古典德性理论的基本伦理精神。对“德性统一论”这一基本命题的再次阐释,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古典德性伦理学,同时也能够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德性伦理学的当代复兴。
一、“德性统一论”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现代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情境主义对德性伦理学展开猛烈攻击,尤其针对“德性统一性”的命题。他们采用描述的研究方式对伦理学问题展开讨论,立基于对人心理问题的事实性描述,并以此来批判关注人内心稳定的德性准则的传统德性伦理学,并从经验上彻底否定“德性”的存在论依据。与此同时,德性伦理学内部也开始倾向做“德性非统一”或“有限统一”的论证,并以此来捍卫德性伦理学的正确性,而这种阐释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因为在传统观点看来,“德性统一性”是古典伦理理论的一个基本定论。
情境主义将矛头对准了德性理论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其代表人物当属约翰·多里斯(John Doris)和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多里斯于1998年发表了《人、情境与德性伦理学》②J.M.Doris,“Persons,Situations,and Virtue Ethics”,Nous,1998,(32):504-530.一文。在文章中,他对德性伦理学的“品质”概念的实在性进行了质疑,通过引入“电话亭实验”③多里斯所引用的这个实验来自于伊森和莱文在1972年所做的实验。实验分了两组进行。变量是电话卡槽里是否放置了一枚一角硬币。实验工作者会在被试者打电话后安排一个人走过电话亭,并假装无意掉落文件夹中的文件,以此观察被试者是否在打电话后为其提供帮助。放置硬币组共16人,打电话后给予帮助的14人,没有提供帮助的只有2人;而未放置硬币的那一组共有25人参与试验,帮助的仅有1人,没有提供帮助的却有24人。因此,实验给出的结论是,放置了硬币的实验组的人更倾向于给予他人帮助。否认了存在着稳定不变的“品质”,即跨情境的(cross-situational)品质。一年后,哈曼发表了文章《道德哲学遭遇社会心理学:德性伦理学与基本归因谬误》④G.Harman,“Moral Philosophy Meets Social Psychology:Virtue Ethics and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uion Error”,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1999,(99):315-331.。文章指出,将行为的稳定性归因于人内在的“品质”是一种“基本归因谬误”,从而彻底否认“品质”的存在。在这之后,二人又接连发表了诸多文章⑤G.Harman,“Virtue Ethics without Character Traits”,in A.Byrne,R.Stalnaker and R.Wedgewoods,eds.,Fact and Valu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1:117-127;J.M.Doris,Lack of Character:Personality and Moral Behavi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G.Harman,“Skepticism about Character Traits”,Journal of Ethics,2009,(13):235-242;J.M.Doris,“Skepticism about Persons”,Philosophical Issues,2009,19(1):57-91;M.W.Merritt,J.M.Doris and G.Harman,“Character”,in J.M.Doris,ed.,The Moral Psychology Handboo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355-394.,对各自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和辩护。他们无疑都从心理学①情境主义同样面临着心理学内部的批评,例如人格心理学。该理论的基本论点是:人在早年中会确立一些人格特征,这些人格在人的一生中十分稳定,同时与其他变量都有关联。其中最著名的理论是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的延迟满足理论(Delayed Gratification)。参见W.Mischel,Y.Shoda,&M.L.Rodriguez,“Delay of gratification in children,”Science,1989,(244):933-938.成果中开始自己的伦理学讨论。多里斯否认了全境品质(global traits)的存在,指出传统德性统一论恰恰就在于承诺了全境品质,并认为只要从实验中否认了大多数人始终如一地做出德性行为,就能否认德性伦理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存在着稳定不变的品质。哈曼则更加极端,彻底否认“品质”的存在。
如何从由于失去“德性统一性”而招致的伦理危局中脱困,这无疑是当下德性伦理学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面对情境主义的批评,德性伦理学内部主要采取两种应对策略:一种是坚持捍卫古典德性伦理学;一种是吸收情境主义的成果,并借此修正传统的德性理论②Michael W inter and John Tauer,Virtue Theory and Social Psychology,Value Inquiry,2006,(40):73-82.。捍卫者中又有两种主要的论证策略:一种是从德性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和基本理论的阐释入手,力图澄清被情境主义所批判的德性理论并非真正的德性理论③Lorraine Besser-Jones,Social Psychology,Moral character,and Moral Fallibility,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8,76(2):310-332;Robert M.Adams,A Theory of Virtue:Excellence in Being for the G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徐向东、陈玮:《境况与美德——亚里士多德道德心理学对境况主义挑战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陈玮、徐向东:《境况主义挑战与美德伦理》,《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一种是从情境主义所采用的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或其理论自身的逻辑问题入手④Diana Fleming,The Character of Virtue:Answering the Situationist Challenge to Virtue Ethics,Ratio(new series),2006,19(1):24-42;李义天:《情境主义挑战为什么不成功?——基于现代美德伦理学立场的辨析与回应》,《哲学动态》2018年第5期。,直接对情境主义自身发起攻击。本文主要是从古典德性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入手,把“德性统一论”放在古典伦理学的整体背景中去考量,借此明晰古希腊伦理学家在论述这一话题时究竟想要塑造什么样的人,从而揭示这一伦理命题的古典特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重新回到它的源头去探寻。本文将选取其中两个最为典型的版本,《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的“德性是一”的极端(强)版本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全有或全无”的经典(较强)版本。文章第二、三部分分别论述了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统一论,第四部分则立足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阐释,回应情境主义以及德性伦理学内部关于“德性统一性”的批判和修正。
二、苏格拉底的“德性是一”
在《普罗泰戈拉篇》⑤本文的这个部分,仅涉及《普罗泰戈拉篇》的相关论述,首先是为了规避不同文本之间的调和问题;其次,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该文本也是古典“德性统一论”最为强烈(极端)的版本。学界关于苏格拉底持有何种形式的“德性统一性”主张是存在巨大争议的。第一种观点是弗拉斯托斯的“互为条件说”。参见:Gregory Vlastos,“The Unity of the Virtues in the Protagoras”,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1972,(25):415-458.弗拉斯托斯认为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案,分别为“统一说”(the unity of thesis)、“相似说”(the similarity thesis)和“互为条件说”(biconditionality thesis)。而前两种解释方案与《欧绪弗洛篇》中的论点相矛盾,因此不予采用。他坚持“互为条件说”(biconditionality thesis),认为诸德性之间以“互为条件”的方式共存。他对文本的解读显然并非是一种字面解读。他的解读实质上是认为:“单一德性”概念在苏格拉底那里只是一个抽象性名词,并不具有实存性。但是这种解释与文本有巨大冲突,也因此得不到学界的普遍认同。第二种观点是佩内的“同一说”。作为“同一性”解释方案的奠基性作品的佩内的《德性统一性》一文,恰恰是在从对弗拉斯托斯的批判入手的。参见,Terry Penner,“The Unity of Virtue”,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73,82(1):35-68.佩内在文章中主要论证了苏格拉底关于“德性是一”的命题,持有一种强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苏格拉底对“德性”的追问是一种实质性问题而非概念性问题的追问。苏格拉底是要探索德性背后的灵魂状态,各种德性行为是由一种灵魂状态引发的还是多种。他给出的答案是:“德性是一”指的是德性是一种单一的灵魂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被表述为关于善恶的知识。佩内专注于文本在字面上给人直接传达的意义。第三种观点是德弗罗的“不连贯说”。参见:Daniel T.Devereux,The Unity of the Virtues in Plato’s Pratagras and Laches,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92,101(4):765.德弗罗认为,苏格拉底在“德性统一性”问题上并不持有连贯性的立场。在他看来,《普罗泰戈拉篇》中是“同一性”立场,而在《拉凯斯篇》中则认为智慧是德性整体,其他德性是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中,苏格拉底充分阐述了“德性统一论”。但是,学界关于苏格拉底持有何种德性统一性立场存在着巨大争议。对话先后给出了三种主要的立场:德性具有部分,且各部分之间是异质的(简称为立场a1);德性具有部分,但各部分之间是同质的(立场a2);德性是单一是者,不可分(立场b)。本文认为,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持有强立场b(强德性统一论)①强统一的主要代表性人物及著作有:Terry Penner,“The Unity of Virtue”,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73,82(1):35-68;Daniel T.Devereux,The Unity of the Virtues in Plato’s Pratagras and Laches,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92,101(4):101;John M.Cooper,“The Unity of Virtue”,Social Philosophy&Policy Foundation,1998,(15):233-274.,即坚持德性是不包含部分的单一是者,各种具体德性只是单一德性的不同名称而已。
这个问题的回答以苏格拉底向普罗泰戈拉的提问始(329C-D)②《普罗泰戈拉篇》的文本参考Plato:Protagoras,trans.and notes C.C.W.Tayl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德性是一,诸德性(正义、节制、明智和虔诚)是它的部分(简称为立场a);还是,所有名称都指的是同一个东西(简称为立场b)?普罗泰戈拉选择了立场a。紧接着苏格拉底又问道,诸德性是异质(五官喻,立场a1)还是同质(金子喻,立场a2)?在普罗泰戈拉再次选择前者后,苏格拉底与之展开论辩,并最终迫使他承认作为德性不同部分的正义、虔敬、节制、智慧、勇敢都是同质的。苏格拉底先后论证了:(1)正义和虔诚是相同的(330C-331E);(2)节制和智慧是相同的(332A-333B);(3)节制和正义是相同的(333B-334C);(4)“勇敢是知识”(351B-362A)。苏格拉底用四个论证反驳了普罗泰戈拉最初的立场(a1),二人止步于立场a2。再加上苏格拉底在对话中一贯扮演着“发问者”的角色,因此在文本中,他并没有从正面提出自己的立场。对话明确否定了德性具有部分且各部分之间是异质的(a1),但是在德性具有部分且各部分之间是同质的(a2)还是德性不具有部分因而是单一的是者(b)上存在争议。立场b和立场a2虽然都承认某种程度上的德性统一性,但是二者在德性是否具有部分(即德性是否可分)上是有分歧的。
在前面的论证(第二个论证)中,苏格拉底诉诸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每个事物只有一个和它相反的事物”,即一个事物要么是其自身,要么是其相反者且相反者在数目上为一。节制和智慧都与愚蠢相反,而作为愚蠢的相反者在数目上只能是一,因而节制和智慧就是一个东西。在立场a2的“金子喻”中,作为金子这个整体中的各部分——金块,它们之间是还可以相互分离的,起到连接作用即使得各金块能够作为一个整体的金子的那个东西就是“智慧”。各金块因其“是其自身”而不是其相反者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因而可以在“金子”这个整体中作为部分而存在,同时可以在分离后各自作为区别于之前的那个“金子”的“新的金子”而存在。但是,这显然又与一开始所要论证的金块之间是同质的相矛盾。“金子喻”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各金块必须是完全相同的。各金块之间除了都是“金子”之外,它们更加是其自身,因而不是它物,不是金子的其他部分。苏格拉底正是以这种方式间接否认了立场a2。更为直接的一个论证是第四个论证。
论证四(“勇敢是知识”)是通过两个相关且极具争议的命题完成的。这两个相关命题就是:“快乐是善”以及“无人自愿作恶”。对苏格拉底来说,某人能够做A也能够做B,同时他/她也知道A好于B,但还是选择B,这是十分荒谬的③要理解这里的“荒谬”,需要诉诸快乐的可度量性来予以澄清。首先明确一个前提——快乐是(或等同于)善。A好于B,就在于A中的善(快乐)在数量上多于B中的善(快乐),这个人选择B而放弃A,就代表他放弃了数量更大的善(快乐)。这个人为何会在能够选择较多善(快乐)的情形下却选择了较少的善(快乐),关键就在于,这个人错误地判断了善(快乐)在数量上的大小。。善(快乐)在量上的可度量性,使得我们可以用统一的标准来判断善的大小,从而作出选择,因而规避了“不能自制”的问题,以此来消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之间可能的冲突。善或快乐是可以度量的,因而具有德性也就是具有关于何者为较大的善或快乐的知识。因此,苏格拉底在随后的论证中指出,勇敢就是“关于应该害怕什么不应该害怕什么的知识”(360D),得出“一切都是知识”(361B)的结论,最终将德性问题转化为知识问题。这里的知识不是对特殊对象的知识,而是对德性本质的知识,对整体善的认知。
根据上述两个论证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将德性问题转化为善知识的问题,最终认为具体德性的不同名目只是知识在不同情境下的运用。观点b这种强的统一性主张各种德性在本质上是“一”,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单一的灵魂(心灵)状态,而这种灵魂状态可以表述为关于善和恶的知识。因此,《普罗泰戈拉篇》中的“德性统一论”可以概括为是一种“单一德性的统一性或同一性”①Terry Penner,“The Unity of Virtue”,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973,82(1):35-68;John M.Cooper,“The Unity of Virtue”,Social Philosophy&Policy Foundation,1998,(15):233-274.。
相较于对苏格拉底的强德性统一论的激烈批判而言,学者们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的态度则更显温和。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蕴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而这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自身对经验抱有更多同情和关注。虽然苏格拉底的强德性统一性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某种程度的德性统一性却仍然值得追求。这些学者们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作为一个典范,并且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指出的“统一性”能够很好地回应情境主义者所提出的种种批判。
三、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全有或全无”② 本文这个部分仅就“明智”统一诸伦理德性而言,侧重道德行为发生机制的论述。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理论中其他维度的统一,例如诸德性在“正义”“大度”“智慧”之下的统一,文章暂不予以考虑。相关内容可参见刘玮:《亚里士多德论德性的四重统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亚里士多德并未像苏格拉底那样专门论述“德性统一”问题。不过,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的一段话可以表明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
德性不仅仅是合乎正确的逻各斯的,而且是与后者一起发挥作用的品质。在这些事务上,明智就是正确的逻各斯。苏格拉底因此认为德性就是逻各斯(他常说所有德性都是知识的形式)。而我们则认为,德性与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显然,离开了明智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善,离开了伦理德性也就不可能有明智。(这一见解也解答了有些人在对辩中提出的一种诘难。他们说,德性可以互相分离。他们说,一个人不可能具有所有的德性,所以,他获得了某种德性,而没有获得另一种德性。说到自然德性,这是可能的。但说到使一个人成为好人的那些德性,这就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明智的德性,他就有了所有的伦理德性)。③文中《尼各马可伦理学》选段均引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部分地方笔者据希腊文略作改动。(《尼各马可伦理学》VI.13,1144b25-1145a2)
通过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并不认同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德性是一”的观点。苏格拉底主张德性就是逻各斯,即德性就是知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德性与逻各斯(知识)一起发挥作用。再结合他在第六卷中将伦理德性划分到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不同于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德性是灵魂理性部分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德性涉及灵魂的理性和非理性部分的协同运作。人的道德行为体现的恰恰是人的灵魂的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的联动。正如库珀④John M.Cooper,“The Unity of Virtue”,Social Philosophy&Policy Foundation,1998,(5):265.指出的,苏格拉底所坚持的是单一德性的统一(the unity of virtue),而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则是诸德性的统一(the unity of virtues)。对前者而言,“德性统一性”意味着德性的本质是人的灵魂的一种单一状态。后者则强调众多德性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集群(cluster),因此德性的本质是灵魂的一种混合状态。紧接着,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区分了两种德性,即自然德性和严格意义上的德性,并指出自然德性无须统一,而严格意义上的德性却是统一的。最后提出了“一个人如果有了明智德性,他就有了所有的伦理德性”,而这一说法恰恰标识了德性统一论最为经典的论述,即“德性全有或全无”⑤参见John M.Cooper,“The Unity of Virtue”,Social Philosophy&Policy Foundation,1998,(15):233,265.。换句话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德性不具备明智德性,同时也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统一性,而严格意义上的德性因为具备了明智,所以具备了“德性统一性”。我们先来澄清“明智”在他的伦理学中的特殊作用,以此来说明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的统一究竟指的是什么,最后再回过头来阐述亚里士多德为何要区分出两种意义上的德性(自然德性和严格意义上的德性),并据此回应情境主义的批判。
实现德性的全有是因为“明智”这一特殊德性,也因此,学者们①Neera K.Badhwar,“The Limited Unity of Virtue”,Nous,1996,(30):306-329;Susan Wolf,“Moral Psychology and the Unity of the Virtues”,Ratio,2007,20(2):145-167;Linda Trinkaus Zagzebski,Virtues of the Mind: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Virtue and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Know 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37-139.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统一性称为明智(实践智慧)的统一性。“明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何以能够从“明智统一性”推出“德性统一性”?明智(,或实践智慧)是西方伦理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更是最早对其进行系统性论述的思想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亚里士多德对其进行了集中而系统的论述。他将德性划分为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同时又进一步将理智德性划分为理论理智德性和实践理智德性,即智慧()和明智(,二者分属于灵魂理性部分中的知识性部分()和推理性部分()。智慧是努斯(和科学()的结合,与永恒不变的事物相关;明智则与可变的事物,尤其是与人的事务相关。明智作为灵魂的推理性部分的德性具有什么特点?
明智的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考虑对于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不过,这不是指在某个具体方面的善和有益,例如对他的健康或强壮有利,而是指对于一种好生活总体上有益。(《尼各马可伦理学》VI.5,1140a26-29)
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尼各马可伦理学》VI.5,1140b6,20)
在灵魂的两个有逻各斯的部分中,明智必定是一个部分的德性。就是说,它是那个构成意见的部分的德性。因为,意见是同可变的事物相关的,明智也是这样。(《尼各马可伦理学》VI.5,1140b25-27)
根据第六卷第五章给出的关于明智以及明智的人的简要说明,我们可以看出明智是:(1)一种品质;(2)一种求真的实践品质;(3)一种灵魂的推理性部分的求真的实践品质;并且,明智的人考虑的是(4)对一种好生活总体上善的事。正如厄文指出的:“明智概念具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整体性特征,拥有明智就意味着拥有了一种整体性的知识”。②参见T.H.Irwin,Disunity in the Aristotelian Virtues,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1988,Supplementary Volume:61-78.因此,明智就是一种灵魂推理性部分的拥有关于好生活整体知识的、合乎理性的、求真的实践品质。
那么,明智和伦理德性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什么作为理智德性之一的明智可以成为伦理德性统一的关键性因素?在第六卷第十二章,亚里士多德向我们抛出了两个有关明智和伦理德性关系的难题(1143b20-34):明智考虑那些增进人的幸福的事物(1143b20),(1)仅仅知道德性并不能使我们更有德性,明智如果只是关于伦理德性的知识,它便不能使我们更有德性,因而于幸福没有助益;(2)如果明智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涉及如何成为好人(何以有德性)的技艺,那么明智对有德性的人和没有德性的人都无用。有德性的人因为已经是好人所以不再需要明智这门教人成为好人的技艺,没有德性的人也同样不需要,因为他们可以不用自己有德性而只是出于听从有德性的人的教导而行事,因此对有德性和没有德性的人来说,似乎都不需要明智。
这两个难题最后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好人(拥有伦理德性的人)和尚未成为好人的人为什么还需要明智这种理智德性?亚里士多德给出的回答是(1144a2-9):明智(1)即使不产生什么结果,它因自身即值得欲求;(2)产生结果——幸福;(3)与伦理德性都取决于我们自身(在我们能力之内),它们一起完善着人的活动,从亚里士多德自己抛出的两个问题以及随后给出的解答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智同时涉及“知”和“行”两个方面,更具体来说,恰恰是明智这种实践理智德性沟通了“知”与“行”以及“理[性]”与“欲[求]”。理性与欲求的二分在明智这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弥合。关于这一点,将在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伦理]德性与明智关系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说明。
在这一部分,亚里士多德两次①《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其他类似的表述:“愿望更多地是对于目的的,而选择则更多地是对于手段的”(1111b26-28);“我们所考虑的不是目的,而是朝向目的实现的东西”(1112b10-11);“所考虑的东西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1113a1);“使得我们的目的正确的是德性。而使得我们去作为实现一特定目的而适合于去做的那些事情的却不是德性”(1144a20)。提到“德性使我们确定目的,明智使我们采取实现目的的正确手段()”(《尼各马可伦理学》VI.12,1144a7-9;VI.13,1145a5-7)。对目的的思考是认识性思维的功能,明智不思考、不设定目的。但是,明智也不是工具性的思维,它涉及一般性伦理知识和特殊的(来自经验)知识。
明智不仅仅同普遍的东西相关,也要考虑具体的东西。因为,明智是实践性的,而实践就是要处理具体的事情。因此,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比如,如果一个人知道白肉容易消化、有益健康,却不知道何为白肉,他就还不如一个只知道鸡肉容易消化、有益健康的人更能有益其健康。既然明智是实践性的,我们就需要这两种知识,尤其是需要后一种知识。不过,这种知识,还是要有一种功能的能力来指导它。(《尼各马可伦理学》VI.7,1141b13-23)
这段话一直反复强调明智处理具体的事情。虽然亚里士多德指出,明智需要普遍知识和具体知识这两种知识,但又明确提出,尤其需要具体知识。这段文本的最后一句话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它表明:“亚里士多德想要纠正由于前面的叙述而给人的一种印象,即明智不需要普遍的知识或普遍知识的指导,表明他并不认为普遍的东西对明智的人不重要。”②参见:T.H.Irwin,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85:245.正如他在上文(《尼各马可伦理学》VI.5,1140a26-29,1140b19-20)中指出的,明智关乎一个人对“生活得好”的整体认识,是一种同人的善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统一性论仍然坚持知识的重要作用。明智需要普遍和具体知识,恰恰在于它是将普遍应用于具体,是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明智需要或关涉知识,但它本身并不是知识,而是另一种直接地把握真的能力。
显然,明智不是科学。因为,如已说明的(1141b14-22),明智是同具体的东西相关的,因为实践都是具体的。明智是努斯的相反者()。因为,努斯相关于始点,对这些始点是讲不出逻各斯来的。明智则相关于具体的事情,这些具体的东西是感觉而不是科学的对象。不过这不是说那些具体感觉,而是像我们在判断出眼前的一个图形是三角形时的那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中也有一个停止点。然而这种感觉更靠近的是感觉而不是明智,尽管它是不同于具体感觉的另一种感觉。(《尼各马可伦理学》VI.8,1142a23-31)
明智不是科学在于:首先,明智不是知识,不是关于本原的证明知识;其次,明智虽然也关于普遍,但是更加与具体事物相关;最后,明智是直接地把握对象的能力,而非科学式地间接把握。关于第三点的论证,亚里士多德主要诉诸明智与努斯的关系来予以说明。明智与努斯是相反者。在他的理论中,相反者是逻辑上同范畴的东西。作为同一范畴的东西,二者都是一种直接把握对象的能力,区别于科学的间接把握。“相反”则体现在,努斯是对最高本原的把握,而明智则是对具体事物的把握。①参见:“”。努斯相关于始点,明智相关于思考的终点(具体事物),所以是相反者。两个相反者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在逻辑上同范畴的。亚里士多德在此处是说,明智同努斯是同范畴的(尽管相反),两者都与科学(作为证明的即间接的把握真的能力)不同,它们都是直接地把握对象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9页;“正像理智是对最高本原的一种直接把握的能力,明智却恰相对立,是对这样一种等级序列中的最低端的东西的一种把握能力,从而,就此而言,它多少有些类似于感觉。但是,很显然,就它并不是像感觉那样对具体个别的东西的直接认识,而是要经过一番具体地筹划和计算而言,它又和具体的感觉不同。从而,它便是将普遍具体地运用于个别,以在具体事物上实现总体生活目的的特殊理智德性,它所起到的正是在思维上沟通一般和特殊、普遍和具体、理智和欲望、认识和实践的特殊中介功能 。”聂敏里:《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世界哲学》2015年第1期。因此,可以看出,明智就是将普遍应用于具体,处理具体事务时直接把握真的能力。
明智与伦理德性的互惠关系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统一的依据,幸福是德性统一的最终目标。亚里士多德借助“明智”沟通理性与欲求、普遍与具体、认识与实践的中介作用,完成了对苏格拉底德性强统一(即德性就是知识)的改进,确立了在明智这一理智德性统御下的诸德性的全有或全无。拥有明智就意味着拥有了一种关于好生活的整全知识,更加意味着知道做什么、如何做才能实现“好生活”。
四、对“新挑战”的回应
在情境主义者们看来,传统德性伦理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就是“德性的统一性和实在性”。统一性所坚持的德性“全有或全无”认为,德性是一个整体,具有德性的人就是一个所有德性的拥有者,从而否认了人在现实的伦理生活中具有某种德性而不具有其他德性。实在性指的是,德性作为一种品质,其特征就是稳定、确定、不变。一个具有德性(或品质)的人能够在生活中始终如一地做出合德性的行为,可以维持较长时间内的行为一致性。更进一步,他们认为,德性伦理学所宣称的德性统一性和实在性向我们预设了行为者的心理机制(或灵魂结构)与行为的因果关系。因此,只要在实验中发现受试者们缺乏某一或某些德性,或者在不同的情境下做出不同行为,那么便可以从根本上否认德性伦理学家向我们所许诺的强健“品质”。他们认为,德性伦理学构建了一个没有经验根据的“品质”概念。从本质上来说,情境主义就是要反对对道德进行形而上学的构建,反对向人们作出人具有固定本质的德性许诺。
对此我们的回应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认为现实中大多数人能够实现德性的全有,即成为拥有真正德性的人。相反,他正是知道通向德性的道路是一条十分艰辛的道路,更加经验到大多数普通人并不能够真正地拥有德性,因而提出了“自然德性()”和“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的划分。
然而,如果自然的品质上加上了努斯,它们就使得行为完善,原来类似德性的品质也就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德性。因此,正如在形成意见的方面灵魂有聪明与明智两个部分,在道德的方面也有两个部分:自然的德性与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离开了明智就不可能产生。所以有些人就认为,所有的德性都是明智的形式。苏格拉底的探索部分是对的,尽管有的地方是错的。他认为所有德性都是明智的形式是错的。但他说离开了明智所有的德性就无法存在却是对的。(《尼各马可伦理学》VI.13,1144b11-20)
这段文本向我们传达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在德性统一性上基本观点的异同。在这一章对理智德性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转变了在第二卷中对苏格拉底的全然批判态度①在第二卷论及“德性如何获得”的问题时,亚里士多德隐含性地否认了苏格拉底的主张,“说到有德性,知则没那么要紧”(1105b4),“但是大多数人不是去这样做,而是满足于空谈”(1105b12)。亚里士多德在此处并未直接指出这是苏格拉底的观点,使用的是“大多数人”。“满足于空谈”(又翻译作在中寻求庇护),出自《斐多》99E。再结合第六卷对灵魂的二分和对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的灵魂归属问题的说明,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1)伦理德性不仅仅是知识问题,还涉及人的行为;(2)伦理德性也不仅仅关乎灵魂的理性部分,同样涉及非理性部分,而且伦理德性本身就是属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部分接受了苏格拉底的观点。他指出,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命题既正确又错误,“他认为所有德性都是明智的形式是错的。但他说离开明智所有的德性就无法存在却是对的”(1144b19-20)。“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离开了明智就不可能产生”(1144b16)。亚里士多德用明智(或智慧)统合诸德性,而这一点恰恰也是苏格拉底所持有的关于德性的基本观点②《美诺篇》88C-D。,从而可以将他伦理学中的在“明智”之下的德性统一性看作是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继承和发展③参见:John M.Cooper,“The Unity of Virtue”,Social Philosophy&Policy Foundation,1998,(15):266;T.H.Irwin,Disunity in the Aristotelian Virtues,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1988,Supp lementary Volume:61—78,特别是66—72页。。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自然德性和严格意义上德性的划分。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德性离开了明智就不可能产生(1144b16,20)。德性[作为品质]与逻各斯[理智知识]一起发挥作用,离开了明智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善,离开了伦理德性也不可能有明智。亚里士多德划分了两种德性,并指出,二者的核心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努斯。更具体来说,没有努斯的自然德性:(1)也存在于儿童和野兽(1144b9);(2)既能用于恶的行为,也能用于善的行为(1129a11-17;1144b10-11);(3)通常是有害的(1144b10;Rhet.1389a17-24,1389a25-28)。依据他在第二卷第四章中所提出的“德性行为”需满足的三个条件④首先,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其次,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那行为自身故而选择它的。第三,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尼各马可伦理学》II.4,1105a29-b2),可以归纳出另外三点不同出于自然德性的行为;(4)缺乏对行为的知识;(5)并非经过选择且不是因事物自身故;(6)不是出于一种稳定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然德性和严格意义上的德性,前者不涉及知识,后者则相反。由于拥有知识,严格意义上的德性能够使人获得对真的坚定和稳定的理解,并促使人始终如一地作出合德性的行为。
与这两种德性相对应的是两种德性的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隐含性地区分了两种德性的人:真正具有德性的人和一个尚未具有德性但是朝向德性的人那样努力去做的人。我们阅读《尼各马可伦理学》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对第二种德性的人的描述丝毫不亚于第一种人。对尚未具有德性的人而言,他朝向好的方向发展,即模仿真正德性的人的行为去做事。在他的伦理学中,这个模仿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自然。首先,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尼各马可伦理学》II.1,1103a24-26)自然给我们提供了获得德性的基础,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我们并不能最终获得德性。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对人而言的“好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通过习惯化,即通过运用逻各斯而逐渐获得德性。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了真正德性的获得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却仍然值得我们追求。真正德性的人是普通人做人、做事的范式。普通人通过模仿⑤谈到这种模仿,很自然让人联想到柏拉图所提出的事物对理念的分有和模仿。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每个理念在它的类别里都是最完善的。所有的东西都达不到它的完善性,但是都在趋向于那个完善性。达到了就是最好的,从而彻底实现了自身的完善性。现象世界都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现象世界也都是在不断模仿理念世界从而变得更好一点。真正德性的人行事,在这个过程中让灵魂的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相和谐,并最终使德性趋于完善。
因此,我们给出的答案是:情境主义的经验实验并不能表明根本上不存在德性(或品质),最多只是表明大多数普通人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德性,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理论也并未排除德性只有少数人才能具有的可能。正如安娜斯所言:“情境主义者们攻击了一个错误的靶子。他们误解了他们所攻击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或经典的)德性伦理学(的德性概念)。”①Julia Annas,“Virtue Ethics and Social Psychology”,A Priori,2003,(2):27.但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德性和严格德性的划分以及真正德性只能是少数人才能具有的论断却导致了一个难以摆脱的诘难,那就是:能够真正拥有严格德性的人是世所罕见的,从而这种伦理学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伦理学。当代许多德性伦理学家显然不能接受这种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描述为精英主义的企图,同时更为了有力回击心理学家以及情境主义者所提出的批判,他们试图论证亚里士多德所坚持的并非强统一论,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弱统一论。这也是情境主义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德性伦理学内部的分化。一部分学者开始对“德性统一论”做弱化的处理,以此缓解其中的紧张关系。虽然承认德性可以是有程度的,能够缓解和应对情境主义者上述的指控,但是德性统一论所蕴含的恰恰是对德性具有程度的否定。弱统一论的解读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有关文本向我们传达的意蕴,更加不符合古希腊传统的伦理精神。
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给出的具有德性的三个要求:(1)知道;(2)因事物自身故;(3)稳定不变的状态。情境主义的主要攻击点即为“要求(3)”,德性是一种稳定不变的状态。多里斯和哈曼指出,当代社会心理学证明了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是偶然性质的情境(外在环境)而非稳定性质的品格。他们引用米尔格拉姆实验②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该实验始于1963年史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发表的《服从的行为研究》(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一文。,否定了强健品质的存在,因而进一步否定了“德性”的存在,并且,就我们的日常观察而言,一个人似乎只在某个或某些领域具有德性或智慧,而不是在所有领域。较为常见的例子是,一个博学多识的教授,在许多普通人都驾轻就熟的琐事上,笨拙不堪;一个在战场上极为勇敢的士兵,却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基本的同情心,等等。基于此,沃尔夫、巴德沃和赫斯特豪斯都通过否认德性强统一性的主张来缓解情境主义所提出的批评。在沃尔夫看来,德性在知识上的统一性指的就是,德性来自我们对“好生活”这一概念及相关构成要素的概念分析。她并不认同拥有一种德性实际上就具有所有其他德性,因此大大弱化了“德性统一性”。巴德沃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明智(实践智慧)包涵一般性的伦理知识以及关于相关情境的特殊知识且尤其关乎特殊知识这一点,并据此认为,有德性的人就是在具有经验的领域中,具有相应的敏感性,能够习惯性地做出德性行为,因而指出,德性不具有跨领域的统一性,而只能满足在特定领域中的统一。赫斯特豪斯的“弱多元德性统一性”则认为,行为主体可以在诸德性的拥有程度上存在差异,拥有某种德性,并不需要完全地拥有其他德性。③Rosalind Hursthouse,On virtue Eth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无论是苏格拉底的诸德性只是单一德性的不同名称的极端统一论版本,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诸德性的全有或全无的经典(较强)版本,其核心就在于向我们揭示了德性本质或者说人的本质。二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将德性问题转化为知识问题,最终将人规定为理性的存在物。古典目的论认为万物都有一个最终目的(最完满价值),这是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所共同坚持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就在于实现这个最终目的,这就是事物的最好状态。因而存在着最高善,对人而言这种善就是幸福(《尼各马可伦理学》1094a19-22,1097a26-b1,1098a7-18)。高一层级的善事物包含着低层级的善事物,但对于低层级的善事物来说,高层级善事物作为目的存在其中。有德性的人,对诸种善事物之间的价值排序有清楚的认知。他们知道,在不同的情境中,哪种善事物更有利于最终善的实现,并具有对“如何生活得好”的总体认识。剥离了目的的“德性”概念对于古典德性理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始终围绕目的的“德性”,同样不能脱离包含经验性因素在内的“适度(中道)”概念。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德性仅仅拥有特定生活领域的统一性。
结 语
情境主义针对传统德性伦理理论所坚持的“品质是决定行为的唯一要素”基本观点的批判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果因此就提出,情境是决定行为的要素,行为主体在道德行为过程中尤为软弱无力,那无疑也是矫枉过正。当代德性伦理学研究在回应经验实证的心理科学的挑战的时候,应该在坚守自己作为一门思辨科学的独特性的同时,关注该哲学理论所提出的历史背景。不同理论所提出的历史时代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情境主义理解为环境决定论,应该看到它背后立足的“人的有限性”的现代特质,同时也应该看到西方古典伦理理论所提出的古希腊城邦的历史背景。传统“德性统一论”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德性不能与德性处于冲突,否则我们似乎没办法要求一个人始终如一地做出德性行为。古代伦理理论无法承担“自由”带来的彻底变动不居的世界,他们所要追求的是一个不动的、完满的、永恒的世界。如果说,立基于当代心理学成果的情境主义是通过对人和人的心灵的诸多细节的考察来获得对人的道德的整体把握,那么传统的德性理论则是从人的本质这一根本性、总体性问题入手,从而寻求对人和人的心灵(灵魂)的系统性理解。古希腊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追问是关于人整体生活的伦理探寻。德性统一性背后所蕴含的德性的单一性和实在性,正是为了确立最终善的普遍性。只有完满的“一”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因为,只有自然的必然性才能确保普遍的必然性,只有不变的自然规律才能给现实存在的社会以合理性。抛弃“德性统一性”从而寻求德性伦理学的新出路,恰恰是对德性伦理学的最大背离。
苏格拉底通过“德性即知识”,将德性问题转化为知识问题,从而简化了伦理问题的复杂性。亚里士多德从基于经验的伦理方法出发,修正了苏格拉底式的极端德性统一性,认为德性涉及灵魂的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但是仍然坚持了德性统一论的强版本,“德性全有或全无”。他通过形而上学的完善性概念确立了幸福(最终目的)的本体论地位。古希腊思想蕴含了某种形式的德性统一论。人皆求善,并期望实现最大善——幸福。传统的作为目的的善的退场,使得这种具有普遍性蕴意的“善”概念变得很难再被我们现代人所理解。我们今天在诉说“善”和“德性”概念的时候似乎不再抱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善”更多是能够使我们获得当下满足的事物,而非具有永恒的、唯一的命意。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执着于追求某种或某些令我们感到即时快乐的“善”。古典目的论的伦理精神就在于,人皆求善,同时自身是善的事物因其自身就值得追求,而一旦最高善确立了,我们也就确定了应该如何行动,或者说什么样的行为是有德性的、正确的。因此,无需追问我们应当做出何种行为的问题,而只要我们成为有德性的人就会自然(出于本性)地做出有德性的行为。古典的德性理论是否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最佳出路,暂且存而不论。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当今许多人确实缺少这样一种对“好生活”和“善”概念的整体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