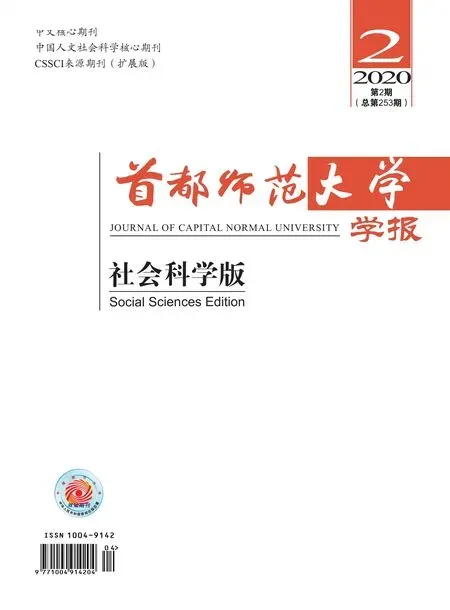关于唐克新的小说《沙桂英》
——兼论“社会主义新人”“中间人物”的写作及其限度
谢保杰
一、《沙桂英》的写作与发表
在十七年时期上海的工人写作中,唐克新是与胡万春、费礼文齐名的工人作家,他们一起被称为上海工人写作的“三驾马车”。作为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唐克新从1953年发表成名作《车间里的春天》开始,在整个十七年时期,他发表了40多篇小说,其中收编成小说集出版的就有《车间里的春天》《种子》《我的师傅》《铁链也缚不住的人》等。他早期的作品倾向于用朴素的笔触描写新生活、新事物,到20世纪50年代末,其创作手法有所转变,开始专注于写人物,创造鲜明的艺术形象。在上海工人写作中,胡万春曾经是钢铁厂的工人,他的作品擅长描写钢铁工人;费礼文是机器厂工人,他的创作钟情于描写机器厂工人;而唐克新则擅长塑造纺织女工形象,这与他解放后在纺织厂工作,经常接触纺织女工有很大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唐克新写了一系列纺织女工,如黄宝妹(《黄宝妹》1958年)、王小妹(《种子》1960年)、史大妈(《主人》1960年)、俞爱珍(《旗手》1961年)、沙桂英(《沙桂英》1962年)等。这些不同年龄、性格各异的纺织女工,她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所表现出的不平凡的思想、行动是唐克新写作的关注点。唐克新曾说:“对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我会予以特别的注意,而且对他们的一举一动特别敏感,特别容易吸收。在生活中我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他,……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去美化他,把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同他的思想品格相一致的最美好的东西灌注到他的血液里。”①左泥:《润物细无声——忆魏金枝先生》,《编辑之友》1985年第3期。唐克新善于从生活出发,用清新淡远的笔调探索这些平凡而又普通人物的心灵世界,在十七年时期的工人写作中呈现出独特的风格。
《沙桂英》最初发表于1962年2月号的《上海文学》,是唐克新的代表作,代表着唐克新在创作上“新的探索与突破”。在小说中,沙桂英是一个略带稚气的姑娘,她已经连续十个月不出次布,不久就要当选为全市劳动模范,可是她居然心甘情愿地和出次布最多的新嫂子换车,将自己的好车换成老爷车。对于沙桂英来说,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不出次布,搞好生产。她的这种让人看来有点“傻”的行为,引起了工区副工长邵顺宝的反对。经过了一番行动的示范和思想的较量,沙桂英终于说服了邵顺宝,制服了老爷车,减少了次布。小说还有一个主题就是邵顺宝在与沙桂英的接触中,对这个带有“傻劲”的姑娘萌生了爱情。小说最后,沙桂英没有评上劳模,但是她的大幅照片依然和几个劳模并列在一起,并且登上了本市的报纸。
这篇小说在发表之前,原稿就在评论家之间传阅过,唐克新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根据评论家的建议与意见进行过一些修改与调整。据当时《上海文学》编辑左泥回忆:“《沙桂英》在发表以前即有争论。稿子在编辑部外面曾有不少人看过,多数同志认为沙桂英作为一个劳动模范,思想行动如无源之水,本身不完美;而作为她的对立面的车间主任邵顺宝,他是党员,不应该写‘低’,这有损党的形象,因此都主张修改。”①
这样一个有“缺陷”的小说,后来又为什么能发表呢?负责编辑部工作的《上海文学》副主编魏金枝②魏金枝(1900—1972),浙江嵊县人,现代作家,编辑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艺月报》编委、《上海文学》副主编、《收获》副主编。作为文艺刊物的组织和领导者,为培养文学新人和上海工人作者队伍做出很大的贡献。工人作者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人的创作都得到过他的辅导和帮助。20世纪60年代,在魏金枝的榜样示范下,上海作协曾举办过“老作家带徒弟”的活动,帮助新人作者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显示了他的“不适时宜”。在《上海文学》编辑部讨论这部稿子时,“几乎没有人说不需要修改即可发表”,编辑左泥也认为邵顺宝这个人物写得太“低”了。可是魏金枝“还是力排众议,把稿子在当期的刊物上作为带头篇发表了,并且还写了《为〈沙桂英〉辩护》的文章”③左泥:《润物细无声——忆魏金枝先生》,《编辑之友》1985年第3期。。
小说发表以后,所引发的争论④主要的评论文章除了魏金枝的《为〈沙桂英〉辩护》(《文艺报》1962年7月号)外,还有欧阳文彬的《跨上一个新的阶梯——谈唐克新的短篇小说》(《文艺报》1962年4月号)、晓立(李子云)的《新的探索 新的突破——谈唐克新的〈沙桂英〉》(《上海文学》1962年第4期)、刘金的《议论〈沙桂英〉的一二问题》(《上海文学》1962年第7期)、林志浩《拭目看新人——“沙桂英的性格”辩》(《上海文学》1962年第7期)、姚文元的《蕴藏着无穷潜力的人——谈唐克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上海文学》1962年第9期)、沐阳(谢永旺)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文艺报》1962年9月号)、黎之(李曙光)的《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文艺报》1962年12月号)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沙桂英人物形象的塑造,二是邵顺宝人物形象的塑造。在1962年相对宽松的语境下,争论尽管是在学理层面展开,但是由于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涉及社会主义文艺相关的立场、原则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沙桂英》这篇小说所引起的争论在当时是引入注目的。
二、沙桂英:“社会主义新人”的写作及其限度
《沙桂英》发表以后,评论界给出的最初感觉是“耳目一新”。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这一印象主要来自于小说主人公沙桂英的人物形象。有的评论家认为沙桂英给当时的文学画廊“增加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形象”①晓立:《新的探索 新的突破——谈唐克新的〈沙桂英〉》,《上海文学》1962年第4期。。小说中,沙桂英是一个纱厂的青年女工,她来自于革命家庭,在新的社会环境里成长,没有受到任何旧思想、旧习气的沾染。她性格倔强、泼辣,却心地纯洁犹如一湖清水;出现在周围人面前时,“她刚得使人害怕,却又柔得让人可爱”。她在工作上敢于担当,积极上进。为了集体的利益,她和新嫂子调车,她和邵顺宝的庸俗思想进行斗争,她雷厉风行地修车,都表现了不同寻常的个性。最后,她通过自己的行动征服了所有的人。这样一个有点不善言辞的姑娘,她身上散发出特有的魅力,就连和她斗气的新嫂子也非常佩服她:“她觉得这小姑娘身上似乎有一股奇特的力量,她不但能驾驭那些机器,而且也驾驭了那些人,她好像是《西游记》中的唐僧,会念紧箍咒似的。”
小说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生产的主题,一个是爱情的主题,沙桂英的形象就在这两个主题所设置的矛盾中展开。在生产上争取先进、争取当劳模,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劳动者来说,是一种无上光荣的行为,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不仅仅是工人小说,当时很多小说家都涉及这一主题。但是,在小说《沙桂英》中,沙桂英争取的却是“不当劳模”,这就有点让人惊奇了。在小说中,推动情节发展的正是副工长邵顺宝的“惊奇”。邵顺宝知道沙桂英与新嫂子的调车行为会损害工区的荣誉和他作为副工长的荣誉,为了说服沙桂英收回成命,邵顺宝与沙桂英进行了行动与思想上的较量,正是这种较量衬托出沙桂英的思想高度。小说指涉的是生产,但其意义远超出生产问题之外,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在较量。沙桂英身上没有一点个人主义的影子,她“不当劳模”为的是集体的荣誉和利益,这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合拍的,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只有像邵顺宝那样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才会感到“惊奇”与不理解。
另一方面,小说还触及当时比较稀缺的爱情领域,这在恋爱、婚姻与家庭的功能越来越弱化的十七年小说创作中难能可贵。邵顺宝在与沙桂英的工作接触与思想较量中,逐渐地爱上了这个一身“傻劲”的姑娘。邵顺宝对沙桂英的爱一方面源于被沙桂英高尚的气质所吸引,另一方面也因为沙桂英是“劳模”这样一个非常功利主义的择偶观。但是沙桂英后来拒绝了邵顺宝的爱情。小说隐含着那个时代的爱情观,就是共同的生活理想与道德标准是爱情的基础。这一爱情观在胡万春的工人小说《青春》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技术科绘图员小朱正在和工人干部、先进工作者李小刚谈恋爱。小朱人长得漂亮,专爱打扮,“走起路来总是轻飘飘的”。她和李小刚接近,有自己的“美妙想法”,她想嫁一个劳动模范,这样跟他在一起,自己也体面起来。但是李小刚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陪小朱,小朱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李小刚不会生活。新来的材料员阿英出现了,她虽然对业务还不熟悉,但是追求上进,“有着饱满的工作热情”。在一次抢修水泵的工作中,阿英与李小刚互相萌生了爱意。很显然,在小说中,小朱和李小刚在生活理想和幸福观上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他们分手的原因。在《沙桂英》中,沙桂英最后拒绝了邵顺宝的爱情,沙桂英拒绝的不仅仅是邵顺宝这个人,还意味着她拒绝了与那个时代、与那个时代理想、与革命格格不入的一种庸俗的人生观。
在唐克新的写作中,沙桂英的人物形象不是孤立的,而是延续了他一贯关注纺织女工的写作偏爱。与以前小说中的人物王小妹(《种子》)、俞桂珍(《旗手》)不同的是,沙桂英的视野、境界要开阔得多,她所经历的矛盾与斗争也比王小妹、俞爱珍要尖锐和复杂。小说把沙桂英放在邵顺宝、新嫂子等带有落后思想意识的人中间去接受考验,从生产上、爱情的纠葛上让她的个性逐渐明晰起来。与当时很多概念化的人物形象相比,沙桂英这个人物形象给当时的读者与评论界留下的印象显然要亲切、“新鲜”得多。就是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
在一个摒弃个人欲望和私心杂念的时代,沙桂英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她身上流露出来的简单和清纯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质。这是一个在新的生活理想与道德标准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看上去普普通通,但精神世界高尚;虽然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但对社会主义集体事业无限热爱,敢于同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个人主义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同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梁生宝一样,沙桂英也同属于“社会主义新人”行列,只是她出现在工业题材领域。在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中,他们都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理想人物,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和道德的内容,虽然沙桂英与梁生宝相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略显单薄。小说的最后,沙桂英为了帮助邵顺宝成长,送给他两本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本是《不死的王孝和》。沙桂英坚信:“书是能够帮助人看清自己的。”这两本书正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成长寓言。在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中,无论是农村题材还是工业题材,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新人”,都或多或少具有一种保尔·柯察金式共产主义“圣徒”的气质。为了实现一个集体性的目标,不断克服个人性的欲望,从而达到一种完美的近似宗教性的人生境界。沙桂英身上没有个人主义的影子,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集体的荣誉和理想,而邵顺宝身上更多的是个人的一己私利。时代标举沙桂英而摒弃邵顺宝,是因为沙桂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正是力图依靠这样“圣徒”式的“新人”以最终完成一个集体性的目标。在写作《沙桂英》之前,唐克新曾以散文特写的形式写作了《黄宝妹》,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上海纺织工业著名劳动模范黄宝妹①黄宝妹,1931年出生,13岁进厂工作,上海国棉十七厂纺织工人,上海纺织系统人人尽知的技术革新能手。曾先后7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和全国劳模;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8年,导演谢晋以真人真事为题材创作电影《黄宝妹》,37岁的黄宝妹在影片中饰演自己,使黄宝妹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的形象。沙桂英的形象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黄宝妹。和沙桂英一样,黄宝妹同样是纺织女工,同样是劳动模范,同样为着集体的目标而从不计较个人的私利。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新人”与想象中“社会主义新人”交相辉映,共同书写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尽管沙桂英作为“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价值理想,但是,就沙桂英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当时的批评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沙桂英作为一个劳动模范,“思想行动如无源之水”,作品没有写出她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根源,有简单化之嫌。如晓立(李子云)所说:“在几个关键的时机,作者没有发挥自己的向纵深挖掘的特长,深入下去,因而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成长历程不够分明,人物精神异彩也没有能够充分放射出来。”②晓立:《新的探索新的突破——谈唐克新的〈沙桂英〉》,《上海文学》1962年第4期。刘金认为,小说里的沙桂英挺身而出批评新嫂子,和新嫂子调车,乃至调车以后受到邵顺宝的劝说、批评,都被描写得无动于衷,“什么也没有想”,这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在沙桂英的性格塑造方面,刘金认为:“作者应该借助于艺术形象或心理描写,把读者需要她说而她偏不肯说的思想脉络,向读者展示出来。”③刘金:《议论〈沙桂英〉的一二问题》,《上海文学》1962年第7期。同样,在沙桂英之前,梁生宝的“新人”形象也遭遇到类似质疑。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新人”,是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是时代最先进的人物,他的出现被认为是《创业史》最大的成就。然而,在一片赞扬声中,目光敏锐的严家炎则认为:“梁生宝在作品中诚然思想上最先进。但是,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这是因为“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作品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形象的完成”。④严家炎:《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就十七年的小说创作来说,作为艺术形象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创作上的不成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为一个新的历史主体,“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为实现集体目标的依赖对象,同时在他们身上,也负荷着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苛刻的政治要求和道德内容。就其写作而言,其实面临一种悖论,他们既要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面貌,又最终必须以集体的形态出现。实际上,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目标而言,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写作并没有形成一种更成功的经验。“因为在‘作为典型的个体’和‘阶级主体’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悖论性的困境。如若小说过分地将英雄人物表现为一个个体,就很难不把人物从阶级群体和环境中特别地突出出来,而当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容易失落其‘阶级性’而陷入某种‘个人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的嫌疑”①贺桂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贺桂梅的分析展现了在社会主义写作中,“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的困境。这一困境唐克新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小说集《种子》后记中,他曾经说:“这十年来,我写的不多,自己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却不算少。”②唐克新:《种子》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317页。他为了克服困境所做的努力就是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补充甚至改写”。由于“主题与结构的约束”,他的“修改”与“改写”谈不上成功,甚至他自己“也仍然感到有许多不满意之处”。在十七年时期,唐克新在写作中所经历的困境很多作家都遭遇过,他们为克服困境所作的种种努力我们今天依然能从作品中感觉到。就“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而言,十七年社会主义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
三、邵顺宝:“中间人物”及其相关争论
小说中另一个人物邵顺宝,是沙桂英所在车间的副工长,是沙桂英的领导,是党员。作为沙桂英的对立面,他的思想境界不高。当时的评论界认为党的干部应该十全十美,不应该写“低”,都主张邵顺宝这个人物形象应该写得高大、完美,具有充分的工人阶级意识。针对这种声音,魏金枝认为:主张把邵顺宝“抬高一点”的观点,不但否定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和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在写作上也模糊了沙桂英与邵顺宝两人之间的“是非之分”和“真伪之分”。魏金枝从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出发,为邵顺宝辩护:“凡是赞成现实主义的作家和评论家,凡是承认矛盾永远存在的人,凡是知道正反面人物都可以作为教材的人,照理都不应该再发生人物高不高的疑问。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有些同志,总是从主观出发,希望在作品中不出现精神状态低下的人物,只希望出现英雄。这种心意固然是好的,但也确实违反了客观现实的规律。”③魏金枝:《为〈沙桂英〉辩护》,《文艺报》1962年第7期。作为一个受过五四精神影响的老作家,魏金枝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当时着实难能可贵,也显得“不合时宜”。
如果说沙桂英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那么邵顺宝则是“中间人物”的典型。他聪明、能干,有文化,也想把工作做好。但是他缺乏远大理想,安于现状,对自己所领导的工区的生产采取一种敷衍的态度;对摆在眼前的矛盾,采取一种息事宁人、折中主义的立场。从本质上看,邵顺宝不是坏人,心地也算善良,也爱慕沙桂英这样高尚的人,只是在沙桂英的高大形象的映衬下,他内心的虚荣与自私自利才显示出来。在爱情方面,他非常实利主义的择偶观也是思想落后的一个方面。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唐克新塑造邵顺宝这个人物形象是成功的,他性格的复杂性,他身上附着的矛盾比当时很多理想化的人物更能帮助我们认识、思索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在邵顺宝这些“精神状态低下”的人身上,恰恰保留了那个时代鲜活的生活经验,也留下了人物成长的空间。
《沙桂英》发表以后,邵顺宝这个人物形象引起更大的注目是因为它参与到“中间人物”的争论。在争论中,邵顺宝作为工业题材小说难得的“中间人物”形象,与梁三老汉(《创业史》)、严志和(《红旗谱》)、亭面糊(《山乡巨变》)、喜旺(《李双双小传》)、糊涂涂(《三里湾》)等一起被并列讨论。写“中间人物”的主要提倡者是当时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不同场合表达文学创作要写“中间人物”的主张。1962年8月,为了纠正农村题材创作上的浮夸思想和人物形象单一化的问题,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在这次会议的引言和总结性发言中,邵荃麟比较集中地谈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最进步最先进的人,用不着你教育。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只写英雄模范,不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小说的现实主义就不够。”①《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在英雄人物、理想人物遍布文坛的背景下,邵荃麟的文学主张显然是为当时逼仄的文学环境拓展开阔的写作空间,很多作家对这一主张持肯定态度。
为了配合宣传大连会议精神,1962年9月号《文艺报》发表了沐阳(谢永旺)的文艺随笔《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沐文首先认为邵顺宝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而在艺术创作中却相当少见,他的出现在创作领域是“可贵的创造”。其次,沐阳认为梁生宝、沙桂英作为艺术典型得到了评论界热烈的讨论与“争辩”,而“艺术成就不亚于他们的梁三老汉和邵顺宝”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沐阳号召作家“像《创业史》、《沙桂英》那样,在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同时,把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多种多样的人物,真实的表现出来”。《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一文中并没有使用“中间人物”这个词,沐阳只是谨慎地使用了“中间状态”人物,同时又加上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句话是当时《文艺报》值班的编辑部副主任黄秋耘加上的②黄秋耘:《中间人物事件始末》,《文史哲》1985年第4期。)。由于这个定义在修辞上的形象性,后来被广泛使用。沐阳的文章并没有提到大连会议以及邵荃麟的讲话精神,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沐阳肯定了邵顺宝、梁三老汉这些人物形象的意义,并且非常谨慎地倡导作家写“中间状态”人物,很明显是呼应邵荃麟的大连讲话精神。由于当时大连会议讲话没有公开发表,沐文发表以后影响很大自在情理之中。③详情参见谢永旺:《秋耘同志在〈文艺报〉》,《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1期。
沐阳的文章发表后,形势发生变化,中宣部领导指示《文艺报》对沐文进行批驳。1962年12月号《文艺报》发表黎之(李曙光)的文章《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到的……〉》,黎文虽然不同意沐阳文章的观点,但是在论述上只是把“中间人物”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商榷,基本上是在学理的层面展开。其后,“左”的思潮越来越严重,写“中间人物”被无限上纲上线,最后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主张”“黑八论”之一,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