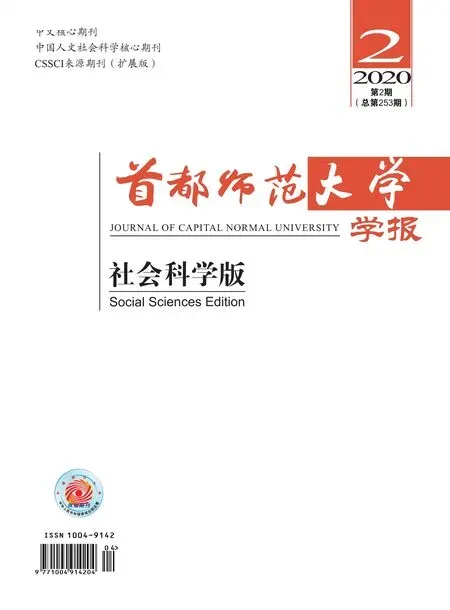美学重建与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四大形态
赵奎英
一、中国美学重建的当代进程
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审美活动领域的扩张、各种新兴的艺术类型的产生,以往美学学科中存在的问题日渐突显,某种更具整合性的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当今的语境中,美学重建的工作显得尤为紧迫,但中国美学建构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若从1902年王国维把它从日语翻译成汉语算起,已有逾百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学学科经历了近现代的草创、奠基和当代的确立、发展两个重要阶段。而对于中国当代美学来说,它又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两次美学“大讨论”,90年代“实践论”与“后实践论”美学的论争,以及接续着这种论争而来的、继续围绕着美学理论转型而展开的美学研究的历程。纵观这种历程,前两次美学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美学基本理论的确立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论争和新世纪以来的美学转型研究,则触及对美学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建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美学“大讨论”,主要是围绕着美的本质问题展开的。由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四大流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派美学作为中国当代美学基本理论的经典形态确立下来。实践派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研究在一定时期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其在中国当代美学基本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就功不可没。但这一美学主要还是奠定在认识论哲学基础上的认识论美学,具有一些在其自身内部很难克服的局限。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实践论美学以其本体论上的局限和作为认识论美学的特征,更多地受到人们的批判与质疑,于是围绕着对实践美学的反思,又掀起了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第三次热潮,“实践派”美学与“后实践派”美学的论争,产生了“修正改造”的新实践美学和“超越”实践美学的“后实践美学”两大理论取向或“阵营”。前者主张重建实践本体论,如“新实践美学论”“实践存在论美学”,①张玉能:《新实践美学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后者如生命美学、生存美学则主张以“生命本体”“语言本体”超越取代传统的实践或“工具本体”论。②潘知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张弘:《存在论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的新视界》,《学术月刊》1995年第8期。“后实践美学”中也有主张以“主体间性”来超越实践派美学的主客二分的特征。③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学应向何处去的问题伴随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仍然是众多美学研究者关注的中心。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论争虽然已经到了沉淀期,但其依然存在。有学者继续在发展中为实践美学的合理性寻找依据,也有学者继续主张走向以往所坚持的“后实践美学”,如“生命美学”。国内的生命美学坚持感性生命的本体地位,把美学研究置于更为本源的基础之上,它对矫正传统实践论美学的某些缺陷,对促进中国当代美学的存在论转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生命美学一直不愿正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生命美学虽然使用了“生命”这个人与动物、植物等所共有的现象术语,但在其视野中又只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其他生命的价值则处于被盲视或漠视之中。这使得就像刘成纪所说的,这种建基在人的个体感性生命基础上的美学,实际上又未能真正摆脱传统实践论美学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④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在世界万物之中,不仅人拥有生命,自然界的动植物也都拥有生命,其他自然生命同样应该得到关怀和尊重。根据《说文解字》,所谓“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所谓“命”:“使也。从口令。”段玉裁注曰:“令者,發號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⑤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页、第57页。因此,“命”亦作“天命”。从这种解释也可以看出来,“生”的原义主要是草木植物的“生”,后来才指人的“生”。“生”是自然的、天然的,而又是必然的,因此它像是“天之令”或“天命”,这或许是人们后来又把“生”与“命”联结在一起称作“生命”的原因。“生命”这一词意味着“生”是“天生的”,它承载了“天之命”,生命因此也是庄严的、伟大的、令人敬畏的。中国古代哲学正充满了这种对“生”的敬畏和爱护。《周易·系辞下》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正义》陈玄英疏:“‘天地之大德曰生’者,自此已下,欲明圣人同天地之德,广生万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在乎无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①王弼等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这也就是说,天地之德之所以是一种“大德”,是因为它既“广生万物”,又“常生万物”。我们知道,《周易·系辞上》中还有:“生生之谓易”,人们常据此把“天地之大德曰生”之“生”理解为“生生”,“天地之德”因此也被说成“生生之德”。但若根据《易传》全文并结合《中庸》中的看法,这里的“生”应该包含“生生”与“成生”两大方面的含义。《周易·系辞上》开篇中就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后面又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周易·系辞上》)这实际上都是在说,天地之大德是“生”“成”。天地既“生”万物又“成”万物;既“广生万物”“常生万物”,又“养育万物”“成就万物”。《中庸》第二十五章“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与《易传》中的“继善成性”是一致的,但它把“天地之大德”通过“诚”推及到“人”了。根据这种观点,这种“大德”当然不只是关心爱护、成就人的“生”,而且是促进人与天地万物各遂其生、各尽其性、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的和谐共生。所谓“大人”“圣人”,都是合于天地之大德、与天地万物同体同流的“人”。所谓“大美”,首先就是显现天地“生成”之大德的美。而最高的文学艺术境界也是指向或合于这种天地之“大”境、大美的。如果今天的生命美学,仍然仅仅拘执于所谓“自由自觉”的人的生命,认为“人是美学舞台上始终如一的主人公”“美学的历史从少年到白头,所写下的,都是人自己的历史”,这无疑是狭隘的。②潘知常:《“生命”视界与生命美学》,《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要重建的中国当代美学绝不是“无人”的美学,它只是呼唤具有更博大的生命关怀和伦理关怀的“生态人”。因此,更多学者在充分认识到实践美学的痼疾和以生命美学等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的缺陷后,开始为中国当代美学的重建寻找其他新的出路。
二、当代中国美学重建的几种主要形态
刘成纪在《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理论进程》中对新时期中国美学从“实践”“生命”向“生态”演进的历史和逻辑进程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性描述,在这里,生态美学被置于代表中国美学新方向的位置上。③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理论进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曾繁仁先生在他《美学之思》中曾谈到自己在美学探讨上所经历的“从认识论到存在论过渡”的问题,④曾繁仁:《美学之思》,山东大学出版2003年版,第2页。并在以后的文章中继续阐发了“当代存在论美学观”,并把它有效地贯穿于对美育和生态美学的研究之中。后来,随着生态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曾繁仁先生又提出了建立在生态存在论基础上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并指出,这种建立在生态存在论基础上的生态美学,并非“简单地是一种美学形态或新的分支学科,而应该将其看作是美学学科的新发展与新延伸,是一种相异于以往的、当代形态的、包含生态维度的新的美学理论”,⑤曾繁仁:《20世纪环境美学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广义的“生态美学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并且从多方面论证了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对“人类中心论”“艺术中心论”、形式静观美学、“西方中心论”美学的反思与超越,以及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更具有本土性质的当代美学,对中国传统的美学学科进行改造和重建的可能。⑥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的反思性与超越性——兼论中国美学的发展》,《上海文化》2015年第8期。
谈到生态美学,我们不应该忽视与此相近、相关的环境美学研究。环境美学在西方兴起,不仅直接引发当今中国的环境美学研究,也对生态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美国学者伯林特、卡尔松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环境美学研究,以陈望衡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环境美学研究,实际上也都包含着一种美学重建的雄心。伯林特在他的《美学再思考》中曾提出要思考环境审美对于美学重建的意义,认为“环境的审美价值甚至引导我们超越对美的追寻,而认识到否定性审美价值和特定环境审美批评的重要性”。①阿诺德·伯林特:《美学再思考》,肖双荣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在回答环境美学与一般美学的关系时又谈道:“我不认为环境美学是孤立的区别于一般美学”,二者“其实形成一种互动的关联:环境美学的某种理论被‘上升’后用以突破传统美学原论的局限,反过来,美学原论的某些拓展也被‘下放’到环境美学当中”。②刘悦笛主编:《美学国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由此可以看出,环境美学对于传统美学进行重建的意图。但相比而言,生态美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是一种更具本土性的美学研究,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总体背景下,在中西方美学的交流中,西方环境美学研究也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生态化的趋势。西方当代环境美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伯林特坦言:“通过对环境美学的理论基础的回顾,我开始认识到生态视野能够做出重大的、事实上也是决定性的贡献。通过从生态方向开始,我们的探索获得一种启发性视野,因为生态观点既使我们对于环境的理解也使我们对于美学的理解出现改观。事实上,生态美学这里可以作为指导性观念。”正是在这种改变和调整的基础上,伯林特“提出环境美学的主导性观念进展的秩序”。他说:“这是一个逻辑的秩序,我们把环境视作一种最宽泛的概念,把它与美学结合起来,最终达到特别意义上的作为生态美学的环境美学的观念。”③Arnold Berleant,“The Language of Environment”,Presented in a panel 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t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 in Beijing in August2010.感谢伯林特教授把大会论文提供给本人使用。尽管伯林特理解的生态美学与中国学者所理解的生态美学还存在较大差异,但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环境美学向生态美学发展或被生态化的趋势。环境美学的生态化趋势其实也发生在中国环境美学研究中。以环境美学研究著称的陈望衡先生,近两年提出“生态文明美学”的概念。④陈望衡:《“生态文明美学”初论》,《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无论如何解释这一概念,“生态文明美学”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其强调“生态性”应在常理之中。
我们知道,“生态学”(ecology)最早出现在德语中,为“Ökologie”,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海格尔合并两个希腊词“oikos”和“logia”构成的。 “oikos”的原义是“房屋、栖居地、住所”,“Logia”就是“关于……的研究”。这样生态学的原义可以说是“关于房屋、栖居地、住所”或“居家”的学问。而对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海格尔则把它界定为,研究生命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以及生命体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⑤纳什:《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并见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allowed_in_frame=0&search=ecology&searchmode=none。综合生态学在古希腊语中的原义和海克尔对生态学的界定,可以说“生态”这一概念包含三个关键义项:家园(栖居地、环境)、生命与相互关系。如果说一种美学是具有生态精神的,就意味着它是关心栖居家园的、关心生命存在的、关心关系整体而不是主客分离、人类中心主义的。⑥详见赵奎英:《论自然生态审美的三大观念转变》,《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根据这一界定,生态美学是开放的、包容的,它与中国传统的强调“广生万物”“成就万物”之德的“生生美学”或“生成美学”,与肯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当代“生命美学”,与把环境当作栖居家园、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环境美学”,都是相融相通的。因此,我们这里把“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放到一种形态之中。
在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趋向中,另一个强劲的势头是关于“生活美学”(或“生活论美学”)的构想和讨论。早在1991年,王德胜就曾发表《美学如何可能走向大众生活》的文章,谈论当代中国美学走向大众生活的必然性问题,并具体探讨了美学走向大众生活“如何可能”以及美学走向生活的文化建构意义;后来,王德胜、陶东风、周宪、金元浦等又进一步发起并推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从而“从根本上明确了当代美学走向日常生活的理论新景”。⑦王德胜:《美学如何可能走向大众生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王德胜:《美学的改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6、83页。仪平策在《生活美学:21世纪的新美学形态》中更是明确主张“生活美学是21世纪人类美学的重要形态和发展趋向”。①仪平策:《生活美学:21世纪的新美学形态》,《文史哲》2003年第2期。高建平在《美学与艺术向日常生活的回归》中也指出:“近年来,首先是在国外,然后在国内,出现了许多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这些争论,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当代美学所面临的任务,了解当代艺术的处境,对于我们思考美学和艺术的未来,是非常有益的。”他通过对美和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与梳理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种观点其实很早就有,它是一个被主流美学所压制但却一直存在着的传统。这种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一种美学转向,这种转向就是让美学走出“审美无利害”和“艺术自律”论,让美学和艺术回到生活世界中去。②高建平:《美学与艺术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让美学和艺术回到生活世界,也是让美学和艺术回到它本来的状态中去,“因为美学观念和道理就在饮食起居交往劳作这样普遍的生活现象中”。③周宪:《美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只是中国当代美学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语境和现实土壤都与西方美学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美学研究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重构一种“生活美学”或“生活论美学”,“重建美学与生活的关系”,④王德胜:《回归感性意义:日常生活美学论纲之一》,《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可谓当今中西方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以至有学者提出,“当代艺术”“环境”与“生活”美学已经成为了全球美学发展的新潮与主潮。⑤刘悦笛:《从当代艺术、环境美学到生活美学》,《艺术百家》2010年第5期。当代中国的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来加以重构。⑥刘悦笛:《“生活美学”的兴起与康德美学的黄昏》,《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在中国当代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中,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领域是“身体美学”研究。国内的身体美学研究与美国分析美学和新实用主义美学的代表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被引介到中国有关。但目前这种研究已不止于一般地引介一种新的美学形态,而且还深入地反思这种美学形态对经典美学的冲击,以至走向以身体美学对中国当代美学基本理论的整体重构。姚文放教授在《肉体话语、身体美学、身体的审美化》一文中谈到,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三人不谋而合对同一个问题叫板,那就是经典美学对于最大的感性存在——肉体、身体的忽视。有鉴于此,他们力倡“肉体话语”“身体美学”“身体的审美化”等理念,这“无疑是当代美学的重大事件和重要转折,相信它对于当今乃至日后美学的发展将产生深刻影响”,对于当今的美学学科重建具有重大意义。⑦姚文放:《肉体话语、身体美学、身体的审美化》,《江海学刊》2012年第1期。这实际上就是说,对身体的重视,身体美学的兴起,也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的美学形态的兴起,它在学科的层面对经典美学进行挑战,试图重建一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王晓华的《身体美学导论》可谓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尽管我们这里仍然把它作为一种美学形态来谈,但在王晓华的研究规划中,他的身体美学已不是一种美学形态或美学分支学科,而是一种以身体为中心对美学进行整体重构的普遍意义上的美学。因为该著的学术雄心在于,“完成尼采、马克思、梅洛-庞蒂、米歇尔·亨利等人的未竟之业,建构完全从身体出发的美学体系”。⑧王晓华:《身体美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
在中国当代的美学建构性研究中,另一个具有明显本土特征并受到较多关注的美学形态是“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文艺美学’命名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台湾学者王梦鸥在1971年出版了一本讲美学的书,叫做《文艺美学》;1980年中华美学学会的会议上,北京大学教师胡经之提出:应在大学艺术和文学系科开设文艺美学课程,并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支持。”⑨参见杜卫:《文艺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文艺研究》2019年第1期。1982年,胡经之先生又发表《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指出:“文艺学和美学的深入发展,促使一门交错于两者之间的新的学科出现了,我们姑且称它为文艺美学。”1986年5月,山东大学等六家学术单位在山东泰安发起召开首届全国文艺美学讨论会;2000年12月,教育部批准在山东大学建立文艺美学重点研究基地;⑩参见曾繁仁:《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2001年5月,“全国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1999年11月,暨南大学也曾举办“文艺美学在中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这一时期,人们围绕着文艺美学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也涉及到它与美学学科、美学基本理论建设的关系问题,文艺美学也曾被一些学者视作中国当代美学的生长点,并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后来随着其他美学形态的兴起及其他原因,“文艺美学在创建本土美学”等方面的“自觉意识明显淡化了”。①杜卫:《文艺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文艺研究》2019年第1期。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明确提出“文艺美学”学科以来,西方美学中的艺术哲学、艺术美学研究,在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界,主要是以“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形式存在。②胡经之在《文艺美学的反思》(《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一文中,是把“文艺美学”与“艺术美学”混称的,有几个地方谈到“文艺美学”时都使用了“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的表述。并且国内学界对于“文艺美学”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关注度。以“文艺美学”为主题,通过超星发现系统进行检索,截至目前,可以发现3万余条记录,尽管这种检索有一些不精准,但这足以说明文艺美学受到的关注程度。并且文艺美学所具有的建构性特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重新提起。如杜卫教授指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文艺美学应该继承中国现代美学融合中西、建构本国美学理论的精神,接着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做下去。”③杜卫:《文艺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文艺研究》2019年第1期。2018年11月,“新时代文艺美学的使命与创新”青年博士论坛在福州举办;2018年6月,“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也说明文艺美学在新时代所具有的生长力。
我们知道,2011年“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升格为“学科门类”之一,原来下设的同名二级学科“艺术学”升级为一级学科,为避免与学科门类名称相同,更名为“艺术学理论”。这样,原来的艺术美学、艺术哲学,都将成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合法而重要的研究领域。艺术学理论把艺术哲学、艺术美学拿过去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领域,并不意味着美学自此不能再研究艺术哲学、艺术美学了。艺术学即使宣布从美学中独立出来,也不能阻挡愿意讨论艺术问题的美学家继续谈论艺术问题,但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向是,当今的美学已不再把艺术当作自己的研究中心了,美学不能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称作“艺术哲学”了。但文学和艺术仍然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进行美学重建的重要依托,尤其是当代艺术实践活动的发展和新兴的艺术理论形态、艺术哲学观念的产生,正在强有力地推动着当今美学基本理论的变革和重建。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在当今中国的美学研究中,表现出明显的美学重建意识并产生了标志性成果的主要有四大美学理论形态: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这些新的美学形态,作为具体领域的美学研究,它们都已经有意识地触及到美学重建问题,为转型期的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并且这四种美学形态不只是从中国语境中表现出来,而且也在西方语境中较早地表现出来,或者具有类似形态。
三、四大美学形态与西方当代美学研究
正如上文已经谈到的,身体美学是由美国分析美学和实用主义美学的代表理查德·舒斯特曼首先提出来的。舒斯特曼从分析美学内部批判分析美学,认为鲍姆嘉滕最初的美学方案要比我们今天的美学观念更为广阔和更具有实践性,并提出了建设“身体美学”学科的构想。他把“身体美学”定义为“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aisthesis)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④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54页。并规划了身体美学三个基本维度:分析的、实用主义的和实践的身体美学。舒斯特曼希望这样的一种身体美学能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在传统的美学学科中获得一席之地,并以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性,使传统的美学学科得到某种扩展和改造。
在日常生活美学方面,德国哲学家沃尔父冈·韦尔施对西方传统美学进行系统地批判反思,并有意识地对当代美学进行重构。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指出:“本书的指导思想是,把握今天的生存条件,以新的方式来审美地思考,至为重要。”①沃尔夫岗·韦尔施:《重构美学》“序”,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而当今现实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审美化”。审美化不仅弥漫在整个现代生活中,体现在生活的表层,还深入到认识论层面,存在于哲学思想的核心,“真理、知识和现实正越来越呈现出审美的轮廓”。因此当今审美不仅关系到艺术,而且关系到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影响到社会存在和个人生存的方方面面。这种现实领域的审美扩张改变着当今美学的结构和地位,使它成为一门超越传统美学的、用来理解整个现实的“元媒介”,一种“超越美学的美学”。这种美学“必须超越艺术论”,并打破对艺术的单一概念化理解,恢复美学作为审美感知的学科的丰富性,并向艺术之外的问题开放,成为一种“综合了与‘感知’相碰的所有问题,吸纳着哲学、社会学、艺术史、心理学、人类学、精神道学等等的成果”的“跨学科”或“超学科”。②沃尔夫岗·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36-137页。
伯林特在《美学再思考》中,也主张恢复“美学”这个名称与感官感知的联系,反对康德对于“审美”所做的一系列区分,主张重建一种“后康德美学”。伯林特的美学重建思路,特别强调环境审美对于美学重建的意义,认为“环境的审美价值甚至引导我们超越对美的追寻,而认识到否定性审美价值和特定环境审美批评的重要性”;并在环境审美研究的基础上,强烈反对传统美学学科基于纯粹艺术得出的静观的、有分界的审美模式,强调审美经验的连续性、介入性,并提出“审美参与”的概念加以说明。正是与他的环境审美研究相一致,伯林特也强烈反对康德以科学模式对审美感知的清晰区分,强调恢复审美感知的丰富性、连续性、整体性甚至混沌性;强烈反对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观,以及把审美看成完全区别于道德、实践、社会和政治等其他价值的特殊领域,而积极地寻找审美价值对其他领域所能作出的独特贡献。③阿诺德·伯林特:《美学再思考》第一章,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伯林特的环境美学,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表现出明显的向生态美学发展的趋势。
伯林特的美学重建,对当前国内的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韦尔施的美学思想对国内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则引发了国内的身体美学研究的热潮。他们的美学思考和重构不仅对美学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也具有启示作用,尽管这种启示仍然是从对某一领域、某种形态的美学研究中拓展、引申出来的。与以上情况有所不同,德国美学家马丁·泽尔的“显现美学”,则是在根本上从正面对美学进行重建的成果。海德堡大学教授、伽达默尔弟子布不纳(Rudiger Bubner)认为,马丁·泽尔的《显现美学》
一书是“危险领域的动人篇章”,以“显现”概念开启了其他问题的广阔空间,建立了美学的“新世纪”。④马丁·泽尔:《显现美学》“内容简介”,杨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封二。泽尔的《显现美学》有三大目标:第一,打破柏拉图时代以来的巨大影响,在“存在美学”和“假象美学”之间做出两分。第二,力图探讨“如何可能发展出一种整合式的理论,让自然美学、艺术美学以及日常生活形态美学都能得到同等的辩护”。第三,阐明美学在哲学中的核心角色。⑤马丁·泽尔:《显现美学》“中文版前言”,杨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这意味着,泽尔要从根本上重建一种统一的、整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的美学,而不是一种具体领域、具体形态的美学。这种美学也可以说就是一种“美学基本理论”。泽尔美学以“显现”概念为起点,充分考虑当代艺术实践和各种新兴的美学形态,并综合运用现象学方法,以实现对美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革,对于当今的美学基本理论重建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还有一些西方美学研究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重建一种新的美学体系,但他们对西方当代美学转向的描述以及对当今西方美学研究主要概念领域的勾画,对于我们的美学重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意大利美学家马里奥·佩尔尼奥拉在《当代美学》中的描述与勾画,⑥马里奥·佩尔尼奥拉:《当代美学》绪论,裴亚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当代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一样,都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美学的观念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并且美学发挥作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宽泛,传统的美学学科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美学的重建是中西方学者共同面对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美学的重建工作中,中西方美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重要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当下几种新兴的美学理论形态,如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以及涉及美学观念和审美观念变革的显现美学,对我们今天的美学基本理论重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当今中西方美学的重建只有这几种形态,也不是说这些美学形态的重建不存在任何问题。从国内学界来看,目前美学重建工作的一个最主要问题是,大多数的美学重建还主要是通过对某一领域的审美活动、某一种具体的美学形态研究来展开的,采取的主要是一种“以局部促整体”或“以局部代整体”的思路,并且各种具体形态的美学研究之间还缺乏足够的沟通。而对于那些已有的正面展开的美学基本理论重建来说,又往往不注意吸收新兴美学形态的重要成果。如国内的一些美学基本原理教材,对于这些新的美学形态,有的置若罔闻,有的只是作为美学新的增长点轻描淡写地提一下,并没有吸收到自己的美学基本理论的体系之中。这就是说,当今的美学重建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重要成果,但这些成果尚未得到系统整合,仍然处于分散的状态。因此,我们美学基本理论重建工作的一个首要任务是,从当下理论语境出发,对当今美学重建的几种主要理论形态,进行分析梳理和系统整合,对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整体蓝图,做出更加系统的规划和建构。
我们的美学重建不仅要从这样一种理论语境出发,面对各种新兴的美学理论形态,而且要从当下的现实处境出发,面对审美活动实践领域出现的各种新变化。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变化,归根结底主要还是由审美活动领域的变化导致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当今中国社会的生存现实、审美活动的现实都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原来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审美活动,如今已经扩展到人类生存和文化活动的各个方面。不仅艺术,身体、自然、环境、日常生活等也都已成为审美的对象或审美活动发生的领域。随着审美活动领域的扩张,美学的王国也不能固守原来的疆域,随着艺术边界的消失,美学也无法固守纯粹艺术的定义了。面对审美活动领域的扩张,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无疑应该做出积极的回应,拓展美学关注的对象和范围,不能像以往的西方美学研究那样,主要关注艺术问题,把美学看成“艺术哲学”了。美学基本理论重建应该面向审美活动的所有领域,力求建构一种更具有整合性的、能让所有的审美活动得到解释的美学基本理论。一种理想的美学基本理论,不仅仅是解释性或分析性的,不仅仅是能够对已经出现的审美现象进行解释,肯定其合理性存在,或仅仅对其进行分析,帮助人们对它进行理解,而且也应是批评性、批判性和构成性的,亦即它能帮助人们对某种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做出审美评价和审美判断,发现其优点或问题,并对那些存在着问题的方面进行批判、引导,促进或构成一种健康的审美活动实践。这也就是说,美学不应仅仅是追在各种艺术和审美现象后面的、只是负责为它们寻求解释的“肯定性”美学,它还需要与艺术现实、审美现实以至生活现实保持一定的批判间距和张力,发挥“否定性”美学的功能。美学也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和审美分析的理论,也应是一种艺术批评或文化批判的工具;美学也不只是提供普遍的概念和空洞的逻辑,它也应有助于解释、参与或构成专门领域的审美活动。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这里进行美学重建研究的目标是,立足于中国美学研究的当下语境和现实问题,梳理中西方美学的当代转型,勾画中国当代美学形态的多元格局,把握当今中西方美学研究的主导趋势,确立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理论范式;紧密联系生活世界和审美活动现实领域发生的变革,还原清理当下美学重建的问题领域;整合古今中外的美学理论资源,总结吸收当下美学具体形态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重建一种以生态审美为指向、以艺术审美为依托、以生活世界为基底、注重身体诸知觉的、既具有理论解释性又具有文化批判性和实践构成性的美学基本理论,以回应美学研究中所遇到的新问题、审美活动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从根本上推进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