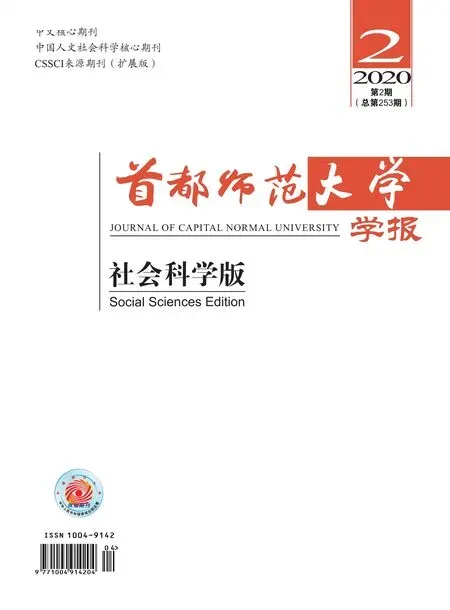论德里达对阿尔托“支撑基底”(subjectile)概念的演绎及其意义
陈 庆 牛宏宝
安托南·阿尔托作为20世纪初法国超现实运动的一员,以其“残酷戏剧”理论而为世人所知。然而其影响并不仅限于戏剧界,他也同样对20世纪法国思想有着重要影响,比如正是其关于身体的思考以及其在广播稿《为了上帝审判的终结》中提出的“无器官身体”的说法,促使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演绎出一整套的关于“无器官身体”之理论。而另一位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则在其早期代表作《书写与差异》中也有两篇文章《被劫持的语言》与《残酷戏剧与再现的关闭》专门论述阿尔托关于语言与再现问题的思考。
同时阿尔托所涉及的领域还有诗歌与素描,事实上其对于素描的实践与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不仅有着根基性的深度,也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一些艺术家有着重要影响,如英文本的《安托南·阿尔托:纸上作品》一书所收录的访谈中美国艺术家南希·斯佩洛(Nancy Spero)与德国艺术家奇奇·史密斯(KiKi Smith)所谈到的,二者都受到阿尔托的素描及观念的影响,前者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后者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①Antonin Artaud:Works on Paper,Edited by Margit Rowell,New York:The Museum of Modern Art,1996,p.122.
而德里达晚期的两个文本《刺穿支撑基底》(Forcener le subjectile)与《阿尔托/莫玛》(Artaud le Moma)便是对阿尔托的素描以及素描观念的讨论。在后者中其甚至将阿尔托与另一位开启性的现代艺术家杜尚加以关联:“无数对艺术以及作为艺术作品之作品的反对使得阿尔托成为一位杜尚的同时代人……。”②Jacques Derrida,Artaud le Moma,Paris: Éditions Galilée,2002,p.85.这也迫使我们关注阿尔托的素描与素描观念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尤其是德里达所阐发的阿尔托那里出现的“支撑基底”(subjectile)这一观念的内涵与意义。
一、“支撑基底”这一概念的来源
“支撑基底”这一概念在阿尔托那里多次使用,特别是在其中晚期即1932—1948年这一段时期。然而这个词在法语中并不是一个常用的词,如赫尔曼·拉波波特在《晚期德里达:对近期作品的阅读》中指出的,即使在埃米尔·里特赫(Émile Littré)所撰写的字典中直到如今这个词也只是被作为附录收入,③Herman Rapaport,Later Derrida:Reading the RecentWork,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3,p.122.而在德里达看来,阿尔托对于这个非常规的法语词的使用也涉及阿尔托对于语言本身的反思,“subjectile”这个词本身成为了一个“支撑基底”,它抵抗着由法语向其他语种的翻译。事实上这个很少被定义的法语词确实带来了语义上的模糊性以及丰富的可能性,但因为其尚未被明确定义,因此必须追溯这一概念的来源。而对于这一概念的来源需要在四个维度,即语源学意义上、艺术史意义上、阿尔托文本意义上以及哲学意义上进行追溯。
首先,从语源学意义上,“subjectile”一词是“subject”一词与“ile”这一后缀进行的合成,而“主体”(subject)这一概念则是20世纪法国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ile”这一法语中常用的后缀有着两种用法:一种是名词后缀,表示“具有……属性的物”,而另一种是形容词后缀,表示“倾向于……的”“易于……的”。而在阿尔托的语境中,“subjectile”使用的是前一种用法。但问题的复杂在于“subject”这个词的组成,前缀“sub”来自拉丁语,表示“在……之下”,而“ject”来自于拉丁语中的“jacere”,表“投掷”之意,这一词根在“主观的”(subjective)、“投射物”(projectile)、“投入”(introjection)、“对象”(objection)、“排泄”(dejection)、“抛弃”(abjection)等词语中都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一意义上“subject”一词所意谓的便是“在抛投的下面”,而“subjectile”则成为了“在抛投的下面的事物”。正是因此,在这里通过意译将“subjectile”一词翻译为“支撑基底”,其与“投射物”(projectile)相对应,既是作为基底对后者的承接,同时也是在这种承接之上的支撑与生成,这种双重属性使其有着根基性的重要意义。
其次,“subjectile”这个词并不是阿尔托自身所创造的,而是有其历史的来源。德里达在文章中为这种历史来源提供了三个线索:第一个是意大利语中的来源,文艺复兴时期的蓬托尔莫(Pontormo)写给瓦尔齐(Varchi)的信件;第二个是法国艺术史家迪迪·于伯尔曼1985年出版的《具身化的绘画》(La Peinture incarné)中所提到的“‘subjectile’这个古老的概念”;第三个则是保尔·德维南为德里达提供的一个文本,画家特里斯坦·克林索在1921年为波纳尔写的文章,德里达指出在其中“subjectile”这个词出现了三次,并认为阿尔托很有可能读过这篇文章。④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64.在德里达给出的第一个线索中事实上并未出现“subjectile”这个词,而对于第三个线索,拉波波特在《晚期德里达:对近期作品的阅读》中对阿尔托是否真的读过这一文本提出了质疑,①Herman Rapaport,Later Derrida,Reading the RecentWork,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3,p.122.但是第二个线索中所指出的这一概念出现在法国著名艺术史学家的书籍中则是确凿无疑的,那是在于伯尔曼《具身化的绘画》中名为《墙面》(Le pan)的章节中出现的,于伯尔曼的原文写道:“在这一问题中,‘subjectile’这一古老的概念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枢纽,这丝毫不会让人意外。我们应该感谢让·克莱(Jean Clay)的理论重建,在那时他通过19世纪的绘画实践而恰当地重新激活了这一概念,他讲道:‘通过编织、溢出、交叠’绘画‘倾向于超越表面的问题以抵达……层状、底床、厚度的范畴’。存在着边饰、褶子、缝隙,这是‘空间的跳动’,底基通过这种跳动‘显示表面、穿越表面、制造表面’……”②Georges Didi-Huberman,La Peinture incarné,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1985,pp.38-39.,可以看到于伯尔曼将“subjectile”这一概念追溯到19世纪的让·克莱,并且也间接指出了这一概念在更早之前便已存在,因此可以说“subjectile”是艺术史中早已存在却长时间被遗忘的一个概念;同时在于伯尔曼的语境中他所谈论的是绘画的“表面”的问题,在其看来绘画的表面并不是平滑的,而是有着多个层次,有着褶子的存在,事实上这种思想与阿尔托的对于面容的思考有着相通之处,然而于伯尔曼并没有提及阿尔托,同时其所谈论的也不仅仅是“subjectile”这一概念,还有与之相近的“subjectio”等概念,而德里达在这里所谈论的“在下面”“被抛”“支撑”等主题,于伯尔曼也同样有论及,只是德里达的论述以阿尔托为出发点并且更加哲学化。
再次,在德里达的梳理中,阿尔托对于这一概念的谈论主要出现了三次,分别是在1932年、1946年与1947年。正是在1932年9月一封写给安德黑的信中,阿尔托第一次使用了“subjectile”这个词,他写道:“与此一道的一幅差的素描,在其中被呼作支撑基底的事物背叛了我”③Antonin Artaud,Oeuvres complètes V,Paris:Gallimard,1956ff,p.121.;而在1946年,阿尔托再次谈论“subjectile”的问题:“这幅素描是一个墓穴,在其中试图给予那些直到今天都从未被艺术接受的事物以生命和存在,给予支撑基底的蹂躏、形式那可怜的笨拙……以生命和存在。页面被污染与损坏,纸张崩溃,人们以一个孩子的意识来进行描画”④Antonin Artaud,Oeuvres complètesⅪⅩ,Paris:Gallimard,1956ff,p.259.;而最后一次则是:“在这惰性纸张上的图形于我的手底什么也没有说。它们将自身作为负担提供给我,这种负担并不能激励素描,而对于它我可以刺、切、刮、锉、缝、拆开、撕碎、砍、编织,而在这同时这一支撑基底并不会通过父亲或通过母亲而抱怨什么。”⑤According to 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137.在这种种表述之中可以看到在阿尔托那里“支撑基底”始终是作为对立因素而存在的,而其素描实践则是对这一对立物进行的种种操作。
最后,“支撑基底”出自与艺术相关的领域中,在哲学的历史中,尚未看到对这个词的使用,然而因为其所包含的“subject”一词,也必然使其与哲学中的话语发生关联。可以看到在法国结构主义对于主体问题的阐释中,这一概念和“支撑基底”这一概念一样都是作为一个肯定性的概念却包含着对否定性的要求。而在德里达讨论主体问题的访谈文本《“用餐愉快”或主体的筹算》⑥Jacques Derrida,“ ‘Eating Well,’or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ubject,”Points...,translated by Peggy Kamuf&other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255-287.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关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对“被抛境况”的阐释也在《刺穿支撑基底》一文中再次出现,正如德里达指出的“subjectile”不仅仅是指物,也有可能是指人称化的对象;而《晚期德里达》中则甚至指出在德里达的思想过程中用“subjectile”一词代替了“此在”一词:“通过一种对语言本身的非常规使用,德里达让阿尔托与海德格尔相接近。他在阿尔托那里为此在找到了另一个词——也许是更好的一个词,虽然有些粗糙——‘支撑基底’(subjectile)。”⑦Herman Rapaport,Later Derrida,Reading the RecentWork,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3,pp.121-122.那也便是说在拉波波特看来“subjectile”这一个概念能够更好地体现“此在”的“被抛境况”。那么从拉波波特的判断出发,可以说“支撑基底”这一概念也涉及德里达对于海德格尔“此在”概念的批判与推进。
在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根源性的追溯之后,另外一个问题便自然浮现,那便是:什么是支撑基底?阿尔托并未言明这一概念的具体所指,只是强调“支撑基底”是一种对抗性的因素;而德里达的演绎则将这个概念进行了扩展,它不仅是指艺术作品涉及到的许多材质,如木头、纸张、铁、铜板、青铜或者是石头等,同时也有画布、织物等,正像不同材质的框架为画作提供边界和保护一样,这些材质为艺术作品的发生提供基础;并且不仅仅是这些,语言、身体、博物馆的墙壁也被德里达纳入到了这个词的内涵之中。
在德里达的思想脉络中,其在谈论艺术相关话题的时候所关注的往往是边界上的概念,如其在《绘画中的真理》①Jacques Derrida,The Truth in Painting,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Ian McLeo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一书中对于“边饰”“边框”的讨论,其在阿尔托文本中选取的这一概念也不例外,它也是一个边界性的概念,然而这次不再是内与外之间的边界,而是上与下之间的边界,它既是支撑也是屏幕,正是在支撑基底之上艺术的种种行为才得以展开,而支撑基底之下则涉及从根本意义上让艺术得以可能的事物。
二、德里达对“支撑基底”这一概念的演绎
德里达对阿尔托的阐释是沿着两个线索进行的:一个是将这个概念通过词源的探索而与哲学话语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进行关联,另一个是德里达指出的阿尔托对于这一概念的三次表述。
正如前文所提,“subjectile”这个词从词源方面来讲表示的是“在抛投的下面的事物”,而事实上法语中表示前提的词“supposition”以及表示预设的词“hypothèse”有着相似的构成。正如德里达在晚期的另外一篇文章《绘画、书写与素描的“下底”》中指出的:“因为一个预设(来自希腊语的词)或一个‘前提’(来自拉丁语的词),便是我们放置在下面的事物。”②Jacques Derrida,Les 《dessous》de la peinture,de l’écriture et du dessin,Penseràne pas voir,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2013,p.242.“sup”是“sub”的变形,而“position”是位置,供以放置事物的位置,来自希腊语的词“hypothèse”中“hypos”亦是在下面的含义,“thèse”则来自“thesis”,在希腊语中是指人们所放置的、安放的事物。在这篇文章中德里达同样分析的是在下面的这个位置,这个支撑基底,只不过这次是脱离阿尔托而只是谈基底的问题。德里达所强调的是这种“在被抛的下面的事物”在西方的体系中总是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之上,正像在拓扑学的等级制度中,下底总是在下面的,但同时这种低级的存在物却可能有超越性的奠基价值。而在《刺穿支撑基底》中德里达也指出“subjectile”与“前提”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一个前提也是一个支撑基底,而支撑基底则是一个运行中的前提,正像有人可能会说的一个工作台……。”③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121.因此可以说“支撑基底”首先是艺术以及艺术作品的前提。
“支撑基底”中最为核心的是“抛投”,在这个词中是“ject”,而德里达演绎了这个词根的拉丁语来源“jacere”的两种动词形式,一种是“jaceo”,这是一种被动的形式,有着“被抛”的含义:“在第一种情况中,‘jaceo’,我伸展着、躺在下面,在床上如同‘墓室卧像’,被放倒、被放在下面,没有生命,我在我已经被抛的位置上。这是主体或支撑基底的境况:它们是‘被抛在下面的’”④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77.;而另一种则是“jacio”,它所说的是我进行抛投的主动含义:“在第二种情况中,‘jacio’,我抛出‘某种事物’,一种投射物,那也是石头、火、种子或者骰子——或者我抛出一条线。同时,因为我已经抛出了某种事物,我便能够将其抬起或者为其奠基。‘jacio’也可以有着这种涵义:我抛出根基,我通过抛投而构建。”⑤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77.而在德里达的演绎中这两种形式是同时被“支撑基底”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并且这涉及到“支撑基底”的一种双重属性,既有着“不可传递性”又有着“可传递性”,这是因为“支撑基底”必然进行抵抗,抵抗那种仅仅作为再现的支撑物的功能,但作为一种屏幕般的存在,它又需要保留部分的“可传递性”。德里达演绎出的“支撑基底”所具有的双重属性确实可以在阿尔托的作品中看到,如阿尔托提出的对“支撑基底”的种种处理,他的“咒语”系列对纸张的烧灼和穿孔。
凭借着对“jacere”这一词根主动形式与被动形式的双重演绎,德里达事实上正是在这一点上将海德格尔与阿尔托联系在了一起。正如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它向着它被抛入的种种可能性筹划自己。自身之为自身不得不为自身设置它的这根据;这自身却绝不能控制这根据,而是不得不生存着接受根据性的存在。”①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5页。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的“被抛境况”总是在先的,而此在之能在的根据也是在其被抛入的种种可能性的筹划中形成的。而在德里达对阿尔托的演绎中,虽然“支撑基底”同时包含着主动的抛投与被动的被抛,但是这种被抛也总是在先的:“并且如果我自身不是在出生时便是被抛的,那么我也不能抛投或投射。”②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77.这与阿尔托关于身体的思考有相契合之处,在阿尔托那里从我们被出生的时刻,从我们被家庭给予名字的时刻,我们也便是被偷走了,上帝在让我们出生的同时也让我们流产。但一方面阿尔托并没有真正地谈论这种被抛境况,而是谈论一种窃取结构的存在,另一方面事实上阿尔托那里关于“ject”的经验,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被抛经验,而是一种主动的抛掷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书写之中有许多与身体有关的抛投,如吐口水、说脏话、汗液以及种种其他的与身体有关的排泄。正如在《阿尔托/莫玛》一书中,德里达所讨论的才是真正意义上阿尔托的抛投经验,那便是如闪电般的射击以及在谈论素描时带有亵渎成分的关于排泄的说明。关于素描同样是如此,阿尔托并不是认为那些图形是画上去的,而是被自己抛投或者射击到上面去的。
在这种哲学式的对这一概念进行阐述之外,德里达也以阿尔托的三次表述为线索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演绎,涉及三个问题:支撑基底的背叛、出生的场所以及无所抱怨的惰性。
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阿尔托至少三次谈论过“subjectile”这个概念,分别是在1932年、1946年与1947年。1932年,他写道:“与此一道的一幅差的素描,在其中被呼作支撑基底的事物背叛了我。”③Antonin Artaud,Oeuvres complètes V,Paris:Gallimard,1956ff,p.121.
正如阿尔托所说,他的素描不是素描而是记录④Antonin Artaud:Works on Paper,Edited by Margit Rowell,New York:The Museum of Modern Art,1996,p.60.,重要的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再现而是表达,是对艺术家的某种观念的表达。阿尔托的素描是对“素描原则”的放弃,对于素描原则的放弃是因为这种原则恰恰是在一种错误的身体的控制之下产生的:“所以阿尔托抛弃素描的原则首先是因为它已经对其‘绝望’。而他所指使的‘劣行’不仅仅会使一种手工技能、一种画线的能力堕落。同时它也是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眼睛、我们视觉的界限的干扰,也是对‘颅骨盒子之原则’(正是它控制着‘素描的原则’)的干扰,对我们的有机结构这种普遍构造的干扰。”⑤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105.正是这种错误的身体带来了错误的素描原则,而这样的身体的出现是出生时的一种劫掠或流产所造成的。而支撑基底,起码是某种现成的支撑基底也为这种错误的身体下的素描原则提供支撑,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背叛“我”,背叛那个渴望表达“深渊-身体”的“我”。
而对“颅骨盒子之原则”进行的反抗事实上涉及两个层次的操作:一是必须攻击既有的支撑基底,二是这种进攻必须以我们抛投出某种东西作为新的支撑基底而进行,以此来让支撑基底成为既是死亡又是新生的场所。可以说这是双重的背叛,一方面支撑基底背叛了“我”,另一方面我必须通过对支撑基底的处理,让支撑基底背叛再现,接着背叛它自身,从而形成新的观念性的表达。
而在1946年,阿尔托的表述变成了:“这幅素描是一个墓穴,在其中试图给予那些直到今天都从未被艺术接受的事物以生命和存在,给予支撑基底的蹂躏、形式那可怜的笨拙……以生命和存在。”①Antonin Artaud,Oeuvres complètes XIX,Paris:Gallimard,1956ff,p.259.在德里达看来这一次支撑基底不再是背叛,不再是真理的主宰者,而成为了“一个出生的场地”②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122.。也正因此德里达将其与他所分析过的另一古老的概念“khora”结合了起来:“接纳,‘接受’,在一个主体的主体之上,在某种严格来讲正是指接收器/容器的事物的主体之上,在某种几乎是空无的并且必须在其位置上被位置所代替的某物的主体之上——因为支撑基底便只是这种位置的空无地位置化,一种khora的形象,如果不是khora自身的话。”③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123.在上与下之间的支撑基底,在表面与支撑之间的支撑基底,只是一个空无的位置,只是一种空无化的间隔,而正是在这种空无化的位置中阿尔托试图“给予直到今天都从来没有被艺术接纳过的事物以生命和存在”④Antonin Artaud,Oeuvres complètes XIX,Paris:Gallimard,1956ff,p.259.。“khora”的概念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谈论空间时所提出的,而德里达在《Khora》一文中则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正如他所指出的它既不是可感的也不是可知的,接纳一切但却不进行财产般的占有⑤Jacques Derrida,“Khora,”in Thomas Dutoit ed.,On the Name,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99.。在这里德里达显然把支撑基底的这种接纳性归属给“khora”那样的性质。这样的空无化的位置是超出存在论意义上的出生场地,存在并不在场,而是有待出生的,正像阿尔托试图发现的那个“遗失的世界”,事实上这个世界从未存在过,这样的发现因此是朝向未来的。阿尔托在文本中确实强调出生,强调这一场所,但在德里达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借用“khora”这一概念对“支撑基底”进行演绎,在这种意义上他已经超出了阿尔托所讨论的范围,赋予了它新的肯定性涵义。
1947年2月,阿尔托写道:“在这惰性纸张上的图形于我的手底什么也没有说。它们将自身作为负担提供给我,这种负担并不能激励素描,对于它我可以刺、切、刮、锉、缝、拆开、撕碎、砍、编织,而在这同时这一支撑基底并不会通过父亲或通过母亲而抱怨什么。”⑥According to 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137.我们可以看到阿尔托提出了对于支撑基底的一系列操作,事实上这些操作在其自身的素描中只是应用了一小部分,德里达关注的不仅仅是阿尔托的一系列操作中的双重性,以及它的无所抱怨的惰性还有它与父亲和母亲的关系。
“支撑基底”只是为出生提供一个场所,但这次并不是女性化的子宫,而是同时可以是男性和女性:“一方面,支撑基底是一个男性,他是主体:他从他被设定的异常的中立出发制定法则,他是父亲;……那么支撑基底,这个女性,也是一位母亲:工作和生育的位置,在同时躺着并躺下。”⑦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132.这是同时为父亲又为母亲的支撑基底,它是雌雄一体的。同时它也是一个孩子,它正是在那里被抛投出来的,从那里走向前来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支撑基底并不居有任何事物,它没有专有的属性。事实上它并不给出任何事物,而是通过自身让事物出生,在这种出生的过程中助产。
从德里达对阿尔托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遵从的是阿尔托那里的线索,并从这一线索出发完成了对于“支撑基底”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构建,之所以说德里达是在演绎在阿尔托那里出现的“subjectile”这一概念,而不是“解构”,那是因为不同于其在《书写与差异》中肯定阿尔托对身体的肯定的同时还保留有对在场形而上学的幻想,而在这里德里达所做的更多是补全阿尔托那里未详细阐释的“subjectile”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扩展。德里达在这里对“支撑基底”的演绎为这一概念打开了多个层次的褶子,那也就是说通过赋予它一种肯定性的意义,使其具有了肯定与否定的双重张力,从而涉及艺术领域中“基底”丰富性的处理与思考方式。在其演绎中“支撑基底”获得了如下内涵:艺术及艺术作品的前提;同时具有“可传递性”与“不可传递性”的供以抛投的平台;既有艺术形式与规则的根基;上与下之间空无化的间隔;如“khora”般的接受器;让事物出生的场地。但需要问及的是这种演绎是否是阿尔托思想的必然结果?而被如此演绎的这一概念又有着何种意义?这要求我们重新回到阿尔托思想和作品的整体之中。
三、“支撑基底”这一概念的意义
阿尔托对于素描的思考及其素描的实践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中并未得到重视,1986年,即阿尔托死后近40年,收录了大部分阿尔托素描与自画像副本以及保尔·德维南和德里达各自文章的《安托南·阿尔托:素描与自画像》一书才出版,而阿尔托的作品在美国得以被展示则是在十年之后,即1996年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以“安托南·阿尔托:纸上作品”为题进行的展览,并且在此之后出版成书。关于阿尔托的素描及素描思想在中国更鲜有人论及。这或许是因为阿尔托的作品是在学院范畴之外的,他从一开始便是以反素描的方式进行素描,以反艺术的方式进行艺术。然而,正如上面指出的,阿尔托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一些艺术家确实有着影响。
德里达在《阿尔托/莫玛》中甚至将阿尔托与后现代艺术中另一位反叛性形象的代表杜尚联系在了一起:“无数对艺术以及作为艺术作品之作品的反抗使得阿尔托成为一位杜尚的同时代人……”①Jacques Derrida,Artaud le Moma,Paris:Galilée,2002,p.85.,在这样联结式的断言中并不是说阿尔托与杜尚在当代艺术中有着同等的地位,事实上这样说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由杜尚所开启的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对后现代的艺术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样的联结旨在说明的是阿尔托与杜尚不仅在事实上处于同一个时代,同时也在精神以及对艺术的认识上处于同一个方向,那便是以反艺术的方式从根本上对以往的艺术形式以及规则进行更新,因此可以说阿尔托有着对当代艺术影响并且有着继续影响的可能性,他的关于素描的思想也是当代艺术诸种形式与操作的源头之一。那么德里达做出这样的断言的依据是什么?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也为了阐明“支撑基底”的意义,我们必须回到阿尔托的纸上作品,即1937年至1944年的“咒语(spells)”系列、1945年至1946年居住在赫德(Rodez)期间的素描作品以及1946年至1948年其去世前所创作的众多肖像(事实上在阿尔托那里还有着早期作品,即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巴黎时期所画的素描,然而正如德维南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素描对于阿尔托来说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②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6.,与其中晚期的作品并没有较强的关联,因此在这里不作为考察的范围);同时也必须回到阿尔托思想之整体。
阿尔托作品中的“咒语”系列有着最为独特的面貌,这是一系列信件,却有许多由香烟以及火柴烧出的孔洞,边缘也被烧成残缺,同时在上面也有一些描画的图式。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也对这一问题有所论及,他将这种孔洞的塑造与精神分裂症的感受联系在了一起:“精神分裂的首要证据是表面、表层是被刺穿的。身体不再有一个表面。精神分裂的身体像是一种身体-筛子。”③Gilles Deleuze,“The Schizophrenic and Language:Surface and Depth in Lewis Carroll and Antonin Artaud,”in Josue Harari,ed.,Textual Strategies: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Ithaca:Cornell,1979,pp.286-287.阿尔托确实被自己的精神医师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这种烧穿与孔洞有可能如德勒兹所阐释的那样是一种精神分裂的语言,然而问题是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只是在这个时期出现,而在之后的素描作品和肖像画中没有再出现?另一方面,我们或许也可以用德里达反驳布朗肖对阿尔托的阐释时所用的话同样来反驳德勒兹:“他没有质疑那种不可还原地属于阿尔托的东西”①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版,第309页。,也便是说在德勒兹那里也同样是将阿尔托首先作为精神分裂症这个类别的典范性代表而忽略了他自身独特性的特质所在。而在德里达的阐释中,这样的孔洞的存在则是和“支撑基底”的特性有关,那便是支撑基底的“可传递性”与“不可传递性”;从德里达对阿尔托的这种哲学式的阐述出发,我们也可以继续推演,这种支撑基底是在抛投的过程中作为承接的平台而存在的,而孔洞的存在事实上恰恰显示的是抛投的力量,它所映现的是已经消失的抛投轨迹;但同时这种穿透事实上也是将纸张这种支撑基底赋予了皮肤般的属性,纸张上的孔洞如同皮肤上的毛孔,正是通过这些孔洞也让在下面的事物以及力量得以涌现。因此确实如德勒兹所说精神分裂的表面、表皮是被刺穿的,但并不是说身体的表面就不存在,而是说身体表面本身便具有的这种渗透性(如毛孔的存在)被放大了,才使得表面的可传递性被突显出来,而德里达事实上将这种身体的双重属性进行了一般化,也就是说那不再仅仅是皮肤的属性,而是一般的支撑基底的属性。
1945年至1946年赫德时期的素描可以说是阿尔托作品中最具综合性的,在画面上可以看到大量支离破碎的身体、谜一般的诗意文字、加农炮以及棺木等等。而这也使得阿尔托那里的支撑基底这一概念与其晚期另外的核心概念即“象形文字”“残酷”以及“无器官身体”等概念纠缠在了一起。
阿尔托素描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们总是和书写以及文字相关联的,无论是在咒语系列还是在赫德时期的作品中,文字与图形总是纠缠在一起,正如德维南指出的:“他作品中的这种独有特性便是在素描与书写之间的一种彻底的混融,它们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分离性。”②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40.阿尔托将自身的素描称为“写下的素描”,他的素描上总是有着书写的文字,而那些书写不再是标题,也不再是解释,而是这两者成为一体。按照阿尔托的说法这些文字不再只是插入在形式之中,而是让形式陷入在自身之中:“这些是写下的素描,在其中语句被插入形式之中就为的是让形式沉淀/陷入。”③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79.事实上这也使得素描与书写无法再分离,它们共同构成了作品,在德里达看来:“按照这种命令,我们将不再能够将书写与素描相分离:在其之中的书写与在其之外书写显然是在与之打交道。”④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124.因此“对于一件作品来说有着两个支撑基底”⑤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124.。这事实上是阿尔托早期在残酷戏剧的舞台上要求的“象形文字”的继续推进,在阿尔托的理解中象形文字所实现的正是图画、文字、声音以及姿势的一体化。
而有关“残酷”,阿尔托在《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中构建了这一概念,而在与素描相关的话题中,德里达指出“残酷总是在一个支撑基底上被释放出来的”⑥Jacques Derrida and Paule Thévenin,The Secret Art of Antonin Artaud,translation and preface by Mary Ann Caw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8,p.103.,可以说阿尔托将残酷戏剧的舞台重新搬到了素描之上,这种表现在其素描中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其对躯体形式的种种分解,也在于其对“支撑基底”的种种操作,正如我们在阿尔托第三次对于“支撑基底”这一概念的表述中看到的。
正如德勒兹所指出的,在阿尔托那里被上帝窃取的身体便是“无器官身体”⑦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287页。,同时其在《千高原》中对“无器官身体”的可能模型进行演绎⑧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在德勒兹看来“无器官身体”仅仅是力量的集合,而其反抗的并不是器官而是有机体的组织;而学者巴克则指出了“无器官身体”与“支撑基底”的关联:“如果我们将支撑基底看作主体/支撑+投射物,看作一种力的集合,它事实上便是一副无器官身体,一种未被组织的无秩序的航线……。”①Stephen Barker,“Subjectile Vision:Drawing On and Through Artaud”,Parallax,2009,Vol15,no.4,http://www.tandf.couk/journals,DOI:10.1080/13534640903208859,p.25.也就是说可以将阿尔托“咒语”系列中那些烧穿的孔洞看作德勒兹所说的“逃逸线”,而那被刺穿的“支撑基底”则是对“无器官身体”的寻求。事实上在阿尔托的素描以及素描文本中其也表达了对于一副身体的寻求:“这种素描是对一副身体的寻求……”②Antonin Artaud,Oeuvres complètes XVIII,Paris:Gallimard,1956ff,p.75.,但“无器官身体”的概念要在1947年他的名为《为了上帝审判的终结》的广播稿中才首次出现,而在其谈论素描的文本中涉及到的是不同于“无器官身体”这一概念的另一种表述,那便是“深渊—身体”:“好像它也是一副身体,并且好像阿尔托也是一副身体,不是观念,而是身体的事实,并且是那空无之物应该是身体的这一事实,应该是脸的无底的深渊,是无法通达的表面层级,正是通过这个层级,深渊的身体被揭示……这副深渊—身体……。”③Antonin Artaud,Oeuvres complètes XIV,Paris:Gallimard,1956ff,pp.146-147.这种身体观念首要涉及的是表面或者表层,正如德国艺术家奇奇·史密斯在访谈中谈到的,她受到阿尔托影响之处便在于阿尔托对于面容的理解,面容的皮肤是像一个包裹一样有待打开的。④Antonin Artaud:Works on Paper,Edited by Margit Rowell,New York:The Museum of Modern Art,1996,p.145.相对于“无器官身体”,“支撑基底”更多地将我们带向的是对于身体之表层的思考,这也使得身体本身成为如一张画布般的存在,画布成为如身体之皮肤般的存在。
德里达之所以将阿尔托称为杜尚的同时代人,则是因为阿尔托对于艺术、艺术作品以及艺术史乃至博物馆的挑衅性态度。在德里达看来阿尔托那里有着三重的反对形式:“辱骂宗教式的诅咒、所呼求的控诉、充满激情的指控,有时所反对的是这种人们称为艺术的事物,有时是作为艺术作品的作品,有时是作为历史、神圣历史以及艺术的基督教历史的历史。”⑤Jacques Derrida,Artaud le Moma,Paris: Éditions Galilée,2002,p.85.
阿尔托通过自身的作品向既有的艺术形式与规则进行宣战,首要涉及到的便是阿尔托最后一个时期的肖像作品。在德里达看来这样的宣战首先是通过面容开始的:“这种反对艺术作品之历史的战争——我们已经读到——是以一种思想的名义引领的,必须说那是一种面容的经验。正是以面容的名义,阿尔托宣战……。”⑥Jacques Derrida,Artaud le Moma,Paris: Éditions Galilée,2002,p.85.阿尔托对于面容的思考可以在其肖像画中看到,而同时正如其在文字中所表述的:“这也就是说人类的面容还尚未找到他的面孔。”⑦Antonin Artaud:Works on Paper,Edited by Margit Rowell,New York:The Museum of Modern Art,1996,p.94.那么可以说其肖像画上的面容所展现的必然是超出人类史之外的面孔,而任何艺术史中也不会有对这种面孔的囊括,对艺术史的反抗首先在于超出既定的艺术规则以及诸种艺术史中沉积的话语的脉络。在阿尔托那里面容被表述为“一种空洞的力”,而在德里达的表述中则将阿尔托对于面容的经验称为“深渊”,它尚未被建立,关于面容的真理也有待被给予,而这样的仍然有待给予的真理,在德里达看来:“那足以切断艺术史中的那些重要的形象,一方面是具象绘画的写真主义下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是一种抽象绘画。阿尔托所要进行的正是与这种艺术史之间的决裂。”⑧Jacques Derrida,Artaud le Moma,Paris: Éditions Galilée,2002,p.62.那也便是说既不走向现实主义对面容的再现,也不走向抽象艺术对面容的完全抹消,而是重新发现一种在历史中尚未存在过的面容。而这种思考在抽象绘画与具象绘画的顶峰都已经过去而艺术陷入危机的今天,仍然有着启示意义。
阿尔托关于此一概念及其从此出发对于素描的思考与实践,事实上涉及到了对现代艺术根基的思考,那主要体现为以“支撑基底”为出发点来反对艺术、艺术话语的既有建制,同时可以说阿尔托开启了对基底的破坏性处理,特别是开创了用火在画面底基上烧穿孔洞之方法的先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里达对于阿尔托与杜尚的“同时代人”之宣判才有效。
可以看到德里达对“支撑基底”这一概念的演绎中所涉及到的问题贯穿了阿尔托的思想整体,阿尔托的“支撑基底”这一概念,一方面与其早期的“残酷”以及更晚期的“无器官身体”这两个概念有着诸多关联,另一方面这一概念是在这两个概念产生的时期之间存在的,它有着自身独立的、重要的价值。德里达对于阿尔托这一概念的继续演绎在三个方向上给出了关于艺术的新启示:首先,“支撑基底”的接纳性使得诸多操作可以在其上展开,如“抛投”“刺穿”“烧灼”“刮擦”等等,这事实上都是对于艺术中基质的处理,不论是雕塑的底座、绘画的框架与画布,还是博物馆供以展示的墙壁,都在其所涉及的范围之内,同时它也为我们指明了基底对于这种种操作的抵抗性力量的存在,从而显示出一种行动者与承载者之间的张力;其次,这一概念的独特之处还在于虽然它与“身体”这一概念有诸多关联之处,但不同于“无器官身体”,它所涉及的更多是“表面”与“表层”,带给我们更多是关于表层以及平面空间的感受方式,同时也使画面之基底与身体之皮肤有着隐喻性的关联;最后,从这一概念出发涉及到的是对艺术史以及艺术理论中处于“底层”位置的因素,也就是说对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因素的重新认识,在指出这种以往建构方式的同时,试图通过摧毁性的操作进行翻转并形成新的艺术模式。
结 语
综上所述,正是阿尔托重新唤醒了西方艺术史中“支撑基底”这一古老的概念,德里达重新演绎而不是解构了这一概念,那也就是说他从阿尔托所唤醒的这一概念出发进行了延伸和扩展。可以说德里达对“支撑基底”这一概念的演绎为我们理解现代艺术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路,为我们的艺术批评话语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同时其对这一概念的演绎并不全面,仍然留有值得继续挖掘的空间,例如德里达只是用“Khora”这一概念来阐释“subjectile”这一概念,并没有阐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同时在德里达的阐释中涉及到了对身体“表面”或“表皮”的独特思考,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展开;另外也有必要进一步探明德里达与于伯尔曼对这一概念的阐释的异同。
——探讨解读阿尔托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