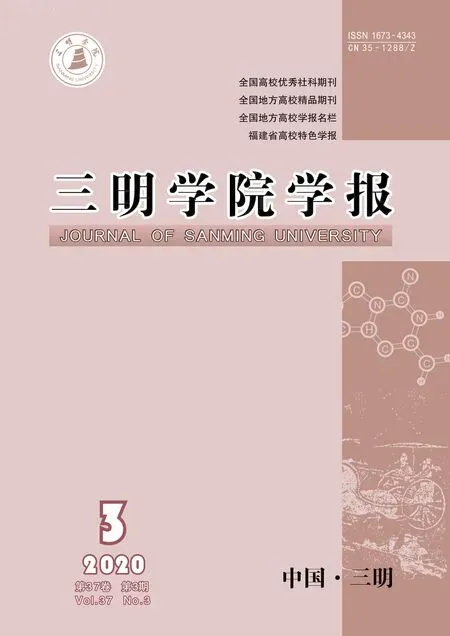文学教育视角下朱熹诗文选本编纂理念及其影响
梁桃英,邱光华
(1.三明市闽学文化研究中心,三明学院 海外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2.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文学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前代文学作品的整理和注释上,还体现在其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上,这两方面的卓越成就,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朱熹文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呈现出不断深化和渐趋拓展的演进态势,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在这当中,对朱熹文学教育方面的研究,整体而言较为薄弱,仅有少数几位研究者注意到其文学活动所蕴含的文学教育意识、文学教育观念或所具有的文学教育意义,如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的相关章节以及李路芳《文学评论中的朱熹文学教育思想》、张鹏宇《论朱熹童蒙文献的文学教育意义》;而朱熹诗文选本编纂方面的专门研究,则更为缺乏。鉴于此,本文选取文学教育这一观照视角,对朱熹的诗文选本编纂理念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对其在朱子后学中的影响接受情况略作梳理。
一、朱熹的诗文选本编纂活动及其文学教育旨趣
朱熹编选的诗文选本,可知者有《昌黎文粹》《欧曾文粹》《楚辞后语》。《昌黎文粹》,即韩愈文章之选本,今佚,刊刻传布情况不详。据王柏《跋昌黎文粹》一文披露,是集选入韩文三十四篇,朱熹意在以此“惠后学”。[1](P200-201)《欧曾文粹》,即欧阳修、曾巩二家文章选本的合集,今佚,刊刻传布情况不详。据王柏《跋欧曾文粹》的描述,该编分为上集和下集,共六卷,选文合计四十二篇,显然也有基于“惠后学”的考虑。[1]((P202)《楚辞后语》是《楚辞》作品的选编本,乃本于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所录作品而加以增删和评注。该书生前未及完稿,后由其子朱在整理并于宋嘉定十年(1217)刊刻单行,凡六卷,已佚,今有《楚辞集注》本。[2](P21-23)据莫砺锋先生的研究,朱熹所删汰者是他认为“辞有余而理不足”的作品,增补者则是在思想内容或精神内涵上与屈赋一脉相承的作品。[2](P290-296)可见,该书是对前人所编《楚辞》作品选的“再编纂”,体现了朱熹在选文经典性方面的理解和要求。
此外,朱熹还曾计划编选一部通代的诗选。在写给门人巩仲至的一通书札中曾披露说:“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答巩仲至(第四书)》)[3](P7)后因专心致志于经学事业,无暇将此设想付诸实践。从朱熹这里所作的描述来看,该计划编纂的选本分为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各为两编,并拟按照一定的价值梯次加以编纂。
在朱熹看来,熟读前人经典作品并加以模仿,是培养文学趣味、习得写作技法的重要途径。他指点弟子说: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4](P3321)
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4](P3306)
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5](P3333)
重视学习经典,这是朱熹学术实践的重要特点。他广泛评骘文学史诸诗人作家作品,并严加择取,编纂成集,以之作为阅读和研习的范本,这当中蕴含着与其学术理念相为表里的文学教育旨趣。据前述王柏所撰跋文,朱熹特意编纂韩、欧、曾三家“文粹”,以授门人弟子;他在与门人巩仲至说诗论文之际,通过陈述其有关诗选编纂的构想,为后学指明诗学境界之所在以及效仿、取法的对象范围。凡此,皆有其文学教育上的考虑。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指向。
朱熹秉持“诗言志”的诗歌本质观,主张以“志”作为衡量诗人诗作的基本准绳。《答杨宋卿书》云:“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6](P5)诗歌作品的境界,根本上取决于作者情志趣尚之高下;因此,对于学诗者而言,应首先致力于以“德”为核心的情志涵养。考虑到“诗言志”在历代儒家学派文学观念中的基础地位,循此可知,朱熹编纂诗文选本,从文学教育层面来看其实也是以涵养情志为首要之务。在朱熹认为,孔子所编订的“诗三百”,正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为后世文学选本的编纂树立了高标。这在《诗集传序》对“诗所以为教”的论说上便可看出,有云: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7](P304-305)
孔子基于垂世教、正人心的价值诉求,对其时之存世诗作进行汰选、编订,其所关切者在于学《诗》者能循此而得性情之正。由此可见,在朱熹这里,“志之所向者”其内涵侧重于心性义理涵养,也即以“诚意”“正心”作为文学教育的最终归宿。
朱熹编纂诗文选本,文学教育上的又一指向是借此体认历代诗文典范的格调和法度。
他在《答巩仲至(第四书)》提及昔日有关诗选编纂的计划时明确说:“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3](P7)之所以严于去取,是想保证入选作品的格调,因为,学习者对此的涵濡体认是造就诗歌创作高远境界的重要前提。而要达成这一境界,还需体认其法度。对于巩仲至所言“潄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澹”,朱熹一方面肯定此为“极至之论”,另一方面又强调“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云云,这实际上是将辨识法度并取法乎上视为学诗的正途。他所计划编纂的诗歌选本,显现出宏阔的诗史视野,而其中各阶段诗人诗作之价值梯次的划定也是以法度的古今嬗变为重要依据。
《昌黎文粹》《欧曾文粹》二书的具体编纂情况已无从查考,但据《答巩仲至(第四书)》可推知也是注重选文的格调、法度及其示范意义。在书札中,朱熹论及巩仲至的记体文,在肯定其“甚健,说尽事理”之后,明确提出还应以欧、曾二家文章法度作为参照,润色打磨,从而实现“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这样一种格调境界。他在其他场合下的相关论说,与此可相印证。如评韩文,所谓“高古”“庄敬平易”等,侧重于格调;“文从字顺”“反复曲折,说尽事理”“语意连接,文势开合”,侧重于法度。[8](P376、474)又如评欧文,所谓“敷腴温润”,侧重于格调;“纡余曲折,辞少意多”,侧重于法度。[4](P3308-3309)而格调与法度其实相为表里,因此他站在文学习得的立场,为学习者指示门径说,“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间文章自会高人”[4](P3301),也就是主张熟读范文,经由对古人文章法度的体认和摹拟而渐臻于其格调境界。
二、朱熹诗文选本编纂的审美趣尚
朱熹将德性情志与格调法度作为其文学教育的两个基本面向。以此为观念前提,其诗文选本编纂也蕴含着相应的审美趣尚。
朱熹将韩文和先秦、西汉的文章相提并论。从中,我们可看出他推许韩文之所在。《论语》《孟子》,“平易而切于日用”(《答赵佐卿》)[9](P34);《孟子》,“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10](P2630);《荀子》,“诸赋缜密,盛得水住”[4](P3299);《庄子》,“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11](P2992)。战国文字“有英伟气”,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西汉,如司马迁《史记》,文风“雄健”,“有战国文气象”。[4](P3297-3299)在他看来,“韩文力量不如汉文”,但“议论正,规模阔大”[4](P3302),且其“文气笔力之盛,关键纪律之严”以及“文从字顺”“庄敬平易”“说尽事理”等特征[8](P376、474),可谓接续了先秦诸子及《史记》的文风,堪称典范。可以想见,《昌黎文粹》所选韩文,当是以此为其价值指向,王柏在跋文中即曾指出其中的选文在“体致气韵”“议论规模”方面皆出类拔萃。
朱熹对欧阳修、曾巩之古文经典的建构,也不仅仅体现在《欧曾文粹》的编纂,同样体现在其具体的批评论说上,二者实可并置互观。如:
欧公文子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4](P3308)
欧公为蒋颖叔辈所诬,既得辨明,《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无些窒碍,此文章之妙也。[4](P3308)
六一文一倡三叹。[4](P3308)
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4](P3309)
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辞严而理正。[12](P26)
于欧阳修之文,朱熹所推许者,一是立论正大且雄辩有力,二是情志表达平易畅达而又纡徐委婉、自然蕴藉,前者如《朋党论》,后者如《醉翁亭记》;于曾巩之文,所推许者,主要是议论平正、文字峻洁谨严,如其一些“拟制”之作,可与三代的诰书相媲美。《欧曾文粹》中的选文,当是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观察与趣尚,王柏在其跋文中即曾述及上文所称引的朱熹有关欧、曾二家文章的一些批评论说意见。
朱熹计划编纂的通代诗选,据《答巩仲至(第四书)》的描述,拟收录的作品,除“《三百篇》”、《楚辞》外,至少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史诸书所载韵语,《文选》中的汉、魏古诗以及郭璞、陶渊明的诗作;二是晋、宋间颜延之、谢灵运以来直至唐初诸人的“近于古”的诗作;三是沈诠期、宋之问以来直至当下诸人的“近于古”的诗作。由于这一计划未及付诸实践,详细的选目设想整体上无从知晓,但从他在自注中所例举的部分篇目及所披露的意见,仍可大概获知其选诗的趣尚,有云:
且以李、杜言之,则如李之《古风》五十首,杜之“秦蜀纪行”、《遣兴》《出塞》、《潼关》、《石濠》、《夏日》、《夏夜》诸篇。律诗则如王维、韦应物辈,亦自有萧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细碎卑冗,无余味也。[3](P7)
这里所胪列乃朱熹肯认的“近于古”者。结合他对诸人的评论,可明确其实际内涵。评李白《古风》,谓“多少和缓”“从容于法度之中”。[5](P3325-3326)李白的主导诗风是豪迈奔放、雄浑峻拔,而《古风》组诗却迥异于此。朱熹在论诗之际着意借此指出李白诗“不专是豪放”“非无法度”,显然更为推崇此类雍容雅正的诗作,因而其诗选编纂计划中也便有了相应的选目。杜甫晚年移居夔州后所作诗,黄庭坚推崇备至,谓“不烦绳削而自合”“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一、之二)。[13](P322-324)自其首倡,宋代以来诗学界普遍奉此为定论。朱熹则对此不以为然,谓“自出规模,不可学”“郑重烦絮”,指摘其自出机杼而未遵循传统的诗歌法则,率意挥洒以至于词意繁琐;他称赏的是杜甫夔州以前诗,尤其是早年自秦州入蜀期间所作诗,因为其合乎“选诗”的法度。[5](P3324-3326)从上文所引自注中例举的杜诗篇目来看,其编选设想体现了这一批评意见。韦应物、王维诗,具有“萧散之趣”,显然在其编选之列。不过,朱熹于二家仍有所轩轾。他认为韦诗高于王诗,因其“无声色臭味”。[5](P3327)这表明他特为标举的是“高雅闲澹”一格的诗作。如,评《寺居独夜寄崔主簿》诗“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二句,有云:“此景色可想,但则是自在说了……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5](P3327)韦诗的“自在”,在美学趣味上和汉魏古诗、陶诗有一脉相承之处,故为朱熹所极力推崇,可以想见,此类诗作当是其诗选编纂计划中的一个趣尚。唐代诗人韩愈、卢仝虽被视为诗风险怪一派,实则不乏平易晓畅之作。朱熹评韩诗,谓“冲口而出,自然奇伟”[8](P398);评卢诗,谓“句法虽险怪,意思却是混成底气象”,并明确提倡说:“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5](P3327-3328)无疑,其诗选编纂计划若涉及该诗派,也当倾向于择取这一类诗作。
朱熹对宋代诗人诗作的评议,也表现出同样的趣尚。评杨亿诗,谓“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肯定其工巧而不失自然深密。[5](P3334)评欧阳修诗,对于其平易晓畅而又抑扬婉转、温润雄健的《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极为推崇,称之为“第一等好诗”。[5](P3308)评石曼卿诗,拈出《筹笔驿》诗“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及《金乡张氏园亭》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一再称叹其“雄豪”而“方严缜密”。[5](P3329)评梅尧臣诗,谓“不好底多。如《河豚》诗……只似脱了衣裳,上人门骂人父一般,初无深远底意思”,即鄙薄其发露叫嚣、了无余味。[5](P3334)但对其“闲暇萧散,犹有魏晋以前高风余韵”的一些诗篇则颇为肯认。[3](P3)评苏轼、黄庭坚诗,谓“只是今人诗。苏才豪,然一滚说尽无遗意。黄费安排”。[5](P3324)评陈与义诗,也将其定位为“今人诗”,谓“直是一直说将去”。[5](P3330)在前文所引答巩仲至书札自注中,朱熹也专门论及“今人诗”,谓“细碎卑冗,无余味”。在他看来,苏、黄、陈诸人诗普遍有此弊病,这些诗作大多应该不在其诗选的选目计划之列。不过,在江西诗派中,黄庭坚的“善叙事情”、陈师道的“雅健”也为朱熹所肯认。[5](P3334)对于其时诗坛,朱熹极为推重陆游,将之列为第一流诗人,谓“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并例举其诗篇加以评议:“初不见其著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自已”(《答徐载叔》)。[14](P11)由此可以推测,陆游的诗,尤其是这类近于陶诗格调的作品,在朱熹的诗选计划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从上述作家作品批评可以看出,朱熹对于唐宋律诗,倾向于标举体现了古诗传统的作品,倡扬自然闲雅、平淡深邃的诗风。在这当中,《诗经》《楚辞》和汉魏晋古诗,最为楷式。关于前者,他编撰有《诗集解》《诗集传》《楚辞集注》《楚辞辨证》《楚辞后语》,蕴含了深邃高远之旨趣,而借此发掘、建构诗学传统亦属题中之义。关于后者,他早年学诗即曾以《文选》中汉魏古诗、陶渊明诗、谢灵运诗等作为范本而加以模仿。在他的诗选编纂设想中,《文选》汉魏古诗、郭璞诗、陶诗,和《诗经》《楚辞》一并被作为“诗之根本准则”,处于价值梯次的最高层级;颜延之、谢灵运以来直至唐初以前,那些承接了汉魏古诗传统的诗作,处于第二层级;从沈诠期、宋之问以来,直至当下,部分“近于古”的诗作也可占一席之地,与第二层级的诗作一并作为“羽翼舆卫”,至于那些“无复古人之风”者,则皆摒弃不录。这与其诗史批评所体现出的审美趣尚是一致的。
三、朱熹诗文选本编纂理念的影响与接受
朱熹的诗文选本编纂理念为其后学所接受、承纳,对他们的选本编纂实践以及诗史叙述与批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朱熹的再传弟子,南宋福建著名理学家真德秀尝编选《文章正宗》,试图借以确立合乎理学价值取向的诗文典范。在《文章正宗纲目》总论中,真氏主张诗文学习者应以“穷理而致用”为归宿,作为文学教育重要载体的诗文选本,相应地也应能够让学习者在“文辞之多变”的文学发展史中“识其源流之正”;为此,他还明确提出其选录标准,即“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7](P378)这一指导思想,与朱熹的诗文编选理念可谓一脉相承。尤为突出的表现是《文章正宗》“诗赋”一门的编纂。《文章正宗纲目》“诗赋”条,真氏在称引朱熹《答巩仲至(第四书)》中有关诗史“三变”的论述及其诗选编纂设想之后,明确说道:“今惟虞夏‘二歌’与‘三百五篇’不录外,自余皆以朱文公之言为准,而拔其尤者,列之此编。律诗虽工,亦不得与。若箴铭颂赞、郊庙乐歌琴操,皆诗之属,间亦采摘一二,以附其间。至于辞赋,则有文公《集注》《楚辞后语》,今亦不录。”[7](P380)真氏在《文章正宗》诗歌选录上的要求,几乎完全遵循了朱熹关于诗选编纂方案的设想,而他对于“性情心术”这一价值取向的强调,也与朱熹编纂诗文选本的文学教育旨趣相呼应。
朱熹的三传弟子,宋元金华学派的第二代中坚王柏著有《可言集》,前后集二十卷,专以评诗,已佚。据方回《可言集考》一文披露,该书前集七卷,前三卷“取文公文集语录等所论‘《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诗之教之体之学,而及于《骚》”,后四卷“取文公所论汉以来至宋及题跋近世诸公诗”。[15](P275-276)由此可知,朱熹的诗学观念及其诗歌选评的趣尚亦为王柏所尊奉。
王柏门人,金华学派的第三代中坚金履祥选录理学家诗,编集为《濂洛风雅》六卷,卷一为四言古诗,卷二为杂言古诗,卷三为五言古诗,卷四为七言古诗及五绝、五律,卷五、卷六分别为七绝、七律,体现出以古体为尊的诗学趣尚;而其文体分布所隐含的价值秩序观念,渊源亦在朱熹《答巩仲至(第四书)》。该书选目的编排者唐良端在其所撰序文中也透露了个中消息,有云:“断取诗、铭、箴、诫、赞、诔四言者为风雅正体,其楚辞、歌操、乐府韵语则为风雅之变体,其五七言古风则风雅之再变,其绝句、律诗则又风雅之三变矣。”[16](P1)他描述的风雅之“三变”,正是该书选目排比条次的观念依凭之所在,这与朱熹的诗史“三变”论及其对诗史各阶段诗作的层级界定虽不尽相同,但前后之间的承袭脉络仍清晰可见。
宋末元初尊崇朱子之学的著名诗学家方回,在《又跋冯庸居(恪)诗》一文中将诗史的源流演变划分为三个段落,其一是以《诗经》为楷式的“古之所谓诗”,其二是以“建安四子”、陶渊明及李白、杜甫、陈子昂、韦应物、韩愈、柳宗元等诗人诗作为典范的“后世之所谓诗”,此二者皆为他所推重;其三是以西昆体诗人和四灵、江湖诗人为主流的“近日之诗”,此则为其所鄙薄。[15](P218)这一叙述框架,显然于朱熹的诗史“三变”论多有汲取;方回的褒贬抑扬态度,也显现出和朱熹大抵一致的价值取向。朱熹《答巩仲至(第四书)》提出“古今之诗,凡有三变”,并将历代诗作归纳为“三等”,据以确立选文篇目,其着眼点主要是诗歌的体式和法度。方回于此也加以借鉴,其《俞伯初诗跋》即曾概括说:“诗三体:唐虞三代,一也;汉魏六朝,二也;唐宋始尚律诗,三也。”[15](P209)以诗之“体”的历史演变为线索,分疏古今之诗,明显承纳了朱熹的意见而略有调适。又如,《婺源黄山中吟卷序》一文提出的“沈、宋始概括为律体,而古体自是几废”这一论断,即此前朱熹所言“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而他推重陈子昂、元结、韦应物、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诗人的古体诗创作,将之视为汉魏晋古诗传统在唐代的承续,这也契合于朱熹所谓“近于古”的选录原则。[15](P94)此外,方回还曾专门以《文选》为中心,选评颜、鲍、谢诸人诗,由此揭示汉、魏、晋古诗创作的源流正变之线索,并标举建安诸子诗及陶渊明诗所缔造的审美范型。朱熹在《答巩仲至(第四书)》中将颜、谢视为古诗创作体式之承转沿革的关键性人物,将《文选》汉魏古诗、陶诗作为其诗选编纂设想中的典范作品。两相对照,再考虑到方回对朱熹诗学的推崇态度,可以想见其间的承接关系。
朱熹在人文教化实践中,不仅注重讲解儒家经典、探讨性理之学,也重视文学教育,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广泛评骘文学史诸诗人作家的作品,甚或严加择取、编纂成集,从而为后学提供阅读、学习的经典文本。朱熹对韩愈、欧阳修、曾巩诸家文章作品的选编,大抵以平正谨严、刚健峻拔为其审美趣尚;而他有关通代诗选编纂的构想,也鲜明地流露出崇尚古体以及推尊《诗经》《离骚》和汉魏晋古诗传统的审美趣尚,这与他所再三致意的文学教育层面的基本旨趣相互贯通。朱熹的诗文选本编纂理念,在其后学及尊朱诗学家那里各有相应的承传与接受,这不仅体现在选本编纂方面,还体现在诗史叙述与诗史批评方面,借此或可增进对于理学文化语境下的诗学话语以及宋末元初有关理学与文学之间关系论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