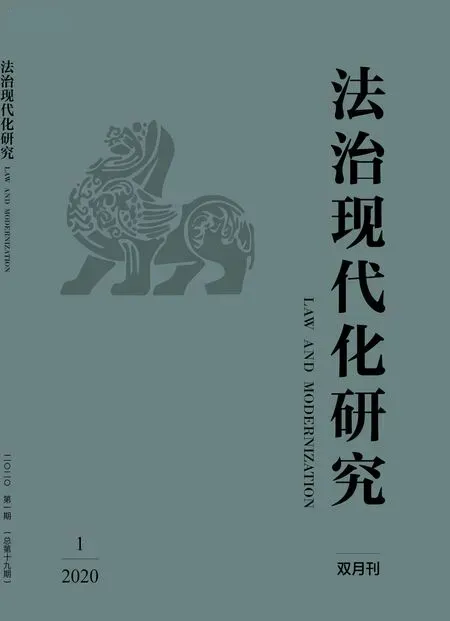加拿大央地立法事权冲突解决标准及其借鉴意义
张 鹏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是关系国家权力界分与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国内现有研究聚焦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中由分工型向分权型的转化,但将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划分与财政事权划分混为一谈,并且认为财政事权划分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关系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否则,分权就没有任何意义”。(1)叶必丰:《论地方事务》,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然而,考察域外司法实践可知,植根于三权分立基础上的宪法决定了加拿大、美国等联邦制国家央地立法事权的划分,直接决定着央地政府的财政事权,与我国立法事权和财政事权划分“两步走”的构建路径大相径庭。并且,即使是联邦制国家宪法就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作出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央地立法事权仍有可能发生冲突。以加拿大为例,《1867年宪法》第91条和第92条分别就联邦与地方不同立法事项进行了列举:第91条规定了联邦议会所拥有的31项立法事权;第92条则将15项事权归入地方立法机关的权限范畴。立宪者明确上述立法事项之间是互斥关系。但是,150余年以来,联邦与地方立法还是在双方立法事权的划分问题上纠纷不断。(2)参见Dwight Newman, “Canada’s Re-Emerging Division of Powers and the Unrealized Force of Reciprocal Inter jurisdictional Immunity”, Constitutional Forum, Vol. 20, No.1(2011).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形成了解决联邦和地方立法事权纠纷的三重标准——合宪性标准、跨司法权豁免标准、至上标准,为央地立法事权冲突之解决构建起有效的解决机制。
一、 合宪性判定标准
鉴于联邦与地方立法可能分别从不同事权角度出发共同规制同一调整对象,立法合宪性的判断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双面原则,承认双方的有效性。例如,在地方立法对证券市场的主体登记、证券交易作出规定的同时,联邦将发布虚假招股说明书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立法同样有效。(3)Smith v. The Queen, [1960] SCR 776, 1960 CanLII 12, pp. 781-782.但与此同时,加拿大司法审查采用了“核心和要旨(pith and substance)”原则来区分立法的主导目的(dominant purpose)和附随效果(incidental effects),并以前者对立法加以定性。联邦或地方任何一方立法的附随效果触及对方立法事权的,并不影响该项立法合宪性的判断;(4)Canada Attorney General v. PHS Community Services Society, [2011] 3 SCR 134, 2011 SCC 44,p162.但若构成有色立法,即从表面上来看归属中央或地方立法权限范畴,但其所追求的实质立法目的和立法效果却落入了对方的事权范畴,则将被判定无效。
立法目的和立法效果成为上述两项判断的核心要素。立法目的的考察对象包括法律文本的前言、目的条款等直接证据,以及立法机关的立法议事录等间接证据。立法效果则被区分为法律效果和实践效果两类:法律效果是指立法作为整体对法律受众的权利和义务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其往往直接体现出立法的主导目的;(5)R. v. Morgentaler, [1993] 3 SCR 463, 1993 CanLII 74, pp. 482-483.而实践效果则是指立法在实施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副效应。立法效果对于立法目的而言具有印证作用:即使某一立法目的并未得到立法者明确宣称,但该立法所产生的立法效果一旦能够印证立法者潜在追求的社会或经济目的,则立法目的的认定将超越立法者自身的声明。(6)Kitkatla Band v. British Columbia Minister of Small Business, Tourism and Culture, [2002] 2 S.C.R. 146, 2002 SCC 31, p171.“加拿大诉摩根泰勒案”被公认为“核心和要旨”原则的适用范例,确定了前述判决标准并被最高法院沿用至今。该案的争议焦点是:新斯科舍省制定的《医疗服务法》中禁止在公立医院以外的其他私人机构接受堕胎服务的规定,是否超越了地方立法权限。最高法院判定,《医疗服务法》所追求的立法效果同时涉及联邦和地方立法事项两个方面:既包括防止医疗服务私人化(医疗服务归属于宪法第92条第7项规定的“本省建立、运营、管理医院等机构”的地方立法权限),又包括对违法实施堕胎手术者处以刑事处罚(刑事处罚规定于宪法第91条第27项属于联邦立法权限)。当立法效果模棱两可,立法主导目的的辨明就成为定性的关键。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一致判定,该省所主张防止医疗服务私有化之立法目的并无可靠依据:第一,该法草案最初版本并未明确规制医疗服务私有化;第二,私人诊所的医疗水平完全可以媲美公立医院,没有证据证明私人诊所会对女性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第三,立法时并无任何有关私人诊所服务质量和效率的记录;第四,私人诊所开展的相关服务并不会导致省政府医疗费用的增加。因此,最高法院认定,该省出台《医疗服务法》的主导目的是将在公立医院以外的堕胎行为界定为不可欲之社会行为,除此以外的其他目标——包括对于医院或者医疗服务的管理、孕妇的安全和健康考虑、医疗保险、医院和医疗行业的规制等,皆为附随效果。易言之,该法主要是从公共过错和公共犯罪的角度来规制堕胎行为,并非从医疗卫生角度来加以规制。(7)See note ⑤, p513.由此,最高法院将该法定性为刑事立法,属于联邦立法权限,该省立法因越权最终被判定无效。(8)Ibid, pp. 494-516.
附属效力原则,则是挽救本应被认定为无效的具体条款。其与附随特征判断的区别在于:附随特征重在法律文本整体主导特征的判断,不得因其附随效果超出了立法主体的权限就被判定为无效;而附属效力原则重在挽救个别条款。附属效力原则的判断标准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其一,判断争议条款是否超出立法机关权限范围以及对央地立法机关的相对方权限造成侵蚀的严重程度。衡量要素包括:该条款的性质是单独能够提供诉因的行为调整规范还是单纯的法律责任规定;该条款的适用是否受到同一法律文本中其他条款的限定;宪法是否禁止该条款的立法机关创设相关规定。其二,判断争议条款所在立法体系是否构成有效规制体系。认定要素包括立法是否构建起明确有效的行为调整规范、清晰的程序性规定、以及相应的救济机制。(9)General Motors of Canada Ltd. v. City National Leasing, [1989] 1 SCR 641, 1989 CanLII 133, pp. 674-676.其三,判断争议条款是否属于该立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该判断根据对立法相对方权限侵蚀的严重程度而采用不同标准:若侵蚀程度较低,则仅要求争议条款与立法之间形成作用关系(functional relationship);而侵蚀程度较高时,则采用更为严格的真正必备(truly necessary)又称完整性(integral)标准。(10)Kirkbi AG v. Ritvik Holdings Inc., [2005] 3 SCR 302, 2005 SCC 65, p324.
二、 跨司法管辖豁免判定标准
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是指,联邦或地方的某项立法尽管在整体上有效,但其实施效果将对另一方至关重要或者对其实质的立法事项发生干预,则该项立法将被严格限缩解释至不侵犯他方立法事权的范围之内。与联邦至上标准相同的是,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同样仅仅事关立法适用效力的判断,而不涉及立法合法性的判断。
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的雏形是,有效的地方立法一旦伤害或者阻滞联邦创设企业或联邦规制企业的地位或者核心权力,则该地方立法被排除适用于该企业。纵观司法实践历史,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呈现出了审查门槛先高后低、而后又折中化的发展趋势——该标准最初的核心判断在于地方立法损害或者阻滞联邦企业的核心地位或者权力,而20世纪80年代末该标准即降为“核心部分标准”,即只要地方立法影响联邦事业管理或运营的核心部分,则该地方立法将被认定为无法适用于联邦事业,不必再行判断是否构成对联邦事业的损害抑或阻滞。正是由于《1867年宪法》为联邦和地方专门设定了立法管辖权限,因此,需要为双方立法权限的冲突创设多重预防性措施,以解决双方冲突和难以协调的难题。(11)Bell Canada v. Quebec (Commission de la Santé et de la Sécurité du Travail), [1988] 1 SCR 749, 1988 CanLII 81 (SCC), p843.但仅仅时隔一年,“核心部分标准”又增设了“直接作用”的限定,即唯有“意在直接作用于联邦事业的地方立法”方属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范畴,对联邦事业仅有间接影响的地方立法不受此限制。(12)Irwin Toy Ltd. v. Quebec (Attorney General), [1989] 1 SCR 927, 1989 CanLII 87 (SCC), p957.同时,“核心部分标准”被界定为构成联邦立法“基础性的、最低限度的、不容撼动的”调整事项。2007年,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重拾损害标准,进化为损害联邦事业核心或必备部分。“加拿大西部银行诉阿尔伯塔案”(以下简称西部银行案)中,争议焦点在于规制保险推销的地方立法是否适用于联邦银行。1991年《联邦银行法》修订后允许银行向储户推销与信用相联系的特定类型的保险。但2000年阿尔伯塔省出台《保险法》,立法目的在于建构一项许可制度,用以规制联邦银行的有关保险销售业务。最高法院判定,联邦银行保险销售业务尽管是为了保证其贷款投资组合的安全性,但银行贷款与销售保险产品应当被加以区分,保险销售并未构成联邦银行“基础性的、最低限度的、不容撼动的”固有权力,因而不能排除地方立法的适用。(13)Canadian Western Bank v. Alberta, [2007] 2 SCR 3, 2007 SCC 22, p57.本案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以往的规则:一方面,区分影响与损害两种不同情形,“仅仅对联邦事业的主观或客观权利产生影响”不足以构成否定地方立法适用性的标准。另一方面,不再采用对联邦事业的直接与间接效果的判断。(14)See note , p39.2010年以来,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中的损害要求进一步提高,被严格限定为严重妨碍或者损害联邦权力,但不要求达到致使联邦权力瘫痪的程度。(15)Quebec (Attorney General) v. Canadian Owners and Pilots Association, [2010] 2 SCR 536, 2010 SCC 39, pp. 554-555.
与联邦至上标准中联邦享有的单向压倒性优势不同,在跨司法豁免标准中,联邦和地方均对宪法已明确划分的事项具有专属立法权,因而具有双向作用力。在司法实践中,航海、港口、跨省铁路、联邦通信设施、土著居民保留地等事项,均依据跨司法豁免标准被判定为联邦专属立法权限。但自2007年西部银行案宣判以来,跨司法豁免标准被严格限缩,仅仅适用于先例确认的立法事项。加拿大最高法院的顾虑在于:首先,联邦和地方立法对同一事项均享有立法权,是加拿大在未来的法治发展中必须加以立法规制的问题,而跨司法豁免标准显然与之相互冲突;其次,该标准与联邦体制下不同政府间的相互协作存在固有张力;最后,该标准易导致联邦和地方政府均不愿就特定事项展开立法,因而产生法律空白地带。(16)Canada Attorney General v. PHS Community Services Society, [2011] 3 SCR 134, 2011 SCC 44[EB/OL]. 2011-09-30. https://www.canlii.org/en/ca/scc/doc/2011/2011scc44/2011scc44.html?autocompleteStr=2011%5D%203%20SCR%20134&autocompletePos=1,2017-12-30.以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为例,鉴于先例的缺位和医疗卫生事务的复杂程度,加拿大最高法院认定医疗卫生并非地方立法机关依据宪法第92条所拥有的专属立法事项,不可依据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主张该领域免于联邦立法的干涉。(17)See note .
三、 至上性判定标准
联邦至上性标准同样并非对于一项立法的合宪性的判断,而是对于其能否实际发挥效力的判断。在立法实践中,联邦立法权限和地方立法权限往往发生交叉,即同一立法事项既可以划归联邦立法权限,也可以划归地方立法权限。一旦联邦与地方均出台法律规范,两者在法律效力判断上均为有效,但在实际适用中将造成相互冲突,则根据至上标准,与另一方发生冲突的整部法律或者部分条款将不可被运用。一旦另一方立法效力终止,则该立法仍有适用之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1867年宪法》明文规定的至上性标准并非是联邦至上的单向标准,而是央地之间的双向至上,适用于以下情况:其一,第95条和第92A条明确赋予联邦在农业、移民、一省向其他省份出口自然资源等三种事项中具有至上效力,任何地方对上述事项的立法不得与联邦立法发生冲突。其二,第94A条规定对于养老金和福利补贴事项,任何联邦立法都不得影响地方立法的实施。(18)参见Patrick Macklem, et al., Canadian Constitutional Law (4th edition), Emond Montgomery Publications, 2010, p272.
对于宪法未曾明确的事项,至上性标准则仅仅化身为联邦至上标准,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第一,地方立法在适用上与联邦立法存在直接冲突。即两者对同一问题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导致法律受众无法同时遵守联邦和地方立法,但并不要求央地立法之间实际已经发生了冲突。(19)Saskatchewan (Attorney General) v. Lemare Lake Logging Ltd., [2015] 3 SCR 419, 2015 SCC 53, p436.第二,尽管未对联邦立法构成直接违反,但地方立法阻碍了联邦立法目的之实现。(20)Alberta Attorney General v. Moloney, [2015] 3 SCR 327, 2015 SCC 51[EB/OL]. 2015-11-13.https://www.canlii.org/en/ca/scc/doc/2015/2015scc51/2015scc51.html?autocompleteStr=2015%5D%203%20SCR%20327&autocompletePos=1, 2017-12-30.例如,在“哥伦比亚律师协会诉门格特案”中,联邦《移民法》允许非律师作为代理人出席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的听证会,然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律职业法》禁止非律师提供任何形式的法律服务,这一规定被认为同样适用于移民和难民委员会这一类行政法庭。最高法院判定,联邦立法的目的在于为外国移民和难民申请者提供可负担的、迅捷的法律服务,而地方立法则完全违背了这一立法目的,因此,地方立法被判定不可适用。(21)Law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 v. Mangat, [2001] 3 SCR 113, 2001 SCC 67, p154.至上性标准的适用并不要求联邦与地方立法之间具有实际冲突。
四、 三项判定标准之间的张力
(一) 根本取向之间的张力
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至上性标准之所以在近年来被严格限制适用,根本原因在于:联邦与地方立法之间出现重合与相互覆盖是现代联邦制无法回避的问题,创设核心和要旨标准、双面标准等正是意在顺应此客观存在而创新出的联邦体制的弹性设计,(22)See note , p36.以解决央地立法之间的潜在矛盾,促进两者之间的和谐解释与适用,(23)Saskatchewan (Attorney General) v. Lemare Lake Logging Ltd., [2015] 3 SCR 419, 2015 SCC 53, pp. 461-462.宽泛地适用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和至上性标准恰恰是对联邦制的僵化限制,不符合现代联邦制发展的趋势。
(二) 适用顺序的争议
加拿大最高法院并未明确上述标准之间适用逻辑上的推演顺序,司法实践中首先判定立法的合宪性毫无争议,但在跨司法审查豁免标准和至上性标准的适用顺序上却长期存在争议。在加拿大西部银行案中,Binnie和Lebel等五位大法官认为核心和要旨标准与至上性标准应当优先于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24)See note , p54.因为受制于先例而展开的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将使法院陷入冗长的讨论却可能无果而终。但是,有学者统计,在2007年至2011年最高法院的判例中,情况恰恰相反,跨司法管辖豁免标准完全优先于至上性标准。(25)Guy &Dwight Newman, p206.2012年以来,最高法院仍然贯彻着这一顺序,(26)See Marine Services International Ltd. v. Ryan Estate, [2013] 3 SCR 53, 2013 SCC 44; Bank of Montreal v. Marcotte, [2014] 2 SCR 725, 2014 SCC 55; Rogers Communications Inc. v. Chteauguay (City), [2016] 1 SCR 467, 2016 SCC 2.仅在双方当事人未就至上性标准提出诉讼主张时才先行对其加以分析。(27)Tsilhqot’in Nation v. British Columbia, [2014] 2 SCR 257, 2014 SCC 44, pp.310-312.这一顺序背后的逻辑在于:跨司法审查豁免标准在于判断立法的适用性,“如果地方立法都不可能适用于联邦立法事项,则不可能确认联邦立法优位于地方立法,或者判定地方立法不可被运用”。(28)See note , p69.尽管司法实践中有此倾向,但尚未有专门案例给出定论。
(三) 三项判定标准对宪法原意的违背
《1867年宪法》第91条和第92条连续使用了五处“专有”字样以区分联邦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这一区分被宪法学者称为“密闭隔舱问题(watertight compartments problem)”,并强调联邦权力的至上性:第一,宪法起草者在第91条开篇专门写明,“无论本法任何规定”,联邦议会享有第91条中规定的立法事权,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地方享有何种事权,均不可撼动联邦立法权。第二,《1867年宪法》第91条在结尾处着重强调“可被归入本条列明的事权分类的任何事务,均不应被认定为归属本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的、具有地方或者私人性质的各项专属权限”,以此明确央地之间立法权限的相互排他性。(29)Asher Honickman, Watertight Compartments: Getting Backto the Constitutional Division of Powers, 55 Alberta Law Review, 2017, 55:1, p234.最后,立法事权划分难免发生重合,但双面原则、附属效力原则等强调事权划分的自我约束性,致力于排他性地解决立法事权冲突,以及预防和减少央地立法事权的冲突。而现有立法事权纠纷解决的三项判定标准所代表的是灵活性联邦制,为立法事权的冲突大开方便之门。(30)Ibid, p250.
五、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的启发
在加拿大、美国等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宪法对于联邦与地方立法机关立法事权的划分直接决定着政府的行政权限,(31)William Araiza, M. Isable Medina, Constitutional Law: Cases, History, and Practice, New Providence: LexisNexis, 2011, p219.立法事权与财政事权具有同构性。而我国财政事权的划分在时间上晚于立法事权的划分,两者在划分模式、划分依据等方面存在差异。
(一) 我国央地立法事权与财政事权并非同一概念
我国现有研究中,对于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和财政事权的相互关系的判断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其一,以两者的同构性为前提,在联邦制国家与单一制国家立法事权宪法安排的维度中探讨财政事权划分,(32)参见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划分的理念、标准与中国实践——兼析我国央地立法事权法治化的基本思路》,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6期。即将两者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33)参见前引①,叶必丰文。其二,事权概念应在立法事权、财政事权和司法事权三个不同维度上加以区分。(34)参见刘剑文、侯卓:《事权划分法治化的中国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前一种观点实际上将联邦制国家宪法中立法事权划分的理念直接带入了我国央地财政事权划分的改革进程之中,混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从而未能意识到财政事权改革与立法体制之间的潜在矛盾。
第一,根本性质的差别。立法事权划分关乎国家立法机关之间纵向的权力配置,决定着法律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形成和演绎其他诸多央地关系的基础。(35)参见前引,封丽霞文。相比之下,从1993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到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财政事权概念总是与财权、财力、支出责任紧密联系。(36)参见前引,刘剑文、侯卓文。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用以确定各级政府的税收和整个财政收入分配体系,是“深化财税改革和建设法治财税的重要举措”,(37)前引,刘剑文、侯卓文。因而在财税体制中居于基础性地位。(38)参见徐阳光:《论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理论基础与立法路径》,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5期。央地财政事权划分的法律化并不等同于立法事权的划分。《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央地财政事权法律化的体现和结果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法”,以其推动“保障财政事权、科学合理划分责任的法律体系”的形成,而非直接同构于宪法、立法法中立法事权的划分。
第二,划分模式的差别。世界各国纵向层面的立法事权划分,以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关系、地方立法权的本质属性为标准,可主要归结为行政分工型与法定分权型两种体制。行政分工型体制主要存在于单一制国家。地方立法权力来源于中央的授权与分配,地方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权;而分权型体制则出现于合作型央地关系之下的联邦制国家,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各方均在法定权限范围内拥有专属立法权。(39)参见前引,封丽霞文。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的划分采用分工型体制,“地方立法必须接受中央立法的单方面的纵向监督”“中央与地方立法冲突的最终裁决者是中央立法主体”。(40)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法治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335页。相较而言,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则倾向于分权型体制。《指导意见》划定了中央财政事权、地方财政事权、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的不同领域,明确“地方的财政事权由地方行使”,中央对地方的财政事权履行以法律化形式提出规范性要求,从而“赋予地方政府充分自主权,依法保障地方的财政事权履行”。
第三,划分依据的差别。从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来看,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的划分,主要以立法事项的“重要程度”,同时辅以立法调整对象的性质、调整方法作为标准,而未将“影响范围”纳入其中。(41)参见封丽霞:《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重要程度”还是“影响范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财政事权的划分,自分税制推行以来,一直以影响范围作为改革和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的基本思路。《指导意见》中明确以“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受益范围”作为财政事权的首要划分原则:“体现国家主权、维护统一市场以及受益范围覆盖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中央负责,地区性基本公共服务由地方负责,跨省(区、市)的基本公共服务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由此可见,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基本采用影响范围的划分标准。
以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中央立法事权与《指导意见》明确的中央财政事权的对比为例,立法事权与财政事权划分依据的不同直接导致两者在外延上既有重合之处又有重大差别。“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等中央财政事项与“国家主权”“海关”等中央立法事项高度重合。但是,“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中央财政事项难以归入中央立法事权之中,至少需要从逻辑上作进一步地解释;而立法法第8条规定之“犯罪和刑罚”“诉讼和仲裁制度”等中央立法事项与央地财政事权的划分关联性微弱。
第四,争议解决的差别。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产生的争议,遵循宪法第5条第3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总体原则,按照立法法第5章规定的具体规则加以解决。根据立法法第88条和第95条第3款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但是,当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根据立法法第95条第2款的规定,国务院并非最终的有权决定机关:国务院提出意见,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则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而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的划分争议,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则全部由中央政府裁定。
(二)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改革对立法事权的潜在影响
由于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与财政事权并非一一对应的相互关系,中央或地方任何一方的立法事权可能与对方专属财政事权以及央地共同财政事权发生关联。如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事权所涵盖之“城乡建设与管理”一项,既涉及《指导意见》中“市政交通”这一地方财政事权,又涉及“国防建设”这一中央财政事权。另一方面,央地立法事权的对象可能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并无任何关联。例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不在《指导意见》规定的任何一项财政事项之中,但却属于立法事权的调整对象。
详言之,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均有可能介入另一方的财政事权之中。
第一,地方立法权可能触及中央财政事权。从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来看,根据是否存在上位法的标准,地方立法分为执行性立法和创造性立法(实验性立法)两类。仅以地方性法规为例,根据立法法第73条和第82条的规定,当存在上位法时,地方性法规是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属于执行性立法;当上位法缺位时,地方性法规有权就地方性事务,以及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规定的事项外、其他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事项进行立法,属于创造性立法。两者均可能介入中央立法的范畴。(1) 执行性立法实际上肯定了地方立法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而触及中央立法的事项范围,也为其深入中央财政事权留下了余地。首先,执行性地方立法中的细化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中央立法的执行平添了限制条件。例如,国防属于中央财政事权,但在立法实践中,地方性法规就国防事项作出规定的不在少数,《福建省国防动员条例》《重庆市国防动员条例》等皆是依据国防动员法制定。以后者为例,第26条对征用程序作出了补充规定:征用民用资源,应当及时向被征用组织和个人下达征用通知,对被征用的民用资源进行登记并出具凭证。其次,执行性地方立法可能与中央财政事权发生冲突。在实践中,执行性地方立法直接抵触上位法的情况并不罕见。(42)参见程庆栋:《执行性立法“抵触”的判定标准及其应用方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如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福建省台湾船舶停泊点管理办法》《福建省台湾同胞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等9部涉台地方性法规,公然涉猎国防等中央专有立法权事权。(43)参见秦前红、曾德军:《地方立法的主要问题及其反思——以湖北省为例》,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2) 创造性地方立法同样可能介入中央财政事权。有学者以《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的制定为例,指出:由于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和权限交叉重叠,涉及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等诸多法律法规,导致创造性地方立法处于怪异状态:既有创造性立法的隐形上位法作为“紧箍咒”,又无执行性立法的直接上位法。该条例最终在诸多上位法之间闪转腾挪而艰难出台,却已难以完成原定的立法目标。(44)参见沈寿文:《“分工型”立法体制与地方实验性立法的困境——以〈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为例》,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1期。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到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不难断定,国家公园应属于《指导意见》中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的中央专属财政事权的范畴,而云南省地方立法显然已介入中央财政事权之中。
第二,地方财政事权不能排除中央立法权,即中央立法权可介入地方财政专属事权。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事权与中央政府的财政事权同质化程度很高,除少数专属国务院的事权以外,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内容几乎都是国务院事权的复刻。(45)参见前引,刘剑文、侯卓文。因而,地方财政事权不可能排除中央立法权的介入。以社会治安这一地方财政事权为例,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被排除在立法供给侧之外。又如,2017年底公布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第33条第2款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具体办法。而立法法第72条第2款中规定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等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而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完全可以纳入城乡管理和环境保护的范畴。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同立法法相关规定的潜在冲突。
因此,在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中央或地方立法介入对方的专属财政事项以及央地共同财政事项的情形。此时,立法的合宪性、合法性研判既需要在立法法范围内展开,又需要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体制内展开。
(三) 介入对方财政事权构成立法合宪性的影响因素而非判断标准
与联邦制国家在宪法中为联邦与地方立法合宪性提供事权标准的单一维度不同,伴随着我国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改革并实现法律化,立法的合宪性、合法性判断面临着立法事权与财政事权两个维度的诘问。核心问题在于财政事权的划分是构成立法合宪性、合法性的判断标准还是影响因素。在笔者看来,财政事权仅仅构成影响因素。
第一,中央立法介入地方财政事权和央地共同财政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无论是立法事权还是财政事权,都应涵摄于中央统一领导即中央至上的标准之中。由此而言,中央立法介入地方财政事项具有宪法依据。接下来需要明确的问题是,中央立法在何种情况下适宜或者不适宜介入地方财政事项?在此,应当引入财政事权划分所采之影响范围标准,中央立法适宜就全国性、跨省区财政事项作出统一部署。另一方面,中央立法不适宜介入的范畴应当依据立法法和财政事权划分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凡属“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由地方提供更方便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地方性事务”,原则上不宜由中央立法统一加以规制。
第二,地方立法介入中央财政事权和央地共同财政事项。对于不同种类的地方立法,其介入中央财政事权的判断标准也不应完全相同。首先,对于有中央立法作为上位法的执行性地方法规、规章,对于符合立法法标准的地方立法,应引入双面原则,承认中央和地方立法均为有效。其次,对于创设性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合法性判断,需要作进一步考虑。(1) 财政事权改革的重要原则是“更多、更好发挥地方政府”的优势,“激励地方政府主动作为”,因此,地方立法应跳出照抄照搬上位法的牢笼,大胆地就地方事权范围内的地方性事务先行先试。尤其是针对历史上未曾出现的新鲜事物,如人工智能所产生的法律问题,应当发挥地方立法引导改革的作用。(2) 对于中央立法缺位的中央财政事项、央地共同财政事项,地方立法的介入并不必然导致违宪。如作为中央财政事项之一的全国性自然资源,“全国性”有赖于“地方性”的集合,前述《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对于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公园进行立法恰恰反映出这一问题。(3) 从宪法的调整对象与作用而言,国家机构的设置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构成我国宪法以及其他国家宪法的主要部分。从加拿大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央地政府间的紧密合作,立法事权的司法案件绝大多数并非来自政府之间权力的争夺,而是公民个人由于其权利受到立法负面影响而提起的诉讼。(46)See note ②, p1.由此而言,公民权利是央地立法事权划分的试金石。在我国中央立法缺位的情况下,涉及中央财政事项、央地共同财政事项的地方立法如果侵入“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等法律绝对保留事项,则应被判定无效。对于该类仅在法律责任部分侵入法律绝对保留事项的地方立法,应作出限缩式合宪性解释,仅仅否定前述法律责任条款的效力,而保留地方立法的其他有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