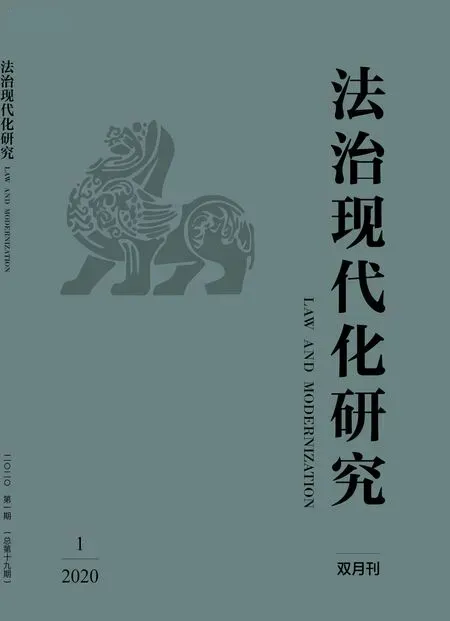论诈骗罪的欺骗行为
[日]桥爪隆 著 王昭武 译
一、 引 言
通过“欺骗他人”的行为(欺骗行为),让被害人交付财物(日本《刑法》第246条第1款),或者取得财产性利益(同条第2款)的,成立诈骗罪。(1)日本《刑法》第246条[诈骗罪]规定:欺骗他人使之交付财物的,处10年以下惩役(第1款)。以前款方法,获取非法的财产性利益,或者使他人获取该利益的,与前款同(第2款)。——译者注不过,我们也不应认为,只要是欺骗他人而使之交付了财物,就总是成立诈骗罪,仍然必须存在能够将作为诈骗罪予以处罚这一点予以正当化的法益侵害性。多数说正是基于这种问题意识,作为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要求“发生了财产损失”,试图以此来实质性地限制诈骗罪的成立范围。相反,近年的判例不是通过财产上的损失概念,而是试图通过对欺骗行为的解释,来划定诈骗罪的界限。
我个人此前曾研究过此问题,(2)参见橋爪隆:《詐欺罪(下)》,载《法学教室》第294号(2005年),第91页以下;橋爪隆:《詐欺罪成立の限界について》,载《植村立郎判事退官記念·現代刑事法の諸問題(1)》,立花書房2011年版,第175页以下。另外,本文主要想探讨近年的学说与判例的观点。这里想基于对最近的判例动向的分析,就此问题再重新做些思考。
二、 判例理论的展开
(一) 相当对价的给付与诈骗罪
被害人虽然因上当受骗而交付了钱款,但同时收到了对方交付的价格相当的财物的,此类情形是否成立诈骗罪呢?对此,既有持肯定态度的判例也有持否定态度的判例。例如,被告人明明没有医师执业证,却谎称是某医院的医师,按照药品定价,将对被害人的疾病有效的药卖给了被害人,对此,大决昭和3·12·21刑集7卷772页表述为“完全不存在对方因购买了行为人出售的药品而蒙受了财产上的非法损害这一事实”;相反,明明是市场上很容易买到的电动按摩器,却谎称一般很难买到,是对中风以及小儿麻痹等具有特殊疗效的治疗设备,并以商品定价出售给了被害人,对此,最决昭和34·9·28刑集13卷11号2993页则认为,“在即便提供的是价格相当的商品,但如果告知实情,对方就不会支付钱款的场合,尤其是就商品的效用等,告知对方有违真实的夸大事实,从而使对方信以为真,进而接受了对方交付的钱款的,应成立诈骗罪”。
上述两个案件在如果被害人知道实情就不会交付钱款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但是,在大审院昭和3年(1928年)的案件中,由于被害人想的是,购买对自己的疾病有疗效的药品,因而不管怎样,被害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相反,在最高裁判所昭和34年(1959年)的案件中,被害人正是因为想到对治疗中风以及小儿麻痹等有特殊疗效才会购买,但其目的并未达到(单纯买一个电动按摩器,对被害人而言毫无意义)。为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左右了是否成立诈骗罪。总之,对于判例的态度,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并非是只要存在若不实施欺骗行为就不会交付财物这种关系,亦即,并非是只要欺骗行为与财物的交付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总是能认定成立诈骗罪,而是还包含着从实质性法益侵害的角度限制诈骗罪成立范围的契机。
(二) 由欺骗行为构成的诈骗罪的判断
1.由举动实施的欺骗行为(举动欺骗)
可以说,作为对诈骗罪进行实质性限定的要件,近年的判例很重视“欺骗他人”行为(欺骗行为)的意义。例如,被告人命令朋友A隐瞒将自己名义的银行存折与借记卡转让给第三者的意图,向银行职员申请开设自己名义的普通存款账户,由此从银行接受了存折与借记卡的交付。案发当时,首先,根据普通存款规定,银行禁止储户擅自转让存折、借记卡等;而且,就是对实际接待A的银行职员而言,如果知道A有转让给其他人的意图,银行职员也不会答应其交付存折、借记卡的要求。最决平成19·7·17刑集61卷5号521页以这两点为前提,就此行为判定,“应该说,针对银行支行的职员,提出开设存款账户的申请本身,就已经表示了申请者本人自己使用该账户的意思,因此,明明存在将存折与借记卡转让给第三者的意思,却隐瞒这一点提出申请,这种行为就正是诈骗罪所谓欺骗他人的行为,由此接受存折与借记卡之交付的行为,显然构成《刑法》第246条第1款之诈骗罪”。
对于非法取得银行存折的情形,最决平成14·10·21刑集56卷8号679页此前曾就非法取得他人名义的银行存折的案件判定,(3)该案大致案情为:被告人出于使用非法获取的A名义的国民健康保险证,以A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并由此取得银行存折这一意图,伪造了A名义的“开设新账户客户用申请书”,并装出该申请书是真正的申请书,自己就是A本人的样子,将申请书、A名义的国民健康保险证以及刻了A的名字的印章一同交给了银行窗口的职员,使得该职员等人信以为真,并接受了该职员交付的一本储蓄综合账户存折。——译者注“银行存折不仅仅是其本身有可能成为所有权的对象,还能认定其具有利用存折进行存款与取款等财产性利益,因此,即便是以他人名义开设存款账户,进而由此接受银行所交付的存折的场合,也相当于《刑法》第246条第1款的财物,这样理解是适当的”,进而以此为理由判定成立诈骗罪。这里重要的是,即便是以自己名义申请开设存款账户的场合,如果隐瞒转让的意图而实施申请行为的,就能够被评价为由举动实施的欺骗行为(举动欺骗)。
2.属于交付之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
被告人A将共犯B名义的登机牌交给企图非法入境加拿大的外国人C,让C作为B搭乘该航班,却对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值班人员隐瞒此意图,装出是B本人搭乘班机的样子,接受了国际航线的登机牌的交付。(4)该案大致案情为:被告人A与B经过共谋,出于将登机牌交给在中转站候机的中国人C,帮助其偷渡至加拿大的目的,B把以自己名义经过正常手续购买的机票以及护照交给登机柜台,换取了登机牌。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主张,交付(发放)本案登机牌,不会由此给航空公司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以维持出入境行政管理秩序为由,将本案登机牌的交付定位为财产性处分,并不妥当。作为控诉审的大阪高等裁判所基于下述理由,判定成立诈骗罪(大阪高判平成20·3·18刑集64卷5号859页):“不具有同一性的人使用登机牌搭乘飞机,存在给飞机的飞行安全带来重大弊害的危险,会导致航空公司的社会信用的降低、业绩的恶化,并且,在本案中,如果航空公司因本公司发放登机牌的不完善,而使得登机牌的(冒名)使用者非法进入加拿大,会被该国政府科处最高额3000美元的罚款,因而,对航空公司而言,防止他人非法使用登机牌是具有极大的财产性利益的。”对此判决,被告人向最高裁判所提起了上告。——译者注对此行为,最决平成22·7·29刑集64卷5号829页指出,(1) 在交付登机牌之际,之所以要进行如此严格的本人确认,是因为如果机票上记载的乘客之外的其他人搭乘航班,存在给飞行安全带来重大弊害的危险。而且,加拿大政府也赋予了本案航空公司为防止有人非法进入该国而应该切实发放登机牌的义务,因而,在这一点上,不让该乘客之外的其他人搭乘飞机,对本案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输业务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2) 如果本案柜台的值班人员知道,要求换取登机牌者具有将登机牌转交给他人而让本人之外的其他人搭乘飞机的意图,就不会答应其换取登机牌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最高裁判所进一步判定,“从上述事实来看,要求换取登机牌者本人是否搭乘飞机,对本案柜台的值班人员而言,应该说,属于判断是否交付登机牌的重要基础事项,因此,明明具有将发给自己的登机牌转交给他人并让该他人登机的意图,却隐瞒该意图,向本案柜台的值班人员要求换取登机牌这一行为,就正是诈骗罪中的欺骗他人的行为,由此换取登机牌的行为显然应构成《刑法》第246条第1款的诈骗罪。”
在本案中,问题也在于,是否存在诈骗罪中的“欺骗他人”的行为,与前述最高裁判所平成19年(2007年)的判例以欺骗行为的样态作为问题不同,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是以欺骗行为的内容作为问题。亦即,正因为申请交付登机牌的申请者本人是否搭乘飞机相当于财物之“交付的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就这一点进行伪构的行为才被评价为欺骗行为。在本案中,被告人等是在支付了机票价款之后领取了登机牌,因而,并未给航空公司(因登机牌的交付而直接地)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按照此前的学说所关注的问题,是否存在财产性损失可能为成为讨论的焦点,但本决定以针对“判断是否交付登机牌的重要基础事项”存在欺骗为理由,判定成立诈骗罪。这一点也是值得关注的。尽管很早以来就一直在使用类似的表述,(5)指出这一点者,参见成瀬幸典:《詐欺罪の保護領域について》,载《刑法雑誌》第54卷第2号(2015年),第137页。但本决定仍然特别采取了“判断是否交付的重要基础事项”这种表述,由此来判断是否成立诈骗罪。对照那些以是否发生了财产性损失作为问题的案件而言,可以看出最高裁判所的意图在于,以该要件作为实质性的判断标准来判断是否成立诈骗罪(事实上,此后的判例也一直采取这种表述)。(6)指出这一点者,参见上嶌一高:《最近の裁判例に見る詐欺罪をめぐる諸問題》,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31号(2012年),第19页以下。
有关“判断是否交付的重要基础事项”的含义,我们也完全有可能这样解释:能够被谓为,存在如果知道该事项被害人就不会交付财物这种情况,亦即,凡是与交付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都属于这里的“重要事项”。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作出“实际的被害人如果知道实情就不会交付财物”这种判定即可。那么,对于上述最高裁判所平成22年(2010年)的判例,也理应只要就上述第(2)点作出判断即可。但判例在第(2)点之外,还特别指出了第(1)点,有鉴于此,我们就能够这样理解:不仅要求被害人的错误认识与交付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还要求重视该事项也存在客观上的法益侵害性。并且,按照这种理解,还能够推导出,存在通过判断是否属于“重要事项”,由此实质性地限制诈骗罪的成立范围的情形。
另外,在最高裁判所平成22年(2010年)的决定中,申请交付登机牌的行为本身就属于能够表明申请人本人具有搭乘该航班的意思的行为,对于能否将该行为评价为“由举动实施的欺骗行为(举动欺骗)”这一点,本决定并未作出具体判断。不过,既然最高裁判所平成19年(2007年)的判例已对此作出了判断,本案行为能够被评价为“举动欺骗”,也是理所当然的。(7)关于这一点,参见増田啓佑:《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22年度),法曹会2013年版,第186页。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对于判例就诈骗罪的理解,将其区分为欺骗行为的内容(重要事项性)与欺骗行为的样态(举动欺骗),并分别进行探讨是很重要的。下面将基于这种视角,对近年最高裁判所的判例做进一步的分析。
(三) 近年的重要判例
1.暴力团使用高尔夫球场的案件
在那些拒绝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相关设施的高尔夫球场,对于暴力团相关人员申请使用设施,并实际使用了高尔夫球场的行为,最判平成26·3·28刑集68卷3号582页否定成立诈骗罪,而同一天作出决定的最决平成26·3·28刑集68卷3号646页则肯定成立诈骗罪。下面就这两个案件分别做些探讨(依据高尔夫球场的所在地,将前者、后者分别命名为“宫崎案”“长野案”)。
首先是“宫崎案”。本案被告人是暴力团成员,与暴力团其他成员D等人一起,在本案高尔夫球场的前台,作为非会员来宾,没有虚构信息,在“来宾登记表”填写了自己的姓名、住所、电话号码等信息,并将该登记表交给前台工作人员,由此申请使用高尔夫球场设施。当时,该登记表上并没有确认是否是暴力团相关人员的栏目,球场管理者也没有采取措施让客人签字保证自己不是暴力团相关人员,也就是说,工作人员既没有确认对方是否是暴力团相关人员,被告人等也没有以自己并非暴力团相关人员这种旨趣提出虚假的申请。(8)本判决是针对申请使用两个高尔夫球场的行为,分别研究是否成立诈骗罪。不过,“B俱乐部”允许非会员来宾单独使用相关设施,相反,“C俱乐部”仅限于会员或者会员的同伴、经会员介绍者使用设施,被告人也是经会员E所邀,与E一同使用了设施。本案高尔夫球场在章程中规定,拒绝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设施,并且,还在俱乐部出入口竖立了“谢绝暴力团相关人员入内”的招牌,但并未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确认来宾并非暴力团相关人员。并且,周边的高尔夫球场大多允许或者默许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设施,并未彻底开展暴力团排除活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本判决认为,“属于暴力团相关人员的(非球场会员的)客人不告知自己是暴力团相关人员,而是和其他一般客人一样,如实填写姓名等指定事项之后,将‘来宾登记表’交给前台工作人员,由此申请使用球场设施,该行为本身只是表明,申请者会按照通常使用方法使用球场设施,使用之后会支付相关费用这一意思,而不能由此认定,除此之外还表明,申请者当然并非暴力团相关人员。这样的话,本案中的被告人以及D申请使用本案各个高尔夫球场的各种设施的行为,就不属于诈骗罪中所谓欺骗他人的行为”,进而以申请使用高尔夫球场的行为本身不能被评价为“举动欺骗”为由,否定成立诈骗罪。(9)在本判决中,判决书添附了小贯芳信裁判官的反对意见:就“C俱乐部”而言,能够评价为,由会员介绍或者带来的人不是暴力团相关人员,这一点已经由会员的使用申请所保证,因而能认定存在欺骗行为。
其次是“长野案”。本案高尔夫球场不允许暴力团相关人员入会;并且,在入会之际,还采取措施,要求对方在“誓约书”上签名、盖章,保证“本人与暴力团等毫无关系。而且,(来贵俱乐部时)不与暴力团成员同行,不介绍暴力团成员,不给贵俱乐部造成麻烦”;此外,在球场的使用章程上,也明确禁止暴力团成员进入球场与使用球场设施。共犯A在上述“誓约书”上签名、盖章之后,向球场提交了“誓约书”,从而成为本案球场的会员。被告人是暴力团成员,已经意识到长野县内的高尔夫球场对于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球场设施持严厉态度,自己有可能遭到拒绝,但受到A的邀请,在案发当时作为A的同伴,来到了本案球场。本案高尔夫球场不管是会员还是非会员来宾,都一律要求在前台在“签到本”上亲自签名之后提出使用申请。A担心被告人被发现是暴力团成员,采取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在前台,A自己先在“签到本”上签名,对于包括被告人在内的5名同伴,故意在“分组表”上将他们的名或者姓打乱互换,然后将表交给前台工作人员,再请工作人员在“签名本”上代为签名。另外,在A递交使用申请之际,球场工作人员也没有再确认同伴中有没有暴力团相关人员,A自己也没有进行同伴中没有暴力团相关人员的这种虚假的申请。
就此案件,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指出,(1) 高尔夫球场之所以拒绝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球场设施,其意图是防患于未然,是为了防止因暴力团相关人员在此打球而使得其他来宾感到畏惧,进而导致球场客流量减少以及损害球场的信誉或者等级,是从高尔夫球场经营的角度采取的措施;(2) 在本案高尔夫球场,在使用章程中明确禁止暴力团成员进入球场与使用球场设施,并且,入会审查之际,还要求会员保证不与暴力团相关人员结伴来球场,不向球场介绍暴力团相关人员,除了采取这些措施之外,还将“长野县防犯协议会”提供的排除暴力团的相关信息加以数据化,从而在预约时或者前台接待时予以确认,由此预先防止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本球场;(3) 在本案中,如果工作人员知道被告人是暴力团成员,就不会同意被告人使用球场设施。最高裁判所在指出这些情况的基础上,再基于下述理由,判定成立第2款诈骗罪:“本案高尔夫球场会员A在入会之时曾保证,不与暴力团相关人员结伴来球场,并且不向球场介绍暴力团相关人员,因而A向球场申请与其同伴一同使用球场设施,这本身就表明,A已经保证其同伴不是暴力团相关人员,而且,客人是否是暴力团相关人员,这是本案高尔夫俱乐部工作人员是否允许对方使用球场设施的重要判断事项,因此,同伴明明是暴力团相关人员,而在申请使用球场设施时却不告知这一点,该行为使得球场工作人员误以为其同伴并非暴力团相关人员,这正属于诈骗罪所谓欺骗他人的行为,因而让A订立使用球场设施的合同,并与A之间存在意思沟通的被告人使用球场设施的行为,就显然构成《刑法》第246条第2款的诈骗罪”。
在“长野案”中,在将申请使用设施的行为本身理解为“举动欺骗”的基础上,由于来宾是否是暴力团相关人员属于“作为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因此,行为人的行为被认定成立诈骗罪。在判断是否存在欺骗行为时,本决定显然是从下面两个视角来考虑问题:(1) 原本能否被谓为欺骗“行为”(“举动欺骗”的欺骗行为性)的视角;(2) 欺骗的内容能否被谓为重要事项(重要事项性)的视角。(10)关于这一点,参见野原俊郎:《判解》(有关“宫崎案”的判例解读),载《法曹時報》第68卷第4号(2016年),第270页。不过,是以同一事实为前提概括地认定这两个问题,因而就两个问题的判断之间究竟有何不同,这一点未必得到了明确。(11)关于这一点,参见前引⑩,野原俊郎文,第305页以下。相反,在“宫崎案”中,由于是以原本就不能被认定为“举动欺骗”而否定成立诈骗罪,因而,对该案高尔夫球场俱乐部而言,来宾是否是暴力团相关人员这一点能否被谓为“重要事项”,也并未作出具体的判断。(12)关于这一点,有观点指出,就是否属于“重要事项”,判例也有可能做消极的理解。参见宮崎英一:《詐欺罪の保護領域について》,载《刑法雑誌》第54卷第2号(2015年),第183页。
2.暴力团成员取得存折的案件
被告人是暴力团成员,被告人在综合账户开设申请书上写有“本人在表明并保证申请书第三页反面的内容(非反社会势力等)的基础上,提出申请”这一内容的“姓名”栏上填写了自己的姓名,装作自己不是暴力团成员的样子,向邮局银行职员申请开设综合账户,(13)所谓综合账户,是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记入一本存折的户头,在活期存款余额不够时,以定期存款为担保,可以在定期存款金额的90%的范围之内借款。——译者注并接受了该职员交付的被告人名义的综合账户存折与借记卡。对此行为,最决平成26·4·7刑集68卷4号715页判定成立第1款诈骗罪。具体而言,对此案件,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指出,(1) 政府制定了《企业防止因反社会势力造成损害的指针》,接受该指针的指导,邮政储蓄银行也决定,在存款者属于包括暴力团成员在内的反社会势力的场合,应该拒绝该人提出的开设存款账户的申请,为此,在存款人提出开设通常存款账户时,要求申请者表明并保证自己不是包括暴力团成员在内的反社会势力;(2) 本案当时使用的综合账户开设申请书上,在第一页的“姓名”栏中,写有“本人在表明并保证申请书第三页反面的内容(非反社会势力等)的基础上,提出申请”这一内容,并且,第三页的反面内容是,“本人表明并保证自己不是暴力团成员等反社会势力,如果该保证内容被判明是虚假的,即便被停止存款交易,也不提出异议”;(3) 接待被告人的邮局职员通过用手指指着综合账户开设申请书上第三页反面的内容,向被告人确认其不是暴力团成员等反社会势力,在该时点,如果邮局职员知道被告人是暴力团成员,就不会同意其开设综合账户。在此基础上,本决定判定,“在上述事实关系之下,申请开设综合账户,并由此接受综合账户存折与借记卡的申请人是否是包括暴力团成员在内的反社会势力,这是本案银行职员决定是否交付存折与借记卡的重要判断事项,因此,属于暴力团成员的人,表示并保证自己不是暴力团成员,进行上述申请,该行为就属于诈骗罪所谓欺骗他人的行为,通过该行为接受综合账户存折以及借记卡之交付的行为就显然构成《刑法》第246条第1款的诈骗罪”。
本决定以申请开设账户者是否是暴力团成员等这一点属于“作为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为理由,认定申请行为属于欺骗行为。在本决定中,根本没有就能否被谓为欺骗“行为”这一点作出具体的判断,但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在对本案被告人作出了本银行排除暴力团成员这一说明的基础上,在写有表明并保证自己不是反社会势力这一内容的签名栏中,被告人自己签名、盖章,因此,由上述签名行为所进行的申请就显然属于欺骗行为,裁判所因而也省略了对这一点的判断。(14)关于这一点,参见駒田秀和:《判解》,载《法曹時報》第68卷第5号(2016年),第229页注52;佐藤陽子:《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42号(2014年),第110页以下;橋爪隆:《判批》,载《旬刊金融法務事情》第2015号(2015年),第10页。
由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是否成立诈骗罪,近年的最高裁判所判例也重视“‘举动欺骗’的欺骗行为性”与“欺骗内容的重要事项性”。下面想就这两个要件的含义做些探讨。
三、 举动欺骗
(一) 概述
除了以作为方式显示虚假事实之外,在存在应告知一定事实这种义务(告知义务)的场合,欺骗行为也可以通过不履行告知义务这一不作为来实现。其中,“举动欺骗”(由举动实施的欺骗行为)这一概念是指,举动这一作为本身能够被评价为,显示了虚假的事实,属于作为方式的欺骗行为的一种类型。(15)“举动欺骗”(在从行为的文脉中能推断具有具有欺骗行为性这一意义上)又被称为推断的欺骗。有关该问题的研究,参见冨川雅満:《詐欺罪における推断的欺罔》,载《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第41号(2011年),第193页以下。例如,隐瞒没有付钱的意思或者付钱的能力这一事实,点餐或者登记住宿的,点餐或者登记行为本身就相当于装作有付钱的意思或者付钱的能力的“举动欺骗”。(16)例如,大判大正9·5·8刑录26辑348页等。对于所谓“赊购赖账诈骗”的案件,最决昭和43·6·6刑集22卷6号434页认为,“一般情况下,在订购商品的场合,除了特别存在例外情况的情形,均包含着会就该订单支付价款的意思表示,因此,订购者明明没有能够支付价款的希望也没有支付价款的意思,却简单地订购了商品之时,将该订购行为本身理解为欺骗行为,这是相当的”,并且以此为理由,作出了在这种场合下“没有就不作为的欺骗行为讨论有无告知义务之必要”这一旨趣的判断。
要被认定为“举动欺骗”,必须是能够被评价为,一定的举动本身就显示了虚假的事实。我们以“无钱食宿”为例来说明。点菜者通过在餐厅点菜的行为,向对方申请订立有偿提供餐饮的合同,我们可以认为,点菜行为作为申请订立有偿合同的行为,就表示了点菜者具有支付价款的意思。并且,如果在餐厅点菜,当然会支付价款,可以说,现在已经形成了这种社会一般观念,因此,对于客人是否有付钱的意思或者能力,店方既没有必要一一确认,更没有必要要求客人作出保证,店方以客人当然会支付价款这一点为前提而与客人建立合同关系,这是能够被允许的。(17)即便支付价款等被包含在合同内容之中,如果按照社会一般观念,该价款的履行处于尚不能被评价为切实这种程度的状况,那么,有时候,申请行为就不能被评价为总是表示具有支付价款的意思。与这一点相关,参见松宫孝明:《挙動による欺罔と詐欺罪の故意》,载《町野朔先生古稀記念·刑事法·医事法の新たな展開(上)》,信山社2014年版,第535页以下。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情况,例如,仅仅是对餐厅的店员说“汉堡定食”,该行为就被理解为,行为人表示的是“我有付钱的意思也有付钱的能力,因此,请提供汉堡定食”这一旨趣的意思,因而,没有付钱的意思或者付钱的能力的场合,就被评价为,行为人是通过举动表示虚假的事实,属于欺骗行为。如果将这种情形予以一般化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1) 作为对合同内容的法律解释,申请行为能被评价为何种意思或者事实的表示,以此作为探讨的出发点;(2) 基于社会一般观念或者交易习惯等,一定的举动本身能否被评价为,作为交易的默示的前提,内含着一定的事实或者意思之表达,在具体地考虑这一点的基础上,来解释该举动默示地表示的意思内容。(18)关于这一点,参见前引⑩,野原俊郎文,第280页以下。
另外,尽管采取的是“举动欺骗”这种表述,行为人的表情、外观、声音等具体的态度本身也并非总是重要的。例如,在一般餐厅点菜的场合,基于合同内容或者社会性理解,重要的是,点菜行为本身被解释为支付价款的意思或者能力的表示,在点菜之际,行为人完全没必要显出一副有钱人的派头。关于这一点,下面一个判例可供参考。在采取无需与酒店职员照面,住客可以直接办理入住自己选定的客房这种入住系统的酒店,没有带钱的被告人利用该系统入住了该酒店的客房,对此行为,东京高判平成15·1·29判时1838号155页判定,“被告人的入住行为,并非直接对酒店职员口头申请入住,而属于指向处于由机械装置进行入住管理这种系统的背后的酒店职员的行为,并且,该行为可以被谓为,让知道行为人申请入住的酒店职员误以为,既然已经入住就会切实地支付房费,酒店职员正是基于这一点,作出了提供入住酒店的便利这种财产上的处分行为,因此,该行为属于诈骗罪的欺骗行为”。在本案酒店,入住行为本身能够被评价为,表示了申请入住的意思,因此,即便被告人的表情或者态度没有被酒店职员实际认识到,也能够被评价为,通过入住行为而实施了欺骗行为。(19)关于这一点,参见橋爪隆:《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3号(2006年),第81页。相反,在申请行为本身尚不能被评价为默示地表示了一定意思的场合,行为人试图通过外观、态度等来特别地表达某种虚假信息的,一并考虑到这一点,有时候也有可能将申请行为认定为欺骗行为(例如,在申请融资的场合,就可以想见,行为人会装出一副很有财力的样子)。亦即,虽说是“举动欺骗”,除了一定情况下的申请行为本身能被评价为显示了一定信息的场合之外,我们另外还能想见,那些能被评价为,行为人是通过具体的态度来显示虚假信息的情形。
(二) 对具体案例的探讨
基于上述前提,下面想就判例所涉及的具体案件做些探讨。首先是申请开设普通存款账户的申请行为的含义(参见前述最决平成19·7·17刑集61卷5号521页)。就是在行为当时,按照普通存款规定等,也禁止储户随意转让存折与借记卡等。而且,鉴于在金融机构的业务柜台会严格进行本人确认,所开设的存款账户由申请者本人使用,这是理所当然的前提,因而可以说,禁止随意转让也已经成为社会一般常识。(20)指出这一点者,参见前田巌:《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9年度),法曹会2011年版,第325页。正因为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解释为,“开设存款账户的申请本身表示的是,申请者本人自己使用该账户的意思”,那么,隐瞒转让给第三者的意图的申请行为就能够被评价为,是由举动实施的欺骗行为。相反,即便明知是错误汇款,却对此秘而不宣仍然请求提取存款的,由于在普通存款规定中,并没有将“没有错误汇款的事实”规定为提取存款的要件,而且,当事人(银行职员等)也并非总是意识到可能是错误汇款这种特殊情况,并以此为前提来应对各个储户的取款要求,因此,难以将提取存款的请求本身理解为“请求提取未被错误汇款的钱款”这种意思的表示。(21)关于这一点,参见山口厚:《新判例から見た刑法》,有斐閣2015年版,第325页。事实上,最决平成15·3·12刑集57卷3号322页判定,“在知道有错误汇入自己账户的汇款的场合……存在将错误汇款这一旨趣告知银行的信用原则上的义务”,(不是以“举动欺骗”)是以不作为的欺骗行为作为问题。(22)关于这一点,参见宮崎英一:《判解》,载財団法人法曹会编:《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刑事篇》(平成15年度),法曹会2006年版,第325页。
下面是有关暴力团成员使用高尔夫球场的案件。前述“宫崎案”与“长野案”中的高尔夫球场均在章程中规定,禁止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球场设施。不过,在“宫崎案”中,尽管竖立了禁止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球场设施的招牌,但并未采取相应措施,以确认来宾不是暴力团相关人员,因而可以说,并未采取彻底的暴力团排除措施。并且,就本案而言,周边的高尔夫球场大多允许或者默许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球场设施,这一情况也是很重要的。当然,对于是否存在欺骗行为而言,应该以球场的实际应对作为判断基础,不过,在案发当时,宫崎县境内的高尔夫球场并未严格禁止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球场设施,对于考虑本案申请行为的社会性意义,这种情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材料。(23)并且,在本案中,由于否定客观上存在欺骗行为,因而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即便是那些认定存在欺骗行为的情形,对于被告人等有关欺骗行为的故意的认定,这种情况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以这种具体情况作为前提,那么,即便球场章程禁止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球场设施,但只要并未充分采取措施以保证这一点;而且,暴力团成员使用高尔夫球场是完全不被允许的,还不能说这一点(在当时的该地区)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共同理解,那么,对于作为来宾申请使用球场设施这一申请行为,还难以将其解释为,该行为就表示申请者不是暴力团相关人员。在“宫崎案”中,从这一角度就可以否定存在“举动欺骗”。
相反,在“长野案”中,在该案高尔夫球场,在入会之际就要求在写有不让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设施这一旨趣的承诺书上签名盖章,事实上也已经让共犯A在该承诺书上签名盖章。并且,在该案高尔夫球场,已经将暴力团排除信息加以数据化,试图防患于未然,由此防止暴力团成员使用球场设施。这样,在订立入会合同的阶段,以会员本人保证不带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球场设施为前提,才同意让会员及其同伴经过申请之后使用设施,而且,不仅仅是形式上采取了这种措施,还将其作为用于切实防止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设施的措施之一实际加以实施,鉴于这些情况,对于已经保证上述内容的会员申请其同伴使用设施的申请行为,就能够理解为,该会员默示地表示,其同伴不是暴力团相关人员。这样,在“长野案”中,以会员作出承诺这一点为前提而进行的个别使用申请,这一点就被理解为,对于认定“举动欺骗”具有决定性意义。(24)关于这一点,有观点指出,在个别使用申请之际,共犯A通过让球场前台职员代为签字,未给予被告人直接确认自己是否是暴力团相关人员的机会,结合这一点,能认定存在欺骗行为。参见伊藤渉:《判批》,载《刑事法ジャーナル》第42号(2014年),第103页以下。不过,如果球场为了防止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球场设施而采取了具体措施,暴力团相关人员不得使用球场设施这一点也已经成为社会常识,那么,即便没有会员的书面承诺或者现场保证,对于个别的使用申请行为,也有认定为“举动欺骗”的可能。
另外,即便是申请使用行为等举动本身不能被评价为欺骗行为,也完全有可能将不告知重要事实这种不作为评价为欺骗行为。不过,对于那些事关是否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如果没有被申请人的申请行为本身所体现,那么,原则上,交易的相对方(被害人一方)应该就是否存在该事实进行确认。因此,要认定为不作为的欺骗行为,应该限于行为人负有保护对方财产的义务这种例外情形。(25)在此意义上,前述最决平成15·3·12刑集57卷3号322页基于银行与存款者之间的持续性的存款交易,认定存款人“在知道有错误汇入自己账户的汇款的场合……存在将错误汇款这一旨趣告知银行的信用原则上的义务”,但是,为什么持续地在银行拥有普通存款账户,就会产生信用原则上的作为义务呢?对于这一点,理论上仍然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关于这一点,参见前引,山口厚书,第308页;前引②,橋爪隆:《詐欺罪(下)》,第103页;等等。判例中也有认定成立不作为的诈骗的案件,在本文看来,其中也包含着完全有可能被认定为“举动欺骗”的情形。例如,对于在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不告知被保险人当下的疾病的行为,大判昭和7·2·19刑集11卷85页认定成立不作为的诈骗罪,然而,由于被告人就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告知了虚假内容,因此,该案也完全有可能被认定为“举动欺骗”。
四、 诈骗罪中的实质性法益侵害
(一) 概述
由上可见,对于学界一直以来作为是否存在财产性损失而研究的问题,近年的判例是根据是否属于“作为交付之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来解决的。这里首先想就既往的学说做些简单梳理。
在诈骗罪中,要求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转移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但传统的学说重视诈骗罪财产犯属性,一直以来均要求,因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转移,给被害人造成了财产上的损失。对于这种财产性损害的意义,也有观点主张,应要求被害人整体财产的减少(整体财产减少说)。(26)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林幹人教授。参见林幹人:《刑法各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142页以下。但是,诈骗罪终究是以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这种个别财产的转移作为其本质的犯罪,应该区别于属于针对整体财产之罪的背信罪,因此,通说观点认为,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这种个别财产的丧失本身才是诈骗罪中的财产性损害(个别财产丧失说)。不过,如果丧失个别财产总是意味着财产性损害,那么,只要通过交付行为转移了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就已经丧失了个别财产,就总是应成立诈骗罪,因而作为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要求发生财产性损害,也便丧失了意义。
在这种问题意识之下,学界有观点以“个别财产丧失说”为前提,但主张通过分析交易的具体内容,从实质性的角度研究是否存在财产性损害,这种观点也日益成为学界的有力观点(实质的个别财产说)。(27)例如,西田典之:《刑法各論》(第6版),弘文堂2012年版,第203页以下;山中敬一:《刑法各論》(第3版),成文堂2015年版,第379页以下;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東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第244页以下;高橋則夫:《刑法各論》(第2版),成文堂2014年版,第326页以下;松原芳博:《刑法各論》,日本評論社2016年版,第275页以下;木村光江:《詐欺罪における損害概念と処罰範囲の変化》,载《法曹時報》第60卷第4号(2008年),第2页以下;星周一郎:《詐欺罪における機能と損害概念》,载《研修》第738号(2009年),第5页以下;等等。例如,在谎称是医师而销售对疾病有疗效的药品的案件中(前述大决昭和3·12·21刑集7卷772页),虽然可以说,被害人是因为被告人谎称是医师才信以为真交付了钱款,并丧失了对钱款的占有,然而,由此也获得了被害人所需要的,且试图购入的合适的药品,因而基本达到了其目的。(28)当然,如果认为作为购药的前提是接受医师的切实诊断,这才是被害人的目的,那么,其目的就没有达到,按照这种观点,也能认定成立诈骗罪。因此,按照“实质的个别财产说”,尽管被害人因受骗而交付了财物,但由于达到了交付财物的目的,因而就应该以实质上没有发生损失为理由,而否定成立诈骗罪。相反,在前述“电动按摩器”案件中(最决昭和34·9·28刑集13卷11号2993页),被害人以为是对于中风与小儿麻痹有特效并且很难买到的特殊治疗仪器而才愿意购买,并实际交付了钱款,因而,针对试图达到的目的,被害人受到了欺骗。因此,未能达到被害人的目的,能认定被害人存在实质性损害。这样,“实质的个别财产说”重视的视角是,被害人试图获得但归于失败的东西在经济上能否被评价为损害?(29)持这种理解者,参见前引,西田典之书,第204页。另见山中敬一:《詐欺罪における財産的損害と取引目的》,载《法学新報》第121卷第11号与第12号合并号(2015年),第400页以下。
但是,这里实际上是在实质性损害这一视角之下,研究被害人就何种事实受到了欺骗这一问题。亦即,销售了合适的药品的销售者即便谎称自己是医师也不成立诈骗罪;反之,对于作为对价而收取的电动按摩器的效能而受到欺骗的场合,则要成立诈骗罪,最终就是根据受骗的内容来划定诈骗罪的成立边界。如果是那样的话,即便不勉强以财产性损害这一要件作为问题,通过对诈骗罪中的“欺骗他人”的行为(欺骗行为)进行限定解释,就完全有可能解决此问题。(30)关于这一点,参见伊藤渉:《詐欺罪における財産的損害》,载《刑法雑誌》第42卷第2号(2003年),第24页;中森喜彦:《刑法各論》,有斐閣2015年版,第134页。学界的“有关法益的错误说”就正是基于这种问题意识而提出。该说认为,限于被害人基于对试图处分的法益的内容或者价值的错误认识而同意的场合,该同意归于无效。在这一理解之下,着眼于诈骗罪中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的同意而处分了财物这一点,该说认为,在诈骗罪中,限于被害人存在对交付的财物或者对方给予的反对给付的内容或者价值的错误认识,也就是被害人存在有关法益的错误认识的场合,应成立诈骗罪。(31)持这种理解者,参见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版),有斐閣2010年版,第266页以下;佐伯仁志:《詐欺罪の理論の構造》,载山口厚等:《理論刑法学の最前線Ⅱ》,岩波書店2006年版,第106页以下;内田浩:《詐欺罪における財産的損害》,载《法学教室》第359号(2010年),第36页;前引②,橋爪隆:《詐欺罪成立の限界について》,第176页以下。并且,只要像这样限定性理解诈骗罪中的被害人的错误认识的内容,与此相对应,行为人的欺骗行为的内容也得到了限定。按照这种理解,由于有可能通过欺骗行为以及被害人的错误认识而实质性地限制诈骗罪的成立范围,因此,作为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要求发生财产性损害,就不再具有必然性。
这样,在学界,根据究竟是基于“实质的个别财产说”而要求发生(实质性的)财产性损害,还是在认为不需要发生财产性损害的基础上而采取“有关法益的错误说”,对于是否应该限定性地理解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法益概念,就存在观点之间的对立。(32)另有观点基于认为诈骗罪的保护法益在于财产处分的自由的立场,研究欺骗概念与财产性损害之间的关系。参见足立友子:《詐欺罪における「欺罔」と「財産的損害」をめぐる考察》,载川端博等编:《理論刑法学の探求⑥》,成文堂2013年版,第133页以下。基于以下理由,我本人一直以来主张后一种观点:(1) 与基于发生财产性损害这种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来研究是否成立诈骗罪相比,直接研究是否存在欺骗行为(以及基于欺骗行为的被害人的错误认识)这种法律明文规定的要件,作为解释论来说要更为妥当;(2) 如前所述,判例理论也是从是否就“作为交付之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实施了欺骗这一视角,显现了通过对欺骗行为的解释来限定诈骗罪成立范围的可能性,这种观点相对更接近于“有关法益的错误说”;(3) “实质的个别财产说”虽然原则上以个别财产的转移本身作为认定损害的事实根据,但例外地根据被害人是否达到了目的来决定是否实质性地否定发生了损害,也就是,同时考虑了损害的积极性根据以及例外的否定这样两个不同性质的内容,因而有招致解释论上的混乱之虞。
我本人虽支持“有关法益的错误说”,认为作为诈骗罪的成立要件不需要“发生财产性损害”这一要件,但同时也认为,将两种观点过度对立也不是一种妥当的做法。无论是“实质的个别财产说”还是“有关法益的错误说”,其研究路径都是试图从诈骗罪的实质性法益侵害的视角来限定诈骗罪的成立范围,两者之间不过是应该将其问题意识还原至何种要件论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而已。(33)指出这一点者,参见井田良:《詐欺罪における財産的損害について》,载《法曹時報》第66卷第11号(2014年),第13页以下;杉本一敏:《詐欺罪における被害者の「公共的役割」の意義》,载《野村稔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2015年版,第305页;前引,駒田秀和文,第212页。而且,即便以“实质的个别财产说”为前提,与损害概念的限定相对应,属于诈骗罪之实行行为的欺骗行为也会被限定为,具有引起这种实质性损害之具体危险的行为,因此,无论采取何种立场,也不得不以对欺骗行为的限定解释作为问题。(34)关于这一点,参见大塚裕史:《判批》,载山口厚、佐伯仁志编:《刑法判例百選Ⅱ各論》(第7版),有斐閣2014年版,第103页。因此,无论是按照“实质的个别财产说”还是按照“有关法益的错误说”,欺骗行为的对象、内容都被做了限定性解释,因此,正如近年的判例那样,认为欺骗行为的内容应限于“作为交付之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这样理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作为交付之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的范围。就这一点而言,如果从经济性视角严格地解释“重要事项性”,(可能与判例的结论相比)诈骗罪的成立范围就会受到限制;相反,如果广泛地认为,在如果被害人知道事实就不会交付财物的场合,该事实就相当于“重要事项”,那么,其结论就会走向“形式的个别财产说”的立场。在此意义上,究竟应该如何判断是否属于“重要事项”,对于决定诈骗罪的界限,就属于最为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还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35)另外,有观点主张根据行为的样态或形式、实施行为的场景、社会性意义等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欺骗行为。参见前引⑤,成瀬幸典文,第140页以下。
(二) 对重要事项性的判断
1.是否需要发生直接的经济性损害
围绕被骗事实的重要事项性,被害人所交付的财物本身的价值属于“重要事项”,这一点想必不存在争议。例如,尽管被害人持有的古董实际上是价值极高的东西,却欺骗被害人说,这个东西不值钱,然后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古董的,这种行为就属于对“作为财物(古董)交付之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的欺骗,应构成诈骗罪。而且,被害人试图通过交付财物而得到的反对给付的存在与否及其内容,当然也应该属于重要事项。在无钱食宿的案件中,能否通过提供饮食或者住宿而从行为人处得到相当对价,正因为这一点能被评价为重要事项,伪构付款意思或者付款能力的行为就属于欺骗行为。正如“电动按摩器案”那样,如果反对给付物的价值、属性对被害人的用途、目的而言属于有意义的事实,则能被评价为重要事项。就这些案件而言,可以说,被害人通过该交易本身直接蒙受了经济上的不利益,因而当然应成立诈骗罪。
相反,在近年的判例之中的那些成为问题的案件中,并非是由交付行为本身直接给被害人带来了经济上的不利益。例如,即便允许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高尔夫球场设施,由于高尔夫球场获得了设施使用费,并不会因这种许可本身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关于这一点,有关“长野案”的最高裁判所平成26年决定(最决平成26·3·28刑集68卷3号646页)指出,如果球场允许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球场设施,会使得其他来宾因暴力团成员在此打球而感到畏惧,进而导致球场客流量减少以及损害球场的信誉或者等级,因而该决定重视由此间接地给球场经营所带来的不利益,进而得出来客是否是暴力团相关人员这一点属于重要事项的结论。(36)参见前引⑩,野原俊郎文,第306页以下。进一步指出具体的受害可能性的研究,参见松井洋:《判批》,载《警察学研究》第67卷第8号(2014年),第158页。对于这种重视不是因交易而引起的直接损失,而是因交易间接地造成损失的可能性的观点,出于论述方便的考虑,下面称之为“间接损害型路径”。
对于这种“间接损害型路径”,有观点主张,对高尔夫球场而言,重要的是通过允许使用设施而得到的对价,既然得到了相应的对价,就没有财产性损害,进而反对连间接的损害也要考虑进去。(37)参见松宫孝明:《暴力団員のゴルフ場利用と詐欺罪》,载《斉藤豊治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刑事法理論の探求と発見》,成文堂2012年版,第161页以下;田山聡美:《詐欺罪における財産的損害》,载《曽根威彦先生·田口守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下),成文堂2014年版,第161页以下;前引,松原芳博书,第283页;等等。亦即,该观点将诈骗罪中的法益侵害限定于由被害人的交付行为所直接造成的财产性损害。不过,按照这种理解,在交易中取得了相当对价的场合,就没有成立诈骗罪的余地,因而又过度限制了诈骗罪的成立范围。(38)当然,这属于有关具体结论的评价的问题,因而这种限定在理论上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而且,在商品交易中,行为人的确基本上都是以追求利益作为其最大目的,但是,对其他目的的追求也并非毫无意义。只要收到了钱,即便其他地方上当受骗了,也没有必要以诈骗罪来保护,在本文看来,这种做法未必能够充分地保护被害人。(39)正如这些观点所强调的那样,诈骗罪的法益侵害以由被害人的交付行为所直接造成为必要。但是,所谓诈骗罪的法益侵害结果应该是指,就重要事项被欺骗的被害人在这种欺骗的影响之下,通过交付财物或者利益,而丧失了对个别财产的占有。本文以为,只要占有的丧失是由交付行为所直接引起的即可,受骗的内容(即重要事项)本身不需要与直接的财产损害相关。
2.“间接损害型路径”的含义
在学界,尤其是立足于要求发生实质性损害的立场,依据“间接损害型路径”来进行解释的观点也很有影响。例如,对于隐瞒转让给第三者的目的而接受自己名义的存折之交付的案件(前述最决平成19·7·17刑集61卷5号521页),西田典之教授重视的是,随意转让的账户有可能被用于电信诈骗等犯罪,在漫不经心地按照对方要求办理了从该账户取款的手续的场合,银行就有可能被要求返还不当得利,从而有间接地承担财产性损害的风险的可能,进而以此作为认定财产性损害之发生的事实根据。(40)参见前引,西田典之书,第209页以下。西田典之教授认为,在该案,“能否认定银行蒙受了或者有可能蒙受某种财产性损失呢?例如,A将在X银行开设的A名义的账户转让给B,该账户被B用于电信诈骗,让受骗人将钱款打入该账户,在此情形下,由于B并非正当的存款合同方,因此,B本人从ATM机上提取该钱款的行为,或者,B本人从银行柜台提取存款的行为,就有可能属于盗窃或者诈骗。不过,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说,存在账户的名义人A的承诺。的确,按照有关‘错误汇款’的平成8年(1996年)的民事判例(最判平成8·4·26民集50卷5号1267页),不管具体原因如何,A均有效取得存款债权,那么,B在得到A的承诺之后所实施的行为,看上去似乎不应构成犯罪。但是,最高裁判所平成15年(2003年)的决定则认为,在‘错误汇款’的场合,认为是‘天上掉馅饼’而提取了他人错误汇入的钱款的,该人存在告知属于‘错误汇款’的义务,从而判定该人成立不作为的诈骗罪(最决平成15·3·12刑集57卷3号324页)。并且,最近还有这样一个民事判例:原审认为,X银行向犯罪行为人B支付存款的行为,即便X银行存在过失,也仍然有效,对此判决,平成20年(2008年)的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最判平成20·10·10民集62卷9号2361页)判定予以撤销,并且,为了让原审对‘X银行向B支付存款的行为作为向债权的准占有者的偿还是否有效’这一点进行审理,而发回重审。”总之,“从银行接受他人名义的存折之交付的行为,以及即便是自己的名义,但隐瞒准备转让给第三者的意图而接受存折之交付的行为,均属于通过欺骗行为而取得银行存折这种财物,因而,该当于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并且,在此情形下,如果有人从不知情的银行处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存折,并将该存折用于电信诈骗犯罪,尽管银行有可能作为对于债权的准占有者(具有作为受领权人之外观者)的偿还而得以免于承担存款债务,但有些情况下,银行仍然有可能承担基于被害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或者基于非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银行承担的这种风险,就可以被谓为,存在遭受财产性损失的可能性”。参见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页以下。——译者注并且,对于隐瞒自己是暴力团相关人员而接受存折之交付的案件(前述最决平成26·4·7刑集68卷4号715页),负责该案的最高裁判所调查官指出,存在暴力团成员日后非法使用该账户的风险,或者因同意暴力团成员开设账户而毁损银行的社会信誉等,进而蒙受(间接的)经济性不利益的可能性。(41)参见前引,駒田秀和文,第227页。按照这种理解,尽管是间接性的,但只要是有可能带来经济上的风险的情况(例如,存在随意转让存折的目的、申请开设账户者是暴力团成员等),就可以被评价为“作为交付之判断基础的重要事项”。(42)另外,有观点尽管也要求即便是间接性的,还是应该有造成财产性损害的可能性,但对于不正当地取得存折的案件持怀疑态度:原本有那个可能性吗?参见佐伯仁志:《詐欺罪(1)》,载《法学教室》第372号(2011年),第113页以下。然而,这种间接的经济损害的可能性,不过是在“不能说没有这种情况”这种一般性、抽象性的层面所设想的探讨,而无法作为一种客观可能性,就具体个案进行个别认定。(43)指出这一点者,参见山口厚:《詐欺罪に関する近時の動向について》,载《研修》第794号(2014年),第10页以下。例如,行为人出于用于电信诈骗等犯罪的目的而用假名申请开设账户的情形,以及为了不被家人发现出于存“私房钱”的目的而用假名开设账户的情形。这两种情形之间,银行承担经济上的风险的可能性(也许)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认为,这两种情形是否成立诈骗罪的结论也不一样。最终来说,虽说是间接性的损害可能性,但我们只能是进行抽象的、类型性的判断,其本身无法成为划定诈骗罪之界限的合理标准。(44)由于追问的是抽象层面上的损害可能性,因而,就以所谓“大风刮来个聚宝盆”的方式,最终存在无限扩大损害可能性的认定范围之虞。关于这一点,参见渡辺靖明:《詐欺罪における実質的個別財産説の錯綜》,载《横浜国際経済法学》第20卷第3号(2012年),第157页。
3.对交付财物时的重要的关注点或者目的的保护
这样考虑的话,在本文看来,在被害人交付财物之际,将鉴于该交易的性质或者目的而有必要加以重视的情况广泛地作为“重要事项”加以把握,在此基础上,将间接性地承担经济性损害的可能性定位为,判断该情况之重要性的判断材料之一,这样要更为合适。例如,银行为了追求获得存款等利益而开展业务活动,作为业务的一环,会同意客户开设存款账户的申请,并将存折交付给申请者。但是,银行的业务必然会受到相关部门的各种各样的限制,现在要想无视这些限制而完全独立地开展业务,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并且,在相关部门的各种规制之中,例如,彻底进行本人身份的确认以求账户被合法使用,以及切断与反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对银行业务而言,这些都属于重大的关注点,是银行开展业务时必须总是放在心头的事情。因此,是否是申请者本人使用存折,以及申请者是否是暴力团成员,在银行业务中,这些应该被评价为“重要事项”,因而就此内容进行虚构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这样,在对该交易或者业务内容的性质、目的进行个别判断的基础之上,就应该将那些转移财物、利益之际总是应该予以重视的情况作为“重要事项”,认为这些情况构成欺骗行为的内容,至于引起间接性的损害的风险,就可以将其作为判断材料之一来加以考虑。
下面想结合最决平成22·7·29刑集64卷5号829页就此进行确认。就隐瞒转让给第三者的意图而接受国际航班的登机牌之交付的行为,原判决(控诉审)判定成立诈骗罪(大阪高判平成20·3·18刑集64卷5号859页)。不过,原判决的理由是,“不具有同一性的人使用登机牌搭乘飞机,存在给飞行安全带来重大弊害的危险,会导致航空公司的社会信用的降低、业绩的恶化,并且,在本案中,如果航空公司因本公司没有妥善发放登机牌,而使得登机牌的(冒名)使用者非法进入加拿大,就会被该国政府科处最高额3 000美元的罚款,因而,对航空公司而言,防止他人非法使用登机牌是具有极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进而重视造成间接性的财产性损害的可能性,判定成立诈骗罪。相反,最高裁判所则认为,“之所以进行如此严格的本人确认,是因为机票上所记载的乘客之外的其他人搭乘飞机,存在给飞行安全带来重大弊害的危险,而且,加拿大政府也赋予了本案航空公司为防止有人非法进入该国而应该切实发放登机牌的义务,因而,不让该乘客之外的其他人搭乘飞机,对本案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输业务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最高裁判所的本决定并没有勉强谈及造成间接的财产性损害的可能性,而是指出确保飞行安全以及防止非法入境的措施本身对于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输业务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45)关于这一点,参见和田俊憲:《判批》,载《平成22年度重要判例解説》,《ジュリスト》第1420号(2011年),第213页;前引⑦,増田啓佑文,第188页注18;前引,山口厚文,第10页。本文想主张的,也正是这种旨趣。财产性损害的可能性当然是重要的判断材料之一,但即便不以此为媒介,仍然存在对照经营、业务之内容而被评价为重要关注点的余地。判例采取“经营上”的重要性这一表述,其背后也许有与经济上的或者财产上的重要性划清界限的意图(当然,这也许是笔者想得太多)。(46)关于这一点,参见前引⑥,上嶌一高文,第21页以下。
4.关注点或者目的的客观重要性
这样,是否属于作为欺骗行为之内容的“重要事项”,应该被理解为,对照该交易或者业务内容的性质、目的,被害人在交付财物或者利益之际有充分考虑之必要性的事项。发生经济性损害的盖然性很高的事项,当然属于这里的重要事项,(47)有关暴力团相关人员使用高尔夫球场设施的情况,从这种视角来看,就能肯定具有重要事项性。但即便没有这种情况,在进行业务或者经营上的判断之际,那些总是应该放在心上的情况,也应该属于这里的重要事项。因此,根据被害人的属性或者业务内容,能够被评价为“重要事项”的事实的范围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交付国际航线的登机牌之际,登机牌上的名义人(乘客)是否是实际搭乘本航班的人,在国际航线的运营业务中,能够被评价为重要事项,但在国内航线的运营业务中,防范恐怖活动或者非法入境的要求(至少现在)不像国际航线那么严格,因而在国内航线中,这一点也有可能被理解为,不属于“重要事项”。(48)关于这一点,参见前引⑦,増田啓佑文,第191页。而且,在高尔夫球场的经营中,可以说,没有必要达到银行业务的程度那样正确地管理、掌握球场设施的使用人的同一性,因而即便非暴力团相关人员用假名申请使用球场设施,也有认定不成立诈骗罪的余地。(49)在“重要事项”的判断中,当事人是否存在公共的作用(职责)也具有一定意义。参见前引,松宫孝明文,第165页。
另外,这种重要事项性的判断,不应该是根据被害人个人的关注,而应该是根据一般情况下在该交易、业务中的重要性来客观判断。因此,对于那些在该交易或者业务中(至少在当下的时点)并非应该重视到如此程度的事项,即便被害人个人对该事项尤其予以了关注,也应该认为,该事项不属于“重要事项”。在近年的最高裁判所判例中,就是否存在被告人实施欺骗的事实这一点,不仅要求被害人采取了针对这一事实的应对措施,还反复判定,该事实还应该是在该交易(银行业务、国际航班运营业务、高尔夫球场的经营)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得到重视的事实。(50)关于这一点,参见前引,宮崎英一文,第186页以下。由此可见,不仅仅是被害人本人的关注点,判例还重视一般情况下、客观上在该业务中能否被评价为重要事项。(51)因此,在某个个人纯粹是出于个人目的而交付了个人所有的财物的场合,由于没有加入“一般情况下、客观上”这种视角的余地,因此,即便完全是个人关注的事项,也有被评价为“重要事项”的余地。另外,有观点做相对广泛的理解,将个人主观上处分的自由也纳入诈骗罪的保护对象。参见長井圓:《詐欺罪における形式的個別財産説の理論的構造》,载《法学新報》第121卷第11号与第12号合并号(2015年),第369页以下。
按照这种理解,对于那些在交付财物之际一般会放在心上的情况,即便被害人个人对此毫不在意地交付了财物,该事实仍然有被评价为“重要事项”的可能。例如,在暴力团成员隐瞒自己的身份打算开设存款账户的场合,即便负责接待的银行职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有关排除暴力团这种规制的重要性;或者说,我们无法否定,也有可能虽然知道对方是暴力团成员却仍然会交付存折(或者说,明明知道对方是暴力团成员,却仍然交付了存折),对于这些情形就应认定成立诈骗罪未遂。(52)例如,被告人隐瞒转让给第三者的意图申请购入手机,店长虽然隐隐约约地察觉到对方有转让的意图,但出于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一意思,将手机卖给了被告人,对此案件,东京高判平成24·12·13高刑集虽认定被告人的申请行为属于欺骗行为,但最终判定成立诈骗罪未遂。
5.与“举动诈骗”之间的关系
最后,想就下面两种判断之间的关系做些探讨:对欺骗的内容是否属于“重要事项”的判断,以及对某种举动能否被评价为欺骗行为的判断。
正如前文反复强调的那样,在“重要事项”的判断中,该事实在该交易或者业务中受到何种程度的重视,这属于重要的判断标准。并且,如果是业务开展过程中的重要事实,大多会要求就此采取确认措施,或者要求对方立誓或者作出保证。另一方面,在“举动欺骗”的欺骗行为性的判断中,重要的是能够被解释为,订购行为或者申请行为表示着一定意思,因而,当事人通常会意识到的事情,作为社会一般观念就属于重要的判断材料,而且,如果采取了确认措施或者要求对方立誓或者作出保证,行为人针对这种措施的应对行为,就往往能被评价为欺骗行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两者是从不同角度来限制诈骗罪的成立范围,因而两者的判断要素很大程度上是重复的。(53)关于这一点,参见前引,宮崎英一文,第183页。
不过,在“举动欺骗”的欺骗行为性的判断中,只要能被评价为,是通过举动来说谎即可,因而通过言行所表示的内容就是很重要的,至于当事人是否表示了强烈关注,就不属于不可或缺的要素。例如,虽采取了就一定事实进行确认或者保证等措施,如果这种程序不过是形式上实施而已,就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而言并不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就有可能被认定为“举动诈骗”,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存在由于该欺骗内容根本就不属于“重要事项”,因而应否定成立诈骗罪的可能。(54)指出这一点者,参见前引,杉本一敏文,第314页。一般认为,即便未成年人谎称自己是成年人而购买酒精饮料的,也不成立诈骗罪,不过,在采取了年龄确认等措施的场合,谎称自己是成年人这一行为就有可能被评价为欺骗行为。然而,由于欺骗的内容(在是否成立诈骗罪这一问题上)根本就不能被评价为“重要事项”,因而应否定成立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