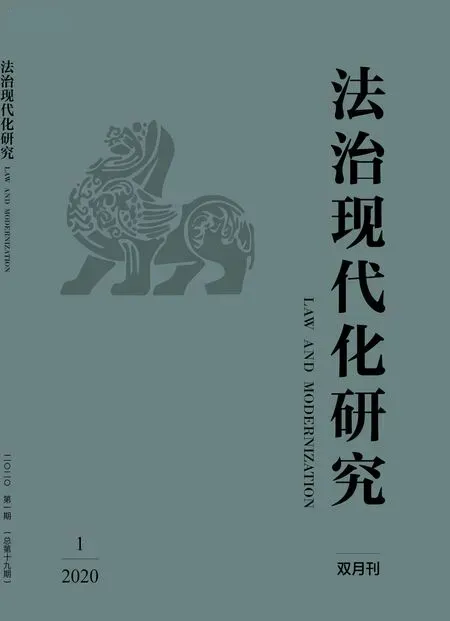跨越实体与程序的鸿沟
——刑事一体化走向深入的第一步
李 勇
一、 引 言
储槐植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刑事一体化”概念,(1)参见储槐植:《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载《中外法学》1989年第1期。到底如何实现刑事一体化,储教授曾提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内部关系,即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也就是作为实体法的刑法,与作为程序法的刑事诉讼法,两者在现实运作中密不可分,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外部关系则包含两层关系:前后关系和上下关系,其中,前后关系是指刑法受到刑法之前的犯罪状态(即犯罪态势)和刑法之后的行刑效果两个方面的制约,即“两头制约”。(2)参见前引①,储槐植文;储槐植:《再说刑事一体化》,载《法学》2004年第3期。受时代的限制,储槐植先生提出的刑事一体化主要立足点是刑法结构,强调是刑法和刑法运行内外协调的关系,而对内部关系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并未作系统阐述。理论界在讨论刑事一体化时,也习惯于从刑事政策学、犯罪学角度研究刑法问题,关注的主要是外部关系。
笔者认为,刑事一体化的真正实现,应当首先从内部关系——即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入手。从犯罪学、刑事政策角度研究刑法仍然是就刑法研究刑法,依然是刑法中心论。李斯特在19世纪提出的“整体刑法学”观念,强调的是犯罪、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耶塞克提倡的“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与犯罪学”,强调的还是刑法学与犯罪学、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3)参见[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同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和犯罪学》,周遵友译,载《刑法论丛》2010年第2期。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都是刑法中心论。这种刑法中心论意义上的刑事一体化,侧重于方法论上的一体化,属于观念和理念层面的一体化,没有具体化到法律的适用、实践问题的解决和个案的处理层面。这种停留于理念、观念、方法论层面的一体化只能是刑事一体化的初级阶段,离深度的刑事一体化尚有距离。要想实现刑事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就必须从理念、观念、方法论这些宏观问题进一步延伸到具体问题。真正高度融合、深度交叉的问题大都寄生于具体的法律争端、具体的实践问题,而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无疑是这种具体问题的集中表现,这是刑事一体化走向深入的第一步。从储槐植教授于1989年提出刑事一体化到今天,已有31年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融合远未实现,呼吁者多,真正做融合研究者少;吆喝者多,真正能一体化“通吃”者少。笔者认为,推动刑事一体化的深度融合,应当从内部关系即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深度融合开始。
二、 实体与程序的应然景象
从应然的角度看,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性不仅体现在司法实践具体案件处理时必须兼顾实体与程序,而且在理论上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也是相互依存的。
(一) 实践层面的应然景象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说,办理刑事案件只考虑实体而不考虑程序、证据,或者只考虑程序、证据而不考虑实体,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实践中,不存在纯粹的刑事实体法问题,也不存在纯粹的刑事程序法问题,二者从来都是相互交织的问题。所以,实践中只懂刑法而不懂刑事诉讼法,或者只懂刑事诉讼法而不懂刑法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是不可能把案件真正办好的。
法释义学为现行法服务,更精确地说,现行法是法释义学之研究对象。法释义学是彻底实务取向之学科。(4)Engisch, 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Denken, 8. Aufl., 1983, 8 ff. 转引自[德]PeterA. Windel:《天啊,德国的法释义学》,黄松茂译,载台湾地区《月旦法学杂志》2019年第5期。尽管刑法理论要高于实践,但也要应用于实践。法学研究具有实践品格,刑法学的实践品格更加突出。刑法学的研究终究是要解决实践问题,脱离实务的理论与脱离理论的实务都不可取。理论和实务彼此之间就像眼睛和手:理论就像眼睛,看见了什么东西;实务就像手,如果认识不能转化,则认识也就无法实现。同样,如果作为实务的手想做什么,而作为眼睛的理论表示反对,则实务的愿望也不会实现。只有当双方融和,才存在理性的、公正的解决方案。(5)参见[德]迈尔·格斯讷:《刑事诉讼中脱离实务的理论与脱离理论的实务》,喻海松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2012年第1期),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刑法理论要应用于实践个案,就离不开事实和证据,因为个案是以事实和证据为存在载体的。例如正当防卫问题,从刑法学角度研究正当防卫的起因、限度等成立条件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研究结论或解决方案也要考虑证据上能否实现,易言之,从司法实务的角度看,“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关键在证据”。如何从证据上证明“不法侵害”是否存在,如何从证据上证明防卫手段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行为必要性)和“造成重大损害”(结果性相当性)?“昆山反杀案”之所以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不久即以正当防卫为由撤销案件,其重要原因正是有完整的监控视频证据,清晰地反映出事件全过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州赵宇案”和“涞源反杀案”。在“赵宇案”中,从认定防卫过当而相对不起诉,再到撤销相对不起诉,最终认定正当防卫而绝对不起诉,两次不起诉公布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有重要变化。(6)主要变化有:将赵某“见李某正在殴打邹某”细化为“见李某把邹某摁在墙上并殴打其头部”;将“赵某和李某一同倒地”修改为“致李某倒地”;将李某“打了赵某两拳”修改为“欲殴打赵某”;增加李某“弄死你们”的表述;删除“(赵某)接着上前打了李某两拳”;将赵某“被自己的女友劝离现场”修改为“离开现场”;增加邹某面部轻微伤的鉴定意见,等等。参见陈菲、丁小溪:《检察机关纠正赵宇案:属正当防卫不负刑责》,载“中国新闻网”,https://mp.weixin.qq.com/s/VFQXtgoMlkgFUXlzHMfkUg,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4月11日。这些事实和证据的变化对正当防卫的认定起到重要作用。“涞源反杀案”从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和逮捕,到检察机关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再到最后不起诉。这两起案件所经历的反复和波折,主要原因在于证据和证明问题。实践中,大量发生在封闭场所的“一对一”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因为没有监控视频和在场证人,是否存在不法侵害?防卫的手段是否过当?证据和证明就成为核心问题。
因此,从实践角度看,实体与程序从来都是相互交织的。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林钰雄教授所言,对于学院以外任何操作实务的法律人而言,这种关系本来近乎至明至理,毕竟真实案例,或者说具体法律争端的解决,从来都是实体与程序的交错适用。(7)参见林钰雄:《刑法与刑诉法之交错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
(二) 理论层面的应然景象
首先,刑法作为实体法,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实体法的罪刑规范依赖于程序才能实现。现代法治国家,要给予一个人刑罚处罚,必须按照特定的程序才具有其正当性。未经正当程序就给予一个人定罪处罚,这是不正义的。对一个人定罪处罚是一种国家行为,应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进行,这也是法治国的基本原则,给予有利害关系的人应有的程序并陈述事实、表达法律观点的平等机会,并且以公开的方式进行,(8)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哲学》,金振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页。这是程序正义的要求。规定犯罪构成要件及其刑罚后果的刑法实体规范,必须通过刑事程序才能落实到具体犯罪人身上。刑事诉讼法是确定并实现国家与具体刑事个案中对被告刑罚权的程序规范,实体刑法唯有通过诉讼程序才能得以实践,而获致一个依照实体刑法的正确裁判,正是刑事诉讼的任务。(9)参见前引⑦,林钰雄书,序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刑事诉讼的内部结构是以实体形成为中心的。(10)参见[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其次,刑法适用过程是事实与规范的对应过程,而事实来自证据和证明。罪名规范是刑法的主体内容,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个罪名,是通过构成要件来判断的,而构成要件事实正是刑事诉讼所要证明的。小野清一郎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刑事追诉的直接目的,在于确认被告人是否犯有一定的犯罪事实。这里所说的犯罪事实,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刑事程序一开始就是以某种构成要件为指导形象去辨明案件,并且就其实体逐步形成心证,最终以对某种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达到确实的认识为目标。这就是刑事诉讼中的实体形成过程。如果从证据法的观点来讲,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证明事项就是构成要件事实”。(11)前引⑩,小野清一郎书,第241页。犯罪成立条件中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及其具体要素,无一不是需要证据证明的。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也同样需要运用证据证明。这里不仅是证明对象的问题,还涉及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等,实体法上的具体规定会直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判断和证明方法的运用。所以,一言以蔽之:“办案就是办证据。”
最后,无论是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是为了限制国家刑罚权恣意发动而存在的。实体上,罪刑法定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程序上,正当程序要求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财产、自由与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是为了不随意地处罚人而设立的。只不过刑法是从规范犯罪构成要件、明确刑罚种类和幅度、设定刑事追究标准等方面来发挥作用的;而刑事诉讼法则是从规范刑事追诉机构的权力、明确被告人的防御权利,确定刑事追究的证据标准等角度来发挥作用的,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正当程序等一系列基本原则,也几乎都是对刑事追诉机构、司法裁判机构的权力施加了限制。(12)参见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52页。实体和程序分别从不同角度限制国家刑罚权,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确保国家刑罚权在合理轨道上运转。
三、 实体与程序的现实面相
如前所述,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实体与程序具有难分难舍的交织关系,但从现实的实然层面看,实体与程序依然存在巨大的鸿沟。
(一) 实体与程序在理论研究上的裂解
首先,跨学科研究的呼声与实际行动的裂解。近年来,跨学科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实际行动并不尽如人意。刑法学研究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井水不犯河水”的现象依然严重。这里面涉及学科的专业化、精密化的问题。德国学者希尔根多夫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当今法学基础研究如何看待跨学科性?从学术政策到大型科研机构都经常呼吁跨学科性,所有学科代表在讨论中也都称赞跨学科性,然而,它在科学实践中难以实行。为什么呢?目前所有学科强调说明的专业化与跨学科性极不协调……然而,法学家们在基础研究的背景下倾向于自我封闭……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直到今天,与相邻学科长期而有益的交流寥寥无几”。(13)[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黄笑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2页。这种现象在德国尚且存在,在我国更甚;在其他领域尚且存在,在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领域更甚。通常认为,刑法教义学关注的是刑法规范本身,刑法教义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解释,来指出具体法律条文之间的意义和原理联系,并且追溯这些意义和原理联系的相关法律思想,从而形成一个协调的体系”。(14)[德]沃斯·金德豪伊泽尔:《适应与自主之间的德国刑法教义学——用教义学来控制刑事政策的边界》,蔡桂生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刑法教义学假定刑法文本的正确性,主张解释刑法文本而非批判文本,刑法教义学的逻辑前提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法律永远是正确的、“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15)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教义刑法学是指以刑法规范为根据或逻辑前提,主要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将法律概念、规范、原则、理论范畴组织起来,形成具有逻辑性最大化的知识体系”,(16)周详:《教义刑法学的概念及其价值》,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6期。追求刑法自身的体系化和精密化。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专业化与跨学科性”之间是极不协调的。长期以来,刑法学形成一个高度精密化的体系,形成一套独立自主、其他专业人士无法听懂的话语体系。精密化的体系对于一个学科的成熟来说或许是好事,但是也会带来自我封闭的风险。所以,现实中刑事诉讼法学者想跨界研究刑法问题“难于上青天”。(17)相比而言,刑法学者跨界研究刑事诉讼法则要容易些。例如,作为刑法学者的邓子滨教授新近出版了自己的刑事诉讼法专著——《刑事诉讼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其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裂解。近年来,涌现出很多刑事一体化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仅停留于宏观层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跨学科的宏观理论探讨,例如从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角度研究刑法问题,进而提出某种创新的刑法理论,这大多属于“宏大叙事”。二是“以刑法为中心”和“以刑事政策为中心”。刑法学界习惯于从刑事政策角度讨论刑事一体化,特别关注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包括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刑事政策对刑法结构的影响,等等;也有从犯罪学以及其他学科出发来研究刑法问题的,但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以刑法为中心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共性在于忽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高度融合和深度交叉的研究。或许是因为宏观跨界比微观跨界更为便利,空发议论比解决具体问题更为容易。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深度融合和交叉研究,必须立足于具体的微观问题,具体微观问题的解决需要扎实的交叉学科知识。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很多刑法理论研究,习惯于在想象中建构的某种高深理论,而没有考虑这种“想象的理论”在证据和证明上是否具有现实的操作可能性。事实上,真正的疑难案件,从实践的角度看,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如何运用证据去证明的问题!正当防卫成立与否、过当与否,罪名之间的区分界限,因果关系的认定,共同犯罪的成立,故意与过失的区分等一系列难题,除了有关刑法理论本身较为复杂外,更重要的就是证据和证明问题!但,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习惯于自说自话,很少考虑其理论研究成果在证据和证明上能否实现,刑法理论与教学如果习惯于“从全知全能的上帝角度出发,无视于诉讼证明及事实不明的真实审判困境,不管演绎如何精彩,终究只是空中楼阁。……另一方面,既然‘获至一个依照实体刑法的正确裁判’是刑事诉讼的任务,欠缺实体刑法作为实践圭臬及延展腹地的刑事诉讼理论与教学,自难正中鹄的”。(18)前引⑦,林钰雄书,序言第2页。
(二) 实体与程序在两大法系走向上的裂解
作为一个大陆法系国家,我国的实体刑法是建立在苏俄、德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刑事程序法却呈现出浓厚的英美法系色彩,作为一体两面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行进,令人匪夷所思。这种两大法系走向上的重大裂解,也给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叉融合带来了严重障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制度设计都存在两大法系走向上的裂解。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说,两大法系的融合趋势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融合并未完全抹掉各自的本质特色和本土底色。法律制度是一国文化的一面镜子,完全脱离本国传统和文化的法律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德国证据法大师密特麦尔指出,职权主义诉讼是不可能确立与当事人主义一样的证据规则,“国家权力主导、职业法官裁判、实质真实探求”的诉讼特质决定了司法官员在刑事证据运用中的决定性作用,且这一作用自侦查阶段便已凸显。(19)参见施鹏鹏:《跨时代的智者——密特麦尔证据法学思想述评》,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5期。我国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传统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
在我国刑事法学界,一方面,诸多有影响力的刑事诉讼法学者,基本都是研究英美法系刑事诉讼法的,对德国等大陆法系刑事诉讼法知之甚少;而另一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则基本师从德日,对英美法系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理论,知之甚少。而司法实践的现实情况又是另一番景象,实务人士的思维方式、办案习惯和行为,自觉不自觉地更亲近大陆法系传统,实践中的很多习惯做法与大陆法系具有高度契合性。理论与实践、实体法与程序法,在两个方向上的裂解,相互交织,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改革和制度设计形成难以估量的冲击,导致很多刑事诉讼制度设计呈现在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姿态。其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卷宗移送制度。卷宗作为大陆法系刑事诉讼事实与证据的重要载体,在英美法系没有类似的对应物。我国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曾尝试借鉴日本的起诉状一本主义而实行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但是卷宗移送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根深蒂固,因此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制度在实践中变得毫无意义,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重新调整为全部卷宗移送制度。
施鹏鹏教授批评指出:“在比较法上,这是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很难想象一个奉行职权主义传统、刑事实体法几乎沿袭欧陆国家做法的国度里,英美证据法的术语体系乃至运行规则却在理论及实践中大行其道……中国的证据法学研究应走出‘英美法中心’的陷阱,走向更契合本国诉讼文化的‘欧陆’证据法学。”(20)前引,施鹏鹏文。也许有人会说,日本也存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分别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个轨道上运行的问题。事实上,日本学界很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进行过一定的调整,最终日本的刑事诉讼走向混合主义模式。但这种混合主义的模式在日本国内也备受批评。二战后,以大陆法系为蓝本的1907年《日本刑法典》沿用至今,日本刑法的大陆法系传统一直被传承。但是,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虽说是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按照英美法当事人主义模式进行修改的,但职权主义的底色仍然存在。正如小野清一郎所言:“刑事诉讼以职权主义为基本,这在旧刑事诉讼法和新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主义被明显地加强了。”(21)前引⑩,小野清一郎书,第205页。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敏锐地指出:“这样,由于日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有矛盾,……不是将刑法按照美国刑法的方式进行修改,就是将诉讼法按照德国的方式进行修改,二者之中必须择一。”(22)[日]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黎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102页。日本终究还是“无法跳脱在这两种主义间徘徊”。(23)何赖杰:《论刑事诉讼法之传承与变革——从我国与德国晚近刑事诉讼法谈起》,载台湾地区《月旦法学教室》2011年第100期。事实上,当今的日本刑事诉讼法并非完全沿袭英美法系,而是大量吸收了大陆法系的合理因素,并且大陆法系传统在实践中更加明显。日本学者松尾浩也指出,“恰如其分地说应当是,日本对于英美法在理念上吸收了不少,但是几乎没有渗透到现实运作中,……其结果,日本的刑事程序,从侦查到审判与美国的刑事程序呈现出显著的不同,……对此现象,用一句话概括,抑或称之为精密司法吧”。(24)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下),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1999年版,第158页。
四、 跨越实体与程序鸿沟的路径
刑事一体化要真正步入深度一体化时代,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深度交叉和融合是必须要跨出的关键一步。
(一) 从客观叙事到微观命题的转向
要实现实体与程序的高度融合、深度交叉,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呼吁层面、宏观架构层面,而要着眼于微观问题的研究。要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深度融合,理论研究就必须要实现“从天上到地面”的转变。
首先,理论研究应该关注实体与程序互动融合的具体制度。事实上,有些具体制度原本就是实体和程序高度融合的,这些具体制度大多是微观的,但是理论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更缺乏对这些具体制度的深入交叉研究。不能因为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之中就归为单纯的程序问题,而与实体法完全割裂;反之亦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融会贯通的问题比比皆是: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该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规定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之中,但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基本特征是程序从简、实体从宽,(25)参见孙谦:《检察机关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前者是程序问题,后者是实体问题。为什么认罪认罚案件可以简化程序?简化到何种程度?如何保障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如何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权利?这些均是程序问题;而为什么可以从宽?从宽到何种程度?与刑法中坦白、自首是何种关系?与罪刑法定的关系、与罪刑均衡是何种关系?与刑罚理论中预防刑和责任刑是何种关系?这些均是实体问题。但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之中,与刑事诉讼法学界的研究如火如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刑法学界的反应非常“冷淡”,研究者(研究成果)甚少,一些刑法学者甚至质疑刑事诉讼法凭什么规定“实体从宽”,认为只有刑法也能进行相应的修改,才能实现认罪认罚从宽。类似观点均是缺乏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化思想的表现。再比如追诉时效制度。这同样是典型的实体与程序交织的问题,有的国家把追诉时效问题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如日本;而我国的追诉时效制度则规定在刑法中的。正因如此,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因为这一制度没有规定在诉讼法典之中,而较少谈论;而刑法学教科书,也因为这一制度本质上并非实体问题,而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从而导致这个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成为一块“研究飞地”。除此之外,像推定制度、存疑有利于被告制度等均是实体与程序交织的问题。
其实,某些所谓的刑法实体疑难问题,只有运用程序思维,才能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例如,在“昆山反杀案”中,有刑法学者质疑:“涉及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的性质认定问题,行为性质的认定问题也能由公安机关决定吗?人命关天的事,没有律师代表死者在法庭上辩论就作出结论,是否有失公平?这样的做法是否与中央‘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方案背道而驰?”(26)参见《感谢网友们辛苦“拍砖”,冯军的回应都在这里了》,载“法律与生活杂志”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k-1lJzK7M3yeEMlNv2G1Cw,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9月17日。这正是缺乏程序法思维的体现。首先,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无罪的行为由公安机关撤案并无不当。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就是任何人未经判决确定有罪前,应推定其无罪。但是,由此能不能推导出要确定一个人无罪也必须经法院判决呢?显然不能。要让法院对天下所有无罪之人都判决无罪,类似于颁发“良民证”,岂不荒谬?无罪推定原则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在判决前推定其无罪,从而有效保障其各项诉讼权利,并让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从而成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由的壁垒”。(27)参见陈光中等:《论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因此,要确定某个人构成犯罪,必须经法院判决;要想确定某个人无罪,则未必都要经过法院判决。其次,如果明显不构成犯罪的正当防卫案件都要由法院判决,那么,在法院判决之前,必然涉及对防卫人的刑事强制措施,可能导致无谓的长期羁押,这不利于保障防卫人的人权。试想,一个无罪之人为了等待法院的一纸无罪判决,却无谓地牺牲自由,无法令人接受!即便是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依然会影响当事人的重大权利。(28)参见李勇:《正当防卫的实体及程序难题研究》,载《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18期。
其次,实体法研究结论需要顾及证明问题。毋庸置疑,刑法学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具有特定的话语体系,理论的体系化、精细化、教义化都是必要的。但是刑法学终究是要解决实践问题的,实践性始终是刑法学的品格。为解决微观的具体实践问题,刑法理论研究成果或者解决方案的提出,就必要考虑实践中能否操作和运用,而操作性的直接体现就是证明问题。刑法适用的前提是事实认定,而事实是依赖于证据和证明来认定的,实体形成的过程就是证明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证明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接头处”。例如,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在论及此罪与彼罪区分标准时,动辄提及“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有无流氓动机”“有无追求性刺激动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等标准,罪名之间的界限竟然取决于“行为人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不仅遮蔽了对个罪行为本质特征的研究;而且在证据证明问题上也是“难以操作”的。试问:行为人“心里想什么”在证据上如何证明?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明方法或许就是获得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如此看来,导致“口供是证据之王”“口供中心主义盛行”现象,刑法学理论也难辞其咎。笔者坚定地坚守结果无价值论的基本立场,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笔者从司法实践中感受到行为无价值论对主观要素的侧重所产生的“切肤之痛”。(29)参见李勇:《结果无价值论的实践性展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以下。同样,有学者认为互殴是参与者在伤害故意和斗殴意图的支配下所实施的相互伤害的行为,并认为斗殴意图是指基于欺凌、报复、逞强斗狠、寻求刺激等动机而主动挑起斗殴或积极参与斗殴的主观心态(即伤害故意+斗殴意图)。(30)参见邹兵建:《互殴概念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但是,让笔者不解的是,这里的“欺凌、报复、逞强斗狠、寻求刺激的动机”如何证明?在证据上如何区分出于防卫的动机还是出于报复的动机?(31)参见李勇:《互殴与防卫关系之检讨——以类型化的实体与程序规则构建为中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4期。再如,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所提出所谓的直接因果关系与间接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与偶然因果关系,可是,从证据上如何证明是直接还是间接、是必然还是偶然?丝毫不考虑证明问题的刑法理论观点难以被司法实践所接受,也难以对司法实践有所贡献。这是加剧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证明问题还直接影响刑法立法(微观的具体条文的设定)。刑法会因为罪名的某些要素难以证明,而逐渐淡化乃至取消该构成要件要素,甚至会直接在刑法中规定证明责任倒置。例如,《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修改,删除了该罪“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使其从具体危险犯转变为抽象危险犯。对此,刑法理论上一般从风险社会、法益保护前置化等角度来论证这一修正的原因,其实,从刑事诉讼的角度(证明的角度),乃是因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在实践中几乎无法证明,删除是基于降低证明难度的考量。
同样,刑法中有些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因为难以证明会导致该罪名的“僵尸化”,例如,赌博罪中规定的“以赌博为业”就是如此,在一个法律上禁止赌博的国家,如何证明一个人是以赌博为业呢?正因如此,司法实践中因以赌博为业被判以赌博罪的案件几乎没有发生过,立法规定在实践中被“僵尸化”了。再如,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作为受贿罪必备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在实践中同样难以证明。正因如此,最高司法机关不断通过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等来弱化、消解这一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事实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总之,上述这些问题,从宏观层面高谈阔论刑事一体化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从具体的问题入手,从微观层面进行观察和研究。
(二) 从理论建构到解释学的转向
刑法教义学的发达促进了解释学的精细化,使我们有一种感觉,即刑法中所有的条文几乎都被研究过;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解释学较为落后,似乎感觉,刑事诉讼法中条文都没有被真正深入研究过。究其原委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多年来习惯于进行“理论建构”而忽略具体条文的解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与刑事诉讼法典本身的长期不稳定有关)。长期以来,粗线条的研究和落后的解释学,直接投射到立法技术的粗糙上。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出现了两个令人诧异之处:一是仅因增加部分条文,而打乱全部法典的条文序号;二是修改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个“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规定放在修正决定的最后一条,看似不起眼,实则兹事体大。素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如此大的修改——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诉讼制度,还调整了整个法典的条文序号,司法实务部门在极短时间内来不及修改法律文书的条文引用,对新制度的适用更是需要很长一段适应期。这与刑事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抓大放小”进行宏观的理论架构研究而忽略微观的解释学研究史有关。
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不发达,刑事诉讼法学者是有责任的,刑事诉讼法学者应当借鉴刑法教义学的方法和成果来提高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水平。同样,刑法学者也有责任和义务来推动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研究。比如,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对于什么是非法证据、什么是瑕疵证据,二者如何区分,远未形成共识。刑事诉讼法第56条对物证、书证的排除设定了“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条件,但如何理解“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学界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了“严禁引诱、欺骗”,而第56条没有列举“引诱、欺骗”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引诱、欺骗所取得的证据要不要作为非法证据排除,什么情况下排除,都需要精细化的解释学研究。笔者曾尝试将刑法学中的实质解释论引入到刑事证据法的解释之中,对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分提出先形式判断后实质判断的“二分法”,实践证明是富有成效的。(32)参见李勇:《刑事证据审查三步法则》,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以下。笔者还尝试将刑法中犯罪构成阶层论的思维引入到证据法的解释中,提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之间的二阶层关系,在判断顺序上,与犯罪构成三阶层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第一步先判断证据的证据能力,如果没有证据能力,直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进而无须第二步的判断;如果有证据能力,才进入第二步的证明力判断。(33)参见李勇:《重视证据能力与证明力之证据判断功能》,载《检察日报》2017年12月31日。
(三) 两大法系从裂解走向弥合
如前所述,我国的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分别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个轨道上前行。对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改革来说,既要合理借鉴英美法系的合理因素,更要吸收大陆法系的基本制度。但是,多年来,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从基本概念到制度设计,忽略了我国整体上属于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传统,盲目推崇英美法系。这种现象值得反思。例如,非法证据排除在美国是指证据准入资格,也就是排除其进入法庭、被陪审团接触的资格。一些学者盲目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也界定为证据进入法庭的准入资格问题,其实我国既没有陪审团,也不存在非法证据不得进入法庭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问题。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其实与德国类似,是指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也就是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属于证据使用禁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和第56条恰恰对应于德国的证据法理论中的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我们需要转换思路,拉近与大陆法系的距离。再比如,一些学者批评印证证明模式,(34)参见周洪波:《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事实上,印证是大陆法系普遍遵守的经典证明规则,特别是言词证据的审查。19世纪享誉欧洲的德国证据法大师密特麦尔指出,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基础条件之一就是“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应形成印证”。(35)前引,施鹏鹏文。印证作为判断证明力的基本方法,与我国整体上属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结构是相适应的,也与我国刑事诉讼的现实和传统是相适应的。(36)参见李勇:《印证证明模式的重新审视》,载《人民检察》2019年第5期;《坚守印证证明模式》,载《检察日报》2015年7月9日。实体刑法上的大陆法系传统与刑事诉讼法上的英美法系传统,理论上英美法系占据话语主导权与实践上亲近大陆法系,这双重矛盾或许是导致我们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诸多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
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要优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制度,但是这种判断可能是存在问题的。职权主义原则是否一定不妥?当事人主义是否一定优于职权主义?这都必须慎重考虑。德国的刑事制度采取职权原则与调查原则的制度,并未见有人批评该国司法制度不符合时代需求或司法欠缺公信力。(37)参见张丽卿:《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证据》,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1999年5月13日至16日,在德国Halle大学举行的刑法学家年会上,日本学者高田昭正、宫泽浩一、山中敬一等教授都毫不讳言地指出,日本虽然实施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诉讼制度,却仍有许多制度上的问题必须借鉴德国的经验,高田教授更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台湾地区应该寻找适合自身情况的刑事诉讼制度,不必学习美国,也不必向往日本。(38)参见前引,张丽卿书,第8页。笔者观察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德国刑法学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对刑事诉讼法学都有一些交叉研究,而且基本都对大陆法系的刑事诉讼制度赞赏有加,前文提到的林钰雄教授如此,张丽卿教授亦如此。我国台湾地区著名的刑法学家林山田教授更加尖锐地指出:“别迷失在主义的丛林中,美国当事人进行主义已经沦为诉讼禁忌,而非发现真实,日本的以当事人进行主义为外表的制度,已经有审判空洞化的危机,这件事是让我们忧心,难道只要采取当事人进行主义,就能将刑事司法的一切弊端都改革了吗?”(39)前引,张丽卿书,第4页。我们似乎应当关注比较证据法学者达玛斯卡所提醒的:“必须回到他们自己的法律文化中,在那里才能寻找到他们正在衰败之制度的疾患治疗法。”(40)[美]米尔建·R. 达玛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210页。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大陆法系,逐步与刑事实体法在法系方向上逐步靠近、弥合,实现实体与程序的深度交叉和融合。
五、 结 语
刑事一体化在观念层面已经取得广泛共识,深入人心,但真正走向深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刑事一体化并非要抹平学科之间的界限,也并非反对专业化、精细化和教义化,而是要以开放和交叉的思维研究具体的法律问题,这样更能促进各自学科的深入发展。如果说,此前的刑事一体化处于理念倡导和宏观呼吁的历史阶段,那么,现在就到了“深度一体化”的时代!深度一体化就是高度的融合和深度的交叉,而真正高度融合、深度交叉的问题大都寄生于具体的法律争端、具体的实践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越刑事实体与程序的鸿沟是深度刑事一体化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