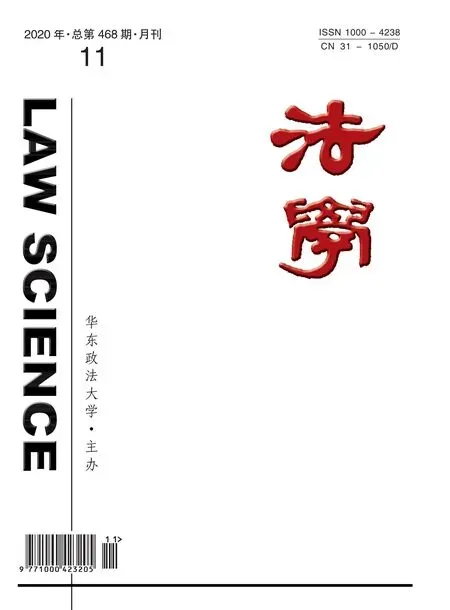领取无正当原因汇款的行为性质
张明楷
行为人(持卡人、存折名义人)利用自己名义的储蓄卡(存折)领取无正当原因的汇款(存款)的行为,〔1〕持存折取款与持储蓄卡取款的行为性质相同,本文通常将行为主体表述为持卡人、收款人。除了被害人将现金交由银行职员转款外,大多是被害人直接从自己的存折或者储蓄卡中将存款汇入他人账户。本文根据案件与语境有时表述为汇款,有时表述为存款。主要有三类情形。(1)汇款人乙本欲向丙的储蓄卡汇款,但因为误写账号将2 万元汇入甲的储蓄卡。甲明知是错误汇款,却从银行柜台或自动取款机中取出2 万元现金(案例1)。〔2〕此外还有银行错误记账或者银行本身错误转款的情形,本文主要以错误汇款为例讨论。(2)持卡人(诈骗犯)欺骗他人,使他人将款项汇入自己的储蓄卡,然后从银行取出现金(案例2)。〔3〕在实践中,还存在通过敲诈勒索等犯罪获得他人汇款的情形,本文仅以诈骗罪为例讨论。(3)持卡人取出他人诈骗所得的汇款,其中,一种情形是持卡人将自己的储蓄卡交给他人使用(无电信诈骗的通谋),在他人实施电信诈骗后,通过挂失领取现金(案例3);另一种情形是持卡人明知诈骗犯(误)将诈骗所得汇入自己的储蓄卡,仍然从银行领取现金(案例4)。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分别讨论上述三类行为的性质,虽然对错误汇款讨论较多,但是没有联系后两种情形展开系统研究。其实,上述三类行为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行为人(持卡人)从银行领取了没有正当原因的现金。案例1 的持卡人事实上取得了没有原因关系的存款债权,属于不当得利;案例2~4的持卡人基于自己或他人的诈骗犯罪在事实上也取得了存款债权,属于不法所得,领取现金的行为所涉及的问题相同。〔4〕参见[日]福嶋一訓:《判批》,《警察公論》第69 卷(2014 年)第5 号,第91 页。既然如此,就应当对三种情形进行体系性讨论,否则,就会导致相关案件的处理不协调。
对上述三类取款行为的处理,至少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持卡人是否取得存款债权以及是否具有取款权利?如果有,对持卡人的取款行为要么认定为无罪,要么充其量认定为侵占罪,案例4 的部分情形可能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无,则对持卡人的取款行为可能认定为诈骗罪或盗窃罪。第二,如何理解和判断刑法上的占有?倘若认为持卡人法律上占有了存款债权乃至银行现金,并认为法律上的占有排斥事实上的占有,那么,对持卡人的取款行为要么认定为无罪,要么充其量认定为侵占罪;倘若持相反观点,持卡人的取款行为都可能构成诈骗罪或盗窃罪。第三,是否承认侵占后的取得、取得后的取得等情形,即在一个行为针对某一财产成立侵占罪或者盗窃、诈骗等取得罪之后,行为人以及第三者能否再针对该财产成立取得罪?〔5〕本文所称取得罪,一般是指转移占有的诈骗罪、盗窃罪,而不包括侵占罪(但本文第三节的标题除外)。如若持否定结论,则取款行为大多不成立取得罪;如若持肯定回答,则取款行为仍然可能再成立取得罪。
本文尝试对上述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但由于三个问题均与民商法关系密切,且相关问题在民商法学界存在争论,笔者实在力所不及、虑所不逮,本文只是投石问路、抛砖引玉。
一、取款的权利
众所周知,德国的刑法判例否认错误汇款的收款人领取汇款的行为成立欺骗罪。例如,乙误向甲的银行账户汇款1 万欧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93 年11 月16 日的判例,根据其民法规定认为甲取得了对银行的有效债权,即使向银行请求支付,也不属于虚假的表示。〔6〕Vgl. BGHSt 39, 392.对错误记账案件的处理也是如此。例如,银行职员给A 的账户错误地多记载了存款金额,A 发现后向银行请求支付。虽然以前的判例认定A 的行为构成诈骗罪,〔7〕Vgl. OLG Köln, JR 1961, 433f.但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2000 年11 月8 日的判决认为,这种情形应当与错误汇款的处理相同,即不认定为诈骗罪。〔8〕Vgl. BGHSt 46, 196.德国也没有将领取错误汇款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的判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德国民法典》第780 条、第781 条的规定,〔9〕《德国民法典》第780 条规定:“为使以通过合同而独立成立债务的方式约定给付的合同(债务约定)有效,如果没有规定其他形式,需采用书面形式约定。”第781 条规定:“为使通过承认债务关系存在(债务承认)的合同有效,需采用书面形式给予承认的意思表示。对承认其存在的债务关系的成立规定有其他形式的,承认合同需采用此种形式。”债务约定、债务承担等法律行为的适法的成立完全不依赖于其“权源”或“原因”;无因性原则贯穿到了德国《民法》的全部体系中。〔10〕参见陈华彬:《罗马法上的traditio、stipulatio 与私法上无因性概念的形成》,载《中国法学》2009 年第5 期。与产生错误的原因没有关系,收款人的取款请求权由来于《德国民法典》第780 条所规定的存在抽象的债务的约束。〔11〕参见[日]松宫孝明:《誤振込と財産犯の解釈および立法》,《立命館法学》第278 号(2001 年),第1004 页。于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无论是在银行错误记账还是第三人错误转账的情况下,行为人账户上所反映出来的即时的存款余额都是正当有效的……错误并不影响账户上所显示的余额的有效性。”〔12〕参见徐凌波:《德国银行卡滥用行为的理论与实务》,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23 页。换言之,账户名义人对其账户上所享有的余额是有效的,即使是自己或者他人诈骗所得的存款债权,也不影响银行向持卡人交付金钱的有效性。根据法秩序统一性的原理,其中不仅没有构成诈骗、盗窃等取得罪的可能性,亦无构成侵占罪的可能性。〔13〕德国《刑法》规定的侵占罪的对象仅限于狭义财物,而不包括债权等财产性利益。于是,不仅上述案例1 的行为不成立侵占罪与取得罪,而且案例2~4 的取款行为也不成立侵占罪与取得罪。
与德国不同,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刑民判例均否认收款人对错误汇款享有存款债权和取款权限,进而对取款行为认定为取得罪。〔14〕参见名古屋高等裁判所1976 年1 月28 日判决,《判例タイムズ》第337 号,第260 页;鹿儿岛地方裁判所1989 年11 月27 日判决,《判例タイムズ》第718 号,第124 页;东京地方裁判所1990 年10 月25 日判决,《判例时报》1338 号,第80 页;东京高等裁判所1991 年11 月28 日判决,《金融法務事情》第1308 号,第31 页。不过,好戏还在后头。错误汇款人在收款人的债权人申请裁判所冻结收款人的账户时,提起了第三人异议之诉。东京地方裁判所(1990 年10 月25 日第一审判决)与东京高等裁判所(1991 年11 月28 日原审判决)均否认了收款人享有存款债权,但日本最高裁判所认为,从汇款请求人汇款到收款人的银行普通存款账户时,不管两者间是否存在作为汇款原因的法律关系,收款人与银行间就成立了与汇款金额相当的普通存款合同,收款人对银行取得了与上述金额相当的普通存款债权。汇款人只能向收款人提起同额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而驳回了第三人异议之诉(以下简称“日本平成8 年判决”)。〔15〕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1996 年4 月26 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第50 卷第5 号,第1267 页。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判决在学界引起了巨大争议,也导致了日本部分学者对领取错误汇款的行为主张无罪说或者遗忘物侵占罪(侵占脱离占有物罪)说。
无罪说否认遗忘物侵占罪的理由是,存款债权属于财产性利益,不是侵占罪对象中的他人的“物”;错误汇款不是“遗忘”物,因为遗忘物是指不是基于他人本意脱离他人占有的财物,被害人没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但错误汇款人是基于转移所有权的意思转移存款的,故转出的存款不属于“遗忘”物。否认取得罪的理由是,收款人取得了汇入行的存款债权,享有正当的取款权限,其取款行为是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而不是欺骗行为;基于同样的理由,收款人从自动取款机取款的行为,也不可能成立盗窃罪。而且,银行也没有任何财产损失。〔16〕参见松宫孝明:《过剩入金と财産罪》,《立命館法学》第249 号(1996 年),第404 页以下;同前注〔11〕,松宫孝明文,第999页以下;[日]川口浩一:《誤振込と诈欺罪》,《奈良法学会雑誌》第13 卷(2000 年)第2 号,第22 页以下;[日]赤根智子、高橋克明:《刑法における法律上の占有》,《CHUKYO LAWYER》第4 卷( 2006 年),第117 页以下。不难看出,否认成立遗忘物侵占罪的理由是从行为对象而言的,而否认成立取得罪的理由则是以平成8 年判决为根据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遗忘物侵占罪的对象问题。其一,我国《刑法》中的财物概念,包括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17〕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932 页以下。遗忘物侵占罪中的财物也是如此。换言之,利益侵占在我国也成立侵占罪。其二,不能因为汇款人具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就否认错误汇款属于遗忘物。因为错误汇款不是汇款人的真实意志表示,汇款人没有将存款转移给收款人的意思。亦即,“在错误付款的情形下,付款人可以对错付账户内的资金主张权利,不能简单适用占有即所有的原则”,“付款方和收款方未就债权变动达成合意,付款行为缺乏权属变动的基础法律关系,不产生权属变动的法律后果”。〔18〕王琳:《付款人对错误付款至查封账户的资金可提起阻却执行异议》,载《人民法院报》2018 年1 月11 日,第6 版。所以,在我国,不能否认错误汇款属于汇款人的遗忘物。
在平成8 年判决之后,主张领取错误汇款构成遗忘物侵占罪而不构成取得罪的理由与上述无罪说的理由相同。例如,曾根威彦教授指出,从认为存款的占有归于存款名义人的立场来看,错误汇入自己账户的金钱,就像被错误投递的邮件一样,不是因为受委托而是基于偶然原因归自己占有的物品,行为人将上述金钱取出据为己有的行为,构成侵占脱离占有物罪。〔19〕参见[日]曾根威彦:《刑法各論》(第5 版),弘文堂2012 年版,第171 页。再如,林幹人教授也认为,被取出的汇款,虽说事实上归银行占有,但只要进入自己账户的金钱处于任何时候都能被取出的状态,就应认为银行对存款名义人的支配能力很弱。况且,在民事上,即使乙将款项错误划入甲的账户,甲与银行也成立普通存款合同,取得了普通存款债权。因此,认为行为人甲的取款行为成立诈骗罪、盗窃罪并不妥当,只能认定为侵占脱离占有物罪。〔20〕参见[日]林幹人:《刑法各論》(第2 版),东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81 页。
但是,上述观点在日本的刑法学语境下或许就难以成立。日本《刑法》明文区分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债权属于财产性利益而不是财物。而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行为对象仅限于财物,并不包括财产性利益。既然认为收款人已经取得了存款债权并具有取款权利,那么,将银行的现金作为侵占罪的对象恐怕不合适。因为如后所述,现金属于银行所有和占有,也从来没有脱离银行的占有和所有,而不可能属于汇款人所有和占有。换言之,虽然存款债权可能是遗忘物,但在日本刑法学的语境下,由于存款债权只是财产性利益,所以,侵占存款债权在日本不可能成立侵占脱离占有物罪。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无罪说与侵占罪说都是以平成8 年判决为根据的。但是,不能不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对平成8 年判决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例如,该判决只是驳回了汇款人的诉讼请求,并不意味着刑法应当正面肯定收款人享有支付请求权;〔21〕参见[日]西田典之著、橋爪隆补订:《刑法各論》(第7 版),弘文堂2018 年版,第256 页;[日]木村光江:《財産犯の保護法益》,《現代刑事法》第6 卷(2004 年)第9 号,第111 页以下。该判决虽然肯定收款人取得了存款债权,但并没有从民法上肯定其能够行使该债权。〔22〕参见[日]四方奨:《自己名義の預金口座からの払戻しと詐欺罪について》,《同志社法学》第69 卷(2018 年)第7 号,第1263 页以下。而且,不管是下级裁判所还是最高裁判所,在平成8 年判决之后,仍然将领取错误汇款的行为认定为取得罪。例如,时隔不到2 年,大阪高等裁判将收款人在银行窗口领取错误汇款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23〕参见大阪高等裁判所1998 年3 月18 日判决,《判例タイムズ》第1002 号(1998 年),第290 页。更引人注目的是,日本最高裁判所2003 年(平成15 年)3 月12 日的决定,仍然肯定了领取错误汇款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在错误汇款的场合,银行在实际业务中存在更正程序;对于收款人账户的多余存款是退回给汇款人还是支付给收款人,是需要由银行来决定的重要事项;为了让银行采取更正程序,错误汇款的收款人有义务将真相告知银行(诚实信用法则上的义务);行为人隐瞒真相取走存款的,成立诈骗罪(以下简称平成15 年决定)。〔24〕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2003 年3 月12 日决定,载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57 卷第3 号,第304 页以下。诚然,如何在理论上说明平成15 年决定与平成8 年判决的协调性(法秩序的统一性)是另一问题,〔25〕不少学者认为二者并不存在矛盾。例如,有学者指出:“向银行告知了错误汇款事实的取款请求,在刑法上没有违反告知义务,不成立诈骗罪,因而是适法的。而且,在民事法上,由于取款人的告知,给银行提供了采取调查确认措施、扣划措施的机会,也应认为是适法的。因此,告知错误汇款事实之后的取款行为,在民刑两法中都是适当的……因此,不告知错误汇款事实的取款请求,在民刑两法中都认为是违法的。”(同前注〔22〕,四方奨文,第1267 页)。但不应直接根据平成8 年判决否认收款人的取款行为成立取得罪。
第二,被平成8 年判决推翻的原审判决否认收款人取得存款债权的观点,得到了许多民法学者的赞成。〔26〕参见[日]塩崎勤:《誤振込による預金に対する差押えと振込依頼人からの第三者異議の诉えの拒否》,《金融法務事情》第1299 号(1991 年),第11 页;[日]木南敦:《誤った振込と預金の成否》,《金融法務事情》第1304 号(1991 年),第7 页;[日]山田誠一:《誤った资金移動取引と不当得利(下)》,《金融法務事情》第1325 号(1992 年),第23 页以下;[日] 渡辺隆生:《誤った振込依頼と預金の成否》,《金融法務事情》第1345 号(1993 年),第10 页;[日] 牧野英之:《判批》,《判例タイムズ》第821 号(1993 年),第64 页以下;[日]滝沢昌彦:《判批》,《ジュリスト》第1018 号(1993 年),第118 页以下;[日]西澤宗英:《判批》,《判例評論》第407 号(1993 年),第189页以下;等等。换言之,平成8 年判决并没有得到民法学界的一致认同,相反,有民法学者指出:“只要有入款记账就发生存款债权的最高裁判所平成8 年判决,是只考虑银行方便的判决,是给予没有原因关系的收款人‘天上掉馅饼’式利益的不当判决,反而会导致对银行信赖的崩溃,因此受到了学说的严厉批判。”〔27〕[日]加賀山茂:《振込と誤振込の民法理論》,《明治学院大学法科大学院ローレビュー》第18 号(2013 年),第2 页。换言之,根据部分民法学者的观点,在民事法上原本就不能承认收款人对错误汇款取得了存款债权。亦即,“在错误汇款的案件中,由于汇款人与(现实的)收款人之间并不存在使金钱的支付具有正当性的原因关系(如买卖关系中的对价支付义务等),所以,也可能以银行汇款的清算手段性(收款人不存在接收无原因关系的汇款的意思)、收款人的天上掉馅饼式的利益性(收款人不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等为根据,认为收款人就错误汇款的部分金额不成立存款债权。”〔28〕[日]上田正和:《誤振込みと財産犯の成否について》,《大宮ローレビュー》2005 年创刊号,第77 页。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平成8 年判决在民事上认定了无因的存款债权的成立,但其后最高裁判所平成15 年决定,认定收款人明知其权利欠缺原因而行使该权利的行为成立犯罪。这样的话,如果收款人即使取得了无因的权利,其行使该权利的行为也成立犯罪,那么,就可以说称不上取得了正当权利。而且,最高裁判所平成15 年决定,尽管是刑事裁判,但也深入到民事上的问题,指出‘基于社会生活上的条理,就错误汇款而言,收款人必须将汇款返还给汇款人等,收款人对错误汇款的相应金额不享有最终归自己的实质的权利’,这就实质上否定了收款人对错误汇款取得存款债权的正当性。这样来考虑的话,可以作出的判断是:最高裁判所平成8 年的判决,由于其后最高裁判所平成15 年决定,实质上丧失了正当性。”〔29〕同前注〔27〕,加賀山茂文,第15 页。换言之,由于最高裁判所平成8 年判决受到了强烈批判,最高裁判所平成15 年决定实质上变更了平成8 年判决。〔30〕同上注,第22 页。
第三,日本最高裁判所其后的民事判例,一方面认为,并不仅仅因为收款人对汇款人负担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就认定其取款请求属于滥用权利,同时又表示,“在领取存款是为了不正当取得与该汇款相关联的现金的行为,是构成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一个环节等情形,当肯定这些情形是明显违反正义的特殊情形时,就属于滥用权利。”〔31〕日本最高裁判所判2008 年10 月10 日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第62 巻第9号,第2361 頁。这一判决是否修正了平成8 年判决,必然见仁见智,但至少可以肯定,如果收款人收到的是自己或者他人诈骗所得的存款,收款人的取款行为就属于滥用权利,因而不是行使权利的合法行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3 年的判例。被告人知道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普通存款账户的存款,是他人通过诈骗等犯罪行为而汇入,但仍然分别从银行柜台和自动取款机取出现金。一审法院对上述行为分别认定为诈骗罪与盗窃罪。被告人上诉后,东京高等裁判所2013 年的判决维持了原判(以下简称“平成25 年判例”)。判决指出:“银行对有被犯罪利用的嫌疑存款账户采取冻结账户等措施,是基于普通存款规定所做的处理,与此同时,也是救济法所期待的。〔32〕根据日本《犯罪利用預金口座等に係る資金による被害回復分配金の支払等に関する法律》(日本学者一般将此法简称为“救济法”)的规定,存款账户有被犯罪利用的嫌疑时,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停止该账户交易等措施,通过采取公告等程序后使存款债权消灭。因此,银行为了免受违反救济法旨趣的非难,也为了避免卷入汇款诈骗等的被害人与汇款的收款人(存款账户名义人)之间的纷争,当然会对可疑账户采取账户冻结等措施。这样的话,被诈骗等犯罪行为利用的账户的存款债权,即使作为债权而存在,但该债权具有如果银行知道了该事实就要通过冻结账户措施使收款人不能取款的性质,在此范围内权利的行使便受到制约。因此,在上述普通存款规定上,账户名义人知道自己的账户被诈骗等犯罪行为利用时,由于给银行采取冻结存款账户等措施提供了机会,所以,具有向银行告知这一事实上的诚实信用的义务,没有隐匿这一事实而提取存款的权限……本案被告人没有提取存款的正当权限,但却伪装成有提取存款的权限而请求取款的,就属于欺骗行为;被告人利用储蓄卡从自动取款机取出现金的行为,违反了存款管理者以及自动取款机的管理者的意志,构成盗窃罪。”〔33〕东京高等裁判所2013 年9月4 日判决,《判例時報》第2218 号(2013 年),第134 页。
日本学者们也是在与平成8年判决相关联的角度讨论平成25 年判例的。亦即,根据平成8 年判决,在为了迅速处理多数、多额的资金流动而进行的汇款中,不管汇款人与收款人之间是否存在作为原因的法律关系,收款人都取得了普通存款债权。与错误汇款不同,汇款诈骗好歹存在原因关系(即具有向指定账户汇款的意思),没有理由否认存款债权的取得。果真如此,则更难将取款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盗窃罪。〔34〕参见[日]田中优辉:《犯罪行為により自己名義口座に振り込まれた預金の払戻しと詐欺罪·窃盗罪の成否》,《広島法学》第40 巻(2017 年)第3 号,第313 页以下。即使如此,平成25 年判例仍然肯定了诈骗罪、盗窃罪的成立。据此,即使收款人享有存款债权,但以不正当取得存款为目的而请求取款时,就属于滥用权利而不被允许,银行如果知情却仍然支付存款的,则对汇款人承担侵权责任。〔35〕参见[日] 石丸将利:《最高裁判所判例解説民事篇·平成20 年度》,法曹会出版社1991 年版,第523 頁以下。
第四,在平成8 年判决之后,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仍然认为领取无正当理由汇款的行为成立取得罪。主要观点如下:(1)收款人没有领取存款的权限,其隐瞒事实领取存款的行为属于诈骗行为。这一观点并不正面肯定平成8 年判决,而是认为,即使事实上可能领取存款,但在刑法上没有正当权限时,原本就不应当认定收款人对错误汇款享有正当权限,故应当否认其法律上的占有。就事实上的占有而言,虽然可能承认收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但不能认为收款人事实上占有了现金,相反应认定银行管理者占有了现金,因此,收款人的取款行为成立取得罪。〔36〕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論)》,有斐阁2005 年第3 版增补版,第694 页;[日]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成文堂2015 年新版第4 版補訂版,第300 頁;同前注〔21〕,西田典之、橋爪隆书,第255-256 頁; [日]山口厚:《刑法各論》(第2 版),有斐阁2010 年版,第296-297 页;[日]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有斐阁2016 年版,第301 页。(2)不需要考虑收款人是否具有领取存款的正当权限,只需要考虑收款人领取存款时汇入行如果知道真相时会如何处理。由于汇入行知道真相将不会支付现金,故认定收款人的行为成立诈骗罪。〔37〕参见[日] 渡辺恵一:《誤って振り込まれた預金の引出し行為と犯罪の成否》,《研修》第599 号(1998 年),第113 页以下;[日]宫崎英一:《判解》,《法曹时报》第58 卷(2006 年)第6 号,第220 页以下。(3)收款人违反告知义务,成立不作为的诈骗。〔38〕参见[日] 大谷實:《誤振込みによる預金の払戻と刑法上の取扱い》,《研修》第662 号(2003 年),第11 页;同前注〔22〕,四方奨文,第1264 页以下。(4)收款人与汇入行虽然成立存款债权债务关系,但由于不存在原因关系,故收款人不具有领取存款的实质理由,收款人的取款行为属于滥用权利,因而构成诈骗罪。〔39〕参见[日]佐藤文哉:《误って振りこまれた預金の引出しと財産犯》,《佐佐木史朗喜寿祝贺:刑事法の理论と实践》,第一法规出版社2002 年版,第338 页。日本也有民法学者以平成8 年判决为前提,认为收款人的取款行为属于滥用权利(参见[日]中田裕康:《判批》,《法学教室》194 号(1996 年),第131 页)。(5)根据救济法的规定,银行对可疑账户有采取停止交易的权利,故收款人丧失了取款的正当权利。换言之,银行不仅要作为储蓄制度的运营者维持业务的顺利展开,而且必须对背后的被害人进行救济,进而作为主体保管现金。就此而言,与收款人或存款债权人的地位相比,银行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银行的这一利益值得刑法保护,所以收款人隐瞒真相取款的行为,对银行成立诈骗罪或者盗窃罪。〔40〕参见[日]照沼亮介:《預金口座内の金銭の法的性質》(3),《上智法学論集》第58 卷(2014 年)第1 号,第68 页以下。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平成8 年判决的观点没有得到日本民法学界的一致认可,相反受到了部分学者的严厉批判,平成15 年决定实质上变更了平成8 年判决。其二,平成8 年判决并没有妨碍刑事审判对领取无正当原因的汇款的行为认定为取得罪。换言之,即使认为收款人取得了存款债权,也依然可能将领取没有正当原因的汇款的行为认定为取得罪。其三,如若认为收款人没有取得存款债权或者不享有取款的权利,其领取没有正当原因汇款的行为便成立取得罪,而不是侵占罪或者无罪。
我国民事立法并无关于债权约定、债权承担的无因性规定,对此民法学者存在不同观点。根据原因关系必要说,在探讨错误汇款三角关系不当得利问题时,应着眼于错误汇款人与收款人之间是否存在原因关系。错误汇款属于欠缺原因关系的交易行为,因此汇入银行与收款人之间的存款合同关系即不能有效成立。反之,原因关系不必要说认为,系争存款债权的成立与否,不取决于原因关系之有无。即便错误汇款人享有委托汇款合同的撤销权,也不影响收款人存款债权的成立。〔41〕参见其木提:《错误转账付款返还请求权的救济路径》,载《法学》2020 年第2 期。本文不可能介入民法领域展开讨论,只是基于对相关规定的理解,认为部门规章否定了无正当原因的收款人取得存款债权和享有取款权利。
例如,《储蓄管理条例》第3 条第1 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显然,只有将货币存入储蓄机构,才能取得存款债权。据此,银行因为错误记账导致账户名义人的“存款额”增加时,由于不存在将货币存入储蓄机构的事实,故不能认定收款人取得了存款(债权)。错误汇款时,收款人也没有将货币存入金融机构,故性质是一样的,收款人也不可能取得存款债权。当然,在错误汇款时,由于他人将货币存入储蓄机构,收款人的存款(债权)似乎具有事实根据。〔42〕参见李强:《日本刑法中“存款的占有”:现状、借鉴与启示》,载《清华法学》2010 年第4 期。可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31 条规定:“个人人民币账户的资金以其持有的现金存入或以其工资性款项、属于个人的合法的劳务报酬、投资回报等收入转账存入。”〔43〕《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7 条规定:“借记卡按功能不同分为转账卡(含储蓄卡,下同)、专用卡、储值卡。借记卡不具备透支功能。”显然,就存款与汇款等而言,储蓄卡与存折的功能是相同的。这充分表明,不是基于合法原因转入的款项,都不属于持卡人账户内的资金。在本文看来,这一规定更为明显地否认了无正当原因汇款的收款人享有存款债权。此外,《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47 条规定:“发卡银行通过下列途径追偿透支款项和诈骗款项:(一)扣减持卡人保证金、依法处理抵押物和质物;(二)向保证人追索透支款项;(三)通过司法机关的诉讼程序进行追偿。”这一规定表明,在储蓄卡中所记载的款项是诈骗所得时,持卡人对该款项并不享有存款债权。我们显然不能认为,持卡人享有存款债权,具有领取存款的权利,只是领取后需要被追索或者追回。诚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银发〔1993〕7 号)第13 条规定:“各储蓄机构必须保证储蓄存款的支取,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储蓄存款的提取。”但这是以《储蓄管理条例》第3 条第1 款的规定为前提的,亦即,只有当持卡人支取的是有正当原因的储蓄存款时,储蓄机构才无条件支付。
我国的一些判例也与上述规定相吻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表达了以下观点:错误付款系事实行为,双方无转移该款项的合意,收款方并非该款项的实际权利人,错误付款未与账户内其他资金混同,错误付款人可以以此为由阻却另案执行程序;〔4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89 号判决书。案外人汇款至查封冻结账户的,账户所有人并未实际占有、控制或支配该款项,不具备适用“货币占有即所有原则”的基础条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旨在保护案外人合法的实体权利,在已经查明所涉款项的实体权益属案外人的情况下,应当直接判决停止对所涉款项的执行,以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4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22 号裁定书。人民法院对登记在案外人名下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时,该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法院在审理中应当对该执行财产来源和流转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和认定;〔4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50 号裁定书。“占有即所有”是判断资金所有权性质的一般原则,在无相反证据证明资金的真实权利人与账户所有人不同一的情况下,才适用该一般原则。〔4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31 号裁定书。一些高级人民法院的判例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查封账户冻结后,错误付款至另案被执行人账户的财产,未与该账户原有资金混合,不属于可供执行的对象,原权利人对错误付款的资金享有的权利足以阻却强制执行;〔48〕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终1322 号判决书。资金原权利人有权利要求收款人返还其错误汇出的款项,不当收款人对错误收到的款项不享有所有权。〔49〕参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终205 号判决书。不难看出,上述判例的观点并不同于日本平成8 年判决的结论。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以德国立法、判例与理论观点或者日本平成8 年判决的结论为根据,直接对领取无正当原因汇款的行为得出无罪或者仅成立侵占罪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国主张无罪说或者侵占罪说的学者却大抵都是如此。例如,持侵占罪说的学者指出:“从银行操作流程来看,汇款人弄错了收款人,不仅与银行无关,也不影响该转账的有效性。根据‘谁是存款账户户主谁就是存款债权人’的原理,汇款人的错误汇款或者转账,可以说是汇款人在为收款人设定或者增加存款债权(虽是错误设定,但亦有效)。由此,一旦汇款进入收款人账户,收款人便相应地就该错误的汇款取得对银行的债权。”〔50〕参见钱叶六:《存款占有的归属与财产犯罪的界限》,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2 期,第228 页。上述论者没有论证“谁是存款账户户主谁就是存款债权人”的原理,也没有说明该原理源于何处,其实只是以德国的学说、判例或者日本平成8 年判决为根据。本文难以认为这种观点在我国具有法律根据与实践根据。况且,权利的归属与权利的行使是两个不同概念,承认权利的归属并不必然承认权利的行使。〔51〕参见[日]山口敬介:《判批》,《法学協会雑誌》第128 卷(2011 年)第2 号,第536 页。“虽说是行使权利,但并不是不受制约,行使权利会例外地受到制约。”〔52〕同前注〔22〕,四方奨文,第1263 页。
二、占有的判断
以上分析只触及一种可能性。换言之,收款人对无正当原因的汇款享有存款债权,则是另一种可能。所以,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倘若收款人对无正当原因的汇款享有存款债权,能否将其从银行领取现金的行为认定为取得罪?这便涉及存款的法律上的占有与事实上的占有以及占有的要保护性问题。
众所周知,盗窃等取得罪中被害人的占有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被害人是否占有财物,是区分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关键。委托物侵占罪中的代为保管,其实就是受委托占有他人所有的财物。〔53〕同前注〔17〕,张明楷书,第966 页。从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关系来说,侵占罪中的占有原本也应只是事实上的占有。日本《刑法》明文规定委托物侵占罪的对象是“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但是,日本的判例与学说却对委托物侵占罪中的占有进行了扩张或者变容,使其中的占有不仅包括事实上的支配,而且包括法律上的支配。〔54〕参见日本大审院1915 年4 月9 日的判决,载日本《大审院刑事判决录》第21 辑,第457 页。
例如,村长将作为村里的基本财产的现金存入银行,然后取出据为己有。日本大审院认定村长的行为构成委托物侵占罪。〔55〕参见日本大审院1912 年10 月8 日的判决,载日本《大审院刑事判决录》第18 辑,第1231 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侵占罪的对象只限于狭义财物,而不包括债权等财产性利益,如果否认村长占有了基于存款的现金,那么,虽然可以就取出的现金认定为委托物侵占罪,但如果在村长将存款汇入他人而不取出现金的场合,就不成立委托物侵占罪,只能认定为背任罪,于是有失罪刑均衡。因此,判例与通说肯定基于存款的现金的占有。〔56〕同前注〔21〕,西田典之、橋爪隆书,第255 页;同前注〔36〕,山口厚书,第295 页。但这种占有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占有,而不是事实上的占有。亦即,村长虽然事实上没有占有与存款债权对应的现金,但在法律上占有了该现金。只有进行这样的扩张解释,才能认定村长将受委托占有变为所有,进而肯定委托物侵占罪的成立。
但是,对基于存款的现金的占有,显然不是由取款可能性这种事实上的支配来奠定基础的。这是因为,如果说只要行为人具有取款可能性就占有了基于存款的现金,那么,行为人窃取他人储蓄卡与密码后也具有取款可能性,于是只对取款行为认定为侵占罪,而不是认定为取得罪,这显然不妥当。反过来说,对基于存款的现金的占有是基于在银行与存款人的关系上所认可的取款权限。由于行为人具有取款权限,就不可能用法律手段阻止银行的付款,或者说,银行利益没有要保护性,故取款行为对银行不成立犯罪。因此,只得承认具有取款权限的人对基于存款的现金的占有。〔57〕同上注,山口厚书。简言之,由于日本侵占罪的对象只能是狭义财物,又由于行为人具有取款权限,才承认其对基于存款的现金(狭义财物)的法律上的占有。
由此可见,法律上的占有是日本裁判所为了扩大委托物侵占罪的处罚范围而形成的概念,而且事实上仅在委托物侵占罪与业务侵占罪中使用该概念。〔58〕对业务侵占罪也使用法律上的占有概念,但无相关判例。倘若侵占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则不需要法律上的占有这一概念。例如,奥地利《刑法》第133 条第1 款规定:“以不法使自己或者第三者获利为目的,取得或者使第三者取得自己受委托管理的财产的,处6 个月以下自由刑或者360 日以下罚金。”根据奥地利最高法院1990 年10 月30 日的判决,受委托管理存款账户时,存款债权本身就是作为财产受刑法保护的。因此,如果受托人违反约定领取现金,就构成对存款债权本身的侵占。〔59〕Vgl.OGH JBl 1991, 808.另一方面,法律上的占有这一概念以具有法律上认可的取款权限为前提,否则就不能称为“法律上”的占有。换言之,不合法的占有不可能成为法律上的占有。正因为如此,日本没有将对领取无正当原因的汇款的行为认定为遗忘物侵占罪的判例,刑法理论的通说也不承认无正当原因的收款人法律上占有了银行的现金。〔60〕同前注〔21〕,西田典之、橋爪隆书,第255 页;[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第6 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15 年版,第168 页。这是因为,“只有对银行存款具有正当的取回权限时,才能认可‘法的支配’,因此,只能在此限度内肯定存款的占有。所以,就错误汇款的案件,不能肯定侵占脱离占有物罪。”〔61〕同前注〔36〕,井田良书,第301 页。
在我国,一般来说,在盗窃、诈骗罪等取得罪中,行为人所取得的正是他人事实上占有的财物,行为人不可能就自己事实上占有的财物构成盗窃、诈骗等取得罪。财产性利益虽然可以成为侵占罪与取得罪的对象,但对财产性利益的占有是事实上的占有,还是法律上的占有,并无深入研究。这是因为,我国刑法理论关于作为盗窃罪对象的占有的解释,基本上源于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但德国所称的占有就是指事实上的支配,而日本仅在委托物侵占罪与业务侵占罪中承认法律上的占有。就如何解释对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而言,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是,可以对狭义财物使用事实上占有的概念,对财产性利益使用法律上占有的概念。事实上占有不以具有正当根据为前提;而对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属于法律上占有,必须具有正当根据,或者说必须有权利享有、支配这个利益。但是,针对不同类型的财物分别使用不同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区分,不仅没有特别意义,而且可能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设定收款人对现金存在法律上的占有、银行对现金存在事实上的占有,进而讨论两种占有是什么关系。
日本有学者认为,“相对于事实上的占有,法律上的占有占据特别法的地位,法律上的占有得到认可的场合,事实上的占有便后退,法律上的占有排斥事实上的占有,这样的关系仅仅在侵占罪中成为问题。相反,法律上的占有被否定的场合,事实上的占有才会露面,仅仅在夺取罪中成为问题。”〔62〕同前注〔16〕,赤根智子、高橋克明文,第112 页。
大体可以肯定的是,当法律上的占有是具有正当原因的占有时,上述观点无疑是成立的。亦即,持卡人享有取款的正当权限时,事实上的占有才后退。例如,持卡人正当取回自己储蓄卡中的存款时,银行无理由拒绝,持卡人的行为不可能对银行构成任何犯罪。但如前所述,日本之所以承认受托者在法律上占有了对应的现金,进而认定受托者领取现金的行为构成委托物侵占罪,既是因为委托物侵占罪的对象只能是狭义财物(只能将现金作为委托物侵占罪的对象),也是为了避免处罚的不均衡(受托人并非取款而是转账时,也认定为对银行现金的侵占,而不是认定为背任罪)。但是,这一问题在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这便使我们丧失了使用法律上占有概念的前提。那么,倘若承认法律上的占有这一概念,“法律上的占有被否认的场合”是指什么场合呢?在这种场合,是否仍然存在法律上的占有呢?显然,如果占有者对利益的占有不具有正当原因,不享有相应的实质权利时,就不存在法律上的占有,当然也要否认法律上的占有。例如,乙欠甲的20 万元赌债,由于甲没有索要赌债的权利,所以,甲并不享有20 万元的债权(财产性利益),即不能认为甲对赌债享有法律上的占有,刑法更不可能保护这种利益。再如,B 对A 实施卖淫行为后,A 拒不支付嫖宿费用。B 也没有权利向A 索要该费用,刑法不可能支持B 的索要行为,否则就意味着刑法保护卖淫行为。所以,不能认为B 法律上占有了这种债权。同样,持卡人储蓄卡中的存款债权源于自己或者第三者的诈骗所得时,不能认为持卡人对该存款债权存在法律上的占有,充其量可以表述为事实上的占有。概言之,将一种基于不正当原因的占有评价为法律上的占有,并不合适。
另一种可能性是,不管是狭义财物还是财产性利益,都使用事实上的占有的概念。这是本文赞同的做法。这是因为,如果说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在我国财产罪中的地位是相同的,就应当采取相同的占有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事实上的占有不以具有正当原因为前提,而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说,即使是无正当原因的占有,也可能值得刑法保护。例如,张三窃取李四所骗取的摩托车。由于李四事实上占有了该摩托车,张三违反李四的意志转移了摩托车的占有,没有疑问成立盗窃罪。显然,刑法对事实上占有的保护,并不必然以占有的合法性为前提。同样,甲实施电信诈骗行为,由于对被害人指定了错误账号,导致被害人将存款汇入乙的储蓄卡时,没有参与共谋的丙通过技术手段从乙的储蓄卡中转走该笔汇款的,无疑成立盗窃罪。基于错误汇款的存款债权也是如此,即收款人事实上占有了存款债权。概言之,承认收款人事实上占有了存款债权,一方面说明第三者骗取或者利用计算机盗取该存款债权的,成立取得罪;另一方面可以说明与收款人事实上的占有相对抗的本权者以及协助本权者收回(扣划)存款债权的行为,不成立犯罪。〔63〕这与盗窃罪等罪的保护法益相关联,同前注〔17〕,张明楷书,第942 页以下。
明确了侵占罪的对象是行为人事实上占有的他人财物或者不是基于他人本意脱离了他人事实上占有的财物,〔64〕一般来说,行为人事实上占有了他人遗忘物后才可能构成侵占罪,只不过该占有不是基于委托关系。而不包括所谓法律上占有的财物,就可以发现我国主张领取无正当原因汇款的行为构成侵占罪的各种观点可能存在的疑问。
第一种观点认为,“存款的占有属于存款的名义人,这一点即便对错误转账的银行存款也适用。”即名义人占有了与存款对应的现金。理由是,“一般来说,存在只要储户愿意,其随时都可以通过在银行的柜台上或者通过自动取款机,取出其账上存款额度之内的金钱。特别是在通过自动取款机取款的场合,银行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审查。这就意味着,储户对于其账户内的金钱,是具有实质上的支配和控制的。对于储户而言,此时的银行不过是一个保险箱或者一种保管财物的手段而已,尽管在形式上看,银行在占有财物,但实际上,在储户的银行账户的范围之内,储户对其财物具有支配、控制权。如此说来,由于某种原因而进入储户的账户之内、本不属于其所有的财物,对于储户而言,属于不当得利,储户必须返还。拒绝返还的场合,一定条件下,构成侵占罪。”〔65〕黎宏:《论存款的占有》,载《人民检察》2008 年第15 期,第21-22 页。这种观点将日本对委托物侵占罪中的法律上的占有直接运用到遗忘物侵占罪中来,本文难以赞同。
关于存款资金的归属,“有学者主张存款人所有权说,认为存款是存款人以保留货币所有权为前提,将货币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权能暂时转让给银行的行为。但通说则主张银行所有权说……最高人民法院也采银行所有权说。”〔66〕同前注〔41〕,其木提文,第71 页。实际上,“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认可存款合同转移的是存款的所有权。具体讲,在大陆法系国家,存款为消费寄托,准用有关消费借贷的规定,而根据各国民法典,无论消费寄托还是消费借贷,均发生的是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在英国,存款转移所有权的判例法原则,早已在1838 年形成……只有在存款合同转移的是存款的所有权的情况下,才能解释为什么:(1)存款合同一旦成立,存款就不再属于存款人,而是属于银行,银行可以任意使用已经属于它的款项;(2)银行没有义务归还原物货币,但有义务到期时或存款人提出要求时偿还本息;(3)存款人可以在到期前提取存款,也可以在期满后提取,但银行并不主动履行债务。”〔67〕刘丹冰:《银行存款所有权的归属与行使》,载《法学评论》2003 年第1 期,第120 页。
既然银行对现金享有所有权,账户名义人就不可能事实上占有银行所有的现金。从事实上说,存款人将现金存入银行后,该现金完全由银行使用、支配。从民法原理来说,除了例外或者特殊情形,对现金通常采取谁占有谁所有的原则。反过来说,就是谁所有谁占有。倘若认为无正当原因的汇款属于特别情形,也不可能由收款人占有。应当认为,在无正当原因汇款的场合,收款人对存款债权存在事实上的占有,而银行管理者则是相应现金的占有者与所有者。既然如此,就不能认定收款人对银行管理者占有的现金成立侵占罪。这样的判断结论,在区分狭义财物(现金)与财产性利益(存款债权)的日本,会形成处罚漏洞或者处罚的不均衡,但在我国将狭义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统一于财物概念的立法例之下,则不存在任何问题。
第二种观点区分存款债权与对应的现金,承认现金由银行占有,同时认为“收款人对他人错误汇入的存款对银行享有债权并具有正当取款权限……但其是否能以所有人的身份自居而处分该财产以及是否应当将等额的财产返还给汇款人,这是收款人和汇款人就该笔错误汇款所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而与收款人是否可以对银行行使债权无关。亦即二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加以混同。”〔68〕同前注〔50〕,钱叶六文,第228 页。还有学者指出:“刑法的占有概念以事实判别为指向,银行通过柜员或ATM 机等物理手段管控现金,可自由使用,并承担占有丧失之责任。故存款现金归银行占有。”“存款名义人享有合法债权,故不构成对银行占有之打破;但其欠缺实体理由而无法获得所有权,故取款或转账行为构成不打破占有前提下的对他人财产所有权之侵犯,成立侵占罪。”〔69〕袁国何:《错误汇款的占有归属及其定性》,载《政法论坛》2016 年第2 期,第127 页、第129 页。显然,这种观点将行为人取款或者转账后的拒不退还认定为侵占行为。
然而,这种观点完全采用了日本对委托物侵占罪中的法律上的占有的概念。如前所述,日本就受托人对现金的法律上的占有持肯定态度,是基于特殊原因,但这一原因在我国并不存在。而且,既然区分存款债权与对应的现金,并且承认银行占有现金,就不应当得出侵占罪的结论。这是因为,收款人最终取得的是现金,但现金由银行占有;相对于收款人而言,现金既不是代为保管的财物,也不是遗忘物与埋藏物,收款人当然不可能成立侵占罪。亦即,“只要考虑到银行处于应当保护该现金的所有与占有的法的地位,‘取款行为’就成立诈骗罪(从银行窗口取款的场合。从ATM 机取出时成立盗窃罪)。”〔70〕同前注〔36〕,井田良书,第301 页。
本文也注意到,上述第二种观点并不是主张收款人对银行现金成立侵占罪,而是认为取款后不归还被害人(汇款人)的行为构成侵占罪。但是,这样的分析可能不符合遗忘物侵占罪的构造。(1)之所以认为收款人拒不退还的行为构成侵占罪,是因为收款人没有返还不当得利才构成侵占罪。可是,在无正当原因汇款的案件中,收款人的存款债权就是不当得利,〔71〕同前注〔41〕,其木提文。而不是只有取出的现金才是不当得利。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在错误汇款的场合,错误进入收款人账户中的存款,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应返还给错误汇款人。”〔72〕同前注〔50〕,钱叶六文,第221 页。既然如此,在财产性利益也属于侵占对象的我国,收款人不返还其事实上占有的存款债权,就对存款债权本身成立侵占罪。〔73〕但是,我国主张收款人的取款行为仅成立遗忘物侵占罪或者无罪的观点,其实是无形中受到了法律上的占有这一概念的影响。亦即,收款人法律上占有了存款债权,因而在法律上就享有取款的正当权限。然而,如果明确了法律上的占有这一概念的来历,就会发现该概念在我国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反过来说,既然收款人对事实上占有的存款债权属于不当得利,就不能认为其具有利用不当得利领取存款(现金)的法律上的权限,如同盗窃犯不能将盗窃所得谎称为合法所有的财物出卖给他人一样(否则就成立诈骗罪)。〔74〕Vgl.BGHSt 14,38.(2)在遗忘物侵占罪中,行为人据为己有的财物,必须与他人的遗忘物具有同一性。否则,就不可能符合“将他人的遗忘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构成要件。可是,在无正当原因的汇款案件中,汇款人没有遗忘过现金,只是遗忘了存款债权。既然如此,就只能将存款债权作为遗忘物侵占的对象,而不应将取出的现金作为侵占罪的对象。反过来说,如果要将收款人没有退还取出的现金认定为侵占罪的对象,就必须证明收款人取出的现金是汇款人所有且遗忘的现金,但这是不可能的。〔75〕同前注〔11〕,松宫孝明文,第1022 页。即使认为遗忘物侵占时,应以行为人已经取得对遗忘物的占有为前提,收款人依然只是对存款债权成立侵占罪,而不是只对现金成立侵占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存款人不仅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占有着存款债权,而且在事实上及法律上与银行共同占有着存款现金。”同时认为,“在错误汇款的场合,因为是自己名义的账号,收款人当然占有支配着账号中的存款,其占有存款债权并具有取款权限,银行也不能阻止其取款……只是由于不具有最终的实质性权利,其无权将所占有的存款作为所有者进行利用处分; 若能够证明收款人对于所占有的存款产生了利用处分的意思即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也存在变占有为所有的行为,则成立侵占罪。”〔76〕陈洪兵:《中国语境下存款占有及错误汇款的刑法分析》,载《当代法学》2013 年第5 期,第71 页、第74 页。
上述观点也存在疑问。其一,既然承认收款人事实上及法律上与银行共同占有着存款现金,就不可能得出“银行也不能阻止其取款”的结论;而且在共同占有的场合,任何一个占有者都不可能对共同占有的现金仅成立侵占罪。只有对自己占有但他人没有占有的财物,才可能成立遗忘物侵占罪。其二,认为收款人享有存款债权,也可以实现存款债权,但不具有实质性权利的说法,存在疑问。不能不追问的是,这里的实质性权利究竟是什么?根据上述观点,显然不是指存款债权与取得相应的现金的权利,而是对取出的现金的支配权利。可是,没有理由认为现金就是汇款人所有的现金,既然如此,收款人当然可以使用取出的现金。不难看出,与其通过收款人没有实质性权利来说明其行为构成侵占罪,不如直接说收款人不将存款债权退还给汇款人构成侵占罪。其三,如后所述,认为收款人“享有存款债权并具有取款权限,银行也不能阻止其取款”的说法没有根据;如果说有根据,也只是根据德国法与日本平成8 年判决。
第四种观点认为,“当汇款人由于错误,将存款汇入收款人的账户时,其丧失了对该笔存款债权的占有,相应地,收款人取得了该存款债权。此时的存款债权相当于‘遗忘物’而被收款人事实上支配了。这里,侵占罪所要求的‘他人的财物’并非存款债权所指向的存款现金,而是存款债权本身。收款人取现的行为从根本上消灭了该笔存款债权,表明收款人有‘拒不交出’他人财物的意思和事实,因此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可以很容易地认定为侵占罪。”〔77〕黑静洁:《存款的占有新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 年第1 期,第53 页。从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来说,这一观点是可取的。换言之,收款人取得的存款债权是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却拒不返还,就对存款债权构成侵占罪。但是,这种观点将收款人的取款(取现)的行为视为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则存在疑问。例如,即使将“拒不交出”作为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收款人明确拒绝归还存款债权时,就有“拒不交出”他人财物的意思和事实。而且,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取款行为从根本消灭了存款债权,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款行为进一步侵害了他人法益。此外,取款行为的对象是银行占有的现金,而不是汇款人的存款债权。换言之,收款人不返还存款债权,在民法上构成不当得利;收款人从银行取出现金,则是将债权变为物权,也是不当得利。在刑法上,不能仅评价前一个不当得利,而不评价后一个不当得利。〔78〕诚然,二者可能竞合,即取出现金同时表明收款人不返还存款债权。但从逻辑上说,其实是两个不当得利,或者说两个不法行为。所以,需要另外评价取款行为,而不是将取款行为评价在前一个侵占罪中。
总之,在收款人领取无正当原因的汇款时,收款人只是事实上占有了存款债权,而没有占有银行现金;由于收款人对存款债权的事实上的占有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所以,不能承认收款人具有取款的正当权利,其不返还存款债权的行为本身成立侵占罪。至于其向银行领取汇款的行为,则需要再行讨论。
三、取得后的取得
如上所述,收款人事实上占有了他人的存款债权后,拒不归还存款债权的行为就构成侵占罪,侵占的对象是存款债权,而不是银行占有的现金。问题是,收款人在对存款债权构成侵占罪后,隐瞒真相从银行柜台取款或者从自动取款机取款的行为,是否对银行占有的现金构成取得罪?这涉及在行为人就一个对象成立财产罪之后,行为人或者第三者能否就该对象再成立财产罪的问题。如果承认取得后的取得,则领取无正当原因汇款的行为,完全可能另成立取得罪。本节所称的取得后的取得,包括四种情形:侵占后的侵占、取得后的侵占(如盗窃后的侵占)、取得后的取得(如诈骗后的诈骗)、侵占后的取得(如侵占后的诈骗或盗窃)。
第一,侵占后的侵占。“同一行为人常常反复对同一财物(或者实质上是同一财物)实施侵占行为。将友人委托保管的新电脑作为自己的物品使用(第1 行为)后,又将电脑卖给他人(第2 行为)时,认定成立两个侵占罪,作为并合罪处罚的话,就成立二重处罚了。那么,只有第1 行为构成侵占罪,第2 行为不作为侵占罪处罚吗?”〔79〕同前注〔36〕,井田良书,第309 页。第三者教唆行为人将电脑出卖给他人的,不成立侵占罪的教唆犯吗?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59 年12 月7 日的判例采取的是构成要件的解决方式,即在构成要件上否认侵占后的侵占(重复侵占)。〔80〕同前注〔74〕。但是,刑法理论上有学者主张,侵占后的侵占是完全可能的,只要在罪数上作为共罚的事后行为来处理就可以(罪数的解决方式)。根据罪数的解决方式,后一侵占行为的参与者可以作为侵占罪的共犯处罚。此外,在行为人侵占后,还可能由第三者再实施侵占行为,所以,必须承认第三者对行为人侵占的财物可能构成侵占罪。〔81〕Vgl.Rudolf Rengi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Ⅰ Vermögensdelikte,14.Aulf,C.H.Beck,2012,§5, Unterschlagung, Rn.22-23a.
日本的判例与学说则相对统一。例如,行为人受委托管理他人的不动产时,起先擅自将不动产设定、登记不动产抵押(第一行为),然后又将他人不动产出卖给第三者,并进行了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第二行为)。日本最高裁判所以前的判例认定第一行为是侵占行为,第二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不再构成侵占罪。〔82〕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1956 年6 月26 日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10 卷第6 号,第874 页。但后来明确变更先例,认为存在先前的抵押设定行为,并不妨碍后面转移所有权的行为本身成立犯罪,进而肯定了第二行为成立侵占罪。〔83〕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2003 年4 月23 日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57 卷第4 号,第4674 页。肯定第二行为成立侵占罪无疑具有合理性。这是因为,第二行为的法益侵害更为严重。如果只是设定抵押权,就只是使被害人的不动产处于具体危险状态,而出卖行为则彻底侵害了被害人对不动产的所有权。〔84〕只要承认侵占后的侵占,那么,收款人拒不归还存款债权也不取出现金,而是隐瞒真相将存款债权转移给他人的,在我国至少属于侵占后的侵占。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收款人的后一行为成立利用计算机诈骗罪。本文的初步想法是,如果他人从银行取出现金的,则收款人成立诈骗罪或者盗窃罪的间接正犯,其与先前的侵占罪构成包括一罪。
问题是,在前后两个行为都成立侵占罪的前提下,如何解决罪数问题。日本的少数学者主张两个侵占罪属于并合罪,〔85〕参见[日]铃木佐斗志:《横領物の横領と共同的事後行為》,《判例タイムズ》第1207 号(2006 年),第55 页以下。但多数学者主张以包括一罪处理。例如,井田良教授指出:“如果考虑到犯罪的成立只是指刑罚法规的适用可能性,那么,设定抵押权的行为与出卖行为都具有侵占罪规定的适用可能性,在此意义上说,第一行为与第二行为都‘成立’委托物侵占罪。出卖行为是设定抵押权行为的共罚的事后行为(所谓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以任何一个侵占行为来立案都是可能的,但不能以将各自作为可以独立处罚的旨趣予以起诉(两个侵占的罪数关系是包括一罪,将其作为包括一罪同时起诉也是可能的)。”〔86〕同前注〔36〕,井田良书,第310-311 页。松原芳博教授指出:“考虑到立法者的念头是将对一个物的所有权的完全的侵害设定侵占罪的法定刑上限的,所以,两个行为不是并合罪,而是作为相互的共罚的事前—事后行为解释为包括一罪。”〔87〕[日]松原芳博:《刑法各論》,日本评论社2016 年版,第332-333 页。西田典之教授认为,设定抵押权之后的出卖行为,是对所有权的新的侵害行为,应当将先前的抵押权设定行为作为共罚的事前行为。〔88〕同前注〔21〕,西田典之、橋爪隆书,第267 页。
第二,取得后的侵占。行为人窃取或骗取他人财物后又消耗了该财物的,后行为是否成立侵占罪?“例如,行为人先窃取了被害人的木材,然后又将这些木材用于修建他人的仓库的,是否能够在盗窃罪之外再成立侵占罪?部分学者对此持肯定回答。因为行为人的后行为仍然表征了其将被害人物品据为己有或者使之为他人所有的意思,同样成立侵占罪。只是在罪数上,由于行为人随后的侵占行为没有进一步扩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因而对行为人仅依据前行为所犯之罪(在上例中为盗窃)处罚。该说的优点在于,即使是事后中才教唆、帮助行为人将其已经取得的他人物品据为己有或使第三者所有的,也可以被认定为侵占的共犯。”〔89〕王钢:《德国判例刑法(分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9 页。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故不展开讨论。
第三,取得后的取得。行为人在实施诈骗等取得罪后,行为人或第三者完全可能就实质上的同一财物再实施诈骗等取得罪。根据民法学说,“作为民法的两大基本财产权,物权与债权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与债权相比,物权具有对世性、支配性、特定性、排他性、绝对性、公示性等特征。也正是因为如此,物权的效力即法律赋予物权的强制性作用力,在优先权方面远远高于债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和财产的结合表现为物权,当财产进入流通领域之后,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换则表现为债权。主体享有物权是交换的前提,交换过程则表现为债权,交换的结果往往导致物权的让渡和转移。正是基于物权与债权上述情况下的融合,就出现了同一标的物上既有物权又有债权的情况。”〔90〕同前注〔67〕,刘丹冰文,第118 页。既然实质上的同一财产完全可能由不同法益主体分别事实上占有,对不同法益主体的事实上的占有就均应保护。当同一行为人对同一标的物既有侵害物权的行为又有侵害债权的行为时,就要分别讨论两种行为各自构成何种犯罪;〔91〕例如,在德国,在因缔约诈骗签订合同的时点成立诈骗罪的场合(如行为人明知自己不具备雇用单位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却通过欺骗手段使雇主与自己签订雇用合同的,由雇用所产生的经济负担就能认定为财产损失),如果合同按约定得到履行,诈骗就继续到履约阶段。因此,在签订合同就达到既遂的诈骗,由于履行而终了的,整体上成立一个诈骗罪,而不是说后一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同前注〔81〕,§13, Betrug,Rn.183-195)。类似情形在日本则属于包括一罪。例如,行为人骗取价款请求权之后又基于该请求权使他人交付金钱的,成立包括一罪(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1987 年11 月18 日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40 卷第7 号,第523 页;高松高等裁判所1953 年7 月27 日判决,载《高等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6 卷第11 号,第1552 页。另参见[日]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第5 版),成文堂2018 年版,第275 页;[日] 高橋則夫:《刑法総論》(第4 版),成文堂2018 年版,第530 页)。当不同行为人分别侵害同一标的物的物权与债权时,更应分别讨论不同行为人的行为各自对物权与债权构成何罪。例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案例2 中的诈骗犯(持卡人)前面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后面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或者盗窃罪,但由于最终只有一个财产损失,所以成立包括一罪。据此,在诈骗犯担心受处罚而放弃取款念头后,第三者唆使诈骗犯取款的,成立诈骗罪或者盗窃罪的共犯。案例3 的持卡人通过挂失领取现金的,成立诈骗罪,而不是侵占罪,也不只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92〕针对前一诈骗犯取得的存款债权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针对银行占有的现金则构成诈骗罪,二者属于想象竞合。案例4 的持卡人从银行柜台取款成立诈骗罪,在自动取款机取款的,成立盗窃罪。
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除了现金由银行管理者占有外,重要的理由是,取款行为分别符合诈骗罪与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根据相关规定,如果金融机构发现不法分子利用银行账户,就会中止该账户所有业务,并向侦查机关报案。〔93〕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开户管理及可疑交易报告后续控制措施的通知》(银发〔2017〕117 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6〕261 号);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银发〔2015〕第43 号)。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6〕261 号)规定:“凡是发生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的,应当倒查银行、支付机构的责任落实情况。银行和支付机构违反相关制度以及本通知规定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这充分说明,如果银行职员知道持卡人储蓄卡内的资金属于不法所得,就绝对不可能向持卡人支付现金。反之,持卡人只有隐瞒真相才能从银行柜台取款。同样,银行管理者也不可能同意持卡人从自动取款机中取得诈骗所得的汇款。这足以说明,持卡人取得诈骗所得汇款的行为,另成立诈骗罪或者盗窃罪。
不可否认的是,诈骗犯通过欺骗行为使被害人将存款汇入其指定账户后,诈骗罪就已经既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取走存款的行为不另成立犯罪。其一,犯罪既遂虽然表明行为已经侵害了法益,但是,既遂标准只是表明对相关犯罪行为不能以未遂犯论处,而不意味着任何犯罪一旦既遂其对法益的侵害就已经完全彻底化。财产犯罪既遂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案件中,行为人在既遂后仍然会进一步实施侵害行为。在诈骗犯骗取了他人汇款的场合,只要没有取款,被害人追回汇款的可能性就相当大。反之,如果诈骗犯或第三者已经取款,被害人追回汇款的可能性就特别小。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评价取款行为对法益的进一步侵害这一事实。其二,所谓诈骗既遂,只是相对于存款债权而言,而不是相对于银行占有的现金而言。在存款与现金虽有对应关系但并不同一的情况下,在行为人诈骗了他人汇款后,行为人或者第三者领取银行现金的行为,对银行构成诈骗罪或者盗窃罪。其三,诈骗犯骗取的汇款与取走的现金,虽然最终实质上可谓同一财产,但在不同阶段就是不同样态的财产,且不同样态的财产在不同的法益主体占有之下,侵害不同财产所符合的构成要件也不相同,〔94〕例如,诈骗犯骗取他人汇款的行为虽然是诈骗行为,但其在自动取款机上取出现金的行为,则是盗窃行为。因而需要分别评价。〔95〕即使认为诈骗犯的取款行为只是共罚的事后行为(包括一罪),该行为也是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因为该行为明显违反银行管理者的意志,将银行管理者占有的现金转移为自己占有),需要予以评价。
基于同样的理由,在电信诈骗犯骗取他人汇款后,没有共谋但知道真相的第三者“帮助”诈骗犯从银行柜台或者自动取款机中取出现金,成立诈骗罪或者盗窃罪的正犯,〔96〕日本的通说认为,即使事先无通谋,电信诈骗的取款人的取款行为也成立诈骗罪或者盗窃罪(参见[日]富山侑美:《振り込み詐欺“出し子”の罪責について》,《上智法学論集》第59 卷(2016 年)第3 号,第214 页以下)。而不是仅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97〕取款人的取款行为就电信诈骗所得的存款债权成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就银行现金成立诈骗罪或者盗窃罪,二者属于想象竞合。
第四,侵占后的得取。亦即,在无正当原因的汇款案件中,收款人不归还存款债权的,就存款债权对汇款人构成侵占罪;收款人从银行取款的,则不仅侵害了银行对现金的占有,而且进一步侵害了汇款人的财产,就现金另成立诈骗罪或者盗窃罪。下面以构成诈骗罪的情形为例展开说明。
首先,收款人不归还存款债权的行为,仅对存款债权本身成立侵占罪,而不可能对银行的现金成立侵占罪。所以,收款人取得现金的行为,需要另行评价。
其次,收款人原本应当返还存款债权这一不当利益,却不仅没有返还,而且掩盖不当得利这一事实,持储蓄卡或者存折到柜台取款的行为,从作为的角度来说,是基于举动的欺骗行为(滥用权利);从不作为的角度来说,是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的不作为欺骗行为。〔98〕当然,对领取错误汇款与诈骗汇款的欺骗行为的说明可能是不同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展开讨论。这一行为让银行职员误以为其存款债权不是不当得利,因而实施了处分行为。如果银行职员知道收款人的存款债权没有正当原因,就不会支付现金。
有学者指出:“从柜台取款的现实来看,除所持存折或银行卡真实且输入密码正确外,银行的确会审查取款人是否与存折等反映的存款人一致,但银行并不会‘审问’取款人所取款项是否自己存入及存款来源。存款名义人并不负说明存款非他人误汇之义务,银行也并没有因未说明而受骗,故存款名义人欠缺诈骗行为。”〔99〕同前注〔69〕,袁国何文,第129 页。还有学者指出:“可以确定的是,即便因为错误汇款而使得账户占有人的存款增加,银行也无权将多出的款项直接划走,而是需要事先征得账户占有人同意。”〔100〕马寅翔:《侵占罪保护法益的反思与修正》,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 年第1 期,第91-92 页。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银行不审问,是因为收款人的举止使得银行职员误以为收款人所领取的是其基于正当原因的存款。如果银行职员知道真相,就不可能向收款人支付现金。更不能认为,错误汇款人对收款人具有转移金钱所有权的意思,银行必须向收款人支付金钱。这是因为,“移转金钱所有权之意思,是处分行为层面的意思,该意思不仅必须存在,而且应当真实。错误汇款之所以不能移转金钱所有权,系因对收款人或错汇金额而言,汇款人根本就没有移转所有权之效果意思,或者说该移转意思因内容错误(对方当事人、金额) 可被汇款人撤销。在电信诈骗等情形,汇款人确有移转所有权之意思,但该意思因乃受欺诈而生,故可被汇款人撤销。”〔101〕孙鹏:《金钱“占有即所有”原理批判及权利流转规则之重塑》,载《法学研究》2019 年第5 期,第40 页。此外,否认收款人负有诚实信用法则上的说明或告知义务,也难以妥当。〔102〕《民法典》第7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同前注〔38〕, 大谷實文,第11页;[日]安井哲章:《誤振込みと詐欺罪》,《法学新報》第120 卷(2013 年)第5、6 合并号,第68 页。
在银行本身错划的场合,银行不经过收款人同意,就可以将款项扣划回来。〔103〕同前注〔36〕,山口厚书,第592 页。同样,在错误汇款的场合,银行首先可以对收款人止付,然后也可能为汇款人扣划回来,而不需要经过收款人的同意。这是因为,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规定了相应的义务。例如,《商业银行法》 第6 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商业银行法》第73 条还规定:“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以及其他民事责任:…… (四)违反本法规定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损害的其他行为。”既然如此,银行职员就不可能在明知收款人在将不当取得的存款债权转变为对现金的所有权时不闻不问。换言之,不闻不问的行为就没有保障存款人合法权益不受他人的侵犯,因而违反《商业银行法》的规定。〔104〕诚然,上述结论只是根据相关法律的推理,并没有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但笔者通过多种途径询问银行的权威人士,得到的答复是一致的:银行如果发现是错误汇款,就会对收款人止付;在汇款人申请扣划时就会将存款扣划到汇款人账户;在汇款人不明的情况下,还会将存款托存。
不管是从法律规定来说,还是从银行的具体做法来看,银行并非任由错误汇款的收款人取走现金,相反会阻止其取款。这说明,收款人只有隐瞒真相才能取款,这种隐瞒真相的取款行为就是诈骗行为。概言之,“知道了错误汇款事实的收款人,隐瞒该信息请求取得汇款,该当于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此外,应该认为关于有无误汇的错误该当于诈骗罪中的错误。”〔105〕[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第2 版),付立庆、刘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27 页。
此外,如果说收款人不仅取得了存款债权,而且银行扣划必须征得其同意,那么,银行没有经过其同意的扣划行为反而成立盗窃罪。恐怕没有人会赞成这一结论。
最后,银行存在财产损失。关于诈骗罪的财产损失,存在各种学说,其中存在形式的个别财产损失说与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说,至于整体财产损失说,则与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说在结论上没有实质区别。根据形式的个别财产损失说,银行职员将现金交付给行为人就是财产损失。根据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说,需要考虑的是银行交付现金的目的是否实现。但交付现金的目的不只是经济目的,还包括社会目的。〔106〕参见张明楷:《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载《中国法学》2005 年第5 期。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在错误汇款时,银行按当事人的申请会采取恢复到汇款前的状态的‘扣划’手续。这一措施对于避免银行卷入纠纷是必要的,从防止发生无用的纠纷的观点来看对社会也是有意义的。要使这样的手续成为可能,银行就具有应当保护该现金的所有与占有的法的地位。”〔107〕同前注〔36〕,井田良书,第301 页。换言之,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避免银行卷入纠纷、避免银行因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责任,是银行的重要社会目的。既然如此,就不能否认收款人的取款行为导致银行的上述社会目的落空,不能否认银行的财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