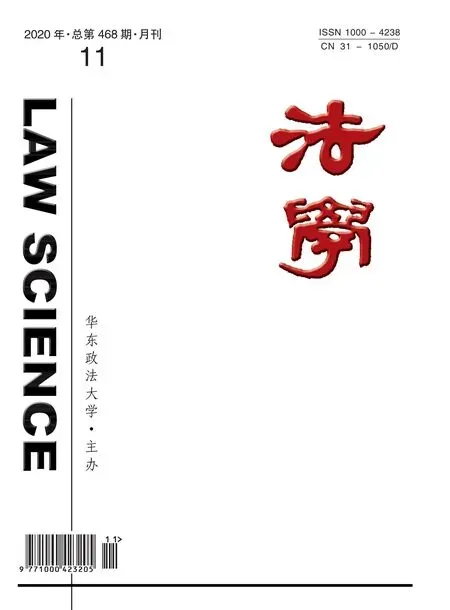国际舰机相遇规则的一体化与中国参与
李 伟
一、国际舰机相遇规则及中国因应
国际社会开发利用公共海域范围的逐渐扩张,大大提升了不同国籍的舰机在海上相遇的概率。〔1〕不同于“碰撞”,“相遇”是指舰机共同出现于海上、空中的固定航线上,此时需要采取合理的绕道规则,一是避免舰机碰撞,二是避免因绕道而有损舰机登记国家或地区的主权尊严。2015 年,美国濒海战斗舰“沃斯堡”号与中国海军护卫舰舰艇相遇,双方使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首倡的《海上相遇规则》的“语言”有效沟通;2016 年,美国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与俄罗斯两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波罗的海相遇,美国对俄方的这种行为“予以谴责”,俄国防部强调俄飞行员在可视范围内发现美国驱逐舰后掉头转向的行为遵守了美俄(以及过去的美苏)之间签订的关于海上和空中相遇协议中所有安全规范;2018 年4 月15 日,中国海军军舰与澳大利亚军舰在南海海域相遇,中方舰艇使用专业语言与澳方进行沟通,其操作“合法合规、专业安全”。从国际公共海域的客观结构出发,舰机相遇空间不再局限于舰与舰、机与机的二维式平面结构,而被扩展至包含公共海域平面〔2〕从立体层面讲,海平面以下的水域同样属于公海,只是水下领域同样适用船舶“相遇”规则故而忽略不计。故此,下文除有特殊说明外,海上领域均包含海平面及水下领域。和天空的舰与机相遇的三维式立体结构,这意味着国际主体相遇的情形〔3〕本文将相遇扩展至海上相遇的原因在于海上环境的三维立体性、海上相遇规则的现实性与紧迫性,但有的国家之间的“机”在陆地上空相遇也可以参鉴本文倡导的国际法规则进行调整。已非传统意义上军舰相遇或飞行器相遇,而是现代意义上的除了前述相遇情形外还包括“舰”与“机”相遇的情形。〔4〕也有媒体将本文所称的“相遇”标为“意外相遇”,但笔者认为“非意外”的相遇皆为叵测故意,非本文的研究范围,而“意外”乃应有之义,故而不表。
顾名思义,“舰”乃军舰,〔5〕原则上,舰机相遇仅指军事舰机相遇,不包含其中一方为非军事舰机之情形。在构建一体化舰机相遇国际法规则的背景下,以军舰为主、涉及非军用舰机的情况同样应被重视。现有的舰机相遇国际法规则滥觞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军事需要,也局限于区域间的客观环境。随着舰机相遇规则的适用空间不断扩张,舰机相遇的复杂性也相应提升,非军用舰机与军用舰机相遇的问题不容忽视。其主要特征为行动空间限于海上;“机”乃航空器,其主要特征为行动空间限于空中。囿于人类科技水平,“舰”与“机”的行动空间曾经不存在交叉点故而两者不易相遇,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诸如“舰”可载“机”等技术不断成熟并被广泛用于公海领域,抑或是互联网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大大提升了舰机之间联系的便捷程度,“舰”与“机”的本体已经扩张至包含行动接受指挥的雷达信号,“相遇”已从两个以上有形体相互接触引申至既有航行路线可能受到对方的影响。〔6〕See Marcelo Viana de Freitas, Jose Andrés Santisteban,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an Automatic Positioning System for Antennas Installed on Ships, J.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2,1549(403): 3578-3586.
现行的国际航空法里并不涵括“舰”与“机”的相遇规则,诸如《华沙公约》《海牙议定书》《蒙特利尔第四号议定书》等均以民用航空器为调整对象,不涉及在信息技术日渐发达的国际背景下“舰”与“机”可能相遇的特殊航行样态。鉴于此,国际社会针对如何设计国际舰机相遇规则进行了积极努力,现有的主要成果是2000 年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提出的、2014 年由中国海军承办的第十四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获得通过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The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以下简称CUES)。〔7〕参见《有关方面不应曲解〈海上意外相遇规则〉》,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425/c1011-24940321.html,2018 年3 月10 日访问。为了推广CUES,近年来中国也做出了重要努力:2016 年9 月,在第十九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并且在2018 年中国—东盟联合军演中成功使用了该规则。CUES 的设立有利于减少和平时期各国海空军事行为的误解误判、避免海空意外事故、维护地区安全稳定。〔8〕参见《增进理解互信 避免误判误解》,载《人民日报》2015 年4 月14 日,第23 版。伴随CUES 参与主体数量的与日俱增,问题也开始凸显。不可否认,CUES 自身技术条款设计及与时代相符合的程度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国际航行规范。它是各成员海军舰艇或航空器在不期相遇时〔9〕构建一体化国际舰机相遇规则不仅应解决军用舰机相遇问题,在国际社会层面还应当注重解决涉非军用舰机的相遇问题,除了紧急情形涉军用舰机优先通过外,军用舰机与非军用舰机相遇规则同样应当遵守共建和谐世界的国际法原则。为减少相互干扰和不确定性及为通信方便所应采取的安全措施和手段,除了规定有海军舰机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还规定了舰机相遇时的海上安全程序、通信程序、信号简语、基本机动指南等内容,此外其在国际上产生的重要影响的范围还远不止于各参与主体,如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表示他已就中国与美国海军舰船相遇时应该如何行动举行过几次独立的双边会谈。〔10〕参见《美海军作战部长称愿与中方多接触:这是一个机遇》,http://mil.news.sina.com.cn/2014-10-17/0752805966.html,2020年8 月20 日访问。
尽管CUES 参与主体期冀能将其推至统一规则的高度,〔11〕参见《外媒:〈海上相遇规则〉或可扩及南海周边国家海警》,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61010/1335730.shtml,2018 年3 月10 日访问。但就目前情况看,CUES 尚无法担此重任,毕竟其只是一些建议规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CUES 不被部分国家接受的原因之一就是该规则过细,期望能够建构更加原则性、更加弹性化的规则内容。从统一相遇规则的角度出发,制定详细规则总体上优于弹性化规则,但不易被国际社会或绝大多数国际主体接受的现实亦值反思,这也是被完善的CUES 或未来全新的统一规则应当注意的重要问题。这其中既有国际主体间法律文化差异的因素,也有CUES 自身的问题。前者说明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应当充分注重各成员国的个体特性,至少应在制定过程中尽量顾及不同类型法律文化背景下国际主体的参与程度;后者说明CUES 的内容列举再详细也难免挂一漏万。另一个不便于被普遍推广的原因是CUES 的准用语言。格林纳特上将曾与我国吴顺胜将军达成一致使用英语作为应急语言的合意,化解了中国舰船与美国“考本斯号”巡洋舰之间的对峙。〔12〕当时正在该海域进行演习的中国新航母船长通过无线电用熟练的英语与“考本斯号”巡洋舰进行了有效沟通。参见冯春梅:《中国军队将根据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载《人民日报》2015 年11 月27 日,第11 版。但是,此类个案并不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在统一规则层面,其实任何一种语言均不具有权威性,即便按照国际上将某几种语言视为国际组织章程或文件的标准语言,也难以适应舰机相遇情况的紧迫性。故此,笔者认为舰机相遇的情形只适合足够应急的标志、符号抑或是既已遵守的程序性规则,而非参照某种语言来作进一步“沟通”。除此之外,CUES 自身不包含明确的纠纷解决机制,也极易导致相似纠纷的处理结果不一的情况。〔13〕参见周萍:《海上相遇有了交通规则》,载《中国国防报》2014 年4 月29 日,第2 版。
于我国而言,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舰机相遇规则一体化的构建工作具有必要性。一则,涉及我国的舰机相遇纠纷与涉及他国的类似纠纷处理结果差异过大容易间接降低我国涉外活动的整体质量;二则,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我国有必要“以点带面”式地主动帮助国际社会解决部分纠纷,打造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纠纷解决机制,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14〕参见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10 期。三则,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完善升级,〔15〕参见王少永等:《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表征实证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 年第14 期。传统的“舰”与“机”概念在新时代有必要作出全新的引申,以适应当前国际海上广义的航运环境之需求,这意味着全新的“相遇”纠纷不断涌现但又缺乏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状况亟须改变;四则,在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的今天,航运技术也进入了全面变革时代,需要及时处理和解决因传统航运技术飞速升级而产生的新型问题。
一国是否参与构建国际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工作涉及政治、外交、技术、法律等领域的全方位配合,不可一蹴而就。当前,舰机相遇规则的不统一与国际海上舰机相遇纠纷不断出现矛盾的现状进一步加剧了出台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的紧迫性。舰机相遇规则虽非新事物,但局限于国家(地区)之间不同的熟悉与信任程度,在实际操作中各国舰机对于安全的规定存在诸多差异,一时间难以被化解在同一个方案中,导致舰机相遇规则暂无法实现一体化,这成为影响建设规范化国际航行秩序的重要问题。如何解决有两个可供遵循的路径:一是分别构建海上与空中、军用与非军用以及多个双边相遇规则;二是拟定统一的国际社会舰机相遇规则,并借助外交手段加以推广。两相比较,后一路径显然更能节约司法资源、便于构建规范化的国际航行秩序、有利于提高国际航行的效率,也更有挑战性。
基于此,国际舰机相遇规则一体化的研究便主要聚焦于海空一体化、身份一体化和规范一体化等三位一体的规则构建上。下文将分而述之。
二、海空一体化:空中相遇规则是否可与海上规则相统一
“舰机”分为“舰”与“机”,两者之间可以构建通用的相遇规则是进而探讨如何构建两者相遇规则的前提。海上与空中相遇规则可以统一的基础,不仅在于海空之间航行工具逐渐实现了广义上的一体化,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海空之间航行过程因为均借助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通信设备而应当提升避免相互干扰的能力。〔16〕See Seeley Thomas D, Visscher P. Kirk, Stop Signals Provide Cross Inhibition in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by Honeybee Swarms, J. Science, 2011, 335(6064): 108-110.相较于航空技术,航运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普遍应用的时间较晚,随着航空、航运技术的广泛运用,海空之间的相遇形态逐渐演变为信号传播空间出现交叉而需要确定传播信号的合理秩序,否则无论海上还是空中航行规则均将受到不合理干扰。〔17〕参见《中方在南沙岛礁建设是为更好履行相关国际责任和义务》,载《人民日报》2015 年5 月27 日,第21 版。这种技术本体的无国界性成为海上与空中相遇规则可以统一的基础。
(一)我国海上与空中立法脱离现象的改善
海上与空中立法在理论上可以实现无缝对接,然而在实践中,我国海上与空中立法存在相脱离的现象,〔18〕参见汤喆峰、司玉琢:《论中国海法体系及其建构》,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 年第3 期。这影响到我国参与国际舰机相遇规则一体化的构建进程。我国空中立法与陆上立法一贯采纳一套法律体系,空中立法的特殊性仅表现为调整与航空相关的专项法律规范,其立法指导思想与陆上立法完全相同。近年来,我国学界有海上立法应独立于陆上立法之呼吁,并以海上立法尤其是海商法在中世纪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文件作为主张。在此笔者无意评价海上立法的独立性问题,但单从舰机相遇规则的角度观之,其更适合采纳海上与空中相一致的法律体系,否则难以形成统一的行为指导规范。
追本溯源,海上立法呈现独立性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其中的海商立法成果最早成文于中世纪的地中海区域,并在拿破仑主持制定的商法典中第一次被纳入民商事法律体系中,长久以来保持着自身的特色。〔19〕See Michal Galedek, Anna Klimaszewska, A Controversial Transplant? Debate over the Adaptation of the Napoleonic Code on the Polish Territorie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11(2), 2018.中世纪地中海地区海商立法出现的原因与当时欧洲法治环境的联系密不可分。中世纪欧洲立法成果极少的原因是其时欧洲封建社会以教会法为主,其地位高于之前既有的古罗马法和古日耳曼法等世俗法。在发展过程中教会法一度占据了社会关系的支配地位,甚至控制了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调整的主体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私人法律关系,制度设计将社会成员划分成有等级的教阶制度,神职人员与普通民众的社会地位不同。教会法主要以《圣经》、教令集、宗教决议和由世俗法转化过来的法律为主要法律渊源,将其称为是一种政治性的统治理念更为准确,这意味着当世俗法本体的适用过程出现问题或者与教会法相冲突时,是由教会按照正义理念出具“指导意见”,对现实制度进行不完全修复。因此,在中世纪海商法问世时,欧洲大陆近似于不需要全新的立法成果,由此导致教会法与海商法的冲突,一方面表现为教会法严重的滞后性与海商法强烈的灵活性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出于中世纪教会和国家对沿海地区极有限的控制力。可以说,中世纪的海商法只调整教会法疏于管辖的范围,其被纳入拿破仑主持制定的商法典的史实并非法律体系自身发展之结果,而是有着重要的政治原因。〔20〕参见高启耀:《论交付》,大连海事大学2017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2-44 页。
(二)信息技术的国际性要求统一空中与海上相遇规则
空中与海上舰机相遇规则实现一体化是信息时代的诉求。信息技术是不分国界的,国际舰机相遇规则的构建需要以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为基本参照,立法体系也要为此作出相应的发展和完善。当前我国重视海上强国的体系建设并不意味着我国需要完全独立于陆上立法的海上法律体系,更不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上陆上与海上法律体系无法分割。即便我国将立法重点投向海洋,也无法摆脱相关海上立法与陆上规范的联系。海上立法仅以海上相关纠纷为着眼点,同样应以基本的、由陆上发展至海上的相关法理为基础。〔21〕参见叶秋华:《资本主义民商法的摇篮——西欧中世纪城市法、商法与海商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 年第1 期。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与陆地有着天然紧密的联系,加上前已述及的互联网时代技术成果的发展态势,诸如无人船舶、无人机等航行技术日渐成熟,海上与空中航行行为模式间的差异性正在缩减,〔22〕参见徐景明:《无人化全自动化码头系统试运行》,载《厦门日报》2014 年8 月14 日,第A01 版。这都是统一舰机相遇规则提供了必然性与可行性,但是,构建统一舰船相遇规则时也不能忽略海上立法多年来独具特色的发展成果,所以,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共性与特性便成为摆在统一舰机相遇规则征程上一个需被重视的问题。
传统的相遇规则原则上并未实现“舰”和“机”相遇规则的一致性,因为遵守“舰”和“机”相分离属于彼时的时代特征抑或是技术层级。时至今日,舰机相遇规则一体化已属归纳总结现实技术发展的成果。如前所述,舰与机相遇在当下的技术支持上已成为现实,若舰与机相遇的规则再不加以明确,势必会导致纠纷解决不畅。譬如,全球定位技术的逐渐升级大幅提升了人类借助侦察设备直接观测的范围,舰机“相遇”已从传统的物理碰撞转型为信号接触。前文述及的舰机相遇统一规则的一个重点是调整涉及军事身份的舰机相遇问题,军事身份的一个特殊性为隐秘性,涉及军事身份的舰机航行路线及航行状况原则上不应被他国查知,故而有必要在信号相遇之前双方达成有效的避触协议。这些新类型的问题亟须在舰机相遇规则中得到反映,而空中与海上长期奉行不同的相遇规则,并且我国乃至国际社会互联网技术行为规范尚不确定、也难以被统一,因此,传统观念在当下应该如何发展也实在地影响了舰机相遇规则的统一进程。
三、身份一体化:军用与非军用舰机相遇规则是否可以统一
军用与非军用舰机相遇规则存在适用统一规则的可能性是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两者相遇规则的前提。当前,军用舰机相遇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军用舰机的特殊身份要求其适用更便于保护涉军事权利的相遇规则。
(一)军用舰机的特殊身份影响统一规则的出台
构建军用与非军用舰机统一的相遇规则的主要问题在于规范两类舰机相遇后的特殊航行秩序问题、舰机相遇出现冲突后高效的维权纠纷解决机制等。探讨构建军用与非军用舰机统一的相遇规则不仅可行而且必要,毕竟国际间航行相遇的主体身份的最大差别就在于用途而非国别。传统意义上,国际主体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涉军事纠纷,〔23〕参见张芳:《军事外交风格形成中的重要因素分析——以中国军事外交为例》,载《国际观察》2013 年第3 期。纠纷主体事先明确相遇规则的做法少见,此一做法有时容易导致外交程序冗杂的资源浪费。〔24〕参见赵可金:《建设性领导与中国外交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 年第5 期。构建涉军事身份的舰机相遇规范意在创造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用以简化外交途径解决纠纷的程序。
军用舰机的特殊性表现在身份上。军队乃国家的象征,使得不同国家的军用舰机之间,或者是军用舰机与非军用舰机之间,相遇的纠纷处理机制极难被统一。军用舰机的特殊性表现在:(1)军用舰机的行动规则具有隐秘性;(2)军队的特殊身份要求军用舰机的正常国际通行秩序原则上完全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25〕参见王寿林、王世臣:《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若干理论问题》,载《政治学研究》2011 年第2 期。这两点意味着涉及军事身份的航行主体的相遇问题应当接受本国主权的管辖。当此类舰机与其他舰机相遇后,要及时解决避碰问题需要立足于完全尊重他国军事主权的基础上。从一定程度上言,适用军用舰机主权国家特殊规则具有合理性,需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下两点:一是相遇双方均为军用舰机时适用其中一个主权国家特殊规则的弹性范围,主权平等原则会导致同时尊重军用舰机各自国家的相遇规则难以实现,这要求我们要充分考虑主权国家的平等国际地位;二是相遇双方仅有一方是军用舰机时在国际规范层面拟定其适用本国特殊规则的前提条件,或者是国际通用规则,或者是损失补偿机制,这要求若军用舰机涉及相遇规则后可以优先适用该国的特殊规定,但同时应当保证非军用舰机的损失有必要的填补机制。
(二)尊重主权原则要求统一军用与非军用舰机相遇规则
涉及军事身份的舰机相遇问题不同于军用舰机相遇问题,后者指相遇双方均为军用舰机,而前者在包含后者的前提下还包括仅相遇一方为军用舰机,另一方是非军用舰机的情形。涉军事身份的舰机相遇纠纷的解决机制不同于一般的或完全非军用舰机相遇的纠纷解决机制,后者仅需尊重既已形成的国际航行规则。在涉及军用身份的舰机相遇问题中强调主权平等原则的理由是军用舰机的航行规则应当有其特殊性,毕竟军事活动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国家安全的终极保障。〔26〕See David Devlaeminck, Revisiting the Substantive Rules of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An Analysis Through the Lens of Reciprocity and the Interests of China, J. Water Policy, 2018, 20(2): 323-335.
因此,从尊重一国主权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情况进行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的设计:第一种情况是非军用舰机与军用舰机相遇的情况,此时应遵循非军用舰机让位于军用舰机的处理规则;第二种情况是军用舰机相遇的情况,此时应当允许第一次相遇优先通行的军用舰机在第二次相遇时处于后位通行的次序。第二次相遇并非指第一次相遇的军用舰机,而是包括该舰机及该舰机所属的主权国家的其他军用舰机与第一次相遇的军用舰机及该舰机所属的主权国家的其他军用舰机相遇。确定通行秩序的意义在于:确定涉及军用舰机所代表的主权问题中可以适用仲裁制度的范畴;在部分不宜适用仲裁制度的纠纷中,仲裁制度仅能借助一般的尊重主权原则裁判后续的补偿问题,而不适合对行为的适法性作出价值判断。
四、规范一体化:双边(包含多边)舰机相遇规则是否可以统一
当前国际社会不存在统一的或者是统一适用于大部分国际关系主体之间的相遇规则,所以是否有必要建立国际通用的舰机相遇一体化规则值得进一步研讨。
(一)双边规则与统一规则效力层级不明的消除
不同于国际贸易规则,由于涉及公海上主权问题、军用与非军用舰机的让位顺序问题及舰机相遇本身的效率问题等,如果舰机相遇规则多元化,那么极易扩大前述问题的实际影响。当前,影响舰机相遇规则一体化进程的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双边或多边规则之间极易发生冲突,以至于在舰机相遇后可能会因遵守不同惯例而引发冲突。〔27〕See Esma Gül Emecen Kara, Olgay Oksas, Gökhan Kara, The Similarity Analysis of Port State Control Regimes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Flag States, 2020, 234(2):558-572.国际舰机相遇规则的订立方式多采取双边协商式,国际主体众多的现状导致双边规则与统一规则的效力层级难以被有效认定。〔28〕See Narcisa Galeş, Dumitriţa Florea, The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Feudalism, 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49: 365-370.国际主体数量众多呼唤统一的相遇规则优位于双边相遇规则。放眼国际社会,部分内陆国家不可能涉及舰机相遇问题,但其也会借助方便旗制度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29〕See Anthony van Fossen, Flags of Convenience and Global Capitalism, J.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16, 6(3):359-377.这就使得公海上国际舰机相遇的情形变得更加复杂。在缺乏统一处理纠纷国际规则的年代,国际纠纷通常通过外交途径抑或是双边规则来解决。该做法的优点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针对性强,当处理结果满足双方期待后,便极少再引起进一步的纠纷。〔30〕参见谷昭民:《中国开展法律外交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载《现代法学》2013 年第4 期。但问题在于,此举的效率低下且适用范围极其受限,凡是涉及第三方国际主体的问题均导致双边规则的效力层级降阶,因为此时适用双边规则解决纠纷的结果可能不会被第三方国际主体完全接受而致无效。国际参与主体数量的增多意味着与之相应的外交成本的提升及周期的延长,所以将双边相遇规则推广至多边相遇规则以提升效率殊有必要。
探讨多边国际主体的特性、协调既有舰机相遇规则以扩张其适用范围甚至是创造全新的舰机相遇规则,是有效降低国际航行冲突的基本甚至是最低要求。当然,这并不意味全新、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能够完全取代既有的双边规则,而是应从两个角度逐渐发展统一的相遇规则:一方面,暂时适宜建立有层次性的舰机相遇规则,即在无其他相关国际主体的前提下双边的舰机相遇规则优先于统一的相遇规则;另一方面,除了有特殊要求外,可以根据统一规则完善并推动双边规则的修改,直至与统一规则相符。故此,在国际主体之间构建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既是一项基本工作,也是一项严峻挑战,关键在于如何缓和特殊规则与统一规则之间的关系。
(二)国际法主体多样性要求统一舰机相遇规则
国际主体类别众多,对舰机相遇规则的呼声高于与此相关的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国际主体包括主权国家和一系列国际组织。〔31〕See Bentley B. Allan, From Subjects to Objects: Knowled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2018, 24(4):841-864.国际组织使用非军事、非政治功能的舰机与军用舰机相遇规则不明确,容易导致国际纠纷数量增多,还会因舰机相遇问题导致继发性国际纠纷。〔32〕See Veton Latifi, Th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Response to the Refugee Crisis Along the Balkan Route in the View of Strate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 SEEU Review, 2016, 12(1) :167-179.单论舰机相遇问题,涉及部分国际组织使用悬挂某一国国旗的舰机时,理论上,舰机接受其悬挂国旗国家的管辖,〔33〕See Anonymous, Blockchain for Ship Registration, Renewal, Sea Technology, 2019, 60(12).但实际上与该国际组织或部分国家共用的舰机相关的国际主体均与该舰机有实质联系,这就导致非悬挂国旗的国家均有就舰机相遇主张权利的可能。即使认定舰机相遇规则处于优位的效力层级,诸如涉及与国际组织使用的舰机相关国籍公民的人身权等问题,同样会引起国际纠纷乃至受到适用双边规则的掣肘。无疑地,舰机相遇规则优位于与此相关的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能在事实上降低纠纷出现的概率并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
从概率学角度讲,适用不统一的多边相遇规则会产生与适用纯粹的双边规则相类似的后果,唯有统一相遇规则方能平衡适用于国际主体之间的效力层级。
五、构建舰机相遇一体化规则的中国参与
由上分析可知,舰机相遇规则一体化面临的挑战主要包含如下三个方面:(1)空中与海上舰机相遇规则不易被统一;(2)军用与非军用舰机相遇规则不易被统一;(3)国内与国际舰机相遇规则不易被统一。这些问题不仅源于构建舰机相遇规则本体的技术条款,而且与立法环境乃至法律体系的发展方向相关。建立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是一项持久而浩大的工程,其基础工作涉及普及统一舰机相遇规则理念、协调成员国之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准确预判互联网技术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和基本的技术性条款的合理性审查等内容。
(一)协调既有的国内规则与统一的国际规则
应当辩证地看待前文言及的我国军舰在与美国军舰相遇时主动选择英语交流以及同意与东盟国家在我国南海地区适用CUES 的开放性态度,这并不能代表未来一体化的舰机相遇规则的架构模式。
1. 辩证取舍CUES 的优劣机制
针对未来相遇规则中使用语言选择的问题,可考虑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应采取符号代替语言的技术规范。事实上,让全部或大多数国际主体的航行管理人员统一接受某一语言非常困难,而通用的航行符号作为交流媒介似更方便可行。在互联网时代,数据信息应用程度的逐渐加深为这种建议提供了技术支持。不唯独互联网通信设备使用由0 和1 组成的语言代码,传统通信技术亦然。〔34〕See UniPy: A Unified Programming Language for MGC-based IoT Systems, 2019, 24(3):77-86.因此,拟定好相应的舰机相遇情形并在此类情形中预先达成一致的行动标准共识,进而再制定特定的行动信息代码,便能够大幅提升纠纷处理的效率。
针对未来相遇规则中涉及军事身份的问题,可在充分尊重军事主权的前提下视情况分别进行讨论。于相遇双方均为军用舰机的情形,首先应当遵循主权平等原则,即军用舰机优先通过机会平等。详言之,军用舰机首次相遇应当遵守二者均非军用舰机的相遇规则,优先通过的军用舰机在二次相遇时负有主动避让对方舰机的义务。于相遇一方涉及军事身份的情形,应当在尊重军事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军用舰机优先通过。凡掩盖军事身份的舰机无优先通过权,且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中应当针对冒充军事身份的行为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
针对未来相遇规则中涉及国内、国际规则冲突的问题,我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在我国南海地区相遇适用CUES 之举对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不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其实,我国适用CUES 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即基于我国当前尚未参与到推动建设国际统一舰机相遇规则的进程中去,而南海地区的舰机相遇问题又亟待解决的背景。应当承认,CUES 对未来形成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的指导意义,但是从我国自身的特殊性角度考虑,应当以此为前提推动有特色的舰机相遇规则的一体化进程。
2. 推进我国主导的国际舰机相遇规则
有效执行海上相遇规则不但受到船员、船舶、环境这个系统的影响,而且受到避碰规则中关于交叉相遇局面中避碰行动具体行为要求的约束。总体上看,每个相遇过程均需考虑三个问题——何时行动、如何行动及行动后果。纯被适用于国内舰机相遇的规则较全面且独立,国内与国际接轨的舰机相遇规则需要被一体化建设是建立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过程中一个重要难题。现有的部分国际标准并非由我国主导建设,CUES 问世多年后我国才加入便是考量了既有规则的特殊性与CUES 之间的关系。在成为CUES 成员国后,处理国内与国际相关纠纷时也可能出现因规范复杂而无法统一适用规则的问题。
由于复杂的国际航运环境与我国境内航行秩序之间存在差异,所以完全推行我国已具备的航行秩序至国际社会并不妥适,而过分依赖既有或我国未参与制定的相遇规则,又会对我国既有的航行秩序造成剧烈冲击。前文述及的我国在南海地区适用CUES 的开放性态度表明存在境内航行秩序与国际接轨的可能,以此为基,推动我国主动参与国际舰机相遇规则的制定,一来能够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二来又能有效地实现我国内部航行秩序与国际的接轨。
3. 以前沿技术为基础构建先进的国际舰机相遇规则
舰机航行一体化是指传统的相遇理念在未来应当被合理引申,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的今天,信号交叉理应被认定为国际航行的舰机在客观上相遇的新形式。
第一,在遵守技术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再进一步商讨如何构建具体规则。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实质影响之间均有不可忽视的联系,忽视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极有可能降低社会运转体系的灵活性。〔35〕See Policy and Internet: Investigators from Lund University Report New Data on Policy and Internet, Computers, Networks & Communications, 2020.客观上,控制海上与空中航行设备的枢纽均为陆上操作系统,即依赖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其有效地解放了航行工具的人力依赖特质,或者说,大大降低了航行工具的人身危险系数。当前有必要将互联网技术相关的立法工作从私法层面的电商平台等问题延展至公法层面的舰机相遇一体化规则等问题。
第二,在抓攫舰机航行共性规律的前提下再进一步商讨如何把握特性规则。这是前述受互联网技术影响的航行工具的新时代特性,可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方面,应当与应用互联网技术较为成熟的国家从协商先进设备航行秩序的角度出发,合理打造舰机相遇一体化的规则;另一方面,应当与应用互联网技术略微落后的国家深化交流技术应用愿景,合理拟定高新航行工具与传统工具之间信号相遇的处理规则。鉴于我国既属于发展中国家又独具如此巨大经济总量的特质,理应承担起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际主体之间进行技术交流的重任。
(二)构建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
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可选的模式主要包括外交途径、国际法院审判、国际仲裁裁决和ADR 四种,各有其优势和局限性。
1.外交途径效率较低且程序不透明
外交途径属于纠纷双方协商解决问题的典型模式,也是传统解决舰机相遇纠纷的基本模式。作为国际主体解决国际纠纷的基本手段及最有保障的手段,即使在建立并完善专项解决舰机相遇纠纷的国际仲裁制度之后,外交途径同样能够在解决舰机相遇纠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建立专项的国际仲裁制度首先是为了解决普遍性的、原则性的、透明性的纠纷,而外交途径代表国际主权主体的权威,在舰机相遇纠纷中应当起到应有的“后发式”的保障作用。但同时需要注意如下两个方面的局限性:(1)外交途径依靠双边(包括多边)式的逐一解决纠纷的运营模式会造成效率过低的结果。〔36〕参见许传玺:《构建统一权威的“一带一路”国际仲裁机制》,载《学习时报》2020 年1 月22 日,第2 版。不否认很多国际主体宁可纠纷不解决也要保证掌控主动权,但在本文的语境下,纠纷数量的积增将会直接导致舰机通行质量的下降,而效率是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所首要考虑的问题。外交途径本质上属于国际主体依赖其主权身份所作出的交涉活动,是将纠纷置于平等的国际主权主体之间进行谈判。外交途径的针对性强,其最终解决成果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不可更改性。但是,也应看到外交途径的期间相对较长,主要源于外交途径本身的程序性。〔37〕See Li Na,Wu Ping, Comparative Study on American and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s of Reports from the Pragma-Dialectical View,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Literature and Teaching, 2019, p. 20-25.该程序性的最大特质在于结果引导主义,即外交途径的最终结果有其相当的决定意义。换言之,外交结果被遵守的前提在于该结果必然是双方所共同接受的,除非有其他影响因素存在,外交结果不会发生不利于一方且此方主动接受的情形,这也是双方协商争议解决模式存在的天然缺陷。〔38〕See Achim Hurrelmann, Political Controversy Abou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greements: Lessons for Canada-UK Trade Negotiations After Brexit, 2019, 74(3):453-462.(2)外交途径没有透明化的程序,这也是影响外交结果纯粹性的重要因素。外交结果的任意性与舰机相遇纠纷解决结果的规律性呈现天然的矛盾:外交结果只是主权主体之间利益的碰撞与交融,其强烈的针对性仅解决对象式主体之间的问题,而舰机相遇纠纷解决结果具有明显的指导性,即适用于此类结果的规则原则上在未来将被纳入统一的国际舰机相遇规则中,故其程序正义原则的积极意义不言自明。
2. 国际法院的建设目标不易于解决此类纠纷
国际法院不适宜被纳入国际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国际法院自身建设的特征导致其无法成为眼下解决舰机相遇纠纷的可行性选项;二是国际“司法”活动的被动性抑或国际惯例自身的滞后性导致国际法院当前不存在被适用至国际舰机相遇纠纷解决环节的可能性。
于第一个问题,影响国际法院参与国际纠纷解决环节的关键因素包括国际法院的基本功能、既有的裁判舰机相遇纠纷的国际惯例及国际法院诉讼成本与周期。很显然,三者均阻碍了国际法院发挥其功能:国际法院的基本功能在于解决国际主体之间极具针对性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依据为既有的国际惯例或国际法律性规则,但是当前并无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因而即使存在国际法院也无法发挥其基本功能,而国际法院诉讼成本高且运转周期长的特点又与舰机相遇纠纷需要被快速解决的要求相悖,使得国际法院审判并非是最优的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
于第二个问题,国际“司法”活动具有强烈的被动性,其能够为舰机相遇规则的完善提供必要帮助,但对形成舰机相遇规则的贡献甚少。舰机相遇纠纷得以被妥善投入国际法院诉讼环节的前提是存在明确的舰机相遇规则作为裁判依据。法律本身存在滞后性特征,国际惯例的出现离不开基本原则和惯用规则的长期积淀。〔39〕See Brenda S. A. Yeoh, Charmian Goh, Social Protection for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the Law, and Civil Society Action, 2020, 64(6):841-858.国际法院欲在解决舰机相遇纠纷中发挥功能,一般应在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成立后再通过既有的解决舰机相遇纠纷的基本原则作进一步引申。
与外交途径相比,国际法院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本身为引入不相关第三方作为解决纠纷的居中裁判方,该裁判者有权威性。〔40〕[美]菲利普·C.吉瑟普:《国际法》,张文彬译,《清华法学》2006 年第3 期。这意味着,裁判结果即使不利于某一方,该方原则上也应当承认该结果。国际法院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程序正义和适用法律正确,这需要保证其权威地位,因而不适宜在舰机相遇规则出台之前便将其投入到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当中。
3. ADR 模式欠缺必要的程序性
作为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ADR 无疑是一种高效的国际纠纷解决机制,其特点在于不限于程序性的裁判规范。原则上,ADR 包含但不限于仲裁这一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其不适宜被应用于解决舰机相遇纠纷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ADR 的适用范围主要为私法领域,若将其适用至国际公法领域将导致部分国际问题的处理规范不够严谨。〔41〕See Jie Hua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an Old BITs Fulfill China’s New Initiative,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16, 50:737-738.究其原因在于其尚不完善的当事人权利救济问题,因为ADR 产生于对效率价值的追求。〔42〕See Laurie Greyvenstein, Mediation & the Law - compensation of Crime Victims in the South African Legal System - ADR and Other Options, 2019, 112(7):78-79.应当承认舰机纠纷解决机制同样追求效率价值,但是该效率价值与ADR 所实现的效率价值存在本质差别。ADR 主要被适用于私法领域归因于私法当中效率与公平两个理念的冲突可以被理解成同位阶的价值选择问题,即二者的价值位阶相同因而ADR 仅为更加倾向于效率原则,这意味着当ADR 适度选择更加倾向于公平的方向时,效率的价值将要受到一定影响。而以舰机纠纷解决机制为代表的公法层面当中所追求的效率和公平价值处于不同位阶,笔者认为应当将公平置于第一位阶而效率放在第二位阶。将公平置于第一位阶的意义在于公平应当是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追求效率价值应以充分保证公平价值为基础。国际纠纷解决机制的首要原则是遵守主权平等原则,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的私法理念在公法层面无法被适用的原因是无法保证有条件限制行使主权的行为得到等价的回报。
第二,恰是因为ADR 包含但不限于仲裁的运营模式,导致其不适宜被应用至舰机相遇纠纷的解决。ADR 的产生意在摆脱司法程序效率相对较低的运营模式,其中,仲裁制度的优势表现得较为明显。在接纳仲裁(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商事仲裁)制度的前提下,ADR 还接受调解、和解、谈判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了仲裁制度可能存在的效率不足的现象。〔43〕See Ogbor John Oghenechuko, Eromafuru Edward Godbless, Interest-Based Conflict Management Systems: Beyond Traditional and ADR System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8, 10(17):80-91.正是这一制度设计使得ADR在公法层面不宜被适用于解决舰机相遇纠纷,因为ADR 包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同时被选择的可能性,导致以仲裁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不能完全被选用,提高了纠纷解决结果的任意性。这符合商事活动乃至跨境商事活动所追求的结果,却不适合解决舰机相遇纠纷。因为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同样可包含仲裁和外交途径两种,与ADR 在形式上相近,但是二者的区别在于本文所倡议的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应以仲裁作为主要的争议解决机制,而外交途径仅能在必要时作为候补式的争议解决机制,即选用这两种模式的优位性不同。
第三,ADR 的高度自由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规则限制,不易被凝结为高效实用的纠纷解决机制。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原则上应当构成国际舰机相遇规则的一部分,应在协调国际主权主体纠纷的同时保证自身的权威性。〔44〕See Pierre Lalive, On the Reasoning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010, 1:55-65.故而,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宜存在过于弹性的运营模式,也不宜因此产生不确定的争议解决结果。
(三)优先适用国际仲裁作为解决纠纷机制
构建国际舰机相遇一体化规则的问题在于,何种纠纷解决机制应被作为基础性、首要式的途径,建议国际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首选国际仲裁模式,而前述外交途径、国际法院审判及ADR 等纠纷解决机制应被视为国际仲裁不能时替补式、完善式、递进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当然,其也不是唯一的争议解决途径,若国际社会对某一个或某一类争议解决机制达成高效一致的话,则其可作为备选。
首选国际仲裁的优势有:(1)国际仲裁能在保持必要的程序性的基础上实现相对较高的效率。当前,国际仲裁在解决国际争端的过程中一般坚持了必要的程序,这是仲裁制度形式上相似于诉讼制度的重要特质。〔45〕See Barbara Kwiatkowska, The Eritrea-Yemen Arbitration: Landmark Progr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Equitable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2001, 32:1-25.相较于诉讼制度,仲裁制度的效率较高,〔46〕See Nigel Blackaby, Ricardo Chirino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ura Novit Curia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014, 6:77-93.因为“一裁终局”的裁判模式能够节省不必要的程序资源浪费。(2)国际仲裁是在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未出台时探索舰机相遇纠纷解决规则的最佳途径。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的出台因涉及多元因素,故需要从长计议,尤其是在当前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尚且只是一种正确的理念、未被付诸实践的历史节点,统一规则的技术性因素的具体制定过程处于空白期,也意味着其有着较大的商榷空间。仲裁制度相较于诉讼制度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准则依赖程度较低,表明仲裁制度更注重协调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的关系。仲裁程序为纠纷双方提供了协商拟定裁判人员的空间,越是在缺乏裁判依据的情况下,越能协商并出具让双方信服的裁判结果。习惯法是重要的法源之一,而协商拟定纠纷解决方案是积累沉淀优势规则的重要途径。依笔者看来,出台统一规则的进程既是一项长久之计,又是一个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文化交融的过程,因此,在达成共同制定统一规则的国际合意之前,积累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经验、待统一规则制定时再协商具体规则的技术性规定,无疑是出台统一规则的不二法门。
但其亦有劣势,表现在:(1)缺乏统一的舰机相遇国际规则作为裁判依据。国际社会共建舰机相遇规则是一个必然趋势,然而统一规则如何制定尚待探讨,即使按照学界所倡导的以扩张CUES 的适用范围为着眼点、以挪威和加拿大等国的既有经验为参考也仅可被称为是一种可行的思路。这会影响到仲裁制度基本理念的设计,因为在仲裁制度为出台统一规则服务的时间段应当首先保证仲裁结果的基本方向。(2)国际仲裁的适用对象有待明确。传统意义上仲裁制度的对象一般仅包含涉公或涉私的独立主体,而舰机相遇纠纷的仲裁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涉军事身份的舰机相遇纠纷应当如何解决,其中包含了涉公主体与涉私主体相遇的问题。(3)国际仲裁的裁判理念有待更新。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生活、社会理念的变革必然影响到国际仲裁的裁判理念,使舰机相遇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进一步增加了纠纷解决的难度。当前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速度与法律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已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舰机相遇纠纷虽仅为其中的冰山一角却不容被忽视。舰机相遇问题并非独立地存在于国际交往当中,其纠纷能否被妥善解决又不止依赖于统一规则的制定,而与国际层面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准则,或仅存在应用原则息息相关。仲裁制度专项定位于舰机相遇纠纷势必应先解决传统裁判理念与前沿技术之间的矛盾。
六、余论
我国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沿线很多国际主体发生舰机相遇问题,“一带一路”沿线中类型丰富的国际主体能够尽可能地为未来出台一体化舰机相遇规则提供充分的参考情形。以部分国际主体作为规则制定主体,有助于在权衡国际主体特性的过程中较早地抓攫共性以推动原则性规定优先出台,抽象化的原则性规定是吸引更多的国家接受一体化舰机相遇规则的前提。我国推动建立一体化舰机相遇规则的理念与该倡议在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理念完全一致,〔47〕参见蔡武:《坚持文化先行 建设“一带一路”》,载《求是》2014 年第9 期。能为建设一体化舰机相遇规则提供信誉保证,在平衡舰机相遇之后涉及利益纠纷时出台与我国紧密合作的国际主体相遇后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主体深度合作的缩影,随着倡议被深入推动,相信更深层次、更高程度的国际合作也为时不远,这都为建设一体化舰机相遇规则提供了不可错失的重要历史机遇,而且该规则的出台也是提升国际合作质量的重要帮衬。
从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的出台历程看,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早于统一规则,而从统一的舰机相遇规则的本体架构看,纠纷解决机制本身属于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应先于统一规则出台。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时代的诉求,即当前国际航运环境提升了舰机相遇的概率,相应地增加了舰机相遇纠纷的潜在可能性,事前预防措施远比事后救济措施更能节省成本。二是规则本体的要求,即规则本身的架构是一项综合的、长久的工作,其中涉及航行规则的制定、责任承担模式的筛选、纠纷解决机制的比选等工作,这些均要求参与统一规则制定的国际主体之间首先达成基本的国际合作协议,并就统一规则的基本原则交换再达成共识,纠纷解决机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三是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纠纷解决机制本身属于程序性规则,并不涉及统一规则的实体性内容,二者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纠纷解决机制对统一规则的出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为既已形成的国际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涉军事的航行纠纷解决机制不多,甚至可以说,这符合人类理解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规则:或双方协商,或第三者居中裁判。纠纷解决机制能够集中解决国际航行过程中舰机相遇问题并对部分极具代表性的问题形成基本统一的认识,这种实体规则的形成过程符合海事规则的发展规律,因为从海事规则的起源看,其多数属于对解决航行过程中纠纷的优化规则的归纳总结,凡是流传长久的纠纷解决机制均为优势的规则。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进一步筛选并优化其中最适合解决舰机相遇纠纷的程序机制。
近年来,我国对外交流迈上了新台阶,航行轨迹实乃国际交流的脚印,一体化的舰机相遇规则是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走向更广阔的国际社会所必须推广和主导的基本规则。笔者认为,在舰机相遇规则尚且碎片化的当前,提出构建一体化舰机相遇规则的时代诉求并考察该工作的困难之处,只能勉强视为是一种理性化的呼吁。虑及出台一体化舰机相遇规则的遥远将来与随着互联网技术日益普及而极速加深的国际交流程度,建设一体化舰机相遇规则的下一步工作应当是:在明确舰机相遇规则重要性的前提下预先出台基本的舰机相遇纠纷解决机制,以服务于当前日渐频繁的国际航行态势,为最终出台一体化的舰机相遇规则提供先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