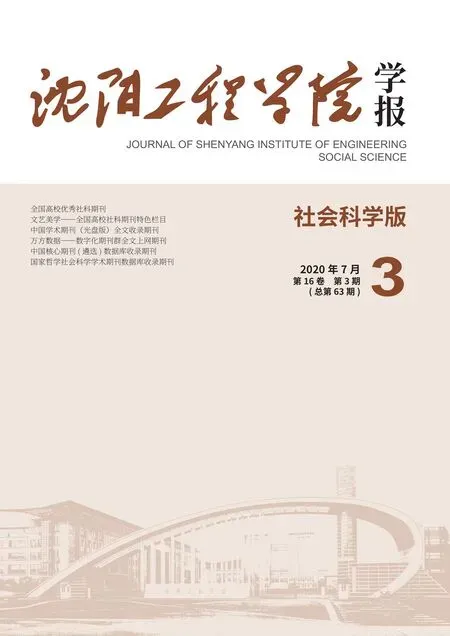先锋小说对传奇叙事传统中形象序列的择取与拓新
邱 丹,吴玉杰
(长春工程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中国传统文学素有“传奇”传统。“传奇”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独立与成熟的审美标志,确实为中国小说叙事传统延伸出很多可供承续、挖掘、激活和改造的资源。“传奇”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文体形式,至唐代得以成熟,并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发展演进中基本的叙事模式与传统。传奇,“源盖出于志怪”,在人物在形象的构思与书写中基本上延续了志人志怪小说中的人物之“奇”的审美特征。譬如,《山海经》面目混沌的帝江、虎齿豹尾的西王母、鸟身人面的怪神;《搜神记》《世说新语》中打破人鬼、生死界限的神魔人物;《封神演义》中各种神通广大,神化变形的形象;《西游记》中变幻莫测、神通广大的仙魔序列等,这些形象群体也构成后世文学“征奇话异”的重要资源。先锋小说在人物形象的书写上了也呈现了传奇色彩。这主要体现在鬼魅形象、神化形象、奇人异秉形象等方面的描写上,并构成了对传奇叙事传统的呼应。
一、先锋小说对传奇叙事中鬼魅形象的延承与构设
从古至今,传奇叙事从不缺乏对鬼魅形象的书写。而鬼魅形象也在不同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审美意义。在先锋小说中,传奇叙事中鬼怪世界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与现代主义所承载的存在意识得以复合。先锋小说在文学观念中重新阐释了真实与虚构、记忆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边界。而鬼魅形象逾越生死、跨越时空的传奇性恰恰模糊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它们不仅能够为先锋小说带来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异化体验,更在先锋作家奇诡的想象中成为把握世界、传达现代体验的重要方式。
在余华的《古典爱情》中,柳生在小姐坟茔旁盖了一间小屋,决定守候小姐了却残生。小姐出现了“借魂还生”的征兆,无论小姐挑灯夜读的剪影,在干草上睡觉留下的痕迹,还是定情发丝闪烁的绿光,都颇具“人鬼情恋”的传奇色彩。然而不同于《牡丹亭》中杜丽娘为柳梦梅还魂再生的团圆结局,小姐鬼魂复生却功亏一篑,抱恨黄泉。所有生命遭际与生死离别在余华笔下都变成了无法设定也无法确定的存在。《世事如烟》的形象设置充满着符号化的隐喻色彩,并传达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感。小说中,“6”总能看到江边的两个垂钓者,无声无息且“没有腿”,“他们的脸的正面与反面并无多大区别”[1]111。接生婆答应陌生男子去城西的家中接生,而“他好像没有腿,他的身体仿佛在凌空走着”[1]127,孩子捧在手中的感觉像“一团水”,孩子没有哭声,母亲生产没有血迹,母亲与孩子的皮肤都像“刮去鳞片后的鱼的皮”[1]128。接生婆吃下男子做的面条与鸡蛋,回家之后吐出来却是“一堆乱麻和两个麻团”,她想返回接生的房屋,却只见一座新坟。司机的鬼魂经常会出现“2”的梦中,直至“2”帮助他完成冥婚。这种模糊的、飘忽不定的不确定感以及被鬼魂、死亡阴霾笼罩的诡异氛围,也呈现了一种面对生存所真实体验到的虚无感。格非《褐色鸟群》中,那个穿栗树色靴子的神秘女人是否真实存在似乎难以确定,这个女人的丈夫淹死在粪池中,“我”却真切地看到尸体抬起右手解开了上衣领口一个扣子的举动。格非并不着意刻画鬼魂形象,却在不经意的点染之中增强了叙事的神秘性与不确定性。还有《青黄》中似是而非的鬼魅,《隐身衣》中如鬼魂般存在的丁采臣。人踩在现实的土壤上,却如鬼魂一般永远停留在假定之中。叶兆言的《绿色咖啡馆》以相互冲突的人物语言构建了线圈式的迷宫。李谟与神秘咖啡馆女主人的几次相遇神秘迷离,而这种奇幻般的艳遇,却被同事张英质疑,“见你的鬼,哪来的什么咖啡馆”[2]361,这种错位式叙述使得人物本身与亲历事件都变得诡异模糊。这些先锋小说鬼魂形象的书写,体现了传奇传统的一种继承。但同时,余华、格非、叶兆言等先锋作家以鬼魂形象为载体,混杂着宿命与无可奈何、交叉着偶然与不确定性、模糊着生与死的边界,交错着真实与虚构,且真切地将现代人两难的生存境遇与独特的生命体验灌注其中。
而扎西达娃、苏童等先锋作家笔下的鬼魅形象又多了一层诗性传奇色彩。《西藏,隐秘岁月》里察香死后“灵魂从头颅飞出升向了天界”。苏童认为:那些民间流传的鬼故事,对情绪能造成“轰炸性的效果”,作为非主流的民间文化,“它恰好对大家都产生了影响。”[3]68在苏童的《U 型铁》里,纺织娘“奇病而死”,“据说老街人收殓纺织娘的时候,听见屋里响着纺车嘤嘤鸣叫的余音”[4]54。七个壮汉抬起大铁砧子时,他们听见了“老屋吱吱嘎嘎的断裂声”[4]63。《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里,么叔作为烧花节(鬼节)的送鬼人,“一车子大鬼小鬼就跟着幺叔出发了”[4]179。在么叔的黑字忌日里,人们能够感受其晃荡的灵魂,翘着腿坐在石磨上,凶恶地拽着老榆树上的钟绳敲着自己的丧钟。《仪式的完成》中,有一种风俗,即“拈人鬼者,即从活人中抓阄拈出鬼祭奠族人先祖的亡灵”[4]234。用红墨水画好的鬼符则是人鬼的标志,民俗学家死后,其笔记本中掉出写着大大“鬼”字的鬼符。《妻妾成群》中,颂莲总能感觉到鬼魂的存在。“我走到那口井边,一眼就看见两个女人浮在井底里”[5]47。雁儿吞了草纸死后,颂莲总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梦见她的鬼魂从髻后抽出一根长簪,刺向自己的胸口。陈家大院总是笼罩着阴森、诡异的氛围,在这里看到是生命在堕落的欲望下逐渐消耗与陨落的生命过程。《樱桃》中,与邮递员尹树相恋的女孩,原来已经死亡,尸床上的她还握着尹树赠予的手绢,人鬼情恋走进了日常生活,却也触及到现代人内心的孤独,而这份孤独他者仿佛永远无法靠近。而鬼魅形象在残雪的笔下更加的怪诞而极端,残雪笔下的形象不是鬼魅,却永远走不出诡异的怪圈,这些人物似乎比厉鬼更为尖刻。先锋小说中,人鬼之间的关系既分裂又复合,既吊诡又融合,鬼魅形象成为先锋作家把握与探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作为呓语者的幻想神游,也不乏死者的书写。如橙子林的“反陈述节”是死者与生者会晤的节日,“死者们总是在反陈述节这天从天堂和地狱的各个角落赶到剪纸院落的池塘来洗凉水澡。”[6]165而且均以裸体呈现,死者裸露的是灵魂,生者裸露的是肉体。这不仅让人陷入意义的指涉之中,仿佛唯有这天可以卸去伪装,以赤诚相见,灵肉才能融合。我们不能不说,孙甘露不仅是语言的鬼才,他的想象与文体构思也是一种传奇。
传奇传统的鬼魅形象本来就是被排拒在理性门墙之外的特异群体,它们边缘而虚幻,传奇而神秘。正是这种契合,为先锋作家复活传奇传统的鬼魅或鬼魅式的特异形象提供了可能,并以此为载体投射着当下关于存在的体验与追问。吴玉杰在评论林声的“自提画诗”谈到:“素心并不是一种柔弱。恰恰因为素心,才有一种内在的抵抗力,才会有铮铮傲骨。”[7]先锋作家在非理性世界中探寻精神真实时,其实也恰恰体现了这种“素心”以及对理性秩序的一种内在抵抗。
二、先锋小说对传奇叙事中“神化”形象的借鉴与改造
在先锋小说中,除了鬼魅形象的穿插,神化形象的构设也散发着传奇色彩。在《山海经》《淮南子》《搜神记》《世说新语》《太平广记》《西游记》等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仙怪奇侠、奇人异秉等神化形象。这里不仅寄予着人们对摆脱困境超现实能力的向往,也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想象,并在不同时期被赋予新的审美意义。在先锋小说中,对神化形象的继承与改造也独具特色。
余华的《鲜血梅花》借用武侠故事,突破了武侠小说的叙述模式,兼容传统与现代元素,体现了对文学传统的另类继承与突破。《鲜血梅花》的人物设置颇具避重就轻的意味。无论是曾经仗剑风靡武林的父亲阮进武,还是仿佛无所不知的武林高手青云道长、白雨潇,还是涂满剧毒花粉近身则死的胭脂女、黑发如黑针的暗器高手黑针大侠,都充分体现了武林奇侠的传奇特质。作者无意渲染这些传奇高手的“强”,却将真正的主要人物阮海阔的“弱”暴露在丢失目的复仇中。动机与结果在偶然间彻底错位,寻找即是虚无。这样吊诡的人物设置又何尝不是“另类”的“传奇”。
古有尧舜,目生重瞳。潘军《重瞳》里的项羽,也是生有异样,得尧舜之风采,潘军保留了《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项羽“重瞳子”相貌特征,但对“重瞳”加以神化。《重瞳》里的项羽,当两个瞳孔重叠时就能目测千里。譬如文中写道:“我的眼睛又出神了。怎么视野里的北方渐渐变成了绿色?而且这绿还越来越浓,像一块绿云似的朝这边汹涌而来。”[8]5在项羽观察北方绿地的第十天,战马与虞姬一同从远方奔向项羽。“它长嘶一声扬起前蹄,把一个白色的东西掀到云中,就像一片白云自九霄而落”[8]9。项羽接住白云,原来是个姑娘。虞姬与项羽的相遇具有“不可思议的传奇性”,而且“她这一出现便结束了我内心长达八载的矛盾”[8]10。“重瞳”与“虞姬”在《史记》等源文本中都不是重笔,只是轻微带过。而潘军在“重瞳”与“虞姬”留下的巨大历史空隙中充分发挥了想象与重塑的再生力量,增强了叙事张力。“重瞳”不但具有了多重内涵,是将相异相,也是多重视角;虞姬也不再是衬托英雄没落的陪衬,她是独立的个体存在并具有神性的光泽,她不仅能够与项羽心灵契合,也是唯一一个能够牵引项羽内心从喧嚣焦躁走向平静安然的人。也因此,虞姬的归天在“项羽自述”的视角中充满了传奇。“我头顶上还有一双亮眼——那是天的眼……第二年春天,这块地方开出了一片不知名的红花……它叫虞美人。”[8]52
苏童在《碧奴》里塑造了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孟姜女”形象——碧奴。碧奴作为“哭灵人”的后裔不能哭泣,桃村的女儿寻找独特的、符合自己特长的排泪秘方。“他们根据各自的生理特点,动用了各种人体器官引导眼泪”[9]8,碧奴的眼泪可以隐藏在头发里,用头发哭泣,后来可以用手掌哭泣,用脚趾哭泣,用乳房哭泣。碧奴的眼泪本就比别人多,丈夫岂梁失踪后,碧奴踏着“执拗的不断重复的脚步”,连路上的青草都能辨认那“悲伤的足迹”,她“罗裙尽湿”,所过之处,可以扬起泪水的风暴。而且泪水能沁入食物,连家里的南瓜都带有“泪水苦涩的气味”[9]11-12。可见,苏童在继承碧奴传统形象中的执着、坚韧的性格之外,也为形象注入了神化般的浪漫主义气息以及强劲的生命力。
当传奇叙事已成为一种传统,也会形成一种传奇“不奇”的现象,而此时“反传奇传统”也是再生传奇的策略之一。在《后羿》里,叶兆言对后羿这一神话英雄进行了降格处理,后羿、嫦娥、吴刚等形象呈现了一种“神性的缺失”与“人性的再现”,神性的不在导致了人性的沦丧。这些人物都经历着神性逐渐丧失、人性逐渐暴露的生命曲线。后羿的出生与嫦娥有关,嫦娥拾起洪水里的葫芦,“突然间葫芦像孵化的鸡蛋壳那样四分五裂,从中间探出来一个孩子血淋淋的小脑袋”[10]39-40。这个孩子就是后羿,他生长速度惊人,力大无比,骑射惊人,凭借神力成为了万众瞩目的英雄。但却在性欲、权欲、报复欲的欲望狂欢中神性渐失。而嫦娥在后羿的背弃中彻底绝望,由人性的善转向了人性的恶。“重述神话”也是对心灵故乡的重温,希冀通过现代诠释远古的神话传说,重新释放神话的光彩并为个体存在提供一种参照。显然,叶兆言解构的戾气太重,反伤了神话的美与诗性。与《后羿》不同,北村《施洗的河》里恶贯满盈的刘浪,灵魂在神性的光泽中得以苏醒并获得拯救,但又陷入了“刻意为之”的圈套,人物失去了自然而然的塑造,这一点在余华的《第七天》中,也是如此。
三、先锋小说对传奇叙事中术士奇人形象的延揽与创新
先锋小说关于人物形象的传奇叙写,还体现在对术士、奇人等形象的塑造上。首先,术士形象的塑造。术士文化在中国渊源已久,“史汉之京房、唐之李淳风、宋之邵康节、明之刘伯温,皆知阴阳、察乎天变,世称奇士。”[11]而这些奇能异士的神秘莫测自然能够为文学提供充沛的艺术想象与神奇魅力。在余华、苏童、格非的先锋小说中能够看到“各种术数文化的形相”。这些人物往往能够未卜先知,有超常的预见能力,甚至料事如神。如,余华《难逃劫数》的老中医,当东山跃进他的视野之后,他仿佛就能预知露珠与东山的悲剧命运;《世事如烟》的算命先生,熟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内在肌理,能够准确预测文本中所有人物的命运,并对人物命运有一种神秘的支配力,他不仅用五个儿子的性命延续自身的生命,而且将所有人都推至在无法摆脱宿命的阴影之中。人性裂隙与虚无感被强化。在此,对人物的传奇书写不仅是外在形式,也是对先验性叙事的自我强调,更是进行现代思索的重要手段。格非《迷舟》的算命先生,他的预言也是萧的结局;《敌人》的赵少忠竟在瞎子预言的“召唤”下,杀害其子赵龙,此时的“天数”为“人术”所用,重述了“命相数理”何以成为“权术”的历史场景。苏童的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陈宝年会给女人算命,他能占卜“凤子就是死里无生的命”[12]163。与蒋氏成婚的第一夜开始,陈宝年连续“七个深夜”“重复着他的预言”[12]156,即蒋氏是个灾星。后来,蒋氏孩子的先后死去以及村庄里发生的瘟疫,都好像应验了她是灾星的预言。除此之外,1934 年“枫杨树”乡发生瘟疫,有一名黑衣巫师出现在马桥镇,“摆摊子驱邪镇魔”。“黑衣巫师的话倾倒了马桥镇:西南有邪泉,藏在玉罐里,玉罐若不空,灾病不见底”[12]180。而通神般的巫术使人们意识到“西南邪泉”乃是“瘟疫之源”,而这确实与财主陈文治相关。而留下神秘预言的黑衣巫师在灾民火烧陈家之后悄然失踪。苏童则在家族历史中嵌入了神秘与魔幻的因子,演绎了隐藏在家族根节深处的人性与历史。除此之外,《碧奴》中,“柴村的女儿经其实是一部巫经,神秘而阴沉”,她们由于玄妙的巫术,耗损着精神,面容消瘦。她们为碧奴“算出人间最离奇的命运”[9]19,碧奴乃葫芦所变,不该随便远出,否则灵魂无处寄托,但所有的困难都没有挡住碧奴寻夫的征程,碧奴的坚韧品质重启光辉。
其次,奇人异士形象的塑造。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奇传统中,奇人异士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书写对象,这些形象不仅会带给人丰富的想象,也增添了文本的叙述魅力与传奇性。苏童《水神诞生》里,寻找水源的水神高佬、额角刻着神秘刀印的瞎眼老人,带领八个孩子修路的蓝娘、从未见过父亲却能逼真画出父亲淹死画面的赤虎……这些人物不同于巫士,却具有未卜先知的神奇性。蓝娘归天前的谶语是“高佬找到水了,高佬在水里淹死了”[4]248,果然一语成谶。瞎眼老人和马桑能够用“目光和腹语交流了各自关于火的观念”[4]252。那个被视为水神第八个儿子的马桑自焚于火中,奉行了“新的水神必将诞生于火种”的预言,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过路的盐商。《祭奠红马》里那个随着怒山红马丢失由强健走向衰亡的怒山老人;《仪式的完成》中那个贯穿行文的锔缸老人,仿佛只有他能洞悉神秘或者宿命的循环;《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那个鬼节赶着花车送鬼的幺叔。格非《人面桃花》里的秀米父亲的“发疯”和出走,“秀米”的发疯与秀米的一生都充满了神秘与传奇,还有花家舍的王观澄、六指都充满了传奇性。格非故意设置了“空缺”,而这个“空缺”恰恰起到了“增魅”的审美效果,是“空缺”也是“悬念”,与传奇传统不同的是这个“悬念”没有答案。
先锋派小说受西方现代派小说影响较多,接受非理性思潮的先锋小说更加强调拆解经验现实的内心真实,也因此更注重叙事上的想象与虚构。而源于传奇传统,“中国历代小说常用超越于世俗常规和世俗伦理的传奇事件、传奇人物来构想世俗生活中所不能的景观;或是以讽喻寓言式的手法,来传达世俗生活的各种令人警醒或感慨的命运逻辑”[13]。传奇叙事对超常人物、超异时空的虚构架设与先锋小说追求的虚构想象、超常时空序列、超验世界竟不谋而合。传奇传统的非理性色彩以及寓言性,也为先锋小说投射现代主体自身境遇与现代焦虑等现代情绪提供可供择取与吸收的可能。毕竟“心灵传奇与理性建构”是密不可分的[14]。先锋小说的叙事不能称为传奇叙事,但传奇叙事却以“嵌入式”的叙事方式穿插于先锋叙事之中,先锋小说中不乏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事物景,它不但增强了先锋小说的神秘感,也点亮了先锋小说的传统色彩。可以说,对传奇叙事的承续与新变,也拓展了先锋小说的审美表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