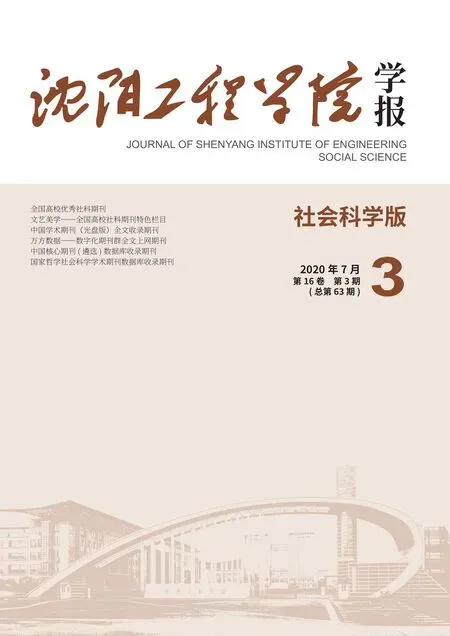男权视角下的女性书写
——以温庭筠词为例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学界对花间词中的女性形象、女性语言、“双性人格”的美学特征多表达赞美之词。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也说,早期花间的小词“可以令人生寄托之想,则是由于这些艳歌中所叙写的女性之形象,所使用的女性之语言,以及男性之作者透过女性之形象与女性之语言所展露出来的一种‘双性人格’之感情心态,因此遂形成了此类小词之易于引人生言外之想的双重或多重之意蕴的一种潜能。”[1]246但通过男性之口写出的女性心理、女性语言、女性形象是真正的女性形象吗?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花间词派文客骚人对女性的书写,并不能表现他们笔下女主人公的真实状况,是一种男权视角下的女性书写。这表现在对女性外形的书写、对女性心理的“误读”和伪女性化的语言叙述三方面。我们主要以温庭筠的词为例进行分析。
一、对女性外形的物化书写
我们读花间词派写女性的词,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词人笔下的女性,仿佛不是一个具有生命体征的人类,而是一件等待被欣赏和评价的艺术品,即作为一个审美对象、一个被物化的他者而存在的。
这一方面表现在对服饰与容貌的过度描写。纵观《花间集》,词人们笔下涌现了大量表现女性衣服饰物的名词,如“芙蓉带”“绣罗襦”“石榴裙”“碧玉冠”“凤凰鞋”“鹧鸪衫”“玉钗”“翠钗”“金雀钗”等。这些服饰一方面是女性外表美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由于词人的审美关照角度,服饰词汇在有些语境中取代了女性本身,女性鲜明生动的个性和形象在文本中隐没了。可以说,词人描写女性就是在描写一件事物,描写服饰就是在描写女性。以温庭筠为代表的大部分花间词人,他们笔下的女性无不呈现出浓妆艳抹、绮罗香泽之态。词人欣赏她们容貌的态度似乎也与欣赏脂粉装扮无异,这种纯客观的审美关照使女性形象没有了个性和生命力,沦为一个静态的被物化的他者。
又如对女子服饰的描写,以《归国遥》为例:
双脸。小凤战篦金飐艳。舞衣无力风敛。藕丝秋色染。锦帐绣帏斜掩。露珠清晓簟。粉心黄蕊花靥。黛眉山两点。[2]73
全词以大量首饰、衣服、闺中环境等意象铺叠而出,细致地描绘了一个外表华丽绮美的女子形象。词的上阕写该女子的服饰,下阙写她的闺床与打扮,尽管描写尽态极妍,甚至可以还原为一幅逼真的闺中女子图。但正如袁行霈所说“(温庭筠)词中的女性大多是静态的”[2]74,就如同一幅风景画一样,等待被鉴赏。此词中的女子形象,也不过是上述物的意象的堆砌罢了,女子缺失了其本身作为“人”的形象特征,沦为“被看”的对象。因此,词看似在写女性,是关于女性的审美,实际则是以男性为主体,从男性角度“看”女性,是关于物的审美。
另一方面,表现在女性形象与环境的融为一体。如《菩萨蛮·其二》: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2]12
花间词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与对客观环境的描写是融为一体、不分你我的。这就像画一幅肖像画,人物的衣着色彩与环境之间的相得益彰一样。词人用“水精帘”“颇黎枕”“鸳鸯锦”等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描绘了深闺的精美和雅洁,同样以“双鬓”“香红”“玉钗”等意象来表现女子的柔美之态。在这里女子与她所处的环境被同化,女子隐没在环境中,消失不见。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人对女性的描写具有这种一致的特征。《花间集》中的女性所处的环境多为深闺和庭院,这些环境的描写无不镂金错采、精美雅洁。词人所选取的客观环境本身如此,他们的措辞用语也是如此,这种一致的特征正是花间词人的一种审美理想。“薰炉蒙翠被。绣帐鸳鸯睡。”[2]358“凤帐鸳被徒熏。寂寞花锁千门。”[2]120女性人物形象和客观环境不分你我,“完美”交融,某种程度上说不过是在写他们的审美追求和审美理想。这看似体现了词人表现手法的高超,实则是对女性形象更深层、更隐蔽的隐没,是对她们的“被缺席”。
二、对女性心理的“故意误解”
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派词人,常常写到思妇的离情别绪、哀怨愁思。但实则不乏对这些女性心理的误解或“故意误解”。例如《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2]3
陈廷焯论沉郁说时说温庭筠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3]6其实是不妥当的,这里最多只能是温庭筠设想中的女主人公的无限哀伤。浦江清就说:“此章写美人晨起梳妆,一意贯穿,脉络分明。论其笔法,则是客观的描写,非主观的抒情,其中只有描写体态语,无抒情语。易言之,此首通体非美人自道心事,而是旁边的人见美人如此如此。”[2]8故我们更倾向于承认此词只不过是词人面对一件客观之物——一位“弄妆梳洗迟”的女子所做的客观的观照,然后对其心理做一个主观的猜测和臆想。甚至很可能是词人凭着回忆或者想象进行的一次虚构的文学创作,只是一种艺术表现和艺术加工,而与这女子本来的形象无关。我们可以说这首词在艺术上很成功,却不能说这反映了当时歌姬女子们的真情实感。
再如《更漏子·其六》: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2]67
“红蜡泪”、薄“眉翠”、残“鬓云”“三更雨”“秋思”“离情”“叶叶”“声声”“滴到明”,道出思妇的相思离别之苦,读来令人动容,可见温庭筠的才华不可谓不高。但是试想,词中的女子是一般的“思妇”吗?这真的是她们的相思之苦吗?
我们知道,温庭筠花间词中的女性形象的真实身份多是指晚唐时期的青楼歌姬。她们隶属乐籍,身份卑微甚至低贱,生活悲苦,备受盘剥和辖制,自身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到青楼来寻欢作乐者众多,但能真正不以玩物待她们者有几何,更不用说不顾世俗偏见将之救出苦海者。她们生存于这样的场所,对这种状况并非不知,又怎会日日做着获得拯救拥有美满幸福的婚姻和爱情的白日梦。她们整日为求生存自顾不暇,又怎会倚门望情郎、垂泪苦相思到词中这般境地。虽然我们读到,词中的女子不仅用繁杂的物饰装扮自己,也把自己当物品,像花瓶一样供人玩赏。她们苦心迎合男性的喜好和审美趣味,也不过是为谋得生存而已。词人笔下精心编织的痴情苦守的女子形象,是一种虚假的存在,只不过出于词人们的幻想和期望,或是艺术创作的需要,抑或是为供歌姬传唱以教化女性、引导她们忠贞和思念的需要。
至于这些女子的真实境遇和真实想法究竟如何,只能留待后人揣测。如花间词所写那般为思念而哀愁则很难令人信服,恐怕是为自己的凄苦命运哀愁者更多。歌姬们受教育不多,文化水平并不高,根本没有话语权可以为自己书写或作诗。若她们真有机会和能力写,恐怕也极少写这些莺歌燕舞之美,而是写自身境遇、生存之悲了。即使这些女性有自己的真实想法,甚至有作诗,她们对自身被物化的寥寥无几的“反抗”,恐怕也流传无几,无所见证,以至于无足轻重了。
三、伪女性化的语言叙述
不少词作常常以女性化的语言和女性的口吻写出,例如《更漏子》及其三这两首: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2]56
金雀钗,红粉面。花裏暂时相见。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2]63
叶嘉莹说花间小词男性词人以女性的口吻创作的部分词作,表现出女性化的情思,具有“双性人格”的美学特质,“‘女性’与‘双性’实当为形成小词之美学特质的的两项重要因素。”[1]248构成花间词美学特质的两项因素——“女性”和“双性”——都包含女性因素,但没有一项是由女性的能动参与完成的,女性在此只是没有意义的符号。事实上,这些词作所表现的并不能说是女性化的情思,而是男性模拟女性语言、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思。那么男性作者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思,又何以要用女性的口吻和女性化的语言表达呢?
劳伦斯·利普金在《弃妇与诗歌传统》中深入研究过诗歌中弃妇思妇的形象极为普遍却几乎没有被弃的男性形象这一现象,并指出男性也时有失意和被弃之感。温庭筠在词中借助女性口吻和女性化语言所表现的便是这样一种被弃和失意。男性作者用被弃的女性形象来宣泄自己内心的失意和抑郁,一方面,是对中国自屈原《离骚》以来“美人香草”“以夫妇喻君臣”的比兴寄托诗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个角度上,陈廷焯“无限伤心,溢于言表”之语是说得通的。只是到了温庭筠和花间词这里,对女性形象、女性心理、女性化的语言运用得更加细致和出神入化。另一方面,与男刚女柔的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一阴一阳之谓道”[4]268“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4]326,先秦《周易》提出的阴阳对立观,包含“阴阳”“乾坤”“天地”“男女”“刚柔”“尊卑”等相互对立的概念,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倾向于要求女性柔弱,男性刚强,男性表现出女性的特征便为世俗所不容。然而弗洛伊德在《论女性本质》中指出,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兼具男女两性的特征,“科学提醒你注意,在女人的身体里,也存在着部分男人的性器官,虽然这些器官处在一种萎缩状况中;反之亦然。科学认为这种现象表明了双性的存在,就好像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一个男人或女人,而永远是两者兼而有之。”[5]36只是一直以来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规范将彼此的性征压抑了。故此,温庭筠等男性词人模拟女性口吻和女性化的语言委婉地表达男性的失意。
再结合温庭筠的身世和仕途经历来看,我们知道,温庭筠与其他封建男性文人一样向往功成名就的仕途道路,但是他的求仕之路并不顺利,只能依附于贵族生活。几乎可以断言,温庭筠若是有更好的选择,断然不会整日与一群被视为下等人的歌姬为伍。温庭筠在青楼女子中寻求慰藉,是没有选择之后的选择。他在政治和仕宦途中碰壁,从而借助被弃女性的形象来宣泄内心的抑郁。他的不少词作和白居易创作《琵琶行》一样,是以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写他们自己的人生失意,并非是真正的女性化的语言和情思。如果仕途功名是冷酷无情的“负心汉”,他自己就是那多情苦守的“相思女”。他叙写的不过是他自己被弃和失意,这样的女性口吻和语言,并非真正的女性口吻和女性化语言。
加上温庭筠的不少词作是为宫廷娱乐而作,创作动机主要是为了“应歌”,故而显得绮靡华丽。创作这类词也许主要出于谋生的需要,他的不同可能在于比其他寻欢作乐的文人对歌姬或多或少多出几分同情。这样的同情使他刻意对词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艺术的加工和美化。这种艺术美化,并不能真正体现对这些女子的平等相待,反而让人忽视她们真实生存境遇的凄苦。由于古代女性所处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她们常常误以为男性多看一眼便是对其的尊重和平等相待。其实,他们的多看,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垂怜和施舍,是一种将她们当作一种审美对象的欣赏和喜爱,本质上与喜欢美丽的花瓶、精美的画作没有区别。那么,拟用女性化的语言,就如同拟用一个花瓶、一幅画作的语言一样。这是一种伪女性化的语言叙述,是一种男权视角下对女性的物化书写。
小 结
花间词派以温庭筠词作艺术成就最高,不少女性形象的塑造集中于表现其外表之美、相思之苦,体现出温庭筠对下层女性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同情。这些形象的描写精湛细致,在艺术上也取得很大成功,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男权视角下的对女性的物化书写,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不是当时歌姬真实形象。这与晚唐五代时期的社会审美风尚有关,也显示着女性地位的卑微、人性的被忽视,这与传统社会中女性的附属地位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