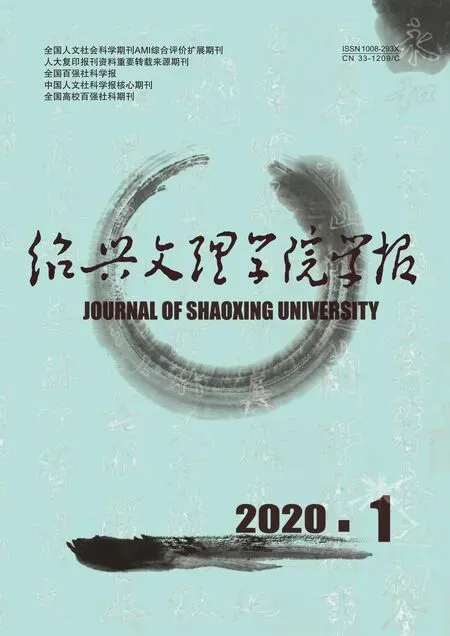香港《译丛》对周作人的译介
葛文峰 季淑凤
(1.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
一、引言
近年来,学界关于周作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散文创作及外国文学汉译方面,周氏作为作家与翻译家的文化史贡献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的视野下,学人重点关注了周作人早年与其兄长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神盖记》以及他中晚年对日本、希腊等亚欧古典文学的译作,肯定了周作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积极意义:他“数量庞大的翻译是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最具个人风格、最经得起专家推敲的作品之一”[1]20。然而,跨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交互、双向、多维度的。颇为遗憾的是,文学家周作人的对外译介却极为罕见,外国读者对周氏的文学成就知之甚少。
自1977年起,40余年来香港的《译丛》一直对周作人多有译介,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周作人的窗口。《译丛》在《发刊词》(1973)中确立了办刊宗旨即“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作品”[2]3。《译丛》杂志及其丛书致力于对外翻译、传播中国文学,并成长为中国文化对外推介的有生力量,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迄今为止,《译丛》成功构建了中国文学对外翻译传播的有效模式,积累了丰富的中国文化成功“走出去”经验[3]166。其中,《译丛》对周作人的译介是最具代表性的个案之一。
二、《译丛》中的周作人:介绍与作品
2003年,《译丛》创办30周年之际,编辑部重申其出版目标是“永远把最好的中国文学翻译成英语,送给读者”[4]62-63。《译丛》的官方网站间或对重要作家进行英文简介,其中对周作人的“著者介绍”文字较为丰富、详尽,不仅勾勒出周作人在不同时期的人生际遇,还简述了他所从事的主要文化活动。在文学成就上,着重强调了周作人的文学史地位,诸如“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与其长兄鲁迅均为新文学著名作家”“周作人以散文见长,是当时最优秀且多产的散文家”[5]。
中国文学浩如烟海,《译丛》的译介选材不仅涉及历朝历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不同作家、不同体裁的作品,仅就现当代文学而言,又覆盖了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优秀之作。因此,唯有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才能被《译丛》选译。正因选材广泛、多方兼顾的缘故,即使是周作人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入选《译丛》的作品数量也十分有限。截止2018年,鲁迅独占民国作家入选《译丛》作品数量之首,也仅有20种作品得到《译丛》的译介。为了配合作家作品的对外翻译,早期的《译丛》常设“专论”(Articles)、“短论”(Briefs)等栏目,刊登关于某位特定作家的研究性学术论文,或某位文学家的创作和翻译、随笔、文摘,以便为海外读者提供丰富详尽的背景知识。1977年春,《译丛》第7期首次介绍、翻译了关于周作人的主题内容。“专论”中的第一篇便是王靖献(C.H.Wang)的专题研究文章“Chou Tso-jen’s Hellenism”(《周作人的希腊文化观》),该文从早年周作人与希腊文化的接触写起,论述了周作人对希腊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及他汉译希腊作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论者指出,周作人与希腊文化的因缘皆由日本启示而起,在考察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与评论乃至探究他对日本的爱与憎的复杂感情时,这一点均需重点考量[6]5-28。“短论”中刊登了两段题为“How I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我是如何翻译希腊文学的》)的短文,该文选译自周作人的回忆录片段之第“184”“185”两则。第一段译文对应的段落是“我弄古希腊的东西,最早是那一册《希腊拟曲》,……所以这本小册子可以说介绍她的诗与人的”[7]421;第二段译文对应的段落是“我回到北京以后,所做的第二件事乃是重译英国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农诺斯)又通现代希腊语,译有小说集名曰《在希腊诸岛》”[7]423。实际上,这两段周作人回忆录的节选译文,主要在于向西方读者交代周氏与希腊文学的结缘及其早期的希腊文学汉译篇什。换言之,这两段篇幅极短的译文可以视作一份出自周作人“口述”的“引文”,作为王靖献论述周作人深厚希腊文学情结缘起的例证。
1986年秋,时值鲁迅逝世50周年,《译丛》第26期推出“鲁迅专栏”(Special Section on Lu Xun),集中译介了鲁迅的《破恶声论》《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野草》以及早年古体诗若干,以示纪念。在推介鲁迅的同时,《译丛》的编者也没有遗忘周作人。在编者看来,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在文化史上的时代际遇形成强烈反差:长期以来,鲁迅被誉为著名的勇士,而周作人被视为默默的隐士;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坛的领袖,而周作人则囿于沉寂的角落长达30余年[8]4。1980年代中期,恰逢周作人在中国大陆文学史上逐步得到公正评价,其作品也渐渐得到学界关注。因之,当期的《译丛》在“散文”栏目中一次性译介了周作人的作品7篇,选材数量甚至比鲁迅的作品更多。在无其他散文家作品译介的情况下,“散文”栏目可谓是“周作人散文专栏”,编者也感慨道:“迄今为止,这或许是周作人散文最大的一次对外英译之举。”[8]4不仅如此,周氏兄弟的作品几乎占当期刊登内容的80%,故而第26期的《译丛》是名副其实的“周氏兄弟专号”。
7篇周作人散文分别由三位译者翻译完成。英国汉学家卜立德(D.E.Pollard)翻译了《鬼的生长》(TheAgeingofGhosts)、《哑巴礼赞》(InPraiseofMutes)、《谈过癞》(On“PassingtheItch”),时任《译丛》助理编辑、青年学者翻译家龚丹(Don J.Cohn)英译了《入厕读书》(ReadingontheToilet),澳大利亚青年汉学家任格瑞(Richard Rigby)译介了《日本和中国》(JapanandChina)、《支那的民族性》(TheChineseNationalCharacter——AJapaneseView)、《日本之再认识》(JapanRe-encountered)。三位译者均为学者型翻译家,无论是域外汉学家还是国内学者,他们的治学范围均覆盖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譬如,卜立德曾出任《译丛》“联合主编”(Co-editor)多年,又担任刊物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从1961年开始,他便致力于周作人研究,并长期从事中国散文研究与翻译。卜立德的周作人研究成果丰硕,曾发表过《周作人及其“种植园”》(ChouTso-jenandCultivatingOne’sGarden,1965)、《周作人的文艺思想》(AChineseLookatLiterature:TheLiteraryValuesofChouTso-jeninRelationtotheTradition,1973)、《周作人:一位隐匿的学者》(ChouTso-jen:AScholarwhoWithdrew,1976)。译者一致指出,尽管文学名声一直处于鲁迅的影子中,但周作人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多产散文家之一[9]68-69。第26期《译丛》所选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时间跨度长达15年(1925—1940),较之22年间(1923—1945)出版的近20部散文集,这7篇作品在数量方面的确不多,却毫无疑问是周作人的代表性作品,是经过译者与编者细致甄选的佳作。
作为英国汉学家的卜立德,如何与周作人建立学术研究上的关联?一方面,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有其独到的特点,其写作本身与英国文学存在某种师法的关系。1921年6月16日,《晨报》副刊刊登了周作人论述散文革新的文章《美文》,他认为外国文学中的所谓“论文”,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笔者由此推测,周作人眼中西人所作的“论文”,对应的是“Essay”。在五四运动稍后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散文范畴中尚无类似“Essay”出现。故而,周作人在《美文》中不得不再三鼓励白话新文学作家对此进行开拓:“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10]97-100另一方面,卜立德早年专治英国散文,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所以,当他对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进行研究时,在1920年便名气初显的周氏散文即引起了卜立德的注意。后来经过系统研读,卜立德对周作人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尽管周作人因与鲁迅为同胞兄弟而广为人知,但是,直到1920年代后期,周作人在文坛的名气并不低于鲁迅——即使在他不创作小说的情况下。周氏文学名声的确立,如同鲁迅一样,是在《新青年》时期。周作人作为《新青年》的作者,其散文在导向新文化运动方面贡献良多。此后,他为多种刊物撰文而名声鹊起,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一时期,周作人出版散文集约15种,并译文集数卷。他的若干散文以课文形式入选教材[11]332-356。
1999年,卜立德翻译的《古今散文英译集》(TheChineseEssay)作为“《译丛》丛书”(RenditionsBooks)之一,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译丛》杂志推出的系列文丛主要有“《译丛》丛书”和“《译丛》文库”(RenditionsPaperbacks),相对于后者,面向普通英文大众读者译介中国文学的初衷是“《译丛》丛书”的受众定位。但于海外专业读者群体中,其亦以译文的上乘质量和文本的严谨学术性著称。《古今散文英译集》出版之后广受好评,评论者赞誉“其考究的译文和新颖的研究范式,为英语读者和学者提供了译本难得的经典译作”[12]51-66。该译集不仅收录了第26期《译丛》杂志已刊的《入厕读书》《谈过癞》《鬼的生长》《哑巴礼赞》等4篇周作人散文的译文,还补入一篇《苦雨》(RelentlessRain)。《古今散文英译集》共计编入古今36位作家的74篇散文译文,始于诸葛亮的《出师表》(ToLeadouttheArmy),止于张行健的《婆娘们》(Goodwives)。周作人以5篇散文入选其中而居首位,李渔、鲁迅则分别以4篇散(杂)文得以编译其中而居其次。卜立德认为,周作人的创作旨趣与英国散文大不相同,却又能对英国散文持有赞赏态度,并在创作中借鉴某些成熟的技法[13]17。
2017年,《译丛》杂志第87、88期合刊为“民国城市小说”(RepublicanUrbanFiction)专号,重点译介了周瘦鹃、徐卓呆、孙了红等“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家的经典之作。《译丛》主编、美国汉学家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在开篇长文《构建“伟大分水岭”:20世纪早期的城市文学》(Cultivatingthe“GreatDivide”:UrbanLiteraturein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a)中,系统论述了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民国通俗文学所面临的不同文学评价,勾勒出其文学批评史的轮廓。在文中,胡志德分别援引、翻译了三段周作人论述通俗文学的文字,分别译自周氏论文《论“黑幕”》《再论“黑幕”》《贵族的与平民的》:
We are absolutely not saying that things[behind the]black screen should not be exposed,and in fact we strongly advocate that they should be,but absolutely not in this way….To do something like this,one must be a man of letters with an elevated outlook on life to qualify, and this is simply not something a person who creates“light reading”can do.(我们决不说黑幕不应披露,且主张说黑幕极应披露,但决不是如此披露。……做这样事,须得有极高深的人生观的文人才配,决非专做“闲书”的人所能。)[14]7-8
The Black Screen[novel]is a produc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citizenry,quite sufficient to provide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the psychological abnormalitie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ociety,but as for literary value,it is“not worth a penny”.(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性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14]7-8
Literature should be written in the key of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people, then be baptized by the aristocrac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re be created a true humane literature. …From the literary perspective,the best thing is for the common people to be rendered aristocratic.(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从文艺上来说,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14]7-8
不同于以往《译丛》对周作人散文(含回忆录)作品的译介,胡志德译介的上述内容是对周氏文学思想的一次较为集中的展示。这三段译文集约式地阐明了周作人对民国黑幕小说的基本态度,他以直率的道德与个人偏好为标准衡量黑幕小说,既指明黑幕小说由文人进行评论,又指出其价值更具社会性。就通俗文学而言,其生成应是平民素材的贵族化,方为“真正的人的文学”。
三、《译丛》对周作人散文的翻译
“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读者”是《译丛》持之以恒的办刊原则,这使得《译丛》出版物极其重视域外读者的理解与接受,将其中国文学译作的传播效果作为根本追求。因此,明确的受众意识是《译丛》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出版准则。尽管《译丛》编者也颇为无奈地承认,“即使著作等身的学者,也不一定成为优秀的散文家。这也正是散文在各类文学译介中数量较少的原因”[15]5-6。但卜立德等译者均能遵从《译丛》的编译方针,根据英文读者的文化语境、母语习惯与跨文化认知能力而采用多样化的翻译策略,将周作人作品的精髓尽力译介出去。
《入厕读书》是周作人的代表性散文之一,以戏谑幽默的口吻讽刺了民国时期国民的若干劣根性。该文首次以龚丹译文收入《译丛》杂志,“《译丛》丛书”《古今散文英译集》汇编时又收录了卜立德的译文。《入厕读书》先后两种不同译文同属《译丛》的不同出版物,更便于比读、管窥翻译策略的异同。试举《入厕读书》中幽默片段的翻译如下:
原文:小时候听祖父说,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诀云,老爷吃饭快,小的拉矢快,……[16]282-287
龚丹译文:When I was a boy,my grandfather told me that male servants in Peking had a saying that went like this:
Our masters may eat quickly,but we servants shit quickly.[17]87
卜立德译文:When I was small my grandfather told me the footmen in Peking had a saying:“The old masters make fast work of their food,the young masters make fast work of their crap”.[13]136
周作人以北京的跟班的口吻,道出一则俗语“老爷吃饭快,小的拉矢(屎)快”。“跟班”指旧时达官贵人身边的使唤佣人,多为男性,龚丹译为“男仆人”(male servants),传达了基本的含义。卜立德将“跟班”译为“footman”,较之龚译更地道,特指旧社会府宅大院中的男仆、门房或侍者。“老爷吃饭快,小的拉矢(屎)快”源自民众话语,读来诙谐幽默又不失风趣。前后两个短句虽然均指动作“之快”,但是意在对比,形成强烈反差,令人哑然失笑:“老爷”与“小的”、“吃饭”与“拉矢(屎)”。龚丹将此句俗语的译文另起一行,以示突出并以“but”连接前后意义转折的两个并列短句。他更将“吃饭”“拉矢”对译为“eat”与“shit”,分别辅以副词“quickly”修饰,别具音韵效果。卜立德在译文中也重复使用了英文中的惯用短语“make fast(quick) work of”(快速、简便地做完某事),将“吃饭”与“拉矢(屎)”的两个动词性词组译为名词“food”“crap”,置于句末以便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卜立德误解了“小的”的含义。“小的”原本是跟班的自称,卜立德误以为是对应“老爷”的“少爷”,遂译为“young master”。
作于1924年的《苦雨》是周作人早期散文的代表作,他以书信体的札记形式向“收信人”孙伏园讲述各种各样的“雨”带来的苦楚。作者在这种“私人化”的散文写作中,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借物抒怀,在平淡的叙述中又不乏诙谐幽默。卜立德给予《苦雨》高度评价,强调该文特别之处有三:一是书信体、日记体散文在当时的散文中并不多见,是一种“名副其实”却未发扬光大的文学样式;二是作者以日常“琐碎”状写“人生趣味”(human interest),极富文学性;三是该文写作淡雅脱俗,正是周作人性格的显现。文中的幽默正是作者的幽默[13]131。周作人在描述北京的雨时,如是写道:
原文: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10]97-100
译文:A week ago the rain caused the west wall of our back garden to collapse, and the next night we had a visit from gentlemen of the burglar fraternity to test the steel mesh over our north wing windows.The day after discovering that we hurriedly hired seven or eight building workers,and in two days they had the wall practically rebuilt,after which we sleep soundly. But another downfall the night before last brought down twenty or thirty feet of the south wall next to the main gate.[13]133
卜立德的译文一如周氏原文那般简约、质朴,行文紧扣书信体的“诉说”特征。卜译的最大特色是对原文幽默的传译,并进行适度文化层面的归化,以便于英文读者理解。周作人文中言及大雨淋坍院墙之后便有窃贼光顾,称他们为“梁上君子”。“梁上君子”是汉语中常见的对“小偷”的别称,既形象又诙谐,并能体现被盗者戏谑、讽刺的口吻。卜立德其译为“窃贼同盟的绅士”(gentlemen of the burglar fraternity),虽然失去了“梁上”形象化的意象,在以“gentlemen”对译“君子”的同时,增译出了“fraternity”(同盟、联谊会)以及“造访”(visit),幽默效果骤然倍增。不仅如此,原文中盗贼系“破(铁丝)窗而入”,作者使用“摸索”一词,委婉滑稽。译者以“test”译之,意为“测验、检查(铁丝窗)”,同样令读者哑然失笑。当院墙重修几近完工时,作者失盗的担忧消除,“可以高枕而卧”了。显然,“高枕而卧”源自“高枕无忧”,译者译为“沉睡、酣睡”(sleep soundly),舍弃“高枕”的意蕴,消除读者阅读的障碍。同样,“二三丈”的长度单位“丈”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词汇,译者也将“二三丈”的长度转化为“二、三十英尺”(feet)。
“散文难译,难就难在‘求真’基础之上再‘求美’,且要美得自然、美得出神入化。”[18]117-119《译丛》译介的周作人散文可谓基本达到了这一标准,译者在“求真”“求美”的向度上孜孜以求,更兼顾西方读者阅读理解的便利,向域外展示了周作人作为散文家的文学审美与特质。
四、结语
在周作人对外译介极为少见的情况下,香港《译丛》对周作人颇为关注,对其作品与文学思想进行译介。时至今日,《译丛》杂志及其丛书业已传播到全世界20多个国家,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及大洋洲等地。由此可见周作人凭借《译丛》而流布的广泛程度:一方面,周作人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散文创作而被列入《译丛》译介选材范围;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周作人能够长期进入《译丛》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与鲁迅难以隔断的关联使然。美国学者保罗·福斯特坦言,罗曼·罗兰的赞誉极大地提高了鲁迅的国际声誉,亦即鲁迅因罗曼·罗兰的“托庇有了名”[19]39-48。无独有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姗姗来迟”的周作人,恰逢鲁迅逝世50周年纪念(1986)获得与兄长一同被《译丛》译介的机会,让西方读者一睹周作人作品的风采。虽然《译丛》强调周作人的文学价值,凸显他于鲁迅之外的独立性,但周作人在《译丛》中的译介在极大程度上正因鲁迅的“托庇有了名”。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办的国际汉学名刊《中国季刊》(TheChinaQuarterly)极为认可《译丛》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它在深度、广度与质量方面,均超越了另一份推介中国文学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1951—2001)[20]225-226。剑桥大学荣休汉学教授、《剑桥中国史》主编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称赞卜立德编译的《古今散文英译集》让英文读者切实体验了中国散文的文体特征,更能从中体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细节[21]。作为周作人对外译介传播的载体,《译丛》杂志与“《译丛》丛书”之一《古今散文英译集》在英语世界享有如此盛誉,其国际传播中国文学的权威地位使得周作人的对外跨文化传播效果得到了可靠的保障。《译丛》对周作人的译介,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在《译丛》的启示下,我们期待周作人的更多作品通过译介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