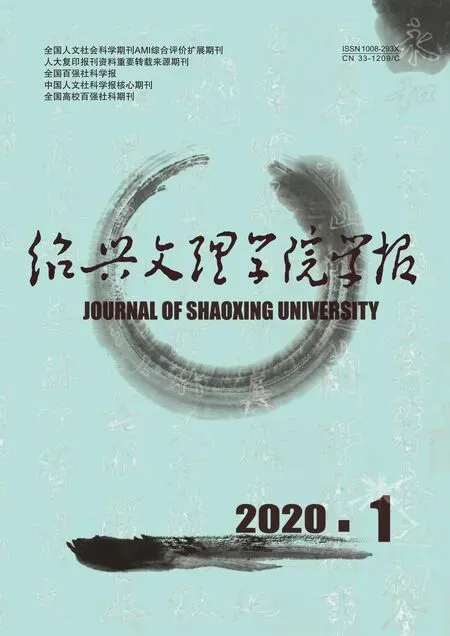刚健与平和:鲁迅、周作人美学思想比较论
丁文敬
(绍兴文理学院 图书馆,浙江 绍兴 312000)
刚、柔是中国哲学的一对核心概念,如《周易·系辞下》所言:“刚柔者,立本者。”刚、柔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两大基本原则,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里即指出:“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1]同时,刚、柔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两大主要范型,这就是清代姚鼐概括出来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阳刚之美”的文学“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2],“阴柔之美”的文学“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2]。作为两种文学创作原则和美学风格范式,“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中仍有突出的表现,譬如鲁迅和周作人,他们虽为同胞兄弟,但其精神境界却截然两分:“一个是进取的,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残酷的,一个是飘然的;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谧的。”[3]其美学思想,一个是刚健的,一个是平和的;一个是激进的,一个是中庸的;一个是崇高的,一个是冲淡的。本文试图对鲁迅和周作人的美学思想寻根溯源,通过比较,发掘其深层蕴涵和理论意义。
一、刚健:鲁迅美学思想的核心
毛泽东主席对鲁迅有一个经典性的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4]这个评价主要从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凸显出鲁迅的“阳刚之气”,充分肯定了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精神。关于鲁迅的文学精神,刘再复有精当的看法:“鲁迅是一种典型的热文学。《呐喊》《热风》《铸剑》,连名称都是炽热的,鲁迅把自己的杂文称作‘匕首与投枪’,称作‘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当然是热的。即使是前期的小说,其基调也是批判的,抗争的,感愤的。”[5]这里所谓的“热”,实际上指的就是鲁迅美学思想的激进、批判和刚健精神。
具体而言,鲁迅的刚健美学思想最早形成于他留学日本期间。1902年,鲁迅在东京即与革命党人有所接触,尤其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许寿裳回忆道:“一九O二年春,革命元勋章太炎先生避地东京,和中山先生会见,英杰定交,同谋革命,……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沈痛。……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元勋的莫大的影响。”[6]鲁迅的革命和抗争精神由此被点燃,但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主要表现为“尚武”精神。1903年,鲁迅译《斯巴达之魂》一文,其目的就是借斯巴达三百勇士的历史故事来弘扬“尚武”精神:“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7]5鲁迅指出:“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7]2可见,鲁迅早年的刚健之气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反叛和革命精神完全合拍。
此后不久,鲁迅接触到尼采思想。尼采是鼓吹超人学说和强力意志的哲学狂人,对鲁迅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他对欧洲传统伦理道德的猛烈批判。简括地说,尼采认为,旧道德违反自然,否定生命;旧道德提倡柔弱,导致生命意志的退化;旧道德提倡无私,抹杀个人;旧道德反对创新,阻碍人类的进步。在鲁迅眼中,中国的封建道德恰好具有类似缺陷,需要尼采式的摧枯拉朽的批判。“尼采执著于人生的态度和积极寻求人生意义的奋斗者形象,为鲁迅所神往。鲁迅褒扬尼采反对19世纪文明之‘伪’与‘偏’,赞叹尼采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也’,突出其反抗传统和发现个人两大功绩”[8]。据说,鲁迅最爱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将其作为案头之作,颇多征引,乃至模仿。所以说,尼采的强力生命意志和反叛精神也成为鲁迅刚健之气的重要来源。
鲁迅的刚健美学思想集中体现于《摩罗诗力说》一文。鲁迅在文中主要介绍、评论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八位“摩罗诗人”。这些诗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9]87,他们的诗作“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9]48,“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9]67!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平和”极为不满,譬如,他批判老子学说令人心如死灰,以无为之治、小国寡民之道麻木世人。他提倡“伟美之声”,认为真正的诗人应该“撄人心”,应当具有崇高、刚健的风格,“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激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9]51。他对拜伦赞赏不已,认为拜伦直抒胸臆,意气风发,充满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对突破旧传统具有示范意义。在文章的结尾,鲁迅呼吁:“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9]88
以上可见,鲁迅在留日期间就已经将“刚健”确立为自己美学思想的核心,由此也奠定了他终身的审美理想。回绍兴期间,他在《越铎》创刊辞中声明办报宗旨为“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在辑录家乡先贤著作的过程中,他又深受越文化中复仇、韧性、进取、叛逆等精神因子的影响。写于1925年《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传统中庸之道的战斗檄文,是鲁迅表达刚健精神的力作。之后,鲁迅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将刚健精神融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去了。鲁迅留下的遗嘱中就有“一个都不宽恕”的愤世之言,这正是他刚健精神的遗世之音。在文艺创作方面,鲁迅将这种刚健精神渗透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等忧愤深广的小说杰作,以及数量巨大的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展开深刻批判的杂文之中,成为“精神界之战士”和“中国现代文学之父”。
二、平和:周作人美学思想的主旨
赵京华将周作人的审美理想称为“东方境界”,认为周作人的“以中国传统道释二家自然主义人生观为哲学基础的自然主义审美理想,与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共生互补,其极境是包含同时又超越了世俗人间、伦理规范、人情物理而化成的自然、宁静、淡泊、飘逸、闲寂、平和的空灵境地”[10]。这种观点相当有见地,“平和”确实是周作人美学风格和美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细究起来,周作人的平和美学思想也是在留日期间形成的。周作人在日本留学六年,对日本的人情风俗喜爱有加,甚至声称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与鲁迅喜爱叛逆型的“摩罗诗人”不同,周作人最喜欢的作家是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松尾芭蕉等人,而这些作家的总体风格便是平和、冲淡。他在一篇文章中毫不掩饰地表明对这种美学范式的喜爱之情:“这类文章我平常最所钦慕,勉强称之曰冲淡,自己不能写,只想多找来读,却是也不易多得,浅陋所见,唯在兼好法师与芭蕉,现代则藤村集中,乃能得之耳。”[11]事实上,这些作家的美学风格可以归属于日本美学中最具本土特色的三个美学范畴:“幽玄”“物哀”“空寂”,追求的是朦胧、含蓄、隐约、悠远、空寂和余情之美,这都是周作人深得于心的。新文化运动失败之后,周作人从十字街头遁入象牙之塔,往后又做起了“苦雨斋老人”,其创作趋向和美学追求具有十分自觉的“幽玄”“物哀”“空寂”意识。
除了受到日本文化和美学的影响,周作人平和美学精神中还含有中西“中庸”哲学和文化思想的底蕴。随着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退潮,周作人对复兴古文明兴趣日浓,他甚至主张应当将先秦时期的儒家文明与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兼容,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现代文明。在他看来,中国初始儒家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庸”:“希腊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思想相同很多。‘苏格拉底,即中国之孔子’一语,实是。他们一样地求生活之舒适,注重现在,取中庸态度,自然中看出人生他们同样叫‘过犹不及’‘满招损’的口号。这样类同的思想,东方的中国决计能了解。”[12]周作人偏爱性心理学家蔼理斯恰好缘于其中庸思想,“蔼理斯的思想我说他是中庸,这并非无稽,大抵可以说得过去,因为西洋也本有中庸思想,即在希腊,不过中庸称为有节,原意云康健心,反面为过度,原意云狂恣”[13]。
《中庸》开篇即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4]表现在美学精神方面,即倡导“中和之美”,也就是“文质彬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节制”“和谐”“适度”。周作人曾直接表明自己的美学理想:“我的理想是颜之推的《家训》,但是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这部《颜氏家训》所表示出来的,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可以说是这类著作之极致,后世惜少有知者。”[15]由此可知,周作人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平和冲淡的小品文,正是其平和美学思想在文学上的呈现。
如果说周作人早年的文章尚有一些批判封建礼教之气,那么,1924年之后,他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追求逐渐明晰起来,文章越来越走向冲淡与平和,这尤其体现于他的《看云集》,他写下了“草木虫鱼”系列,对“金鱼”“蝙蝠”以及“水里的东西”进行文化品读;还有《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苍蝇》等,也都成为他以平淡自然为特色的现代散文名篇。
三、拯救与逍遥:美学思想背后的人生选择
鲁迅和周作人的美学思想具有刚健与平和的鲜明差异,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从性格、血型、气质等偏重于生理的层面来加以解释,正如林语堂所说:“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16]但是,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也从来不存在抽象的美学思想,人的性格性情和审美理想与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人生遭际等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譬如,周作人曾自白说他心中住着“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也就是说,他的个性之中既有温和,也有叛逆,而且这种叛逆性格在其留日期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确实有所体现,即,在政治方面,追求“新村主义”的进步理想;在文化方面,对封建吃人礼教进行揭露和批判;在文学方面,倡导“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但是,面临五四启蒙运动的挫败和政治形势的恶化,他开始宣扬文学无用论、“自我表现”论、“言志”论,沉迷于小品文创作,追慕文章的平淡自然之境,进而躲进书斋,当起了“文抄公”。处于同样历史语境下的鲁迅,则克服了虚无主义情绪,做了一名不屈不挠的“这样的战士”。由此可见,鲁迅的刚健和周作人的平和,既是他们的审美追求,更是他们自觉的文化抉择和人生选择。
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生态度,前者是“拯救”,后者是“逍遥”。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是要唤醒并拯救国人麻木的灵魂,改造国民性。他从事小说创作,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启蒙主义思想,有着明确的批判社会、改良人生、改造国民性的崇高目的,进而鄙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观”。在1930年代,当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倡导超功利主义的晚明性灵文学时,鲁迅尖锐地指出,“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欣赏这些雅致小品呢?这些都是消极避世、麻醉斗志的精神毒品,而“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7]。非常明显,在刚健与平和美学冲突的背后,存在的是政治方向、人生态度上的不同选择。
周作人的平和、逍遥思想成因尤其值得关注和反思。首先,是悲观主义思想。“我最喜欢读《旧约》里的《传道书》。传道者劈头就说,‘虚空的虚空’,接着又说道,‘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都是使我很喜欢读的地方。”[18]以这种历史循环论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来观照现实人生,周作人对社会改革和国民性改造充满悲观绝望的情绪,他感叹“教训之无用”,逐渐放弃了启蒙理想,进而躲进故纸堆中麻醉自己,在文学上选择了“为艺术而艺术”,甚至连“文学店”也要关门。这与鲁迅的历史进化论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周作人的怀疑、悲观和逃避,成就了他的冷漠、冲淡与平和,同时也丧失了思想的深刻性和积极性。其次,是中庸主义思想。如前所述,周作人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中庸”,虽然周作人用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现代性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有所改造,但中庸主义对和谐、适度、中和精神的强调渗透到他的心灵深处,在那个需要抗争的时代氛围中,难免会导致冷漠、保守、消极和颓废,“周作人抱着全部‘精炼的颓废’,也带着他的全部的功绩和成就,一步一步离开人民,一步一步离开国家民族,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古老的传统的悲剧”[19]。在周作人身上,我们体察到传统中庸主义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中庸与道家的柔弱、守雌、不争、无为,以及佛教的超脱、空无等思想糅合起来,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因袭负担和精神麻痹,因此也才能更好地理解鲁迅反中庸主义思想的深刻,更好地领悟鲁迅韧性文化人格之伟大。
综上所述,鲁迅的刚健美学思想和周作人的平和美学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大重要的美学范型。在鲁迅的影响下,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胡风、冯雪峰、聂绀弩、萧军、萧红等一大批作家、批评家成长起来,并将其批判和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周作人也影响了一批弟子,如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江绍原、任访秋等人。不过,后世对鲁迅的评价远高于周作人,其原因在于,鲁迅的刚健美学思想蕴涵了“拯救”精神,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0]中国需要的不仅是刚健的美学思想,更需要具有拯救精神和济世情怀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