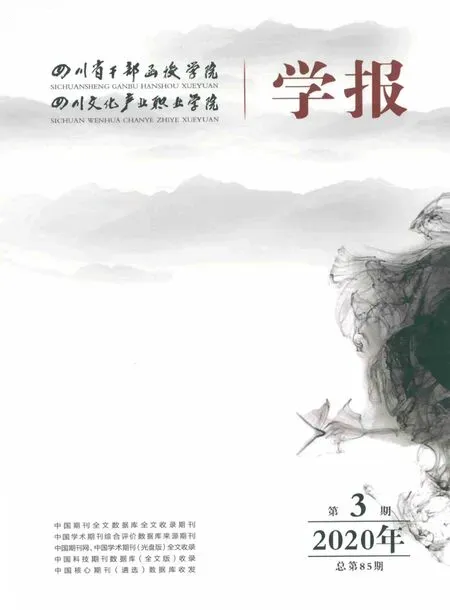“保守”传统的英雄:《斯通纳》中的自我塑造
◇闫现磊◇
美国小说家约翰·威廉斯在1965年出版了《斯通纳》,适逢“二战”结束,各种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被年轻人奉为圣经。“60年代,文学大师福克纳、海明威相继逝世,文坛涌现了形形色色的文学潮流,紧跟时事政治,先锋实验、反传统小说叙事,成为大家的圭臬。黑色幽默、荒诞派、存在主义等文学流派盛行,《第五屠场》《第22条军规》等小说兴起,青年崇尚叛逆、嬉皮士运动、摇滚乐。”①周南焱:《斯通纳,一个美国中西部的堂吉诃德》,《北京日报:文化周刊·艺谭》2016年4月7日。这样的时代,没有幽默、没有浪漫、没有甜蜜幸福、古板固执而又略显老套,《斯通纳》的出版明显不合时宜,销售寥寥。然而它近十年在欧美各国重新出版,却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小说开头,作者就交代了主人公平淡无奇的一生:
威廉·斯通纳是1910年进的密苏里大学,那年他十九岁。求学八个春秋后,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拼杀犹酣的时候,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职位,此后就在这所大学教书,直到1956年死去。①〔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页。
威廉·斯通纳于十九世纪末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贫苦务农家庭。他父亲送他到密苏里大学学习农学经营,但他却爱上了与贫瘠农地相差甚远的英语文学,后来甚至成为一位学者。不过,年复一年,斯通纳的生活遭遇一件又一件的挫折:与“上流社会”女子的婚姻使他与家庭疏远、教学与研究陷入困境、妻子和女儿逐渐淡漠自己,以及一段被丑闻胁迫而终止的婚外恋情。斯通纳在他不断向自己内心追求的过程中,重新探索了纯朴祖先们传承下来的理智德性与静默隐忍等力量,这些力量伴随他面对一生无法逃避的孤寂,这孤寂最终成就他完成自我的塑造。
引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启示
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基于对文艺复兴“自我造型”的研究,力求在“反历史”的形式化潮流(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中重标历史的维度,要在“泛文化化”的文学批评中重申文学话语范式对历史话语的制约,要在后现代“语言游戏风景”中,张扬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关系。他认为“自我”是能够塑造成型的意识,“自我”通常指自我意识,强调人能进行自我对象化和自我区分,在认识活动和道德活动中具有主体的作用。“自我”问题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是在生命活动中力图塑造自我而实现真正的善,自我意识将自身和一定欲望相统一,就产生了行为的动机,而动机就是“行为中的意志”。人之所以有意志,就是因为人不满足现状,力图通过自我塑造而趋向善②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9页,第400页,第400页。。
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自我塑造是在自我和社会文化的“合力”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1)自我约束,即个人意志权力;(2)他人力量,即社会规约、精英思想、矫正心理、家庭国家权力;(3)自我意识塑造过程,即自我形成“内在造型力”。而造型本身就是一种本质塑形、改变和变革。这不仅是自我意识的塑造,也是人性的重塑和意欲在语言行为中的表征③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9页,第400页,第400页。。格林布拉特打破了传统历史—文学的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致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而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它异权力相激相荡的“作用力场”,是新与旧、传统势力与新生思想最先交锋的场所。他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划分为两个层面: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人物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史是人性重塑的心灵史,“人性和人性的改塑都处在风俗、习惯、传统的话语系统中,即由特定意义的文化系统所支配”④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9页,第400页,第400页。,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个体也是处在这种复杂的权力运作中,具有特定的时代性和局限性。但真正伟大的作品,同时也向主流意识形态发起进攻,“它们置身于特定地点特定时代能够被言说的内容的最边缘,冲击着自己文化的疆界”⑤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679页。,特别是一流的言说者,对于主流权力话语存在着能动性。
回观《斯通纳》,从一定程度来讲,这是一本毫不讳言地坦诚自己的失败、孤独、有限性的小说,斯通纳出生于穷苦的土地,以教书度过一生,始终追求着文学的价值、语言的魅力、历史的智慧。他秉持着正直、纯洁,梦想着一切崇高的事物,但却和时代异常疏离,当他的命运、道德、伦理、情欲、人格、学问面临来自历史、现实、战争等组成的庞大的权力关系网络的压制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不与战争的“正义”、社会的“规范”、世界的“秩序”为象征的蝇营狗苟同流。然而,换个角度来说,他的一生又是平庸的,平庸至极,20世纪前期的一切巨变,在他身上都只不过是用来标记时间的日期而已。小说在一开始就指明了,斯通纳所留在世界上的一切,仅仅是一本无人翻阅的关于中世纪的学术文献手稿,他的一生看来都是那么单调而无趣,甚至用几个词就足够概括:出身农家、读书学习、获得教职、教学研究、结婚生女、工作纠纷、因病逝世,外加一段故事中唯一有些色彩却转瞬即逝的婚外恋情。
生活总给人两难的抉择,也许很多人面对自己无力改变的平庸、面对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美国梦”的破灭,面对战争过后满目疮痍丧失感知能力的灰暗生活,都会认为生命不值得再继续下去,如同斯通纳的银行家岳父,如同斯通纳一生纪念的好友戴夫;同样还有一些人,荒唐地为了那些所谓充满意义的理想和幻想而死,比如小说中为了战争的正义、国家的荣誉而轻易地走上战场客死他乡的年轻人们。一些人在失去自视为珍贵事物的同时,也随之主动放弃了对生命的占有,而另一些在精神性反思上过于偏执的人,则是在纯粹的反抗中进行了思想的自杀。然而斯通纳却一直默默地对一切保持着疏离,面对庞大的权力机制,他既颠覆疏离着荣誉的“正义”战争,也同样颠覆性疏离着生活的平庸本身。约翰·威廉斯以一种文本的“能动性”,极力让斯通纳在他不断向自己内心追求的过程中,保守住纯朴祖先们传承下来的理智德性与静默隐忍等力量,这些力量伴随他面对一生无法逃避的孤寂。新历史主义人为自我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一个处于历史、社会、文化、伦理等诸多面向影响作用下的过程。借助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启示,深入考掘,在对《斯通纳》展开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斯通纳一生中四次重大事件,我们可以揭橥出斯通纳自我塑造构成了一个“本来自我、道德自我、伦理自我、社会自我”的四元结构,正是这四元结构,对应着斯通纳的四重人格——文学人格、历史人格、情欲人格和社会人格,由此形塑了斯通纳的真实“自我”。
一、本来自我:文学人格的意识苏醒
威廉·斯通纳出生在密苏里中部布恩维尔村附近的一家小农场里,“这是一个孤单的家庭,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全家被逃不掉的辛劳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儿”。①〔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第4页。原本高中毕业后回农场务农便是他必然的命运,然而,县里来了一个陌生人,他的一番话从此改变了斯通纳的命运。那人“上个星期”说在哥伦比亚的大学里新设了一个农学院,做父亲的应该送儿子到那里去学习。“上个星期”,说明斯通纳的父母就此已经做了全面的思考,其中定涉及一定的牺牲和顾虑。从这一刻,我们开始看到斯通纳面前的光:
斯通纳的双手平摊在桌布上,在灯盏亮光的照耀下,桌布闪烁着暗淡的光。他去最远的地方没有超过布恩维尔……他尽量抑制着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②〔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第4页。
可见,斯通纳的内心是非常向往的。于是,一个崭新的人生开始了。那年秋天,斯通纳去了哥伦比亚,正式报道,成为农学院的一名新生。
在农学院,斯通纳修的是理学士学位,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需要修两门课程——土壤化学和英国文学概论。土壤化学他很感兴趣,可是,必修的英国文学概论“却空前的让他有些烦恼和不安生”①〔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第14页,第17-18页,第23页。。这种不安和烦恼促成了斯通纳新生命的萌芽。老师阿切尔·斯隆通过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发现了斯通纳。“这首十四行诗讲的是什么意思?”斯隆持续追问,“莎士比亚先生穿越三百年再跟你讲话,斯通纳先生,你听到了吗?”老师通过经典文学去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斯通纳被这首诗点亮了:
有那么几个时刻,威廉·斯通纳意识到自己使劲屏住呼吸……他把目光从斯隆身上移开,打量着教室。阳光从窗户里斜照进来,落在同学们的脸上,所以感觉光明好像是从他们自身散发出来。迎着一片黑暗释放出去……②〔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第14页,第17-18页,第23页。
那一年的第二学期,斯通纳中断了农学院的课程,选修了几门哲学和古代史导论课,以及两门英国文学课。等夏季回到父母身边,他对自己在大学的学习只字不提。“斯通纳的自我意思开始苏醒,他从未以这种方式感知过自己”,他开始有了孤独感:
有时,晚上在自己的阁楼房间,他正看书时会抬起头来,盯着房间那些黑乎乎的角落,在暗影的衬托下,灯光闪烁不定。如果盯的时间很长又太专注了,那片黑暗就会凝聚成一团亮光,它带着自己阅读的东西的那种无形的样式。他又会觉得自己走出时间之外,就像那天阿切尔·斯隆在课上跟他讲话的感觉。过去从它停留的那片黑暗中出来聚集在一起,死者自动站起来在他眼前复活了;过去和死者流进当下,走进活人中间。③〔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第14页,第17-18页,第23页。
鉴于斯通纳在文学课程上的优异成绩,斯隆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建议斯通纳继续攻读文学硕士,然后边做助教边攻读博士学位,进而正式成为一名教师。这个建议让斯通纳倍感惊喜,当问及斯隆自己为什么确定“想当个老师”时,斯隆给出了一个自己兴奋的回答:
“是因为爱,斯通纳先生”,斯隆兴奋地说,“你置身于爱中,事情就这么简单。”④〔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第14页,第17-18页,第23页。
是的,因为爱。约翰·麦格翰在《斯通纳》台湾译本引言中提道:“如果这部小说有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必然是关于爱,各种不同形式的爱及各种摧毁它的力量,‘那并不是一种灵,或者是肉的激情;相反的,它是一种包含了灵与肉的力量;更具体地说,它仿佛是一种爱’。”⑤〔美〕约翰·威廉斯:《史托纳》,马耀民译,台北:啟明出版社,2014年,第18页,第27页。“他对未来还没有什么规划,而且对谁都没有说起过自己的这种不确定”,斯通纳的爱,是源于对文学世界古老的爱,“从农到文”是斯通纳自我意识觉醒的本我选择。这种爱甚至不顾前来参加学士学位毕业典礼的父母的麻木、痛苦和扭曲。面对持续的沉默,斯通纳完成了文学性格的最终洗礼:
斯通纳想给父亲解释他打算干什么来,试图在他心中唤起自己的重要感和目标感。他听着自己的语词落下来,好像都发自别人之嘴。他望着父亲的脸,这张脸接受者这些语词,就像一块石头接受着一只拳头的反复击打。他讲完后,坐在那里双手紧扣在膝盖之间,低垂着脑袋。他听着屋子里的沉默。⑥〔美〕约翰·威廉斯:《史托纳》,马耀民译,台北:啟明出版社,2014年,第18页,第27页。
二、道德自我:历史人格的决然疏离
1915年春天,斯通纳修完了文学硕士课程,完成了论文,一方面着手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开始在斯隆的安排下正式成为一名大学讲师。“他刹那间就变成另一个人,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他意识到自己内心某种东西在不断变化……他知道了,他读过的弥尔顿的诗歌或者培根的随笔,乃至本·琼森”的戏剧改变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文学的主题,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文学依赖它”。
也正是这个阶段,斯通纳有了自己的朋友,他们是自己的硕士研究生留校工作的同学:马斯特思和戈登·费奇,这类似于一种人生阶段的重大仪式,他有了能够进行精神沟通的朋友,马斯特思和戈登·费奇正是这种具有典范意义的朋友。“虽然大家相处的不错,可并没有成为亲密朋友;他们并不吐露心声,也很少在每周聚会之外见到对方。”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关于大学本质关于每个人本质的谈话。在谈到斯通纳的本质时,马斯特思面带微笑,带着恶毒的冷嘲热讽的表情,转向斯通纳:
你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单纯的土地的孩子,像你对自己假装的那样?噢,不是,你也在弱者之列——你是个梦想家,一个更疯狂世界的疯子,我们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诃德,但没有自己的桑乔。在蓝天下欢跳……但是你有这个瑕疵,那个顽疾。你觉得有某种东西,有某种东西值得去寻找。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快就会明白。你同样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不会跟这个世界拼搏。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躺在那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你总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而它没有那个东西,它也不希望如此。棉花里的象虫,豆荚里的蠕虫,玉米里的穿孔虫。你无法面对它们,你又不会与它们搏斗;因为你太弱了,你又太固执了。你在这个世界没有安身之地。①〔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页,第42页。
这一部分可以看成一场被奥古斯丁思想洗礼过的斯多葛式占卜。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预言,但他并没有因此丧失偶然性和创造力,他依然拥有自由意志, 因为正是这样属于他的自由意志引领他走向属于他自己的命定。②张定浩:《爱的秩序》(上),《书城》2016年第8期。接下来,这种“自我塑造”立刻遭遇到了考验——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三年,美国宣布参战。宣战后不久的那几天,斯通纳“忍受着某种迷茫的折磨”。他发现自己内心有一片巨大、冷漠的保留地。“他憎恨战争对大学强行制造的撕裂;可是他又发现自己内心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也无法促使自己去恨德国人”。当费奇笑着跟他说马斯特思打算跟自己一起去报名应征参军后,斯通纳怀揣困惑与迷茫来向老师斯隆询问,斯隆提起了另一场战争——美国南北战争:
当然,我记不得那场战争,我还很小。我也记不得父亲了,他在战争的第一年就被杀死了。但是我看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一场战争不仅仅屠杀掉几千或者几万年轻人,它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残暴者了,动物,那些我们——你和我以及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污秽中培养出的动物。③〔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页,第42页。
面对历史的宏大叙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具有颠覆现实道德、伦理等诸多权力关系的隐形力量,关键在于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面对斯隆没有答案的答案,斯通纳沉默了好长时间。实际上,作为生命个体,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虽然有征兵制,但是斯通纳也有申请免征的权利。参军与否的选择权完全在于他自己,“这又是一个精巧的设置,我们由此可以有机会看到某种古典思想的回声,它强调人身处十字路口时掌控自己命运的义务,迥异于日后我们熟悉的种种现代、后现代处境下的人的无助、妥协乃至绝望悲凉。”①张定浩:《爱的秩序》(上),《书城》2016年8月。斯隆对斯通纳说:
你必须记着自己是什么人,你选择要成为什么人,记住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意义。②〔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页,第44页,第60页。
斯通纳回去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天没去上课,他必须做出选择,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大事件,第二次重大选择。唯有第二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最终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找到马斯特思和费奇,告诉他们,他不跟他们一起去打德国人了。马斯特思告诫道:“你注定要遭受灭顶之灾”③〔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页,第44页,第60页。。这种来自周遭的道德谴责,正是斯隆看透战争本质之后所预料的:“一场战争不仅仅屠杀掉几千或者几万年轻人,它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残暴者了,动物,那些我们——你和我以及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污秽中培养出的动物。”人性的光环往往被这种道德暴力绑架所挤压。这是来自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权力含纳,稍有不慎,个体的自由意志、生命力即可走向衰败。斯通纳突然意识到,斯隆在美国参战的这一年骤然老了很多,已经了无生命力,斯通纳心想“他快要死了”,这种必然性正源于道德伦理环境的巨大变化。一定程度来讲,道德自我(motal self)是指自我意识的道德方面,或道德的自我意识。包括自我道德评价、自我道德形象、自尊心、自信心、理想自我和自我道德调节等。毫无疑问,斯通纳身上存在着堂吉诃德式的顽疾,他一直默默地对一切保持着疏离,疏离着荣誉的“正义”战争,疏离来自周遭的道德怨恨。很明显,他对自己的决定毫无内疚感,“没有任何特别的悔恨感”。差不多入伍一年后,马斯特思战死在蒂耶里堡。1918年那个夏天,他的大量心思都用在琢磨死亡上。“马斯特思的死对他的震撼比自己想象的要强烈得多”,但他又由于与文学的紧密关联而培养出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他不断地退回到经典之中,从文学语言的修辞和词汇中,从诗性语体的韵律和节奏中,一次又一次地惊异于罗马抒情诗人接受死亡时坦然、优雅的态度,好像他们面对的那个虚无不过是自己曾经享受过的绚丽岁月的一种应有属性;一次又一次地惊奇于拉丁传统的后期基督徒诗人看待死亡时表现出的痛苦、恐惧以及勉强掩饰的憎恶,好像死亡承诺会有一种华丽、愉悦的永恒人生,好像死亡和承诺不过是一种嘲弄,让他们活着的光阴腐烂变质。他的历史人格在此次道德自我建立的过程中得以升华,参与到剩余人生的自我塑造中去。
三、伦理自我:情欲人格的静默隐忍
斯通纳在复员老职工的招待会上,见到了后来的妻子伊迪丝,他被伊迪丝的美貌和气质所吸引。特别是那双最淡的蓝眼睛,“吸引着他,抓着他”,让他“似乎从自己的躯体脱身而出,进入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状态”④〔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3页,第44页,第60页。。随后的交往看似很自然,双方各自对对方有了更深的了解。直到上了带他们去圣路易斯度一个星期蜜月的火车时,斯通纳才意识到他有了一个妻子。
他们开始步入婚姻的纯真状态,不过是方式完全不同的纯真。两人都是处子,都意识到谁也没有经验,但是,一直在农场长大的斯通纳把生活的自然过程视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而这些过程对伊迪丝来说却完全神秘和出乎意料。她对这些一无所知,内心有种东西不希望知道这些。①〔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第80页。
所以,像许多其他人那样,他们的蜜月很失败,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这点,直到很久以后才认识到这种失败的滋味。不到一个月,斯通纳就知道自己的婚姻失败了。不到一年,他已经不抱改善的希望。
他学会了沉默,不再固执地去爱。如果他要跟伊迪丝说话,或者在温柔的冲动下想抚摸,她就躲开,沉溺在自己的内心里,变得沉默寡言,强忍着,然后会连续好几天强迫自己达到新的疲惫极限……有时,他的决心和学问在自己的爱面前粉碎了,就爬到她的身上。如果她从睡眠中被彻底弄醒了,就会很紧张,很僵硬,以某种熟悉的姿态朝两侧转着脑袋,把头埋进枕头里,强忍着侵犯。在这种时候,斯通纳就尽可能迅速地表演着自己的爱,痛恨自己的轻率,后悔自己的激情。②〔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第80页。
他们两人性事的失败成为婚姻失败的一个原因,由此成为一种象征。伊迪丝不愿意接受斯通纳的身体,换言之,她不愿意在他面前打开自己的身体,并拥抱一种无法忍受的差异。这种来自身体的诚实,是任何情感教育都无法阻止的。伊迪丝的身体告诉她,她根本不爱斯通纳,她之所以嫁给斯通纳只不过因为她像任何一个家教森严的小女孩那样渴望来自外部的爱,他恰好是第一个和她约会并向她求婚的男人。然而这种来自身体的提醒又是无法启齿的事情,这是她亲手铸就的婚姻,她不可能打碎它。③张定浩:《爱的秩序》(上),《书城》2016年第8期。先有生活,而后有伦理,面对情感与婚姻的两难,斯通纳将伦理和情欲幻化为一种能动性,以某种令系里新来的老师敬畏的强度和坚韧不拔的态度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工作,进而实现个体的“伦理自我”塑造。斯通纳身上堂吉诃德式的顽疾,使他一直默默地对一切保持着疏离,先前疏离着荣誉的“正义”战争,也同样疏离着生活的平庸本身。
结婚将近三年,伊迪丝提出想要个孩子。她并非性冷淡,逐渐释放出性的讯号,为了怀孕,两个月的疯狂交合的激情让斯通纳对伊迪丝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这种情欲就像饥饿感,如此强烈”。但他们两个的关系并没有改变,斯通纳很快意识到,把他们的肉体拉到一起的那股力量跟爱没有多大关系。激情过后,一旦确认怀孕,伊迪丝就再也无法忍受斯通纳的抚摸。
1923年3月,女儿格蕾斯出生了。斯通纳立刻喜欢上她,他那无法向伊迪丝流露的感情可以向女儿流露,“他从对孩子的关爱中找到了意想不到的乐趣”。对自己的女儿,斯通纳更像是一个母亲。出生的第一年,格蕾斯只认父亲的触摸,以及他的声音和疼爱。在格蕾斯六岁那年,斯通纳意识到两件事:“开始知道格蕾斯在他生活中具有多么核心的重要地位;开始明白自己是有可能成为一名好老师的”。之后,长期无爱的婚姻让伊迪丝对斯通纳暗生恨意,这恨意又因斯通纳跟女儿关系亲密的美好转变成一种嫉妒。于是,伊迪丝施展出各种聪明和技巧展开对格蕾斯爱的竞争,她开始介入到父女关系之中,有计划的拆散他们,以一个母亲的名义,以一个顾惜丈夫工作的妻子的名义,将格蕾斯一点点纳入自己的领地。斯通纳很快发现了伊迪丝的这种行为,“他的心头渐渐升起某种憎恶感”,但他不足以起身抵抗,相反,他眼睁睁地把女儿交给一个看似精神渐渐出现问题的不太正常的母亲管教,看着女儿一天天变得面目全非。而他却假装无事,极度坚毅隐忍,只想在阅读和写作中找到一个避难所。
除开与妻子伊迪丝、女儿格蕾斯的伦理困境,斯通纳还遭遇了一段短暂的婚外情。在研究文学中,斯通纳和凯瑟琳萌生了爱情。
斯通纳还非常年轻的时候,认为爱情就是一种绝对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一个人挺幸运的话,可能会找到入口的路径。成熟后,他又认为爱情是一种虚幻宗教的天堂,人们应该怀着有趣的怀疑态度凝视它,带着一种温柔、熟悉的轻蔑,一种难为情的怀旧感。如今,到了中年,他开始知道,爱情既不是一种优美状态,也非虚幻。他把爱情视为转化的人类行为,一种一个瞬间接着一个瞬间,一天接一天,被意志、才智和心灵发现、修改的状态。①〔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4页,第237页,第201页。
四十三岁那年,斯通纳学会了别人——比他年轻的人——在他之前早就学会的东西:你最初爱的那个人并不是你最终爱的那个人,爱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一个人想去了解另一个人。像所有的情人那样,他们谈了许多自己的事情,好像可以借此理解造就了他们的这个世界。凯瑟琳的适时出现,让处在弃女痛苦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斯通纳找到了情爱的自由。他们在一起过的生活,以前谁都没有真正想象过。他们从激情中萌发,再到情欲,再到深情,这种深情在时时刻刻不断自我翻新着。他们做爱、看书、研究,好像爱情和学问是一个过程:
“情欲和学问,”凯瑟琳曾经说,“真的全都有了,不是吗?”②〔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4页,第237页,第201页。
四、社会自我:底线人格的勇敢坚守
斯通纳试着拒绝了一场历史造成的战争,随后真真正正经历了两场战事:一者,来自家庭的伦理战事;再者就是来自学院的学术战事。在家庭伦理战事中,斯通纳以极度的坚毅隐忍,保护着那来之不易的婚姻和爱情,他淡漠疏离,步步退缩,完成了伦理自我、情欲人格的自我建构。而在学院这一场战事中,他变得异常勇敢,不屈不挠,获得最终胜利。
为了阻止一个浮夸懒惰、无知、不诚实、品行低劣的学生沃尔克获得学位,乃至进入学院体系,斯通纳不惜与即将成为顶头上司的系主任劳曼克思公开决裂,劳曼克斯想尽一切方法帮助他的学生通过答辩,但是斯通纳依旧无法对一名连最基本的文学常识都不知道的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至于被后来成为系主任的劳曼克斯折磨了半辈子,断送了职业晋升的道路,备受冷落与排挤。面对如此境遇,斯通纳依旧没有后悔当年的决定,并甘愿承受随后种种报复性的课程安排和升职无望。他对打算来劝解他的朋友费奇,提及已经死去的另一个朋友戴夫·马斯特思,并说了一番无比动容的话:
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对那些贫困、残缺的人来说,大学就像一座避难所,一个远离世界的庇护所,但他不是指沃尔克。戴夫会认为沃尔克就是——就是外面那个世界。我们不能让他进来。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变得像这个世界了,就像不真实的,就像……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阻止在外。③〔美〕约翰·威廉斯:《斯通纳》,杨向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4页,第237页,第201页。
我们或许会记起斯通纳的朋友戴夫·马斯特思对他的预言,一个来自中西部本土的没有桑乔做伴的堂吉诃德。他是疯狂和勇敢的,又是无比怯懦的;他太固执,又太软弱。有些瞬间我们会觉得无话可说,仿佛身陷其中。作为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自我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担任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知觉,包括对各种角色关系、角色地位、角色技能和角色体验的认知和评价。斯通纳所坚持的,维护大学的纯洁性,不为自己的职称利益而通融,是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曾经经历的焦虑。一个人的坚持唯一的结果,也许就是要直面自己的诘问与世界的沉默之间,那难以逃脱的绝望。更何况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没有同路人的,一个也没有。
余论:“保守”传统的英雄
在一次罕有的访谈中,作者约翰·威廉斯这样看待斯通纳:
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很多人读了小说之后认为斯通纳竟有如此悲哀与糟糕的一生。我认为他的一生极为美好。他的一生比别人都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且对所做的事情怀有感情,他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有其重要性。他是重要价值的见证人……对我来说,小说的重点在于斯通纳对工作的观念。教书对他来说是一个工作——这是就美好而且可敬的层面而言。他的工作赋予他特殊的身份认同,并成就了他……他对工作的爱才是重点所在。如果你爱一样东西,你会去了解它;如果你了解它,你会学得很多。缺乏爱就是坏老师的定义……你不会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想这总结了我在《斯通纳》中想要掌握的。你必须要保有信仰。重点是要让传统继续运作,因为传统就是文明。①〔美〕约翰·威廉斯:《史托纳》,马耀民译,台北:啟明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本书中译本的封面设计格外别致,从《解放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贝奥武甫》(Beowulf)《李尔王》(King Lear)《十四行诗》(Sonnets)《文艺复兴英语诗集》(English Renaissance Poetry)六本书中各取出一个字母,组成了主人公斯通纳的名字,Stoner——一位教授英语文学的大学教师。
Stoner,也许这名字本身就暗示着一种与石头有关的生存——西西弗斯式的英雄主义。他全身心地投入没有意义留存的事业之中,他搬动巨石,将它推上山顶,精疲力竭达成目标之后,看着石头滚动而下,再一次走下山重复这无限循环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一部悲剧,是因为设定了西西弗斯是痛苦的。然而这个神话故事的起因是西西弗斯藐视作为异己力量的神祇,并且绑架了死神,尽管他受到了在大地上永久重复无意义劳作的惩罚,他却确确实实地获得了永生,并且在每一次工作中都得以向众神报以轻蔑的微笑——那石头和大地都可以切实被自己的手所掌控。西西弗斯也许确实是幸福的,人一定要想象西西弗斯的快乐,因为向着高处挣扎本身就足以填满一个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