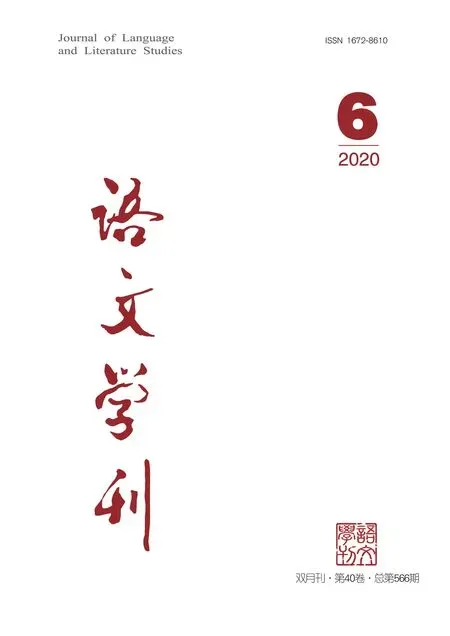从“悲恸”到“给予”:威廉·戈尔丁小说中“我”“你”关系的衍变
○ 肖霞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1983年,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1911-1993)获诺贝尔文学奖,简短的授奖辞中有这样的语句评断戈尔丁作品的价值:“阐明了当今世界中人的境况”[1]。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众多读者和学者的努力,戈尔丁小说中展现“人的境况”的笔触越来越清晰,许多朦胧晦涩的意象和题旨都得到很好阐释,但是这些阐释大多只关涉单部作品,像保罗·克罗福德(Paul Crawford)的《戈尔丁小说中的政治和历史》(PoliticsandHistoryinWilliamGolding, 2002)一样,能够把作者的长篇小说全部纳入视野,在罗列现象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廓清小说中呈现的 “人的境况”某种概貌的努力显然还不够。
戈尔丁的小说哲思深蕴,严肃的主题与互文戏拟等创作手法催发的玄妙意趣相映生辉,以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棱镜观照,可以折射出多种肉眼不及的“人的境况”。如果从伦理视角入手,以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论述的“我-你”关系为理论阐释框架,纲要性探讨戈尔丁十二部长篇小说中呈现的人物个体伦理形象,可以发现:从深陷“它”之世界,内心焦虑万端,向外冷漠戒备,疲于审视、占有、攫取、利用,徒劳寻求“我”的属人的本质,到辗转无助中试图超越到人世之外想象的乌托邦中锁定生活意义,在归于虚无的神性世界中获得安慰,再到最后淡定接受在与人交往的行为过程中创造自身价值,通过爱和奉献与他人互动定义自身,获得在“它”之世界中“你”之瞬时诗意,作者呈现的“人的境况”在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上总体完成了一个从二战之后的“悲恸”反思到体悟“给予”的个体社会感回归的过程。这种伦理关系视角下人物形象的衍变趋向呼应了人文学科其他领域时代反思的诸多成果,是小说创作与时代互动的有力例证。
一、“悲恸”:“我-它”关系中的个体伦理困境
在创作早期,戈尔丁常常发表一些自己生活中体验到的关于“人的境况”的断语,比如,经历过二战岁月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人类作恶犹如蜜蜂产蜜”[2]87。他也会对某部小说中“人的境况”做一个总结,比如:“《蝇王》的主题是悲恸,纯然的悲恸,悲恸,悲恸,悲恸。”[3]。虽然在妻子帮助下,戈尔丁写作《蝇王》(LordoftheFlies, 1954)的时候,已经勉力走出二战退伍返乡之后严重的情绪阴霾多年,重新适应了日常生活,但亲身参加海战,目睹炮弹呼啸、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还是给戈尔丁的价值观留下了巨大冲击。《蝇王》中描摹的人类世界确实前途暗淡,不但成年人以军舰、原子弹进行大规模杀戮,坠机后流落热带富庶海岛,温饱无忧的青少年也充分利用简陋的条件,以棍棒、木矛、林火进行小规模杀戮。所谓“文明”“民主”“科学”不过是用来维护强权或者本能恶的掩护色,甚至只是工具本身。传统价值语言逻辑的荒诞和欺骗性再也无法被遮蔽,个人只能孤独环视四周,找不到任何可以毫无戒心依赖的屏障。我与世界、与他人、甚至与自己都陷入了马丁·布伯所说的“我-它”关系之中。
在布伯最重要的著述《我与你》中,“我-它”人生与“我-你”人生的不同,栖居于“你”之世界与置身于“它”之世界的迥异,都得到了全面的论述。如果人与共同在者是“我-它”关系,主体“我”审视四周,看到的都是客体式的“它”,各守其位,各遵其轨,以因果律缔结时空关系网络。“我”按照自己的意图理解世界和他人,赋予世界与他人某种秩序,于是世界与他人对“我”来说,都只是一个工具化、秩序化、可解说的“它”,一切意义都由“我”单方来确定。每个“我”也便如此被反控于“它”的世界某种既定秩序之中,以物的形态与“它”物产生关系,成为殊性之表征,不会有人格塑形。
以此观照,戈尔丁前期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正是一些为“它”所苦,无法走出“我-它”关系的当代人。他们鲜有衣食住行的烦恼,也几乎不为个人得失忧患,读者看到的都是现实世界刺激下的一个又一个在客体“它”之世界中辗转冲撞,精神莫名悲恸甚至绝望,却看不到任何脱困途径的个体人物。不仅《蝇王》中的青少年致力于把世界转变成“我”的视野所期待的图景,利用各种手段把他人纳入“我”的生活设计,毫不迟疑地消灭逆“我”者,《继承者》(Inheritors,1955)中的“新人”也是以自己的想象来整饬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它”,使之符合自己的生存意义阐释框架。《品彻·马丁》(PincherMartin,1956)中的马丁更是把他人当作满足自己所有情绪或想法的棋子任意摆布,从设计伤人到强奸谋杀无所不为。《自由坠落》(FreeFall,1959)里的萨米意识中几乎从未真正想到过他人,只是依照生活为他设计的轨道滑行。贫民窟的卑贱生活,母亲去世,同学利用,抛弃辛苦追得的爱人比阿特丽丝,萨米都无所谓,与他人之间无关注、无沟通、无了解。《教堂尖塔》(TheSpire,1964)中教长乔西林一心一意想要在自己管理的教堂中添加一座四百英尺的高塔,为了造塔不但调动各种资源,还不惜践踏宗教社会伦理规范,不断牺牲他人也被他人抛弃,在困惑痛苦中死去。《金字塔》(ThePyramid,1967)是以事业有成的牛津毕业生奥利弗的视角回顾了故乡小镇的生活。那里的人们被限定在阶级和地位规定的行为模式中,毫无同情心地“互相暴露在对方视野中,互为猎食对象,全都衣冠楚楚却又在内里羞惭不堪”[4]。
令人深思的是,所有这些陷于“我-它”关系的人物生活都不幸福。不要说安排规划“它”之世界失败的时候,即使成功也没有快乐可言。“新人”杀灭了尼安德特人这样的山林恶魔,独木舟中驶向未来生活,并无幸福憧憬。马丁在孤礁求生之前几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支配了他人,但计谋得逞之后非但丝毫没有体验到满足快慰,反而痛苦不堪,不知道命运为何赋予他吃掉同类的嘴巴。萨米虽另结新欢,但抛弃旧情人始终心有不安,不知不觉要为自己辩护。乔西林为了建塔施予他人的不公日益沉重地压在心头,虽然他尝试道歉,但在“我-它”关系中,他不过也就是一个无法被理解的“它”,结果只是被数落了一顿,紧接着又被暴打。奥利弗目睹种种名利挣扎、算计之后看不到任何出路,只能为拥有高级轿车为标志的身份地位沾沾自喜,把小镇人们的痛苦抛诸脑后,丝毫不为自己曾利用艾薇的肉体满足性欲而心生歉意,也不会对老师彭斯的人生悲剧施以同情,竟然好像从此再也不会考虑脱离“它”之世界。布伯认为,“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5]6这些为了利益遗忘生活的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我”。
如果以时间计,上述长篇小说均发表在1954年至1967年之间。在这个时期,戈尔丁曾在自己的散文中用过去时写道:“我那时相信人是一种道德病态的造物”[2]87。他在小说中塑造的孤立个体形象在“我-它”关系中体验到的只有从主体“我”视角出发,在“它”之世界中“病态”生活的痛苦和困惑。浸淫在痛苦和困惑中,有些人物如《蝇王》中的拉尔夫刷新了对世界的认识,更多的则提出了问题: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这种个体“我”深陷于“它”之世界的伦理困境中阴郁冥思,无能窥见任何解决问题的门径。
经过十余年的沉寂,深思这种人的“悲恸”境况,沉淀体验,升华认识,戈尔丁慢慢找到了从人的困境中破茧的生活意义,所以自1979开始到1995年,后期的六部长篇小说,包括最后一部由他人整理出版的遗作,都为冲抵浓重黑暗提供了或浓或淡的亮色。
二、“给未知的神”:归于“你”的“我”
尽管处境恶劣、希望渺茫,即使在戈尔丁早期长篇小说里丝丝缕缕的亮光也没有彻底断绝。人物遭受现实挫败和精神磨难时,常常有颇具神性色彩的人物相伴,只是他们的双眼被蒙蔽,不但绝无可能接受神启,甚至还会偶然或蓄意杀掉这些人物。《蝇王》中的西蒙被陷于狂热杀戮仪式中的孩子们集体刺死,当时,他正要告诉同伴他们惧怕的根本不是什么恶魔,不过是一具飞行员的腐尸而已。《品彻·马丁》里的马丁借行船转弯的时机,意图把毫无防备的好人兼好友纳特甩入大海以终结心中对纳特包含着忌惮、嫉妒、怨恨等种种情绪的轮动。从这些代表“善”的人物的命运来看,在前期小说中,戈尔丁对善与救赎并无信心。在神性世界中寻求救赎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们超越现世苦难最常用的手段。“我们被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决定了自己”[6],戈尔丁也不例外。他很难在这种基督式救赎之外找到出路,又对救赎心怀希冀,于是,类似西蒙或纳特这样微弱而且无用的“善”的影子便成为这种渺茫希冀的写照。
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的变化,生活压力的减轻,戈尔丁多年的救赎思考显现出新的底色,模糊无力的“善”在后期长篇中变得实在丰满起来。《黑暗昭昭》(DarknessVisible,1979) 中的麦蒂一次又一次寻求与周围人交流、被周围人接纳的努力都被挫败,他苦苦思索,历尽磨难终于理顺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为救护一个男童而被烧死,重返天国福地。像《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一样,麦蒂成为一种苦苦求索得到生命意义的象征。这个人物在戈尔丁小说人物脱离个体孤独隔绝的伦理困境道路上迈出了转折性的一步:他不问任何个人得失,皈依于“相遇”的自由,以个体的活动、个体的精神在“你”之世界中承担对他人的责任,成就了自身生命的意义。
这种精神境地与马丁·布伯定义的“我-你”关系高度契合。“价值呈现于关系,呈现于‘我’与宇宙中其他在者的关系。”[5]9“我-你”关系是“我”对宇宙中其他在者价值的承认,是在关系中寻求价值,强调的是直接性、相互性、对话性和相遇性,强调“人通过‘你’而成为‘我’”[5]29。“我”“它”“你”之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关系的进程相应变动,只有在关系中“它”才可能成为“你”,反之亦然。要走出殊性之“我的”,走出秩序化、工具化的“它”之世界才可能成就人格直观的“自我”,进入“你”的神性世界,与世界中的其他在者沟通。
麦蒂虽能亲身体验与“你”沟通的安宁幸福,与内心神灵交流获益,也可以为他人献出生命,却始终无法与他人有效沟通,至死未能广布福音,甚至没能得到所爱的老师派迪格里自愿追随。如果说麦蒂只是精神上准备好与他人沟通,却无法与他人沟通,无法把“它”彻底转为“你”,与共同在者发生真实的互动,在相遇中把握虚无的需求,《过界仪式》(RiteofPassage,1980)中的塔尔博特已经能够践行“我-你”关系,理解他人,不但走进了牧师科利的内心,理解了他的柔弱善良和充沛情感,还可以体恤科利妹妹,愿意写信安抚她失去哥哥的苦痛。在《近甲板》(CloseQuarters,1987)、《甲板下的火》(FireDownBelow,1989)中,在远洋客船的小世界里,塔尔博特加深了与大副萨默斯的友谊,“心甘情愿用金甲换取铜甲”[7],也理解了普莱缇曼夫妇的对于乌托邦式美好社会的激情,对他们造福他人的崇高动机深感钦佩,不再像他人一样把他们当作威胁社会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尽管塔尔博特个人幸福的最大值体现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不包含任何门第、财产等世俗考量的纯粹爱情,但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塔尔博特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担当起自己对他人的责任。无论在假想敌船逼近的危难时刻还是在爱情降临的幸福时刻,他都没有违背本心追逐名利,而是与许多人建立起某种“同理心”,理解他人也被他人理解,所以能够在改良“人的境况”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但构建了自己的高贵人格,也能欣赏他人的高贵人格。戈尔丁一定也很喜欢这个人物,否则不会运用作者特权赋予他一个更广阔的造福他人的舞台,让他作为议员到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前期有“它”无“你”的个体伦理问题在戈尔丁的后期小说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解答,答案不在“我”之中,全在“你”,所以读者看到戈尔丁的后期小说中明显有了更多对主要人物之外的其他人物的描写,甚至在《过界仪式》中把一部分叙述由另一人物来承担,借此反衬主要叙述人塔尔博特记述的偏颇,这比前期小说,比如《继承者》中简短的视角转换带来的震撼对比更丰富,更有启发性,为理解他人而不是臆测他人提供了更实在的实践。即使这一阶段最让读者感到阴郁悲观的《纸人》(ThePaperMen,1984)中作家巴克雷也在小说结尾部分实质上开始了与假想敌塔克沟通的准备,接受了自己,也准备接受塔克迫近,奋笔书写着打算赠予塔克的个人自传材料。而《双舌》(TheDoubleTongue,1995)中的德尔菲神庙女祭司艾丽卡在领悟神意、关爱信众,周旋权贵之中,渐渐洞悉语言的神秘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奥赜,已经可以把“我”完全融入爱他人、爱神的生活中,所以她拒绝接受信众为纪念她的贡献树立一座石雕,只要求建造一座简朴的祭坛,并镌刻这样的文字:“献给未知的神”[8]。
三、双重世界:“你”之瞬时诗意
在戈尔丁后期出版的长篇小说中,主要人物都开始真正注意到他人,体谅他人,理解他人,如果不是一直如此,至少已经开始如此。但戈尔丁自称为评论家的“移动靶”,不会像固定靶一样等待被击中。他小说中的“人的境况”也从来不会被轻易辨识,而是立体多面,每一面都自有风景。上文曾提到,终生思考如何与他人相处,为他人牺牲的麦蒂彻悟“我-你”之妙之后也未能与身边人建立对话性、相互性的关系。从他引领老师派迪格里去天国时,把老师紧紧抱住用来吸引男孩子们靠近的彩球夺下丢弃这个动作就可以看出,麦蒂只是把自己看好的自由天国强加于自己热爱的老师,并未顾及派迪格里的个人需求。派迪格里这个人物形象全凭一己之力坚守着不那么美好的本性,自有一份人的尊严。他问心无愧,从未对喜欢的男孩子施予伤害,还勇敢地公开了自己喜爱俊美男童的癖好,始终不曾俯首作假取悦压迫他的社会伦理规范。但这样一个与自我达成了境遇中平衡的人,也没有公正、平等、开放地对待所有人。他喜欢的男孩会得到他的热忱爱心,丑陋的麦蒂只能得到疏远、嘲讽和厌恶。即使知道麦蒂对他感情深厚,并无过错,也不能喜欢麦蒂。按照这种情形看来,人们以“我-你”关系栖居于“你”之世界更多的只是一种希望,不是事实。戈尔丁小说中人与人关系的境况验证了人们进入“我-你”关系的难度,人物也由此变得更加复杂。相较于前期长篇中的人物,后期小说里的人物更为立体多面。“海洋三部曲”中的叙述人塔尔博特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
塔尔博特当然是一个正直、真诚、善良的年轻人,从他对查姆利小姐的爱情,对萨默斯大副的友情,对渎职副官不正当要求的拒绝,对迎敌任务毫无犹豫地担当,对重返已成为两个人自杀现场的舱房以维护他无神论者荣誉的坚决中,读者都可以看到一个没有被物化、工具化为“它”的人格化的“我”。塔尔博特的“我”对所爱的人不计得失,不计功利,但并不妨碍他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把其他人工具化。仅举“航海三部曲”最后一部《甲板下的火焰》近结尾处一例来说明。在航船到达殖民地之后,为了给无权无势、升职无望的好友萨默斯提供助力,塔尔博特狐假虎威,对副总督说他位高权重的教父大人将收到他称颂副总督的信,诱使对方为萨默斯书写并递送升职申请。为了自以为正当的目的玩弄物化他人的小手段在塔尔博特的行为中并不鲜见。即使明白无我的爱他人是一种美德,是令人幸福的人际关系,塔尔博特仍然穿梭在“它”之世界与“你”之世界之间。
塔尔博特对共同在者执双重态度,在关系中时而“你”、时而“它”,随时调档,并未拘泥于某种理想状态。他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我过去是,现在也是,诚挚地希望能运用权力增进我国福祉”[7]。而作为“增进我国福祉”的方式,也就是当上国会议员的手段却是依靠教父操作。这种灵活适用伦理原则的心态远离了康德的“绝对律令”,呼应着当今世界流行的伦理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也呼应着布伯所说的“它”“你”双重世界。在恒定不易、实惠有益的“它”之世界的漫长时空历史中,“‘你’之瞬时片刻乃是神妙离奇、缥缈虚无之诗意插曲”[5]34。好在塔尔博特付出真心对待爱情、友情,心甘情愿为增进国家福祉贡献力量的想法奉献所有,已经可以享受“‘你’之瞬时片刻”,并在与志同道合者、灵魂高尚者的相遇中“通过‘你’而成为‘我’”[5]29。
在“航海三部曲”中,塔尔博特真情洋溢,时常与船上偶然相遇的人们进入“我-你”关系的境界,这种“人的境况”在戈尔丁前期小说中杳无踪迹。对比《教堂尖塔》中乔西林的状况,差别显而易见。乔西林坚信上帝赋予自己建塔使命,排除万难一心一意建塔的行为表现似乎与布伯所说的宗教式“我-你”关系相近。但他不过是以上帝之名谋一己之利,企图借永恒存在成就自我价值,“口诵‘你’而心谓‘它’”[5]34罢了。乔西林借上帝使命之说横扫一切建塔障碍,把姨母、教堂杂工、杂工妻子、建筑师、建筑工人都当作了建塔资源,为了达到目的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上帝并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他增添荣耀,只是乔西林需要一座高耸的尖塔来填补自身卑微的深坑,所以,最终践踏他人也被他人践踏,狼狈败退,除了摇摇晃晃的尖塔失去了钟爱的一切,临终前他甚至不愿意再看那尖塔一眼。
正如布伯所言,人与人的关系会在“它”“你”的双重世界中进出,互为可用之物的“我-它”关系恒定不易,“我-你”关系虽摆脱了世俗功利,却不过是瞬间片刻。戈尔丁后期小说中的人物虽享有“你”之瞬间诗意,但并非完美践行了“我-你”关系的人,但因为这些人物能够体验“你”之世界的诗意,借他人的助力使殊性之“我的”步入人格之“我”,虽存身于“它”之世界却能偶尔脱离物的境地,拥有了不同于前期人物的独特人性色彩。
四、“给予”:时代反思的共鸣
戈尔丁自己表达“通过‘你’而成为‘我’”的主体间性观念时使用的词汇是“给予”。八十二岁的戈尔丁曾在诺贝尔奖宴会上向来宾简短致辞。他抓住这个能够吸引重要人物的机会,以人类一员的身份向所有手握权力的人们进言:“你们之间要达成一致不需要聪慧、雕饰和操控,需要的是常识,最重要的是,大胆勇敢的慷慨之举。给予,给予,给予!”[9]这个有关人与人关系的看法对于理解戈尔丁后期小说人物的伦理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对比作者前后期小说中的人物就可以发现,后期人物显然更注重他人,注重“给予”。
前期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唯我主义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社会感,不能准确定位自我,自然也不能理解生活之于我的意义。宗教的迷雾、自由的困惑,情欲的魔障、利益的诱惑都能遮蔽他们的自我,让这些自我中心主义者在痛苦中辗转找不到出路:《蝇王》中杰克等人展示的逆我者亡的强权暴力性残酷,《继承者》里“新人”推定尼安德特人为林中恶魔的偏见,《品彻·马丁》里马丁阴郁无情到不见理性的自利,《自由坠落》里萨米没有伦理边界的恣意生活,《教堂尖塔》中乔西林遮蔽在基督教价值观之下的对他人毫不犹豫地践踏,《金字塔》里奥利弗为了所谓身份地位的尊严对自己、对他人人性的贬低,所有这些都证明人物社会感的极度匮乏。处于“我-它”关系之中的人们不可能定义人格之“我”的价值,有的不过是工具性的物化价值而已。当麦蒂提出“我有什么用”[10]这样的问题之后,戈尔丁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便不再执迷于“我”的意识,不再痛苦沉溺于我是谁,我为什么这样,我是什么等等深奥难解的“我”之迷思,开始踏踏实实在他人的视域中体验我能做什么,并或多或少在实践中“给予”他人,奉献分享给他人自己的生命创造力,由此体验到不带任何功利色彩而被他人接受、追随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只要对戈尔丁的经历和他的小说稍有了解,读者便很容易意识到他的小说与时代思潮息息相关,不但反映了二战后普遍存在的对传统价值世界的质疑和困惑,也为解答质疑走出困惑提出了某种启示。实际上,戈尔丁小说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探索与人文学科其他领域的时代反思形成了呼应。上文中,我们已经发现马丁·布伯在代表作《我与你》中提出的“我-它”“我-你”关系对于理解戈尔丁小说中主要人物与他人关系的境况很有启发。布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本体的哲学论述为人们摆脱“我-它”关系各自为营的局面,构建“我-你”和谐的动态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
实际上,近现代以来,主体性哲学便开始走向主体间性探究,马丁·布伯在宗教哲学领域的创见反映的正是这个变化。列维纳斯所言的对他人的责任、萨特的为他的存在等都是在论述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语言哲学领域,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概念,描述语言之间随机多元的互动,实质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体,对即时即地语言意义发生的 “场”更为关注,表达的是对于相对关系和关系发生的场域而不是对本质本体的肯定。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性,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等也以关系作为立论的基础。在心理学领域,精神分析的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卡伦·霍尼(Karen Horney),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Alfred Adler)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了现代人种种以“我”为主体,以“我”之外的一切共同在者为客体,并以“我思”构建的世界为真而产生的种种“神经症”问题,切近时代的精神脉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阿德勒提出:“我们判断个人只能用社会感这个概念作为标准,据此衡量其思想和行动。”[11]人本主义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曾在《爱的艺术》(TheArtofLoving, 1956)中谈论给予:“最重要范畴还不是物质范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范畴”,人并不需要把生命奉献给他人,而是“应该把他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他应该同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12]。这个看法为戈尔丁在宴会致辞中所说的“给予”做出了解释,也为戈尔丁后期长篇小说中人物在“给予”关系中营建的温暖友谊和热烈爱情提供了支撑。戈尔丁在塔尔博特身上已经展示了“心甘情愿用金甲换取铜甲”式的给予,也在《双舌》中借女祭司艾丽卡传达了对在关系中表达自己、成就自己,也接受他人,成就他人的可能性。只有在爱中放下自己,给予他人正能量,才能超越 “它”之世界理性利益分析的羁绊,进入无物存在的“你”。从这个角度上看,戈尔丁的小说创作不过是时代思潮在文学领域中腾跃的浪花,是以小说形式表达的对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深刻思考。
五、结 语
“文学展现我们普通的生活,由此聚焦行为或选择引发后果、影响自身或他人的方式。就其根本而言,文学是对道德生活的一种探索。”[13]每一种对道德生活的探索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发生的,所以毫不奇怪,以人与人的关系为纲考察戈尔丁长篇小说中“人的境况”,尤其是人的精神境况,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人文思潮的反光。戈尔丁看重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力:“我敢说,没有什么艺术可以如此出入一个灵魂和肉体,活在另一个生命里”[14],而他的小说也确实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个灵魂在“它”或“你”之世界的生活状态,为人们通过出入另一个灵魂反思自己的生活境况提供了启示。